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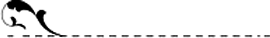

平静的海面闪闪发光,只是有点儿潮汐引起的微小的波动,勒阿弗尔全城居民都在防波堤上看着船只进港。
他们望着远处不可胜数的船只;有的是冒着黑烟的大轮船,有的是被一些几乎看不见的拖轮拖着的帆船,这些帆船的赤裸裸的桅杆,像剥去了树皮的树直插天空。
它们从四面八方的天际,向这吞噬它们的狭窄的堤口涌来;它们呻吟着,呼喊着,像喘气一样喷出一道道蒸汽。
两个年轻军官在这熙熙攘攘的防波堤上散步;他们向人致敬,还礼,有时候还停下来聊聊。
突然,他们中间的那个个子比较高大的保尔·当里塞尔,抓住他同伴让·勒诺尔迪的胳膊,随后轻轻地对他说:“注意,普安索太太来了,好好看看,我保证她会向你做媚眼。”
她挽着她丈夫、一个有钱的船主的胳膊走过来了。这是一个四十来岁可是还相当漂亮的女人,稍许胖了一点,不过就因为这种丰腴,使她看上去还像二十岁时一样鲜艳。因为她有高傲的举止,一双乌黑的眼睛,雍容华贵的气派,所以在她的朋友之中,大家都称她为“女神”。她一直是无可指摘的,私生活也无可疑之处。大家提到她时,都把她当作一个朴实厚道的女人的典范,庄重得没有一个男人敢对她有非分之想。
可是一个月以来,保尔·当里塞尔总是非常肯定地对自己的朋友勒诺尔迪说,普安索太太总是含情脉脉地注视他,而且一再说:“你放心,我是不会弄错的;我看得很清楚,她爱你,而且深深地爱你,就像一个从来没有爱过人的冰清玉洁的妇人一样。对正派女人来说,如果性欲旺盛的话,四十岁的年纪是个可怕的年纪。她们会失去理智,干出一些傻事来的。这个女人已经被击中了,我的好朋友,就像一只受伤的鸟,它正在掉下来,就要掉到你的怀里来了……喂,你瞧。”
这个高个子女人,跟着一个十二岁一个十五岁的两个女儿过来了,当她瞧见这位军官时,面色顿时变白了。她用热烈的眼光直勾勾地注视着他,仿佛对自己周围的一切,无论是她的孩子,她的丈夫和其他人,都看不见了。她向两位年轻军官还了礼,可是并没有低下她那火辣辣的目光,以致连勒诺尔迪中尉心里也产生了疑惑。
他的朋友喃喃地说:“这件事我早就料到了。这一次,你也看到了吧?妙啊,这块肉还肥着呢!”
可是勒诺尔迪根本不喜欢上流社会里那种偷香窃玉的勾当。他并不追求什么爱情,他最最渴望的是一种平静的生活,满足于年轻人经常会遇到的那些偶然交往。一个有教养的女人所必需的柔情蜜意,小心翼翼和脉脉温情,都使他感到厌烦。这类艳遇必然会带来束缚,无论多么轻微,也使他望而却步。他曾说过:“这种事我一个月就够了,可是出于礼貌,我不得不耐着性子拖上半年。”随后还有一件事情也是他大为恼火的,那就是被遗弃的女人在分手时的吵吵闹闹,指桑骂槐和纠缠不清。
因此他避免和普安索太太相遇。
可是有一天晚上,他在一个晚宴上发现她恰好是他的邻座;于是他不断地在皮肤上,眼睛里,甚至在灵魂深处,都感到他邻座的火热的眼光。他们的手相遇了,几乎是不由自主地相握了。一种关系就这样开始了。
他不由自主地又和她见面了。他感到自己被爱上了;他受到了因这个女人的强烈情欲而产生的带有虚荣色彩的同情心的感染,心软下来了。于是他听任她爱慕自己,只不过表示了点殷勤,希望他们的关系保持在感情方面。
可是有一天,她提出要和他约会,说是为了见见面,推心置腹地谈谈。她却晕倒在他的怀里,于是他不得已而成了她的情夫。
这样过了半年。她用一种疯狂的,气急败坏的爱情爱着他。她深深地陷在这种狂热的情欲里,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顾了。她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她的名誉,她的地位,她的幸福,她把所有这一切都扔进了她心中的这团烈火之中,就像人们在献祭时,把所有珍贵的东西都扔进火堆一样。
他呢,却早已觉得受够了,对他这个漂亮军官的信手拈来的胜利后悔不已;可是他已经有了束缚,有了牵制,成了俘虏。不论在什么时候,她都对他说:“我把一切都给你了,你还要什么呢?”他真想回答她说:“可是我什么也没有向你要过啊,我恳求你把你给我的东西拿回去。”她不顾会被人看见,搞得身败名裂,还是每天晚上到他家里来,而且这股热情还在与日俱增。她一下子扑进他的怀里,紧紧地搂住他,在一些使他深恶痛绝的狂热的接吻中兴奋得欲仙欲死。他用厌倦的声音说:“喂,理智一点。”她回答说:“我爱你。”然后她扑倒在他的膝前,用一种无比爱慕的姿态久久地端详他。在这种固定不变的注视之下,他终于被激怒了,想扶她起来:“喂,你坐起来吧,我们谈谈。”她喃喃地说:“不,就让我这样吧。”她还是这样心醉神迷地待着。
他对他的朋友当里塞尔说:“你知道,我会揍她的。我再也不愿意了,我再也不愿意了。这一切必须结束,而且要马上结束!”接着他又说:“你说我该怎么办呢。”那一位回答说:“断绝往来。”可是勒诺尔迪耸耸肩膀说:“你说得真轻松。一个女人对你关怀备至,体贴入微,满怀情意,她唯一关心的事是讨你喜欢,唯一的错误是不管你愿不愿意委身给了你;你以为和这样一个女人断绝关系是容易的事吗?”
可是有一天上午,有消息说那个团队就要换防了;勒诺尔迪高兴得跳起舞来。他得救了!可以不用吵闹,不用大吵大闹。得救了!得救了!……只要再熬上两个月就行了……得救了!
当天傍晚,她又来到他家里,比往常更加狂热。她已经知道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她连帽子也没除下,便抓起他的双手,紧紧地握着,眼睛盯着他的眼睛,用颤悠悠的声音坚定地对他说:“你要走了,这我知道。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真是吓得魂飞魄散,后来我想通了,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再犹豫了,我要把一个女人所能献出的最伟大的爱情的证明送给你:我跟你走。为了你,我要抛弃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完了,可是我是幸福的;这就像我再次委身于你。这是最后的,也是最大的牺牲;我永远属于你了!”
他觉得背上冒出一阵冷汗,一下子被一种无声而强烈的怒火,一种弱者的怒火控制住了。不过他还是使自己平静下来,用一种淡漠而温和的声调拒绝她的牺牲,极力想让她平静下来,和她讲清道理,要她明白这是不理智的行为!她听他说,一面用她那双黑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不屑地撇着嘴唇,什么也不回答。等他讲完以后,她只是对他说:“难道你是个懦夫?难道你是个朝三暮四勾引女人的老手?”
他的脸色发白,再次把道理讲给她听,他向她指出,这样一个行动必然会带来的永久的后果;他们的生活要被破坏,别人将不再和他们往来……而她总是固执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只要彼此相爱就行了!”
于是,他突然发火了,嚷道:“那好吧!我说不行,我不愿意。你听明白了没有?我不愿意,我不准你这样做。”随后,由于积怨日久,他把心里的话一下子全倒了出来:“唉,见鬼!你一厢情愿地爱我已经很久,就只差远走高飞了。谢谢,算了吧。”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可是她那铁青的脸上慢慢也产生了一种痛苦的抽搐,就像她所有的神经和肌肉都在扭曲。她没有向他告别就走了。
当天夜里她服了毒。有七八天时间大家都以为她死了。城里都在议论纷纷,为她抱怨,看在她强烈的情欲份上,反而宽恕了她的错误;因为种种剧烈的感情,由于它们的狂热而变得像是英雄行为,使本来应该受罚的人反而得到了原谅。一个自杀的女人就不能被看作是犯通奸罪的女人了。很快,那个不会再和她见面的勒诺尔迪中尉受到了舆论的一致斥责。
大家说他遗弃、背叛了她。上校动了恻隐之心,就此事向他的部下做了一点暗示。保尔·当里塞尔便去找他的朋友说:“唉,见鬼!我的好朋友,不能够让一个女人就这样死去。这件事干得不漂亮。”
另一个怒气冲天,不准他朋友再说下去,后者讲了一些污辱人格的话。他们决斗了。勒诺尔迪受了伤,大家都拍手称快;他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
她知道了这件事,以为他是为了她才决斗的,因此比以前更加爱他;可是她不能离开自己的卧室,所以一直到团队出发也没有见到他。
他到了里尔
 三个月以后,一天上午突然有个年轻女人来找他;她是他过去的情妇的妹妹。
三个月以后,一天上午突然有个年轻女人来找他;她是他过去的情妇的妹妹。
普安索太太在经受了长期的痛苦和她无法克服的绝望以后,现在已经奄奄一息。她肯定要死了。她想在最后闭上眼睛以前见上他一分钟,只要一分钟就行。
长时间的离别已经缓和了年轻人厌烦的情绪和恼怒的心情;他的心肠一软,哭了,去了勒阿弗尔。
她好像已经奄奄一息。别人让他和她单独待在一起;他在这个他在无意中置其于死地的垂危的女人的床前突然感到悲痛欲绝。他呜咽抽泣,用他从来未曾对她有过的柔情吻她。他结结巴巴地说:“不,不,你不会死的,你会痊愈的,我们将相亲相爱……我们将永远……相亲相爱……”
她喃喃地说:“是真的吗?你爱我吗?”而他呢,这时候心如刀割,赌咒发誓地答应要等到她痊愈,一面吻着这个心律紊乱的可怜的女人的骨瘦如柴的双手,久久地表示对她的怜悯。
第二天,他回到他的驻地。
六个星期以后,她又来和他团聚了,她一下子老了许多,让人都认不出她了,可是却比从前更加热恋他。
他昏头昏脑地又跟她恢复了关系。后来,因为他们堂而皇之地就像合法夫妻一样地生活,那位原来因为他抛弃了这个女人而有所不满的上校,这时又对这种非法的,不符合团内军官生活准则的生活方式表示愤慨。他把他的不满告知了他的部下,随后加以严惩;勒诺尔迪提出了辞呈。
他们随即来到地中海——古典式的情人之海——海边的一座别墅里住了下来。
三年又过去了。俯首听命的勒诺尔迪已经完全屈服,并习惯于这种不屈不挠的柔情了。她已经有了白头发。
他呢,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万事皆休的人,一个遭到了没顶之灾的人。任何希望,任何工作,任何欢快的事情,现在对他来说,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一天上午,有人给他送来一张名片:“约瑟·普安索,船主,勒阿弗尔。”丈夫来了!这个丈夫过去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因为他懂得对女人们坚定的意志是无法抗拒的。他现在来干什么?
他在花园里等着,因为他拒绝进入别墅。他彬彬有礼地鞠躬致敬,可是他不肯坐下,连花园小径上的长凳也不肯坐;他开始清晰而缓慢地说了起来:
“先生,我来这儿决不是为了责备您什么,过去的事情完全清楚。我经受了……我们经受了……一种命运的播弄,如果不是情况有所变化,我是决不会到您退隐的住所来打扰您的。我有两个女儿,先生,其中一个年长的,爱上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很爱她,可是那个男孩的家庭反对这门亲事,原因是我女儿的……母亲的地位。我并不因此而生气,也不怨恨,可是我非常爱我的女儿,先生,我来这儿向您要回我的……我的妻子;我希望她今天能同意回到我家里去……到她家里去。至于我,为了……为了我的女儿,我可以假装已经忘记。”
勒诺尔迪感到心头受到猛烈的一击,高兴得像发了疯一样,活像一个得到了赦免的罪犯。
他结巴着说:“好的……当然好,先生……我自己……请相信……这是公正的……非常公正的。”
他真想跟这个人握手,拥抱他,吻他的双颊。
他接着说:“那么请进来吧,在客厅里更好一些,我马上找她去。”
这一次,普安索先生不再拒绝了,并坐了下来。
勒诺尔迪跳跳蹦蹦地窜上了楼梯,随后在她情妇的房门口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神情严肃地走进去。“有人在下面找你,”他说,“为的是一件跟你女儿有关的事情。”她站起来说:“和我女儿有关?什么事?究竟什么事?她们没有死吧?”
他接着说:“没有,可是有一个严重情况,只有你才能解决。”她不愿再听下去,迅速地跑了下去。
这时候,勒诺尔迪很激动,瘫倒在一把椅子上,等待着。
他等了很久很久,随后听到有一些愤怒的声音穿过地板,传入他的耳朵。他决定下楼去。
普安索太太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正准备离开,她的丈夫则扯住她的连衣裙,连声说:“可是您要知道,您这样要毁掉我们的女儿,您的女儿,我们的孩子。”
她固执地回答:“我不会回到您家里去的。”勒诺尔迪全明白了,他有气无力地走过来,结结巴巴地说:“什么?她拒绝了吗?”她向他转过头来,出于某种廉耻的考虑,在她合法丈夫的面前,她不再用“你”称呼勒诺尔迪了
 ;她说:“您知道他对我提出了什么要求?他要我回到他家里去!”随后她冷冷一笑,带着一种对那个几乎跪在她面前的男子的无限轻蔑。
;她说:“您知道他对我提出了什么要求?他要我回到他家里去!”随后她冷冷一笑,带着一种对那个几乎跪在她面前的男子的无限轻蔑。
这时候,勒诺尔迪带着一种失望者孤注一掷的决心,想再作一次最后的尝试;他也劝说起来,为了她可怜的女儿,她的丈夫和她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在他中断议论,寻找新的论据时,一筹莫展的普安索先生,出于本能的老习惯的原因,倒用“你”来称呼她了,他喃喃地说:“算了吧,德尔菲娜,为你的女儿考虑考虑吧。”
接着她用高傲而轻蔑的目光看了他们两人一眼,随后冲到楼梯口,向他们喊道:“你们两个都是坏蛋!”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他们相互端详了一会儿,神情都是一样的沮丧和悲痛。普安索先生拾起他掉在他身边的帽子,用手掸了掸膝盖上从地板上蹭来的白灰,随后,在勒诺尔迪带他去门口时,他用一个失望的手势向他告辞,一面说道:“我们都是很不幸的,先生。”
随后他拖着沉重的步伐走了。
王振孙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