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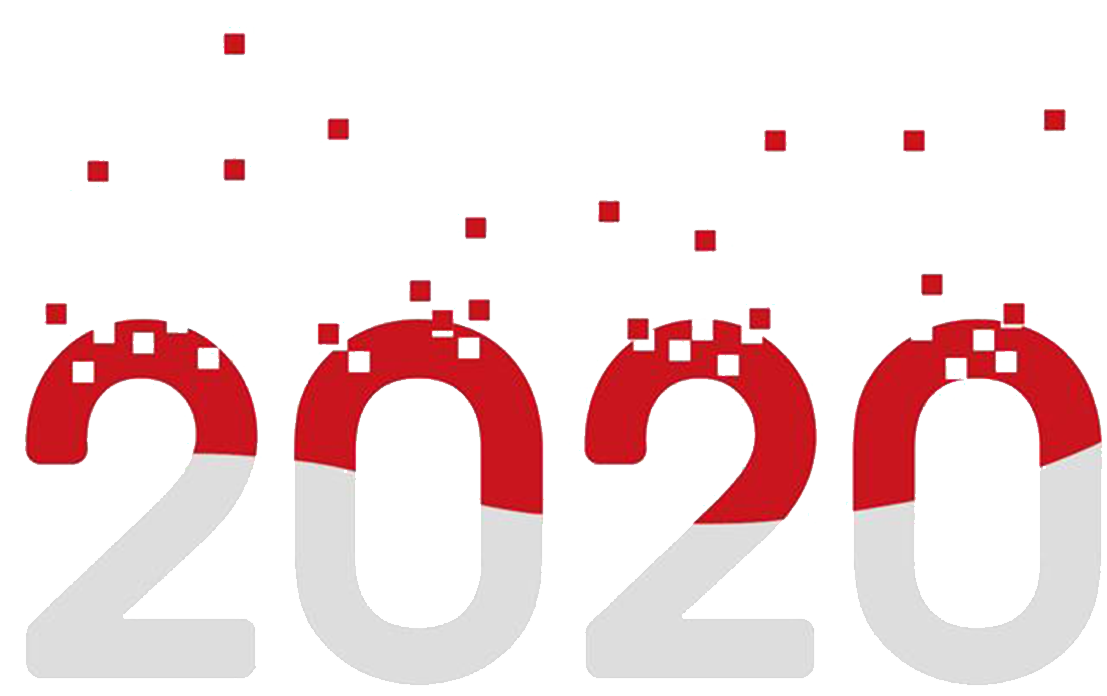
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这意味中美将发生全方位的摩擦。贸易冲突只是中美经济结构及总量规模逐渐换位的过程,这只能是一个“伟大的痛苦”,而不是觥筹交错、皆大欢喜的过程。中美之间的争端是超级大国之间命中注定的矛盾和摩擦,对此要做好攻守、文武的两手战略准备,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中美贸易战最直接、最浅显的原因是贸易不平衡。美国维持比较优势及中美经济结构互补的重要产物就是中美贸易逆差,过去一二十年,中国人力成本低、资源成本低、环境成本低,顺差一直保持上升趋势。2016年,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和日本的出口额分别为2659.6亿美元、2309.6亿美元、1157.8亿美元和632.6亿美元;自中国、墨西哥、加拿大和日本的进口额分别为4628.1亿美元、2941.5亿美元、2780.7亿美元和1322.0亿美元;美国的前四大逆差来源地依次是中国、日本、德国和墨西哥,逆差额分别为3470.4亿美元、689.4亿美元、648.7亿美元和631.9亿美元。而到了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303.7亿美元,自中国进口的总额为5056.0亿美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3752.3亿美元,同比增长8.1%。商人出身、特别看重利益的特朗普,怎么能够容忍贸易失衡状况越来越严重地持续下去?
中美贸易是结构性失衡,不是中国不想弥补贸易逆差,而是中国想要的高科技产品,美国根本不肯卖,更别提在服务贸易、金融贸易上,美国对中国是远远顺差的。对此美国心知肚明,只是拿贸易平衡当作针对中国的借口罢了。不管是对中兴、华为的刻意打压,还是在科技前沿领域对中国“封锁”,都已透露出美国对中国科技赶超和实力崛起的恐慌。毕竟中国GDP一年上一个新台阶:2016年74.36万亿元;2017年82.17万亿元;2018年突破90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已达13.6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美国在GDP上依然是老大,2018年GDP为20.5万亿美元,但美国的全球占比已从20世纪最高时的40%降至24%。相比30年前美国GDP是中国的17倍,1995年缩减到10倍,2005年不足6倍,到2012年,中国GDP占美国GDP的比例已超过50%,2018年追到了66%。照此速度,市场普遍预测到2028年中国GDP就将首次超过美国。而且从历史看,美国两次被对手(苏联和日本)赶超的焦虑都是以GDP的60%为临界,这让崛起的中国被顶在杠头上。即便美国内部急剧撕裂,可在对华态度上,竟连分歧的两党都形成统一战线,当下美国社会唯一高度统一的意见就是遏制中国。从贸易冲突到产业之争,从国家战略到经济模式之争,从超级大国到生存空间被挤压,中美本质上的六大冲突积累了这么多年,终究走到了中美经济由规模到质量全面换位的历史岔口。
既然中美势必狭路相逢,那么贸易冲突既是终极也是过程。因为中美之于世界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2018年中美GDP的增量合计达2.58万亿美元,约为全球增量的62%。一旦双方发生争端,不仅对全球局势不利,仅对中美来说,2018年两国货物贸易额和双向投资分别超过6300亿美元和2400亿美元,每天平均1.4万人往来中美之间,每17分钟起降一次航班,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所谓“合则两利,斗则俱伤”,20世纪末中美曾就中国加入WTO进行了长达13年的谈判,到如今中美建交40周年再度寻找共识,双方都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再加上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带着朋友共同发展,遏制中国等同于遏制各国发展的共同机遇,就连美国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自然难以快刀斩乱麻。从国家战略角度看,美国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这意味着中美将发生全方位的摩擦,贸易冲突只是中美经济结构及总量规模逐渐换位的过程,这只能是一个“伟大的痛苦”,而不是觥筹交错、皆大欢喜的过程。
进一步说,中美之间的争端是超级大国之间命中注定的矛盾和摩擦,不止于贸易,更不只有竞争,两国在太多领域有重合的利益和合作的需求。正因“相互需要”,中国还没实力与美国硬碰硬,而在目前政经格局下,美国也不会轻易动手。因而中美爆发全面战争的概率极小,大概率是以战略挤压的方式逐渐逼近,或在分歧长期存在的情况下相互牵制着寻找均衡。

贸易战越演越烈,注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大战。特朗普强硬地盯上了中国,实际上折射的是大国困境。美国靠工业生产立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为其提供了特殊机遇,制造业飞速发展。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之后,制造业的国际分工逐渐由之前的发达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原材料、初级产品,过渡到发达国家主要从事技术创新、设计和制造核心高端技术部件,而发展中国家则负责中低端部件的生产及最终制成品的组装。巨大的经济落差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原材料、社会资源存在巨大的成本差异。在利润的驱使下,美国的制造业企业纷纷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制造业空洞”,美国国内仅保留了一小部分极高端制造业和庞大的金融行业。“二战”后,美国第一、二、三产业占经济规模的比例分别从大约8%、47%、45%发展到2017年的1%、19%、80%,制造业严重萎缩。由于美国农业不但自给,而且出口居于世界前列,结合美国经济所处的阶段,可以认定美国的第一产业非常发达。这就使美国这个巨人的身材变得相当畸形——有着硕大无比的脑袋(高科技核心技术)、粗壮的下肢(农业)和太过瘦弱以至于无法支撑头部的躯干(制造业)。物质消费作为一切的基础决定了货物贸易仍然是当前世界贸易的主要构成部分,逆差的产生和持续扩大就不足为奇了。
产业结构改变还促使体系内的固有矛盾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作为“二战”的最后赢家,美国主导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确定了以黄金—美元本位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直接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又和美元挂钩。美元虽然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但是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美国国际收支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顺差国,这个悖论就是有名的“特里芬难题”。“二战”后至第三次工业革命结束,美国工业的市场扩张不自觉地起着缓解“特里芬难题”的作用。但是由于之后工业外流,顺差缩水,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汇率进入自由浮动时代,美元保持稳定和顺差的要求及机制限制(也就是特里芬难题的第二条)自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由于美元仍然是世界核心货币,也就是说特里芬难题的第一条仍然在起作用,于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如脱缰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
同时,美元体系和美国贸易逆差使大部分充斥全球的美元必须回流到美国的金融资产,这就令美国政府可以长期无所顾忌地发行国债和大搞赤字财政。美国企业和居民也可以轻易得到廉价贷款进行投资和消费,加速信贷消费型经济的形成。这令美国整体债务激增并达到占GDP 300%的比例。制造业空洞和大量的廉价美元,使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后进入房地产带动的过度金融化时代,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的产值占GDP比例高达33%,金融泡沫催生债务飙涨并反过来强化金融泡沫,最终引发次贷危机。制造业空洞、经济金融化、债务攀高等这些美国经济中结构性、常态性的问题,是各大公司“土豪”式逆回购推动的股市走牛等表面上、非常态的繁荣所无法掩盖的。并且,这些问题还挤压就业,导致中产阶级返贫,美国社会快速地由橄榄型变成哑铃型。1971~2015年,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比从62%减少到43%,社会明显分为富裕层和贫困层两极,占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和占总人口90%的普通家庭拥有的财富不相上下。民众的抱怨声越发高涨,特朗普这位带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的总统候选人适逢其时地出现了,民众和时代选择了特朗普上台。另外,次贷危机后,美国拼命量化宽松,过剩货币爆仓推动了第四次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全面引爆股市、债市危机。
由此可见,美国经济结构性颓势的原罪在其内部,但特朗普却赖上了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