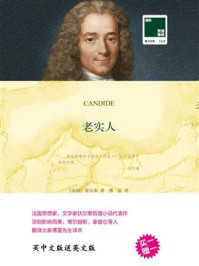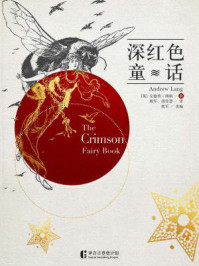堂·桑托斯·乌里盖先生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奉告,数日前有一位年轻人从美国来到布埃纳斯蒂埃拉斯,目前暂住舍间。我不想引起可能落空的希望,但是我认为这人可能是您失踪多年的儿子。
您最好亲自来看看他。如果他确实是您的儿子,据我看,他很想回家,可是到后不知将会得到怎样的接待,不敢贸然前去。
汤普森·撒克谨启。
半小时以后……这在布埃纳斯蒂埃拉斯还算是快的……乌里盖先生的古色古香的四轮马车,由一个赤脚的马夫鞭打着那几匹肥胖笨拙的马,来到了领事住处的门口。
一个白胡须的高个子下了车,然后搀扶着一个穿黑衣服,蒙黑面纱的太太下来。
两人急匆匆地走进来,撒克以最彬彬有礼的外交式的鞠躬迎接了他们。他桌旁站着一个瘦长的年轻人,眉清目秀,皮肤黑,乌黑的头发梳得光光的。
乌里盖夫人飞快地把厚面纱一揭。她已过中年,头发开始花白,但她那丰满漂亮的身段和浅橄榄色的皮肤还保存着巴斯克妇女所特有的美貌。
你一见到她的眼睛,发现它们的倩影和失望的表情中透露出的哀伤,你就知道这个女人只是依靠某种记忆才能生活。
她带着痛苦万分的询问神情,向那年轻人瞅了好久。她一双乌黑的大眼睛转到了他的左手。
接着,她噎了一下,声音虽然不大,但仿佛震动了整幢房屋。她嚷道:“我的儿子!”
紧接着便把小利亚诺搂在怀里。
过了一个月,小利亚诺接到撒克捎给他的信,来到领事馆。
他完全成了一位年轻的西班牙绅士,他的衣服都是进口货,珠宝商的狡黠并没有在他身上白费力气,他卷纸烟的时候,一枚大得异乎寻常的钻石戒指在他手上闪闪发光。
“怎么样啦?”撒克问道。
“没怎么样。”小利亚诺平静地说。“今天我第一次吃了软蝎肉排,就是那种大四脚蛇。你知道吗?我却认为咸肉煮豆子也配我的胃口。你喜欢吃蜥蜴吗,撒克?”
“不,别的爬虫也不吃。”撒克说。
现在是15时,再过几个小时,他就要达到那种飘飘然的境界了。
“你该履行诺言了,老弟,”他接着说,他那张猪肝色的脸上露出一副狰狞相。
“你对我太不公平。你已经当了4星期的宝贝儿子,你喜欢的话,每顿饭都可以用金盘子来盛小牛肉。喂,小利亚诺先生,你说应不应该让我老是过粗茶淡饭的日子?毛病在哪里?难道你这双孝顺儿子的眼睛在白屋里面没有见到任何像是现款的东西?别对我说你没有见到,谁都知道老乌里盖藏钱的地方,并且还是美国货币,别的钱他不要。你究竟怎么啦?这次别说‘没有’。”
“哎,当然,”小利亚诺欣赏着他的钻石戒指说,“那里的钱确实很多。至于证券之类的玩意儿我可不懂,但是我可以担保说,在我干爸爸叫做保险箱的铁皮盒子里,我一次就见到过50000元现款。有时候,他把保险箱的钥匙交给我,主要是让我知道他把我当做那个走失多年的真的小弗朗西斯科。”
“哎,那你还等什么呀?”撒克愤愤问道。“别忘了只要我高兴,我随时随地都可以揭你的老底。如果老乌里盖知道你是骗子,你知道会出什么事?”
“哦,得克萨斯的小利亚诺先生,你才不了解这个国家。这里的法律才叫辣呢!”
“他们会把你绷得像一只被踩扁的蛤蟆,在广场的每一个角上揍你50棍。棍子都要打断好几根。再把你身上剩下来的皮肉喂鳄鱼。”
“我现在不妨告诉你,伙计,”小利亚诺舒适地坐在帆布椅子里说,“事情就按照目前的样子维持下去,目前很不坏。”
“你这是什么意思?”撒克问道,把酒杯在桌子上碰得“咯咯”直响。
“计划吹啦!”小利亚诺说。“以后你同我说话,请称呼我堂·弗朗西斯科·乌里盖,我保证答应。我们不去碰乌里盖上校的钱,就你我两人来说,他的小铁皮保险箱同拉雷多第一国民银行的定时保险库一样安全可靠。”
“那你是想出卖我了,是吗?”领事说。
“当然。”小利亚诺快活地说。“出卖你,说得对。现在我把原因告诉你。我到上校家的第一晚,他们领我到一间卧室里。不是在地板上铺一张床垫……而是一间真正的卧室,有床有家具。我入睡前,我那位假母亲走了进来,替我掖好被子。”
“‘小宝贝,’她说,‘我的走失的小宝贝,天主把你送了回来,我永远赞美你。’她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废话,接着落了几点雨,滴在我的鼻子上。这情形我永远忘不了,撒克先生。”
“那以后一直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我说这番话,别以为我为自己的好处打算。我几乎没有跟女人多说过话,也没有母亲可谈,但是对于这位太太,我们却不得不继续瞒下去。她已经忍受了一次痛苦;第二次她可受不了。”
“我像是一条卑贱的野狼,送我走上这条路的可能不是上帝,而是魔鬼,但是我要走到头。喂,你以后提起我的名字时,别忘了我是堂·弗朗西斯科·乌里盖。”
“我今天就揭发你,你……你这个双料叛徒。”撒克结结巴巴地说。
小利亚诺站起来,并不粗暴地用他有力的手掐住撒克的脖子,慢慢地把他推到一个角落去。接着,他从左腋窝下抽出他的四五口径手枪,用冰冷的枪口戳着领事的嘴巴。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怎么会来到这里的。”他露出以前那种叫人心寒的微笑说:“如果我再离开这里,那将是由于你的缘故。千万别忘记,伙计。喂,我叫什么名字呀!”
“喂……堂·弗朗西斯科·乌里盖。”撒克喘着气说。
外面传来车轮声,人的“哈哈”声和木鞭鞭打肥马背上的响亮的“啪啪”声。
小利亚诺收起手枪,向门口走去。但他又扭过头,回到哆嗦着的撒克面前,向领事扬起了左手。
“这种情况为什么要维持下去,”他慢慢地说,“还有一个原因。我在拉雷多杀掉的那个人,左手背上也有一个同样的刺花。”
外面,堂·桑托斯·乌里盖的古色古香的四轮马车已经驶到门口。马车夫不再吆喝。
乌里盖太太穿着缀有许多花边和缎带的衣服走出来,一双柔和的大眼睛显露出幸福的神情,她向前探着身子。
“你是否在里面,我亲爱的儿子?”她用西班牙语喊道。
“妈妈,我回来啦!”年轻的堂·弗朗西斯科·乌里盖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