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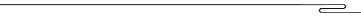
文|大萌倩

我,24岁,18岁高中毕业来到美国留学,患病的时候正是一名在读博士生。
从小身壮如牛,我生过最大的病是感冒发烧。饮食健康,定期运动,无不良嗜好,偶尔熬夜。无法理解乳腺癌这个词为何会与我有关系,可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事情往往都无法解释。
一切都发生得很突然。
我自检时摸到了右乳硬块,或是出于马虎,抑或是出于心存侥幸的讳疾忌医,我安慰自己也许是正常的生理周期导致的。可是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没有等来想要的结果。
在我男友的催促之下,我预约了医生。超声波、钼靶、活检,检查一项一项做下来,在每一次医生告诉我不能确诊需要进行更多检查的消息里,我隐隐感觉到了事态正在朝着坏的方向发展,而事情的恶化最终会在某一个临界点忽然如同雪崩般急速坍塌。
等待活检结果的那几天,空气里无处不是焦虑和不安。那种对未知审判的恐惧,将我残存的理性一点一点蚕食殆尽。白天无心工作,晚上夜不能寐。恐惧会见缝插针地在下一秒冒出来。
但是当最坏结果来临时,我却出乎意外地倍感轻松,如同你绞尽脑汁想要算计的对手,今天跟你打明牌了。当我看到病理报告是三阳的时候(ER+, PR+,HER2+++),我甚至觉得很幸运,上天让我抓了副烂牌,可这或许是烂牌里情况最好的那一种。
在美国生活的第6个年头,我第一次进医院。
作为留学生,学校担心你无力承担高昂的医疗费,会有强制性的健康险。在得病之前,我对美国医疗的了解仅仅停留于同学和网络上的奇闻轶事,比如去急诊室输液,第二天收到天价账单。为避免这类情况地发生,我逐字逐句地研究起了健康保险的条款。
学校为我购买的医疗保险是属于PPO类型,这类保险可以去任何医院和诊所治疗。具体是哪间医院或者哪位医生,取决于是否与所属保险公司有合约,可以划归为“网络内”或者“网络外”。如果选择网络内的机构,报销的比例高、自付比例低。不仅如此,医疗保险有一个最强大的条款,便是每年有一个maximum-out-of-pocket(最高自付额度),每年在患者自付了一定的额度之后,剩下的医疗费用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
用我自己举例,如果我在加州大学系统的任何一家医院治疗,每年最多支付2000美元;其他医院,350美元封顶。这个费用,就算是对于一个念博士的学生来说,也就是两个月的工资而已。打消了经济上的顾虑,我便着手开始了我的治疗之路。
首先,如何选择医院和医生。
刚开始,我或许同许多国内的患者一样,大病一定是往大医院跑,医生一定要找业内首屈一指的专家。我所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当地排名第一)为我推荐了一位刚刚新招来的年轻女肿瘤医生艾琳(Erin)。艾琳对待患者非常热情、细致。我的第一次问诊,足足谈了两小时,从疾病本身、治疗方案、临床试验可能性到心理建设,包括伴侣关系、人际圈对我的支持,等等。
不同于我对一般癌症治疗的认知,她给出了先化疗、再手术的方案,这样的化疗称为新辅助治疗(neoadjuvant therapy)。可是正因为她的年轻,我当时对此方案保持怀疑态度,便陆续问诊了加州其他5位业内专家,寻求secondopinion(第二方案)。5位专家都给出了相同的新辅助治疗方案:化疗和靶向治疗联合用药(cocktail)TCHP(Taxotere、Carboplatin、Herceptin、Perjeta,即多西他赛、卡铂、赫赛汀、帕捷特);接着手术(全术切或者保乳术);术后使用赫赛汀一年。并且我有幸见到了最先提出这cocktail疗法的医生之一,她称这个治疗方案是No-brainer,俗称“无脑上”。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医生一致要求我务必在开始真正治疗之前做两件事情:
第一,基因检测咨询,特别是BRCA1、BRCA2,这对后续治疗方案有指导性意义。
对于第一条,国内大部分患者,甚至医生都认为没有必要。在美国,这却是一项乳腺癌患者(或者有家族史的非患者)必经的测试。其必要性在于:
第二,看生育科医生,做必要生育风险告知,以及相关fertility preservation(保留生育能力)的措施(如冻卵)。
我成为癌症患者之前,也是癌症患者家属,但我可以说对第二条闻所未闻。
许多化疗药物会有生育毒性(gonadal toxicity),随着癌症发病的日趋年轻化,以及各种癌症预后的改善,这一条对于患者以后长期生存的生活质量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美国,有专门为癌症患者提供服务的癌症生育咨询科(oncofertility),相信在国内对于癌症患者生育咨询也会逐渐完善。但现在而言,辅助生育措施(例如冻卵),在国内仍是一个模糊地带:按照卫生部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医疗机构不允许给单身女性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生育科咨询的情况总结如下:
在这些初次问诊的经历里,我学到了很多。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每一个医疗决策后面的“有据可依”:大到化疗用药,小到是否打升白针,医生都给我提供了相关的论文资料,对于论文的缺点都进行了讨论。
这种深度的参与感,让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一个不幸地被动接受治疗的患者,也让我有了强烈的掌控自己健康的信心。
在此基础之上,我逐渐开始感受到了美国医疗资源的丰富、平均、精确和一致性。医院的条件、医生的技术不再是我最优先考虑的因素,决定我选择的因素是交通的便利与医生团队的投入程度。我最终选择了学校的附属医院,选择了那位年轻的女医生,后来事实证明,我做了最好的选择。
每个女人从新生儿期卵巢内约有200万个未发育的原始卵泡。经历儿童期直至青春期,卵泡数量进一步减少到30万~50万个。各种激素水平作用下,从青春期开始,绝大多数卵泡在发育的各个阶段退化闭锁,每个月有15~20个卵泡继续发育成长,使卵巢内同时存在多个处在不同发育时期的卵泡,但是通常只有一个发育成优势卵泡,并排出其中的卵细胞,即卵子。当育龄女性因为恶性肿瘤接受化疗时,某些类别的药物会对卵泡造成影响。其结果就是导致身体里的卵泡被提前用光,这样闭经年龄就提前了,甚至直接导致绝经。
那冻卵又是什么原理呢?
上面提到的,对一个女性而言,每个月通常有15~20个卵泡发育成长,不过最终只有其中一个卵泡能排出卵子。促排卵就是利用这十几个本不能排卵的卵泡,让它们在人工注射的激素刺激下,发育成熟,孕育卵子。网上有很多信息,诸如“本来一个月只排一个卵,你现在排10个,提前透支了卵巢,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加快衰老”,都是没有根据的无稽之谈。
一言以蔽之,促排卵并非“揠苗助长”,而是“废物转化”。当卵泡在药物的作用下发育好了,医生会择日安排取卵手术。这个手术加上麻醉、准备大概用时1个小时。医生会用一根直径不到2毫米的穿刺针通过阴道穿刺到卵巢内取出成熟的卵子。取出的卵子可以被冷冻保存起来,这些卵子也可以先进行人工受精,形成受精卵,分化到一定的程度再冷冻。有需要的时候,解冻卵子(受精卵),移植进母体。
这种生育保留措施可以让很多年轻女性从容面对癌症治疗所带来的生育风险。不仅如此,对于基因突变(如BRCA1/2)携带者,可以经过活检方法,筛选没有遗传突变的受精卵,进一步控制癌症遗传风险。
整个冻卵的过程,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排卵针是每天自己在小腹进行皮下注射,一连打1~2周,期间2~3天复查一次,监测卵泡发育以及血液中不同激素含量。待到时机成熟,一次全麻手术“卸货”。我的医生成功取出了13颗卵子,其中8颗成功受精并且分化。在正式开始癌症治疗之前,我骄傲地成为了8个正在孕育着的小生命的“妈妈”了。
取卵手术的第三天,医生马不停蹄地安排了第一次化疗。
化疗之前,我在脑海里无数次想象过化疗之后情景:
终日卧床,无法自理,痛不欲生,不成人形……
我是个务实的人,根据医生给我的建议,我非常仔细地安排着“化疗之后事”:我买了冰棒(减少口腔金属味)、漱口水(预防口腔感染)、灭菌喷雾、止泻药、抗过敏药、止疼药;给我的猫洗了澡,把手机设上紧急呼叫联系人。全副武装迎接这场战斗。
然而情况并没有想象那么糟。整个化疗做下来,除了头发掉光以外,我没有太大的化疗副作用。甚至到后来,我很期待每一次治疗。一方面,我能摸到我的肿瘤在变小,证明癌细胞在凋亡;另一方面,我清楚,看那一袋袋价格远超黄金的液体输入自己的身体,不知为何,我有种自己身价也在暴涨的感觉;最后,化疗时有各种饮料、小零食,有时候还有狗志愿者每个隔间地去提供“特殊服务”,对我来说有无比的心理疗愈功能。
此外,化疗期间,我干过很多“不像化疗患者的事”。我去夏威夷火山公园徒步16公里看火山入海,在零下10℃的太平洋高地等了3个小时日出,且坚持每星期去游泳池游泳3000米,几次开两小时的车去吃正宗的麻辣川菜。除了头发掉光了之外,我感觉自己仍然是个正常人。这一点给了我极大的心理暗示和信心,正是因为没有了身体上的不适,我也不太把自己当患者看,这种正面的反馈机制让我内心安定、充满力量。
虽然化疗的不良反应程度因人而异,我的医生团队在这方面也做了非常细致入微的方案和安排。在每一次化疗结束后24小时都进行了升白针(neulasta)的注射,以维持免疫功能;每次化疗之前会使用止吐药、抗过敏药以及地塞米松。而对于饮食,除了生食不建议吃之外,其他百无禁忌。我的主治医生一再向我强调要stay active(保持运动),无论是遛弯也好,剧烈运动也好,只要能让自己动起来,便是好的。
我很顺利地度过了4个月的化疗、手术以及后来的放疗。在最后一次放疗的那一天,护士们为我准备了一次特殊的毕业典礼。在美国,每一位结束癌症治疗的患者,都会进行一个敲钟仪式(ring the bell),标志着癌症治疗的结束和新生活的开始。
我含着热泪敲响了钟,等候区的患者、前台的护工,还有医生、护士都向我鼓掌祝福。我从我的护士手里接过毕业证书,并且跟她拥抱。
为了不让家里担心,我向父母隐瞒了我的病情。没有了家人的支持,独居异乡,在这可谓是没有家人的半年里,我的医生、护士、志愿者如同我的亲人一般。他们经常会打电话询问我身体状况,问我男朋友什么时候来看我,问我父母在国内好不好,问我爸爸的身体怎么样。虽然我从家到医院走路只需要5分钟,每次化疗结束,志愿者都想要开车送我回家,甚至想要帮我买菜做饭。
我现在仍然分不清楚这是他们专业素养的一部分,还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患者的同情和关怀。后来,我从一位哈佛医学院的朋友那里得知,他们医学院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建立和维持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与患者相处的每一个细节都大有学问。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患者坐着说话,那么医生就不能站着,这样会有居高临下等级感。医生必须也坐下,或者蹲下,保持与患者的眼睛在同一高度,这样能让患者感到舒适自在,有利于医疗过程的开展。
2017年7月,在我刚刚结束所有治疗之后,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通过了一种针对HER2扩增的口服化疗新药Nerlynx(neratinib,那来替尼)用于预防乳腺癌的复发。临床试验显示,对于我这种二十几岁的高危人群,Neratinib可以降低将近30%的5年复发率,然而最主要的副作用就是腹泻
 。
。
2018年2月,在我完成最后一次赫赛汀治疗之后,我开始了一年的Nerlynx疗程,因为药物太新了,而此药又需要在赫赛汀治疗结束一年之内开始,所以我是整个校医院第12位使用此药的患者。相比于国内许多具有先进医疗资源的大城市,在美国治疗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新药能迅速临床运用。前一个月还是论文里的药物,下一个月可能就在患者手里了。
新药的出现,使得我的治疗仍在继续。回望癌症治疗的这一年,如同一场真真切切的梦,更像是一场无疾而终的无妄之灾。近几年来癌症新药的井喷,免疫治疗、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更让我对未来怀着无尽的期望。
就如同当年敲响的钟上刻着的铭文:
My treatment is done.
This course is run.
And now I’m on my w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