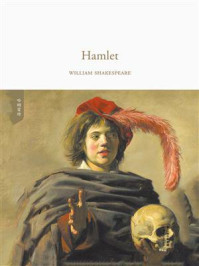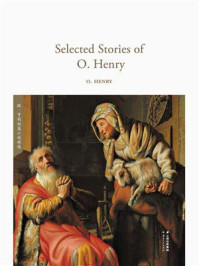黑暗中响起电话铃声。铃响到第三声,床垫弹簧吱吱嘎嘎,手指在木台面上摸索,坚硬的小物件砸在铺地毯的地上,弹簧继续吱吱嘎嘎,然后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你好……对,是我……死了?……好的……十五分钟。谢谢。”
开关咔嗒一声,天花板中央三根镏金铁链挂着的白色碗灯用光线充满了房间。斯佩德光着脚,穿绿白格的睡衣,坐在床沿上。他怒视床头柜上的电话,双手拿起电话旁的一包棕色卷烟纸和一袋达勒姆公牛烟草。潮湿的冷风吹进两扇洞开的窗户,带来了恶魔岛上每分钟六次的沉闷雾号声。杜克的《美国刑事名案》面朝下扣在桌上,铁皮闹钟不牢靠地压着书的一角,指针指着两点过五分。
斯佩德粗壮的手指小心翼翼地卷着烟,他把适量的棕色烟丝撒在卷曲的纸上,平铺烟丝,两头一样平,中间微微凹陷。他用两个大拇指将纸的内侧边缘向下卷,压在被食指按住的外侧边缘上,大拇指和食指移到纸筒的两头抓住,舌头舔过封口,左手食指和大拇指捏紧左侧尽头,右手食指和大拇指抚平潮湿的接缝,然后用右手食指和大拇指拧一下右侧尽头,把另一头塞进嘴里。
他捡起掉在地上的猪皮套镍壳打火机,按一下点火,嘴角叼着点燃的烟卷站起身。他脱掉睡衣。他的手臂、双腿和躯干光滑而健壮,加上下垂的塌肩膀,使得他的身体就像一头熊,一头剃了毛的熊:他的胸口没有毛发,他的皮肤像孩童一样柔软和粉嫩。
他挠了挠后脖颈,开始穿衣服。他穿上白色薄连体内衣、灰色袜子、黑色吊袜带和深棕色皮鞋。系好鞋带,他拿起电话,拨通灰石街4500号,要了一辆出租车。他穿上绿条纹白衬衫,戴上柔软的白色假领,打好绿色领带,穿上他那天穿的灰色正装和宽松的粗花呢外套,戴上深灰色帽子。他把烟草、钥匙和钱塞进衣袋,临街大门的门铃响了。
布什街从斯托克顿街上方越过,然后下坡通向中国城,来到这儿,斯佩德付钱下车。旧金山的夜雾稀薄而湿冷,无孔不入,街道变得影影绰绰。斯佩德下车之处的几码外有一小群人,他们站在一条巷口向内张望。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站在布什街的另一侧,也盯着那条小巷。周围住户的窗口同样有人向外看。
铁栏杆夹着的下街通道口底下是光秃秃的丑陋台阶,斯佩德从两个通道口之间穿过人行道来到挡墙前,双手按着湿漉漉的墙顶,俯视脚下的斯托克顿街。一辆汽车像是被炸出来似的射出隧道,轰轰地呼啸着开远了。隧道口不远有个男人蹲在一块广告牌前,广告牌上贴着一部电影和一种汽油的广告,广告牌背后是两幢商用建筑物之间的墙缝。为了从广告牌底下张望,蹲着的男人都快把脑袋贴在人行道上了。他一只手按着路面,另一只手抓着广告牌的绿色框架,摆出一个稀奇古怪的姿势。另外两个男人难看地一起挤在广告牌的一头,从广告牌和建筑物之间的几英寸缝隙中向内窥视。另一头的建筑物有一面空白的灰色侧墙,俯瞰广告牌背后的空地。侧墙上灯光闪烁,人影在光线中摇曳。
斯佩德从挡墙前转身,顺着布什街向北走,来到人们聚集的小巷口。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在嚼口香糖,他头顶上是一块深蓝色的搪瓷标牌,上面用白字写着“布里特街”。警察伸出胳膊,问:“你干什么?”
“我是萨姆·斯佩德。汤姆·波尔豪斯打电话叫我来的。”
“哦,是你,”警察放下胳膊,“刚开始没认出你。去吧,他们在后面。”他朝背后一甩大拇指,“情况很糟糕。”
“太糟了。”斯佩德附和道,走进小巷。走到一半,离巷口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深色的救护车。救护车背后靠左的地方,小巷被齐腰高的栏杆截断。所谓栏杆,其实只是几根横着钉住的粗糙木板。栏杆背后是深色土地形成的陡坡,一直通到斯托克顿街的那块广告牌。栏杆最顶上是一根十英尺长的木板,一头从立柱上被扯了下来,另一头挂在栏杆上。陡坡向下十五英尺处伸出了一块平坦的岩石。迈尔斯·阿切仰面躺在岩石和陡坡之间的夹角里。两个男人站在他身旁,其中一个用手电筒照着死者,另一个用手电筒顺着陡坡上上下下扫动。
其中一个招呼斯佩德:“你好,萨姆。”然后爬回小巷里,影子拖在背后的陡坡上。他个子很高,啤酒肚,长着精明的小眼睛和厚嘴唇,黑黢黢的面颊上胡子刮得很潦草。他的鞋子、膝盖、双手和下巴上星星点点都是棕色土渣。“我觉得你大概想在我们运走他之前看看他。”他说着跨过损坏的栏杆。
“谢了,汤姆,”斯佩德说,“发生什么了?”他用胳膊肘撑着栏杆柱,望向底下的人,有人朝他点头,他也点头回礼。
汤姆·波尔豪斯用脏兮兮的手指戳着自己的左胸口说:“正中心脏——用的是这个。”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把粗重的左轮,递给斯佩德。手枪表面的凹陷处嵌着烂泥。“一把韦伯利。英国货,对吧?”
斯佩德从栏杆柱上抬起胳膊肘,俯身低头端详武器,但没有伸手触碰。“对,”他说,“韦伯利-福斯伯里自动左轮。没错。点三八口径,八颗子弹。已经停产了。开了几枪?”
“就一枪。”汤姆又戳了戳心口,“他撞破栏杆的时候肯定已经死了。”他抬起沾泥的左轮,“见过吗?”
斯佩德点点头。“韦伯利-福斯伯里我见得多了,”他说得了无兴趣,然后立刻问道,“他在这儿中枪的,对吧?就站在你现在的位置,背靠栏杆。开枪的人站在这儿。”他在汤姆前方转身,把一只手举到齐胸高,食指平伸,“给他一枪,迈尔斯向后倒,撞开最顶上的栏杆,穿过去往下滚,直到被石块挡住。是这样吧?”
“是这样,”汤姆慢吞吞地答道,眉毛皱成一团,“枪口的火焰烧焦了他的外套。”
“谁发现他的?”
“巡逻的弟兄,西林。他从布什街向南走,刚走到这儿,一辆车拐弯,车头灯照到这儿,他见到栏杆顶上开了。于是他过来看看情况,就发现了他。”
“拐弯的那辆车呢?”
“啥也不知道,萨姆。西林根本没留神,当时还不知道出事了。他说他从鲍威尔街过来的路上,没人从这儿出去,否则他肯定会看见的。另外只有一条路,是从斯托克顿街那块广告牌底下钻出去。没人走那条路。雾弄得地面湿漉漉的,地上只有迈尔斯滑下去和枪滚落的痕迹。”
“没人听见枪声吗?”
“老天在上,萨姆,我们也刚赶到。肯定有人听见,我们会找到的。”他转身,抬起一条腿跨过栏杆,“下去看看他?否则我们就运走了。”
斯佩德说:“不了。”
汤姆停下来,骑在栏杆上,扭头用惊诧的小眼睛望着斯佩德。
斯佩德说:“你看过他了。我能看见的你都看见了。”
汤姆依然望着斯佩德,模棱两可地点点头,收回跨过栏杆的那条腿。“他的枪插在腰上,”他说,“没开过火。他的大衣系着纽扣。衣服口袋里有一百六十几块钱。萨姆,他在工作对吧?”
斯佩德犹豫片刻,点点头。
汤姆问:“所以?”
“他应该在跟踪一个叫弗洛伊德·瑟斯比的男人。”斯佩德说,复述了温德利小姐描述瑟斯比的那番话。
“原因?”
斯佩德把双手插进大衣口袋,对汤姆眨了眨睡意蒙眬的眼睛。汤姆不耐烦地重复:“原因?”
“一个英国人,有可能。不知道具体混哪一行。我们想弄清楚他住在哪儿。”斯佩德黯然一笑,从口袋里抽出一只手,拍拍汤姆的肩膀,“别逼我了。”他把手塞回口袋里。“我去通知迈尔斯的老婆。”他转过身。
汤姆瞪着他,张开嘴又合上,什么都说不出来,他清清喉咙,卸下脸上的怒容,用沙哑但柔和的声音说:“他就这么没了,够惨的。迈尔斯有他的缺点,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但要我说,他肯定也有他的好处。”
“我也这么觉得。”斯佩德赞同道,声调里完全没有任何感情,他走出小巷。
斯佩德到布什街和泰勒街路口的通宵药店借用电话。
他摇了个号码,等了一会儿,然后对着听筒说:“宝贝儿,迈尔斯中枪了。对,他死了……听我说,你别激动……对……你得去告诉爱娃……不,我他妈才不去呢。只能交给你了……真是好姑娘……还有,别让她来办公室……告诉她,我会去找她的——唉——回头吧……对,但别替我做什么承诺……就这样。你真是个天使。再见。”
斯佩德再次打开吊碗灯,铁皮闹钟说现在三点四十。他把帽子和大衣扔在床上,走进厨房,带着一个红酒杯和一瓶百加得朗姆酒回到卧室里。他站在那儿倒了一杯喝掉。他把酒瓶和酒杯放在桌上,面对着它们坐在床沿上,开始卷香烟。酒过三巡,他正在点第五支香烟,这时临街大门的门铃响了。闹钟指着四点半。斯佩德叹口气,从床上起来,走向卫生间门口的内线电话。他按下开临街大门门锁的按钮,嘟囔道:“麻烦的娘们儿。”站在那儿瞪着黑色的电话盒子,呼吸不太规则,面颊潮红。
走廊里传来电梯门打开又关上的咔啦咔啦声。斯佩德又叹了口气,走向通往走廊的公寓门。外面铺着地毯的楼板上响起柔和但沉重的脚步声——两个男人的脚步声。斯佩德脸色一亮,眼神不再充满厌烦。他飞快地打开门。“你好,汤姆,”他对先前在布里特街交谈过的高个子啤酒肚警探说,然后对汤姆身旁的男人说,“你好,警督。请进。”
两人一起点点头,谁也没说话,走进房间。斯佩德关上门,带他们来到卧室。汤姆坐进窗口沙发的一头。警督坐进桌子旁的一把椅子里。警督是个结实的小个子,脑袋浑圆,剪短的斑白头发和剪短的斑白胡须底下是一张四方脸。他戴着五块钱的金领带夹,领口有个秘密社团的精致镶钻徽章。
斯佩德从厨房拿来两个酒杯,连他的酒杯一同斟满百加得,递给两位访客一人一杯,然后拿着他那杯坐在床沿上。他表情平静,看不见一丝好奇。他举杯道:“祝破案顺利。”然后一饮而尽。
汤姆喝完他那杯酒,把酒杯放在脚边的地上,用沾着黄泥的食指擦擦嘴。他盯着床脚,像是在回忆能让他隐约想起点什么的事情。警督盯着酒杯看了十几秒,抿了一小口,把酒杯放在胳膊肘旁的桌上。他不慌不忙地用冷酷的视线扫视房间,然后望向汤姆。汤姆不安地在沙发上动了动,没有抬起头,问:“萨姆,你通知迈尔斯的妻子了吗?”
斯佩德说:“嗯哼。”
“她情绪怎么样?”
斯佩德摇摇头:“我对女人一窍不通。”
汤姆柔和地说:“一窍不通个屁。”
警督用双手按住膝盖,向前俯身。他的绿眼睛盯着斯佩德,视线格外严苛,就仿佛他的眼睛靠机器对焦,不拉操纵杆或按电钮就不会移开。“你带的是什么枪?”他问。
“不带。我不怎么喜欢枪。不过办公室里当然备着呢。”
“我想看看其中一把,”警督说,“你这儿不会凑巧有一把吧?”
“没有。”
“确定?”
“自己看呗。”斯佩德微笑,挥了挥他的空酒杯,“愿意的话,尽管翻个底朝天。我一声都不会吭,只要你拿得出搜查令。”
汤姆劝慰道:“哎,够了,萨姆!”
斯佩德把酒杯放在桌上,站起来面对警督:“邓迪,你要干什么?”声音和眼神一样无情和冷酷。
邓迪警督移动视线,焦点始终落在斯佩德脸上。他只动了动眼珠。汤姆再次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从鼻孔长出一口气,哀怨地低吼道:“萨姆,我们不想找麻烦。”
斯佩德没理会汤姆,他对邓迪说:“好了,你要干什么?有话直说。你他妈以为你老几,跑到我家里来唬我?”
“行了,”邓迪从胸膛深处发出声音,“坐下,听我说。”
“我他妈爱站就站,爱坐就坐。”斯佩德说着,纹丝不动。
“老天在上,讲点道理吧,”汤姆恳求道,“咱们吵架有什么意思?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有话直说?都是因为我问你这个瑟斯比是谁,你的回答等于在说关我屁事。萨姆,你不能这么对待我们。这么做不对,对你也没好处。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要完成。”
邓迪警督一跃而起,贴着斯佩德,把他的四方脸捅到高个子的面前。“我警告过你,你迟早要失手的。”他说。
斯佩德蔑视地撇撇嘴,挑起眉毛:“是人就有失手的时候。”他友善地揶揄道。
“这次轮到你了。”
斯佩德微笑摇头:“不,我会留神的,多谢提醒。”他不再微笑。他上嘴唇的左边翻上去,露出犬齿。他眯起眼睛,视线变得暴虐。他的嗓音变得和警督的一样低沉。“我不喜欢这样。你们转来转去想找什么?告诉我,否则就滚出去,让我睡觉。”
“瑟斯比是谁?”邓迪逼问。
“我知道的全告诉汤姆了。”
“你他妈只告诉了他一点点。”
“我他妈只知道一点点。”
“你们为什么跟踪他?”
“我没有。是迈尔斯——原因很简单,我们有个客户,付了一笔硬邦邦的美国钞票,请我们跟踪他。”
“客户是谁?”
斯佩德的表情恢复冷静。他斥责道:“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的,必须等我和客户商量过才行。”
“要么你告诉我,要么就上法庭去说。”邓迪怒道,“这是杀人案,你别忘记了。”
“也许吧。但也请你别忘记另一点,亲爱的。我告不告诉你全他妈凭我高兴。上次警察不喜欢我我就号啕大哭已经是很久以前了。”
汤姆从沙发上起身,在床脚坐下。他刮得很潦草的脸上沾着黄泥,表情疲惫,皱纹明显。“你讲讲道理,萨姆,”他恳求道,“给我们一个机会。你不把你掌握的情况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破迈尔斯的案子?”
“不需要劳烦你们头疼,”斯佩德对他说,“我的人我自己埋。”
邓迪警督重新坐下,双手回到膝头。他的眼睛是两个炽热的绿色圆盘。“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他说,笑得狰狞而满足,“所以我们才来找你。汤姆,对不对?”
汤姆哀叹,但没说什么能听清的话。斯佩德警惕地看着邓迪。
“我就是这么对汤姆说的,”警督继续道,“我说:‘汤姆,我有个直觉,萨姆·斯佩德属于家里事家里了的那种人。’我就是这么对他说的。”
警惕离开了斯佩德的双眼。他的厌倦让眼神变得黯淡。他扭头看着汤姆,用特别无所谓的语气说:“你男朋友这又是哪儿痒痒了?”
邓迪跳起来,弯曲两根手指,敲敲斯佩德的胸口。“很简单,”他说,特地把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并且用指节敲斯佩德来表示强调,“你离开布里特街后仅仅三十五分钟,瑟斯比在他住的旅馆门口被枪杀。”
斯佩德开口了,同样特地咬准每个字的读音:“把你的爪子拿开点。”
邓迪收回他敲斯佩德胸口的手指,音调没有任何变化:“汤姆说你走得很急,甚至没留下看一眼你的搭档。”
汤姆抱歉地低声说:“呃,真该死,萨姆,但你就是那么跑掉的。”
“你也没去阿切家通知他妻子,”警督说,“我们打电话过去,你办公室的那姑娘在,她说是你派她去的。”
斯佩德点点头。他面容沉静,表情迟钝。
邓迪警督抬起两个弯曲的指节对着斯佩德的胸口,但立刻又放下手,他说:“你找到电话,打电话给那姑娘,算你十分钟。去瑟斯比的旅馆,也算你十分钟,就在吉里街快到利文沃斯街路口的地方,十分钟肯定能到,顶多十五分钟。因此你有十到十五分钟可以埋伏在那儿等他现身。”
“我知道他住在哪儿?”斯佩德问,“也知道他杀死迈尔斯后没有直接回家?”
“你只知道你知道的,”邓迪固执地答道,“你几点到家的?”
“四点差二十。我走了走,想事情。”
警督上下摆动圆滚滚的脑袋。“我们知道你三点半没到家。我们试过打电话找你。你去哪儿走了走?”
“布什街上走了一段,然后回来。”
“有没有见到任何人能——”
“没,没有目击证人,”斯佩德说,愉快地呵呵一笑,“请坐,邓迪。你还没喝完你的酒呢。汤姆,拿起你的杯子。”
汤姆说:“不了,萨姆,谢谢。”邓迪坐下,但一眼也没看他的朗姆酒。
斯佩德给自己斟酒,喝完,把空杯子放回桌上,回到床边坐下。“现在我知道我的处境了,”他说,友善地轮流端详两位警探,“很抱歉,我刚才奓毛了,但你们两只鸟儿飞进来,想方设法让我紧张。迈尔斯被干掉我已经很心烦了,然后你们两只鸟儿又兜着圈子说话。不过现在没事了,因为我知道你们要干什么了。”
汤姆说:“算了吧。”警督没有说话。
斯佩德问:“瑟斯比死了?”
警督还在犹豫,汤姆说:“对。”
这时警督气呼呼地说:“你说不定已经知道了,要是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他没来得及对任何人说任何话就死了。”
斯佩德正在卷香烟。他连头也没抬,问:“这话什么意思?你认为我知道什么?”
“我的意思全在话里了。”邓迪粗鲁地答道。
斯佩德抬头看着他,微笑,一只手拿着卷好的香烟,另一只手拿着打火机。“你还没准备好逮捕我,对吧,邓迪?”他问。邓迪用冷酷的绿眼睛盯着斯佩德,没有回答。
“那么,”斯佩德说,“我也就没有特别的理由要在乎你他妈怎么想了,对吧,邓迪?”
汤姆说:“哎呀,萨姆,讲点道理。”
斯佩德把香烟放进嘴里,点燃,笑着喷出烟雾。“我会讲道理的,汤姆,”他保证道,“这个瑟斯比我是怎么杀的?我已经忘了。”
汤姆厌恶地哼了一声。邓迪警督说:“有人在他背后开了四枪,点四四或点四五口径,从马路对面,当时他正要进旅馆。没人看见,不过现场看起来是这样。”
“他肩膀的枪套里有一把鲁格手枪,”汤姆又说,“没开过火。”
“旅馆里的人对他有什么了解?”斯佩德问。
“没什么,除了他已经住了一个星期。”
“一个人?”
“一个人。”
“你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什么?他房间里呢?”
邓迪抿起嘴唇,问:“你认为我们会发现什么?”
斯佩德用手卷的香烟随随便便画个圈。“能告诉你们他是谁、他有什么故事的东西。发现什么了吗?”
“我们等着听你说呢。”
斯佩德用黄灰色的眼睛望着警督,眼神坦白得出奇。“我从没见过瑟斯比,无论死活。”
邓迪警督起身,表情不怎么满意。汤姆站起来,打哈欠伸懒腰。“我们要问的东西问完了。”邓迪说,他皱起眉头,眼神比两块绿色石头还硬。他留着小胡子的上嘴唇紧贴牙齿,用下嘴唇吐出来几个字。“我们告诉你的比你告诉我们的多。对你够意思了。你了解我,斯佩德。无论是不是你干的,我都会秉公处理,也会尽量给你机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看你特别不顺眼,但该抓你的时候我肯定不会手软。”
“够意思,”斯佩德淡然道,“不过要是你愿意喝完那杯酒,我会觉得更高兴的。”
邓迪警督转向桌子,拿起酒杯,慢条斯理地喝完。他说:“晚安。”伸出手,两人仪式性地握手。汤姆和斯佩德也仪式性地握手。斯佩德送汤姆出去,然后脱衣服,关灯,上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