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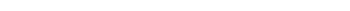

二月二十二日这天我们接到通知,说是要返回哥伦比亚。我们已经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市待了八个月,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在这里修理它的电子系统和武器系统。在舰船维修期间,全体水兵会接受特殊训练。而不用上课的日子里,我们会干一些所有水兵在岸上时都会干的事情:约女朋友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到港口一家名叫乔艾·帕洛卡的酒馆,大家聚在一起痛饮威士忌,也时不时起起哄打打架。
我女朋友叫玛丽·埃德瑞斯,是我到莫比尔两个月后通过另一个水兵的女友认识的。尽管她学起西班牙语来一点儿都不费劲,我还是觉得她从来都没有弄明白为什么我的朋友们都把她叫成玛利亚·迪莱克西奥
 。一到假日我就会请她去看电影,可她好像更愿意让我请她去吃冰激凌。我们就这样用我的半吊子英语和她的半吊子西班牙语交流,反正不管是在电影院还是去吃冰激凌,我们总能互相听懂。
。一到假日我就会请她去看电影,可她好像更愿意让我请她去吃冰激凌。我们就这样用我的半吊子英语和她的半吊子西班牙语交流,反正不管是在电影院还是去吃冰激凌,我们总能互相听懂。
只有一次我不是和玛丽一起去看的电影:因为那天晚上我和伙伴们去看了《凯恩号哗变记》。我们中有些人听说,这是一部讲述扫雷艇上生活的片子,很不错。我们就都去看了。可那部电影里最精彩的并不是扫雷艇什么的,而是那场暴风雨。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在那样一场暴风雨里,最恰当的做法就是转变船只的航向,就像那些哗变者所做的那样。可是,不管是我还是那些伙伴们,谁都没有遇过那么大的暴风雨,因此,整场电影看下来,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数那场暴风雨了。我们回去睡觉时,水兵迭戈·韦拉斯克思还深深沉浸在那部电影之中,想想几天之后我们就要去海上航行,他对我们说道:“要是我们碰上那样一场暴风雨会怎么样?”
我承认我也被那部电影震撼。八个月来我几乎已经忘记了海上那套生活习惯。我倒不是害怕,因为指导员早就教过我们落水时应该如何自救。可在看完《凯恩号哗变记》的那天晚上,我还是感到心中那阵不安并不寻常。
我并不是说从那一刻起我就对灾难有了什么预感。可是,我从未像这次这样在临近出航的日子里感到如此害怕。小时候在波哥大,我常看连环画,可从来也没有想过会有人淹死在海里。相反,每次想到大海,我总是信心满满。加入海军快两年了,每一次出海航行,我也从未有过任何不安。
不过承认这个也没什么丢脸的,在看完《凯恩号哗变记》后,我心里总有种近乎恐惧的感觉。我仰面朝天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我睡的是上铺—想念自己的家人,也想着我们回卡塔赫纳的航程,久久不能入睡。我用双手支着头,耳边回响着海水轻轻拍打码头的声音,以及睡在同一间舱房里四十名水兵宁静的呼吸声。在我下铺睡的是一等兵路易斯·任希弗,他的呼噜声大得像吹长号。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美梦,可倘若他知道八天以后自己将葬身海底,一定不会睡得这么香。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被这种不安所笼罩。起锚的日子飞快地临近,我一直试图通过和伙伴们聊天来放宽心情。卡尔达斯号驱逐舰已经整装待发。这些天里,我们都情不自禁地谈论各自的家庭,谈论哥伦比亚,也谈及各自回去之后的打算。一点一点地,舰船上装满了我们要捎回家的礼物:大都是些收音机呀电冰箱呀洗衣机呀电炉什么的。我只带了一台收音机。
出发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完全无法排解那种揪心的感觉,于是我做出一个决定:一回到卡塔赫纳,我就脱离海军。我可不想再经受这种航行的风险。出发前一天晚上,我去同玛丽告别,原本是想把自己的担忧和决定一并告诉她的,但后来没那么做,因为我曾向她保证过一定会回来,如果我跟她说以后我不再航行了,她就不会再相信我了。我只向我最要好的朋友、二等兵拉蒙·埃雷拉透露了这个决定,他也对我坦言,说等回到卡塔赫纳他也要脱离海军。拉蒙·埃雷拉和我忧心忡忡,我们约上水兵迭戈·韦拉斯克思一起去乔艾·帕洛卡酒馆喝杯告别威士忌。
本来我们只想喝上一杯,结果一下子喝了五瓶。几乎每晚都和我们厮混在一起的女友也对我们的行程了若指掌,她们决定为我们饯行,要喝个一醉方休,还要痛哭一场以表情义。乐队指挥是个神情严肃的男人,戴了副眼镜,这让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个音乐家,他把一组曼波还有探戈曲献给我们,他一定是把这些都当作哥伦比亚乐曲了。我们的女友全都哭了起来,喝了不少一块半美金一瓶的威士忌。
因为最后这个星期发了三回钱,我们决定好好挥霍一番。我是心里有事,想一醉解千愁。拉蒙·埃雷拉则是开心,他一向都开开心心的,他是阿尔霍纳人,打得一手好鼓,还特别擅长模仿各路时髦歌手的演唱。
正当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一个美国水兵走到我们桌前,请求拉蒙·埃雷拉允许他邀请拉蒙的女友跳一支舞,那女伴身材高大,一头金发,是那天晚上喝得最少却哭得最凶的一位—而且哭得真心实意。那美国佬说的是英语,拉蒙·埃雷拉推搡了他一把,用西班牙语回答:“你说的我他娘一个字儿也听不懂!”
那算得上是莫比尔市最热闹的一次打斗了,椅子在脑袋上砸得散了架,还惊动了巡逻的警车,来了不少警察。那个美国佬头上吃了拉蒙·埃雷拉重重的两拳。等拉蒙·埃雷拉模仿丹尼尔·桑托斯唱着歌回到军舰上时,已经是凌晨一点了。他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登上这艘军舰。实际上,这的确是最后一次。
二月二十四日凌晨三点,卡尔达斯号从莫比尔港起航开往卡塔赫纳。一想到要回家,大家都开心不已。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些礼品给家人。最开心的要数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我觉得米格尔·奥尔特加是最仔细和节俭的水兵。在莫比尔的八个月里,他没浪费过一美元。发下来的每一分钱他都用来给在卡塔赫纳等他的老婆买礼物了。军舰起航的这天凌晨,米格尔·奥尔特加在舰桥上待着,还在讲他老婆孩子的事,这倒不算什么稀罕事,因为他只要一开口就不会说别的。他往回带了一台冰箱、一台全自动洗衣机、一台收音机,外加一个电炉。十二个小时后,米格尔·奥尔特加军士长将会躺在铺位上,晕得天旋地转。而七十二小时之后,他将葬身海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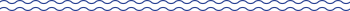
舰船起航的时候,通常会下达这样一道命令:“全体人员各就各位。”这时每个人必须待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舰船驶出港口。我静静地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对着鱼雷发射架,眼见莫比尔的灯火消失在雾霭中,可此刻我脑海里想的并不是玛丽。我想的是大海。我知道第二天我们将驶入墨西哥湾,在一年的这个月份里,这条航线不算太平。天亮后我一直没有看见海梅·马丁内斯·迪亚戈中尉,他是舰上的二副,是这次海难中唯一殒命的高级军官。他高大魁梧,寡言少语,我总共也没见过他几次。我只知道他来自托里玛,是个大好人。
不过这天凌晨我见到了一级士官胡里奥·阿玛多尔·卡拉巴约,他是我们的第二水手长,高高的个子,总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他从我身旁走过,看了一眼莫比尔逐渐淡去的灯火,便向他自己的岗位走去。我觉得这是我在舰上最后一次看见他。
整个卡尔达斯号上,要说起回家的快乐,谁也比不上士官艾里亚斯·萨博加尔,他是轮机长。他简直就是头海豹,身材矮小,皮肤黝黑,身体很壮实,特别能侃。他四十来岁,我猜这四十年他多半时间都在侃大山。
萨博加尔士官有理由比别人更高兴些。在卡塔赫纳等候他归来的有他老婆和六个儿女。六个儿女中他只见过五个:最小的那个是我们在莫比尔的时候出生的。
直到天亮之前,这趟航行还算是风平浪静。不到一个小时我就重新适应了航行生活。莫比尔的灯火消失在远方,消失在宁静清晨的薄雾中,东方已经能看到缓缓升起的太阳。这会儿我的不安情绪没有了,只觉得很疲惫。我一整夜都没睡觉,嘴里渴得慌,翻上来的全是威士忌的苦味。
早晨六点,我们驶出了港口。这时又有命令下来:“撤岗,值勤人员各就各位。”声音未落,我便向卧室舱房走去。我的下铺,路易斯·任希弗已经坐起身来,正揉着眼睛,还没完全清醒。
“我们到哪儿了?”路易斯·任希弗问我。
我告诉他说,我们刚出港。说完我就爬上我的床铺,想好好睡上一觉。
路易斯·任希弗是个十全十美的水兵。他出生在远离大海的乔科,可他血液里流淌着航海之魂。当卡尔达斯号前往莫比尔大修时,路易斯·任希弗还不是这艘舰船的成员。当时他正在华盛顿学习枪炮制造。他严谨好学,英语讲得和西班牙语一样顺溜。
三月十五日,他在华盛顿拿到了土木工程的学位。一九五二年,他在那里和一位多米尼加姑娘喜结良缘。卡尔达斯号大修的时候,路易斯·任希弗从华盛顿赶过来,成了舰上的一员。离开莫比尔前不久,他对我说,一到哥伦比亚,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安排,把他的妻子迁到卡塔赫纳来。
路易斯·任希弗已经有好长时间没航行了,我敢肯定他会晕船。就在这次航行的第一天凌晨,穿衣服的时候他问我:
“你还没有晕船吗?”
我跟他说没有。然后任希弗说了句:
“再过两三个小时,我就会看见你连舌头都要吐出来。”
“我看你才会这样。”我回敬了他一句。他又说道:
“想看我晕船,那得整个大海都晕了才行。”
我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竭力想睡一会儿,可这时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那场暴风雨。头一天晚上那种恐惧的感觉又从我心底升起。我又变得忧心忡忡。我转过身,冲着刚刚穿好衣服的路易斯·任希弗说:
“还是小心点儿。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