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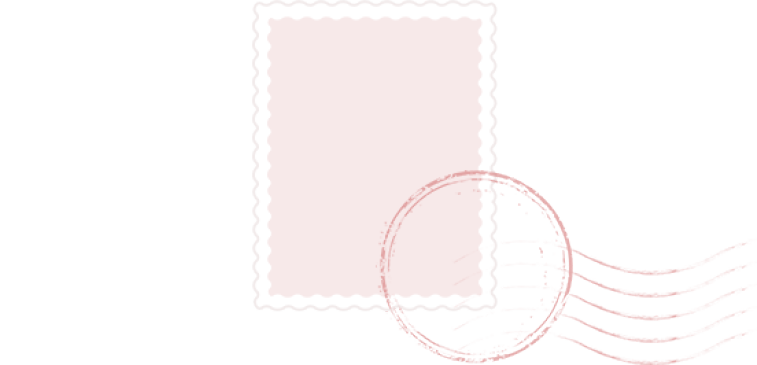
“悦颜。”
她想不起来陈思恒是在哪一天从哪一声称呼开始,不再叫她高小姐,自然而然的转变,仿佛认识很多年的朋友。
不过她还是改不了口,第一声总是叫他陈先生。
他来是跟她询问一个人,一个让悦颜觉得意外的名字。
“你认识何仁杰吗?”
悦颜点头:“认识,他是我爸爸的助理。”
“他现在还跟有你联系吗?”
“没了,自从爸爸出事后,我就没有见过他。”
“你知道他人现在会在哪儿吗?”
悦颜想了想:“不知道。”
陈思恒说:“我查了他的户籍资料,目前他人不在杭州,名下房产通通变卖,大概是回老家了。”
悦颜一愣:“回老家,他回老家干什么?”
陈思恒沉吟:“不知道,总觉得这个人不对劲,老婆儿子都丢在杭州不管。悦颜,我想这个礼拜天去他老家一趟看看。”
悦颜立刻说:“我跟你一起去。”
“行,具体时间我们再商量,我这边有点情况,先挂了。”
陈思恒收起手机,护士夹着一块板子蹬蹬蹬跑过来,说有份鉴定报告单要他签字,本来不关陈思恒的事,不过他下班时刚好撞见车祸现场,十字路口两车相撞,场面惨烈,一车司机飞出车外撞到栏杆,颅骨破裂,当场昏迷,他打电话给救护车,把人送到了医院。
“严不严重?”他合上板子,笔夹在中间,他神情严肃地问了一句。
看他一身警服,所以护士语气还算客气,不过听到高位截瘫的可能性时,陈思恒头皮还是一阵发麻。
挺年轻一个男孩儿,不到二十五岁,万幸救了回来,结果下辈子都可能在轮椅上过。
下楼经过咨询台时,他听见几个小护士在议论,说从来没看到过这么惨的现场,血肉模糊,残肢跟主干只靠一点皮连着。
胃部翻滚,实在听不下去,他快步出了医院大厅。
他还是软弱。
放下手机,沈子桥拿着调羹慢条斯理地在汤里画了几个圈,随口问了一句:“要去哪儿?”
悦颜咬了半口的馄饨,等咽下才讲:“还没定。”
“跟谁去?男的女的?”
“男的。”
他依旧不动声色,问:“同学吗?你那个姓孙的老同桌?”
她摇了摇头:“你不认识。”
他抿嘴:“去多久?”
“两天吧。”
“什么时候出发?”
“周五,周六,说不定,要看他时间。”
看他时间,四个字里的每个字都听得他心像针扎,沈子桥还不能表现出来,故作平静地继续看她:“那就周六吧,我有空。”
他有空?悦颜一脸懵,才反应过来:“啊,不用。”
“你一个人离家我不放心,就这么说定了。”他扯来纸巾,先递给她几张,自己随便地一擦嘴角,拿好车钥匙站起身,姿态里一副不容置喙的强势。和他人一样,一个人即便装的再柔软,藏不住的是天性使然。
悦颜无奈起身,跟他回去。
这一路他也什么都没有问,表明他态度的是他的车速。沈子桥把车开的很野,像是有什么怒意亟待宣泄,几次转弯的时候,悦颜都被安全带夺进座位中,不得已,她悄悄抓住把手,车很快停在了家门口。悦颜推门要下去,他不让,中控锁死,悦颜心尖莫名发颤,后背抵住车门,有点慌地回头看住他。
她大概自己也没注意过,每次她害怕的时候,都习惯从下往上地看人,湿漉漉的眼底藏着一点娇、一点怯,很招人疼。无论经历多少世事卜测,她总带着少女式的纯真。
沈子桥一只手架在方向盘,侧身对她,脸上依旧笑笑。
“是那个陈思恒吗?”
二十分钟的车程,足够他把她的人脉理了个干干净净,除了陈思恒,他想不到第二个千方百计想拐走悦颜的人,从他第一眼见到这个男人开始,就有种危机感挥之不去。
大部分时间,沈子桥都充满自信,无论硬件还是外在条件,他都坚信自己是最好的,只有在悦颜面前,他才会发怯。用一个现在网上很俗的词语形容他们的关系,就是女神,她是他的女神,各方面都完美,他的择偶对象因她才有具体的标准,漫长的青春期足以令沈子桥将高悦颜奉上神坛,也让他对眼下的局面失去恰当的判断。
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是从少年起就定下来的,长到再大,再难改变。
沈子桥放浪地看着她,带着点痞,一点坏,越没有安全感,他就越不把话说明白,他手里就那么点牌,打完也就打完了。
他问得很随便:“认识他多久了?”
悦颜说:“回杭州认识的。”
他算了下时间:“那也不到一个月。你觉得,一个月时间就能彻底了解一个人是好是坏?他喊你出去你就出去,有想过后果吗?”
悦颜有点累地摇头,拒绝跟他沟通:“他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也是男人,男人想的什么样,你确定知道?”
悦颜倍感烦扰地看一眼他。
在夜色封闭的车里谈论这种问题,他让人觉得危险,目光和表情都是:“就比如,每次你这么看我的时候,我都只想干一件事。”
悦颜不解:“干什么?”
他弯到她脸边,贴着她的耳朵,气息拂过时吹起她鬓边的散发几缕,他声音暗哑,低低地说了一个NI字。
悦颜强装“镇定”地看他,眉头皱了一下:“你要是再说这种话,我就……”
“你就什么?”他目光深深地看着她,嘴角轻提着。
她就不出什么来,面对一个心怀不轨的男生,任何威胁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她恼怒地把脸转向一边,只给他一张侧脸。
“觉得我下流是不是?但这就是男人,他们想的要的,只会比我更下流。颜颜,听我的话,现在不是念书那会儿了,大家都不像你这么单纯。”
“那你呢?”悦颜毕竟也不傻,其他男人这样,那你呢。
他靠在椅背上,歪过脸来,眼神昏昏的,暗暗的,藏着欲望和火花:“我喜欢你,所以想跟你做那种事,我敢正大光明地说出来,他们呢?”
悦颜轻轻地笑了:“就你可以喜欢我,别人不行吗?”
沈子桥看着她,沉默了两秒,忽的又笑了,来拉她手:“颜颜,别跟我闹。”
她躲开,抿着嘴,神色认真起来:“我没有跟你闹。沈子桥,我们是真的没可能。”
他靠向椅背,笑得近乎轻蔑:“那跟谁有可能?陈思恒?那个小白脸?”
感觉自己被冒犯了,悦颜的声音还算平静:“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看了她一会儿,揣度着她话里多少出赌气的成分,悦颜避开了他的打量,垂下眼睛。
沈子桥扯了扯嘴角:“颜颜,我说你太单纯,你果然还是单纯。跟那个男人在一起,你们靠什么活,爸爸医院每个月三万多块的开销,他负担得起吗?结了婚以后将来住哪儿,难不成住在咱们俩的那套房子里?”
悦颜牙齿轻咬下唇,在他给的难堪里几乎无地自容,她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告诉他,那也是他的爸爸,自从高志明跟李惠芬离婚后,两个人再没一点关系。她眨了眨眼,视野中有一小片他的西裤,还有自己的裙摆,渐渐变得模糊。
再接着,一滴泪直直地滚出眼眶,就轻轻一下,把他的恶形恶状、把他的刻薄无耻击得粉碎。
他说了什么啊?
沈子桥忍受不住地伸手过来,要去抱她,被她回避性地躲掉。他的手只得克制地留在她肩膀:“颜颜……”
他弯下腰来找她的眼睛,央求道:“就跟哥哥在一起,不好吗?哥哥什么都会帮你弄好,你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就跟哥哥在一起,不好吗?”
好吗?
她从十八岁好不容易走到这里,再让她回去找十八岁的自己,她心有余悸,已经没有力气了。
她说:“沈子桥,谢谢你。”
他深深地看着她:“谢什么?”
悦颜抬起头,眼底已经红了一片:“但是,我们也真的不可能再回去,我……”
悦颜还没有说完,就见他一直没吭声,低头在储物格里翻找一阵,找了太久,东西拨拉来拨拉去。
悦颜被他动作一打岔,再说不下去,忍不住上去问:“你找什么?”
“我手机。”
“不是在这儿吗?”
她把档位旁一个黑色长方形拿给他,他接过,揣入裤袋,又找来钥匙,推门下车,悦颜有些懵地坐了一会儿,也跟着下来。
他走在前面,悦颜跟着他进来,背影挺拔。上楼时,悦颜叫了他一声。
他回头,脸色寻常,只不过比平常见时更白了一点。
“你没事吧?”她有些不安。
他笑了下,仿佛她问的有些多余:“没事啊,你也早点休息,明天早上老时间。”
他在自己的爱情里孤注一掷,她的所有拒绝他都听之任之。
这究竟是好是坏,谁知道?
工作渐渐上手,生活也透出它本来的枯燥。悦颜还是尽心尽力地把每件事都做好。
蒋洁开始着手下季度的预财报销,悦颜整理完一叠发票,拿给韩玲过目,她扫了一眼,又用邮箱发给她一张excel表格,让她按照各部门的费用做几张报账的单子。公司的销售每天都有应酬,报销也几乎每天都有,请甲方吃饭的招待费、酒水费、送礼,还有各费那费,每个项目都有资金预算,而销售经理们也尽量把额度报足,反正油水不捞白不捞。填报时悦颜注意到一个叫林东刚的销售经理,他目下的交通费一直是0,往前翻了几个月都是。
悦颜跑去问蒋洁,蒋洁跟她解释:“霍经理不开车的,都是公司派车,偶尔打个的什么的,都是从沈总的账上直接报。”
悦颜想起了昨天那个来问修理费的男人。她刚给韩玲送资料的时候,还看到那几张发票在她文件夹下面压着,这次不报,到下一年这几张修理费的发票就用不上了。
她想了想,把那张发票挑出来,拿了个别针别在林东刚报销的单据最上面。整理完拿去给韩玲审批,她翻了翻,又似笑非笑地看她一眼。悦颜不免忐忑:“这样行吗?”
“你去让小蒋姐签字吧。”
过了韩玲的手,蒋洁一般都不复点,刷刷签了字,要喊魏浩然拿给沈总签字,也快中午了,悦颜主动说:“我去给他吧。”
蒋洁说:“那也行,沈总你认识吧?”她自以为很幽默地加了一句,“不认识也没事,你找人堆里最高最帅的那个就行。”
刚好中午下班,悦颜出去接了个电话,又跑回来把报销单子揣上,走了。
韩玲停了笔,抬头看了她背影一眼,没什么表情。
吃完饭,悦颜把报销的单子拿给他,他看也不看地签完字,抬眼看悦颜还盯着自己,他挑眉:“还有事吗?”
“那个,”她犹犹豫豫地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什么事?”
“不是说进来让我做销售吗?为什么现在还把我放在人事?”
沈子桥低下头,翻着手上的文件,自从昨天开始他就这幅模样,故意冷着她:“再等等。”
悦颜强压心头不忿:“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沈子桥现在可坏了,说来说去还是那一套,不行,还早,再等等。
悦颜知道她又被这人给摆了一道,急得叫起来:“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沈子桥手在鼻梁两侧轻按了按,抬头看她一眼,神色近乎冷淡:“你以为销售是干什么的,过家家吗?你要做就做,把单子交给你,你做的出成绩来吗?”
悦颜气得眼圈都红了。
如果不一开始答应的她好好,她会进康盛吗?
沈子桥不为所动,扪心自问,他是有些溺爱她的,但一到工作,他分的特别清楚,不会因为感情影响判断,因而显得格外冷酷。
最重要的,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沈子桥看看她,把笔丢桌上:“还有事吗?没事这边睡一觉,我给你买了条美少女的新毯子。”
谁要他买美少女的新毯子了?
不是。
“睡你个大头鬼啊!”悦颜越想越生气,拿起他桌面上一只硬面纸巾盒朝他丢了过去,又怕他站起来打她,丢完悦颜就跑走了。
门砰的一声,余音在空气中隐隐震颤。
沈子桥坐在大班椅里,腿上落了一盒纸巾,他仿佛也难以置信,拿起摆弄翻看,嘴角压着的一缕笑纹抖了两下,又余韵悠长地漾开来。
悦颜跑回办公室,办公室就一个韩玲还在,也打算午歇了,所以拉着窗帘关着灯。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把她惊动,她从折叠床上探起头来,见是悦颜也没理她,自顾自拉上毯子继续睡。蒋洁不在,她连基本的客气都懒的装。
悦颜也没说什么,静悄悄地出去,在一楼大厅坐了片刻,想到附近有面湖,又出去沿湖散了会儿步,中午的初冬,空气里聚集了些若有似无的寒意,但光线充足,云也遮不住,走走就热了。沈子桥打来过几个电话,她一概没理。
到了下午上班时间,蒋洁座机响,接起后只听她一直嗯嗯好的好的,最后来了一句:“我明白了沈总。”电话拿开,她叫,“悦颜,沈总找你。”
悦颜慢腾腾地走到她工位的隔板边,接过话筒,放在耳边,嘴里极不情愿地碾出两个字:“沈总。”
沈子桥笑了:“肯接了?大小姐,你发脾气就发脾气,哪里学会的用东西砸人了啊?疼不知道?”
一个办公室的人,连男孩子魏浩然在内,佯装做着手头上的事,哪个不是竖了耳朵暗中在听。
悦颜闷声说:“我知道了。”
“知道有什么用?要做到。”
她好不情愿地嘟囔:“哦……”
他忍笑,还要装作一本正经地道:“这次就放你一马。”
等挂了电话,她还是有些闷闷的。蒋洁看这小姑娘撅着嘴,要委屈不委屈的,只当差事没办好,被沈总批评,于是安慰她说:“你别担心,沈总最好说话了,不是什么大问题,他都不会往心里去,不过你也不要侥幸,沈总向来公私分明,真发起火来也挺可怕的。”
悦颜好奇:“小蒋姐你见过他发火吗?”
蒋洁摇头:“这倒没有,不过几个销售经理都在他办公室里被骂哭过。”
悦颜睁大眼:“这么凶吗?”
蒋洁笑了:“你也不用担心,反正不做销售,也没业绩压力。小姑娘坐坐办公室挺好的,结了婚将来还能照顾家里。”
结果蒋洁这话说完没过几天,事情就来了。
签过字的报账单交给魏浩然去银行划账,报销下来的当天上午,林东刚就发现财务转给自己的钱少了六百。立刻打电话来问,韩玲给他查了查,发现他有笔款报在维修费下,他本来是不开车的,维修费一上来,从沈总那边领来的款相应也少了六百。这笔维修费最后划给了钱宁。
这下好了,两个销售经理当时就吵了起来,光吵不算,互相翻起旧账,从办公室吵到走廊,又从走廊吵到沈子桥面前。
单子上经办签的是悦颜的名字,韩玲没过手,他一个电话就把蒋洁和悦颜都叫到办公室来。蒋洁翻了翻,这才看出来,林东刚本来一直是0的交通费下,夹了一张钱宁司机的发票。
蒋洁急火攻心,持着发票送到悦颜眼皮底下:“你好好的小姑娘怎么能干这种事?”
报私账,挪小账,本来就是公司大忌,企业大或许没人发现,但是小公司一旦查出来,就是人品的问题。
悦颜百口莫辩,她不能说自己给韩玲看过,因为韩玲没签字,她也不能说这蒋洁也复核过,毕竟她是被自己拖累的。
林东刚是个精干消瘦的男人,三十左右,面目还算端正,就是一脸的鹰隼相,看着就不好惹,他冷笑着钉了悦颜一眼:“我是不是该去把银行流水都拉出来,以防有些人再动些下三滥的手脚。”
悦颜长这么大,都没被人指着鼻子骂过下三滥,眼中的泪迅速聚集,脸差点红破,眼下更是一句话都说不出。蒋洁赔着笑,替她在下面兜着:“不会不会,之前都是韩玲在报。小姑娘才来没多久,还在学习阶段,犯点小错误也再所难免。霍经理你大人有大量,包容一下咯。”
沈子桥坐在大班椅里,从他们进来开始就认真在听霍钱两人的矛盾,一眼都没往悦颜身上看,这时才说:“高悦颜是吧,你说说看,这账怎么会这么报?”
感受到他隐含鼓励的目光,悦颜稳住情绪,把事情原委简单说明了下。
“做好单子没给韩玲看过?”
悦颜一顿,她摇了摇头:“看过。”
“她没说什么?”
“没有。”
听到这个没有,他心里已经有点数了,沈子桥放了笔:“这事发生了就下不为例,林经理的钱从我下季度的报销出。”
林东刚连连摆手:“沈总别别别,我哪是为了这点钱啊,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我知道,小高那边我会让蒋洁好好教育的,该扣该罚按公司的章程来,钱你拿着,哪有给公司白干的道理。传到外面去,我底下的销售都要跑光了。”
林东刚搓手赔笑:“沈总,您说的我这不要都说不过去了,那行吧,反正都是为了公司。”
林东刚这人钱宁再清楚不过,从头到尾都是当笑话在看,倒是沈总,在人散光前,把高悦颜单独留下。钱宁殿后走的,带门前无意瞄了一眼,沈总探身抽了几张纸巾捏在手里,要起不起,尚有顾忌似的。
等人都没了,沈子桥才过来,要擦她的脸,被她躲开。他语气无奈:“哭什么?怕我骂你啊?”
从前高志明教育过她,哭可以,但是做错了还哭,那就是在威胁爸爸。
她瓮声说:“我没哭。”接着,一滴泪不争气地打在衣襟上,很快就有了第二滴、第三滴。
沈子桥靠坐在办公桌上,反手撑住桌面,耐心等她发泄完。
泪中不仅是委屈,更多还有自责。这是社会教她的第一课,告诉她善心不要滥用。
她抽噎着说:“钱你从我工资里扣吧……”
沈子桥拉她到自己分开的两腿之间,一个半靠,一个立着,他用手轻轻托起她的下巴。
这个女孩的泪,一直都是让他妥协的东西。
“当然要扣你钱了,让你吃一堑长一智,记住这个教训,别做烂好人。职场上,你有什么动作一定要让你的领导知道,出了事也不要傻乎乎地全揽在自己头上,你看看这回有谁帮你。”
她回不了嘴。
“现在知道外面的人都是怎么样了吧,哥哥没骗你吧,还嚷嚷着要做销售吗?”他用指腹擦去她眼角的泪,顺手抹在自己衬衣上。
沈子桥觉得这次让她见识过人心卜测,以为这姑娘能生点望而却步的意思,岂料她泪眼朦胧地看着他,还在说,要。
沈子桥看着她,被噎了一下,也不知道该气还是该笑,反正最后是笑了。
在沈子桥宽大为怀的政策处理下,这件事就这么过去,蒋洁批评了她一顿,又把她经手的报账单翻出来,逐笔核对,带着她加了好几天的班,悦颜也认,回头准备了一个男孩能用的上小礼物送蒋洁,从此做人做事更加谨慎小心。
时间转眼到了这周五,她在房间收拾行李时接到一个电话,是陈思恒打来的,跟她确定出发时间,就定在周六早上。
结果在飞机场上一碰头,淡定如陈思恒也愣了,悦颜先从出租车里下来,沈子桥紧随其后,拎着两人的行李跟着下来。
两个男人打了照面,没什么真情实感地互道寒暄。他跟悦颜说话的时候,沈子桥就默默地退到一边,看管着属于他们的两个行李箱,仿佛一个合格但不能被忽视的强烈存在。
飞机上,他买的机票跟悦颜挨在一起。沈子桥自己另买,不坐一排。不一会儿他就过来,跟他们旁边的乘客商量,坐到了悦颜身边。
格局就成了陈思恒靠窗,中间是悦颜,沈子桥坐在最外边。隔着悦颜,沈子桥又假惺惺地跟陈思恒打了声招呼。
他也就没方便问为什么沈子桥会一块儿跟过来。
结束两个多小时的飞行,他们在西南一座小城落地,然后做机场大巴,又改出租车,颠簸了一路才到目的地,那是一座靠山的小村落,田垄纵横交错,都是旱地,很少能见到湖泊。
他们先在县里的一家小旅馆落脚,开了房把东西放好,然后分头行动,陈思恒去联系当地的乡政府,悦颜去村里打听何仁杰的情况。沈子桥跟着悦颜从村头跑到村尾,一句话都没问。
他的户口从这里迁出,何仁杰还是后来改的名字,各房亲戚都没有再联系,也不清楚这人跑去哪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能让他怕成这样,老婆孩子都还在杭州,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
这天傍晚,他们精疲力竭地回到旅馆,各自回房。
洗漱完,陈思恒去敲她房间的门,想交换下今天获得的信息,怎么也没想到开门的会是沈子桥,换了一身藏青色的家居服,袖口随便往上折了两折,显出一种跟平时截然不同的放松。
陈思恒愣在那里。
沈子桥手扶门框,故意没遮全里面的景象。
床边摆了一双女孩的球鞋,尺码小巧,一只脚底踩着另一只脚面,像是匆忙之间踢下来。
“你找颜颜吗?”
陈思恒回过神来,尽量用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表情问:“她睡了吗?”
“嗯。”
“这么早?”
他笑着,带着含糊的可恶:“颜颜就是这样,一累就会睡得很快。”
陈思恒说:“那我晚点打她手机。”
“可以。”沈子桥点点头,来了这么一句。
陈思恒转身回自己房间,听见身后房门关上的声音,他忍不住回头,走廊上没有沈子桥的踪影,他回了悦颜房里。
回房后,陈思恒从双肩包里掏出笔记本,在灯下看着手绘的枝叶图,本来沈子桥这三个字被他用圆圈圈出,在旁边打了个问号。
他盯着那个问号,思绪有点飘,也有点懵。
这个懵从沈子桥出现在机场起就一直持续到现在。
陈思恒是独生子,没有亲妹妹,表妹倒是有一个,小姨家的孩子,他忍不住在心里问自己,如果妹妹大了去外面,他会不放心地一起跟去,甚至住一间房里吗?
他的答案是不会,顶多打几个电话关心一下。
所以他无法理解沈子桥的行为。
不光是陈思恒不理解,连悦颜都自己有些费解,尤其在她一觉睡醒,睁眼看到另一张床上的男人时,她相信或许真有宿命这种东西,你会被它纠缠得彻彻底底。
她在床上转过脸去,耍赖似地躺了一会儿,终于还是爬坐起,伸手顺了顺睡乱的头发。
他没开电视,窗户关得死死,房间里安静到没有一丝噪音,他在壁灯那种昏黄的灯光里看着自己,目光带点研判的意味,看得悦颜有些喘不过气。
不过真正让她喘过气的是下面一句话。
“颜颜,你不要搞了,你搞不来的。”他垂下脸,手放在一条曲起来的膝盖上面,手指一下一下轻点,“我妈为什么躲在四川不敢回来,何仁杰为什么一出事就丢下老婆儿子跑得无影无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怕那个人,你把何仁杰找出来又怎么样,被人抓到就是坐牢,把那人告发他就是死路一条。”
悦颜慢慢握紧拳头,指尖无意识地在雪白的床单上抓出一朵素色的花,她哑着嗓子说:“难道我爸爸就该白白躺在医院吗?”
“你还有哥哥啊,”他认真地说,“颜颜,你相信哥哥。”
西南这一行也不能说毫无收获,陈思恒最后在乡政府调到了他户口迁出后的记录,查到他改前的名字,陈思恒联系当地警方,让他们帮忙寻找。
翌日一早,一行三人踏上回杭的飞机,在机场分道扬镳。
提着行李进客厅,沈馨儿扶着腰惊喜地站起身:“你们回来了?”周阿姨过来接他们的东西,沈馨儿挺着肚子迎出来,“玩得开心吗?”
沈子桥看了悦颜一眼:“挺好的,风景不错。颜颜说下次让你跟姐夫一块过去玩儿。”
沈馨儿笑:“你们要玩就尽兴地玩,像我这样有了家庭生了孩子,更加玩不动。”
韩玲从二楼下来倒水喝,经过客厅的时候瞄了他们一眼,然后一句话没说,转身上楼。
沈馨儿背着他们,向周阿姨努努嘴,意思是你看到没有,招呼都不打一个,真跟仇人一样。
周阿姨无奈地摇了摇头。
沈子桥回自己房间收发邮件,处理工作上的一些事。不一会儿房门被敲响,他说了声请进。不会是悦颜他知道,不过他没想到是韩玲,踩着棉拖翩然走近,把个文件夹摊在他面前给他过目:“沈总,这是下季度的销售计划。我在做报表的时候发现有两处数字跟年初制定的计划对不上,这么下去的话今年年度预算可能不够。”
他翻了几页,没下主意,而是说:“等周一开会再讨论吧。”
“行。”
她转身要走,被他叫住:“等等。”
她心砰的快跳了一下,回过头,脸上静静地看他。
他双手合十,手肘撑着桌面,脸上的表情若有所思,看着她说:“颜颜这个人比较单纯,也没什么心眼,她要是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你直接来跟我说,我会提醒她的。”
韩玲依旧立在原地,下颌如常微扬,像是不屑跟他解释什么,连敷衍也没有,她推门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