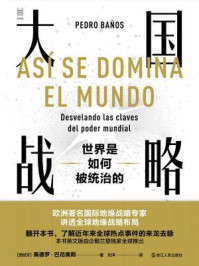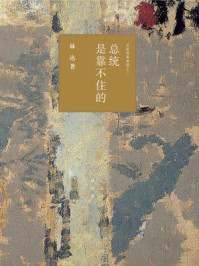在对希腊城邦社会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其经济特征的评价,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影响到学者们对其他方面诸如城邦政治乃至希腊文明特征的评价。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把希腊文明看成是一个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很少有人对古希腊的手工业和商业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手工业的各部门以及从事工商业的人口结构进行过系统而又详细的研究,但上述结论一直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没有人对此提出诘问。更有甚者,从这个结论出发,又推出了一系列同历史真实不相符合的结论,如梭伦代表了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其改革是工商业阶层对贵族阶层的胜利,雅典民主政治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等等。这些观点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普遍存在于大学的教科书中,吉林人民出版社版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上古史》说梭伦所持的“是工商业奴隶主的立场”,而雅典的平民领袖是“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代表人物,……他们同贵族寡头派的矛盾,实际就是工商业奴隶主同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更是发挥和强调了上述观点,把梭伦改革的阶级实质说成是“以适应正处上升阶段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要求为主,……以为工商业奴隶主阶级掌权开路为主调”,并进一步强调说“它最关键的作用就是使梭伦所代表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家成为城邦的领导,从而为奴隶制民主政治奠基”。出身于雅典最显赫的贵族家庭的克里斯梯尼也被说成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另一个富有贵族家庭出身的伯里克利则“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民主政治家,也是包括第四等级的平民群众的代言人”
;199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更是发挥和强调了上述观点,把梭伦改革的阶级实质说成是“以适应正处上升阶段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要求为主,……以为工商业奴隶主阶级掌权开路为主调”,并进一步强调说“它最关键的作用就是使梭伦所代表的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家成为城邦的领导,从而为奴隶制民主政治奠基”。出身于雅典最显赫的贵族家庭的克里斯梯尼也被说成是“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另一个富有贵族家庭出身的伯里克利则“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民主政治家,也是包括第四等级的平民群众的代言人”
 ;1994年出版的新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重复了上述观点,说梭伦改革“是为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准备了条件”,而伯里克利还是“一身兼二任,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政治家,也是平民群众的代言人”。
;1994年出版的新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重复了上述观点,说梭伦改革“是为工商业奴隶主掌握政权准备了条件”,而伯里克利还是“一身兼二任,既是代表工商业奴隶主的殷富公民的政治家,也是平民群众的代言人”。
 这些传统的观点使得我们对希腊城邦社会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阶级对立的分析上,如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对立、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与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阶级的对立等等。当然,在这些传统观点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现实根源,即国内的学者往往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相对比。由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由今而古,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农业特征,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亦即古希腊文明。但事实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对古希腊社会所进行的详实历史考察。实际上,希腊城邦社会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古代希腊人的农业观念、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之地位、土地财产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工商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等方面的分析来揭示这个论点。
这些传统的观点使得我们对希腊城邦社会的研究仅仅停留在阶级对立的分析上,如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对立、工商业奴隶主阶级与占有大土地的奴隶主阶级的对立等等。当然,在这些传统观点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现实根源,即国内的学者往往有意识或下意识地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相对比。由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由今而古,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农业特征,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亦即古希腊文明。但事实上这个结论的主要依据并不是对古希腊社会所进行的详实历史考察。实际上,希腊城邦社会同古代中国社会一样,是一个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为特征的社会。本文的目的即在于通过对古代希腊人的农业观念、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之地位、土地财产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工商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等方面的分析来揭示这个论点。
在早期希腊人的观念中,农业即已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希腊最早的文学作品即荷马史诗中,农业已经被看成是文明的标志。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在向他人描述野蛮的独眼巨人时,以两条依据把他们同文明生活区分开来:一是他们不事农耕,二是他们没有社会成员集体议政的会议(agora)。
 虽然荷马告诉我们,那些独眼巨人以放牧为生,但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生活,而只有农耕才是文明生活的象征。赫西俄德与荷马生活在同一时代,他的长诗《工作与时日》以农耕为主题,诗人劝诫其兄弟勤于耕作,顺应农时。只有这样,个人才能维持生计。对赫西俄德来说,农业是个人及其家庭赖以生活的根本,而海上贸易则带有极大的风险,只能作为家庭的副业。早期希腊人这种以农为本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作家色诺芬著有《家政论》(
Oeconomicus
)一文,其主要内容是如何经营和管理家庭的土地。文献传统归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篇论文也以《家政论》为题,但作者也论及城邦的经济,并列举了城邦经济的主要来源。对他来说,城邦最大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于土地的收成,其次是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再次是其他收入;而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同样是农业,其次才是其他收入。
[1]
虽然荷马告诉我们,那些独眼巨人以放牧为生,但对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生活,而只有农耕才是文明生活的象征。赫西俄德与荷马生活在同一时代,他的长诗《工作与时日》以农耕为主题,诗人劝诫其兄弟勤于耕作,顺应农时。只有这样,个人才能维持生计。对赫西俄德来说,农业是个人及其家庭赖以生活的根本,而海上贸易则带有极大的风险,只能作为家庭的副业。早期希腊人这种以农为本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古典时代。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作家色诺芬著有《家政论》(
Oeconomicus
)一文,其主要内容是如何经营和管理家庭的土地。文献传统归于亚里士多德的另一篇论文也以《家政论》为题,但作者也论及城邦的经济,并列举了城邦经济的主要来源。对他来说,城邦最大宗、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于土地的收成,其次是港口税和市场交易税,再次是其他收入;而家庭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同样是农业,其次才是其他收入。
[1]
古希腊社会的农业特征也反映在希腊人对农业和其他职业的不同态度之中。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经济行为的因素是职业的高低贵贱之分,而不只是获利的多少。
[2]
对他们来说,有些职业是高贵的,符合贵族与上等人的身份,而另一些职业却是低贱的,只适宜于没有土地财产的下等人、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和奴隶。在职业等级中,农业是最为体面的,也最符合“绅士”(kaloi kagathoi)
 的身份,它同其他所有职业形成一种对立,而商业和手工业则是低贱的职业。因此,色诺芬把手工业说成是不适合城邦生活亦即文明生活的职业,其笔下的苏格拉底则认为,于“绅士”而言,没有比农业更为合适的职业,因为他是从农业中获得生活所需。
的身份,它同其他所有职业形成一种对立,而商业和手工业则是低贱的职业。因此,色诺芬把手工业说成是不适合城邦生活亦即文明生活的职业,其笔下的苏格拉底则认为,于“绅士”而言,没有比农业更为合适的职业,因为他是从农业中获得生活所需。
 由于同样的原因,柏拉图在其晚期的著作《法律篇》中,把他的理想国描绘成一个由5040个农民公民组成的城邦。
由于同样的原因,柏拉图在其晚期的著作《法律篇》中,把他的理想国描绘成一个由5040个农民公民组成的城邦。
 虽然柏氏所述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但在这里,当时的历史现实对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柏氏又着重强调,这个理想的城邦应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它甚至不应生产过剩的粮食。因为如果粮食大量出口,“城邦将会充满大量金银钱财——而如果一个城邦想要培养公正而高贵的习性,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形了”。
虽然柏氏所述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但在这里,当时的历史现实对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柏氏又着重强调,这个理想的城邦应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它甚至不应生产过剩的粮食。因为如果粮食大量出口,“城邦将会充满大量金银钱财——而如果一个城邦想要培养公正而高贵的习性,那就再也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形了”。
 伪亚里士多德的《家政论》同样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至于财产,首先应使之与天性相符合。按照天性,农业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与土地相关的行业,如采矿。农业是最好的职业,因为它是公正的,且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无论这妨害是有意的——如贸易和雇工,还是无意的——如战争。”
伪亚里士多德的《家政论》同样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写道:“至于财产,首先应使之与天性相符合。按照天性,农业是第一位的,其次是与土地相关的行业,如采矿。农业是最好的职业,因为它是公正的,且不妨害他人的利益,无论这妨害是有意的——如贸易和雇工,还是无意的——如战争。”
 或许有人会说,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对手工业的蔑视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希罗多德注意到希腊人对手工业的一般态度:“我不能肯定是否也像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接受了对手工业的这种态度,但据我所知,色雷斯人,斯基泰人,波斯人,吕底亚人和几乎所有的蛮族人都蔑视从事手工业的公民及其子女……所有的希腊人都接受了这种态度,尤其是斯巴达人,而科林斯人的态度则最为温和。”
或许有人会说,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对手工业的蔑视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希罗多德注意到希腊人对手工业的一般态度:“我不能肯定是否也像其他许多东西一样,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接受了对手工业的这种态度,但据我所知,色雷斯人,斯基泰人,波斯人,吕底亚人和几乎所有的蛮族人都蔑视从事手工业的公民及其子女……所有的希腊人都接受了这种态度,尤其是斯巴达人,而科林斯人的态度则最为温和。”
 实际上,这种对手工业和商业的轻视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对手工业和商业的一种典型态度。但仅仅从观念的考察并不足以说明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实际的历史情形又如何呢?
实际上,这种对手工业和商业的轻视反映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对手工业和商业的一种典型态度。但仅仅从观念的考察并不足以说明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实际的历史情形又如何呢?
[1] 伪亚里士多德:《家政论》 (Oeconomica ),1346a5—13。
[2] 对此最为深入的分析当属芬利:《古代经济》(M.I.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伦敦1985年第2版(1973年初版)。芬利提出,古代人的经济活动是“嵌入”(embedded)在社会生活之中的,其核心在于维持和提升现有地位。
正如许多古典史家所指出的那样,希腊城邦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和乡村的组合,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公民集体。公民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只有公民才能参加公民大会,担任城邦的官职,或在法庭上提出诉讼,也只有他们才能拥有土地和房产。公民权是希腊城邦社会中的一个最基本要素,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后者实际上主要指的是土地和房产的所有权,这是公民群体的特权。一个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或外邦人可以十分富有,但他不能购置地产,而只能租赁房子。公民拥有土地的特权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农业是城邦生活最根本的基础,城邦的主体阶层主要是土地所有者,以农业为生。这在斯巴达尤其明显。早在公元前7世纪,莱库古改革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在公民群体内进行份地的平均分配。虽然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平等份地是后来的虚构
 ,但如果对斯巴达的社会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就不难看出,平等份地实则是斯巴达城邦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基础。斯巴达在公民群体内实行共餐制,为此公民每年都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这个定量为12斗(medimnoi)大麦和一定量的酒、奶酪和无花果。
,但如果对斯巴达的社会制度进行综合分析,就不难看出,平等份地实则是斯巴达城邦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基础。斯巴达在公民群体内实行共餐制,为此公民每年都必须向城邦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这个定量为12斗(medimnoi)大麦和一定量的酒、奶酪和无花果。
 如果一个公民不能交纳这个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
如果一个公民不能交纳这个规定量的粮食,他就会丧失公民权。
 同共餐制相适应的是公民的军事化制度。斯巴达城邦禁止公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而要求他们把保卫城邦的自由作为首要职责,凡60岁以下的男性公民都必须不断进行军事和身体的训练。这种公民军事化的制度和共餐制都要求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斯巴达城邦正是通过平等份地的分配使其公民具备同共餐制和军事化制度相适应的经济条件,而公元前7世纪早期斯巴达对美塞尼亚的征服使得平等份地的分配成为可能,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又被迫沦为斯巴达人的黑劳士,亦即斯巴达人土地的耕种者。从这里已不难看出,公民的份地是斯巴达城邦社会、政治和军事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城邦的生活是同土地以及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同共餐制相适应的是公民的军事化制度。斯巴达城邦禁止公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活动,而要求他们把保卫城邦的自由作为首要职责,凡60岁以下的男性公民都必须不断进行军事和身体的训练。这种公民军事化的制度和共餐制都要求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斯巴达城邦正是通过平等份地的分配使其公民具备同共餐制和军事化制度相适应的经济条件,而公元前7世纪早期斯巴达对美塞尼亚的征服使得平等份地的分配成为可能,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又被迫沦为斯巴达人的黑劳士,亦即斯巴达人土地的耕种者。从这里已不难看出,公民的份地是斯巴达城邦社会、政治和军事制度必不可少的条件,城邦的生活是同土地以及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雅典,梭伦的改革实际上确立了公民的土地私有权。不少学者认为,梭伦代表了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但这种说法缺乏可信的历史根据。在公元前7世纪末和前6世纪初,梭伦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实际上主要是雅典的农业危机,是债务奴隶制对“六一汉”人身自由的威胁,其主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废除所有债务和债务奴隶制,它同工商业并没有什么关系。梭伦在自己的诗歌中也说,他的改革涉及土地问题,他清除了黑色土地上的界碑(horoi),“以前她为人所奴役,但现在获得了自由”。
在雅典,梭伦的改革实际上确立了公民的土地私有权。不少学者认为,梭伦代表了工商业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但这种说法缺乏可信的历史根据。在公元前7世纪末和前6世纪初,梭伦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实际上主要是雅典的农业危机,是债务奴隶制对“六一汉”人身自由的威胁,其主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废除所有债务和债务奴隶制,它同工商业并没有什么关系。梭伦在自己的诗歌中也说,他的改革涉及土地问题,他清除了黑色土地上的界碑(horoi),“以前她为人所奴役,但现在获得了自由”。
 有些学者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认为梭伦还进行了币制改革。但古钱币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梭伦改革时,货币还没有出现,雅典最早开始使用货币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而不是在这以前。
[1]
古典作家归功于梭伦的币制改革,实则是后来的立法。正如学者们早已指出的那样,因为梭伦以立法者著称,古典作家往往将新的立法都归功于他。梭伦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将公民按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计算财产的标准完全是按照个人土地上“干的和湿的”(亚里士多德语,“湿的”即指橄榄油)收获,而不是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收入。也就是说,公民政治权利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其拥有土地的多少,而不是其他财富。只有土地才是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基础。同样,这条措施的目的也不在于发展工商业,认为梭伦代表工商业阶层利益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有些学者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记载,认为梭伦还进行了币制改革。但古钱币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梭伦改革时,货币还没有出现,雅典最早开始使用货币的时间是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而不是在这以前。
[1]
古典作家归功于梭伦的币制改革,实则是后来的立法。正如学者们早已指出的那样,因为梭伦以立法者著称,古典作家往往将新的立法都归功于他。梭伦的另一项改革措施是将公民按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每个等级享有相应的政治权利。值得注意的是,计算财产的标准完全是按照个人土地上“干的和湿的”(亚里士多德语,“湿的”即指橄榄油)收获,而不是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收入。也就是说,公民政治权利的多少完全取决于其拥有土地的多少,而不是其他财富。只有土地才是个人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基础。同样,这条措施的目的也不在于发展工商业,认为梭伦代表工商业阶层利益的说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再从雅典的土地所有者和农业人口在公民群体中所占的比例来看,我们拥有的数据仍然说明,农业是雅典城邦社会最根本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公元前322年,马其顿将军安提帕特在雅典扶植起一个寡头政体,规定只有财产价值在2000德拉克马以上的公民才拥有全部的公民权,大部分公民因此而失去了公民权。据西西里史家狄奥多鲁斯记载,失去公民权的人数达到22000(普鲁塔克则认为是12000),约九千人仍然拥有全部的公民权。
 正如戈麦所指出的那样,从寡头政治的特征来看,这种财产限制主要是根据土地财产的价值而定
[2]
,而价值2000德拉克马的土地正好足以维持重装步兵的社会地位。
[3]
也就是说,这个寡头政体是一个以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寡头政治。公元前411年,雅典的五千人会议试图建立重装步兵阶层的民主政治,即有土地财产限制的有限民主,根据这一限制,只有约九千人享有全部的公民权。
正如戈麦所指出的那样,从寡头政治的特征来看,这种财产限制主要是根据土地财产的价值而定
[2]
,而价值2000德拉克马的土地正好足以维持重装步兵的社会地位。
[3]
也就是说,这个寡头政体是一个以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寡头政治。公元前411年,雅典的五千人会议试图建立重装步兵阶层的民主政治,即有土地财产限制的有限民主,根据这一限制,只有约九千人享有全部的公民权。
 这个数字正好同上面的数字相同,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基本上反映了古典时代雅典较为富裕的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力量。但中小农阶层的情况又如何呢?公元前403年,某个名叫弗尔米修斯的公民提议,将政治权利限制在拥有土地的公民群体内。狄奥尼修斯告诉我们,如果此项提议得以实行,那么近五千人将失去公民权。
[4]
这个数字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至少五分之四的雅典公民拥有土地,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公民没有土地。虽然这些数据并不一定完全准确,而且它们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情况,但综合来看,它们仍然反映了古典时代雅典公民的大体构成。雅典公民的主体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小农阶层。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雅典的捐助者阶层和重装步兵阶层只占公民的小部分,同样,没有土地的平民阶层也只是公民群体中的少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雅典公民都以农业为生,而不是手工业和商业,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决定其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根本因素。不少学者认为,古典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工商业不断发展、工商业者阶层力量壮大的结果,但从上述分析来看,雅典公民群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同自由农阶层的力量相抗衡的工商业者阶层。即便雅典公民中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政治力量也仍然是十分微弱的。同时,他们也没有政治上的代表。在雅典的民主政体中,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来自于富有的捐助者亦即大土地所有者阶层,客门如此,伯里克利如此,阿西比德也如此。
[5]
也有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在伯里克利之后登上雅典政治舞台的平民领袖如克利昂和克利奥芬代表了一个新兴的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其根据是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作品中把克利昂说成是鞋匠,克利奥芬则是琴匠。
[6]
但在这里如果过于简单地理解阿里斯托芬所说就错了。我们知道,无论在政治观点上还是个人关系上,阿里斯托芬同克利昂都是敌对的,并且在作品中一再对其进行攻击。鞋匠的说法至多只能算是对政敌的诋毁,而且阿里斯托芬的毁谤恰恰说明手工业是为人所鄙视的行当。相反,阿氏在作品中所推崇的人物形象往往是阿提卡的农民,如《阿卡奈人》中的迪卡约波利(Dikaiopolis),《财富》中的克里米鲁斯(Chremynus)等。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往往代表观众亦即公民,而阿氏喜剧中的合唱队则常常是由农民组成的。这足以说明,雅典公民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工商业者。
这个数字正好同上面的数字相同,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基本上反映了古典时代雅典较为富裕的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力量。但中小农阶层的情况又如何呢?公元前403年,某个名叫弗尔米修斯的公民提议,将政治权利限制在拥有土地的公民群体内。狄奥尼修斯告诉我们,如果此项提议得以实行,那么近五千人将失去公民权。
[4]
这个数字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至少五分之四的雅典公民拥有土地,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公民没有土地。虽然这些数据并不一定完全准确,而且它们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的情况,但综合来看,它们仍然反映了古典时代雅典公民的大体构成。雅典公民的主体是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小农阶层。富有的土地所有者——雅典的捐助者阶层和重装步兵阶层只占公民的小部分,同样,没有土地的平民阶层也只是公民群体中的少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雅典公民都以农业为生,而不是手工业和商业,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是决定其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根本因素。不少学者认为,古典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工商业不断发展、工商业者阶层力量壮大的结果,但从上述分析来看,雅典公民群体中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同自由农阶层的力量相抗衡的工商业者阶层。即便雅典公民中有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的政治力量也仍然是十分微弱的。同时,他们也没有政治上的代表。在雅典的民主政体中,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来自于富有的捐助者亦即大土地所有者阶层,客门如此,伯里克利如此,阿西比德也如此。
[5]
也有学者认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在伯里克利之后登上雅典政治舞台的平民领袖如克利昂和克利奥芬代表了一个新兴的工商业阶层的利益,其根据是阿里斯托芬在其喜剧作品中把克利昂说成是鞋匠,克利奥芬则是琴匠。
[6]
但在这里如果过于简单地理解阿里斯托芬所说就错了。我们知道,无论在政治观点上还是个人关系上,阿里斯托芬同克利昂都是敌对的,并且在作品中一再对其进行攻击。鞋匠的说法至多只能算是对政敌的诋毁,而且阿里斯托芬的毁谤恰恰说明手工业是为人所鄙视的行当。相反,阿氏在作品中所推崇的人物形象往往是阿提卡的农民,如《阿卡奈人》中的迪卡约波利(Dikaiopolis),《财富》中的克里米鲁斯(Chremynus)等。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往往代表观众亦即公民,而阿氏喜剧中的合唱队则常常是由农民组成的。这足以说明,雅典公民的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工商业者。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还反映在古希腊人的战争方式中。从公元前7世纪早期起,希腊人便普遍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战争方式,即方阵的作战方式,其主要的战斗力量是由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实际上这种战争方式是由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所决定的。首先,方阵的出现是中小农民阶层力量壮大的结果,重装步兵的主要来源是拥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农民;其次,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只能在平原上进行有效的战斗,在山地则无法作战,这说明战争旨在占领敌方肥沃的平原或保卫己方平原地区的庄稼;再者,虽然城邦之间战事不断,但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古代希腊的战争完全是季节性的。战事通常集中在每年5至7月的收获季节,即便是希腊世界规模最大的战争——公元前5世纪后期爆发于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也是如此。斯巴达军队每年入侵雅典的领土,但入侵总是在收获季节,而且每次入侵都不超过40天,而在同时,雅典的舰队也从海路入侵斯巴达同盟的领土。两个因素决定了这种战争的季节性:其一,城邦没有职业化的军队,其主要的军事力量即重装步兵实际上是农民,农忙时节他们必须耕种自己的土地;其二,战争的主要目的是破坏敌人土地的收成,而实施这种战术最为有效的时间是在收获季节。
[1] 参见克拉亚:《雅典古风时期的钱币:分类与纪年》(C.M.Kraay,“The archaic owls of Athens:Classification and chronology”),载《钱币学年鉴及皇家钱币学会丛刊》(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Numismatic Society )第6辑,第16期(1956年),43—68页;华莱士:《早期雅典与尤卑亚的货币》(W.P.Wallace,“The early coinage of Athens and Euboia”),载《钱币学年鉴及皇家钱币学会丛刊》第7辑,第2期(1962年),23—42页。
[2] 戈麦:《公元前5至前4世纪雅典的人口》(A.W.Gomme, The Population of Athens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ies B.C. ),牛津大学出版社1933年版,17—18页。
[3] 琼斯:《雅典民主政治》(A.H.M.Jones, Athenian Democracy ),牛津1957年版,81页、142页注50。
[4] 狄奥尼修斯:《论吕西阿斯的演说》(Dionysius, On Lysias ),32。
[5] 对于雅典富有捐助者阶层的系统研究,参见戴维斯:《公元前600—前300年的雅典有产家庭》(J.K.Davies, Athenian Properfied Families 600-300 B.C. ),牛津1971年版;及其《古典雅典的财富及其力量》( Wealth and the Power of Wealth in Classical Athens ),纽约1981年版。
[6] 参见科诺尔:《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新政客》(W.R.Connor, 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ary Athens ),普林斯顿1971年版。
让我们再来看看古代希腊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情况及其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占的位置。雅典历来被认为是古希腊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城邦之一,同时它也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研究的最详细资料。但即便如此,古典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材料都无法让我们得出雅典手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结论,因为无论是古典文献还是考古材料都少有关于手工业的记载,唯一有充分历史证据的手工业是雅典的制陶业,这也是雅典最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从公元前6世纪早期起,雅典生产的彩陶就控制、甚至几乎垄断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市场,出口到远至黑海沿岸、法国南部和北非的广大地区,但制陶业在雅典经济中所占的位置却是十分次要的。根据考古专家们的估算,即使在制陶业最兴盛时期,雅典从事制陶业的总人数也不超过200人。
[1]
而且到公元前4世纪,由于海外市场对彩陶需求的消失,雅典的制陶业也随之迅即衰落下来。除彩陶外,雅典城邦似乎很少出口其手工产品。也就是说,雅典手工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给的需要,因而其规模也就十分有限,希腊其他城邦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因为手工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地方市场的需要,所以需求量有限,从而才导致了同行之间的竞争。色诺芬就提到,在一个较小的城市里,同一个工匠往往制作各式不同的产品,包括躺椅、门窗、犁钯和桌子等,甚至还建造房屋。但即使如此,仍不足以维持生计。
[2]
在另一处他又说,即使在如雅典那样的大城市里,工匠之间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在我所知道的所有行业中,银矿开采是唯一不引起嫉妒的行业……例如,如果有太多的铜匠,铜制品的价格就会变得低廉,铜匠就会失业,铁匠的行当也是如此。”
[3]
色诺芬的这两段评论均表明,希腊城邦中的手工业生产并非以大规模的出口为目的,而只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求。科林斯是另一个以工商业著称的希腊城邦,斯特拉波在其《地理志》中,用大量的篇幅描述了科林斯的富有
 ,但也没有提到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因此,当大卫·休谟说,他并不记得任何“古代作家在记载中把一个城市的发展归功于一门手工业”
[4]
时,可谓一语中的。实际上,手工业生产并不是希腊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这里牵涉到一个西方学者早已注意到的问题,即古代城市之一般特征。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古代的城市是消费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
[5]
韦伯的这一定义把古代的城市同中世纪乃至现代的城市明确地区分开来。和中世纪的城市不同,古代城市没有组织和保护手工业生产的行会,不是独立于农村的生产中心。早于韦伯的卡尔·布歇尔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他写到,中世纪的城市“和希腊罗马的城市不同,并不只是一个消费中心”
[6]
,它还是一个手工业的生产中心。行会、会馆和交易所形成了中世纪城市的最重要特色,同时行会也左右了城市的政治生活。而古代希腊的城市则既没有手工业行会,也没有会馆和交易所。
[7]
相反,在城市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农民阶层,他们组成了公民的主体,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主体阶层。
[8]
城市同农村不可分割,它依赖于农村为其提供消费品如粮食、酒和橄榄。事实上许多城市居民本身就是土地所有者,他们从自己的田庄里获得一应的生活必需品。
,但也没有提到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因此,当大卫·休谟说,他并不记得任何“古代作家在记载中把一个城市的发展归功于一门手工业”
[4]
时,可谓一语中的。实际上,手工业生产并不是希腊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这里牵涉到一个西方学者早已注意到的问题,即古代城市之一般特征。马克斯·韦伯早就指出,古代的城市是消费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
[5]
韦伯的这一定义把古代的城市同中世纪乃至现代的城市明确地区分开来。和中世纪的城市不同,古代城市没有组织和保护手工业生产的行会,不是独立于农村的生产中心。早于韦伯的卡尔·布歇尔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他写到,中世纪的城市“和希腊罗马的城市不同,并不只是一个消费中心”
[6]
,它还是一个手工业的生产中心。行会、会馆和交易所形成了中世纪城市的最重要特色,同时行会也左右了城市的政治生活。而古代希腊的城市则既没有手工业行会,也没有会馆和交易所。
[7]
相反,在城市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农民阶层,他们组成了公民的主体,是城邦政治生活的主体阶层。
[8]
城市同农村不可分割,它依赖于农村为其提供消费品如粮食、酒和橄榄。事实上许多城市居民本身就是土地所有者,他们从自己的田庄里获得一应的生活必需品。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古代希腊城市中没有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毋庸置疑,城市是手工业相对集中的地方,是手工作坊如陶器、铁器作坊以及工匠们的集居之地。同时,城市也是唯一的集市。希腊的农村中没有地方集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阿卡奈人》一剧中的主人公这样说道:“我讨厌城市,只想回到我的村庄。啊!我的村庄。我们这里没有卖油或醋的;甚至从没有听说过‘买卖’这个词。我们生产自己所需要的所有东西,我们也不需要航海,因为根本就没有船只。”
 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农业社会中人们不信任买卖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城市在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交换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手工业还是商业都不是希腊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换言之,城市的主要收入不是来自于手工业和商业。事实上,古希腊的城市不是商业化城市,无论是从严格意义上还是从非严格意义上看,城邦都没有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
这段话一方面反映了农业社会中人们不信任买卖的社会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城市在农产品和手工产品交换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是手工业还是商业都不是希腊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换言之,城市的主要收入不是来自于手工业和商业。事实上,古希腊的城市不是商业化城市,无论是从严格意义上还是从非严格意义上看,城邦都没有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
 进出口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换取生活必需品,满足城市的消费需要,而不是旨在谋求利润,雅典的粮食进口可以说明这一点。至迟从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雅典几乎每年都必须进口大量的粮食,方能满足城邦的需求。
[9]
因此,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就成为城邦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个月第四次公民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粮食供应问题。
进出口贸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换取生活必需品,满足城市的消费需要,而不是旨在谋求利润,雅典的粮食进口可以说明这一点。至迟从公元前5世纪后期起,雅典几乎每年都必须进口大量的粮食,方能满足城邦的需求。
[9]
因此,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就成为城邦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个月第四次公民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粮食供应问题。
 城邦还对市场上出售粮食的价格作了严格的规定,并专设官员管理,同时还规定进口粮食的三分之二必须在雅典城内出售,从事粮食贸易的雅典船只必须将谷物运回本土出售。
城邦还对市场上出售粮食的价格作了严格的规定,并专设官员管理,同时还规定进口粮食的三分之二必须在雅典城内出售,从事粮食贸易的雅典船只必须将谷物运回本土出售。
 与17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后所制定的航海条例不同,雅典城邦所关心的是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进口,而17世纪英国的航海条例旨在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打破荷兰对大西洋贸易的控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雅典的粮食进口贸易几乎完全控制在没有政治权利的外邦人手中。
与17世纪中期英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后所制定的航海条例不同,雅典城邦所关心的是以满足消费为目的的进口,而17世纪英国的航海条例旨在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打破荷兰对大西洋贸易的控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雅典的粮食进口贸易几乎完全控制在没有政治权利的外邦人手中。
 即是说,从事雅典最大宗进口贸易的商人并没有任何政治地位,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雅典工商业民主政治的理论。
即是说,从事雅典最大宗进口贸易的商人并没有任何政治地位,这就有力地驳斥了雅典工商业民主政治的理论。
希腊城邦社会的农业特征还反映在借贷行为中。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在古代希腊世界没有现代意义的信贷,通行的货币是银币,因其重量限制,交易的规模十分有限,任何借贷和买卖都要受到这个因素的制约。在希腊尤其是雅典,借贷是常见的现象,但借贷的目的一般都是非生产性和非赢利性的,正如奥什邦所说:“甚至在雅典……财产抵押的目的也几乎完全是非生产性的,如为女儿准备嫁妆等,贸易从来没有成为大批固定投资的对象。”
 比利时学者薄伽特在对古希腊借贷的专门研究中也只找到两个赢利性借贷的例子,而其中一个还是含糊不清的。
[10]
比利时学者薄伽特在对古希腊借贷的专门研究中也只找到两个赢利性借贷的例子,而其中一个还是含糊不清的。
[10]
上述分析充分说明,从社会的各个侧面看,希腊城邦都不是一个以工商业为主的社会,而是一个农业社会。当然这里还涉及另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古风时期希腊人的海外殖民运动。长期以来为许多学者所接受的一个看法认为,希腊殖民运动的动因和目的皆是发展海外贸易,这也影响到学者们对希腊城邦社会性质的认识,但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同样具有影响力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殖民运动的真正动因是由于人口大幅度增长而导致的土地缺乏。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无法对整个殖民运动作出完全符合历史情形的解释,贸易论无法解释为什么许多殖民地都是建立在土地肥沃、但却并不一定适于发展贸易的地方。希腊人海外殖民的两个最主要地区是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地区和黑海沿岸地区,而这两个地区在古代地中海世界都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地,这也许并不纯是巧合。据希罗多德记载,提拉岛人之所以在北非的昔兰尼建立殖民地,是因为在提拉岛发生了旱灾。
 科林斯所建立的殖民地历来被认为是贸易性质的,但科林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殖民地——西西里的叙拉古——却主要是由来自于科林斯内陆一个称作提尼亚村的农民所建立的,他们世代以农业为生,对商业并不熟悉。
科林斯所建立的殖民地历来被认为是贸易性质的,但科林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殖民地——西西里的叙拉古——却主要是由来自于科林斯内陆一个称作提尼亚村的农民所建立的,他们世代以农业为生,对商业并不熟悉。
 贸易论无法对这一系列史实作出圆满的解释。另一方面,土地缺乏的理论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首先,这个理论的前提即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人口急剧增长的假设并不可信,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拟详述。
[11]
更为严重的一点是,土地论者难以回答一个十分明显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希腊人是否需要如此大规模的殖民运动来缓解土地缺乏的压力。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人在地中海世界各地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城邦,其数量也许不少于希腊本土的城邦。有些较小的城邦如米利都和迈加拉甚至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史料中更有记载城邦无法招募到足够的殖民者,而不得不同其他城邦合作建立殖民地的例子,这些都说明土地缺乏的压力不是殖民运动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希腊古风时代的殖民运动有其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它反映了人们观念上的一次变革,其根本的原因是财产私有制的确立。
贸易论无法对这一系列史实作出圆满的解释。另一方面,土地缺乏的理论也没有足够的说服力。首先,这个理论的前提即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人口急剧增长的假设并不可信,由于篇幅限制,这里不拟详述。
[11]
更为严重的一点是,土地论者难以回答一个十分明显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即希腊人是否需要如此大规模的殖民运动来缓解土地缺乏的压力。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希腊人在地中海世界各地建立了众多的殖民城邦,其数量也许不少于希腊本土的城邦。有些较小的城邦如米利都和迈加拉甚至建立了许多殖民地,史料中更有记载城邦无法招募到足够的殖民者,而不得不同其他城邦合作建立殖民地的例子,这些都说明土地缺乏的压力不是殖民运动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希腊古风时代的殖民运动有其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它反映了人们观念上的一次变革,其根本的原因是财产私有制的确立。
 古风时代早期希腊首次出现了有关财产所有权的立法,许多城邦都制定法律,保护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财产的私有制。这种制度及观念上的变革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寻求财富的欲望,反映在考古发现上是这一时期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正如同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殖民运动一样,希腊殖民运动的动因是寻求海外的财富。因为在古代世界,土地本身即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资源,所以它无疑是殖民者所寻求的主要目标;另一个财富的来源是海上贸易,它也受到殖民者的重视。实际上这两者都是殖民者所寻求的,它们之间并不相互矛盾,但它们自身并不能构成殖民运动的根本原因。如此看来,殖民运动本身不能用来证明希腊城邦社会的商业性质,因为贸易并不是决定殖民运动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古风时代早期希腊首次出现了有关财产所有权的立法,许多城邦都制定法律,保护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财产的私有制。这种制度及观念上的变革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寻求财富的欲望,反映在考古发现上是这一时期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正如同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殖民运动一样,希腊殖民运动的动因是寻求海外的财富。因为在古代世界,土地本身即是最有价值的财富资源,所以它无疑是殖民者所寻求的主要目标;另一个财富的来源是海上贸易,它也受到殖民者的重视。实际上这两者都是殖民者所寻求的,它们之间并不相互矛盾,但它们自身并不能构成殖民运动的根本原因。如此看来,殖民运动本身不能用来证明希腊城邦社会的商业性质,因为贸易并不是决定殖民运动的唯一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
[1] 参见罗宾·奥什邦《古典时代的地貌及其数据:古代希腊的城市和它的乡村》(Robin Osborne, Classical Landscape with Figures:The Ancient Greek City and Its Countryside ),伦敦1987年版,109页;拙文《雅典民主政治新论》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把这个数字说成是500人,纯系笔误,特此更正。
[2] 《居鲁士的教育》( Cyropaedia ),VIII,2.5。
[3] 《方式与方法》( Poroi ),IV,4—6。
[4] 引自芬利:《古代经济》(M.I.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伦敦1985年第2版(1973年初版),21—22页。
[5] 马克斯·韦伯:《农业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 Agrarverhaltnisse im Altertum ”),载韦伯:《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图宾根1924年版,第1—288页,尤见第13页。参见芬利:《从古朗治到马克斯·韦伯及其后的古代城市研究》(M.I.Finley,“The ancient city from Fustel de Goularges to Max Weber and beyond”),载《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ciety and History )第19期(1977年),305—327页。
[6] 卡尔·布歇尔:《国民经济的兴起》(K. Bücher, Die Entstehung des Volkswirtschaft ),图宾根1906年第5版,371页。
[7] 关于古代经济特征及其与中世纪及现代经济特征之差别的争论,见奥斯汀和维达尔-那格主编:《古代希腊经济与社会史导论》(M.M.Austin and P.Vidal-Naquet,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ent Greece:An Introduction ),加州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导言部分。
[8] 参见芬利:《古代经济》(M.I.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加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新版(1973年初版),96页及以往。
[9] 见甘绥:《希腊罗马世界的饥荒与粮食供应》(Peter Garnsey, Famine and Food Supply in the Graceo-Roman World ),剑桥1988年版,第7章。
[10] 薄伽特:《希腊城邦中的钱庄与借贷者》(R. Bogaert, Banques et banquiers dans les cités grecques ),莱顿1968年版,第356—357页。最近的一项研究是科恩:《雅典经济与社会:借贷业的视角》(E.E.Cohen, Athenian Economy and Society:A Banking Perspective ),普林斯顿1992年版。但该书的研究结果并不影响本文的一般性结论。
[11] 人口急剧增长的理论主要由剑桥大学考古学家斯诺德格拉斯提出,见其《希腊古风时代——探索的时代》(A.M.Snodgrass, Archaic Greece:The Age of Experiment ),加州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4页。但其理论受到其弟子莫里斯的批评,见莫里斯:《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I.Morris, Burial and Ancient Society:The Rise of the Greek City-State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斯氏后来接受了这一批评,见其《考古学与希腊的兴起:早期希腊及相关问题论集》( Archae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Greece:Collected Papers on Early Greece and Related Topics (1965-2002),爱丁堡2006年版,第VIII页。参见拙著《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第4章。
如同古代社会的其他文明一样,希腊文明从根本上说是农业文明,其农业特征反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观念上看,土地被认为是最重要而且最可靠的财富资源。相应地,农业成为高贵的职业,而工商业则被看成是卑贱的职业,不符合上等人的身份,这种观念最为明显地反映在贵族阶层的社会心理中。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看,农业是社会的经济支柱,也是城邦最重要的经济来源。社会人口的绝大部分所从事的都是与农业相关的生产,而在古代希腊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从事大规模非农业生产的条件尚未具备,正如古希腊史家奥什邦所说:“在古典希腊的任何城邦中都不具备鼓励相当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人们社会与政治地位的是农业和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不是手工业和商业。希腊城邦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土地所有权和公民权以至政治权利的结合,只有公民才有权拥有土地,这也充分说明了土地和农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此相反,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位置来看,手工业和商业都处于次要的位置。首先,从对现有史料的分析来看,手工业的规模十分有限,除个别行业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的需要。其次,从希腊城市的特征及其同农村的关系来看,古代希腊城市从根本上说是消费中心和政治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正如学者们早已注意到的那样,古代希腊的城市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不同,没有组织和保护大规模、分专业的手工业生产之行会或相应的组织。城市主要依靠它的农村以及政治统治手段如税收和贡赋来满足其消费需要,它是农村的政治中心,实际上和其周围农村是一体的。城邦只有公民群体和非公民群体之分,而没有市民和农民之分。再者,城邦没有任何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只有保障城市供应的消费政策。换言之,城邦对商业赖以发展的利润并没有兴趣。最后,古风时代的殖民运动也不能归结于商业与海外贸易的发展。为许多学者所宣称和接受的“希腊城邦社会是工商业社会”的理论,实际上是没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相应地,在希腊城邦社会中不存在工商业阶层与土地所有者阶层矛盾与对立的社会基础,雅典的民主政治也不是工商业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的结果。当然,笔者在这里无意完全否认工商业的存在,只想指出工商业及工商业者阶层还没有形成一种同土地所有者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农业才是希腊城邦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它制约了城邦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把农民推到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贵族政治都如此;它决定了人们选择职业的标准,而且决定了社会的战争方式以及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农业是希腊城邦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古代希腊钱币上的装饰图案往往是农作物,而不是其他东西。
更为重要的是,决定人们社会与政治地位的是农业和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不是手工业和商业。希腊城邦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土地所有权和公民权以至政治权利的结合,只有公民才有权拥有土地,这也充分说明了土地和农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与此相反,无论是从社会地位还是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位置来看,手工业和商业都处于次要的位置。首先,从对现有史料的分析来看,手工业的规模十分有限,除个别行业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的需要。其次,从希腊城市的特征及其同农村的关系来看,古代希腊城市从根本上说是消费中心和政治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正如学者们早已注意到的那样,古代希腊的城市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不同,没有组织和保护大规模、分专业的手工业生产之行会或相应的组织。城市主要依靠它的农村以及政治统治手段如税收和贡赋来满足其消费需要,它是农村的政治中心,实际上和其周围农村是一体的。城邦只有公民群体和非公民群体之分,而没有市民和农民之分。再者,城邦没有任何旨在谋求利润的商业政策,只有保障城市供应的消费政策。换言之,城邦对商业赖以发展的利润并没有兴趣。最后,古风时代的殖民运动也不能归结于商业与海外贸易的发展。为许多学者所宣称和接受的“希腊城邦社会是工商业社会”的理论,实际上是没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相应地,在希腊城邦社会中不存在工商业阶层与土地所有者阶层矛盾与对立的社会基础,雅典的民主政治也不是工商业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的结果。当然,笔者在这里无意完全否认工商业的存在,只想指出工商业及工商业者阶层还没有形成一种同土地所有者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农业才是希腊城邦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它制约了城邦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把农民推到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无论是民主政治还是贵族政治都如此;它决定了人们选择职业的标准,而且决定了社会的战争方式以及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农业是希腊城邦社会的最重要特征。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古代希腊钱币上的装饰图案往往是农作物,而不是其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