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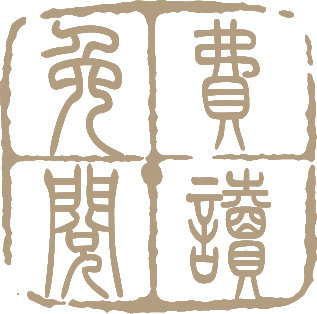
一
我为甚么我比别人多知道一点呢?总之我为甚么如此明澈?我永没有思索过不成问题的问题。我永没有浪费了我的精力。例如我就没有实际的宗教的难题之经验。至于怎样才算“犯罪”我对于这个问题已很隔膜。同样我也没有判定良心发见之可靠的标准:据我所闻,良心发现,似乎并不值得崇敬。……我不喜我的行动陷于苦境;我宁愿从评价的问题完全避去恶的影响和结果。
在恶的结果之前,人们容易失去对于一种行动的正确的观点。在我看来,良心发见好像是一种恶的眼光。失败了的事情因于失败更应当被人尊敬,这与我的伦理观更一致。“上帝”“灵魂不灭”“超度”“彼岸”——这些都不过仅仅是意想,我并不关心,我并不以此而浪费了我的时间,甚至于在幼稚时代即已如此。虽然为那或者我的幼稚还不足呢,我并不以无神论为一种结果,也不以为是一种事实,我以为即是本能的。
我是太精细,太怀疑,太倨傲,不愿让我自己满足于一切问题之暖昧而粗率的解答。上帝我是这么一种暖昧而粗率的解答。对于我们思想家,这种解答乃是一种冷峭的无礼。根本说来,上帝不是别的,只是与我们作对的一种粗糙的戒律:你们不应当思想!倒是我注意到别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比任何神学的探究更解决了人类得救的问题:即营养的问题。
这问题可以这样排定:那不是很正确的么,你必须营养你自己,使你的最大的力,文艺复兴式的奇珍(Virtu in the Renaissance style),超伦理观之道德,充分发展?这里,我的经验是很坏的;我很诧异我这么久才注意到这个问题,才从我的经验得到了理解。我是如此的落后,我的无智差不多类于圣德:这只有德意志文化之全无价值之理想主义,才能解释了这事实。
因为这种文化,始终教人抹杀了现实,而追求一种可疑的,所谓理想的鹄的,例如所谓“古典文化”。好像我们之努力企图将“古典的”和“德意志的”连合为一概念,不是开端就已注定了似的!
甚至于那也是一种小小的滑稽,试想想来卜兹
 的一个受过古典教育的公民罢!真的,我承认我直到了壮年,我的食品都十分不良。用伦理的名词说出来,即我食的是“我个人的”“无私的”“博爱的”,这是厨夫和别的基督教朋友所矜夸的。例如我为来卜兹的烹调,和等一次叔本华
的一个受过古典教育的公民罢!真的,我承认我直到了壮年,我的食品都十分不良。用伦理的名词说出来,即我食的是“我个人的”“无私的”“博爱的”,这是厨夫和别的基督教朋友所矜夸的。例如我为来卜兹的烹调,和等一次叔本华
 的研究(1865年)便严重地否认了我的“求生的意志”。
的研究(1865年)便严重地否认了我的“求生的意志”。
结果,成为营养不良和败坏了胃腑——在我看来,上述的这种烹调法好像已经可惊地解答了这个问题。(据说1866年那里的教育有了改变了。)但说一般德国的烹调说,它甚么不与良心有交涉呢?先汤后菜(这在十六世纪维尼斯人的食谱上仍称为德国式),肉食蒸烤得没有了香味;菜蔬与油和面粉同煎;肉饼摊得如同压条!除此以外,还有古代人,不单是古代德国人——兽性似的正餐后的许多习惯。
你由此可以明白德国人的知性是从甚么地方来的——从不规则的胃腑中来。德国的智性说是不消化;它不能同化任何东西。但与德国相反,甚至于英国底饮食,真的,还有法国的饮食,在我看来,也好像是返于自然,即返于饕餮主义——也根本与我的性质不合。即饮食好像给智性以沉重的脚,英国妇人的沉重的脚。
……最优良的烹调,却是巴德蒙
 人的烹调。烧酒不对我的口味;一天喝一两杯葡萄酒,或啤酒,已足使我的生命坠到眼泪之谷;——所以,在摩尼支
人的烹调。烧酒不对我的口味;一天喝一两杯葡萄酒,或啤酒,已足使我的生命坠到眼泪之谷;——所以,在摩尼支
 城住是我自己的对头。承认我理智底地理解这事很晚,但却在仅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已有了它的经验了。
城住是我自己的对头。承认我理智底地理解这事很晚,但却在仅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已有了它的经验了。
在少年时,我即相信饮酒,抽烟,最初是少年人的虚荣,后来则成为坏习惯。或者,纳闷堡的酒,对于这种苛刻的批判,要负一部分责任的。相信酒是一种刺激,我将不能不是一个基督徒。换句话说,我不能不相信那在我觉得是矛盾的事情。但更奇特的,乃是少量的淡酒,使我沮丧,大量的烧酒,却使我行动兴奋,如同在海天中的水手,这在少年时我最勇敢。
一夜中写成而且抄好一篇很长的拉丁论文,笔下驰骤着奢望,想效法了沙鲁斯
 的严整而简炼,于是以强烈的烧酒最鼓舞了这种精神——这先例,当选在布夫塔
的严整而简炼,于是以强烈的烧酒最鼓舞了这种精神——这先例,当选在布夫塔
 的尊严而古老的学校当学生时,不见得与我的生理不合,沙鲁斯也一样,——但那却是庄严的布夫塔所不会赞成的。
的尊严而古老的学校当学生时,不见得与我的生理不合,沙鲁斯也一样,——但那却是庄严的布夫塔所不会赞成的。
其后到了中年,我渐渐坚决地反对了精神的沉酒:我一个从经验上反对素食主义者,规劝过我的R.瓦格纳也一样,还不够以充分底严肃劝告一切精神质的人绝对地禁绝了烧酒。其实清水也可以满足了同一的目的。
……我宁喜欢有着许多机会,可以饮啜奔流的山泉的地方,如尼斯
 ,如都林
,如都林
 ,如锡尔斯
,如锡尔斯
 那里,我到了那里,水流到那里。“酒中有真理”(in vino Veritas),在这里,我好像与世界关于真理的概念也不一致。——在我,则是精神飘动于水面。这里,再从我的伦理观引出一些劝告。一顿大餐,比小食更容易消化。优良消化的第一条件,乃是胃腑全部活动。因此人应当知道他的胃的容积。
那里,我到了那里,水流到那里。“酒中有真理”(in vino Veritas),在这里,我好像与世界关于真理的概念也不一致。——在我,则是精神飘动于水面。这里,再从我的伦理观引出一些劝告。一顿大餐,比小食更容易消化。优良消化的第一条件,乃是胃腑全部活动。因此人应当知道他的胃的容积。
同理我也反对太无限制的饮食,那我称之为不间断的祭献筵席,旅馆中的饭食即是如此。两餐之间,甚么也不用,不用咖啡——咖啡使人沉闷。茶宜清晨,少量而味浓。茶太淡了,那会有害,且使你终日不快,这里,各人在狭窄而精细的限度之间,各有自己的标准。在可厌的气候,早间饮茶是不宜的:在一小时前,饮一杯没有奶油的呵呵茶,却极有益。少坐;别想不生于光明及自由运动中的思想,也不使筋肉松懈。
一切偏见,都可以从胃腑中追溯到它的根源。如同我随时说过的一种久坐的生活,才是违反圣灵的真实的罪恶。
二
这营养的问题也密切地与地点和气候的问题相关连。人不能随地生活:要使用他所有的精力做伟大工作的人,在这一点,还必须有着一定限度的选择。气候对于身体的功用的促进和阻止其影响如此之大,所以地点和气候的选择,如不当,不单使人对于自己的工作疏远,且可使他完全抛开。人之生物的生力,永不能扩大到他极端奔放自由的境地,使他可以对自己说:我,唯我一人能做这事。
……最轻微的胃腑的麻痹,一度成为习惯,已足够使天才成为凡庸,成为德意志人;惟有德国的气候十分不能促进最强毅,最雄健的胃腑。精神之步履之迟速密切地依于身体作用之节拍;真的,精神之自身,也不过这些身体作用之一种形式罢了。试枚举伟大天才所产生的地方,那里机智、精敏、和谐谑,成为幸福之一部;那里差不多必然地是天才之家:那些地方,都有着一种非常高朗的空气。
巴黎、波罗温斯
 、佛罗林斯
、佛罗林斯
 、耶露撒冷、雅典,——这些地名,都证明了这天才都靠着高郎的空气,靠着澄明的天空。——换句话说,天才都靠着迅速的官能作用,靠着继续得到自己的伟大而多量的精力的那种可能。我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便:一个特立而自尊的人,突然因为失去了对于气候的感觉,成为狭隘而委备的专家;成为一个白痴。假使我的疾病没有迫着我趋于理智,现实底地趋于理智之深思,我也会走到这样的末路的。
、耶露撒冷、雅典,——这些地名,都证明了这天才都靠着高郎的空气,靠着澄明的天空。——换句话说,天才都靠着迅速的官能作用,靠着继续得到自己的伟大而多量的精力的那种可能。我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便:一个特立而自尊的人,突然因为失去了对于气候的感觉,成为狭隘而委备的专家;成为一个白痴。假使我的疾病没有迫着我趋于理智,现实底地趋于理智之深思,我也会走到这样的末路的。
现在长久的实验,已教会我从自己内省,如同从一种精密可靠的仪器知道了气候和天象的影响。所以,我能够依于这种生理的自己内省,测算出温气变化的度数,甚至于在由都灵到米兰
 这短短的旅程。因此,我想到这可怕的事实,我的全生命直到最近十年,最危险的十年,总是在不适宜的地方度过,在那些正应当为我而销闭起来的地方度过。
这短短的旅程。因此,我想到这可怕的事实,我的全生命直到最近十年,最危险的十年,总是在不适宜的地方度过,在那些正应当为我而销闭起来的地方度过。
纳闷堡、布夫塔、都林治亚
 来卜兹、巴色尔、维尼斯,这多这多不适宜于我的体质的地方。所以我没有童年时代欢欣的回忆,以这归于所谓伦理的原因木免愚昧,例如无可否认的缺乏朋友:这在现在和以前仍是一样,但也没有阻止我成为快乐和勇敢。但是对于生理之无智,那种混沌的“理想主义”,这才是我的生命之真实的灾害,是它的多余而无用的成分。
来卜兹、巴色尔、维尼斯,这多这多不适宜于我的体质的地方。所以我没有童年时代欢欣的回忆,以这归于所谓伦理的原因木免愚昧,例如无可否认的缺乏朋友:这在现在和以前仍是一样,但也没有阻止我成为快乐和勇敢。但是对于生理之无智,那种混沌的“理想主义”,这才是我的生命之真实的灾害,是它的多余而无用的成分。
那不会发展出优良的东西来,因为不能有了结也不能有抵补。这“理想主义”的结果说明了一切的错误,说明了本能之最大的反常,说明了使我离开了我的生业的那种“特别谦恭”;例如我之成为一个语言学者,为甚么不成为医生或至少可以使我睁开眼睛的别的人物呢?当我住在巴塞尔的时候,我的全部智力的运用,包括了我每日的日程,都是非凡能力之无意义地滥用,对于能力的消耗没有一种补充,甚至于也没有想到这能力的耗竭和增添的问题。
我没有精敏的自我,没有强烈的本能所给与的自卫;我认一切人与我相等,我是“无关心”,我忘却我与别人之间的距离。总之,我是在一种我永远不能饶恕我自己的状态之中。当我差不多走到了末路,我才开始反省到我的生活的根本乖谬——“理想主义”。疾病最先恢复了我的理智了。
三
对于营养之选择,对于气候和地点之选择;第三件事则是关于营养或恢复人,也是不当疏忽了的。这里,依于精神所适宜的限度,即于他有益的范围,是很狭窄的。在我则读书也是一种休养的方法;那常常使我离开了我自己,漫游于我所不看得太严肃的陌生的学科和陌生的灵魂之中。真的,读书使我从我的严肃中得到恢复。
当我在最深劳作的时候,我左右没有一本书,我不许任何人在我的面前说话,或甚至于默想。因为那便等于读书。……有人注意到,当在最紧张的时候,思想的孕育裁判着精神和感官,意外和各种外界刺激,其作用是太猛烈太深入了么?人必须尽其所能避免了意外,和外界刺激:精神的孕育之第一天性的防卫,就是一种自筑保垒。
我将让一种不相干的思想,秘密地爬过了这围墙的么?假使如此,那也便是读书。……在工作和创作之后,就是恢复!在我,你们快乐的明智的颖睿的书籍啊!但那当是德国书么?……我必须回溯到六个月以前,我拿着一本书在我的手里。那是甚么书?V.波罗查德
 的一本杰作,希腊的怀疑学派。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Laertiana
的一本杰作,希腊的怀疑学派。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Laertiana
 却给我很大的帮助。
却给我很大的帮助。
啊,怀疑学派!正是两面的是呀,多面的族类即哲学家间的最尊贵典型!……在另一方面,我差不多总是藏身于这同类的书籍之中,这少数的,恰恰适合我的需要的书籍。或者不愿读许多的书,或多类的书,乃是我的本性:一种图书馆使我头痛。我的本性也不爱许多的东西,或多类的东西。在我的天性中对于新书的怀疑,甚至于仇视,胜过于“忍耐”“内心的探索”“邻人爱”等等。
……最后,我浸沉于几个法国的名作家;我只相信法国文化,我以为欧洲的别的一切自称为文化的,都是纯粹的误解。德国的变种是不必说的了。……我在德国所发现的较高文化的几个例证,都是渊源于法国,例如哥西马·瓦格纳夫人
 ,她就有着我自来所没有听见过的关于赏味的最超越的判断。
,她就有着我自来所没有听见过的关于赏味的最超越的判断。
即使我不说读过;但还可以,说我爱着巴斯克
 因为他是对于基督教的最足般鉴的牺牲,缓慢地自杀,先见肉体,其后是心,依于非人性的残酷之最可恐怖之逻辑;好像,我有些蒙太尼
因为他是对于基督教的最足般鉴的牺牲,缓慢地自杀,先见肉体,其后是心,依于非人性的残酷之最可恐怖之逻辑;好像,我有些蒙太尼
 的怀疑在我的灵魂里,谁知道呢,或者也在我的肉体里。也好像我对于艺术家的赏味,努力拥护莫里哀
的怀疑在我的灵魂里,谁知道呢,或者也在我的肉体里。也好像我对于艺术家的赏味,努力拥护莫里哀
 、柯纳尔
、柯纳尔
 和拉逊
和拉逊
 ,而而辣地反对如莎氏比亚
,而而辣地反对如莎氏比亚
 那样狂肆的天才。但这些都不能阻止我将近代法兰西人,当作了我的可爱的伴侣。
那样狂肆的天才。但这些都不能阻止我将近代法兰西人,当作了我的可爱的伴侣。
在历史上我不能想像有这样一个时代,比现在的巴黎还有着这多的,更是好奇而精细的心理学家了。我可以随便列举几个人,因为他们的数量是颇不少的,如P.波格特
 、P.罗蒂
、P.罗蒂
 ,如则朴,如麦尔罕
,如则朴,如麦尔罕
 ,如A.法朗士
,如A.法朗士
 ,如J.拉马特尔
,如J.拉马特尔
 ;或者举出一个强盛种族中的特出的人,一个真正的拉丁人,为我特别喜欢的,——G.D.莫泊桑
;或者举出一个强盛种族中的特出的人,一个真正的拉丁人,为我特别喜欢的,——G.D.莫泊桑
 。
。
在我们之间,我喜欢这世纪宁是我喜欢这世纪的被德国哲学所败坏了的那些大师,(例如泰纳
 即被黑格尔所败坏,他因于泰纳而生出对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物之误解)。德国伸张到那里,即败坏了那里的文化。
即被黑格尔所败坏,他因于泰纳而生出对于伟大时代和伟大人物之误解)。德国伸张到那里,即败坏了那里的文化。
最先拯救了法国精神的是战争。……斯坦达尔

 即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偶然的遭遇。因为那生命中成为时代的一切于我都是偶然的遭遇,而不是由于称誉。斯坦达尔的先觉的心理学家的眼光,对于事实的把捉,对于伟大事业者之联想,都是无可估价的;最后,但不是至少,如同一个正直的无神论者一样,一但在法国极少也是很难发见的典型,可算是P.麦里来
即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偶然的遭遇。因为那生命中成为时代的一切于我都是偶然的遭遇,而不是由于称誉。斯坦达尔的先觉的心理学家的眼光,对于事实的把捉,对于伟大事业者之联想,都是无可估价的;最后,但不是至少,如同一个正直的无神论者一样,一但在法国极少也是很难发见的典型,可算是P.麦里来
 的光荣!
的光荣!
或者,我甚至于嫉妒斯坦达尔么?他检去了在一切人之中我所能作的最佳的无神论者的嘲笑:“上帝之唯一的可饶恕,就是上帝并不存在。”我自己在甚么地方也说过:自来,谁是生命之最伟大的反对者?——上帝。
四
给我以抒情诗人之最高的极念的是海涅
 。我不能在一切时代的领域中,觅出与他的甘美而热情的音韵相等的东西。他有着神性的放肆,没有这放肆,我不能感受到完全;我评价人和种族总是看他们如何想像到一个有着牧神之性质的神人。并且他是如何操纵自如地应用了德国文字啊!
。我不能在一切时代的领域中,觅出与他的甘美而热情的音韵相等的东西。他有着神性的放肆,没有这放肆,我不能感受到完全;我评价人和种族总是看他们如何想像到一个有着牧神之性质的神人。并且他是如何操纵自如地应用了德国文字啊!
有一天人们将说惟海涅和我自己是德国文字的最伟大的艺术家;我们超过了纯粹德国人所能对于德文的应用不可以道里计。我必是很深地和摆伦的曼佛来德
 有关系:在十三岁的时候,我对于这本书已很理解,——我在我的灵魂中,发见了他的所有的深处。在曼佛来德之前,敢于说起浮士德
有关系:在十三岁的时候,我对于这本书已很理解,——我在我的灵魂中,发见了他的所有的深处。在曼佛来德之前,敢于说起浮士德
 的人,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有侮蔑地一瞥。德国人不能胜任于伟大的概念——证之于苏门
的人,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有侮蔑地一瞥。德国人不能胜任于伟大的概念——证之于苏门
 罢!
罢!
因不满于这个伤食的撒克逊人,我曾为曼佛来德写了一篇反对的序曲:据H.V.布罗
 说他从来没有见这样的文字,那是对于欧特尔比
说他从来没有见这样的文字,那是对于欧特尔比
 内一种冷峭府袭击。要觅出对于莎氏比亚的我的最高的评骘,我永远只觅到了这:他想像到凯撒的典型。这样的东西,人是不能想像的:是物而又非物。这伟大的诗人仅仅是从自己的经验中引出来,——甚至于到后来他不能再支持了自己的工作了。
内一种冷峭府袭击。要觅出对于莎氏比亚的我的最高的评骘,我永远只觅到了这:他想像到凯撒的典型。这样的东西,人是不能想像的:是物而又非物。这伟大的诗人仅仅是从自己的经验中引出来,——甚至于到后来他不能再支持了自己的工作了。
……在看了我的查拉斯图拉之后,我来回地在我的屋子里蹀躞了半点钟,不能制止自己的悲观。我再没有比读莎氏比亚的书还要碎心的了:为甚么他在表演这主角的时候,却这大的受苦!汉姆来特
 被理解了么?不是怀疑,乃是确定迫人发狂。但要感觉到这自己必须是深沉的,尔邃的哲学家。
被理解了么?不是怀疑,乃是确定迫人发狂。但要感觉到这自己必须是深沉的,尔邃的哲学家。
……我们都恐惧着真理。质言之:我本能地的感觉到培根
 乃是这种最惊怖的文学之创始者,自我凌虐者:我为甚么顾顾虑到亚美利加的笨伯和小聪明者的可鄙的喋喋呢?构想伟大现实的能力,不单是与行为上的伟大现实与神怪与罪恶相关联,它也实际底地是后者的前提。
乃是这种最惊怖的文学之创始者,自我凌虐者:我为甚么顾顾虑到亚美利加的笨伯和小聪明者的可鄙的喋喋呢?构想伟大现实的能力,不单是与行为上的伟大现实与神怪与罪恶相关联,它也实际底地是后者的前提。
我们还不能十分理解培根——现实这个字的最高意义的现实者,不能理解他所做的一切,所愿望的一切,和他自己所经验的一切。……那些批评家都滚开罢!试想我如果不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我的查拉斯图拉,例如以瓦格纳的名字,那末两千年的观察,也不能猜想到那人类太人类了作者乃是查拉斯图拉的梦想者。
五
说到我的生命的恢复,我不能不说一两句话来感谢那给与我最伟大,最热情的振作的一事。这无疑就是我和R·瓦格纳的深交。我与别的人们相与很滇漠;但我愿我的生命永不要抛弃了我在特里斯镇(Tribschen)的那些日月,——信仰而欣快,而清华煜耀的日月,最渊穆的瞬间。我不知道别人看瓦格纳是怎样;但总没有云影来掩蔽了我们的天空。
这使我又要说到法国。我和瓦格纳派,和那些相信瓦格纳如同自己一样而崇拜瓦格纳的人,对于他们我没有争论,我只是侮蔑地抿一抿嘴唇。我的生性与一切条顿人的东西都隔膜,只要见到一个德国人就足以停滞了我的消化,所以最初一接触到瓦格纳,也是在我生命中最初自己呼吸的瞬间:我认识他,我尊敬他,如同一个外国人,如同反德意志道德的对照和化身。
我们都在孩子时代呼吸了五十年代的潮湿气,必然地对于德意志这个观念是悲观者;我们除了革命而外不能做别的,我们不能同意于伪善者所统制着的现状。无论这伪善者显现着不同的颜色,无论他是纡金拖紫,或着轻装,在我看来都是一样。那末好啊!瓦格纳也是一个革命者,他逃离了德国人。
……这艺术家除了巴黎以外,在欧洲没有住处;作为瓦格纳的艺术之条件的五官的精敏,对于色彩之感觉,对于心理的病态,这些都只有在巴黎才能觅到。再没有别的地方有着对于形式问题的热狂,有着对于舞台布景之严肃,只有巴黎人的严肃是卓绝的。在德国人不会有巴黎艺术家灵魂中的那种急切的热望。德国人是天性驯良的。但瓦格纳并不天性驯良。
……我已经说得很多了关于瓦格纳和那些他最密切关系着的人属于那一派这个题目(参看《超乎善恶之外》二六九节)。他是一个后期的法国浪漫派,所以高翔而飞跃的艺术家的乐队,如德拉克鲁士
 与伯里阿兹
与伯里阿兹
 都是患了不治之症,是表现之纯粹的空想家,是彻头彻尾的艺术之意匠。
都是患了不治之症,是表现之纯粹的空想家,是彻头彻尾的艺术之意匠。
……谁是瓦格纳的第一个睿智的门徒?C.波特来尔
 他是第一个理解德拉克鲁士的人,这典型的颓废派,在他之中,全世纪的艺术家都认出了自己,或者他也是他们中的最后的一个。
他是第一个理解德拉克鲁士的人,这典型的颓废派,在他之中,全世纪的艺术家都认出了自己,或者他也是他们中的最后的一个。
……我所不饶恕瓦格纳的是甚么呢?就是他卑躬屈节于德国人——他成为一个德意志国民。德意志伸张到那里即败坏了那里的文化。
六
细想起来没有瓦格纳的音乐我不能恢复了我的青春。因为我好像已被德国社会宣告死刑。人要除运河了自己感情上的不可忍耐的迫压,不能不饮用麻醉乐剂。好罢,所以我不能不欣赏了瓦格纳。瓦格纳正是一切德国的抗毒素——他是一种鸩毒,我不争辩。从特里斯登
 在钢琴上上奏的那一瞬间,谢谢H.V.布罗罢!我也是一个瓦格纳派了。
在钢琴上上奏的那一瞬间,谢谢H.V.布罗罢!我也是一个瓦格纳派了。
我以为瓦格纳以前的作品都在我之下,它们大庸俗“大德国的”了。但直到此时,我仍然追求着一种惊险的,在急切而哀艳之无穷足以与特里斯登相等的作品;但没有。所有L.D.维西
 之美妙。也以特里斯登之第一声而失去其光彩。那绝对地是瓦格纳的极峰的作品;优胜之歌者和指环
之美妙。也以特里斯登之第一声而失去其光彩。那绝对地是瓦格纳的极峰的作品;优胜之歌者和指环
 对于他们是下坡了。要成为更健全,对于瓦格纳那样的天才反是一种退步。
对于他们是下坡了。要成为更健全,对于瓦格纳那样的天才反是一种退步。
我以为生当其时,尤其是在德国人中间成熟了这样的作品,却是第一等的幸运:我的心理学家的好奇心这样强烈地主张。对于没有充足的健全足以纵情于地狱之狂欢的人,世界成为窘苦:于是希望甚至于祈求着神秘之形态。
我以为我比任何人更了解瓦格纳的块伟奇异,要达到这新奇狂喜之五十重天,除非有了十分强健羽翮的人是不能的;因为我现在还有这充足的力,能使最眩惑而惊险的事物于我有益,因此更增强了我的力,所以我称瓦格纳为我的生命之最伟大的恩人。
使我们结合的是这事实,我们比这世纪的大多数人能忍受更大的痛苦,甚至于在彼此的手里;这将使我们的名字永久不能分开。恰如瓦格纳在德国人中仅仅是一种误解,我自己也一样,并将永久如此。我的国人哟,你们要理解我们,必须先有两百年的心理学和艺术的训练!……但可惜你们已不能使时光倒流了。
七
对于很特出的读者,我应当说一句,我对音乐的真实底要求是甚么。音乐应当如十月之午后明丽而幽深。音乐应当是奇特,诡谲而温柔,如同一个放肆,而雅丽,而娇小丽美的女人。……我永不相信德国人能懂得音乐是甚么。被称为德国的最伟大的音乐家都是外国人,——是斯拉夫人、克罗支人、意大利人、丹麦人、或犹太人;或者如H.苏支
 、拜哈
、拜哈
 、和汉德尔
、和汉德尔
 他们是强健种族的德国人,是现在已经消灭了的族类。
他们是强健种族的德国人,是现在已经消灭了的族类。
我特别推崇萧班
 或者我仍然有着十足的波兰人气质。此外有三个理由除开瓦格纳的塞格弗来德·伊德尔
或者我仍然有着十足的波兰人气质。此外有三个理由除开瓦格纳的塞格弗来德·伊德尔
 或者还有里斯
或者还有里斯
 的少数作品,后者曾以他的乐队之高贵底节奏胜过了一切别的音乐家的。最后也除开了阿尔卑斯山之彼面——即是阿尔卑斯山之“这边的”。
的少数作品,后者曾以他的乐队之高贵底节奏胜过了一切别的音乐家的。最后也除开了阿尔卑斯山之彼面——即是阿尔卑斯山之“这边的”。
我不愿忘却了罗色尼
 至少不愿忘却我的南方的音乐即维尼斯作曲家P.格斯蒂
至少不愿忘却我的南方的音乐即维尼斯作曲家P.格斯蒂
 的音乐。当我说阿尔斯山的彼面我的真实的意思只是维尼斯而已。要寻求音乐的别名,我必然只有想到维尼斯。我不知道热泪与音乐的分别。我不知道如何想到了欢欣和南方而不无恐惧之战慄。
的音乐。当我说阿尔斯山的彼面我的真实的意思只是维尼斯而已。要寻求音乐的别名,我必然只有想到维尼斯。我不知道热泪与音乐的分别。我不知道如何想到了欢欣和南方而不无恐惧之战慄。
在黑夜中
我独立桥头。
远处传来了歌声,
如黄金之雨滴,
飘洒在灿烂的天之边陬。
远远游漾于黑暗之中,
音乐的沉醉,是光和小舟。
我的灵魂也如一具兹琴,
在无声地弹奏,
奏着舟子之曲,
有人听到了么?
我心欣愉而悠悠。
八
所有这些一切,如饮食、地点、气候、和休养之选择,皆为自我保存的本能所支配,更分明地说,便是一种自卫本能。限制自己的视听,使自己不和别的一切接近,这便是根本的明哲,这便是人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的证明。这自卫的本能通常又叫作赏味。当在用“是”来表示了无兴味的地方,不但不希望说“否”,甚至于尽其所能地不说“否”。人必须离开了逼迫人一再说否的一切事物。
这理由就是一切自卫的精力的浪费无论怎样轻微,当已成为习惯和定则,总是莫大而又绝对无用的损失。我们的精力之最大的浪费,总是包括了这些小而频数的耗损。保全自己,抵拒一切,便是一种精力之浪费,是一种纯然用在消极的用途的浪费,——在这点请看清楚了罢!仅仅生存之不断的,必需的防卫,已可使一个人疲弱,以至于不能自存。
试假想我走出了我的屋子,我是在一个德国的小城市而不是在幽静而华贵的都林;我的本能将用尽全力抗拒着从这个堕落而卑怯的世界所侵入的一切。或者假想我走到了一个德国的码头,那里一无所有,除了将无论好坏的东西输入而外。要抵抗这一切,我不是要成为一个刺谓么?但棘刺便是力之浪费,一种二重的奢侈,倘若无需棘刺只需伸出了两手。……
明哲和自卫之别种形式,是尽其所能地不反应,只是从剥夺了“自由”和自主,使自己的反应成为无意义的环境和条件之中逃出。这样的一个最佳的典型可以读书来说。除了浸沉于书籍之海不做别的事情的学者——一个语言学家,平均每天要翻阅两百本书籍,最后则是完全失去了为自己而思考的才能。除非有一本书在手里他不能思考。当他思考,他只是反应一种刺激(他所看到的另一种思想),结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反应。
学者专力于肯定,否定,成批评已经想过了的思想,他便不再思考了。……在他的心中,自卫的本能已经薄弱,否则他也要排拒了书本。学者乃是一个颓废派。我亲眼见过天秉聪俊而意志活泼的人在三十岁的时候已经成为书虫,如同洋火一样,必须磨擦才会发光或者说“思考”。在清晨,在曙晓,在生气洋溢,精力正旺的时候而读书——这是严厉的罪过啊!
九
在此我不能不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自己如何完成了自己。”我触到了自己保存之技艺的要点——自私。假使我们认为自己的生业,自己之生业的决定和命运,尊严地超越于一般的计划,那末再没有比以自我面对面地和这种生业相并列还危险的事了。自己完成自己的这事实,必须以自己对于自己毫不怀疑为前提。
从这种观点说来,甚至对于生命中之失败,暂时的乖离和反常,踌躇和怯懦,在无目的的作为中所消费了的严肃,都有着一种独特的意义和评价。在这些事件之中,生出的伟大智慧,或者反是最高的智慧。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知”很有理由走到毁灭,到自己忘却,到误解,到渺小,到平凡,到狭隘和庸俗。用伦理的名词说出来:爱邻如己,舍己为人,也是最强毅的自我生存的一种手段。
这是很例外的事,我反于我的习惯和信仰倾向于“无私”,因为在这里无私便是服役于自私和自己锻炼。全部良知的表面——因为良知就是一层表面,必须从伟大的专断解放。甚至于也提防一切言语和姿态罢!它们都有使本能“自知”太早的危险。同时在心灵深处渐渐生出组织的,成为主体的观念。它开始支配,引导你慢慢地从你的乖离和反常归来,给你准备着整个之完成所不可缺乏的德性和能力。
在它还没有低语着许多大问题如“目标”“目的”和“意义”之先,它也渐渐地培养着一切有用的才能。从这方面看起来,我的生命是很值得惊奇的。因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必需要一个人所不能全有的更多的才能;尤其是必需要不与才能和妨碍相破坏的相反的才能。在才具中之位次;相当隔离之技艺;不含混;不妥协;绝对复杂而不纷乱。所有这些,都是第一的条件,我的生性中长久潜藏的工作和计划。
本能之高尚的保障,表现得如此之强,所以我不能预感我心中正滋长着甚么,直到一切成为圆满成熟,有一天突然地暴露而进发出来。我不能想出我的劳苦的证据,我的生命中没有挣扎的痕迹;我是一种英雄气质之反面。
“意愿”某种东西,“贪求”某种东西,心中有着“大目的”和“大愿望”——我从经验上并不知道这些事情。在这最切要的瞬间,我眺望着我的将来,一种广大的将来啊!——如同眺望着一片宁静的大海:并没有热望搅扰了它的清澄。我没有与现状不同的最轻微的愿望;我自己并不希望异样。
……我总是这样:我永没有过一种欲求。我到了四十四岁之后敢于说没有为名誉妇人金钱苦恼过,这并不是说我缺乏了这些!这情形如此,例如一天我成为大学教授了,这样的观念我从没有预想过,因为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四岁。又如在两年前由于我的最初的言语学论文,应于我的先生吕查尔
 出版的“莱茵博物院杂志”的要求,我成为言语学家了。
出版的“莱茵博物院杂志”的要求,我成为言语学家了。
我至诚敬地说,吕查尔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纯粹的学者。他有着我们都林人所特有的谦卑,那甚至于可以使一个德国人同情——要达到了真理我们宁愿走着迂回的路。但这几句话对于我的都林的同乡即睿智的L.V.郎克
 ,也不是例外。
,也不是例外。
十
这疑问会引起来的罢:为甚么我叙述了这些平凡的琐事,无意义的琐事。在通常的标准,假使我的命定要去从事伟大的工作,这好像还于我有损。但我的回答是我以为这些平凡的琐事——饮食、居处、气候、休养、自爱之全部事件,都是想不到地比自来人类认为重要的一切更重要。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开始重新学习。人类自来所严肃称道的都不是真实的。
那仅仅是空想,或者严格地说那是从病之恶性,从最深有害的天性中发出来的谎骗,——所有这些概念如“上帝”“灵魂”“道德”“罪恶”“彼岸”“真理”“永生”等等。……但人类在其中追求人性之伟大,追求人性之神圣。一切政治问题,社会秩序问题,教育问题,都是根本错误,因为将最有害的人当作最伟大的人,因为邈视了这些“琐事”,更正确地说邈了在生命中是最根本的事。
假使我现在将我自己和自来被尊视为人类中“第一等”的人物互相比较,这不同之点是很显然的。我不认为这所谓第一等的人是人类。在我,他们是人类的废物,是疾病,和恶念之产品;他们是妖怪,是生命之腐败,不可救药,和自己复仇。……我就是他们的最极端的反对者。这是我的特权:极锐敏地感到任何健全的本质之征兆。在我心中没有一点病的痕迹。即使在严重的疾病的时候,我心中还是不病;你们将不能在我的天性中觅出幻想的证据。
无人能指出我生命中的这瞬间我曾经有过一种傲慢或感伤的态度。感伤的态度并不属于伟大;装模作样的人是虚伪的。……提防着一切绘画中的人物罢!在我当生命从我要求最大的劳苦,生命反觉得更容易。无论何人只要能看见我这年秋季的七十日中怀着对于未来的责成,不断地从事于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最高典型的工作——即知道我心中没有一些紧张,正相反,我有着洋溢的新鲜和愉快。
我的饮食没有再快乐的了,我的睡眠没有再甜酣的了。我除了如同游戏一样去从事于伟大的工作不知道别的:这便是伟大之征兆,是伟大之根本先决条件。最轻微的促迫,一种忧郁的面容,任何悲沉的声音,这些都对于人有碍,尤其是对于他的工作!……人必不要有神经。甚至于从孤独感到的苦痛也是有害的。我感受痛苦的唯一的事,是热闹,是我自己的灵魂之无限的变化。
在稚弱的七岁时候,我已经知道了没有人类的话可以入耳:但有人看见我忧闷了么?现在我仍然对于一切人富于爱情,我甚至于充满了对于最卑微者的恻隐:在这之中,是没有丝毫的傲慢或侮蔑的。
我蔑视谁,谁便知道被我所蔑视;我的生存使有坏血液的人感到嗔怨。我规定人心中之伟大是“知命”:人应当不希望改变了甚么,无论在将来,在过去,在永远。他不单是必须支持必然,也必须爱着必然。不应当无故逃避。所以一切理想主义在必然之前都是虚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