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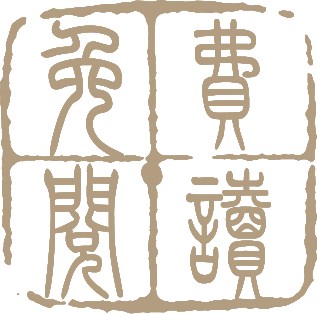
一
我的生存之幸福之独特的性质,乃在于它的宿命之中:以一种谜语的形式说出来罢!如同我的父亲,我已经死了,如同我的母亲,我仍然存活,并且长成。这二重起源,正如生活之梯阶的最高级和最低级,一种颓废和一种上升,这也可以说明了我所以特异于人的那种独立性,那种对于一般人生问题之无偏见,我比在我以前的任何人对于上升和颓废的最初的表征更敏感。在这范围内,我是卓绝的——我知道两方面,因我就是两方面。
我的父亲在三十六岁时死去,他是高雅、仁爱、而多病,一个命定不能终其天年的人。一个生命之悦乐的回忆者,而非生命之自身。在他的生命委落的那年岁,我的生命也低抑下去:我在三十六岁的时候,我的生命力落到了它的最低点。我虽然生活,但我不能看出我面前三步远。在这时候,在一八七九年,我辞去了我在巴塞尔
 的教授职,一整夏住在摩里兹
的教授职,一整夏住在摩里兹
 ,如同一个影子,在纳闷堡
,如同一个影子,在纳闷堡
 过了这年的冬天,也是如同一个阴影,我的生命中最黯淡的时候,《漫游者和他的影》
过了这年的冬天,也是如同一个阴影,我的生命中最黯淡的时候,《漫游者和他的影》
 便是这个时期的产品。
便是这个时期的产品。
所以这无疑的,这时我对于影子很熟习的。这年冬天我在日诺亚
 最初的冬天,也差不多在一种血与筋肉的极端贫弱所伴着的神志的陶然和激昂中,写下了白天的曙晓(The dawn of day)这本书里所反映出的完全的光明和活泼,甚至于精神的洋溢,在我看来,不单是与最深的身体的弱点相结合,也与过度的苦痛相结合了。
最初的冬天,也差不多在一种血与筋肉的极端贫弱所伴着的神志的陶然和激昂中,写下了白天的曙晓(The dawn of day)这本书里所反映出的完全的光明和活泼,甚至于精神的洋溢,在我看来,不单是与最深的身体的弱点相结合,也与过度的苦痛相结合了。
在七十二小时的头痛和呕吐所引起的苦闷之中,我有着非凡的辨证的精明,并纯然冷血地思索万物,那是我在最健康的瞬间不能有这充足的精敏,这充足的冷静,这充足的崇高去想到了的。我的读者当知道我如何地以辨证为一种颓废之表征,例如最著名的如苏格拉底的事件。
一切智性的病态的纷扰,甚至于热病之后的昏迷,在这些日子对我都极生疏;要明白它的本质和习性,我不能不涉览渊博的著作。我的血液循环是很迟缓底。无人能诊察出我心中的热病。一个有时候以为我是神经病患的医生,最后告诉我:“错了,你的神经没有病;我自己才是有了神经病了。”他们不能发现我的局部的败坏,或胃组织的病患,但我所苦恼的消化不良,正是一般的虚弱的结果。
甚至于我的眼病有时候几乎有盲目的危险,也只是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因为每次随着身体健康之增进,也相应增强了我的视力。所以继续消逝的许多岁月,对于我,其意义乃是恢复元气,但也可悲,那意义也是退后,是毁坏,是颓废的时期。
在这之后,还需要我说我经验了颓废的问题了么?我知道这问题最彻底。甚至于一般悟力和理解力的精巧的技艺,色之浓淡的感觉,观察到隐微之处的心理,以及一切我所特长的,都是我在这时候第一次学会,是这个时候的特殊的收获——因为这时我心中的一切,都精微化了:观察之自身,和一切观察之官能。从病的观点观察了更健全的概念和评价,另一面从富裕的生命之自信和丰饶,观察了颓废的天性之隐密作用——这就是我的基本经验,我曾经很久熟练了的。
总之,就在这之中我成为一个制胜者。现在,我的手精巧;它这颠倒了景物的妙诀:这或者就是我为甚么独能够重新估定了一切评价的第一个理由。
二
我承认我是一个颓废者,但也是那反面。这证据是:我总本能底地对于有害的事情采取适当的防卫;但颓废者则永远采取于他不利的办法。就全体说,我是健全的,但在细小节目我却是一个颓废者。那种力那使我绝对孤独,使我放弃了我的生活习惯,那种自己锻炼,禁制我多食和要人服侍和看护,这些都说明了于我最需要的时候,我的天性的绝对的坚持。
我调整我自己,我恢复了我自己的健康,要如此,如一般心理学家现公认的,其成功的先决条件,必须那个人是根本健全。一个典型的病质的人,不能成为健康,至少不能由他自己的力量。反之,在一个真正健全的人,病患甚至于是对于生命,对于生命之丰裕之强力的刺激。因此我现在将我长期的病患作如是观:
——那好像我发见了更新的生命,我自己也在内。
我在别人所不能赏味的一种方法中去赏味一切的善和精微的事物——我从我的求健康,求生物的意志创造了我的哲学。……我希望这一点会被人理解;正在这生活力降至最低抑的时期,我终止成为一个悲观者:自我恢复的本能,禁止我有着窮蹙而绝望的人生观。现在我们该可以认识了自然的最优越的人类的天秉了罢?
那只能由这事实而认识:即这种类型中的最卓绝的人,使我们的感觉舒适;他是坚挺、甘美、芳馨、是一整块石头雕凿成的。他只享乐于他有益的;超过了这限度,他的快乐,他的欲望随即终止。他欲得救而避害;他知道怎样转变严厉的灾祸成为他自己的利益;凡一切不致死的危害都使他更强健。他本能底地从他所见,所闻,所经验的一切,收集了他的材料,他是一条挑选的原则。
他使许多东西不能入选。他自有定见,当他与书籍与人与自然景物接触的时候;他所选中,所承认,所信托的事物,他总是尊重。他以长久的警惕和慎思的矜高所养成的从容其间的态度,临于一切的刺激,他考验一切逼近的刺激,他并不迎合它。他不相信“恶运”或“罪过”;他可以消化了他自己和别人;他知道怎样忘却,——他有这充足的强毅使一切事物成为他自己的利益。
那末看罢!我正是我刚才所说不是别人正是我自己的这个颓废者的反面!
三
这二重的经验,这种向着绝不相同的两个世界的意义,恰在我自己的天性中反映出来。我有一个变化的自我:我有肉眼,有慧眼,或者甚至于也有天眼。我的遗传的天性使我的观察超越过仅仅是局部的,民族的,畛域的视线;要做一个“好欧罗巴人”我一点不费力。在另一方面,我或者比现代德意志人——德意志的国民——更德意志的,我是最后的非政治的德意志人。
但我的祖先是波兰贵族:由于他们,我的血液才有这多种民族的天性,——谁知道呢,或者甚至于有波兰贵族的自由否定权
 。当我想起我在旅行的时候常常被人认作是波兰人,而很少被人当作是德意志人。那好像我是属于仅有少量德意志血缘的一类人。
。当我想起我在旅行的时候常常被人认作是波兰人,而很少被人当作是德意志人。那好像我是属于仅有少量德意志血缘的一类人。
但我的母亲F.奥什丽尔(F. Oeh er),却纯然是一个德意志人;也同样我的祖母E.克兰斯(E. Kranse),后者全在古色古香的窝牧
 ,度过了她的青春,并非和哥德那一班人无关。她的哥哥克兰斯,柯因斯堡
,度过了她的青春,并非和哥德那一班人无关。她的哥哥克兰斯,柯因斯堡
 的神学教授,在赫德尔死后
的神学教授,在赫德尔死后
 被召来窝牧当学务总长。所以那是当然的,她的母亲,我的外曾祖母,曾以玛德金(Mathgen)的名字,出现于少年哥德的日记里。
被召来窝牧当学务总长。所以那是当然的,她的母亲,我的外曾祖母,曾以玛德金(Mathgen)的名字,出现于少年哥德的日记里。
她的再醮的丈夫是伊冷堡
 的宗教会长尼采,即我的祖父。大战争的一年,一八一三年十月十日,当拿破仑统率着他的总参谋部进到伊冷堡的时候,她诞生了我的父亲。因为是撒克逊人,她是一个拿破仑的崇拜者,或者我也是如此。我的父亲生于一八一三年,卒于一八四九年。在接管了离鲁登
的宗教会长尼采,即我的祖父。大战争的一年,一八一三年十月十日,当拿破仑统率着他的总参谋部进到伊冷堡的时候,她诞生了我的父亲。因为是撒克逊人,她是一个拿破仑的崇拜者,或者我也是如此。我的父亲生于一八一三年,卒于一八四九年。在接管了离鲁登
 不远的罗根
不远的罗根
 教区的牧师职务之先,他在阿尔廷堡
教区的牧师职务之先,他在阿尔廷堡
 的宫堡住了几年,在那里教授了四位公主。
的宫堡住了几年,在那里教授了四位公主。
这四位公主,便是汉诺威皇后,康士坦丁的女大公,阿尔登的女大公,和沙克斯亚尔登堡的德丽撒(Theresa)公主。他充满了对于普鲁士王菲德烈克威廉第四(F. William IV)至诚的尊敬,从他,他得到他在罗根教区的职位;一八四八年的政变,给他以很大的悲哀。我是十月十五日,与上述普鲁士王的诞生同日,所以,我自然底地得到了荷亨索伦
 王室的菲德烈克威廉的名字了。
王室的菲德烈克威廉的名字了。
这一日,有许多吉庆的事情。所以我的全儿童时代的生日,都是一个公共的假日。我以为我有着这样的一个父亲是一种特权。在我,这种特权甚至于说明了我能有着一切特权的要求,——除掉了生命和对于生命的伟大的肯定。我所受福于他的,尤其在这一点,我只稍稍忍耐,不必特别用心,就可以不自己底地进到一个更崇高更精美的世界。在那里,我自得,只有在那里,我的最深心的热情能够自由活动。
我差不多为这特权赔偿了我的生命,一定地,这还不算是折本。一个人要约略懂得我的查拉斯图拉或者他必须如我一样的自处,一足跨出生命之外。
四
我永远不知道激起敌对的技艺(为此,我也要感谢我的无比的父亲),甚至于当最值得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无论我怎样是一个非基督徒,我仍然没有遇到任何恶感。你们可以考察我的生活,也寻不出有人对我表示恶意的任何痕迹——甚至于仅仅一次。或者你们反可以发现了人们对于我的太多的好意。……甚至于同那些最难于相爱的人,我的经验也无例外地得到他们的好意。我驯服一切熊熊,我能使顽石点头。
有七年之久,我在巴塞尔的专门学校高级班教希腊文,我没有发生过惩罚学生的事;即使最懒惰的学生,对于我的功课都很勤谨。我总是整备以暇。我必须从容以求自制。我能操起任何乐具,即使那是不和谐的乐具,如同人类这种乐具一样。除非我是病了,我总能使这乐具奏出悦耳的声音。我怎会不被这些乐具本身常常告诉我它们自然没有听过这样的言语。
……或者这种感情的最活泼的表露,当是H.V.斯太因(H. V. Stevin)了,他在这样不可救赎的少年时代死去。他在用尽了心情得到了许可之后,曾一度来锡尔,马里亚
 住了三天,并向那里的人解说,他并不是为恩格顿而来。这个杰出的人,有着少年普鲁士贵族的刚毅的纯朴,曾陷溺在瓦格纳
住了三天,并向那里的人解说,他并不是为恩格顿而来。这个杰出的人,有着少年普鲁士贵族的刚毅的纯朴,曾陷溺在瓦格纳
 的泥塘里——也陷溺在都灵
的泥塘里——也陷溺在都灵
 的泥塘里了。
的泥塘里了。
但在这三天内,差不多,被一阵自由的飙风能激荡,突然变为一个鼓翼高翔的自由人。我一再告诉他这仅仅是爽朗的高山空气的影响;一切人都有同感——人不站在离摆德里德
 六千尺之上,不能有些感觉。但他并不信我。……我得到许多大大小小的攻击,所以致此的原因,那也不是有意,至少不是恶意,如我能已经指明,那宁是使我很不平的善意;我的生命中不少的灾祸,那种善意是要负责任的。
六千尺之上,不能有些感觉。但他并不信我。……我得到许多大大小小的攻击,所以致此的原因,那也不是有意,至少不是恶意,如我能已经指明,那宁是使我很不平的善意;我的生命中不少的灾祸,那种善意是要负责任的。
我的经验给我以这种权利,去怀疑一切所谓“无私”的倾向,去怀疑随时都准备着以言行去救助人的整个的“邻人爱”。在我看来那好像是弱者的表征,是无能力抵抗刺激者的典型——只有在颓废者中间慈悲才是一种道德。
我所以诅咒博爱家就是因为他们太容易忘失了羞耻,崇敬,以及保持相当距离的礼意;他们不知道这种慈悲是使群众腐败,他们不知道那离开恶意只是一步。慈悲的手可以破坏了伟大的命运,创痛的孤独,和忆着伟大罪恶前进的特权。慈悲之征服,我认为是最高贵的道德之一。在“查拉斯图之试探”
 里,我设想到这情形,他听到了求救的呼声,慈悲袭击他如同一种最后的罪恶,要使他破坏了自己的笃信。
里,我设想到这情形,他听到了求救的呼声,慈悲袭击他如同一种最后的罪恶,要使他破坏了自己的笃信。
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自制,在许多所谓无私的行动所激起的无智而浅见的迷乱中,保持了自己的使命之尊严。这是一种试炼,正是查拉斯图拉不能不经过的一种试炼——是他的力量的真实的证明。
五
但在另外一点,我又像我父亲,我是他早死的生命之继续。如同永没有遇过敌手的人一样,我对于报复这个观念之不能理解,正如“平等权利”这个观念一样。无论在甚么地方,我遇到大大小小的无理,我总禁止我作一切安全或防护的计划,——自然也不作抵御或“求直”。
我的报复的形式是这样:敏速地以一种智慧报答了对手的愚昧,这样或者人们还能追及。用一个比喻说:我吞下一罐果酱,为要避去了一种酸味。……所以让人们侵犯我——他可以确信我将“报复”即不久我将觅到一种机会对于“侵犯者”表示我的感谢(为这种侵犯而表示感谢),或者问他要求一点甚么,这会比直接给与甚么更勤恳。在我看来那也好像最粗率的言词最粗率的文字比缄默更温良更正直。
保持着缄默的人总是缺乏心之温和和精细;缄默是一种反抗,隐忍着一种慈悲,必然地要产生一种不良的气质——那甚至于要败坏了胃腑。一切缄默的人都是消化不良。所以你们可以看出我并不以粗率为低下;那是最近人情的一种反抗的形式,并且在现代的孱弱病中,那还是我们的第一等的美德。假使自己丰裕于粗率,即使错误也是一种快乐。一位神降临到大地,除了做错事以外不能做别的了,——因为引罪归已而不责罚,正是初性的表征。
六
对于怨恨之消释和怨恨之理解——总之,谁知道这是得益于我的长期的疾病呢?这问题不是单纯的三个人必须从自己的强毅和自己的弱点得到经验。假使我们对于疾病和弱点发生忌恨,那便是表示了心之深处的恢复本能,即战斗和防卫本能之衰颓。他不知道如何摆脱,如何完成,如何抛弃。一切事都使他受伤。人事交迫,一切经验给与太深的打击。
记忆是一种胆溃的创痕。疾病之自身就是一种怨恨。但这种病人有一种唯一的大救济,我称之为俄罗斯人的命定主义(Russian falalism)即俄罗斯兵卒,当战斗不能支持的时候,即最后躺在雪地上的这么的一种无抵抗的命定主义。甚么也不接受了,——完全终止了反应。……这种命定主义之最高的理智,不单是视死如归,也在最危险的情境中,保全了生存,实在与求生而停止了活动如同一种自动的蛰伏同其价值。
再进一步,我们见过托钵僧,他可以在茔圹中睡几个礼拜。……因为人如事事反应,必会快速地耗竭了自己,所以自己全不反应,这就是这个原理。再没有甚么比怨恨的情绪还要快速地销铄个人的精力的了。忍辱,病的多感,报复之无力,复仇之热望和焦渴,各种恶毒的计划。这些对于一个衰惫的人,实在都是最有害的反应。这足以促进神经衰弱,变态地增加有害的分泌物,例如增加了胆汁到胃里去。
病人最要的是禁止怨恨,怨恨是他的特殊的危险:但不幸,那又是他的最自然的僻好。这是最深奥的生理学家的释迦所最完全明白的。他的宗教,为着避免与这样可恼恨的东西如基督教者相混,最好称之为卫生学,它的效果完全建立在怨恨之克服之上:从怨恨解放了灵魂,那便是向着恢复的第一步。
“怨怨相报,了无终止!以德报怨,怨恨斯已。”这是释教教理的出发点。这不是伦理的呼声,乃是生理学家的呼声。从病弱所生的怨恨于人无伤,除了病者之自身。反之,于根本强毅的人,怨恨都是一种剩余的感情,能自制而克服,更足为生活之富裕之证明。
读者们如知道了我的这种严肃,我的哲学反对一切复仇和怨毒的情感,甚至于到了攻击意志自由的这地步(我之反对基督教,也只是攻击意志自由的一个特例),也将理解了为甚么恰在这一点,我想加重了我个人的态度和我在实施上的我的本能之坚定。在我的颓废时期,我禁止我有这些感情,因为它们是有害的,但到了我的生命恢复,有了充足的丰裕和矜高,我仍然禁止我有着这些情感,但现在却是因为它们在我之下。
我所说的“俄罗斯人的命定主义”,在我心中,是以这种方法显示不出来,所以有几年之久,在几乎是不可堪的环境,地位,社会和人物中,我总是这样坚忍地,把持住。——这比去改变他们,比使他们改变,比反抗他们都强。
……在这种命定主义之中勉强扰动我,要以强力来唤醒我的人,那时在我看来好像是我的死敌。事实上,我这样去做也就有着死的危险。想到了自己的自身,就是一种命定,并不想去“改变”——这在这样的环境中,就是我的最高的智慧。
七
但战斗又是一事。我也天生的地是一个战士。我的攻击是天性的。为一个敌人敢为一个敌人这必以强毅的天性为前提;总之这是与强毅底天性分不开的。它们需要反抗,它们追求反抗:攻战之悲壮,为强者所必需,亦如仇恨和怨毒之感情之必属于弱者是一样。例如妇人便是仇恨的;她的弱点陷于这种热狂,亦如她之易感受于别人的绝望。
攻战者的强力以他所需要的对抗而测定;每次强力的增加,表明了其自身更追求最可怕的劲敌,或难题:因为一个战斗的哲学家,甚至于念同难题决斗。但这种决斗,不是要克服一般的劲敌,乃是要克服那些自己必须用尽自己的强力,技能,和侠气的劲敌——自己的棋逢对手的劲敌。……一个高贵的决斗者的第一条件乃是做一个棋逢对手的劲敌。自己所蔑视的地方自己没有战意。
自己所支配的地方,自己不当有战意。我的战略包括在四种原则之中:第一,我只攻击战胜者,——假使必要,我期待着直到他们先成为战胜者。
第二,我只攻击那些,我觅不到联与者的东西,对于那,我是孤独战斗,我只与我自己休战相关。……我永不公然地迈进一步与于自己无关系的事物:这便是我的行动之标准。
第三,我永不攻击个人,我只将个人看作一面有力的扩大镜,藉之而看到了隐避而不易知,恶而不可见的一切。例如我攻击斯特拉斯
 更正确地说,我攻击德意志文化阶级对于一部老朽著作所给与的热烈的赞成。因此,我抓着了这文化的赃证。又如我攻击瓦格纳,或更正确地说我攻击错误,攻击以丰富混淆了修饬,以伟大混淆了颓废的我们的文化之谬种。
更正确地说,我攻击德意志文化阶级对于一部老朽著作所给与的热烈的赞成。因此,我抓着了这文化的赃证。又如我攻击瓦格纳,或更正确地说我攻击错误,攻击以丰富混淆了修饬,以伟大混淆了颓废的我们的文化之谬种。
第四,我攻击那些不包涵个人的特点,并缺乏不快的经验之背景的东西。真的,在我看来,攻击便是善意的明证,在某种情形,且是感谢的明证。我以攻击尊敬一种东西,和区别一种东西:在我看来,那都一样,无论我的名字关连到一种制度,或一个人,无论我是迎此或拒彼。假使我攻击了基督教,我所以如此,因我没有在其中遇到不幸和困——最诚挚的基督徒,对我都很亲切。
我个人底地基督教的最严厉的反对者,我不主张千年来所不可避免的结来,个人要负责任的。
八
我可以指出使我与人交涉至感困难的我的天性的最后的特质么?我秉赋着一种澄净之至灵敏的特质;所以我能生理底地确知——那就是说我可以嗅到——人类灵魂的深处或者说人类灵魂的内腑或心髓。……这种感觉,有着心理的触角,我藉之而感觉,而把握到一切的秘密;只最初的一瞥视,我就可以揭发了人性的隐秘的污垢,那可以是卑下的血缘所生,可以藉着教育而表皮府地镀饰了的。
假使我的观察是正确的,这样的人,不能忍受我的洁净之感,在他方面,也觉到了由于我的嫌厌所产生的警敏:这不会使他们更芳馨。……在我固执着这澄净之态度,是我生存之第一条件;在不净的环境,我会消亡。所以我总习惯于在清水中,在任何完全透明而发光的原质中,不断地游泳,沐浴,和激扬。就是这个理由,社交对于我的坚忍,成为不小的试炼;我的性格不在于我与我的同类有同感,而在于我能忍耐着那种同感。
我的性格,是一种不断地自己制胜。但我需要孤独——那就是说我需要恢复,需要回到我自己,回到自由的,轻飏的,爽朗的空气之呼吸。……我的全部查拉斯图拉,就是一种孤独之颂歌,为更明白起见,或者说一种纯净之颂歌。幸好那还不是“纯净的愚蒙”
 之颂歌。谁有着识别颜色的巨眼将称那为金刚石。对于人类,于贱氓的厌恶,总是我的最大的危险。你们愿意听听关于解脱了厌恶之查拉斯图拉的言语么?
之颂歌。谁有着识别颜色的巨眼将称那为金刚石。对于人类,于贱氓的厌恶,总是我的最大的危险。你们愿意听听关于解脱了厌恶之查拉斯图拉的言语么?
“其后怎样了呢?我如何从嫌厌中解放了我自己?我的眼睛如何又闪射着青春之新光?我如何能飞到不再有一个贱氓坐在泉水旁边的高处。”
“我的嫌恶为私创造了翅膀和想望泉水的力量了么?真的,我不能不飞到高迈的高处,再觅到了快乐之源泉!”
“唷,我的兄弟们,我觅到了它了!这里在最高迈的高处,快乐之源泉为我而进涌!这里,生命之杯,没有一个贱氓和我共饮!”
“你快乐之泉水哟,你大汹涌地为我而涌流!为要重新装满,你甚至于又空了生命之杯。”
“但我必须学习更谦和地接近你:因为我的心向你跃动得太猛烈了:”
“——我的心上燃烧着我的夏,我的急迫的,炎热的,沉郁的,太幸福的夏:我的炎夏之心,如何地渴望着你们的清凉!”
“我的青春之苦恼的不安已过去了!我的六月雪花之嫌恶已过去了!我完全成为夏天和夏天之日午。”
在最高迈的高峰上之夏天,在清冷的流泉和可祝福的宁静之中的夏天:唷,来啊,我的朋友们,那宁静会变得更可祝福了。
“这是我们的高处,是我们的家:在一切不净者的焦渴看起来,我们住在这里太高,也太陡峻了。”
“我的朋友们说,投你们的纯洁的眼光于我的快乐之泉水,它何能成为污渴!他当以它的纯洁对你回笑。”
“在将来之树枝上我们建筑我们的巢;鹰们的喙当为我们孤独的人们带来食物。”
“真的那不是不净的人能够共享的食物!那会烧焦了他们的嘴,他们以为他们吞食了火了。”
“真的,我们这里没有预备不净者的住处!我们的快乐当是他们的肉体与精神的一个冰窖!”
“如用刚风一样我们生活在他们上面,逼近于鹰,逼近于冰雪,逼近于太阳:如是生活着的刚风啊!”
“有一天我要如同一阵风吹在他们中间,并以我的精神夺去了他们精神的呼吸;我如是愿望着我的未来。”
“真的,查拉斯图拉是一切低卑地方的一阵刚风;他向他的敌人,和所有一切吐唾,和偷掷,石子的人警告:仔细着你们如何逆风而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