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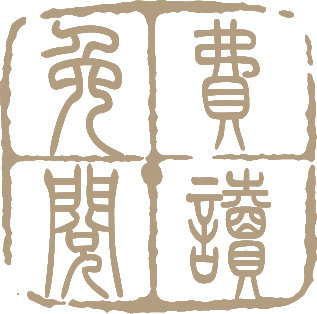
一
在根柢上,这本书中的问题,乃是第一底等级和趣味的问题:甚而那是至深的个人的问题,这可用以纪念这书所产生的时代,即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时普战争的收场时代。当华尔特战阵的炮声震动了全欧洲,未来的这本著作的作者,一个冥想者和谜之爱好者,安居于阿尔卑斯山的一角,结果,他被扰乱了,但同时也不介意;他将他的冥想写在希腊人身上,——这奇异而艰难的著作的核心,那就是后来这篇序言所专论了的。
几个星期之后,他在麦次的墙壁下,仍然想着关于希腊人和希腊艺术的确然的“欢欣”这个问题,最后在最平静的一月,和平条约已在凡尔赛宫
 讨论了,他自己也得到了一种和平,由战地带来的疾病也渐渐痊愈他决心来从事于“悲剧从音乐之精神产生”的著作。
讨论了,他自己也得到了一种和平,由战地带来的疾病也渐渐痊愈他决心来从事于“悲剧从音乐之精神产生”的著作。
音乐?音乐——与悲剧?希腊人与悲剧的音乐?希腊人与悲观主义之艺术品?真的么,希腊人是自来所没有的健全,美,猜嫉,乐生的民族么?希腊人需要悲剧么?是呀,需要艺术么?肯定的艺术,便是希腊人的艺术么?
因此我们可以想想那些从生存之评价引出来的大问题。悲观主义必然地是衰微的,是毁灭,是失败,是耗惫,是无能的天性之表征么?在印度人中也如同在我们“现代”人,和欧洲人中一样么?
有着一种力之悲观主义么?在生存中有着爱艰难,爱惊怖,爱罪恶,爱疑问这种睿知的偏爱么,——有着这种倾向么,这种倾向乃是幸福之结果,是充沛的健全之结果,是生存之充裕和全完?或者过盛的丰裕,也可以有痛苦么?迷人的锐眼的勇敢渴慕着恐怖如同渴慕着敌人,有价值的敌人,要以反抗敌人来衡量了自己的力量么?要从敌人来学习了恐惧之意义么?
对于最强最勇敢的时代的希腊人,悲剧神话的意义是甚么呢?德阿尼西斯的崇宏现象是甚么呢?产生德阿尼西斯,产生悲剧的是甚么呢?还有悲剧死于甚么?死于苏格拉底的伦理,死于理论家之辩难的自是和欢喜么?苏格拉底学派不是颓废,是逃避,是疾病,是散漫崩解的天性之表征么?后期希腊思想之希腊的狂欢不仅仅是一种回光反照么?伊比鸠鲁
 之反对悲观主义不仅仅是受苦者的一种准备么?
之反对悲观主义不仅仅是受苦者的一种准备么?
科学之自身,作为一种生命之象征,所有科学的真实的意义是甚么呢?所有科学都为甚么?科学思想或者仅是悲观主义之一种恐惧和一种逃避么?对于真理的一种精巧的防卫么?伦理底地说来,那不是如同虚伪和怯懦一样么?非伦理底地说来,是一种装作么?啊,格拉底,苏格拉底,或者这就是你的秘密么?啊神秘的讥嘲者,或者这便是你的讥嘲么?
此后我开始要讨论的问题,乃是恐怖而危险的一个带角的问题,但不必是一匹牛,总之乃是一个新的问题。现在我可以说那是科学自身的问题,——科学第一次成为问题了?但这本书我的青年气韵和怀疑的发泄,——何等不可能的一本书,这是一个青年的劳作的结果这是如何地不相称。
仅仅从不成熟的早期的个人经验,写成这入门的一本著作,从艺术观点看来(因为科学问题不能在科学基础上去认识),或者那是为艺术家而写的著作(即艺术家的例外的一类,自己必须寻觅但不必用心寻觅的艺术家),有着艺术家所有的分析和自省,充满了心理学的发见和艺术家的秘密,在那背景上,有着一种艺术家的形而上学,一种青年人的著作,洋溢着青年的朝气和青年的苦闷,青年的独断,和大胆的自足,即使在他折眼某种权威和自我尊严的时候;总之,纯是一种头胎之著作;陈旧的问题中充满了青年人的讹误,青年人的絮咶和粗暴;但在另一方面这著作亦有特长(尤其是在一种种音歌曲中),这著作是献给大艺术家瓦格纳的它是一种证明的著作,总之我的意思乃是说这是尽了那时候的最善的努力的著作。
因此这著作是值得考虑和保存的,但我也不必隐藏,它引起我的感情何等不快,十六年它如何还是一个生客在我的眼前——在我的更非熟的眼前,百倍厌弃的眼前,但不是说更冷酷的眼,乃是看到了这勇敢的著作所袭击的一切问题的一只眼,以艺术家的眼光观察了科学以人生之眼光观察了艺术。
三
现在我再说一遍,这本书之出现,于我是不可能的。我以为它是不良地写成,阴沉,苦痛,充满了想像和用情之后的紧张,有时又加上一些巾帼气,节拍不昼一,缺少了对于逻辑的明晰的意志,完全是口辩而轻视了证据,甚至于不相信适当的证据,将它自己当作一本创始之著作,当作受了音乐的洗礼的人们的音乐,当作自始即被艺术上的共同而稀有的经验所统一了的人们的一本书,当作关于艺术上的血液关系的暗号,一本傲慢而狂想的书,甚至从第一页起即从文化所陶冶过的即悖的俗人引退,比之从人民更引退。
但如那结果之所示,它也知道怎样寻觅同类之热心者,并引诱他们到新的道路和新的舞场。总之,在这里怀着好奇和嫌忌这是必得承认的,——这里说着一种新奇的声音,说着一个不可知的神之信徒,他暂时地在学者的面幕,在辩证之前的德意志的重力和不安之下隐藏,甚至于在瓦格纳的不良态度之下隐藏。
这里一种精神满怀着新奇和无名的需要,一种灿烂着许多疑问,和经验,和蒙昧的记忆,在它的旁边,德阿尼西斯之名如同另一种疑问的符号;这里说着,人们怀着犹疑的心对自己说话,说着对于神秘的几乎是狂醉的灵魂有着关系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不能决定自己的隐现,不能自制地踉跄着,有着以新奇舌头说话的艰难。这种“新的灵魂”应常是歌唱而不是说话。我不敢如同一个诗人一样唱出了我的思想,那是多么可怜!或者我能够这样做了。
或者至少如同一个言语学家:因为即使在现在,在这领域内的一切,仍然未被言语学家发现和说明!总之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当前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总不能回答这问题,德阿尼西斯是甚么?”则希腊人总是永远全不可知和不可理解。……
四
是的,甚么是德阿尼西斯的?在这本书里,觅到了一个回答了,——因为这里说着一个“明智的人”,说着他的神的崇信者和信徒。或者现在我应当更谨慎而质直地来说一个心理学的问题,一个如同希腊悲剧之起源那样艰难的问题。一个希腊人关于痛苦之根本问题,他的感觉的程度,——它是永续的么,是变化的么?他之对于美于庆典,于快乐,于新的仪式之不断增长的渴望,现实底地从需要,从自己,从苦闷,从苦痛生出的么?
因为即使这是真的——贝理克
 (或惹塞德底斯
(或惹塞德底斯
 )已在大祭演说中,指示出来,但我们如何去说明在这种渴望之先的相反的渴望:在生存之根本上对于丑恶之渴望,对于古代希腊人的健全的冀望,对于悲观,对于悲剧的神话,对于一切可怕的,恶的,神秘的,破坏的,不祥的概念之坚决欲求?悲剧必须从何处发生?或者从快乐,从力,从丰饶的健全,从过盛的满溢。
)已在大祭演说中,指示出来,但我们如何去说明在这种渴望之先的相反的渴望:在生存之根本上对于丑恶之渴望,对于古代希腊人的健全的冀望,对于悲观,对于悲剧的神话,对于一切可怕的,恶的,神秘的,破坏的,不祥的概念之坚决欲求?悲剧必须从何处发生?或者从快乐,从力,从丰饶的健全,从过盛的满溢。
其次生理学底地说来,悲剧和喜剧所自发生的一种狂想,那种德阿尼西斯的狂想,其意义又是甚么呢?甚么?那是可能的么?这种狂想必然地狂是腐败之表征,不是衰微之表征,不是一种颓废文化之表征!或者这是无人可以理会的一个问题——有着所谓健全之神经病么?有着少壮人的神经病么?半人半山羊所合成的神是甚么意思?甚么样的个人经验,甚么样的压迫,使希腊人将德阿尼西斯底启示者和原始人,想作是一个半人半山羊的沙德尔?
至于关于悲剧的对唱:或在希腊人的身体焕发,希腊人的精神洋溢的这时代,有着一种风土的狂喜么?幻想或者错觉支配着全部社团,全部宗教集会了么?假使希腊人在最健壮的少年时代就有着悲剧的意志,且是悲观主义者,那是怎么说呢?用柏拉图的话,赋与希腊人以最大福只的乃是狂想之自身,那又怎么说呢?反之,在希腊瓦解和衰微的那瞬间,希腊人却渐渐地成为更乐观,更浅薄,更写意:更热心于逻辑和世界之逻辑化。结果同时也成为更“快乐的”,更“科学的”这又怎么说呢?
是的,虽有一切“现代观念”和德莫克拉西的成见,而乐观主义之胜利常识之得势,实际的和理论的功利主义(如同德莫克拉西一样,它们都是同时起来的)——所有这些不都是衰落的生力逼近的时代肉体底地疲惫之病象么?总之都不是悲观主义么?正因为是一种受苦者伊庇鸠鲁不是一种乐观者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这本书所背负的是何等沉重的问题了,——但我们还要加上这个一切问题中的最沉重的问题!从人生之见地观察,伦理的意义是甚么?
五
即使在致R·瓦格纳的序言里,艺术(不是伦理),也是被认为是人类固有底地形而上学的活动;在这著作中,常常显示了这种苛酷的大前题:要正确认识世界之存在,只有把它当作是一种美学的现象。
实际上全书只承认一种艺术家之思想和艺术家的隐藏于一切思潮之后的潜在思想,——一种神,假使你愿意;真的只有十作无思想的,非伦理的艺术家之神,在创造如同在破坏之中一样,在善之中如同在恶之中一样,愿意自己知道他自己的相等的快乐和胜利;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从丰满和过盛之苦闷中,从钻集心中的矛盾之苦恼,解放了自己。
世界被认为是神之不断底救济,是神永恒的变化,是最痛苦,最不调和,最矛盾的生命之永新的现象,这种生命只在出现的时候救济了自己!你可以称之为僭妄,为怠惰,为空想,假使你愿意,——但这要点是全部艺术家之形而上学已经说明了,一种精神无论如何艰难,总有一天要反对了生命之伦理的见解和意义。
这里或者是第一次“超乎善恶之外”的悲观主义自己表白出来了;这里对于叔本华所不惮烦去轰击的“意志之执着”已被给与形式和说明;——这里是一种哲学故意贬价地将伦理之自身放置于现象世界,不单是在“现象”(使用了理想主义者的术语)中,且是在“错觉”中,如同表象,写真,错误,阐明,理性化,艺术一样。或者这种反伦理的倾向的深处,最好可以从全著作中对待基督教这种戒备而不相容的缄默测算得出来,——基督教被认为是自来人类所不能不听从的伦理主题的最跨大的狂词。
事实上,对于这著作中所说的纯粹美学的世界之解放和辩正,再没有比基督的教条还大的对照了,基督教的教条仅仅是伦理,只愿成为伦理,并且由于它的绝对的标准,(如上帝之真实性)它将艺术,一切的艺术,以为是虚伪而斥黜了。这就是排拒,订罪,宣告死刑。
在这样一种必然地与艺术不相容的思想和评价之范筹之背后,我总觉到一种与生命不相容的东西,一种对于生命之怨恨的,复仇的,意志之否定:因为所有的生命都是依据于表象,艺术,幻觉,人类的幻景,错误,和背景之缺乏之上。基督教自始即是彻底为生活而生活的饱食病,它只有在信仰“彼岸”或“天堂”的生活之中乔装了自己,隐蔽了自己,装饰了自己。
厌世,绝情,美和肉感之恐惧,一种诬蔑这世界的出世思想,总之,一种对于虚无,对于末路,对于寂灭,对于安息的渴望,——一切这些以及无条件地主张基督教是唯一伦理的评价,在我看来,总是显出了最危险而不祥的意愿死灭之可能形式;至少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最深的倦怠,丧心病,虚脱,和贫血病之表征,——因为以伦理判断(尤其是基督教即绝对的伦理),生命必然是失败者,因为生命就是一种非伦理的东西,——真的,生命屈服于侮蔑之重压与永久否定之下,生命必然被感觉到以为是一种无价值的欲望,以为本身就是无价值的。
甚么?伦理本身不会是一种否定生命之意志么?不会是一种求死灭之隐秘的天性么?不会是一种颓废,堕落,诽谤之原则么?不会是一种末路之开始么?因此不会是一切危险中之危险么?……因此我的天性,那种防卫生命之天性,在这本激昂的著作里反对了伦理,为它自己创造出一种生活之根本相反的教条和相反的评价,一种纯粹艺术的和反基督教的评价。
我将称之为甚么呢?我以一个言语学家和词人的资格奉一个希腊之神之名为它施洗,我称之为德阿尼西斯的——这实在妥当极了,因为除此以外,还有甚么是反基督教者的合宜的名称呢?
六
你们能看出来我敢于在早年的著作中所提示的这个问题了么?我现在是如何歉仄,我在那时候还没有这勇敢(或者这不逊?),使我自己为着这样个人的思想和努力而有一种个人的言语)我歉仄,我痛苦地去表现,用着康德和叔本华的名词,去表现那与康德和叔本华的精神和赏味根本相反的新奇的评价!例如叔本华对于悲剧的见解是甚么呢?
在意志和观念之世界里(第二章四九五页),他说:“所给与一切悲剧的唯一的扶摇直上的力,乃是觉察到这世界和生活完全不能使我们满足,结果自不值得我们的留恋。在这之中即构成了悲剧的精神!因此倾心于无可如何的听天由命。”
但是德阿尼西斯的呼声何等地异样啊!这种听天由命何等使我不能理解!但在这著作中有着最坏的一点,那比之于我以叔本华的道理来隐晦,来败坏了德阿尼西斯的创始精神还使我抱歉,总之我以混淆了现代观念来破坏了这崇宏的希腊的问题了!当无望,当一切都分明地指出了一种临到的末路,我仍然期待而且希望!
在我们后期德国音乐之基础上,我开始来构造“条顿的精神”之故事,好像它正在发见了自己,复归于自己——是的,我这样做,在不久以前,领导欧洲,支配欧洲的德意志精神已经寿终正寝,并在建立了一个帝国的夸耀的口实之下,将它的恶果传给中庸主义者,传给德莫克拉西,传给一切“现代观念”。
在实际上我从此知道无望和无爱地对待这种“条顿的精神”恰如我之对于同时代的彻头彻尾的德意志音乐,一切艺术形态之最反希腊思想者,第一等的神经质破坏者,这对于伦理主义者那样皆醉而愚暗的人是两重的危险,——有着麻醉和麻木的两重的危险性。
固然除了这些没落的希望和应用了近代观念而败坏了我的第一本著作的这些过错,那里也坚持着所提示出来的伟大的德阿尼西斯的问题,甚至于坚持着这问题与音乐相关,我们如能感受到这么一种不再是浪漫主义之来源的音乐,不再是德国的音乐,而是一种德阿尼西斯的音乐。……
七
但是先生们哟,假使你们的著作不是浪漫主义的,那末在天堂之名是甚至呢?能有一种对于现在,于“现实”,于现代观念之憎恶,比之于你们的宁相信虚无,相信魔鬼而不相信“现在”的艺术之形而上学还甚的么?在所有你们声音的艺术和听官的诱惑之中,不是有一种根本沉浊的愤怒之咆哮和毁灭之快乐了么?
这本书不是说到了一种狂妄的断案,反对了一切属于“现在”的一种与实际的虚无主义相去无几的意志,那好像说:“让无物真实不久你就对了,不久你的真理胜利!”听听你自己罢,你们悲观主义的先生们和艺术之侮弄者,张耳而听,听听你自己著作中的一节,那不是非雄辩的屠杂者的一节,那可以有着一个诉之于青春之耳与青春之心的迷人的吹鼓手。甚么?那不是一八三〇年的卓越的浪漫主义而戴上一八五〇年的悲观主义么?
固然在那之后,一般浪漫主义者之终曲即刻激昂了,——决裂,破坏,又皈依而屈服于旧时的信仰,旧时的神。……甚么?你们悲观主义者的著作不是一种反希腊思想的著作么?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例证么?不是同时是麻醉和麻木的一种东西么?总之不是一种催眠剂么,一种德意志人的音乐么?谛听这些话罢:
“让我们想像这样一种复兴的时代,有着这勇敢的幻想,有着这渴望伟大庄严之英雄的欲望;让我们想像着这些屠杂者之勇健的步履,怀着矜高和勇敢,弃绝了一切乐观主义之女性教理以求”决绝地生活“,完整地生活,丰满地生活。那不是必需的么,这种文化之悲剧的人,由于他的严峻而恐怖之自己锻炼,热望着一种新的艺术形面上的慰学藉之艺术,即热望着悲剧,——如希腊人一样,并非浮士德一同叫绝:”
“由于最高的热望,我不是要生活。”
“生活在绝对完善的形式之中么?”
“那不是必需的么?”……否,第三次的否!你们年青的浪漫主义者哟:那不是必需的!但或者你们的目的是如此,用我的名词说,即要安慰,而不要严峻与恐怖之自己锻炼;总之形而上学的慰藉,如同浪漫主义者所常有的目的,如同基督教徒所常有的目的一样。
……否啊!我的朋友们,你们应当最先学会了人世的安慰之艺术,你们应当学会欢笑,假使你们仍然想做悲观主义者:假使这样,你们或者将如同欢笑的人实际底地将形而上学的安慰投掷给魔鬼,——最先将形而上学投掷给魔鬼罢!或者用德阿尼西斯的代表者的话,查拉斯图拉叫绝着:
“我的兄弟们哟,高举起你们的心,向上啊!并且别忘记了你们的腿!你们优良的跳舞家哟,也高举起你们的腿,假使你们能倒竖起来那更好了!”
“这欢笑者之王冠,这玫瑰花之王冠,我自己戴上这王冠了,我圣化了我的欢笑。现在我还没有看出别人有着这充足的魄力。”
“查拉斯图拉这跳舞者,查拉斯图拉,这轻捷者,他摇震他的羽翮,预备奋飞,示意一切鸟禽,整备而停当。一个幸福的,有着轻轻之精神的人:”
“查拉斯图拉这预言者,这真实的欢笑者,这非不能忍者,非绝对者,一个喜欢前跳和飞跃的人,我自己戴上了这王冠了!”
“这欢笑之王冠,这玫瑰之王冠:我的兄弟们哟,我向着你们投掷了这王冠!我圣化了欢笑;你们高人们哟,我请你们学习欢笑!”

1886年8月
锡尔·马里亚
阿伯林格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