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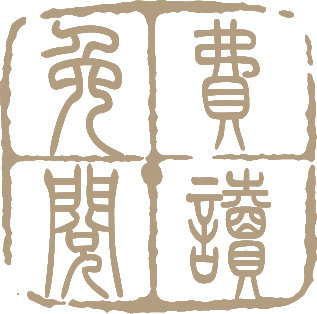
一
要裁判这篇论文,人当为音乐的命运感到如大创伤。我从音乐的命运感到的痛苦是甚么呢?就是这音乐已失了神化宇宙的肯定的性质,——它已成为颓派的音乐,而不再是德阿尼西斯的牧歌了。但是假使一个人觉到音乐是属于自己的,是自己的热情之表露;这时他将觉到这篇论文是非常和平而有礼。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快乐而自嘲,——以谐谈说出真理
 使真理无坚不摧,——这便是人道之自身。
使真理无坚不摧,——这便是人道之自身。
谁知道呢,如同一个老练的战术家一样,我有这力量对准了瓦格纳发射了我的重炮?我保持着在这事件中一切判定,——我曾受过瓦格纳。总之,攻击一个别人所不易测透的,更不可知的人乃是我的生业的最要的一部分。
啊,除了音乐之喀格里阿斯特罗
 而外,我仍然有着几个“不可知的人”要揭开了他们的假面!尤其是我不能不直接攻击德国人,他们在精神上渐渐成为更懒怠,更贫乏,和更“正直”,他们怀着贪馋的食欲,以矛盾不相容的东西来滋养了自己,同时吞下了“迷信”和科学,吞下了基督教的博爱和反犹人主义,吞下了求权力(求“疆士”)之意志和谦卑之福音,——一切这些都是不能消化的呀!
而外,我仍然有着几个“不可知的人”要揭开了他们的假面!尤其是我不能不直接攻击德国人,他们在精神上渐渐成为更懒怠,更贫乏,和更“正直”,他们怀着贪馋的食欲,以矛盾不相容的东西来滋养了自己,同时吞下了“迷信”和科学,吞下了基督教的博爱和反犹人主义,吞下了求权力(求“疆士”)之意志和谦卑之福音,——一切这些都是不能消化的呀!
在这样矛盾的事物之中,他们不属于那一边!甚至是胃脏之中和性!甚么是“无私”德国口味谓一种人都平等,一切事物都美好,那是甚么一种公正!德国人无疑地是理想主义者。当我最后旅行德国的时候,我看出德国的赏味正给瓦格纳与“沙克金(Sakkingen)的喇叭手”以平等的权利;我自己看出来卡兹如何成立了Liszt社,来尊崇一个最道地的德国音乐家,(用德国人的名词),日·苏支音乐师,来培养和传播不自然的教会音乐。德国人无疑地是理想主义者。
二
这里我再忍不住要粗暴,要告诉德国人以一种不快意的真理:除了我谁去作这事情呢?我意思是说在历史事件中,他们的疏怠。德国历史家不单是完全失去了文化进步和文化评价之广大的见解,他们不单是政治的(或崇教的)傀儡;他们甚至于禁制了这种广大的见解。人首先必须是“德国的”必须是“德国民族的”;由是他才能判别历史之价值和非价值。……“我是德国人”成为一种论据“德国超越一切”便是一种原理。
德国人代表了历史上“一般之伦理秩序”;他们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乃是他们是自由之负担者;与十八世纪,则他们是伦理的恢复者,是风教的恢复者。这里有着依于德意志帝国而开明的所谓历史这么一种东西;这里我恐怕即使反犹太的历史也是一H·V·德里契克所不以为耻的皇朝历史。最近一种庸妄的见解,一种幸而溘逝的斯威比美学者维西尔
 的理论,使德国各地报纸将它当作每个德国人必须最先赞成的真理。
的理论,使德国各地报纸将它当作每个德国人必须最先赞成的真理。
这就是说“文艺复兴和家教改革合为整个的,——美学和伦理之再生”。这样的话已经使我不能忍耐,我觉得那是我的一种意欲,甚至于是我的一种责任,告诉所有的德国人,他们的良知上有些甚么。他们的良知上积蓄了最近四百年来所有反对文化的最大罪恶!同理也因于他们在现实之前,根本怯懦,即真理之前的怯懦!因为他们的几乎是天生的虚伪,因于他们的“理想主义”。
德国人剥夺了欧洲的出产,剥夺了最近伟大时代——文艺复兴的整个意义;在文艺复兴这时候,更高的评价制度,肯定生命,保证将来的高贵的价值,正要战胜了堕落之评价,正要克了这种评价之支持者的心理。这时路德
 这个不祥的僧侣,不单是复兴了教会。否定求生意志之基督教成为一种宗教了!路德是一个不可能的僧侣,他在他的“不可能”之基础上攻击了基督教,结果却复兴了基督教!
这个不祥的僧侣,不单是复兴了教会。否定求生意志之基督教成为一种宗教了!路德是一个不可能的僧侣,他在他的“不可能”之基础上攻击了基督教,结果却复兴了基督教!
天主教当为路德开祝宴,当演戏来庆祝他。啊,路德与“伦理之再生”!悲哉一切的心理学!无疑地——德国人是理想主义者。有两次当可怖的勇敢和自制,达到了正直的不含混的,全然科学的态度,德国人却寻觅到了仍归于旧“理想”之秘密的路,却以真理调和了“理想”,其实正是规纳出一种理由去反对了科学而复兴了认说。莱布尼兹
 和康德——欧洲正直知性的两条大锁炼啊!
和康德——欧洲正直知性的两条大锁炼啊!
最后当发见了跨过两百年来颓废的桥梁,发见了超越天才之力与足以锻炼全欧洲为一政治和经济单位,并以此而支配了世界的强毅的意志,这时德国人却以他们所谓的独立战争,而毁灭了欧洲的意义,奇迹的意义,即毁灭了拿破仑的生命。
他们当为此后所发生的一切,现在存在着的一切负责,——那些反对文化的病患和痴愚,欧洲人所苦恼的所谓“民族主义”之神经病,将欧洲永远分为许多小部落,施行小政治:他们毁坏了欧洲自身之意义和容知,——他们引导着欧洲走入黑暗的狭道。除我以外有人从这黑暗的狭道觅到出路了么?有人知道再统一欧洲民族是一种伟大的共同底工作么?
三
总之我为甚么不当说出了我的怀疑?在我看来,德国人要努力实现了一种仅是鼠子可以滋生的伟大的命运。直到现在,他们将他们自己和我调和;我疑心看是否到了将来事情会变得好些。
啊,在这里,但愿我说的是虚伪的预言罢!我的自然的读者和听者已经有俄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法国人——他们都总是一样么?在知识史上,德国人总是仅仅代表了可疑的名号,他们只产生“不自觉的”的骗子(这名词指弗希特
 、席烈
、席烈
 、叔本华、黑智儿、雪尔曼契尔
、叔本华、黑智儿、雪尔曼契尔
 与康德、与莱布尼兹;他们都不过是制造而网者而已。
与康德、与莱布尼兹;他们都不过是制造而网者而已。
德国人当不会有着这荣耀:和他们知识史上是初正直的知识合一,在那种知识中,真理战胜了欺骗经过了四千多年。
“德国底知识”对于我是一种恶空气:我在这种心理的不洁之环境中呼吸困难,虽说这种不洁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天性,——这种在每一言谈和表情上都说明了一个法国人的不洁。他们不能忍受强烈的自己试炼之十七世纪,如同法国人一样,一个L.罗克法开尔德
 ,一个笛斯卡尔
,一个笛斯卡尔
 ,比之第一等德国人已是一百倍的正直。在德国,现在已没有心理学家。
,比之第一等德国人已是一百倍的正直。在德国,现在已没有心理学家。
但心理学乃是实际底地测量一个民族洁与不洁之标准。……假使人不纯洁他如何能深彻呢?德国人如同妇人一样,你不能测出他们的幽深,——他们甚么也不是这就完结。他们甚至于不能被称为浅薄。德国人所谓的“幽深”正是我刚才说过对于自己的天性的不洁:关于他们自己的天性他们不愿意洗洁。我不是可以用“德国的”这个字作为指示这种心理的坠落的形容字么?
例如就在此刻,德帝宣言解放了美洲的奴隶乃是他的基督教徒的责任;在我们好欧罗巴人看来,这也可以称为“德国的”。……自来德国人出产过一本有着深度的著作了么?我知道有些学者以为康德很深。在普鲁士的宫廷里,我也恐怕他们以H.V.德里契克很深。当我有时称赞了斯坦德尔是一个深沉的心理学家,我常常被德国大学教授逼迫为他字并出了他的名字。
四
我为甚么不追溯到底呢?我愿脑无宿物。那甚至于是我的一部野心使人想到我是卓越的德意志之蔑视者。在二十六岁的时候,我已经表露了我对德意志特质的怀疑(参看非时之思想第三部)。在我看来德国人是不可能。当我勉强想出一个与我所有的本质最反对的人,我总想起德国人。
我对于一个人的率先的试炼,乃是他心中是否有着一种距离之感;他是否随时随地看出了人与人之间的级位、阶层、和次第;他是否能区分;因为这便是构成一个君子的要件。否则他就是贱氓是难于改变的,唉唉十分纯良的一类!德国人是贱氓——唉唉因为他如是纯良!人与德国合伙即降低了自己:德国人将一切人放在平等的地位。
除了和几个艺术家交往,尤其是和瓦格纳,我敢说我没有和德国人度过一点钟的快乐的时间。假使几千年的最深沉的精神在德国人中发见,那末神庙里的女救护者至少也要宣言他们自己丑陋的灵魂是最伟大的了。
我不能忍耐,不能和这班人合流,这没有色彩感觉的种族,(唉,我便是一种颜色),是根上无力,不能行走的种族!德国人完全无足,他们只有大腿!德国人不知道他们是何等庸俗——达到了黑点的庸俗,他们从不以他们之仅是德国人为可耻。他们也褒贬一切;他们自以为可以决定一切;我恐怕他们甚至于也来决定了我。……我的全生涯就是这样的一个证明。我在他们中觅不出对于我自己的一种明敏面精雅的表示。
真的这在犹太人中还有,而在德国人中却没有了。我的本性是对一切人和平而慈惠,我没有权利与众不同,但这仍不能阻止我睁开了我自己的眼睛。我没有例外,至少对于我的朋友——我只希望我如是对待他们不是一种仁道的偏见。有五六件事我以为是一种光荣。我差不多将我所接到的每一封信都当作是一种什匿克
 。因为在好意中对于我的什匿克的态度,比在恶意中更甚。
。因为在好意中对于我的什匿克的态度,比在恶意中更甚。
我在率直地告诉我的朋友们,他们永没有思考过很值得他们辛苦研究的我的著作:我从细小之处看出他们甚至于不知道我的著作的内容。关于查拉斯图拉,我的朋友中除了以为是不可恕的无害而傲慢的著作,谁能看出那书中的更高的意义呢?十年已经过去了,这本书埋葬在一种荒诞的沉默里,没有人觉到他的责任乃是和我攻击了这种沉默。
第一个有充足精敏的天才和勇敢去做这事的人,乃是一个外国人,一个丹麦人。
 他愤怒我的所谓的朋友们。在现在德国各大学中,要觅到上年春天布兰兑斯在妥木哈舍所作关于我的哲学的那样的讲义,是可能的么?因此又证明布兰兑斯很有这理由被称为是一个心理学家。
他愤怒我的所谓的朋友们。在现在德国各大学中,要觅到上年春天布兰兑斯在妥木哈舍所作关于我的哲学的那样的讲义,是可能的么?因此又证明布兰兑斯很有这理由被称为是一个心理学家。
我自己却永远没有从这些事感到痛苦;一切“必然的事”都不会损伤我。接受命定乃是我的特性。但这也不能阻止我喜欢讽刺,甚至于世界史之讽刺。因此在投射了使全世战慄的“一切评价之新估”这绝望的霹雳之前两年,我将我的瓦格纳事件先送到世界上。仍然有的是时间:德国人又以完全误解了我而永垂不朽。这目的达到了么?好罢,我可爱的德国人,让我恭贺了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