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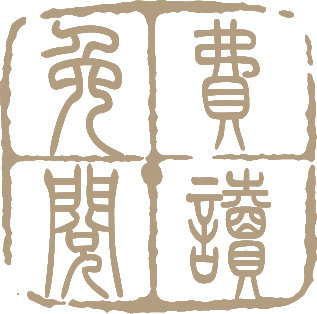
一
现在我愿意告诉你们,我的查拉斯图拉的历史。它的根本概念,永久循环,肯定所能达到的最高公式,是得之于一八八一年的秋天。我写了一条速记在一张纸上,有着这附注:“超过人类和时代六〇〇〇尺”。
那天,我散步在锡尔窪拉纳湖
 畔的大森林中;我伫立在离苏尔里
畔的大森林中;我伫立在离苏尔里
 不远的一座巍峨崇高的巨岩之旁。就在那里,我发生了这感想。假使我回溯到在这两月以前,我也能发见了一种憬悟在突然决然的形式中改变了我的一切赏味,尤其是对于音乐的赏味。
不远的一座巍峨崇高的巨岩之旁。就在那里,我发生了这感想。假使我回溯到在这两月以前,我也能发见了一种憬悟在突然决然的形式中改变了我的一切赏味,尤其是对于音乐的赏味。
或者全部查拉斯图拉都可以认为是一种音乐,我确信它的产生之重要条件之一,乃是我自己的听觉技术之新生。在拉柯落
 ,一个邻近威甤沙
,一个邻近威甤沙
 的有山泉的地方,我度过了一八八一年的春天,我和我的朋友也是作曲家的P.如斯特(则的一个新生者)发现了翱翔于我们之上的凤凰之音乐,装饰着它前此所未有的华美而鲜丽的灵羽。
的有山泉的地方,我度过了一八八一年的春天,我和我的朋友也是作曲家的P.如斯特(则的一个新生者)发现了翱翔于我们之上的凤凰之音乐,装饰着它前此所未有的华美而鲜丽的灵羽。
假使我从这天算起直到这书在不快的环境之中,在一八八三年的二月,忽然诞生,——即它的怀妊显然是十八个月。这书的最后一部我已引了几节在序文里,恰恰完成于瓦格纳在维尼斯逝世的圣洁的一刻。这恰好是十八个月,至少在佛教徒看来,我或者就是一匹母象。在这期间,我从事于“快乐的智慧”,那有一百多处是达到了无比的高处;它的结论显示了查拉斯图拉的开始,因为在第四部,在最末的前一节,它已提供了查拉斯图拉的根本思想。
在这期间我也写了《生命之礼赞》(一种对唱和合唱的圣歌)它的曲谱两年前已由E.W.弗里支
 在莱卜兹出版。或者它是这年中我的精神状态的不小的标志,这时我所谓悲剧的热情,即根本肯定的热情,充满了我的灵魂。有一天,人们会歌唱着它来纪念我的罢。似乎有着一些误解,所以我愿意加以说明,即这著作之写成不由于我;乃是由于这时我们最友好的一个俄国少女L.V.莎乐美
在莱卜兹出版。或者它是这年中我的精神状态的不小的标志,这时我所谓悲剧的热情,即根本肯定的热情,充满了我的灵魂。有一天,人们会歌唱着它来纪念我的罢。似乎有着一些误解,所以我愿意加以说明,即这著作之写成不由于我;乃是由于这时我们最友好的一个俄国少女L.V.莎乐美
 的可惊的灵感。
的可惊的灵感。
能够欣赏这篇诗歌的最后几行的人,将明白我喜欢它赞美它;因它包含着伟大。苦痛不能当作生命之障碍,“那有甚么关系,假使你没有幸福赠给我!你仍然有着你的悲愁啊!”。
在这一章里面,我的音乐也升到了伟大了,(短篇之最后音符乃是高音P,而不是C,后者是印错了)。在这年的冬天,我住在离日诺亚不远,在夏窪里
 和波多芬
和波多芬
 岬中间的可爱的拉波露港
岬中间的可爱的拉波露港
 。我的健康不很好;天气寒冷且特别多雨;我的小屋如是接近于海岸,所以巨浪的喧声,使我不能安眠。这种环境实在是极端恶劣;虽然如此,并好像证明了我的信仰,决定的一切在逆境中产生,所以我的查拉斯图拉在这样的冬天,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产生了。
。我的健康不很好;天气寒冷且特别多雨;我的小屋如是接近于海岸,所以巨浪的喧声,使我不能安眠。这种环境实在是极端恶劣;虽然如此,并好像证明了我的信仰,决定的一切在逆境中产生,所以我的查拉斯图拉在这样的冬天,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产生了。
在早晨,我常常出发,沿着南向的到若格里
 的大道,那大道从森林中升起来,给人以远海的景致。在午后,只要我的健康许可,我绕着从圣达·马尔格里达
的大道,那大道从森林中升起来,给人以远海的景致。在午后,只要我的健康许可,我绕着从圣达·马尔格里达
 越遇了波尔·芬诺的海湾散步。这地点和这周围的乡村,最使我高兴,因为它也是这深地为菲德烈第三(Frederich Ⅲ)所喜爱。在一八八六年秋天,我又碰巧到了这里,当他最后又再来拜访这小小的被忘却的幸福世界的时候。那就是在这两条路上,全部查拉斯图拉,尤其是查拉斯图拉的典型,临别了我——或者最好说袭击了我。
越遇了波尔·芬诺的海湾散步。这地点和这周围的乡村,最使我高兴,因为它也是这深地为菲德烈第三(Frederich Ⅲ)所喜爱。在一八八六年秋天,我又碰巧到了这里,当他最后又再来拜访这小小的被忘却的幸福世界的时候。那就是在这两条路上,全部查拉斯图拉,尤其是查拉斯图拉的典型,临别了我——或者最好说袭击了我。
二
要理解查拉斯图拉的典型,你们必先明白它的最根本的生理学的先决条件,我特谓之为伟大的健全。这种观念再没有比在快乐的智慧第五卷的最后一节(第三八二节)说得更明白更个人的了;“我们,新的,无名的,不易了解的生命,”那上面说着,“我们未知之将来之头胎之子——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工具,以达到我们的新的鹄的;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健康,一种自来所未有的更强,更尖锐,更坚实,更勇敢,更快乐的健康。”
“他的灵魂渴望着经验了自来评价之全山脉,欲求着环航了这理想的‘地中海’由于自己最深的经验之冒险,愿意知道了要做一个这种理想之征服者和发明者是如何感觉;也愿意知道做一个艺术家,圣人、法官、哲人、学者、教徒、神圣的老隐士是如何感觉;这样的一个人,特别需要一事,即伟大的健全——不单是占有,且要继续获得,必须获得之健全,因为他要不断地牺牲,它且必须牺牲它!”
“现在在这样的途程上,走得很远,我们勇敢更多于智慧的阿格纳特
 冒险船的勇士们,也常常船波落水,但如同我所说的,比人们所想到的还健全,健全又不断地恢德。那好像我们的苦恼和到报酬了,好像我们看见在我们面前一片未被探险过的新地,它的境界无人知晓,超越于自来已知未知的理想的国土之外,充满了美丽、新奇、可疑、恐怖、和神异、所以我们的好奇心和占有欲都极端地被激起了。”
冒险船的勇士们,也常常船波落水,但如同我所说的,比人们所想到的还健全,健全又不断地恢德。那好像我们的苦恼和到报酬了,好像我们看见在我们面前一片未被探险过的新地,它的境界无人知晓,超越于自来已知未知的理想的国土之外,充满了美丽、新奇、可疑、恐怖、和神异、所以我们的好奇心和占有欲都极端地被激起了。”
“大地上一切再不能满足我们了。唉唉有这样的美树列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良知和意识充满了这样燃烧的欲望,我们如何还能满足于现代的人类?最坏的,但那是不可免的,我们只以一种严肃望着这最高的目标和希望甚至于不去再想它。别的一种理想又奔到我们的眼前了,一种奇异的,迷人的,惊险的理想,对于那,我们不愿劝导任何人,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容易承认任何人有此权利。”
“那是一种精神之理想,哪种精神无邪底地,那就是说不自觉底地,从他的最丰裕的能力中发出,和自来所认为圣,为善,为强毅,为神异的一切相游戏;对于这种精神,一般人的最高的标准,不过是一种危险,一种废灭,一种卑弱,或者至少是一种懈怠,一种盲目,和一种暂时的自己忘却:一种超人的幸福和善恶之理想,好像是十分地非人的——例如倘在人类自来所谓严肃和尊严之旁,倘在一切姿态,言语,声音,在顾盼,伦理和义务之旁,便如不自觉的极相似的抄袭——但也由于此而最伟大的严肃才开始发生,也发生了正式的疑问,灵魂的命运变换了,时间的手臂移动,于是悲剧开始。”
三
在十九世纪之末,有谁能有对于一个在盛年的诗人所知道的,关于灵感(Inspiration)这个字的分明的意想么?如没有,我愿来说说。假使一个人有着最轻微的宗教信仰,他将不会完全反对人只是一种全能的化身,或通译,或媒介的这个观念。
启示的意念,将这种情况说得最明白;深深地痉挛而苦恼的事物,突然成为可见可闻,有着不可言说的明瞭和正确。自己不追寻而听到;自己不要求而获得:一种思想如同电光一样的闪过,必然而迅迅,——使人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是一种销魂,它的可怖的紧张,有时被一阵眼泪的横流所宽舒了,这时自己的进香由不自觉的兴奋变为不自觉的舒缓了。
这是自己完全无助的一种盛情,有着通彻全身的无限微妙的震颤之这分明的觉识。这是一种深心的快乐,在这之中,极苦痛而阴沉的感情不是相对,乃是必然会有的涣发之光的阴影。这是对于包括全部形相之世界的动律关系之一种本质(长度扩张了的动律之必然的条件,差不多是一种与感之力的尺度,是它的迫压和紧张的象征)。一切事物不自觉地发生了,就好像是一种自由,绝对,力量和神性之突然暴发。
形像和象征是不期然而然的;人不知道甚么是形像和象征的意义;一切事物都好像以最敏捷,最正确,最单纯的表现法呈现了自己。
用查拉斯图拉的话说出来,就是一切事物之自身好像合而为一,成为一种象征而出现(“这里万物抚爱地来到你的谈话里,并谄媚你,因为它们愿意骑在你的背上驰驱。这里你骑在一切象征之上驰向一切真理。这里一切言说,一切存在之言语的宝库,在你的面前打开;这里一切存在都会说话,这里一切生成都向你学习了言谈”)。这便是我的灵感之经验。我并不怀疑我可以倒溯几千年觅到了可以对我说这话的人:“那也是我的经验啊!”
四
后来我卧病在日诺亚几个星期。接着在罗马渡过了一个阴郁底夏天,在那里我逃脱了我的生命。那不是一种快乐的经验。我所不中意的这城池,一切都不适宜于查拉斯图拉的作者的这城池,沉重地压迫着我的精神。我勉强要离开它。
我到了亚克拉城
 ,那完全和罗马正相反对,且是因为纪念一个无神论者和基督教的敌人——荷亨斯塔芬菲德烈大王第二(Frederieh Ⅱ),一个正合我心的人——以对于罗马的敌意而建立起来,(恰如我有一天也要建立的城池。)但命运捉弄我:我仍不能不回到罗马去。结果在我努力寻觅一个反基督教区域绝望以后,我不得不满足于披亚萨·巴亚尔里尼
,那完全和罗马正相反对,且是因为纪念一个无神论者和基督教的敌人——荷亨斯塔芬菲德烈大王第二(Frederieh Ⅱ),一个正合我心的人——以对于罗马的敌意而建立起来,(恰如我有一天也要建立的城池。)但命运捉弄我:我仍不能不回到罗马去。结果在我努力寻觅一个反基督教区域绝望以后,我不得不满足于披亚萨·巴亚尔里尼
 因为要尽可能地避免了恶气味,我耽心着巴拉梭·德尔·圭林那尔
因为要尽可能地避免了恶气味,我耽心着巴拉梭·德尔·圭林那尔
 的人是否有一间一个哲学家可以居住的安静的屋子。幸好有一间高出于披亚萨的敞屋,我可以看到罗马的全景,并能够听着远处流泉潺潺,一切歌中之最寂寞之歌——夜之歌,在这里写成了。在这时,我不断地为一切无名的哀之动律所袭击,用文字将它说出来就是;“通过了永生的死寞!”
的人是否有一间一个哲学家可以居住的安静的屋子。幸好有一间高出于披亚萨的敞屋,我可以看到罗马的全景,并能够听着远处流泉潺潺,一切歌中之最寂寞之歌——夜之歌,在这里写成了。在这时,我不断地为一切无名的哀之动律所袭击,用文字将它说出来就是;“通过了永生的死寞!”
……在夏天,我又转到最初查拉斯图拉的思想曾经如同电光一样闪过了我心的那圣地。我孕育之查拉斯图拉的第二部。十天就够了。无论是第一二和第三部我不要求更多的一天。同年冬天,在第一次以鲜朗的光明充满了我心的尼斯
 之宁静的苍天之下,我创造了查拉斯图拉的第三部,——并完成了这著作。全部的著作占去了我不到一年的光阴。尼斯附近的景物和许多隐蔽的角落和高峰,为我的难忘的瞬间而圣洁。
之宁静的苍天之下,我创造了查拉斯图拉的第三部,——并完成了这著作。全部的著作占去了我不到一年的光阴。尼斯附近的景物和许多隐蔽的角落和高峰,为我的难忘的瞬间而圣洁。
标题着旧榜与新榜的终结的一章写于于勤地从车站爬向伊萨
 ,那奇特的摩尔人
,那奇特的摩尔人
 的山崖上的村庄。我的创作力最自由地涌流的时候,正是我的筋肉的活动力最大的时候。肉体是颖悟了,让我们取消了灵魂的问题。在这些日子,就常会被看见在跳舞。我能在山上走七八个钟头不会感到一些疲劳。我睡得甜熟,也笑得酣畅,——我完全强健而坚忍。
的山崖上的村庄。我的创作力最自由地涌流的时候,正是我的筋肉的活动力最大的时候。肉体是颖悟了,让我们取消了灵魂的问题。在这些日子,就常会被看见在跳舞。我能在山上走七八个钟头不会感到一些疲劳。我睡得甜熟,也笑得酣畅,——我完全强健而坚忍。
五
几个这样的十天,在查拉斯图拉产生的这时候,尤其是自此以后,差不多是我的最苦痛的时候。要酬偿了自己的不朽的生,当是一种最高的代价,在他的一生中,他必须死去了好几次。这便是我所谓的伟大之怨恨:一切伟大、无论是一种著作或一种行为,只要它一完成即紧接着反对了它的创作者。因为现在他是它的创作者的这事实使他衰弱。从此他不能再支持了他的行为。他不能严正地面对着它。
要完成了人类命运的结所紧缚着的事情,人不能如愿操持。那差不多要压碎了自己!伟大的怨恨啊!别的一事则是得胜之奇异的沉默。寂寞有七重厚皮,无物能够深入。你去到人们中间;你向朋友们致意;但不过是你所遇到的一种新的荒凉。他们的面目索然,或者最多不过是一种反抗的表露。在各种不同的极度中,从差不多接近了我的一切人,我经验到这后者的反抗;那好像是再没有比突然觉得自己的疏远还深的痛苦了。
没有崇敬便不能生活,这样高贵的性质是少有的。第三则是皮肤对于细小的棘刺之无稽的敏感,在未屑事物之前的一种无助。在我看来这好像是自卫力之可惊的耗费所当然产生的结果,因为自卫力本是“创造的”行为的先决条件,发生于自我内心之深处。因此自卫力衰退了,即不再有新的精力补充。我甚至于消化停滞,倾向因循,太容易感到冷酷和怀疑,那种怀疑不过是因果不明之故。
在这样的情形中有一次我感觉到一群中的近来,由于我心中更温和与更慈惠的感情之回复:而以前我或者只是用眼睛看见了的。所以现在它们对我传达了温暖了。……
六
这著作是完全无对的。让我放下了作者不说:自然再没有产生过这样一种出自过盛的力之产品。这里我的德阿尼西斯的思想成为最高行为;以它为准则,则一切人类的行为都好像是狭隘而可怜。在这种猛烈和飞腾之恐怖的大气中,哥德或莎氏比亚也将窒息;比之于查拉斯图拉,但丁
 仅不过是一个皈依者,并不是最初创造真理的人——不是一种世界支配的精神,一种命运;吠陀诗人
仅不过是一个皈依者,并不是最初创造真理的人——不是一种世界支配的精神,一种命运;吠陀诗人
 亦仅是僧侣,甚至于不配为查拉斯图拉解鞋。
亦仅是僧侣,甚至于不配为查拉斯图拉解鞋。
——所有这些事实都还不大重要;不是说出这著作所涵藏的生命之距离和苍天之寂寥之感。查拉斯图拉有着这永久的权利说出:“我在我的周围画了圆圈,和神圣的疆界。越到了极高迈的高峰,和我上升的人越少。我为我自己建造了一派永远更神圣的山脉。”所有一切伟大灵魂之善和精神都连合起来还不能创造了查拉斯图拉的一篇谈话。他所升降的云梯没有边际;他比任何人已经看见更远,意愿更远,并去得更远。
他在每一个字之中,在一切精神之最肯定之说教中,反对了自己。但是在他心中,一切矛盾都溶融为一种新的统一。人类本质中最高和最低的力,最甘美的,最轻盈的,最恐怖的,都以一种永恒的确然从一个源头奔流。在他之前无人知道甚么是高,甚么是深;也不知道甚么是真理。在这种真理之启示中没有一瞬间被预料或被最伟大者所猜透。
在查拉斯图拉以前无智慧,无灵魂之试练,无言谈之技艺:最熟习,最普通的事物现在说出了末之前闻的言语。每句话以热狂而微颤。雄辩成为一种音乐。电光投射到梦想不到的将来。比之于这种回复到绘画性质之文字,自来一切寓言的应用都不过是怯懦可怜的儿戏而已。看哪,查拉斯图拉如何从山头上下来,他如何恳挚地对一切人讲说!看哪,他如何温和地对待了他的敌人。
一切僧侣们,他如何和他们共同受苦!这里每一刹那,人是被超越过了,“超人”的观念成为最伟大的现实——自来在人类心中一切所谓伟大都沉沦在下,距离无限遥远。宁静的气质,轻捷的足,无往而不在的放肆和丰饶,以及一切查拉斯图拉的特点自来都没有被思考过以为与伟大之要素有关。真的就在这宇宙的界限内,在这种对立之和解之中,查拉斯图拉感觉到自己乃是一切生物之最高典型:当你听到了他如何说明他自己,你将不再去勉力寻觅和他相等的人。
“有最长梯子之灵魂能到最深的地方。”
“最丰听灵魂,在本身中能向前奔绝和遨游。最贫乏的灵魂则为快乐而将自己投于偶然之中。”
“存在之灵魂投入于生成;占有之灵魂寻求达到愿望和渴望:”
“灵魂从自己逃脱,又在更大的范围中追及了自己,对于最智慧的人最易为愚昧所引诱。”
“在最自爱的灵魂的心中万物有自己的逆流和顺流,有自己的泡沫,有自己的洪涛。”
 但这就是德阿尼西斯的精义。别的考虑也引到了这同样的观念。查拉斯图拉的典型所引起的心理问题是这样:极端否定,实行否定了自来人类所肯定的一切,而仍然反对一种否定的精神。
但这就是德阿尼西斯的精义。别的考虑也引到了这同样的观念。查拉斯图拉的典型所引起的心理问题是这样:极端否定,实行否定了自来人类所肯定的一切,而仍然反对一种否定的精神。
他背负了命运的最沉重的重负,他的生业便是一种命定,他如何还能是精神中之最轻捷者,和最优越者——如何还会是一个跳舞者?于现实有着最严刻和最可恐怖的见解,他思考着最“深的思考”,如何还能在这些事物之中自望着生存,而且对于这生存之永久的循环也无怨恨?——反之为甚至他有这理由以为他自己之生存便是万物之永久的肯定,极端的,无边的,亚门和肯定?
“在一切至深之处,我为生命携带着我的肯定之福祉。”但这仍是德阿尼西斯的精义。
七
当这种精神自言自语的时候,他用着甚么言语呢?我是圣诗之言语之发明者。听听在日出之前,查拉斯图拉之自言自语罢?(第三部第四十八章)。这么一种碧玉的快乐,这么一种神圣的温柔,在我以前无人说过。甚至于德阿尼西斯的最深沉的忧郁,也成为一种诗歌。我以夜之歌作一个例,——因于光与力之充裕,因其日光性,一种不朽的悲愁,遂判定不能相爱:
“正是夜的时候,现在一切迸涌底泉水更高声朗吟。我的灵魂也正是一派迸涌的流泉。正是夜的时候:现在只有一切爱者的歌声清醒。我的灵魂也是一个爱者的歌声。”
“在我心中,有着一种永不平静,永不能使之平静的心情渴望着说话。在我心中,有一种爱之渴求自说着爱之言语。”
“我现在是光:唷,但愿我是黑夜!但这是我的岑寂周围为光辉所环绕着。”
“唷,我如夜一样的黑暗!我将如何愿意吮吸着光的乳房哟!”
“我甚至于要祝福你,你们灿烂的小星,你们高空的光辉之虫,——我也为你们光辉之赠礼所祝福。”
“但我居于我自己的光辉里,我自己再饮下从我爆发出来的火燄。”
“我不知道受施者的幸福;我常常想着偷窃比受施更甘甜。”
“我的贫穷是我的手不断地赠贻;我的嫉妒是我看着期待的眼光和渴望之灿丽的夜。”
“唷,一切赠贻者的不幸哟!唷我的太阳的隐没!唷贪求的贪求!唷餍饱时候的猛烈的饥饿!”
“他们从我取去,但我触到了他们的灵魂了么?在赠贻和受施之间,有一巨壑;最小的巨壑最后才能渡过。”
“从我的美,生出一种饥饿:我欢喜损伤了我所照耀的人们;我欢喜劫掠我给与赡礼的人们!——因此我饥饿于为恶。”
“当别的手向我伸出,我撤回我的手;我踌躇如同在急流时忽然停止的小瀑布!——所以我饥饿于为恶。”
“我的富裕,默想着这样的报复:从我的岑寂涌出了这样的恶念。”
“我的赠贻中的快乐死于赠贻;我的道德以自身的富裕而倦怠!”
“永久赠贻者是危险的,恐怕他会失去他的羞耻;永远布施者的手与心以布施而变得更无情。”
“我的眼不再为求乞者的羞耻而富裕;我的手为空乏的手之颤抖而变得太严刻。”
“我的眼泪消逝到何处去了,我的柔和的心沉落到何处去了。唷赠贻者之岑寂!唷发光者之沉默哟!”
“许多太阳环行于太空:它们以光辉对一切黑暗讲说——对于我它们却沉默无言。”
“唷这是光辉对于发光者的敌意:它不情地追赶着它的路程。”
“一切太阳之前进:心中对于发光者怨恨,对于太阳很凄冷。它们追赶自己的路程如一阵暴风雨:这便是它们的前进。它们跟随着它们的无尽的意志:这便是它们的冷酷。”
“唷你们孤独的,你们黑暗的,你们黑夜的人们,你们只是发光者得到了温暖!唷你们只是从光之乳房饮乳和休息。”
“唉冰雪包围着我;我的手以冰之冷而然烧!唉,我心中有着一种焦渴;它紧追在你们的焦渴之后急喘!”
“正是夜的时候!唉我不能不是光辉!并且渴想着一切属于夜的——焦渴着岑寂!”
“正是夜的时候!如同泉水一样,我心中的热望喷发,我渴望着说话。”
“正是夜的时候!现在一切迸涌的流泉更高声朗吟。我的灵魂也是一派迸涌的流泉。”
“正是夜的时候!现在只有爱者的歌声清醒。我的灵魂也是一个爱者的歌声。”

八
这样的东西自来没有人写出、感觉、受苦;除了一位大神:德阿尼西斯。太阳在光辉中的岑寂对于这种诗情的回答,当是阿里德尼
 。……除我以外谁知道阿里德尼是甚么!自来没有人猜透了这个谜。有一天查拉斯图拉将严重地决定了他的生业——那也是我的生业。不要有人误解了它的意义罢。它肯定到辩正,到救济了一切过去的事物。
。……除我以外谁知道阿里德尼是甚么!自来没有人猜透了这个谜。有一天查拉斯图拉将严重地决定了他的生业——那也是我的生业。不要有人误解了它的意义罢。它肯定到辩正,到救济了一切过去的事物。
“我行走在人们中间,如同在未来之碎片中间:我所想望的未来之碎片中间。”
“我全部的想像和努力是将碎片,和谜,和可怕的偶然品,组合为一体。”
“假使人不是诗人,不是谜之解释者,不是偶然品之救济者。我何能忍受做一个人!”
“救济过去并将每个‘它已如此’变为‘我愿它如是’!——只这我名之曰救济!”
 在别一章里他严格地也是正确地说明了人对于他是甚么,——不是爱的对象,也不是可怜的对象。——查拉斯图拉甚至征服了他对于人类的憎厌:在他看来人是一种始初,一种原料,正需要雕刻的顽名。
在别一章里他严格地也是正确地说明了人对于他是甚么,——不是爱的对象,也不是可怜的对象。——查拉斯图拉甚至征服了他对于人类的憎厌:在他看来人是一种始初,一种原料,正需要雕刻的顽名。
“没有意志即没是评价,没有创造!唷这种大倦怠永远离开我罢!”
“在知识中,除了我的意志之创造和生成的贪欲,我感觉空虚。”
“假使我的知识中有着天真,那是因为其中有创造意志的原故。”
“这意志引诱我远离了上帝和诸神;假使有着诸神还有甚么创造哟!”
“我的炽热的创造之意志,永远驱我向着人:如同铁锤之向着石头。”
“唷你们人们,在石头里熟眠着我的一个理想,我的一切梦想的象征——,它应该熟眠在最坚致,最丑陋的石头里!”
现在我的铁锤放肆挥击着它的囚牢。石头的碎片飞舞:那于我算甚么呢?
“我要完成我的工作:因一为个影像临到我——一切中之最宁静最光明者临到我!”
“我的兄弟们哟,超人之美如同一个影像临到我!现在诸神于我算甚么呢?”

一种最后的观察用点号表示出来。在德阿尼西斯的生业之中,有着铁锤之无情。它的最先的条件之一乃是一种确然的欢喜,即使在破坏的时候。一种德阿尼西斯底本质之重要象征,乃是支配是坚强你自己!是深信一切创造者都是坚强而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