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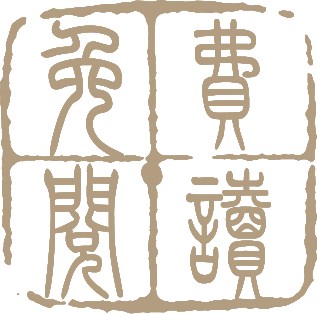
一
在人类,太人类了这文和这文的两篇续篇,标出了一种危机。这是为自由的精神面写的著作:里面的每一句话都表现一种胜利——它能够使我萧清了我的天性所隔膜的一切。理想是我很隔膜的。这本书的标题是:“在你们所看见的理想的事物中,我看见了——人类,唉唉,太人类了!”……我更理解人类。“自由的精神”的意义只能解作成为自由,并重新有了自己的一种精神。
这书显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调子和音韵!人将以它为明敏冷静,甚至于有些地方是严刻和讥嘲。一种高贵而温雅的精神,好像是与一种热情的激流从事着不断的争斗。为纪念佛尔特
 死后的百年祭,这书才早在一八七八年出版,这不是不有意义的。因为佛尔特与他后来的著作家,正相反,乃是一个卓绝的智识之贵胃,真的我也一样。将佛尔特的名字放在我的著作里,这是进一步,向着我更前进了一步。
死后的百年祭,这书才早在一八七八年出版,这不是不有意义的。因为佛尔特与他后来的著作家,正相反,乃是一个卓绝的智识之贵胃,真的我也一样。将佛尔特的名字放在我的著作里,这是进一步,向着我更前进了一步。
假使你更精密底地考察了这本书,将发现一种严峻的精神,深悉一切理想之隐秘的角落——它的根据地和最后逃避所。火炬在手(它的火光不是微顾的火光),我以一种深入一切的光芒烛照了这暗面之世界。
那是争斗,但是没有火药和烟火的争斗,没有争斗的姿态,没有激情和扭折的肢体,因为这些事物之自身也仍然是一种理想主义。种种认误,掷到冰块上;这种理想不必驳斥,它冻结了;这里,例如,天才也冻结了;围着这一隔圣人边冻结了;在重厚的坚冰之下,英雄也冻结了;最后则信仰,即所谓的“皈依”和“慈悲”,也冻结了。这本书中的“物之自相”也冻结了。
二
我在第一次摆里德节期中,开始写这本书;我当时对于环境的落漠之感,便是这本书的先决条件之一。谁有着我所遇到的所谓幻像这类的观念,便可想像到我在摆里德有一天醒来是如何地感觉。
正好像我在做梦。我在甚么地方呢?甚么我也不认识了;我也不认识瓦格纲你搜寻我的记忆,但无用;特里斯镇,远海中的幸福之孤岛:没有一丝毫儿相似!当这举行奠礼的无比的日子,实行庆祝的小小的亲密的集团,心中充满了最精微的敏感:这也没有些须的痕迹!其后甚么发生了呢?瓦格纳成为德国化了!瓦格纳之徒已战胜了瓦格纳了!——德国艺术呀!德国作家呀!德国啤酒呀!
……所有我们最明白瓦格纳艺术是诉与那一班优秀也艺术家,那一种赏味之宇宙观的人,现在有了瓦格纳装饰了德意志的道德,都不胜茫然起来。我想我懂得瓦格纳派,我有他的三代的经验,从以瓦格纳和黑智儿混为一谈的布郎德尔起
 ,到摆里德报纸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又将瓦格纳和自己混为一谈了。
,到摆里德报纸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又将瓦格纳和自己混为一谈了。
我曾经从“美丽的灵魂们”听到了各种关于瓦格纳的忏悔。愿以我的王国。交换了明智的一言!那些人之多,已足使你头发倒竖!诺尔·泼尔,苛尔
 ,和无量数和他们一样的人们。没有一个低能儿不在数,——甚至于反犹太人也在内。可怜的瓦格纳啊!他到何处去了?是否他走到猪群里去了!是的,走到德国人中去了!
,和无量数和他们一样的人们。没有一个低能儿不在数,——甚至于反犹太人也在内。可怜的瓦格纳啊!他到何处去了?是否他走到猪群里去了!是的,走到德国人中去了!
有一天为启发后代,他们应当有一种真正的摆里德标本,最好是保存在酒精里,标题着:“德意志帝国之柱石,一种精神之模范”——因为这正是所缺乏的。……但是够了!突然,我离开那地方几个礼拜,不管一个可爱的巴黎少女竭力想安慰我;我对瓦格纳以一通十分简单的致命的电报告辞。
在深藏于波来尔瓦德
 森林中的一个叫作克林真伯宁
森林中的一个叫作克林真伯宁
 的小村落,我忍着我的苦闷,和我对于德意志的侮蔑,如同一个病人一样。——后来,渐渐地在“耕黎”这标题下,我写了几句话在我的笔记里,都是最强烈的心理的观察,尽可以在人类太人类了这论文中可以看到。
的小村落,我忍着我的苦闷,和我对于德意志的侮蔑,如同一个病人一样。——后来,渐渐地在“耕黎”这标题下,我写了几句话在我的笔记里,都是最强烈的心理的观察,尽可以在人类太人类了这论文中可以看到。
三
我的突然的转变,不单是由于和瓦格纳的绝交,也由于我为我的天性之整个的纷乱受苦,与瓦格纳或在巴锡尔教授职之分离,都不过是一种病象而已。一种急燥征服了我,我看出来正是稍稍自省的最好的时候。即刻我可惊地看分明了我已浪费了多少时间——如何地无用,如何自愿以我的全生存作为一个语言学家,把这当作我的终生的事业。我以这种错误的谦恭为可耻。
……有十年之久,我绝对没有得到精神的营养,我没有得到有用的知识,只是为追求枯燥的学者之饤饾琐屑而丢下了无数的事物。盲目底地,小心底地,耙搔古代希腊的文学这便是我不能不做的事情!我看出我自己,憔悴瘦削和可怜了:我的知识之宝库中完全缺少了现实,只有魔鬼知道“理想”之类有价值!
一种积极然烧的焦渴占有了我:自此以后我的研究完全在生理,在医药,在自然科学范围之内,——我甚至于被我的生业逼迫着又再去实行研究了历史。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这种关系,即在一种与本性不相容的职业之中要调和了虚空和饥饿的感情,便不能不要求麻醉的艺术——例如瓦格纳的艺术。在细心观察之后,我也发现了大部分的青年也感受了同样的苦恼:饮鸩止渴,将错就错。
在德国或者更正确地说在帝国内,大多的人都择业太早,后来都在不可逃避的负累下面凋惫。……这样的人需要瓦格纳作为麻醉剂,使他们忘却自己,使他们从自己有暂时的逃避。多久呢?啊,有着五六小时的逃避而已!
四
在这个时候,我的本性绝对地反对任何进一步的自弃或自误。任何形式之生活,最不适宜生存的情境,疾病,贫穷——一切我认为比无价值的自私更有价值的事物,我以无智和年幼陷溺在里面,后来也仍欲以纯然的惰性和所谓责任心使我不能振据。这时又恰巧我遇到我从我父亲所得的坏遗传,一种可算作夭亡的根本的条件。疾病渐渐给我以我的自由,给我各种突然的决裂,各种强力和暴烈的变动。
这时我不以失去善意受苦;正和反我还得到更多的。疾病也同时给我这权利,完全倒转了我的生活形态;它不单是许诺且实际底地命令我忘却;它加重了休息,从容,期待和忍耐之必要。所有这些的意义,就是思考!
……我的眼疾已足以使我停止了蛀书,质言之停止了我的言语学:我丢开书籍了!有几年工夫我甚么也不读——我赐给我自己的最伟大的恩惠啊!事实上那个原来的自我已被埋葬了,它曾经消失了自己,当他被逼迫着去听从了别人(这就是所谓读书的意义)!但它又慢慢地苏生,生性地多疑地,最后它又说话了。我从来没有过在我的命中最病最苦痛时候的这样的幸福。
一个人必须考察一下,白天之曙晓,或漫游者和他的影才知道回到自我的意义;那是至高上的恢复!……别的肉体的恢复不过是它的一种简单的结果而已。
五
人类,太人类了,这样强烈的自己锻炼之纪念碑的著作扫清一切超等之欺骗,“理想”“美的情感”,和别的我所吞咽的温柔。我在梭林陀
 写成了这本书的大网;在比梭林陀还恶劣的环境之中,在巴锡尔的一个冬天,将这书完成。事实上P.加斯特
写成了这本书的大网;在比梭林陀还恶劣的环境之中,在巴锡尔的一个冬天,将这书完成。事实上P.加斯特
 对于这本书负了很大的责任;他是巴锡尔大学的学生,对我极热心。我因为头痛,缠裹着绷带,我口述,由他书写和校正。他是实际的编者,我仅仅是一个作家。
对于这本书负了很大的责任;他是巴锡尔大学的学生,对我极热心。我因为头痛,缠裹着绷带,我口述,由他书写和校正。他是实际的编者,我仅仅是一个作家。
当我看到了这书的完成(很使这时正在严厉的病中的我吃惊呢),除了送别人以外,我又送了两本稿本到摆里德去。就在同时,我也接到了一本华丽的巴尔西佛尔歌剧的稿本,有着瓦格纳亲笔题字:“给我的亲爱的友弗来德里克·尼采,教会董事里查德,瓦格纳赠。”
这两种著作的投赠,我好像听见了一种信号。这好像两剑交手以后的声响?无论如何我们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都仍然沉默。就在这个时候摆里德小册子最先发行了:我以是知道为甚么这是最洽当的时候,我应当照着我所做的去实行。啊令人难相信!瓦格纳成为虔信的了。
六
在那个时候关于我自己,我所想的(1876年)即这个可怕的保证,我以为我的生业及其世界史之意义,都透彻地说在这本著作里,尤其在最透关的一节里。虽然由于我的天性的敏捷,我避用了“我”这个渺小的字。这时,世界史之光荣所闪照了的不是叔本华和瓦格纳了,乃是我的一个朋友,卓绝的保罗·吕博士
 ——幸而也是太精敏的人(别人则不能如此)。
——幸而也是太精敏的人(别人则不能如此)。
在我的读者中,我有着许多失望的事,例如一个典型的德国教授,总以为上面所说的那一节使他不能不以全著作为一种进步保罗·吕主义。事实上这本书有五六处与我的朋友的主张不同:读者只要一读伦理之谱系的导言即可知道。
这一节的文字是:“那末甚么是这一个最勇敢最冷静的思想家,伦理感情之起源这书的作者(参看尼采第一个外伦理主义者)所得到的结论,——由于他的锐利而绝决的析分了人类行为得到的结论?他说“伦理的人”之不可知亦如物质人一样,但不可知的世界并不存在。谁料到呢这个大前提在历史知识的锤击下面磨得尖而且锐(参看一切评价之新估),在未来的某时(1890年罢!)或者可以作为一柄巨斧斩断了人类之“形而上学的要求”的根本。无论那是人类的幸或不幸,谁能预料到呢?但无论如何这个大前题引出了至大底影响,即刻丰裕而可怕的,以一切大智性所有的丹纳斯之脸
 看透了世界”。
看透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