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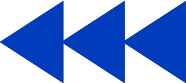
我驶过清晨明亮的阳光,道路不时拐入浓密的松林之中,经过一排排度假小木屋。亚特兰大就在北边一小时路程之外,这附近的人显然企图借地利大赚一笔。我经过了一个名叫“松山”的小镇,它似乎拥有你想在内陆旅游胜地找到的一切。这里挺迷人,店铺也挺好,就缺一样东西——一座山。想想它的名字,这里有点儿让人失望。我特意选择这条路,是因为“松山”在我单纯的脑子里唤起了一番幻景:清新的空气、陡峭的悬崖、散发着馨香的森林和翻滚流动的小溪——这儿是那种你也许会撞见约翰小子·沃尔顿的地方。然而,如果当地人为了多挣一块钱,而把事实夸大了一点点儿,谁会去责怪他们呢?你可别指望人们会专程开几英里路,来参观一个名叫“松平地”的地方呀。
田野慢慢变得起伏多山,但绝不陡峭,在道路前面来了一个温柔的下坡,滑向了暖泉。多年来我一直渴望去那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除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那儿去世之外,我对那个地方一无所知。在得梅因选举大楼的主楼梯两旁,陈列着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报纸头版,令小时候的我为之深深着迷。其中有一张上说:“罗斯福总统逝世于暖泉。”即使在那时,我也已经认为它听上去真像个长眠的好地方。
结果呢,暖泉果然是个好地方。这儿只有一条主街,一边是家老旅馆,另一边是一排商店,不过都重修成了昂贵的时装店和礼品店,专门向亚特兰大的游客开放。里面的东西全都假得明明白白——就连室外背景音乐也不例外,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不过我相当地喜欢。
我出城向小白宫驶去,它大约在城外2英里处,停车场上几乎是空的,只有一辆旧巴士,一群上了年纪的公民正从上面下来。这是来自“炮仗,佐治亚”或者“光腚,亚拉巴马”此类地方的耶稣浸信会包的车。那些老人跟小学生似的,吵吵闹闹,激动万分,在售票亭前面加我的塞儿,一点儿没意识到我会毫不犹豫地推开一位老人,尤其是浸信会教徒。但我只是和气地微笑着站到了后面,想到他们即将不久于人世,便觉得安慰多了。
我买了票,很快就在去罗斯福庄园的上坡路上超过了那些老人。小路穿过高高的松树林,那松树似乎要无止境地向上、再向上,结果把阳光封锁得那么彻底,让树下的土地光秃秃一片,就像刚刚清扫过一般。小路两旁排列着来自每个州的巨大石块,显然每位州长都曾被要求献上本地的一块石头。它们在这里排成一队,像个光荣的护卫队。笨点子开花结果,这可是不常见的呀。许多石头被切成那个州的形状,打磨得亮光闪闪,再刻上州名。可是剩下的那些呢,显然没领会这一计划的精髓,就是平平常常的一块石头,挂着个简洁的小牌子:“特拉华,新罕布什尔。”艾奥瓦的献礼像我预期的那样,是谨慎的中间派。石头倒是切成了本州的形状,可惜啊,干活的人显然从没尝试过这种营生。我猜想,他肯定是一时冲动投了最低标,没承想居然一举中的,至少艾奥瓦还找到块石头送去了,我还挺害怕会是一块烂泥巴呢。
在这一奇观的远处,是一栋白色的平房。从前它曾是庄园邻居的家,现在成了博物馆。和美国的这类博物馆一样,这里搞得不错,很有意思。墙上贴满了罗斯福在暖泉的照片,玻璃柜里陈列着许多他的个人物品——他的轮椅、拐杖、腿架和其他类似装备。其中有些精巧得出人意料,能挑起人的一种病态的兴趣。因为罗斯福一直非常小心,不让公众把他看成是个瘸子。可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正在审视他脱了裤子的模样。有一个房间格外吸引我,里面摆满了他当总统时人们亲手制作、送给他的礼物。这些东西很可能立刻就被塞进了一个巨大碗橱的后面。有成打的雕花拐杖,上面是木镶的美国地图;还有许多海象牙和蚀刻石板,雕刻着罗斯福的头像。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精美,着实令人吃惊。每一件东西都代表着几百个小时的精心雕刻和不知疲倦的抛光打磨,却只是为了送给一个陌生人。对这个人来说,这不过是为他的个人纪念品大军增加一员罢了。我被这些玩意儿迷住了,几乎没注意到那些老人也闯了进来,虽然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却丝毫不减活力。在一个展品前,一位头发蓝灰的女士挤到我前面,匆匆瞟我一眼,意思是:“我是个老人,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然后就把我从她脑子里打发掉了。“我说,哈泽尔,”她大声喊道,“你知道吗?你和埃莉诺·罗斯福是同一天生日呢!”
“真的吗?”隔壁有个刺耳的声音回答。
“我自己和艾森豪威尔是同一天生日,”那蓝发女士依然高叫着说,并为巩固自己在我前面的位置,晃了晃她那丰满的屁股,“我有个外甥和哈里·杜鲁门一天生日。”
我很想攥住她两只耳朵,然后把她脑门猛掼在我膝盖上,但我将这一念头把玩片刻之后,还是步入了另一个房间,发现这里有个入口通往一家小剧院。剧院里放映着噼啪作响的黑白电影,都是表现罗斯福和脊髓灰质炎的斗争,以及他长期待在暖泉的生活。他试图把生命揉进细长的双腿,仿佛它们只是睡着了而已。电影也很完美,由一位合众社的记者撰稿并旁白,感人至深但并不过分煽情。那无声的家庭影片里,每个人物的动作都急匆匆的,就好像镜头之外有人在咆哮着让他们快一点儿。这电影与罗斯福的腿架一样,激起了人们窥阴似的狂热。在这之后,我们终于被放行去见识小白宫的真身。我飞快地跳到前面,免得和那些老人分享这种体验。它就在另一条小路上,要穿过更多的松树,越过一个白色的岗亭。令我吃惊的是,它竟然那么小,不过是林中一栋小小的白色木屋,只有一层楼,五个小房间,都镶了深色木头。你根本没法儿相信这会是一位总统的财产,尤其是像罗斯福这样一位有钱的总统,毕竟,他拥有周边绝大多数的田产,包括主街上的那家旅馆,几栋小别墅和泉水本身啊。然而,小屋那种特别的紧凑反而让它更加舒适迷人了。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显得很舒服、很有人气。你忍不住地想把它占为己有,即使这意味着你得到佐治亚来享用它。每个房间都有一段简短的录音解说词,告诉你罗斯福怎么工作,如何接受治疗。可是它没告诉你,他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和他的秘书露西·默瑟来点儿乡村风味的亲密接触。她的卧室在起居室的一边,而他的则在另一边。录音介绍压根儿没提这个,但它却指明了埃莉诺的卧室——被塞进房子的最后面,而且绝对比秘书的差,大多数时候是用来当客房的,因为埃莉诺很少到南方旅行。
离开暖泉几英里之后,我改道上了一条通往梅肯的风景线,但是沿路好像并无多少风景。不是没什么特别的风景,而是干脆没风景。我开始疑心,地图上那些风景线路恐怕是胡乱画上去的。我想象某个从未去过泽西市南边的家伙,坐在纽约办公室里说:“暖泉到梅肯?嚯,听起来不赖呀。”然后认认真真地画下了标志风景线的橙色虚线,舌头从嘴角边轻轻地探出一点点儿。
梅肯挺好的——所有的南方小镇似乎都挺好。我停车到一家银行去取钱,为我服务的女士来自大雅茅斯,这让我们两个都小小地激动了一下。然后我继续赶路,穿过了奥蒂斯·雷丁纪念大桥。美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南方,都有这种潮流,喜欢用当地杰出人物的名字为水泥建筑起名——西尔威斯特·C.格拉布纪念大桥、切斯特·奥弗里大堤,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习惯实在古怪。设想一下吧,你一辈子辛苦工作,排除万难爬到社会顶端,投入漫长光阴,忽视家人亲情,背后中伤他人,被认识的每个人看成狗屎,到头来只落得塔拉普萨河上一座公路大桥的名字,好像实在有点儿划不来啊。然而,不管怎么说,至少这座桥得名之人我还是听说过的。
我循16号州际公路向东驶向萨凡纳。那是穿越佐治亚红土平原,长达173英里无法形容的沉闷之旅。我花了炎热又毫无回报的五个小时,才到达萨凡纳。而你们呢,幸运的读者,只须眼睛掠到下一段即可。
我兴奋地站在萨凡纳的拉斐特广场上,置身于砖铺小路、涓涓溪流、垂着西班牙苔藓的浓郁树木之中。我的面前矗立着一座精致的、有着新亚麻的洁白的大教堂,一对哥特式的尖顶高耸入云。在它周围,是一些200多年的老房子,砖墙已经风化,抵挡风暴的窗板显然还在使用。我竟然不知道美国还存在着如此完美的地方。萨凡纳有20个这样的广场,凉爽安静地躺在树木的天棚下,旁边那些细长笔直的街道也是同样阴凉而安宁。只有当你跌跌撞撞走出这片市内雨林,进入现代城市的开阔街道,暴露在沸腾的骄阳之下,你才会意识到南方到底有多么闷热。现在是10月,在艾奥瓦,已经是法兰绒衬衫和热甜酒的季节了,可是这儿呢,夏天依然不依不饶。刚刚早晨8点,商人们就已经在松领带、擦额头了。要是在8月,会热成什么样呢?每个商场和餐馆都开着空调,一走进去,汗水便冻干在你胳膊上,再走到外头时,热烘烘的空气扑面而来,仿佛狗的喘息一般。只有在广场里,气候才能达到一种舒适的平衡状态。
萨凡纳是个十分诱人的城市,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逛了好几个小时。该城有1000多栋历史建筑,其中许多仍然有人居住。这是我去过的,除了纽约之外,第一个人们当真住在闹市区的城市。这是多么大的差别啊!你会看到孩子们在街上踢球,或者在门廊里跳绳,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活跃、那样生机勃勃。我沿着奥格尔索普大街的鹅卵石人行道,踱向了殖民纪念墓园。这里到处是剥蚀风化的纪念碑,还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本州历史名人的墓碑:阿奇博尔德·布洛克,第一位出身佐治亚的总统;詹姆斯·哈伯肖,“一位商界领袖”;还有巴顿·格威纳特,他在美国这么出名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参与签署了《独立宣言》,二是他拥有殖民历史上最傻的名字(button,意为扣子)。萨凡纳的人们一不小心,就会把老巴顿给弄丢了。纪念碑上说他可能就埋在我目前站立的这块地方,也可能是拐角那儿,或者干脆就在别的什么地方呢。这么说吧,你可能走上一整天也弄不清自己是不是踩到了巴顿。
萨凡纳的商业区永远地被冻结在了1959年——伍尔沃思商场似乎从那时起就再没换过货。这儿有一家漂亮的老电影院——魏斯电影院,可惜关门了。闹市区电影院在美国早已是陈年旧事了,唉,真可惜!你老是读到报道里说,美国的电影工业多么蓬勃,可是现在所有的戏院都建在郊区的购物中心了。在那儿看电影你有好几十部可以选择,可是每家电影院都跟大冰箱尺寸相仿,只勉强比冰箱舒服一点儿。那里面根本没有楼厅。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没有楼厅的电影院吗?对我来说,看电影就意味着坐在楼上的第一排,跷着脚,把空糖盒扔到下面人的头上(或者,在看到更无趣的爱情场面时,往下滴可乐)并且往屏幕上砸尼布糖。尼布糖是一种甘草味的糖,估计是用朝鲜战争剩下的橡胶做成的,在20世纪50年代颇为流行。它其实是不能吃的,但你若把它嚼上一分钟,然后砸向银幕,它就会“啪”的一声粘在上面。这是一种传统,每个人都在星期六乘公汽进闹市区,去俄尔弗剧院,买上一盒尼布糖,花上一个下午轰炸银幕。
干这事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因为剧院经理雇了一帮恶狠狠的领座员,他们都从科技高中辍学,生命中一大遗憾便是没能生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这些人手拿强力电筒,在走道间来回巡逻,寻找不规矩的小孩子。一场电影中间,总有那么两三次,他们的手电会投射到某个倒霉小子的身上:只见他撅着屁股,拿着一块湿乎乎的尼布糖,定格在投掷的姿势上。他们立刻冲上去将他拿下,他就一路号叫着被架了出去。感谢上帝,我和我的朋友从来没碰上过这种事,可我们一直以为,那些受害人都会被带去经受各种电刑的折磨,然后才转交给警方,在教养院里进行长期的思想教育。多美好的日子啊!有谁敢说,郊区商业城那种鞋盒般的剧院、浴巾般大的屏幕,能够提供半点儿与闹市区电影院相媲美的东西呢?后者大如山洞,令人心醉神迷,还能激发公共意识。好像还没有谁注意到这一点,但我们也许将是最后一代觉得看电影很神奇的人了。
怀着这个令人严肃的想法,我踱过沃特街,走上萨凡纳河边新修的一条河畔人行道。河水又黑又臭,对面南卡罗来纳州的河岸一无可观,只有几家大型商店。下游更远处,是些浓烟滚滚的工厂。不过萨凡纳这边俯瞰河水的那些老棉花仓库却好极了。它们重修得并不过分奢华,底层有时装店和牡蛎吧,二楼却空着,有那么一点儿破败,散发着不可避免的颓废气息。这就是我从汉尼拔开始就一直在寻找的。必须承认,有些商店略显矫饰,其中一家叫作“全镇最可爱小店”,直令我欲做“全国最迅速的小呕吐”。门上有个牌子说:“绝对——千万不要在店内吃喝哟。”我双膝跪地感谢上帝,我永远不必见到那老板了。因为此店关着门,所以我没法儿进去参观它到底有多可爱。
在这条街的尽头,伫立着高大崭新的凯悦丽晶饭店,一看到它,我的心就直往下沉。它硕大无比,由方方正正的钢筋水泥制成,出自美国大连锁饭店深爱的“我×”建筑学院之手。无论是规模还是外观,它都与周围的老建筑格格不入,哪怕是一丝和谐都不存在。它只不过在说:“我×!萨凡纳。”在这方面,这个城市特别令人反感。每隔几个街区,你就会碰上那么个不伦不类的水泥墩子——德索托希尔顿、拉马达旅馆、最佳西部河畔饭店,正如佐治亚人所说的那样,全都诱人得像玉米饼上的唾沫。其实呢,佐治亚人没说过这种话,只是我编的罢了。不过这么说颇有点儿南方味道,你们不觉得吗?就在我快要感觉这些旅馆冒犯了我,我开始对这里心生厌烦的危险时刻,我的注意力被市立法院前面的一个工人给转移了。市法院是一栋金色拱顶的大厦。那工人操着架吹叶机,一个闹哄哄的机关,后面蜿蜒着几里长的电线,一直通进他身后的大楼。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看上去有点儿像真空吸尘器——其实啊,它看起来很像一个《外星人入侵》里的火星人——而且叫得特别响。据我推断,他那意思是想把所有树叶吹成一堆,然后就可以用手收起来了。可是每当那人收拢了一小堆树叶时,就有一阵微风将其吹散。有时候他要提着吹管跑半条街甚至更远去追一片叶子,结果剩下的树叶就抓住机会四处乱飞。显然,这种装置在邮购目录上肯定显得好极了,可是在真实世界中却永远派不上用场。我一边漫步走过,一边隐隐地怀疑:不知道齐威格公司的人是不是在幕后插手呢?
我离开萨凡纳,开上赫尔曼·塔玛吉纪念大桥,这是一座高大的钢架桥,桥面不断升高、升高、再升高,就在你二目圆睁、呼吸停止的当儿,已经把你猛甩过萨凡纳河,扔进了南卡罗来纳。我沿着地图上一条蜿蜒的河畔道路前进,结果证明是条蜿蜒的内陆道路。这片河岸上挤满了小岛、港口、河湾,还有沙丘起伏的河滩,但我却只见到吉光片羽。道路狭窄,车速缓慢,每年夏天,当整个东海岸的千百万游客奔向那些海滩胜地时——泰比岛、希尔顿岬、劳雷尔湾、弗里普岛,这里一定是人间地狱。
一直等我到达波弗特(念成“不由弗特”),我才第一次正式看到大海。我拐过一个弯,突然间屏住呼吸,呆呆凝望着一湾缀满小船和芦苇的明镜似的海面,海水宁静、明亮、湛蓝,与天空一般颜色。根据我的“汽车旅行指南”,这个地区的三大收入来源是:旅游、军人、退休者。听起来真够呛,不是吗?可实际上波弗特很可爱,有许多旧宅子,还有一个老式的商业区。我在贯穿全镇的主干道海湾街停了车,惊喜地发现米表收费只要五分钱。这肯定是五分钢镚儿在美国能买到的最后一样东西啦——在南卡罗来纳波弗特的30分钟宁静心情。我漫步走向一个小公园和码头,从外表看是新近修成的。我这才第四次从这一边看到大西洋呢。你若来自中西部,海洋可是极少遇到的呀。公园里到处都是牌子,命令你不要尽情玩耍,或者行为鲁莽。每隔几英尺就有那么一个,上面写着:“不得游泳或在防波堤上跳水。不得在公园里骑车。禁止攀折或损毁花朵、植物、树木及灌木丛。未经市政府特许,不得在公园里饮用或持有啤酒、葡萄酒或酒精饲料,违者必究。”不知道是哪种迷你斯大林在统治波弗特的议会,我从未见过这样冠冕堂皇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地方,害得我心情大坏,一刻也不想多待。我扭头就走,真可惜啊,米表上还有12分钟呢。
结果,我提前12分钟来到了查尔斯顿,这可是件好事。我本来以为萨凡纳是我见过的最宜人的美国城市,可当我到达查尔斯顿以后,它立刻掉到了第二位。这个城市逐渐变窄,在港口尽头缩成了一个圆圆的岬角。城里挤满了美丽的老房子,一个接一个沿着笔直阴凉的街道排成行,就像是拥挤书架上一本本的大书。有些有最细致的维多利亚式装饰,仿佛漂亮的花边,而有些是简单的白色护墙板和黑色百叶窗。但它们全都至少有三层楼高,而且雄伟壮丽——尤其是它们都那么逼近路边,就更显出巍峨之态了。几乎没有哪家有像样的院子——尽管我在各处都看见越南园丁在精心打理桌布大小的草坪——所以孩子们都在街上玩耍。而女人们呢——都是白人,都很年轻,都很有钱——则在门前台阶上蜚短流长。这种情景不应该在美国出现的呀!美国有钱人的孩子根本不在街上玩,没有那个必要。他们要么懒洋洋地躺在游泳池边,要么躲在老爹花3000美元为他9岁生日建造的树屋里,偷偷吸大麻。他们的母亲若想和邻居说长道短,就直接打电话,或者爬进她们的空调旅行车开上100码。这让我意识到,汽车和郊区——还有无限度的财富——已经在何种程度上摧毁了美国人的生活。查尔斯顿有着那不勒斯的气候与氛围,但也有美国大城市的财富和生活方式,令我为之心醉神迷。整个下午我就在这里漫步,在宁静的街道之间来来往往,暗自羡慕着这些好看、幸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们,还有他们极好的房子和富裕完美的生活。
岬角的尽头是个平坦的公园。在这里,孩子们驾着自行车旋转弹跳,年轻伴侣们携手漫步,西沉的太阳滤过玉兰树,带来一道道长长的光与影,一个个飞盘在光影中穿梭。每个人都那么年轻、漂亮、整洁,真好像逛进了百事可乐的广告里一样。公园再过去,是一条俯瞰港口的宽阔石铺人行道,闪亮、翠绿。我走过去向下窥探,海水拍打着岩石,有鱼腥味传来。你可以看到两英里之外的萨姆特堡,内战就从那里打响。大道上挤满了骑车人和汗津津的慢跑者,他们熟练地在步行者和慢吞吞的游客中间迂回前进。我转身走向汽车,太阳暖融融地照在背上,心中隐隐感觉到,经历了如此的完美,从现在起,恐怕要走下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