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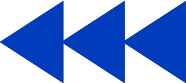
第二天早晨,我又上了南127号高速公路。这段路在我的地图上注明是观光路线,结果证明所言不虚。这里真是一片迷人的田野,好过我所认识的伊利诺伊的任何地方。这里有起伏的如啤酒瓶般墨绿的山丘,有一派繁荣景象的农场,还有那橡树和山毛榉簇拥的密林。因为在往南去,所以当我发现这儿的植物比别处的秋意更浓时,感觉非常惊讶。那些山坡上是芥末黄、暗橙和淡绿的混合,实在是动人。而那明媚的、带着阳光气息的空气,自有一种宜人的轻爽。我可以住在这儿,住在这些小山之中,我心里这样想。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弄明白少了什么——广告牌啊。我小时候,每条路边的田野里都竖立着30英尺宽、15英尺高的广告牌。在艾奥瓦和堪萨斯这样的地方,它们大概是你能得到的唯一视觉刺激了。1960年,约翰逊夫人下令把大部分路边广告牌给拆掉了,作为高速公路美化程序的一大举措。第一夫人总爱投身于那些误入歧途的运动,这便是其中之一。在落基山脉中间,这无疑是件好事,可是在这种空荡荡的平原中央,广告牌简直就是公益服务了。一看到一英里之外竖着面广告牌,你就饶有兴致地想看看它到底说些什么,你会以适度的专注盯着它,看它向你靠近然后走过。作为一种路边消遣,它大概和佩拉的小风车旗鼓相当,不过总比啥都没有强吧。
高级的广告牌上面会有一些三维空间的成分——如果是乳品广告,会有一颗牛头伸出来;如果是保龄球场的广告,就会出现保龄球把球瓶撞得四处纷飞的浮雕。有时候广告牌上是某个即将出现的景点,也许画着一个鬼,还有这样的话:“参观幽灵山洞吧!俄克拉何马最棒的家庭旅游点!只有69英里啦!”过了几英里之后,会有另一个广告牌说:“幽灵山洞提供大量免费车位,只有67英里啦!”广告就这样绵延不断,保证所有家庭都能度过一个期待已久的、最惊险、最有教育意义的下午,至少在俄克拉何马是这样。这些承诺都有图像支持,画上那些阴森森的地下山洞,都像教堂那么大,里面的钟乳石和石笋神奇地融化成巫婆的家、沸腾的大锅、飞翔的蝙蝠、和善的精灵。一切都显得有趣极了。于是后座上我们这几个小家伙就开始提议,停下来去看上一看,我们挨个儿上阵,诚恳而又感人地说:“噢,求求你了爸爸,噢,求——求你啦。”
接下来的60英里路上,我父亲对此事的立场会经历一个老套的过程。先是干脆拒绝,因为那儿肯定很贵,而且不说别的,我们早餐后的表现一直那么差劲,根本没理由得到任何特别奖赏。然后是故意对我们的请求置之不理(这个阶段会持续最多11分钟)。然后会低声地偷偷问我妈的想法,得到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然后又对我们不理不睬,显然希望我们会忘了这事,不再哀求个没完(1分20秒)。然后他说,如果我们听话,而且基本上保持永远听话,我们可能会去。然后又说,我们绝对不会去的,因为看看我们吧,还没到那儿呢,就已经又吵个没完啦。最后他宣布——有时是怒气冲天的咆哮,有时像临终时的耳语——好吧,我们去。你总是能看出来爸爸何时到达同意的边缘,因为这时候他的脖子会变红。每次都是这样,他最后总是会同意的。我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同意我们的请求,让自己也免遭那30分钟的折磨。这之后,他总是会飞快地加上一句:“可是我们只待半小时——而且你们什么也别想买。明白了吗?”这样似乎让他找回了一种感觉:还是他说了算。
到了最后两三英里,幽灵山洞的标志每隔几百码
 就会出现,让我们狂热起来。终于,有一面战舰般大的广告牌上画着一个巨大的箭头,告诉我们在此处右拐再开18英里。“18英里!”爸爸刺耳地叫道,前额的青筋提前暴起,已准备面对可怕的局面:在车辙齐膝深的泥路上颠个18英里,然后不可避免地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幽灵山洞的标志。唉,还真是这样,开了19英里之后,道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路口消失了,没有任何线索表明该从哪边拐,而爸爸则会开上错误的那条路。当最后终于找到地方时,我们却发现幽灵山洞比广告上说的差远了——实际上,每样东西都是敷衍了事。那山洞潮湿阴暗,闻着像一匹死了很久的马,大概只有车库那么大,钟乳石和石笋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巫婆的家和小精灵,看上去就像——唉,就像钟乳石和石笋。这可真是太让人失望了。唯一可能安抚我们的办法,我们发现,就是爸爸在附设的礼品店给我们每人买一把橡皮鲍伊猎刀和一袋塑料恐龙。否则我姐和我就会躺在地上发出悲伤的号叫,以提醒他,未被安抚的悲伤对孩子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就会出现,让我们狂热起来。终于,有一面战舰般大的广告牌上画着一个巨大的箭头,告诉我们在此处右拐再开18英里。“18英里!”爸爸刺耳地叫道,前额的青筋提前暴起,已准备面对可怕的局面:在车辙齐膝深的泥路上颠个18英里,然后不可避免地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幽灵山洞的标志。唉,还真是这样,开了19英里之后,道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路口消失了,没有任何线索表明该从哪边拐,而爸爸则会开上错误的那条路。当最后终于找到地方时,我们却发现幽灵山洞比广告上说的差远了——实际上,每样东西都是敷衍了事。那山洞潮湿阴暗,闻着像一匹死了很久的马,大概只有车库那么大,钟乳石和石笋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像巫婆的家和小精灵,看上去就像——唉,就像钟乳石和石笋。这可真是太让人失望了。唯一可能安抚我们的办法,我们发现,就是爸爸在附设的礼品店给我们每人买一把橡皮鲍伊猎刀和一袋塑料恐龙。否则我姐和我就会躺在地上发出悲伤的号叫,以提醒他,未被安抚的悲伤对孩子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就这样,当夕阳在俄克拉何马褐色的平原上下沉,爸爸已经耽误了几个小时的路程,肩负起找不到旅馆过夜的艰巨使命(他得到了妈妈的大力协助,她会看错地图,几乎把前面的每栋建筑都认成是旅馆)。我们几个小孩为了打发时间,在后面进行闹哄哄的猎刀恶战,不时停下来抽泣,报告伤势,抱怨肚子饿,觉得没意思,想上厕所。那情景,可真是人间地狱哪!而现在呢,高速公路两边几乎看不到广告牌了,这是多么让人悲哀的一个损失啊!
我驶向了开罗,这个地名要念成“剋罗”。不知道为什么,在南部和中西部人们经常这么干。在肯塔基,雅典念成“爱典”,凡尔赛念成“佛赛尔”,密苏里的“玻利瓦尔”是“保利沃”,艾奥瓦的“马德里”变成“麦德里”。不知道这些镇上的人这样发音,是因为他们落后、念书少、是没脑子的蠢驴,还是他们其实有脑子,只不过不在乎被别人当成落后、念书少、没脑子的蠢驴?这种问题还真不能问他们,对吧?其实我在开罗停下来加油的时候,真问了那个晃出来给我加油的老家伙,他们为什么那么念。
“因为那是它的名字呗。”他解释道,好像我是个傻瓜一样。
“可是埃及的那个是念成开罗的呀。”
“听说是这样的。”那人同意。
“而且大多数人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认为是开罗,不是吗?”
“不,在剋罗不是这样。”他说着,有点儿急了。
再追问下去恐怕也不会有更多收获,于是我就此打住,还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念成剋罗。同样让我弄不懂的是,为什么一个自由国家里的公民会选择居住在这么一个垃圾堆里——不管你怎么念它。开罗位于俄亥俄河汇入密西西比的地方,俄亥俄本身就是条大河,它的加入让密西西比壮阔倍增。你会以为,在这样两条大河交汇的地方,应该有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可实际上,开罗却只是个6000人口的可怜小镇。进城的道路两旁,是一排排破败的房子和没刷油漆的廉价公寓。上了年纪的黑人老头儿坐在门廊的旧沙发和摇椅上,等待着死亡或晚餐的召唤——要看哪个先到了。这让我很吃惊。你想不到会在中西部的门廊和出租公寓里看见满满当当的黑人。最起码,不应该在芝加哥或底特律这样的大城市以外见到吧。不过我马上意识到,我已经不在真正的中西部了。南伊利诺伊人说话腔调的南方味比中西部味更浓,我已经向南走到纳什维尔附近了。密西西比就在160英里外,过了河就是肯塔基。我现在正走在一道又长又高的大桥上,穿越密西西比河。从这里直到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河极其宽广,它看上去安全又慵懒,其实却饱含着杀机。每年都有一堆人死在里面。来钓鱼的农夫凝视着河水,心想:“不知道把脚指头伸进去一点点儿会怎么样?”然后呢,你只知道他们的尸体在墨西哥湾里沉浮,膨胀得厉害,却显出奇怪的安详。这条河的凶残是深藏不露的。1927年,密西西比河泛滥,淹没了苏格兰那么大面积的土地。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在河那边的肯塔基,到处是向我致意的巨大广告牌,上头写着:“烟火!”在伊利诺伊燃放烟火是违法的,但在肯塔基却不。所以,你要是住在伊利诺伊,并且想把自己的手炸掉的话,就开车过河到肯塔基好了。过去这种事更常见,如果哪个州的香烟销售税比隔壁州低,州界上所有的加油站和咖啡馆都会在屋顶上打出大广告:“免税香烟!四毛钱一包!不用税!”于是隔壁州的所有人都会跑过来,把车上装满了打折香烟。威斯康星过去为保护其奶农,禁卖人造黄油,结果威斯康星的每个人,包括所有的奶农,都开车到艾奥瓦去,那里到处都是号称“人造黄油特卖”的大广告牌。与此同时,所有的艾奥瓦人正开车奔向什么销售税都没有的伊利诺伊,或者是汽油销售税低50%的密苏里。另外,过去还常常遇到的一件事,就是各州自顾自地实行夏令时,所以一到夏天,伊利诺伊可能比艾奥瓦快两小时,又比印第安纳慢一小时。这些事情实在是荒诞,却让你见识到美利坚合众国的50个独立的州(那时候是48个)独立到何种程度。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又是一个让人悲哀的损失。
我一面开车穿过肯塔基,一面想着那些令人怅惘的失去,猛然间忆起那最悲哀的失去心痛不已——伯马刮胡膏的广告牌。伯马刮胡膏是一种管状的乳膏,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生产。实际上,我压根没听说有谁用过它。可是伯马刮胡膏公司以前会沿高速公路打些有灵气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五个一组,精心摆放,让你一路读起来如念小诗:如果和谐/是你的渴望/就来/一管/伯马刮胡膏。或者是:本遇到/安娜/两人擦出火花/顾不上修理胡子/本和安娜就此散伙。了不起吧?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伯马刮胡膏的广告牌也已经很不合时宜了。在我们走过的几千英里高速公路当中,我记得只看到过六七次。不过作为一种路边消遣,它们可谓出类拔萃,比其他广告牌和佩拉的小风车好上十倍。在娱乐价值上唯一超过它们的,就是尸横遍野的多重连环车祸。
肯塔基和南伊利诺伊很像——丘陵起伏、阳光明媚、颇为迷人,但是四散的房屋看上去不如北边的整洁富裕。这里有众多林木茂密的山谷,凌驾于蜿蜒小溪上的铁桥,路边还粘着一大堆死去的动物。每座山谷里都伫立着一间小小的白色浸信会教堂,整条路旁都是牌子,提醒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圣经带”:耶稣拯救世人。赞美主。基督我王。
我差点儿连出了肯塔基都不知道。这个州在西边缩小成一个点,我正从它一个只有40英里宽的地方切过去,按照美国旅行的时间标准,我真是一眨眼就到了田纳西。在一个州只用不到一小时可是很少见的,而田纳西也无法让我再多留一会儿。这是个模样古怪的州,形状就像一块荷兰砖。它从东到西绵延500英里,从上到下却只有100英里,景观和肯塔基及伊利诺伊差不多——轮廓模糊的农田,镶嵌着河流、山丘和宗教狂热者。但我仍然吃了一惊,我停车去杰克逊的汉堡王吃午餐时,发现这儿特别热。按照街对面一家免下车银行的数字显示,气温高达83华氏度
 ,比早晨的卡本戴尔要足足高上20华氏度。我显然仍深处“圣经带”之中,隔壁的教堂院子里有个牌子:“基督就是答案。”(问题呢,当然就是:你用锤子砸了大拇指时,会说什么呢?)我走进汉堡王,柜台里一个女孩说:“俚(你)要点甚?”我已经进入另一个国家啦。
,比早晨的卡本戴尔要足足高上20华氏度。我显然仍深处“圣经带”之中,隔壁的教堂院子里有个牌子:“基督就是答案。”(问题呢,当然就是:你用锤子砸了大拇指时,会说什么呢?)我走进汉堡王,柜台里一个女孩说:“俚(你)要点甚?”我已经进入另一个国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