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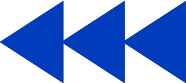
我驾车前行,不听收音机,也没有多少思绪。在惬意山,我停下来喝咖啡。我带着周日版的《纽约时报》——自从我离开之后,生活中最伟大的进步之一,便是如今你能在艾奥瓦这样的地方从售报机里买到当天出版的《纽约时报》。真是非凡的销售技艺啊!于是我在亭子里把它展开。哇!我爱死《纽约时报》周日版了!且不说它作为报纸的诸多优点,单是它那巨大的分量就够让人感到安慰的了。我面前的这一份肯定重达10或12磅,能挡住20码外飞来的子弹。我曾经读到过,出版一期《纽约时报》周日版,要用掉7.5万棵树——它是很对得起每一片颤抖的叶子了。就算我们的孙子因此没有氧气呼吸又怎么样呢?去他们的!
时报上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周边那些小栏目。这部分是如此乏味沉闷,散发出一种催眠的魅力。像“家务改进栏”(“你需要知道的全部修理零件”),还有集邮栏(“邮局纪念航空邮票发行25年”)。我尤其喜爱那广告附页,要是一个保加利亚人问我美国的生活情况,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去抓一堆《纽约时报》广告附页吧,它们展示出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生活,超乎绝大多数外国人最狂野的梦想。似乎是为了说明我的观点,面前的这份报纸就包含了纽约齐威格公司的礼品目录,提供大量你根本想不到有何需要的产品——音乐鞋架啦,手柄里装晶体收音机的伞啦,电动指甲防护器啦。多么伟大的国家啊!我最爱的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电热盘子,你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以免你的咖啡变凉。这对那些脑子受损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天大的恩惠。脑部损伤导致他们四处闲逛,忘记了自己的饮料。全美国的癫痫病患者必定也是同样感激涕零。(“亲爱的齐威格公司:说不清有多少次,我从大发作中苏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思考,‘噢,上帝呀,我敢打赌我的咖啡又凉了。’”)说真的,谁会买这些东西呢?——银牙签,绣着姓名首字母的内裤,印着“年度人物”的镜子。我常常想,要是我开这么一家公司,我就生产一种剖光的桃花心木板,上面的铜牌写上:“嘿,看我干得怎么样?我花了二十二块九毛五,买了这个完全没用的废物。”我敢肯定它会像烤饼一样好卖。
有一次我在精神错乱的一瞬间,给自己买了目录上的东西,其实内心深知会以心碎而告终。那是一个小小的读书灯,可以夹在书上,这样就不会打扰在你旁边睡觉的那个她了。在这一点上,它的表现堪称杰出,因为它几乎不能用。它发出的光线微弱得一塌糊涂(在目录上,它似乎能在你海上迷航时向其他船只发信号呢!),除了头一两行,剩下整页都陷入一团漆黑。我可见过很多小虫子比它亮多了。大约四分钟以后,它那小小的光线开始颤动,然后彻底消失,后来我再也没有用过它。可问题是我明明知道会如此收场,知道它只会带来令人感到苦涩的失望。再一想,如果我真开这么一家公司,我就干脆寄给订货人一个空盒子,内附纸条,上面写着:“我们决定不寄上您订的物品了,因为正如您明了的那样,它是绝不会正常工作的,只会令您失望。所以,就让这一次作为您日后生活的教训吧。”
我从齐威格目录转向食品和日用品广告。这部分通常会有一大堆明亮耀眼的诱惑,勾你去品尝令人兴奋的新产品——名字叫作“大块炖牛肉加肉汤”(“牛肉纤维,肉块多多”)和“闻香快餐”(“让你想用鼻子吃的刺激新快餐!”),还有“乡村阳光蜜烤麦仁加糖霜早餐麦片”(“新推出富含维生素的巧克力葡萄干!”)。我被这些新产品迷得神魂颠倒。很明显,美国垃圾食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已经共同越过了某种合理的界限,正在无尽地追求新口味的感官刺激。现在他们有点儿像那些绝望的瘾君子,已经尝过了所有已知的毒品,为了得到更刺激的效果,终于沦落到静脉注射马桶清洁剂的地步了。在全美各地,你都能看到无数屁股松垮的夫妇静静地在超市货架上搜寻,寻觅新的口味组合,企望找到没尝过的产品来刺醒他们的嘴巴,让他们迟钝的味蕾兴奋一下,根本不管那种兴奋是多么短暂。
这个市场的竞争是白热化的。食品插页不仅提供50美分左右的折扣,你如果寄两三个商标过去,制造商还会快递给你“大肉块海滩毛巾”,或者“乡村阳光围裙与隔热手套组合”,或者一个“闻香快餐”电热盘子,当你正因血糖过高徘徊在昏迷边缘时,为你的咖啡保温。有趣的是,狗食的广告也与此十分类似,只不过它们不常是巧克力口味。实际上,每一种产品——从柠檬清香的马桶清洁剂到松香的垃圾袋——都承诺给你带来一次短暂的沉醉。难怪有那么多美国人一脸呆相,原来他们已经完全被毒倒啦!
我上了218号公路,向南驶向基奥卡克。这段路在我的地图上被标明为观光线,可是,这种事情绝对是相对的。谈起艾奥瓦东南部的观光路线,就像谈起巴里·曼尼奴的好唱片一样,你非得做点儿让步才行。比起整个下午待在一间黑屋子里,它是不坏;可是比起索伦廷半岛的海滨大道之类的地方,恐怕就有点儿乏味了。毫无疑问,路边的风景和今天其他路上的差不多,并没打动我更多。基奥卡克是密西西比河边的一个小镇,在那里,艾奥瓦州、伊利诺伊州和密苏里州隔着一个大弯道面面相对。我本想奔向密苏里的汉尼拔,还指望在去南大桥的路上把这个镇看上一眼。可是不知不觉间,我发现自己已经上了向东往伊利诺伊去的桥。此举令我惊慌失措,结果只瞥到一眼密西西比河,那向着两个方向延伸开去的闪亮褐色,然后,追悔莫及的我就已经进入伊利诺伊了。我真的盼望着能看一看密西西比河呢,小时候,觉得穿越它简直就是一次探险。爸爸总是大叫:“这儿就是密西西比啦,孩子们!”我们闻声爬到窗边,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座真正的云中大桥上,它是那么高,惊得我们屏住了呼吸,而那银光闪闪的河流,在很远很远的下面,广阔、雄浑、安详,正孜孜于它永恒的使命——奔腾向前。这样的景象你可以看上好几里——在艾奥瓦,这可是极其稀有的体验啊!你会看到驳船、小岛还有河边小镇,景色非常棒!然后呢,突然之间,你已经在伊利诺伊了,这里平坦单调,全是玉米,你的心不断下沉,明白就这样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视觉刺激了。从现在起,你得再经过好几百英里无趣的玉米地,才能体验到最琐屑的快乐。
此时此地,我在伊利诺伊,这里又平坦又满是玉米,还很无聊。一个孩子般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大叫:“咱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啊?我觉得好无聊啊。咱们回家吧。咱们到底啥时候到啊?”我本来自信地认为这会儿是在密苏里,已经把地图册翻到了密苏里那一页,因此我在路边停下来,有点儿跟自己怄气的味道,做一点儿制图上的调整。正前方有个牌子上说:“系上安全带,伊利诺伊法律规定。”可是,很显然,读不通禁令句不算是违法。我紧锁眉头,研究着我的地图。如果我在汉密尔顿下公路,就可以沿着河的东岸开,在昆西进入密苏里。这条路甚至也被注明是观光线,说不定最后会发现我的错误并非坏事哩。
我循着这条路经过了沃索(即华沙),一个破败的河边小镇。道路从一道陡坡向着河流纵身一跳,但之后又转回内陆,我还是只能对河流惊鸿一瞥。几乎是在一瞬间,风景又展现为广阔的冲积平原。太阳正在西斜,左边有隆起的座座丘陵,点缀着刚刚露出秋色的树木;右边是平坦似桌面的大地,一队队联合收割机在田野间劳作,扬起了阵阵尘灰,在收获的季节里加班加点。更远处,起谷机捕捉到夕阳余晖,泛出片片乳白,仿佛被从内部点燃一般。在更远一些看不见的某个地方,就是那大河。
我继续向前。这条路上完全没有任何路标。在美国他们经常这么干,特别是在那种从无名之地到无名之地的乡村公路上。没办法,你只能凭自己的方向感来找路了——在我身上,咱们别忘了,这方向感刚刚把我送错了地方。我计算着,如果朝南走,太阳应该在我的右边(我想象自己在一个微型车里穿越一张巨大的美国地图,才得出这一结论),可这条路九曲十八弯,弄得太阳在我前方调皮地游来荡去,先是在路这边,然后又跑到了那边。一整天来,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感觉:我正在一片辽阔大陆的心脏里,在无名之地的中央。
突然间,大路变成了碎石路,箭头般锋利的白石块飞起来,敲打着汽车的底盘,制造出可怕的喧嚣。我的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情景:油管破裂,热油四处飞溅,我冒着热气,咝咝作响,连滚带爬地抛锚在这条荒凉的路上。漫步的夕阳此刻正停在地平线上,向天空泼洒着淡淡的粉红,我一边心神不宁地往前开着,一边鼓励自己坚强面对那暗淡前景:在群星下面过夜,还有狗一样的动物呼哧哧来闻我的脚,再加上到我腿上来取暖的蛇。前方路上有一团步步逼进的尘暴,不一会儿变成一辆敞篷卡车,它以不顾一切的架势飞驰而过,向我的车喷射出石头炮弹,发发炮弹砰砰地砸在车身上,从窗玻璃上弹开,留下了碎裂的声音,然后把我扔在一团尘云中飘荡。我摇摇摆摆地向前开,无助地透过这一团漆黑窥探着。它及时地散开,刚好让我发现自己距离有停车标志的三岔路只有20英尺。当时我的速度是每小时50英里,在碎石路上的刹车距离得3英里。我使出浑身之力猛踩刹车,弄出人猿泰山没抓住藤条的噪音,才停了下来。车子滑出小道,超过停车牌,冲上铺砌的高速公路才停下来,还轻轻地左右晃动着。就在这一刻,一辆巨无霸般的双桥卡车席卷而过——所有的银喇叭都在傲慢地向我怒吼,所有的闪光灯不可一世地向我闪耀——让我的小车又颤动起来。要是我早三秒钟冲上高速公路,定会被它撞成齑粉。我把车开到路肩上,下来检查受损情况。车子看上去就像遭到了面粉袋的俯冲轰炸,油漆被打掉的地方露出了片片粗糙的金属。感谢上帝,幸亏妈妈个子比我小那么多。我感叹一声,突然觉得很失落,觉得自己离家很远。然后我注意到,前面的路牌上指着去昆西的路,原来我正好停在了正确的方向上,这样看来,险情至少还有点儿帮助嘛。
到了停车休息的时候了。一个小镇就伫立在路边,我斗胆把它叫作得拉德(笨蛋),唯恐这儿的人们发现我指的是他们自己,而把我送上法庭,或者打上门来用棒球棍狠狠揍我一顿。小镇边上有家老汽车旅馆,看上去相当破败,不过从院子里没有焦黑家具这一点判断,这里显然比我爹会选的那种地方高一个层次。我把车停在碎石路上,走了进去。一个75岁的女人正坐在桌后,戴蝴蝶眼镜,梳蜂窝头。她正在做一本要你在一大堆字母里圈出单词的书,我觉得应该把它叫作“低能儿的智力测验”。
“要点儿啥?”她头也不抬,懒洋洋地问。
“我想要个房间过夜。”
“三十八块五。”她答道,手中的笔贪婪地落在“没错”这个词上。
我很狼狈。我们那会儿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只要十二块啊。“我不想买下那房间,”我解释道,“我只想在里面睡一个晚上而已。”
她从眼镜上方严厉地盯着我:“房间是三十八块五,一个晚上,税另加,你要还是不要?”她说话的腔调让人讨厌,每个词都加了一个音节。“税”变成了“失味”。
我们俩都清楚,我离其他任何地方都有好几里远呢。“那好吧。”我悔恨地说。我签过字,嘎吱嘎吱地走过碎石路,直奔我的豪华套房而去。这里好像并无其他主顾。我背着包走进房间,四处打量一番,就像你刚到一个新地方所做的那样。屋里有一台黑白电视,看来只有一个频道,另外还有三个弯弯曲曲的衣架。浴室镜子裂了,两扇浴帘还不配套。马桶座上贴了一个纸带,写着“为保护您已消毒”,可是下面却有根烟蒂漂浮在一小汪尼古丁里。爸爸肯定会喜欢这儿的,我想。
我冲了个澡——那就是说,水从墙上的喷头滴滴答答流到我头上——然后就出去考察这个小镇。我在一个贴切地叫作“咯咯”的地方吃了一顿软骨加烤“棒球”,我本以为在中西部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吃到真正糟糕的饭菜,可是“咯咯”却硬是做出了这样的东西。那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食物——而且别忘了,我还是住过英国的呢。它具备口香糖的全部品质,只有口味除外。一直到现在,我打嗝的时候都还能尝到那味儿。
后来我到镇上四处看了看,也没多少可看的,主要就是一条街道,一头是谷仓和铁道,另一头就是我的旅馆,两边是几个加油站和杂货店。这儿的每个人都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多年前,当我还在活泼而敏感的青春期时,读过理查德·马加森写的一个惊险故事,说的是一个偏僻小村的居民,每年都等待一个独自来到镇上的外地人,好在一年一度的烧烤野餐会上把他烤了吃。这儿的人们就正以看烤肉的眼神注视着我呢。
我自觉尴尬,便走进一个阴暗之所,在这个叫作“韦恩酒栓”的酒吧里找了个位子。除了角落里一个一条腿的老人,我是唯一的客人。那吧女很亲切,戴着蝴蝶眼镜,梳着蜂窝头。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她从1931年起就是本地的“豪放女孩”。她整个脸上都写满了“随时做爱”,但全身都写着“最好带个纸袋”。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把她那宽广的屁股灌进了一条红色紧身裤里,还用一件紧身上衣把胸部绷得密不透风,看着真像是错穿了她孙女的衣服。她足有六十上下,样子相当恐怖。我明白那一条腿的家伙为何要选最远的角落了。
我问她,得拉德的人们如何消遣。“你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甜心?”她说道,并且意味深长地抛来媚眼。我不安地发现,那个“随时做爱”的标志闪烁起来了。我还不曾被女人强迫过呢,不过当这一刻到来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是在伊利诺伊的南部某地,和一个60岁的老奶奶。“噢,也许有那种合法的戏院或者象棋比赛什么的吧?”我轻轻地嘟哝着。然而,一旦我们达成共识,接受我只爱她的心灵,她就变得非常理智,甚至相当迷人。她向我详细而坦率地讲述了她的人生,她陷入一连串让人晕头转向的婚姻,嫁的人现在不是在大牢里就是死于枪战。她还顺便做些惊人的坦白,比如:“吉米把他妈给勒死啦,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柯蒂斯从来没杀过人,除了有一次不凑巧,他抢一个加油站的时候枪走火啦。弗洛德——我的第四任丈夫——也从来没杀过人,可要是有人惹恼了他,他往往会弄断人家的胳膊。”
“你要办家庭聚会一定很有趣。”我彬彬有礼地冒昧评论。
“我不知道弗洛德后来怎么样了,”她接着说,“他下巴‘烂里’有一个凹口,”——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这是伊利诺伊南部说“就在这儿,我指的地方”的口音——“这让他看起来有点儿像柯克·道格拉斯。他可真可爱啊,就是脾气不好。我后背有条两英尺长的伤疤,就是他用冰锥割的。你想看看吗?”她说着就动手要卷起上衣,却被我拦住了。她就那样将她的人生经历一年接着一年地讲了下去,角落里那家伙显然在偷听,每隔一阵子就咧嘴欢笑,亮出满口大黄牙,我猜想他的腿一定是弗洛德一时性起给扯掉的。在我们的交谈即将结束之际,那吧女斜眼瞟了瞟我,好像我在使坏骗她似的,说道:“我说,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甜心?”
我不想告诉她我的全部人生故事,因此只是说:“大不列颠。”
“噢,我要告诉你件事,甜心,”她说,“就一个外国人来说,你英语说得可真够好的呀。”
之后,我带着六听装的一箱啤酒回旅馆睡觉。我发现,根据香味和形状判断,那床只可能是一匹马刚刚腾出来的。它中间塌得那么厉害,搞得我非得把两腿大劈叉才能看到床脚的电视,就像躺在一辆独轮手推车上一般。晚上很热,上了年纪的菲哥窗式空调铆足全力,制造出钢铁厂般的噪声,却只能勉强散发出最微弱、极稀少的凉气。我躺着,把那箱啤酒放在胸口,有效地将自己固定住,开始一听接一听地喝酒。电视里演的是个脱口秀,主持人是个油头粉面的浑蛋,穿一件鲜艳的运动衣,名字我没听清楚。他是那种把打理头发当成头等大事的人。他和乐队领队(自然是挂着一把明晃晃的吉他)互相取笑了几句,一点儿趣味都没有。然后,他转向镜头,用严肃的腔调说:“说真格的,朋友们,如果你曾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或困扰,或者你只是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你一定会对今晚第一位来宾的谈话非常感兴趣,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欢迎乔伊斯·布拉瑟博士!”
伴随着乐队奏出的得意洋洋的曲调,乔伊斯·布拉瑟大步上台,我在床铺允许的限度内端坐起来,大叫着:“乔伊斯!乔伊斯·布拉瑟!”就好像在叫一个老朋友。我简直不能相信,已经好多年不见乔伊斯·布拉瑟了,她却一点儿也没变,就连头上的一根发丝都不曾改变分毫。我上次看见她还是在1962年,她唠唠叨叨地讲着月经来潮的问题。好像有人把她放在盒子里藏了25年,这可是我遇到的最接近时空旅行的事啦。我热切地注视着她和光滑先生扯谈阴茎羡嫉和输卵管,盼着他对她说:“现在说真的,乔伊斯,有个问题,全美国一直想要我问你的——你是吃什么药让自己这么年轻的?还有,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把发型变一变?最后,你认为,为什么全美国像我这样的脱口秀傻瓜会一次又一次地请你来?”因为,咱们说实话吧,乔伊斯·布拉瑟相当无趣。我是说,你要是转到约翰·卡森的脱口秀节目,发现她也是嘉宾之一,你就知道,镇上的所有人绝对都去参加某个盛大的宴会或首映礼了。她就像伊利诺伊南部变成的血肉之躯。
然而,就像大多数极度无聊的东西一样,她给人某种美好的安慰。在床脚边发光的盒子里,她愉快的面容令我体会到一种奇怪的温暖、完整和与世无争的感觉。就在这里,在一个空旷大平原的中央,这个脏油桶一样的旅馆里,我第一次有了在家的感觉。不知怎么,我知道醒来时,我会以崭新却又熟悉的眼光来看待这块异国的土地。带着快乐的心情,我睡着了,温柔的梦里有伊利诺伊南部,有奔腾的密西西比河,还有乔伊斯·布拉瑟。你很少能听到有人这么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