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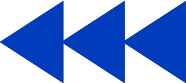
我有一张皱巴巴的小剪报,总是随身携带自娱自乐。那是我从《西部每日邮报》上剪下来的天气预报一则,原文如下:“天气情况:干燥而温暖,但雨水会带来凉爽空气。”
就这么一个简短的句子便完美地概括了英伦的天气:干燥但多雨,一会儿暖和一会儿凉爽。《西部每日邮报》每天的天气预报都能这么写,就我的经验来看,很少会出错。
对于外国人来说,英国的天气最让人吃惊的就是:这儿似乎没什么天气可言。在别的地方,大自然时常狂暴无常,危险无比——诸如飓风、季风、咆哮的暴风雪、让人逃命的冰雹,这些现象在不列颠群岛几乎完全闻所未闻。我觉得很好。我喜欢一年四季衣着不变,我喜欢夏天睡觉时不用空调也不用纱窗,还不担心昆虫和小飞虫吸你的血或者吃掉你的手脚。我喜欢明白这样一件事:只要我不在二月份穿拖鞋去爬斯诺登峰,我就不会在这个四季如春的国家里因天气原因而死去。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离开莫勒坎贝两天后,我坐在温德米尔湖畔的鲍聂斯镇上一家“老英格兰饭店”餐厅里吃早餐,正好读到《泰晤士报》上一篇有关反季节暴风雪的文章,也就是“冰雪暴”。《泰晤士报》称其“席卷”了东英吉利
 部分地区,报道称部分地区的积雪“深达两英寸多”,雪堆“足有六英寸高”。看了这则报道,我做了件从未做过的事——拿出笔记本给报纸编辑写信。在信中我和善友好地指出:两英寸的积雪称不上是“冰雪暴”,六英寸的雪也称不上是“雪堆”。我解释说,真正的“冰雪暴”来袭时连大门都没法打开,真正的“雪堆”能把你的汽车埋起来直到春天来临。“天寒地冻”的含义是你去握门把手、邮箱把手等金属物体的时候,手上都会掉下皮肉。不过,后来我把信揉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差点就变成了漫画《毕林普上校
部分地区,报道称部分地区的积雪“深达两英寸多”,雪堆“足有六英寸高”。看了这则报道,我做了件从未做过的事——拿出笔记本给报纸编辑写信。在信中我和善友好地指出:两英寸的积雪称不上是“冰雪暴”,六英寸的雪也称不上是“雪堆”。我解释说,真正的“冰雪暴”来袭时连大门都没法打开,真正的“雪堆”能把你的汽车埋起来直到春天来临。“天寒地冻”的含义是你去握门把手、邮箱把手等金属物体的时候,手上都会掉下皮肉。不过,后来我把信揉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差点就变成了漫画《毕林普上校
 》中那种自高自大的保守派。我身边就坐满了不少这样的人,正和他们傲慢的太太一起吃着玉米片或喝着粥。没有他们的话,“老英格兰饭店”可能会无以为继。
》中那种自高自大的保守派。我身边就坐满了不少这样的人,正和他们傲慢的太太一起吃着玉米片或喝着粥。没有他们的话,“老英格兰饭店”可能会无以为继。
我之所以到鲍聂斯是因为我有两天时间可以打发,然后再去伦敦会两位友人,周末一起去远足。我极其盼望远足,但要在鲍聂斯再挨过漫长无聊的一天,东瞅瞅西看看等喝下午茶,我就不乐意了。我发现镇上有多得不得了的商店橱窗里摆放着茶巾、彼得兔
 餐具和花纹图案毛衣。我能逛的仅此而已,一点儿购物的欲望都没有。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能否在这样一个最富挑战性的度假胜地再闲逛上一天。
餐具和花纹图案毛衣。我能逛的仅此而已,一点儿购物的欲望都没有。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能否在这样一个最富挑战性的度假胜地再闲逛上一天。
到鲍聂斯来多少有些无奈,因为这里是湖泊地区
 唯一通火车的地方。再说,想想在温德米尔湖畔的静美之中度过两天,沉浸在一座优雅的古老饭店(贵了一点)无边的舒适之中,怎么样也比莫勒坎贝要吸引人得多。可是现在一天过完了,还有一天要挨过去。我已经开始觉得一筹莫展、坐立不安了,就像一个人漫长的疗养期行将结束之时一样。不过,我又乐观地想到那不合时节的两英寸“冰雪暴”刚刚狂暴肆虐了东英吉利,路面交通瘫痪,人们不得不在“极其危险”的雪堆中穿行,有些雪堆居然有脚踝那么高。这样的雪灾竟然慈悲为怀,放过了我所在的这片地方。这里的天气宜人,餐厅窗外的世界在淡淡的冬日暖阳下微微闪光。
唯一通火车的地方。再说,想想在温德米尔湖畔的静美之中度过两天,沉浸在一座优雅的古老饭店(贵了一点)无边的舒适之中,怎么样也比莫勒坎贝要吸引人得多。可是现在一天过完了,还有一天要挨过去。我已经开始觉得一筹莫展、坐立不安了,就像一个人漫长的疗养期行将结束之时一样。不过,我又乐观地想到那不合时节的两英寸“冰雪暴”刚刚狂暴肆虐了东英吉利,路面交通瘫痪,人们不得不在“极其危险”的雪堆中穿行,有些雪堆居然有脚踝那么高。这样的雪灾竟然慈悲为怀,放过了我所在的这片地方。这里的天气宜人,餐厅窗外的世界在淡淡的冬日暖阳下微微闪光。
我决定乘湖上的汽船到安博塞德去。这样可以打发一小时,还能领略湖上风光,能逃离鲍聂斯这座位置放错了的海滨度假胜地,到一座真正的小镇上去玩玩。前一天我就发现鲍聂斯的商店不超过十八家,能买的只有毛衣、茶巾,其中至少十二家出售的都是彼得兔系列产品,只有一家是肉铺。而安博塞德呢,尽管也有大量迎合大批旅客需要的各类旅游商店,可至少有一家不错的书店和许多户外用品店。不知道为什么,后者极其吸引我——我可以花几个小时浏览各种背包、及膝长袜、指南针、求生口粮等等,然后去另一家把相同的东西再看一遍。于是早餐后我满怀热忱与活力,找到了汽船码头。哎呀,我发现汽船只有夏天才通航,这样的规定太没有眼光了。今天天气如此晴好,而且即便是这个季节,鲍聂斯的游人也不少。于是,我只得退而求其次,穿过三五成群漫步的人们去乘往返于鲍聂斯和三四百码远处对岸之间的小轮渡。轮渡的距离不远,可至少一年四季都通航。
渡口已经有几辆车耐心地在排队等候,还有八到十位远足旅行者,全都身穿羊毛外套背着背包,踏着厚重的冬靴,其中有一位居然穿着短裤——这永远是英国远足旅行者晚期痴呆症的一种表现。英国人所说的远足还是我最近才开始亲身体会的,我还没有到愿意穿上有许多荷包的短裤去远足那个地步,不过我已经喜欢上把裤子束在袜子里了(尽管我还没有找到谁来给我解释一下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除了让人看上去严肃认真以外)。
我记得初抵英伦之时,在书店闲逛,惊讶地发现店里居然有一整块全是“步行指南”类书籍,这让我感觉有点怪异滑稽。因为在我们美国,从来都不需要书面指导告诉大家如何走路。不过我慢慢地明白了在英国其实有两种“步行”:一种是每天进行的,“11路”载你去酒吧,一切安好,再载你回家;另有一种就是“远足”,需要一本正经地穿上厚重靴子,塑料袋里装好英国地形测量局地图,背包里带上三明治和茶水罐,最高级别就是恶劣天气里穿上卡其布短裤。
多年以来,我目睹这样的远足者费尽艰辛,在潮湿恶劣的天气下攀登云中耸立的大山。我有位老友约翰·普莱斯,生长于英格兰北部,年轻时曾在湖泊地区那些陡峭的山壁上做过许多傻事。他有一次鼓励我加入他和其他几个朋友的队伍,周末去“干草山”上“走走”(这是他的原话),我当时想“走走”和“干草山”这两个词的组合似乎听上去比较轻松,然后他保证回来后开怀畅饮,于是我便放松了警惕跟着去了。
“你确定不会太辛苦吧?”我问他。
“不会的,就是去走走嘛。”约翰说得斩钉截铁。
当然了,那次绝不是“走走”而已。
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爬过大片陡直的山坡,踏过咯吱作响的碎石和一簇簇草丛,绕过高耸入云如城堡般的岩石,终于来到一片悬于半空中的荒凉“冥界”。这里极为偏僻,就像是无人区,连绵羊看见我们都吓了一跳。远处是更加险峻荒僻的山峰,山脚下几千英尺处是状如黑色细带的高速公路,从那里抬头看不到群山之巅。约翰和他的伙伴们以最残酷的方式戏弄我的求生意志:看见我落在后面,他们便在石头地上坐下吸烟、聊天,休息一会儿,可是等我刚赶上他们,筋疲力尽几乎在他们面前跌倒时,他们马上神采奕奕,扔下几句鼓励的话,又大步流星地走开了。于是我只得跌跌撞撞地跟上,完全没有机会歇个脚。我气喘吁吁,浑身疼痛,口吐白沫,意识到自己以前从未做过这么违背天性的事,然后发誓再也不做这样的傻事了。
后来,就在我差点就地倒下需要叫个担架的时候,我们一行来到了最后一个坡顶。我突然发现自己神奇地置身于地球之巅,站在悬于空中的一片平地上,四面是绵绵不绝如大洋一般的群山。我从未看过及得上这个一半美的景致。“天哪!”我突然间口齿伶俐起来,发现自己完全沉醉其中了。自从那时候开始,只要他们叫我,我都会再来,从不抱怨,也开始把裤子塞进袜子里,简直等不及第二天到来。
轮渡靠岸,我们走上了甲板。和煦的阳光下,温德米尔湖看起来宁静而迷人。难得的是此刻没有一艘游船打搅它如镜的湖面。要说温德米尔湖很受驾船者的喜爱,未免也太轻描淡写了。登记在册在湖上行驶的船就有一万四千艘,让我再重复一遍,一万四千艘。热闹的夏日里,任何时候湖上都会有一千六百多艘动力船,有很多以时速四十英里飞驰,后面还拖着滑水的人。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种无须登记就能下水的东西,如轻舟、帆船、风浪板、独木舟、橡皮艇、皮筏,各种游船和我此刻搭乘的咯吱作响的轮渡。这些船只、皮筏、帆板都在寻觅一大片容身的水域。如果八月的某个周日你在湖岸上看见滑水者在挤满轻舟浮板的水面上飞速穿行,你不吃惊得瞠目结舌、害怕得双手抱头才怪。
一年多以前,我在湖泊地区住了几个星期为《国家地理》杂志写稿。那段时间里令人颇为激动的一段经历就是早晨搭乘国家公园的游艇一览湖景。为了让我知道高速动力的船只在如此拥挤的湖面上疾驰有多么危险,公园管理员把游艇驶入湖中央,告诉我千万抓紧了——我轻轻一笑:听着,我开摩托车可是时速九十英里呢!接着他发动了引擘。这么说吧!四十英里时速行船和四十英里时速开车完全是两码事。船一发动,那速度就把我甩到后面的椅子上,我拼命用两手紧紧抓住椅子保命。船像离膛的子弹一样在湖面跃动,我很少被吓成这样。即使并非旺季的宁静早晨,温德米尔湖也同样危机四伏。我们的游艇急驰在湖中小岛之间,不时迅速躲过前方突然显现的岬角,就像在游乐场乘“疯狂老鼠”。想想看我们要和其他一千六百艘同样横冲直撞的船只共用同一片水域,而那些开船的人大多都是城里来的大腹便便的弱智,毫无动力船驾驶经验,再加上水面还漂浮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木船和皮船等等,湖上没有陈尸大片简直就是奇迹。
那段经历教会了我两件事:其一,在无顶棚的船上呕吐物的蒸发速度为每小时四十英里;其二,温德米尔湖非常袖珍。这里我们就要切入重点了。英国这地方尽管地形多样,历史辉煌永恒,却什么都要小一号。这里没有一处自然风光能在世界上数一数二——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壮美的山脉,没有令人惊艳的峡谷,连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都没有。英国人自己也许会认为泰晤士河是条重要大动脉,可是放之于全球,只不过是一条颇具挑战性的小溪而已,放在北美,根本连前一百名都进不去,准确一点,大概排名一百零八位,排在名不见经传的斯昆克河、卡斯科奎姆河之后,甚至还不如小小的牛奶河。温德米尔湖长十英里,宽半英里,在英国可以傲视群湖了,可是和美国的苏必利尔湖相比,在前者每十二平方英寸的水面,后者可以提供超过四分之三平方英里的水。在我家乡艾奥瓦州有一座丹格林斯洛湖,部分本地人都从未听说过,就算如此,它也比温德米尔湖要大。英国湖泊地区的总面积也赶不上美国的双子城
 。
。
我认为这一切实在是了不起。并不是说这些自然风景面积很小而了不起,我是说这些风景如此袖珍,又坐落在人烟如此稠密的不列颠岛上,还如此美丽,堪称伟大的造化!
你知道吗?要想让美国达到与英国相同的人口密度,得把伊利诺伊、宾夕法尼亚、马萨诸塞、明尼苏达、密歇根、科罗拉多以及得克萨斯诸州的所有人口全塞进艾奥瓦州才行。湖泊地区有两千万居民,一天之内就能来回一趟,每年还有一千二百万游客,相当于英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来这里旅行。难怪夏日周末乘船去安博塞德要花上两小时,你都可以一条船一条船这么踩着穿越温德米尔湖了。
即使是最拥挤的时候,湖泊地区也比那些幅员辽阔的国家里的许多知名景点要迷人得多。只要远离人群——远离鲍聂斯、霍克希德、克什威克,远离那些茶巾、茶室、茶壶以及没完没了的比阿特丽克斯·波特
 牌个人随身用品——湖区仍然有许多纯粹完美的风景。这时,轮渡缓缓靠岸,我们一拥而出。我发现那一瞬间码头变得热闹非凡,一堆汽车开下船,另一堆又上了船;那八九个远足者朝各个方向散开了。突然间一切又迅速复归宁静,我沿着湖边一条漂亮的林间小路拐入内陆,朝尼尔索雷走去。
牌个人随身用品——湖区仍然有许多纯粹完美的风景。这时,轮渡缓缓靠岸,我们一拥而出。我发现那一瞬间码头变得热闹非凡,一堆汽车开下船,另一堆又上了船;那八九个远足者朝各个方向散开了。突然间一切又迅速复归宁静,我沿着湖边一条漂亮的林间小路拐入内陆,朝尼尔索雷走去。
尼尔索雷最负盛名的就是“山顶小屋”,那位无处不在的波特小姐就是在这间屋子里绘就可爱的水彩画,写出那伤感故事的。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从四面八方过来的游客简直泛滥成灾,村子里很多地方都改建成大型停车场了,但掩蔽得很好。茶室打出的价格招牌上甚至还有日文,天哪!其实这里只不过是个村落罢了(你知道“村子”和“村落”有什么区别吗?其实很简单,前者是人们向往的地方,后者是莎翁名剧)。不过,这村子外围小巧精致,未曾遭到破坏:绿草茵茵如同伊甸园,蜿蜒的石板墙和林地灌木丛将其环绕,湛蓝的天幕下是低矮的白色农庄依傍着迷人的山丘。即使尼尔索雷本身也有种精心打造的诱人魅力,是那些成群结队参观名人故居的游客所无法领会的。“山顶小屋”声名如此大噪,国民托管组织都不再为其做广告了,游客们仍是络绎不绝。我到那儿的时候,交头接耳的白发老人们正从两辆大巴上走下,主停车场已经差不多满满当当了。
去年我来过“山顶小屋”,所以这次我从屋子旁边绕了过去,沿着一条僻静小路往上爬,来到一座小湖边,或者说是高地上的一座水潭吧。波特小姐年老的时候定期到小湖中驾舟泛游——不知她是锻炼身体还是自我折磨——不过小湖十分可爱,看上去人迹罕至的样子。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多年来第一个爬上来的游客。小路的另一边,一位农夫正在修补一截垮掉的围墙。我站在那儿看了他一会儿,谨慎地保持距离,因为如果有什么事同修补石墙一样抚慰心灵的话(我是有足以自傲的经验哦),那就是看着别人补墙。这些古旧的石墙是风景中多么特别的点缀啊。我记得搬家到北方之后不久,有一次出门散步,偶遇隔壁农夫在偏僻的小山丘上重修一道石墙。时值一月,寒雨纷飞,最让人不解的是不知道他修这石墙有什么必要。石墙两边的土地都是他的,何况围墙上有一扇门终年敞开着,似乎这石墙没有什么真正的功能。我驻足观望了一会儿,最后问他为什么凄风冷雨地还站在外面修墙。他用约克郡农夫独有的专门对付南方来的菜鸟和白痴的痛苦表情看了看我:“当然是因为墙倒了呗。”从这件事情当中我领会到:第一,绝对不要对约克郡农夫提出任何无法用“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来一杯泰特利啤酒吧”来回答的问题;第二,英伦的自然风光美丽永恒得无法用言语形容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农夫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一直在辛勤维护。
当然,这和钱也没有多大关系。政府每年花在国家公园上的钱平摊到每个人身上还不及一份报纸的价钱。政府在全部10个国家公园里投入的总和还不及在皇家歌剧院一家的投入。整个英国公认最美丽也最需环保的湖泊地区国家公园,年度预算是240万英镑,和伦敦一所大型中学的预算差不多。就这么点经费,国家公园得用来进行日常管理,经营10个信息中心,支付127名全职员工及40名暑期兼职员工的工资,维护并更换设备及车辆,投入经费美化风景,开展教育项目,还要担当地区规划的职责,也就是对于公园范围内所有的规划发展进行评估并做出裁决。在一丝不苟的精心维护下,湖泊地区才能如此美丽迷人,有益身心。这一切都归功于其中辛勤工作的人们,在这里安居的人们以及共享这片优美风景的人们。近来我读到一则报道:半数以上接受采访的英国人想不起任何一件自己国家足以引以为豪的事情。我想他们可以为这个而自豪。
我在温德米尔湖和科尼斯顿湖之间精致而又自在的风景中畅游了数小时,想继续流连下去,无奈天下起了雨。看上去一时间停不了,颇为扫兴,我出门的装备中又完全没有为下雨做准备,真是够蠢。不管怎么样,我开始饥肠辘辘了,于是回头到轮渡码头返回了鲍聂斯。
一小时以后,我吃了份高价金枪鱼三明治,被敲了竹杠,回到了“老英格兰饭店”,隔着大玻璃窗对着雨中湖水发呆。我感觉无聊透顶又无精打采,阴雨天待在这种奢华的地方通常都会有这种特别的感觉。为了打发剩下的一小时,我到饭店住客休息室里去看能否搞到一壶咖啡。休息室里散坐着上了年纪的老军官和他们的太太,漫不经心地读着《每日电讯报》。这些老上校个头都不高,身材滚圆,穿着花呢外套,留着精心梳理过的银发,举止粗鲁,铁石心肠,走起路来有点一瘸一拐的。他们的太太涂着鲜艳的口红和厚厚的粉,像才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样。我发现其中有一位太太友好地与我打招呼,想要攀谈几句,我未免吃了一惊,浑身不自在起来。她顶着银色头发,口红涂得一塌糊涂,好像是地震时化的妆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我总是要过一会儿才明白原来自己现在是一位外表看上去颇值得尊敬的中年男士,不是那个刚从香蕉船上下来的年轻乡巴佬了。
我们的交谈照例是从这鬼天气开始的,当这位女士发现我是美国人之后,她突然转移话题讲起她和阿瑟——我想这个阿瑟就是此刻在她身边羞怯微笑的那个呆子吧——近来去加利福尼亚访友的经历,然后就慢慢变成了有关美国人缺点的老生常谈。我从来就不明白人们这么做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认为我会欣赏他们的坦率,还是忘记了我就是美国人?人们在我面前讲起移民问题时也是如此。
“你不觉得美国人太冒失了吗?”那位女士吸了吸鼻子,啜了一口茶,“你只不过和一位陌生人谈了五分钟,他们就把你当朋友了。我在恩齐诺就遇到一个,大概是退休邮政工人之类的吧,问了我的地址还保证说下次到英国一定来我家拜访。你能想象得出吗?我这辈子都没怎么碰到这个人。”她又啜了口茶,沉思了一会儿,“他的皮带扣可真古怪,全是银色的,上面还有小小的宝石。”
“美国人吃的东西我也搞不懂。”她丈夫坐起来了一点,开始自言自语。不过,很明显他这种男人从来都只说故事开头的第一句话。
“哦,对了,吃的东西!”他太太叫了起来,抓住了要点,“美国人对吃的东西的态度实在是奇怪。”
“怎么个怪法呢,他们喜欢美味食物有问题吗?”我挤出一丝微笑追问道。
“哦,不,亲爱的,是分量。美国人吃东西的分量绝对让人讨厌。”
“我有一次吃牛排……”她先生干笑几声又开口了。
“还有他们把英语给糟蹋的!他们根本就不会说‘女王英语’
 。”
。”
等等,美国人吃东西的分量还有系彩色皮带扣的友善男人,你们想怎么说都可以,可是说到美国英语请注意了。“为什么美国人非得说‘女王英语’呢?”我语气冷冷地问,“毕竟你们的女王又不是他们的女王。”
“可是他们都用的什么词啊,还有他们的口音。阿瑟,你很不喜欢的那个词是什么?”
“Normalcy。”阿瑟回答,“我有一次碰到一个人……”
“可是normalcy根本不是美国英语,”我说,“这本来就是英国人创造的。”
“哦,亲爱的,我觉得不是。”这女人斩钉截铁,愚蠢至极,还露出屈尊的笑容,“不是,我肯定不是英国人创造的。”
“1722年……”我随口编了个谎话。不过基本事实没有错,normalcy的确是英国英语,我只是不记得细节罢了,“……丹尼尔·笛福
 在《摩尔·弗兰德斯》里……”我灵光闪现继续补充道。作为生活在英国的美国人,我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将成为英语的坟墓。人们向我表达这种情绪的频繁程度简直让人吃惊,通常是在晚宴上,某人有点喝多了,但也有时候是像这位一样半痴呆还涂厚粉的干瘪老太婆。有时候你会对这种事情失去耐心,于是我告诉她——我告诉他们夫妻俩,因为她丈夫看上去又要插嘴了——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美国人创造的词汇大大地丰富了英国英语,有些词他们每天都得用,其中之一就是moron(傻瓜)。我对他们露齿一笑,喝光了咖啡,带点傲慢地起身告辞,然后去给《泰晤士报》编辑再写一封信。
在《摩尔·弗兰德斯》里……”我灵光闪现继续补充道。作为生活在英国的美国人,我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将成为英语的坟墓。人们向我表达这种情绪的频繁程度简直让人吃惊,通常是在晚宴上,某人有点喝多了,但也有时候是像这位一样半痴呆还涂厚粉的干瘪老太婆。有时候你会对这种事情失去耐心,于是我告诉她——我告诉他们夫妻俩,因为她丈夫看上去又要插嘴了——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美国人创造的词汇大大地丰富了英国英语,有些词他们每天都得用,其中之一就是moron(傻瓜)。我对他们露齿一笑,喝光了咖啡,带点傲慢地起身告辞,然后去给《泰晤士报》编辑再写一封信。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约翰·普莱斯驾车带着大好人戴维·帕特里奇来到我下榻的饭店门口,我当时正在门口等他们。到了鲍聂斯镇我不让他们停下来喝杯咖啡,因为我不愿意再忍受这地方了。我让他一直开到巴森斯韦特附近的一家旅馆,普莱斯事先已经预订好了房间。我们放下行李,喝了咖啡,让厨房准备三份午餐打包,穿上时髦的远足行头,开始向大朗戴尔山谷进发。
尽管天气阴沉,行将入冬,山谷周边的停车场和路边还是全塞满了车。放眼望去,随处都是人,要么是打开车厢捞出远足装备,要么就是打开车门坐在里面换上暖和的袜子和坚实的靴子。我们也把袜子加上,然后偶遇了一队稀稀拉拉的远足者,全都背着背包裹着及膝的羊毛长袜,接着就向那座郁郁葱葱的班德山丘进发了。我们的目标是那座传奇山峰“落虹顶”,海拔2960英尺,在湖泊地区诸山中排行第六。在我们前面的行人宛如缓慢移动而间距恰好的彩色小点,一直延伸到天边那宏伟的山峰中,最后消失于云端。如同往常一样,我发现居然有这么多人都觉得在11月末潮湿阴冷的周日费力爬山极其有趣,不免暗自惊叹。
我们越过地势较低的草坡,来到更为荒凉的地方,在石块和碎石堆之间穿梭,终于爬上距谷底约1000英尺的片片浮云之中。那景致简直是摄人心魄——大朗戴尔诸峰参差不齐耸立在对面,挤挨着靠在远处狭窄的山谷后方,山谷中饰有小块石墙环绕的田地,西面便是一大片棕色群峰,半截湮没在云雾之中。
我们往前走着,天气越来越糟糕,空气中全是舞动的小冰粒,打在皮肤上如同刀割。快到“三间舍”的时候,天气变得狰狞起来,浓雾弥漫,冻雨纷纷,狂风在山坡上肆虐,我们只能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行进。在大雾中能见度只有几码,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连路都看不清了,这给我敲起了警钟,我才不想死在这里呢——别的不说,我还有14,700英里的常旅客飞行旅程没用过呢。突然,在我们前面的一片阴暗之中出现了一个让人心惊胆战的橙色雪人。再凑近一点,原来是一件高科技远足外套,里面裹着一个人。
“冷啊!”那一大团东西很简明扼要。
约翰和戴维问他是否远道而来。
“布利塔恩,还好。”布利塔恩可是在遥遥十英里之外呢。
“那边天气?”约翰也言简意赅,我才意识到远足者们都是用极简体的语言交谈。
“手膝并用。”那人回答。
他们心领神会地互相点点头。
“这里很快也会是了。”
他们又点点头。
“哦,得走了。”那人似乎无法忍受整天闲扯,很快隐没在浓稠如汤汁的白雾之中。我目送他远去,转身想建议同伴们也许可以考虑撤回山谷,窝在温暖的客栈里吃着热腾腾的佳肴,就着冰凉的啤酒。可是我发现他们两人已经消失在前方三十英尺的迷雾之中了。
“哎,等等我!”我大叫着匆忙赶上。
一路登顶顺顺利利,我数了数我们前面有三十三人,全都在被大雾染白的石堆之间围成一团团,手捧三明治和热水瓶,猛翻地图。然后我就尝试着想象我应该如何向外国人解释这个场景——三十多个英国人冒着冰风暴在山顶野餐。我马上意识到你根本无法解释。我们走到一块岩石边,一对夫妇好心地将背包挪开腾出点野餐的位置给我们。我们坐下,顶着刺骨寒风在棕色背包里掏来掏去,再用冻得麻木的手指剥开水煮蛋的壳,喝着温热的汽水,咬两口压扁了的奶酪酸菜三明治,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花了三小时才穿越的茫茫大雾,什么都看不见。然后我就想(很严肃地哦):天哪,我太喜爱这个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