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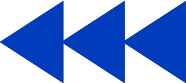
我把我那辆租来的车还到牛津,打定主意直奔米尔顿·凯恩斯。我之所以选那里作为目的地,是因为我飞快地扫了一眼公路图,以为坐火车到那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事实上,这就是英国铁路系统特别古怪的地方。我非得先辛辛苦苦地回到伦敦,再搭上一班地铁,坐到尤斯顿站,最后乘一列火车到米尔顿·凯恩斯——为了在两座相隔约三十英里的城市之间旅行,你可能总共得赶一百二十英里路。
这趟路既费钱,又耗时间,弄得我多少有点儿恼火。尤其是因为从尤斯顿开出的火车挤得很,我坐在上面,脸儿冲着一个在轻轻抱怨的女人和她十岁大的儿子,后者一直晃荡着一双腿,踢在我的胫骨上,还一边用一双猪仔眼瞪着我,一边挖鼻孔、吃鼻涕。说也奇怪,这一幕还真是让人挪不开视线。他似乎把自己的鼻子当成了横在面孔正中的某种零食售卖机。我想专心致志地看书,却发觉自己的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抬起来,每回都看见他在得意洋洋地盯着我,手指忙活个不停。这情形可真让人作呕。因此当火车最后抵达米尔顿·凯恩斯时,我终于能从行李架上把帆布背囊一把拽下来,从他脑袋上绕过,然后扬长而去,心里真是乐不可支。
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这个词儿跟“牛仔裤”(jeans)押韵,是在战后那段短暂而激昂的时期里兴建的三十二座“新城”之一。彼时,至少在那些从事工程技术的人看来,“社会工程”还不是一个不吉利的词儿。在一个盛气凌人、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英国,这些模范社区将位于最前沿——在新闻片镜头里,当时那些英国人似乎正在努力再现1939年纽约世博会的风貌,并扩展成全国性的规模——而米尔顿·凯恩斯在许多层面都是这场运动的精髓。
我并没有立马就讨厌米尔顿·凯恩斯,我想你对这地方最大的期望也不过如此。你踏出车站,迎面就是一片开阔的广场,有三面围着装了反光玻璃的大楼,你立时就觉得空间如此宽敞——在英国的城镇里,这样的感觉几乎绝无仅有。这座城市本身矗立在通往一座小山的斜坡上。小山在半英里开外,对面就是错综交缠的人行地道,俯瞰一大片开阔地,一半是停车场,一半是那些模样古怪的栽在新城市里的树,看上去似乎永远都长不大。
在许多方面,米尔顿·凯恩斯的情形都比我所见过的新城市要优越得多。地道里的墙面上贴着磨光的花岗岩,大部分都没有涂鸦,地上也没有那种永远黑乎乎的小水坑,而后者,似乎成了其他经过规划的社区的一项设计特色了。这城市本身就是一锅古怪的、掺和了多种风格的大杂烩。几条主干道中心岛边沿的绿化带上没有草坪,但绿树成荫,隐隐透着法兰西气韵。而边缘地带那些整饬得漂漂亮亮的轻工业园区,看起来颇具德国风味。至于棋盘式街道布局及替街道编号的做法,就让我回想起美国啦。建筑一律是毫无特色的那种,你随便在哪个国际机场附近都找得到。简而言之,这座城市样样都像,就是不像英国。
最怪的是,附近既没有商店,也没有人。我穿过市中心走了一段,踱上这条街,走下那条道,穿过树阴下连接两条路的小街。明明所有停车场都是满满的,办公楼上洞开的窗户背后也有活人的迹象,可是几乎没有看到路过的车辆。远处,长得永无尽头的马路上,顶多只有一两个行人晃过。我知道城里有一个大型商场,因为我先前在书里看到过,可是我连个可以问路的人都找不到。可恼的是,看起来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跟商场挺像。我不停地发现外观相似的候选对象,便跑过去窥探究竟,结果却发现,它们只不过是某家保险公司或者类似机构的总部罢了。
末了,我沿着往城外的方向逛了一段路,逛进了一处住宅区。那片地无边无际,里头整齐洁净、千篇一律的黄砖房,街道蜿蜒曲折,人行道两边栽着从来都长不大的树,可周围还是空无一人。从一座小山的顶上,我发现大约四分之三英里之外有一大片蓝屋顶,便寻思那里没准儿就是商场,于是径直而去。原本看着挺顺眼的人行道开始变得越来越可气。它们懒洋洋地穿过被湮没的路堑。这些路堑一律设计得美观雅致,却传达着那么一种感觉:不急着把你带到任何地方去。显然,那些道路设计师把这件活儿当成了一道二维习题。它们统统沿着迂回曲折、看上去漫无目的的路线展开,画在纸上想必赏心悦目,却没考虑到:那些在房子和商店之间长途跋涉的人们,多半喜欢沿着一条合理的路线直奔主题。一旦在看不见地标的半地下世界里迷了路,那感觉就更糟糕了。我发觉自己老是得爬上地面,就为了看看自己到底身在何处,却每每发觉,此地跟我想去的地方毫不相干。
最后,在某次咕咕哝哝地爬上地面之后,我发觉我身边是一条繁忙的双车道,对面正巧就是我已经找了一个小时的那片蓝屋顶。我能看到得克萨斯家居、一家麦当劳以及其他类似地方的招牌。可是,当我回到人行地道里,又盘算不出该怎么过去了。那些小路往各个方向分叉,纷纷隐没在漂亮的弯道上,细细打量,走哪一条都不见得肯定能有一点儿回报。最后我选了一条上坡路,一直走到与街面水平,至少在那里,我能看出自己到底在哪里,然后一路走回火车站。现在看起来,火车站离居民区实在远得不像话。显然,只有不折不扣的白痴才会以为米尔顿·凯恩斯是什么徒步者的天堂。怪不得我走了整整一个上午,一个人都没碰上。
抵达车站时,我的疲劳远远超过走那段距离本该达到的程度,气喘吁吁地想喝杯咖啡。火车站外面贴着一张城区地图,先前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可没注意到,现在我细细研究了一番,急着想知道那该死的购物中心在哪里。原来,先前我在市中心勘查的时候,离那购物中心只有一百英尺左右,可当时我愣是浑然不觉。
我叹了口气,莫名其妙地下定决心,非要看一眼那个地方不可,于是我径直穿过人行地道,经过一段空旷的地面,最后回到死气沉沉的办公楼群的中心地带,一边走,一边寻思:一个从事城市规划的老兄,要建立一座模范社区,眼前搁着白纸一张,面对近乎无限的可能性,却居然会决定让购物中心与火车站相隔一英里远,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
简直难以置信,购物中心的设计甚至比它周围的市中心区域还要糟糕。毫无疑问,那些购物中心的设计师不管在哪里碰头,这玩意儿肯定都是个笑柄。它大得要命——超过一百万平方英尺——所有已经存在和将要出现的连锁店,这里无一遗漏。可是,购物中心里光线不好,一点儿都不讨人喜欢,造在两条笔直的、毫无特色可言、至少长达半英里的平行大道旁。除非因为我精神错乱所以看漏了——我想不是这么回事——否则那里是真的没有小吃街,没有中心集合点,没多少地方可以坐下来,没有一丁点儿匠心独运之处好让你对此地稍微产生点好感的。那感觉就好像置身于全世界最大的公共汽车站似的。厕所少得可怜,又很难找,厕所里挤得就跟球赛中场休息时的情形一个样。
我在我所能想象的最最邋遢的麦当劳里喝了一杯咖啡,前面那几位用过我这张桌子的吃客留下了成堆的垃圾,我在其中清出一块地盘,坐下来,摊开我的列车时刻表,对着路线图一起看,当我发现眼前的选择只有两条——要么回伦敦去,要么继续向拉格比、考文垂或者伯明翰进发——心里不由被一阵沮丧猛地刺痛了。这些地方我都不想去。我在牛津扔下租来的车,直奔火车站,脑袋瓜里装着简单的计划,打算从牛津到剑桥,中途在米尔顿·凯恩斯吃顿午餐,稍事休息——这一切似乎不是短短几个小时以前的事,而是发生在几天前。
时间悄然流逝。那是某个遥远的、几乎已被遗忘的人生片段:在约克郡溪谷的一座房子里,我坐在厨房里的一张桌前打好了如意算盘——只消六个礼拜,顶多七个礼拜吧,我就能舒舒服服地把整个国家跑遍。如意算盘里包含着不少白日梦,几乎哪里都能一网打尽——海峡群岛、兰迪、谢特兰,此外还包括几乎每一座城市。我读过约翰·西拉比的《游遍英伦》,他只用了八个礼拜,就从全岛最南端徒步走到苏格兰最北端的约翰奥格罗茨。当然啦,但凡借助一种迅捷的现代公共交通系统,我可以在六七个礼拜里看遍大半个英国。然而,此时此刻,我人在这里,预定的时间差不多已经用掉了一半,可我连英格兰中部都没看完。
于是,在黯然神伤中,我收拾好行囊,走上漫漫长路,先回到车站,再搭上一列去伦敦的火车。实际上,我得从伦敦出发,从头来过。我不晓得该往哪里去,只好采取我惯常的做法。白金汉郡那些连绵起伏的农田刚刚经过秋收,空空旷旷,当火车从其间穿行而过时,我摊开一张地图,顿时就被那些地名搞得晕头转向。在我看来,在英国生活,这是最最深奥、最最持久的乐趣之一。
在英国生活,几乎处处都会被某种取名的天分所打动。随便挑一个类别,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命名的:从监狱(苦艾丛、陌路)到酒吧(猫咪与小提琴、羊羔与旗帜),到野花(针脚麦芽汁、女士蓬子菜、跳蚤毒药、发烧菊),到足球队的名字(谢菲尔德星期三、阿斯顿庄园
 、南方皇后),一下子就把你弄得神魂颠倒。不过,毋庸置疑,英国人取地名的天分,是其他领域望尘莫及的。英国境内三万个地名中,我猜,总有一半是在哪个方面要么引人注目,要么饶有趣味的。有些村庄听起来似乎是在掩藏一个古老的、说不定见不得人的秘密(老公波斯沃斯、内结白霜、白衣女郎阿斯顿),而有些村庄听起来就像是从一部19世纪的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布拉德福德·佩孚雷尔、康普顿·瓦伦斯、兰顿·赫林、伍顿·菲茨派恩)。有些村庄念起来像化肥(速长),像鞋类除臭剂(爽足),像口气清新剂(薄荷),像狗粮(狗仔宝),像马桶清洁剂(便盆通、卫生孔),像皮肤病(白皮疹、踝灼伤),甚至像一种苏格兰污点脱涂剂(黑污净)。有些村子的态度颇有问题(大发雷霆、笑话乞丐、吵架),而有些村子里出的事儿莫名其妙(跳跳肉、假发扭扭、哭哭闹闹屋)。有无数村庄的名字倏忽间唤起这样的画面:慵懒的夏日午后,蝴蝶在草丛间飞舞(间歇河
、南方皇后),一下子就把你弄得神魂颠倒。不过,毋庸置疑,英国人取地名的天分,是其他领域望尘莫及的。英国境内三万个地名中,我猜,总有一半是在哪个方面要么引人注目,要么饶有趣味的。有些村庄听起来似乎是在掩藏一个古老的、说不定见不得人的秘密(老公波斯沃斯、内结白霜、白衣女郎阿斯顿),而有些村庄听起来就像是从一部19世纪的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布拉德福德·佩孚雷尔、康普顿·瓦伦斯、兰顿·赫林、伍顿·菲茨派恩)。有些村庄念起来像化肥(速长),像鞋类除臭剂(爽足),像口气清新剂(薄荷),像狗粮(狗仔宝),像马桶清洁剂(便盆通、卫生孔),像皮肤病(白皮疹、踝灼伤),甚至像一种苏格兰污点脱涂剂(黑污净)。有些村子的态度颇有问题(大发雷霆、笑话乞丐、吵架),而有些村子里出的事儿莫名其妙(跳跳肉、假发扭扭、哭哭闹闹屋)。有无数村庄的名字倏忽间唤起这样的画面:慵懒的夏日午后,蝴蝶在草丛间飞舞(间歇河
 神父、维斯顿催眠野地、西德尔村万圣、伊顿小妞)。最登峰造极的,是几乎不计其数的村子,名字都蠢得可爱——“闲扯得好”“小滚得对”“大嚼特嚼”“木材库泥浆”“舔尖尖”“迷路村”“远方伯格尼”“下面来一拳”,还有那个绝对无与伦比的“把我埋到那里去”。
神父、维斯顿催眠野地、西德尔村万圣、伊顿小妞)。最登峰造极的,是几乎不计其数的村子,名字都蠢得可爱——“闲扯得好”“小滚得对”“大嚼特嚼”“木材库泥浆”“舔尖尖”“迷路村”“远方伯格尼”“下面来一拳”,还有那个绝对无与伦比的“把我埋到那里去”。
有一个无关紧要且极少有人注意的特点:这些名字魅人的地方爱扎堆,这现象是多么频繁啊。比方说,仅在南剑桥那一块弹丸之地,你就能找到“炸掉诺顿”“干草垛真糟糕”“恶人撞翻”“丑八怪”,还有那灵感四溢、叫人难忘的“炮弹大便”。我心里生出一股冲动,想立马就到那里去,去闻闻“炮弹大便”在哪里,还想弄清楚诺顿怎么会爆炸、干草垛怎么会糟糕。不过,当我浏览地图时,我的视线撞到了某块地表上横穿过的一行地名——那个名字念起来余音袅袅、蛊惑人心,唤作“魔鬼堤”。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块地方,不过它听起来让人满怀期望。这下我感觉好多了。
于是,次日上午近午时分,在剑桥郡外一个名叫“抵达”的小村里,那个在偏僻小路上步履蹒跚地寻找“魔鬼堤”起点的家伙,正是鄙人。那是个阴气森森、叫人毛骨悚然的日子。空中雾气蒙蒙,能见度趋近于无。冷不防,从一片黏黏稠稠的灰色中,堤岸耸然立起,简直吓了我一跳,于是我便爬上了堤。这真是一处诡秘而阴郁的高地,尤其在旅游淡季里,看浓雾笼罩中的堤岸,特点就更明显了。“魔鬼堤”建于大约一千三百年前,也就是那段黑暗时代
 中最黑暗的日子。这条土堤绵长、笔直,比周围地面高出六十英尺,位于“抵达”村与“迪顿戈林”之间,长达七点五英里。令人失望的是,没人知道为什么它名叫“魔鬼堤”。这个名字直到16世纪才有记载。它屹立在平坦的沼泽地里,虽散发着某种叫人胆寒、显而易见的古意,却也让人感到奇蠢无比。要造这么个玩意儿显然需要花大把的力气,可是,根本用不着劳烦什么战术天才,谁都能轻而易举地意识到,但凡要率军进犯,只要绕过去就万事大吉,而敌人们也统统是这么做的。于是,没过多久,“魔鬼堤”就压根儿派不上什么用场了,顶多只能给那些沼泽地里的人瞧瞧,待在六十英尺高的地方是什么感觉。
中最黑暗的日子。这条土堤绵长、笔直,比周围地面高出六十英尺,位于“抵达”村与“迪顿戈林”之间,长达七点五英里。令人失望的是,没人知道为什么它名叫“魔鬼堤”。这个名字直到16世纪才有记载。它屹立在平坦的沼泽地里,虽散发着某种叫人胆寒、显而易见的古意,却也让人感到奇蠢无比。要造这么个玩意儿显然需要花大把的力气,可是,根本用不着劳烦什么战术天才,谁都能轻而易举地意识到,但凡要率军进犯,只要绕过去就万事大吉,而敌人们也统统是这么做的。于是,没过多久,“魔鬼堤”就压根儿派不上什么用场了,顶多只能给那些沼泽地里的人瞧瞧,待在六十英尺高的地方是什么感觉。
话说回来,在长满草的堤岸顶上闲逛,还是件颇为轻松的事儿,何况在这个阴冷的早晨,整个堤顶也只有我一个人。直到走了将近一半路程时,我才开始看到别人,多半都是在“新市场石楠丛”那宽阔的草地上训练他们的狗,透过神秘兮兮的雾,他们看起来都鬼气森森。这条堤正好穿过“新市场赛马场”(虽然我什么玩意儿也没看见,可我觉得那里还是挺顺眼的),接下来再穿过一片看上去欣欣向荣的牧马场。雾渐渐转薄,透过纤瘦枯槁的树枝,我瞥见一连串大型种马场,每一个都包含白色围栏的小牧场,一幢大房子,还有散乱分布、装饰花哨的马厩,马厩上既有圆屋顶,又有风向标,弄得它们看上去神秘兮兮,活像是一座现代化的“泰斯科”超市。虽说沿着这样一条特征鲜明的路线慢悠悠地逛逛挺自在的,不过,多少也有点儿无聊。我一连走了几个小时,谁也没碰上,那堤岸在“迪顿戈林”外的一片田野里戛然而止,而我就仿佛横遭遗弃,怀着某种急转直下、没着没落的惆怅,站在那里。当时刚过下午两点,我还一点儿都不累。我知道“迪顿戈林”没有火车站,不过我估计我可以坐一辆巴士去剑桥,果然,在当地的巴士站点上,我发现确实可以这样做——假如我能等两天的话。就这样,我顺着一条熙来攘往的马路跋涉了四英里,抵达“新市场”,在附近随便走走看看,然后搭一班火车直奔剑桥。
在乡间长途步行,有个始终不变的乐趣(尤其是在旅游淡季里),你会有那么个念头,相信到头来你会在一家暖和的旅馆里找到一间房,在炽热的炉火跟前一连喝上几杯饮料,然后美美地大吃一顿,那些丰盛的菜色都是这一整天的激烈运动和新鲜空气授予你的特权。问题是,我抵达剑桥时,整个人神清气爽,也不觉得负担沉重,因此也就不配享受什么特权。更糟糕的是,我先前以为走这趟路会比眼下的实际情况要艰难,而且以为会到得很晚,所以就在大学盾章饭店里订好了房间,满心期待那里会有炽热的炉火、丰盛的菜肴,还散发着大学高年级师生休息室特有的氛围。到头来,我却暗自沮丧地发现,这是一幢漫天要价的现代化建筑,而我那个光线昏暗的房间,也跟我那本旅游手册上的描述南辕北辙,这可真叫人黯然神伤。
我没精打采地打量着这座城市。我知道剑桥是个很雅致的城市,也是个怪名字成堆的好地方——光是“耶稣绿”和“基督碎片”就够绝的了——但那天我对它就是提不起兴趣。中央市场邋里邋遢、乱作一团,而周围似乎三三两两地挤着一大堆让人气馁的钢筋水泥建筑,而且所有这一切都被一场忧郁的细雨给湿透了。临了,我只能钻进一家二手书店,东翻翻西看看。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书要找,但正巧撞到一本书讲的是塞尔弗里奇百货
 的历史,还配着插图,便迫不及待地把它从书架上抽出来,指望能看到书里讲讲陡崖城堡怎么会破败到被人弃置不顾的地步,如果再能讲点塞尔弗里奇和放荡成性的多丽姐妹之间的那档子风流韵事,那就更好啦。
的历史,还配着插图,便迫不及待地把它从书架上抽出来,指望能看到书里讲讲陡崖城堡怎么会破败到被人弃置不顾的地步,如果再能讲点塞尔弗里奇和放荡成性的多丽姐妹之间的那档子风流韵事,那就更好啦。
唉,这一本似乎是塞尔弗里奇逸事的净化版。我只找到有一处顺便提到多丽姐妹,暗示她们俩只不过是一对天真的流浪儿罢了,塞尔弗里奇对她们俩的关切有如慈父。至于塞尔弗里奇从原本的方端正直骤然堕落,书里几乎就没说起,对陡崖城堡更是只字不提。于是我把书放回去,心里明白,不晓得为什么,今天甭管做什么,都会大失所望。我走进一间空荡荡的酒吧,喝了一品脱
 啤酒,又在一间印度餐厅里吃了一顿稀松平常的晚饭,然后在雨中孤零零地漫步。最后,我躲进自己的房间,发觉电视节目乏善可陈,并且意识到我把自己的手杖落在了“新市场”里头。
啤酒,又在一间印度餐厅里吃了一顿稀松平常的晚饭,然后在雨中孤零零地漫步。最后,我躲进自己的房间,发觉电视节目乏善可陈,并且意识到我把自己的手杖落在了“新市场”里头。
我拿着一本书上床,却发觉床头灯的灯泡不翼而飞——不是灯丝烧坏了,是灯泡不见了。这样一来,晚上剩下的那几个小时,我就呆呆地躺在床上看电视上重播的《警花拍档》,半是出于好奇,想弄明白这套古老的节目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BBC一台的头儿如此难以自拔(唯一可能的答案:莎伦·格莱丝的胸脯),半是因为这部戏可靠的催眠效果。我戴着眼镜睡着了,醒来时也不晓得到底几点,只见电视屏幕上乱糟糟、闹哄哄地飞舞着雪花。我起床想关掉电视,却重重地踩在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上,然后居然耍了个好玩的把戏,用脑袋关掉了电视机。我很好奇,想弄明白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万一以后我决定在派对上露一手,还能派上用场。结果我发觉原来刚才挡了我道的玩意儿就是我自己的手杖,它根本就不在什么“新市场”上,而是在地板上,横在一张椅子和一条床腿之间。
哦,好歹还是有一件好事的,我一边寻思,一边用两条宛如海象牙的卫生纸往鼻孔里一塞,堵住突然流下来的鼻血,然后精疲力尽地爬回到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