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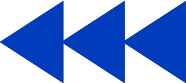
多年前,有一回,我老婆的一个亲戚,估摸着我们总有一天会传宗接代,就送给我们一箱子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瓢虫童书”。那尽是些“出门晒太阳”和“海边大晴天”之类的书名。书里有画工精细、色彩明丽的插图,勾勒出一个繁荣昌盛、心满意足且一尘不染的英国。太阳总是金光灿灿,店主总是笑容可掬,孩子们总是穿着新熨好的衣裳,他们的快乐与幸福来自种种天真纯洁的消遣——坐一辆巴士去商店,在公园的池塘里漂起一艘船模,跟一位和蔼可亲的警察聊天。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岛上历险记》。其实在这书里几乎找不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历险——我记得,最高潮的部分不过是找到一只吸在岩石上的海星——不过我很喜欢它,就因为那些插图(出自才华横溢且备受怀念的J.H.温格菲尔德之手),描绘一座到处都是岩石海湾的岛屿,背后的远景一望便知是在英国,但那气候又分明是地中海式的,而且画面整洁宜人,看不见“自动付费显示”的停车场、宾果
 游乐馆以及那种俗不可耐的游乐中心。在这些插图里,商业活动仅限于模样古怪的蛋糕店和茶室。
游乐馆以及那种俗不可耐的游乐中心。在这些插图里,商业活动仅限于模样古怪的蛋糕店和茶室。
这本书对我产生了莫名的影响,有好些年我一直同意带全家到英国的海滨去度假,满以为有朝一日我们总会找到那个神奇的地方——那里终日阳光普照,海水如同坐浴盆里的水一般温暖,商业病毒亦不为人所知。
等我们终于开始生儿育女,这才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喜欢这些书,因为书里的人物除了光顾宠物店或者观赏一位渔夫替他的船刷油漆,就再也做不出什么更有意思的事了。我努力解释,说这些都是为了在英国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他们不听,宁可兴致勃勃地看托普西和蒂姆
 那对叫人生厌的小笨瓜,这可真叫我沮丧。
那对叫人生厌的小笨瓜,这可真叫我沮丧。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些年里,在我们去过的所有海滨小景点里,拉尔沃斯似乎跟我脑海里浮现的理想画面最为接近。那里小巧宜人,还有一种引人入胜的老派风范。那里的小商店出售的海滨用品会让人想起一个更为纯真的年代——木头帆船,挂在柱子上的玩具渔网,装在长长的网线袋里的五彩斑斓的沙滩充气球——而那些屈指可数的饭店里总是挤满了乐呵呵的旅客,正在享用一杯奶茶。村脚那几乎呈圆形凹陷的海湾美丽绝伦,湾中散布着岩石和巨砾,可以让孩子们爬上爬下,其间还点缀着浅浅的小池子,可以在那里抓小螃蟹。言而总之,那里实在是个惬意的去处。
可是,当我在饭店里洗完一把澡,出门找点东西喝,还想来一顿酣畅淋漓、舒心合意的晚餐时,却发现拉尔沃斯已不复记忆中的风貌。想想看,当时我该多么惊讶啊。如今那里最显著的特征是一座巨大而丑陋的停车场——这个我以前可一点儿都不记得,还有直通海湾的那条街道两边的商店、酒吧和宾馆,看起来邋里邋遢,一副穷酸相。我径直走进一家大酒吧,几乎一进门就后悔了。酒吧里洋溢着一股子泼出的啤酒散发开的酸腐味,闻来令人作呕,而且店里到处都是亮晃晃的水果榨汁机。我几乎是那里唯一的顾客,可是差不多每张桌上都堆满了空空的酒杯、烟头满到快要溢出来的烟灰缸、薯片包装袋以及其他乱糟糟的零碎。我的玻璃杯黏答答,啤酒暖烘烘。我一股脑儿喝光,再去试试邻近的另一家,结果后者的邋遢度只略显逊色,而舒适度却未占上风,非但装修破败、音乐嘈杂,而且对于我的慷慨惠顾多少有点缺乏热情。也真难怪啊(我可是怀着满腔热情这样说的),如今有那么多酒吧生意越来越清淡。
我泄了气,掉转枪头,走进附近一家饭馆。我和太太以前在这里吃过蟹肉沙拉,一边吃一边把自个儿想象成上流人士。如今这里的情形也变了。菜单面向低端市场,其名目堕落到挪威海蜇虾、薯片、青豆之类的水准,饭菜的味道也实在乏善可陈。不过真正让人难忘的是服务。我还从来没有在哪家饭馆里见过这样既富丽堂皇又愚不可及的景象。那里人山人海,但只消一会儿工夫就能确定,根本没有一伙人是开开心心的。基本上,从厨房里端出来的每盘菜,不是多了些没点过的东西,就是少了些点过的玩意儿。有人枯坐百年,菜迟迟不来;有人眨眼之间,各道菜点就几乎一并上全(当然啦,没有人抱怨)。我点了一道杯装明虾沙拉,一等就是半个小时,上来一看,有几只明虾还处于冰冻状态。我把它给退回去,自此之后再也没见它回来。四十分钟以后,一位女侍应生登场,端着一盘薯片、青豆配鲽鱼,愣是找不到有谁要,我就揽了下来,虽说我先前点的明明是鳕鱼。用餐完毕,我照着菜单自己算了算账,扣掉一点儿冰冻明虾的钱,然后留下钞票,翩然离去。
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宾馆,那是个郁郁寡欢、悲悲切切的地方,床单是尼龙做的,取暖器也冷冰冰的。我爬上床,在一盏七瓦灯泡下看书,真心诚意地立下一道小小的誓言:但凡有三寸气在,我就再也不会回到拉尔沃斯来。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但见风卷起大片大片的雨帘,倾泻在层层山峦。我用罢早餐,结完账,在前厅走廊上挣扎良久,才把防雨外套绷到身上。说来滑稽,平日穿衣多半波澜不惊,可是,只要你叫我套上一条雨裤,那情势就好像没人搀扶我就站不起来一样。我用了整整二十分钟,才撞上墙和家具,接着又跌倒在盆栽上。随即,凭借一股子惊天动地的爆发力,我单腿跳了十五英尺,最后将自己的脖子缠到了一根螺旋形楼梯中柱上。
末了,待我全副武装完毕,朝墙上的一面全身镜瞥了一眼,赫然发现,我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只硕大的蓝色安全套。于是,我穿着这套行头,每走一步都响起一阵恼人的尼龙窸窸窣窣的声响,拿起背囊和手杖,向山区进发。我走上“汉伯里陶特”,经过“德尔门”和一个山路陡峭的谷地——其名魅人,唤作“痒臀”,然后走到一条呈“之”字形陡直上行的泥泞山路上,直奔一座云笼雾罩的高地而去,那里名叫“斯威尔顶”。天气叫人生畏,雨水催人发狂。
如果你乐意,且容我扯开两句。若以两只手的十根指头在头顶上敲敲打打,看看多久以后,或是你自己不堪忍受,或是身边的每个人都睁大眼睛瞪着你。不管是哪一种情形,你都会巴不得赶快停下来。现在,再想想,如果那些敲敲打打的不是手指,而是雨点不停地打在你的雨帽上,而你束手无策。更要命的是,你的一副眼镜是两块碰上水汽就完蛋的圆圈,而你的脚步还在一条被雨水打得湿淋淋的山路上不停打滑,但凡一失足就会坠下高山,落到一块海滩边的岩石上——那一摔,就会让你形同一小块粘在一片岩石上的污迹,宛若面包上的果酱。我一边想象着新闻标题“美国作家正欲归国之际坠崖殒命”,一边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往前走,眼睛像玛古先生
 一样斜着,心里老生出不祥之兆来。
一样斜着,心里老生出不祥之兆来。
从拉尔沃斯到韦茅斯有十二英里路。在《海滨王国》(The Kingdom by the Sea)中,保罗·梭罗
 给读者一种印象,仿佛你可以在海边轻轻松松、大摇大摆地走路,而且仍然能匀出时间来喝喝奶茶,奚落奚落当地的土包子,可是我相信他碰上的天气比我好。我走这段路花了大半天。从斯威尔顶再往前,谢天谢地,总算是走在了虽然高却比较平坦的山崖上。山崖高高地悬在一片苍凉灰白的大海上,然而每一步还是岌岌可危,只能走得很慢很慢。在灵斯代德海湾,山势猛地陡直向下落到海滩上。我借着一阵往下冲的泥浆滑到山底的海湾,当中暂停的间歇只够我的小肚子磕在几块大石头上,外带开展了几次对于树枝弹力的测试。滑到山底以后,我拉开地图,用手指充当卡钳,测算出我只不过前进了五英里,但大半个上午已经过去。这样可怜巴巴的进展让我皱起了眉头,只好把地图塞进口袋,气哼哼地继续跋涉。
给读者一种印象,仿佛你可以在海边轻轻松松、大摇大摆地走路,而且仍然能匀出时间来喝喝奶茶,奚落奚落当地的土包子,可是我相信他碰上的天气比我好。我走这段路花了大半天。从斯威尔顶再往前,谢天谢地,总算是走在了虽然高却比较平坦的山崖上。山崖高高地悬在一片苍凉灰白的大海上,然而每一步还是岌岌可危,只能走得很慢很慢。在灵斯代德海湾,山势猛地陡直向下落到海滩上。我借着一阵往下冲的泥浆滑到山底的海湾,当中暂停的间歇只够我的小肚子磕在几块大石头上,外带开展了几次对于树枝弹力的测试。滑到山底以后,我拉开地图,用手指充当卡钳,测算出我只不过前进了五英里,但大半个上午已经过去。这样可怜巴巴的进展让我皱起了眉头,只好把地图塞进口袋,气哼哼地继续跋涉。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都是迈着重重的步子,沿着低矮而湿滑的山坡无聊跋涉。山脚下海浪拍岸,声声入耳。雨势渐弱,变成阴险的毛毛细雨——那种别具风格的英国式毛毛雨,在空中萦回不去,渐渐蚕食人们的精气神儿。约莫下午一点钟,缭绕在海湾那道长长的弧线上的薄雾中,韦茅斯的轮廓渐渐浮现出来,我不由轻声欢呼起来。然而,那里看起来如此切近,其实却是个残忍的骗局。我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走到那座小城的郊区,又花了一个小时才沿着无边无际的海滨人行道走到市中心,而此时我已经筋疲力尽,走路都一瘸一拐了。我在海滨的一家小饭店里订了一个小房间,脚上蹬着靴子,身上那副安全套似的行头也没顾上脱,就这样栽到床上躺了好久。直到我攒起足够的力气,才换上一眼看去不至于那么搞笑的衣服,然后略略洗刷了一把,往城里去。
我对韦茅斯的喜爱程度,远远超过自己的预想。这里有两点特别出名:1348年,黑死病就是从这里开始传入英国的,而到了1789年,这里又成为全世界第一处海滨旅游胜地。彼时,那位招人烦的疯子国王乔治三世开风气之先,头一个到这里来洗海水浴。时至今日,这座小城努力维持乔治时代的优雅氛围,而且大体上也几乎算是做到了。然而,就像大多数海滨胜地一样,至少就观光事业而言,这里弥漫着些许日薄西山的意味。乔治及其随从住过的格劳切斯特饭店(当时那还是座私宅)最近停了业,如今的韦茅斯连一家体面的大饭店都没了。这在一座老牌海滨城市里,可真是一个悲惨的疏漏。不过,有一点我乐于宣告,这里确实有很多上好的酒吧,还有一家出色的饭馆——佩里餐厅,它们都坐落在海滨港口区。这个区新近刚翻修过,海面上渔船起伏摇摆,空气里飘逸着一种踌躇满志的航海气息,让你简直巴望能看见大力水手波派和布鲁多从街角慢悠悠地大步走来。我吃了从普尔港运来的“当地贻贝”——在一连辛辛苦苦地走了三天之后,当我发现在这里仍然可以把普尔叫作“当地”时,真是大吃一惊——还有一条值得称颂的海鲈鱼,然后就躲进酒吧。那种酒吧非但光线很暗,而且天花板很低,让你觉得自己应该穿一件宽宽大大的阿伦牌套头衫、戴一顶船长帽才般配。我自得其乐,一直喝到双脚不再觉得痛为止。
韦茅斯以西,绵延着五十英里长的莱姆湾。紧挨着韦茅斯西侧的地方没什么特别之处——简直毫无记忆的必要,我就打了辆出租车直奔阿伯茨伯里,开始沿着切瑟尔海滩走半程。我不知道沿着切瑟尔海滩走到韦茅斯尽头会是什么情形,不过,在我走过的这一段里,有好多蚕豆形的小鹅卵石形成的大沙滩。经过阵阵海浪千秋万代的洗礼,这些鹅卵石一律光滑无比,简直没法在上面走路。因为你每走一步,沙子都会埋到你的脚踝上方。海岸散步道的地基要更坚实些,紧挨着海滩后方,但是你走在上面就看不见堆满石头的沙丘。你只能听见海的声音,浪涛在沙丘的另一边拍打着堤岸,携卷起海边不计其数的鹅卵石彼此碰来撞去。这段路走得无聊至极,不一会儿,脚上的水泡就开始一跳一跳地痛。待我在午后一两点抵达西海湾时,我已经打算好好坐下来弄点东西吃了。
西海湾是个古怪的小地方,一副杂乱无章的做派,铺展在一片布满了沙丘的土地上。它多少有点淘金小镇的腔调,仿佛是匆忙之间草草建成的,看起来穷困潦倒、灰头土脸,而且有点几经风雨、分崩离析的样子。我四处转悠,想找个地方吃东西,正巧撞上一栋无从言喻的建筑,名叫“河畔咖啡馆”。我打开门,发觉自己立时置身于绝非俗流的背景中。这里挤得水泄不通,空气里满满的全是刺耳的伦敦式闲聊,所有的顾客看上去都像是刚从“拉尔夫·劳伦”的时装广告里走出来似的。他们都把套头衫闲闲地搭在肩膀上,将墨镜架在头顶上,就好比从富勒姆或者切尔西
 那里奇迹般地取下一小块来,吹到多塞特海边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
那里奇迹般地取下一小块来,吹到多塞特海边这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
毋庸置疑,我还从来没有在伦敦以外的哪家餐馆里见识过这等节奏。男女侍应生左冲右突,努力满足那些似乎永无穷尽的需求,务必让顾客填饱肚子,而最最紧要的,是让他们有酒喝。这一点真是不寻常,弄得我一阵心血来潮。通常我不是个对午餐太热心的人,然而,此刻那些食物闻起来如此诱人,周围的气氛又是那么特别,弄得我点菜的气派活像个“大胃王”。我第一道菜叫了干贝龙虾羹,然后是一道精美的海鲈鱼片配青豆外加一大堆薯片,以两杯葡萄酒佐餐,末了是咖啡和一大片奶酪蛋糕。店主是个活泼和善的男人,名叫阿瑟·华生,从这张桌子逛到那张桌子,甚至还过来招呼我。他告诉我,区区十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家传统的海滨咖啡馆,只做点烤肉午餐、汉堡包和薯片的生意,渐渐地,它开始引进新鲜鱼类以及更有噱头的食物,这才意识到需求甚广。如今,每逢用餐时间,此地就人满为患,而且刚刚被《美食指南》评为“多塞特年度最佳餐厅”。不过,这里仍然卖汉堡包,每道菜也都配上薯片,我觉得这真是挺了不起的。
三点以后,当我走出“河畔餐厅”时,除了脑袋瓜子觉得有点轻飘飘以外,身上别的地方都沉甸甸的。我在长凳上坐下来,铺开地图,鼻子里不由懊丧地哼了一声。因为我发觉自己离莱姆里吉斯还有十英里远,而横在我们之间的还有高达六百二十六英尺的“金冠”,那是南海岸最高的山脉。我脚上的水泡开始抽搐,双腿发痛,肚子胀得离谱,天上又飘起了绵绵细雨。
我坐在那里的当口,一辆巴士开始启动。我站起身,把脑袋探进敞开的车门。“是往西去的吗?”我对司机说。他点点头。我一时来了劲头,笨手笨脚地爬上车,买了张票,然后在车厢尾部找了个位子坐下来。我一向有句口头禅:徒步旅行若想获得成功,其秘诀就在于,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