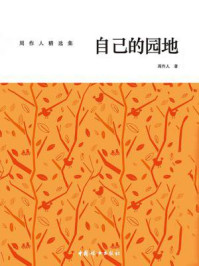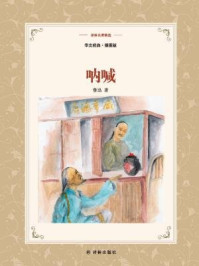王纬宇当革委会主任,已经有整整十年历史了。
尽管最初,并不叫这个名称,那是后来经过敲锣打鼓,庆祝游行,才开始叫的。然而,从实质上讲,自从一九六七年于而龙被打翻在地,并踏上千万只脚以后,王纬宇是这座庞大工厂的第一把手。但是,他比那位党委书记兼厂长要出息得多,竟然攀登到于而龙都攀登不到的“副部级”高峰。从去年年初,甚至更早一点,他就兼管整个部里的运动,那是炙手可热的差使,眼看就要坐上“红旗”轿车了。可是和这上升趋势正相反,于而龙开始走第二段下坡路,而且失败得更惨些,背着氧气袋上台检查,一场心肌梗死差点没见了马克思。
这一对朋友就这样碧落黄泉地彻底分野了。
真是“人还在,心不死”啊!偏偏这个一蹶不振的于而龙,是个不肯丢手、不肯罢休的顽固派。而且一直不认错,不服输,甚至连那个快坐“红旗”轿车的角色都不放在眼里。
“他?”
于而龙的这个问号显然是大有文章的。
可是去年,一九七六年那个暗淡的初春以后,若是有人再给这位垮台的党委书记提他的老战友王纬宇时,那问号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惊叹号了,印成书面文字的话,没准会一连串来三个。
“他呀!!!”
真遗憾,生性精细,滴水不漏的王纬宇,竟不曾注意到于而龙这一点细微的变化。哦!原谅这位忙人吧,去年他那辆“上海”轿车,在部直属机关,耗油量是数一数二的。
从问号到惊叹号的改变,应该说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去年春天,于而龙从濒临死亡的边缘又活了过来。
也许因为他是打鱼出身,要不然,就是精神上的示威,不顾老伴闺女的劝阻,又坐到护城河畔的草地上钓鱼来了。背脊还是那样挺直,像冻不死的野草,又活着钻出地面。
突然有人在他身后不好意思地问:“匀我两条蚯蚓好吗?”
“请便吧!”他信口回答,并未注意是谁,因为钓鱼人的眼睛,不大愿意离开水面上的浮漂。
那人蹲下身来,在装有鱼饵的竹筒里,慢吞吞地翻捡。捡着捡着住了手,抬起脸来望着他:“怎么?老厂长,不认识你的老部下了吗?”
于而龙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没出息的钓鱼人身上。笑话,鱼饵都不准备就来钓鱼,还很罕见呢!可是一看见那刺猬似的络腮胡子,啊哈,他乐了,敢情还是个熟人。
他大概以为于而龙把他忘了,要求一个工厂的总负责人,记住全厂近万职工的姓名,那是不可能的。便提醒地说道:“老厂长,你不记得啦,我是实验场的。”
但他,这个骑兵团的老战士,于而龙却是熟悉的:“谁个不知你是咱们团的挂掌名手!”
他咧开嘴谨慎地笑了笑,凑过来:“真不容易,我在河边候你一个多礼拜了。”他叹了口气:“嗐,部大院的门卫真厉害,说啥也不让我去见你,找了你的电话号码,总机也不给接。”
“有事吗?”
这时正好甩上来一条小鲫瓜子,在河岸草丛里蹦跶,他自告奋勇帮助去捉。别看他是个钉掌的权威,是出色的风泵司机,好不容易才制服了那不丁点大的鱼。扎煞着满手的泥巴,站在那里。那副尴尬样儿,猛地使于而龙想起在暂时困难的六十年代初叶,他种烟叶的事情。
巨大的实验场地,国内最重要的动力科学研究基地,一直是绑住于而龙手脚的耻辱柱,使他有着永远赎不完的罪愆;他本意倒是为了造福,但却为此屡次三番地检讨认错。竟然好像还怕罪状不够似的,一小片生机盎然,长势良好的烟叶,在实验场的空地里迎风摆拂。
“谁种的?”于而龙那时是党委书记兼厂长,还是市委委员,威风凛凛地喝问着。
只见络腮胡子在“自留地”里站起,掸拭掉满手的泥土,和现在捉鱼一样地狼狈。
“要发展小农经济么?”
他不知所措地笑着,不过,笑得有点忐忑、有点勉强。骑兵团的战士都了解于而龙不打雷就下雨的坏脾气,他估计到准是凶多吉少,笑脸凝固了。
“马上给我全部拔掉,一棵都不准剩。”
“厂长——”他有些犹豫,烟叶才刚刚长成啊!
“当过骑兵的人嘛!”
“是!”他脸色严肃起来,笔直地立正站着。老战士的荣誉感,在心田里面压倒了那种小私有者的习气,一声不吭,弯下腰去,一棵一棵薅掉那青枝绿叶的烟草。
多漂亮的烟叶啊!他的一句话,别人的心血全白费了,谁都能体会络腮胡子拔烟草时,该是多么心疼。于而龙甚至觉得所有在场的人,包括那位廖总工程师,都不以为然。
廖思源悄悄说:“大可不必嘛!还怕对你的起诉书里,增加一款罪名?”
“要是现在——”这位第二次又趴下的于而龙想,“或许我该采取另外一种方法,嗐,我这永远改不了的坏脾气啊!说不定络腮胡子还耿耿于怀吧?”
不,于而龙,你可错看人啦!
这位骑兵团抱马蹄的名工巧匠,是专程请你去喝喜酒的,他的儿子要结婚啦!
“好极啦!恭喜你当老太爷啰!”他祝贺着,同时,又把鱼钩甩上来。空钩,护城河的鱼都让人给钓狡猾了。不过,这点聪明,却是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于而龙不得不再挂上蚯蚓。“订的哪天办喜事啊?”
他本是泛泛地问了一句,没料到络腮胡子郑重其事地回答:“看你的方便!”
哦!这才注意到他压根儿不是来钓鱼的,于而龙放下鱼竿,凝视着他。
他有点结结巴巴地说:“我老婆叫我来,请你老团长到家喝喜酒。”
“我?”
“是的。我老婆求你怎么也得赏咱们这个脸,说你准能高高兴兴地答应。”钉掌名手说,“因为我那小子能有今天,全亏了老团长。”
于而龙糊涂了:“你讲得明白一点!”
“是!”他又笔挺地站着。骑兵立正的姿势总是有些不大自然,在马背上征战惯了的老兵,正如水手一样,登上不摇晃的陆地,倒觉得别扭。“多少年前的事了,你许是忘了,老团长。”
他讲起往事来……
“那时,你让我们骑兵回去接家属,来厂里扎根当工人,好,我那出息老婆一来就趴窝了。疼得满炕乱滚,孩子说啥生不出来。我能给再厉害的儿马挂掌,无论怎么尥蹶子,我也能制伏住它;可就是按不住我那疼疯了的老婆。我偷偷摸摸请来的王爷坟独一无二的老娘婆,她骂我是个废物点心:‘你不是骑兵吗?快骑在你娘儿们身上吧!快点儿!要不就该憋死啦!我可用大秤钩子往外掏啦!咱可把话说清楚,只能顾一头,要大人,不能要崽子;要崽子,就保全不了大人,你倒是说话呀,当兵的。’老娘婆容不得我同老婆商量,又转脸数落那一直嗷嗷叫着、疼得受不了的老婆,骂了个狗血喷头:‘你知道疼,还死命把肚里崽子撑得那么大,当兵的钱来得容易是不?哎唷!了不得啦……’老娘婆喊得人魂灵都出了窍:‘孩子的小脚丫都伸出来了!’说着把大秤钩子抄在手里,啐口唾沫就要干,天保佑,不知哪阵风把你给刮来了。你一脚踢开门,冲进屋,二话没说,先赏了我一个拐脖,疼得我像落了枕,然后推倒吓得掉了魂、直是哆嗦的老娘婆,架着我老婆上了吉普车,把司机拨拉到一边去,你一脚油门踩到底,到了医院,才剖腹取出来的。”
“我动手打你了?”于而龙不大相信,有些细节,他记不得了。
“还关了我几天禁闭,要不是接老婆出院,还得写检查呢!”
有这等事?!于而龙觉得自己当时的领导水平,十分可笑。对于战士的无知和守旧,相信老娘婆,而不相信新法接生,竟然动武,太过分了。
他逗络腮胡子:“你为什么不在前些年的批斗会上,再给我两拐脖,算清老账啊?”
没想到这个老实人回答得很干脆:“我不是那种畜生!”看来,他倒不曾计较,而且大概一直把于而龙当做是孩子的救命恩人。是啊!本来是要被秤钩肢解的婴儿,如今成了人,要结婚了。这样的大喜日子,于而龙要不去坐在头席上,那可太不圆满、太逊色了。
盛情难却:“要去的,要去的!”愿者上钩,于而龙满口答应下来。尽管他二次趴下,尽管他并不在乎那些禁令,但还是嘱咐着:“不过,有言在先,你不要搞很多人,尤其是骑兵们,免得头头们说三道四,又在进行什么反革命串联,正催命似的逼着我去什么转弯子学习班呢!”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他满口应承。
络腮胡子很高兴自己完成了任务,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打子烤得金黄蜡亮的烟叶。“老团长,你烟瘾大,尝尝自家种的,看看味道醇不醇?”
“喝,自留地又搞起来啦?”
他红着脸承认:“还是老地方!”
“实验场?”
络腮胡子惭愧地点点头,心痛地说:“这还是去年二次给你贴大字报时种的,如今越发没了王法,偷的偷,拿的拿,就连大鼻子专家都磕头的神庙佛龛——”于而龙明白他指的是那台属于禁运物资的高级电子计算机——“都要拆下来捣买捣卖啦!嗐!……”
烟草的味道果然醇香可口,烤得也够火候,然而关于实验场的噩耗似的消息,使他再没心思坐在护城河畔垂钓。那高高围墙里发生的一切吸引着他,使他关切,也使他苦恼,尽管他又一次离开那个工厂。
实验场要这样下去,门口也该挂起招魂幡,等于寿终正寝一样。于是,他抬腿就走,径直敲开了王纬宇的家门,迈腿进去,也不管人家欢迎不欢迎。
自从发作心肌梗死以来,还是头一回登门。喝!什么时候房间里装上了菲律宾杨木的墙围?工厂在他手里,十年来搞得快要破产,他自己的设备倒经常更新。于而龙不曾问他这些,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如果你多少还有点中国人的味儿,你就该去制止那些新贵们的愚蠢行动。毁坏工厂,反对机器,只有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才会出现的一场历史的反动。”
“你又来危言耸听!”
再比不上七六年的春天、夏天,一直到秋天,有谁比王纬宇更为忙碌的了,简直是青云直上。部里的事,他都得过问一二,特别是有关政治运动方面,更是当之无愧的主宰人物。不过,对于而龙,这样一个不识时务与风向的倒霉角色,倒不像有些势利眼,见了忙不迭地躲开,像害怕黄疸性肝炎传染那样。王纬宇才不在乎,现在,甚至倡议:“我给你煮点英国口味的咖啡喝,如何?”
“是卖了实验场,换来的咖啡吗?”
他宽宏大量地笑笑,因为他理解,凡是在野的草芥君子,免不了满腹牢骚:“大概如此吧!我空挂了十年革委会主任的牌子,厂里弄得山穷水尽,工资都开不出去,真没想到。唉!看起来退居二线,放手让高歌那帮年轻人去干,还是值得考虑呢!”他将咖啡壶的插销插在电门上,不多一会儿,就咕噜咕噜地响开了,水晶球里滚动着茶褐色的香喷喷的咖啡。
“你在犯罪,明白吗?”于而龙从来弹不虚发,这一点有些像牺牲的女指导员,那个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可是人民法院并没有给我发来届时到庭的传票呀!”他嘻嘻地笑着。
于而龙懂得他那笑声里,意味些什么。“老朋友,你操的哪门子心呢?连你自己,至今还是个梁上君子,没着没落,结论也做不出,倒有闲情逸致,去过问完全不用你过问的事。要不是你耗资千万,去建实验场,也许你今天的日子会好过一些。”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总有一天,会有人站在被告席上的。”于而龙望着那毫无一丝邪恶的脸,认为有必要这样说。
“可你,已经提审过,并且尝着甜头啦!”他斟上咖啡,推过来方糖罐,“如果你嫌不甜的话,还可以再放点。”
是的,于而龙自忖着:耗资千万是我的过错,直到今天,我不是还为这个实验场,在赎我的罪么?但是一想到那巨大的动力实验基地,已经饱受劫掠,再大拆大卸,连电子计算机都要变卖,怕是魂都招不回来。于而龙从来不曾乞求过谁:“你得说话呀,老王,你去对那些少爷们讲,我们中华民族不能活了今天,不顾明天。对一个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来讲,实验场绝不是太大。这不是我的话,建厂时中央的决定,老王啊老王!那是我们花了多少外汇买回来的呀,老王,得要多少列车鸡蛋、苹果、猪肉才换到手的呀!”
“干吗这样激动,注意你的心脏病才好!”
也许是浓咖啡的兴奋作用,要不,就是他关切实验场之情溢于言表,果真觉得心前区有点不太舒服,似乎是发病前的不祥之兆。立刻想起几个月前,背着氧气枕头被逼上台做检查的情景,赶紧含了一片硝酸甘油。
王纬宇那时飞黄腾达,一个实验场算得了什么,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于而龙,你和顽固的“将军”一样,只知守着一棵树吊死,那种朴质愚拙的情感,是又可笑,又可怜啊!“……不过,要是建厂初期我在的话,一定也不会赞成你那种做法的。”
“什么做法?”
“正如后来大家批判你的,贪大求洋呗!”
“啊!你——”于而龙气得手里的杯子都颤抖了。他清清楚楚地记得,六十年代,王纬宇刚调来工厂,曾经竭力称颂实验场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赞誉廖总工程师的动力理论为诺贝尔奖金的可能获得者。当时,他兴奋地拍着于而龙的肩膀:“你不愧是条翻江倒海的蛟龙,真行啊!这双捞鱼摸虾的手,倒有搞一番大事业的气魄……”
他当然不会忘记的,但现在却脸皮一点也不红地说:“那有什么可以奇怪的,老于,你别瞪着你的牛眼睛。我是研究过历史的,时间的辩证法,总是不停地修正人们的陈腐观点。过去,曾经视之为正确的东西,隔了一些日子,可能变为谬误;反过来讲,一些荒诞不经的、别出心裁的事物,倒可能是顶礼膜拜的真理。要不断以新的眼光去衡量,要有勇气去改变昨天的观点,甚至一个小时以前的观点。没有什么神圣的准则。再说,这样庞大的实验场,对工厂来讲,很像鸡窝里卧着一只凤凰,不伦不类啊……”
“你给我闭嘴!”于而龙实在压不住火,他快要爆炸了。
“干什么?干什么?”王纬宇连忙递给于而龙一条毛巾,擦那泼溅出来的咖啡汁。“活见鬼,肝火这么旺,你算是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心里想:也就看在多年共事的分上,担待罢了。真可笑,此人至今还拉不下架子,就像孔乙己那样,不肯卖掉长衫,怕丢了斯文一样地令人可悲。很难理解于而龙对于工厂的奇怪情感,难道还有什么牵连么?没啦!六七年第一次被打倒,七六年第二次被打倒。事不过三,历史已经给你作出判决,老朋友,承认现实吧!
于而龙也觉得自己过分,推开了王纬宇送来的听装中华牌香烟,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雪茄,点燃了。然后婉转地,同时也有点痛心地说:“你大概不知道,那个乳毛未褪、狗屁不通的专家组长,也曾经像你这样嘲笑过我!”
王纬宇调工厂前,外国专家在一夜间就全都撤走了,那时,他刚来,和于而龙并肩度过了一些难忘的岁月,使差点停摆的工厂,又正常地运转起来。
“……也许出于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要不,就是嫉妒心理作怪;那个刚拿到文凭就来中国当专家的别尔乌津,对实验场发表些什么感想:‘尊敬的厂长同志,你想在一个早晨,就把天国建成,使我钦佩。可是,除了密斯特廖,原谅我提个问题,使用实验场的中国专家在哪里?怕还在小学一年级课桌前坐着吧?’听,老王,他就这样挖苦我们,瞧不起我们。那种妄自尊大的习性,并不只是一个别尔乌津,我在那个国家实习过两年,我有发言权……”
于而龙站起来踱着,由于脚底软绵绵的异样感觉,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踩在地毯上。哦,大约不久该装上空调设备啦!确实也该武装一下了,如今来走访王纬宇的,除了他于而龙是个不官不民的半吊子,都是屁股后边冒烟的党国栋梁。连个阿猫阿狗一朝得志,还搬进一整套院子去住,他这就算不得什么了。于是笑笑,接着把故事讲下去。
“……那时小狄还是翻译,我叫她按我的原话,一字不落地翻给别尔乌津:‘亲爱的专家同志,如果你不介意,我给你介绍一篇中国古代的文章好吗?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的著名作品,很值得一读。他写道,在中国西南地区,有个叫做贵州的省份,那里奇怪的是,从来没有见过一种叫做驴的动物。一次,有个好奇的客人,用船运去了一头,放在山野里……”
王纬宇笑得前仰后合:“我就知道你不会善罢甘休的,挨了批评不是?”
“老王,实验场花掉人民小米千千万万,错是我铸下的,我已经受到惩罚,也甘心情愿永远接受审判。现在,只求你本着一颗中国人的心,想着民族,想着未来,即使廖总此生此世搞不出个名堂来,还是那句老话,失败的教训也是可贵的,千万别再干那些蠢事了!”
十年,在历史上只是滴答一声而已,而一个多么庞大的实验场,成了失去灵魂的躯壳,像历经兵燹的废墟。王纬宇不曾开着火车头去踏平实验场,也不曾混水摸鱼去偷白金坩埚,但他绝不是清白、干净和无罪的,正是他用最最“革命”的理论,怂恿和支持那些头头们、少爷们、败家子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工厂,砸了个稀巴烂。尤其是于而龙半生心血浇注的实验场,几乎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真是痛心啊!他记得终于磨破嘴唇,使廖总工程师到实验场上班去了。老头儿倒也不挑工作,只要让他干就行。可是一踏进实验场的大门,看到他追寻探索了一辈子的动力理论——其中有些部分在国外都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了,没想到在这个设计师的祖国,仅仅有的这个实验基地,竟落到了这种惨不忍睹的模样。这位工程师,甚至得知他挚爱的妻子逝世的消息,也不曾哭得这样伤心,好多有良心的老工人,都禁不住陪着落泪。是的,毁了,全毁了,而且是自己把自己毁了……
可是,王纬宇还觉得实验场死得不够,连那台电子计算机也要变卖了。
暴徒固然是可恨的,但制造出这批暴徒来的元凶才更可恶,就凭这一点,应该先把他们送上绞架。
于而龙不禁回忆起那些骑兵,在婚礼宴席上,从心田深处吼出来的话。至今,这些洪钟般的响亮语言,还在他耳边响着。在那次作为“反动集会”记录在案的婚礼上,正是那些骑兵,使他把多少年来的问号,改成了触目惊心的惊叹号。
“领着我们同他们干吧!老团长!”
多少双骑兵的眼睛望着他,多少双工人的粗手伸向他,于而龙那颗共产党员的心,活了。十年来,头一回跳得那样匀实、有力,像一个拳头要从胸膛里打出去。是的,三个惊叹号!!!
哦!那个被他弄得一团糟的婚礼啊!
这是他病后第一次出现在工厂附近的马棚住宅区,尽管他故意去得晚些,天都快擦黑了,但还是碰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那是回避不了的。握手、问好、交谈,一个传俩,两个传仨,都羡慕络腮胡子好大的面子,竟把老厂长弄来参加他儿子的婚礼,立刻,这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马棚一带。
当他跨进钉马掌名手喜气洋洋的屋门,哦,人头攒动,黑压压的一片。喝!那么多骑兵啊!房间里挤得满满腾腾,快成了那刚打开来的沙丁鱼罐头。还陆续不断地往里挤,不亚于赶早班的公共汽车。于而龙有点埋怨络腮胡子,违背约法三章,搞来许多人。再说,骑兵和酒,就如同汽油和火一样,一点就着,肯定要闹出些爆炸性的名堂来。络腮胡子的老伴,直埋怨这位挂掌中士的嘴不严实,发誓要往他的嘴里,塞上块马蹄铁才算解恨。不过,她还是蛮高兴的,终究老团长来做客了,所以也并不怎么拦着大家。因此,大家兴致一来,弄得哪像个婚礼啊!倒像个校友同乐会。没等上席,五六瓶酒——都是骑兵听说老团长来了,从自己袖筒里掏出来的——就着花生米,罐头,和不知谁揣来的狗肉,全灌进肚里去了。
钉掌能手无可奈何地朝于而龙表示歉意:“老团长,我要不告诉他们你来,众人还不得生吞活剥了我!”
年轻的新婚夫妇,紧挨着于而龙的身旁坐着,新娘也是骑兵家的后代,有着爽直泼辣的家风。和当今社会上年轻女性一样,毫无羞涩之意地做新媳妇。她劝着公婆:“让大家都进来吧!挤一挤!老厂长难得来一回马棚,就是大伙儿的客人啦!我记得小时候,老厂长常来马棚串门,如今来得少啦,不怪他嘛。大家说是不是?来吧,能喝的喝,能吃的吃,让老厂长一块跟咱们高兴高兴。”
“好哇!好哇!新娘子先敬老团长一杯!”
他举起杯来。骑兵们都挺体谅他,知道他发作过一次险几丧命的心脏病,知道他来一趟马棚,应该说不那么容易,不知什么帽子又在准备给他扣上呢!所以只要求他碰一碰杯,象征性地抿一口就行。这时,于而龙想起了他特地带来的礼品,是他女儿画的一幅油画,多少有点不合逻辑似的,一只强劲有力的巨拳,砸在了铁砧子上。他估计人们未必欣赏,谁知那位新媳妇却先爆出一个“好”!绝不是捧场,看得出她的确很中意,很喜欢。后来知道她正是工厂锻压中心的女锻工,怪不得她一连说了两三句:“真带劲!真够味!”来夸赞这幅画。
于而龙笑着告诉她:“这是一种被批判的画派,印象派,不怎么样!”
新娘子豪爽地回答:“批判?听拉拉蛄叫唤,还不种地呢!别看这拳头跟砧子连不到一块,逼急了,照样往下砸,我看画里的这股劲,正对着大家伙的心思,你们说呢!”
好几个人赞同地说:“别以为我们拳头是吃素的!”
看,酒喝多了不是?于而龙心想:议论渐渐出格了。
正当新娘捧着那幅油画,放得离眼远一点,打算仔细端详的时候,突然间,她的脸色变了。不光她,在座的骑兵们端着酒杯的手,都在空中像静止镜头一样停在那里,怎么回事?正在惊诧间,在门口进不来的人群里,一条粗浊的嗓子,带点半官方的味道问:“新娘新郎,恭喜恭喜,于而龙送你们俩什么礼物?怕不是白金坩埚吧?”
只见剽悍粗壮的小分队负责人康“司令”,从人群里挤了进来。这位康“司令”几年前在市里都是打出名的,只要有他介入的派仗,武斗,打出手,总会有几个脑袋瓜子开瓢的。
新娘,就是那个锻工,站起来,用手指着门,命令地呵斥着:“出去!”
哦!一个多么勇敢的骑兵后代啊!
“马上给我出去!”
他还是不识相地往席前靠拢:“好啊好!于而龙,给我站到前面来……”在干校,这位十年中突然发迹的,当过“盲流”的“司令”,每一次苦楚的“帮助”于而龙之前,总是以这样的口吻开头的。在座的客人中间,也有在干校呆过的,那种对付异教徒的办法,又浮现在眼前。人们实在不能再保持沉默了,豁拉一声,总有七八位吧,全都站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岁数数他最长,用他那低沉的嗓音,吼着:“滚!”
发怒的骑兵,最好不要去惹他,纵使一匹顽暴的劣马,也会叫它趴在地下起不来。康“司令”光棍不吃眼前亏:“好啊好!于而龙,你等着,我去把小分队拉来,你不去学习班,胆敢跑到马棚来搞阴谋活动……”他边说边撤,搬兵去了。
于而龙仿佛从这些骑兵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勇气、一种力量、一种觉醒。便淡淡一笑:“请吧!你有多大能耐,请使吧,咱们大家接着喝酒。”
那个差点被秤钩拉扯碎了的新郎,向尊贵的客人道了个歉,离席走到外间屋去,一会儿,络腮胡子和几个骑兵——都是膀大腰圆的,也请老团长先喝着,嘀嘀咕咕,在外间屋商量些什么,于而龙警告了一句:“可不要胡闹啊!”
新娘说:“老厂长,对付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鞭子比说话更有效果,信不信?”真是马背人家,连一个女孩子说出话来,也这样威风凛凛。她端起酒杯,显然有点生气地:“干吗愣着呀?不就是让条狗给搅了一下,理他呢!喝!”她给众人满上,但谁都不举杯。
于而龙只好端起来:“我借主人一杯酒,祝在座的全体同志和你们的全家老少,身体健康!”说罢向那位年长的骑兵碰碰杯,全都喝了下去。
“老团长!……”那个老骑兵突然被激动得站了起来。他不请自饮,又给自己倒满一盅,咕嘟咕嘟倒进了嗓子里:“老团长,我心里有底了。你是不会服软的,还是当年一马当先,冲在前头的样子。那时候,哪怕死就在眼前,可我们谁打怵过?眉头都不带皱。干革命嘛!为了党嘛!就应该那样嗷嗷地往前冲。可现在,老团长啊!你给我们上上大课吧,为什么人倒是活着,可活得窝囊,简直都憋屈死了的难熬难挨啊?……”他大概酒劲上来了,有些语无伦次,而且每一句话都有进康“司令”专政队的危险:“……我从来没有活得这么颠倒,这么糊涂过,好人成了坏人,坏人成了圣人,婊子成了观音,乌龟王八都上了台。我想不通,要不是我思想反动,是个天生的反革命,那我就要说句不客气的话,今天这个共产党和我昨天认识的那个共产党不一样,要不,就是有一个好人的共产党,还有一个坏人的共产党。老团长,老团长,我们骑兵团多少弟兄的血流在黄河沙滩上呀?我们挖了多少坑,埋掉那一个个为国牺牲的同志,为什么?到底为了什么?你告诉我,我们死了那么多的人换来的江山,就是为了今天,为了让刚才那样一个王八蛋,骑到我们工人头上拉屎撒尿吗?我们这些年拼死拼活图什么?那些牺牲的烈士图什么?……”很清楚,他实实在在地醉了,于而龙夺下他的杯子,但他还是要说下去,抓起那幅油画,指着那斗大的拳头,突然,擂了一下桌子:“老团长,你有没有胆子?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你领着咱们一块儿反吧!……”说着说着抱头呜呜地哭起来。
糟透了,把好端端的婚礼给搅了个乱七八糟,于而龙抱歉地望着当年在炕上打滚的难产母亲,似乎在说:“看,非把我弄来,结果——”但她好像并不在乎,叹了口气:“句句是理,酒后吐真言呐……”
于而龙等了半天,也没见康“司令”把小分队拉来。
“他,只不过是桌底下啃骨头的一条狗罢了!坏透了的是他们背后的老板。”工人们直率的话,震动了于而龙的心。
这时候,来了更多面熟的人,把屋里门外都塞满了,不得不轮换倒班,来同于而龙碰碰杯子。不知为什么,大家脸上都流露出会心的笑,似乎小孩搞一件背着人的恶作剧那样,挤挤眼睛,大口大口地把酒灌下肚去。有些刚建厂时的年轻人,现在都是五大三粗的汉子,还像当年共同野游爬山时那样,调皮地拍拍于而龙,给他做鬼脸。于而龙真想展开臂膀把他们都拥抱住,对他们说:“我于而龙算老几?是你们,是你们两只手,才把王爷坟建成了一个强大的动力基地,你们这样款待我,我倒真是受之有愧呢!”
从人们的笑脸上,可以分明看出来,如果于而龙第一次打倒在地时,他们还半信半疑对待那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那么这第二次趴下来,王爷坟所有正直的人,都认为于而龙是条真正的汉子,是为党、为国、为民的好人。这大概是属于物理学范畴的反馈现象,王纬宇恐怕是料想不到的。但于而龙却深深地感到内疚,过去,他在骑兵团冲锋的时候,总是一马当先,现在,这些战士的马跑到前头去了。
“等着我吧!同志们!”他在心里说,并且自慰地想,今天明白,还不算晚。
新郎回来了,络腮胡子回来了,那些个骑兵也耀武扬威地回来了:“没事了,老团长!”
“我们给你备好了马!”
喝!还从车库搞来一辆吉普,他向所有人告辞,等他走出门外,天哪……他的眼眶顿时热了起来,还有那么多的人进不到屋里,在楼道等候着。当他沿着楼梯往下走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亲切面孔,热情大手,朝他迎了过来,本来不太宽敞的楼道,就显得更拥塞狭窄了。
走吧,走吧!快些走吧!他催促着自己。要是再多待一会,还不定出些什么事呢!但是他的心被人们的热浪烘托着,尽管才喝了不多的酒,倒确确实实晕了。
那是一个没有春意的春天,隆冬的残影还盘桓在大地上,然而,在人们的心中,于而龙确实感到了春天的温暖。
等他回到了家,已经很晚了,没想到书房里还坐着一位客人,他估计到会有这一出戏要唱,但料不到这么快就掀开了上场门的门帘。
“赴宴去了吗?”王纬宇抬起头来。
他点了点头,倒在沙发上,琢磨这场戏该怎样收场。
“喝了什么好酒?”
“十全大补!”
王纬宇站起来在室内来回踱步,终于在他跟前停住脚,问道:“二龙,我不知道你到底还想干些什么?”
于而龙沉默着。
“你我不多不少,已经交往了快半个世纪,听我说,你就承认现状了吧!生活,应该使每个人变得聪明,以卵击石是没有用的。”
于而龙还是不做声。
这使一旁坐着的谢若萍惊奇,那是一个无论在口头上,行动上都不服输、不让步的倔犟水牛,今天怎么啦?竟俯首帖耳地听着,不反驳,不抗议,是近年来鲜见的。她想:十全大补是种什么酒呢?竟会使老头子变得和昨天迥不相同,成了另外一个人似的。
王纬宇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你知道吗?就在你喝十全大补的时候,他们把康‘司令’给揍了。这可是性质相当严重的问题,人家一下子就上了纲,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要不是我捂着,捅到指挥部,就闹大发了……老兄……”正当他要奚落于而龙,没病找病,自作自受,炫耀自己斡旋有功的时候,只见那个喝了十全大补的闯祸家伙,把身子佝偻着弯了过来,脑袋垂下,几乎贴在了膝盖上。“咦?……”
“二龙——”谢若萍顿时觉得天昏地转,扑了过来。
“快……快给我输氧……”于而龙吭吭唧唧地吐出了这几个字。
“莲莲,莲莲——”她抱住他,喊着,“快拿氧气袋来!”
正在画画的于莲,一阵风地进来了,一见这阵势,吓得脸都白了。“爸,爸,不要紧吧?”
“没什么关系……现在好多了!……”等到老伴把氧气枕头的透明胶管粘在他鼻孔附近,于而龙仰卧在沙发上,显得极其疲惫软弱地回答着。然后,他呻吟地对客人说:“老王,你接着,接着往下讲吧……”
“好吧!你先休息吧!”王纬宇要告辞了。
“你,你再坐会儿嘛!我,我好多啦!……”说着,似乎相当累乏地合上了眼睛。
王纬宇走了,谢若萍和于莲送他出来,在楼梯口,他拦住她俩:“别送了,快照顾老于去!”径直回到斜对面的楼里。
谢若萍和她女儿回到屋里,正要责备他不该赴宴、不该饮酒(当着客人怎么好说这些呢?最初她就不同意),发现于而龙已经从沙发里站起来,正扯着粘住胶管的橡皮膏。
“你怎么啦?”医生不解地问。
“我没病——”于而龙回答,“而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健康!”
谢若萍瞪大了眼珠子,莫名其妙地望着她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