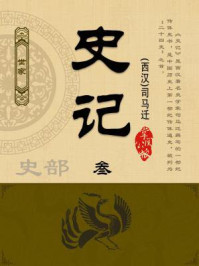近五十年来,我们的史学界,不但在方法上史观上有伟大的进步。而这五十年又恰好是中国有史以来史料发现最多的时期。晋初《竹书纪年》的发现,改变了当时的史学思想和古史研究。宋代古物的出土引起了学者们考古的兴趣。这都是新史料的发现对于学术界的影响,但是和近五十年所发现的新史料相比,实在是渺小得很。
近五十年来,在史料方面,中国有三宗发现:(一)是河南安阳商代遗物的发现,(二)是敦煌古物的发现,(三)是史前遗迹的发现。至于北平内阁大库明清史料的整理,明清实录和清代外交史料的刊印尚不在内。这些新发现为我国文化史增加了无数的新资料。如何将这些新资料用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史这便是我们当前最艰巨的工作。
关于殷墟遗物的发现,董作宾先生的甲骨年表记载已详。简单地说来,最初是无意中发现的。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即是庚子的前一年,河南安阳县小屯村农民因种棉而掘得骨片,遂称之为龙骨,售之于药店。其后古董商人知为古物,挟之入京,引起了中外学者们的注意。最初搜集的有王懿荣、刘鹗及外人明义士林泰辅等人。到了罗振玉先生才为之大量的收集,并录考释。到了王国维先生更应用之作文字学历史的研究。到了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董作宾先生领导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赴安阳调查,这是对殷墟古物作者有系统的发掘的开始。这种工作,前后举行了十五次,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才停止。前后出土的甲骨文字凡二万三千余片,此外出土的铜器,石器骨器,也有数千件。这实在是二千年来,关于古代史料,最重要的发现。甲骨文字的著录工作虽始于孙诒让、刘鹗二氏,而发扬光大之功,实不能不首推罗振玉先生。罗氏对于甲骨文字搜罗之勤,鉴别之精,著录之多,考释之严,并世无两,是这门学问的开山大师。罗氏的工作,又多靠了他的好友王国维先生的协助。王氏以缜密的方法,锐敏的眼光,又将甲骨文字的研究引到了小学及古史上去。罗王两先生的弟子董作宾先生不但领导殷墟的发掘,并将甲骨文字作断代的研究,又根据他推测殷历,是当代甲骨学最高的权威。郭沫若先生据甲骨文来研究殷代社会,又为甲骨文字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方面。此外,现在以甲骨文名家者,不下数十人,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了。
当安阳出土甲骨的明年,也就是八国联军将闹北京的那一年,在西北安静的角落里,又有惊人的大发现。原来甘肃的敦煌,现今虽然是一个穷僻的小县,而自汉至唐,乃是东西交通的孔道,在当时乃是一个繁荣的所在。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敦煌城东南千佛洞道士王圆录无意中在洞中发现了无数的写本刻本书籍,以及古代的绘画。这正是中国情形最混乱的时期,无人注意于此。却是一位英国人名叫斯坦因,威逼利诱,巧取豪夺,共装走了二十九箱。这种国宝本来是不能随意出境的,但是这正当国事混乱空前的时候,那有人来拦挡此事?斯坦因得到了便宜,前后来了数次。其后法人伯希和又从王道士买走了二千卷写本,将一部分携到北平,中国学者才知道此事,遂呈请政府,收归国有。今北平图书馆所保存者,即是这批劫余的残卷。
斯坦因不但诱买了敦煌的残经卷,又在敦煌附近发现近千片的汉简,大部分是汉代守戍人员往来的公文簿册,还有少数的参考书私人函件,以及一些日用工具。1930年中国学术团体和瑞典人斯文赫定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古团又在酒泉以北,汉代振城遗址内发现了一万多片汉简。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冬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又在敦煌西北大方盘城附近发现了一些汉简。
这些古代的遗书,以及石窟中的壁画塑像等都是汉唐期间最珍贵的史料,这些东西的发现增加了不少我们对于汉唐间文化的知识。
其次,近三十年来关于中国史前期遗迹的发现,改变了整个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来源的看法。五十年前不但外国认为中国没有史前文化,即是中国人也说汉族是西来的。1921年仰韶沙锅屯文化的发现,推翻了中国无史前文化的观念,1930年“北京人”的发现,更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久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方在开始,将来的前途是无量的。
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的工作。这些材料的整理、鉴别、解释,只有专家才能胜任,不是一般人能做的。现在史前考古、甲骨文字、钟鼎文字、西北史地皆成了专门的学问。其余别的部门的研究,也是日趋于专门化。本来专门化是科学工作的基础,只有细密的分工,才能有可靠的收获。现在史学界如司马迁、司马光一人包办全史(教科书除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正如亚里斯多德式的科学研究已经过去了一样。现代的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正如有了砖才好造房。
民国以来的史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郭沫若等先生,他们的研绩俱是以专题论文的方式发表出来的,除了他们的作品之外,无数的专题论文,在学术杂志中发表,成了我们现代史学的基础。这种风气经几位大师的提倡,和西洋前例的引导,到了民国十年以后,专门的学术杂志便纷纷的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如《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清华学报》(1924年),《燕京学报》(1927年),《史学年报》(1930年),《辅仁学志》,(1928年),《金陵学报》(1936年),《武昌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年),《地学杂志》(1909年),《禹贡半月刊》(1934年),《食货》半月刊(1934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辑刊》(192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专刊报告》(1928年)《田野报告》(1936年),《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以及其他学报杂志不下数十种,我们史学的拓荒工作,多半首先在这里发表,这里面实蕴藏着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研究的大部成绩。
现代的史学和现代的科学一样,已经走到集体工作的阶段上,没有和以前像司马迁,刘知几等震耀一时的名星了。各专门范围之内,皆有主要的领导者,譬如史前期考古有李济之、梁思永、裴文中、吴金鼎等先生。殷周史以王国维、吴其昌、郭沫若、徐中舒等先生的贡献最大。秦汉魏晋南北朝则有陈寅恪、周一良、劳幹,贺昌群等名家。随唐五代自然以张尔田、陈寅恪二先生为巨擘。宋辽金元近来名家甚多,尤以聂崇歧、冯家昇、邵循正、陈述、陈盘、罗福颐诸先生成绩最多。明清史方面人更多了。老辈如孟森、张尔田皆已作古。后起的则有吴晗、李晋华、专治明、萧一山、王崇武、赵丰田,专治清。西北史地中西交通,老辈张星烺,冯承钧皆有不朽的成绩,后起的如王静如、韩儒林皆深通西北民族语言。至于文学史、哲学史、宗教史、美术史、经济史已各有专科,非本文讨论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