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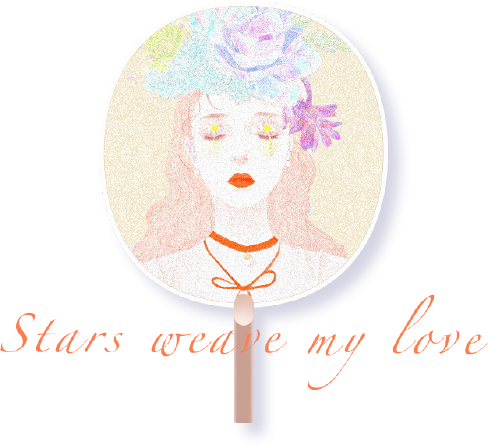
七月的尾巴,公司突然空降重要外籍客户,是位法国籍名媛,叫Jade。她需要订制手工婚纱,指名唐舜华做主设计,带领团队倾力打造。
原本是好事,可办公室里气氛相当诡异,人人一脸讳莫如深,眉眼官司打得热闹。
经过连越的权威科普,欢喜才大致弄清楚原因何在。
这位Jade太太身上充满传奇色彩,做女人的成绩相当斐然,简直可以录入教科书。伊人来历很有点复杂,追溯起来还带着中国血统。Jade的祖母Eva,是民国时期某位军阀的女儿,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随曾祖母避战乱出生在法国,就此代代定居下来。【见《寄鹤抄》】
Jade是画家,年轻时已在业内极有声名,性喜奢华又浪漫奔放,身边情人无数。后来在全盛时期突然嫁人,没几年又轰轰烈烈离了婚,分得大笔赡养费。此次再嫁的第二任丈夫,名字在华尔街新闻上常见,一个显赫到吓死人的金融家族。尤为关键的一点是,据说她的第一任丈夫,就是明唐大股东顾秀谦。两人还育有一个混血女儿,年方12,名叫Mathilde。和《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少女同名,古怪精灵也不遑多让。
会客室冷气开得十足,像笼罩了一层看不见的冰雾。欢喜跟在连越身后默默地找个角落待着,视线不得不被这人群中艳异的存在吸引。
Jade双腿交叠,优雅地浅坐。她的小腿很美,白森森挑不出半点瑕疵。姿态无疑是冶艳的,手执羽毛饰扇,头上还戴一顶十八世纪法国贵妇大檐帽,半扇面纱垂下,枯玫瑰色的红唇依然清晰可见。再贵的口红也会脱色,她习惯在喝水前用纸巾轻轻按一下嘴唇,保证杯沿不留半点痕迹。因此每隔十几分钟,就得去盥洗室仔细补一回妆。
塔夫绸裙子在膝上十公分处斜开衩,行动处簌簌有声。肩带极细,抬手便要断掉的样子。优柔行过,留下身后香风细细。
庄采采站在长廊另一侧,掩住口小声嘀咕:“我的老天鹅呀,这也太夸张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公司今天在拍戏呢,她真是顾总的前妻?啧啧……”
林佩目不转睛盯着Jade的背影,就像看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在眼前化为具体而微的形状。双手不自觉紧握在胸前,渴慕地说:“她这样的女人,就是我的少女梦啊!你看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吧?黛西在西海岸的豪宅里跳舞,她心爱的男人就在楼梯上把数不清的绫罗绸扔下来,还带着标签吊牌,把黛西整个埋在中间……”
她的代入感太强烈,末了还留下一声意犹未尽的叹息。
唐舜华显然不吃这套。
无论Jade的态度如何坚持,她并不打算亲自参与这次设计。顾秀谦在中间打圆场,状况紧张得像绷紧的弦,是个人都看出来不对劲。
仅从第一印象来看,这两个女人都属于那种大开大阖的霸气明媚范儿,美艳不分伯仲。Jade姿仪高贵,天然自带一股金玉中娇养出的底气。同样具有攻击性,找不出过分尖锐的地方,却又无处不在。唐舜华的气场则又不同,是明晃晃不可逼视的,披鳞戴爪头角峥嵘。
甄真对连越使个眼色,说声抱歉起身去了洗手间。几分钟后,连越也借故脱身,两人在走廊尽头的小会议室碰面,欢喜很识趣地站在门口望风。
唐舜华态度谦和无可挑剔,口风却丝毫没有松动。话里话外透露的意思,是打算让甄真接手这个活儿。半个多小时的谈话,甄真在旁看得惊出一背的冷汗。也顾不得讲究措辞,直接问:“他们到底怎么回事?”
连越把她拉到椅子上坐下,简单说:“我觉得吧,这就是个烫手山芋。以唐总如今地位,又不指望靠她这场婚礼去扬名立万,何必留下话柄在人间?一个女人肯这样无微不至地铺排她自己,对旁人的挑剔也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真要接过来,干好了未必有功,出点岔子责任全在你。”
“做生意是你情我愿,没有强压头的道理。唐总不愿意搭理她,直接拒绝就好了,何必非要找不自在?”
连越微微弯了眼睛,“碍着Uncle顾,怎么好开口拒绝?人家明摆着是故意找上门来的。”想了想,又道:“其实也不全是因为这个。”
甄真哑然地张了张口,表示理解不能。
连越告诉她,Jade一直认为唐舜华是她和顾秀谦婚姻破裂的原因,此番风光再嫁,自然要扬眉吐气。顾秀谦虽然对此很头疼,也无力劝说骄傲的Jade改变主意。
甄真沉默了两秒,小心问道:“那顾总真的是因为……你明白我意思吧?”
酷暑阳光猛烈,连越抬手遮了遮眉眼,走去把百叶帘合上,说:“这样,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红尘里的爱恨情仇,每天都在上演。在芦山县医院里,甄真记得连越说起过一些,而那既不是是故事的起点,也远非终点。
二十几年前有个女孩,热爱时装设计,毕业后成了一家跨国设计公司的小助理。她年轻、美丽且天赋过人,本该有大好前途,却在正式入行的第二年,爱上了自己的上司,设计总监孙维光。
恋情无法隐瞒时,为了保全孙维光的职业前途,女孩决定主动辞职。
放弃心爱的设计工作后,两人很快结婚,孙维光向她承诺,她的才华绝不会就此埋没,他们将来必定能在行业里闯出自己的天下。
没过多久,孙维光果然得遇贵人,毅然离开原公司,夫妻开始携手创业。那段日子压力很大,孙维光极度渴望成功,在患得患失中焦虑难安。他变得敏感,脾气暴躁,灵感却渐渐枯竭。
他们的孩子刚出生还没满月,孙维光便干下一件令人齿寒的龌龊事——窃取了女孩的设计稿,将成果全部据为己有。《天桥骄子》国际设计大赛的成功,让他一战成名,拿到十万美元奖金。
那是美国一个业内关注度颇高的娱乐真人秀,所有怀才不遇的设计师们仅剩的独木桥。只要能在千军万马中拼杀过去,接下来是可以预见的青云坦途。他赢得了冠军,受邀参加时装周,又举办了自己的第一场国际时装秀,名字逐渐被业内认可。
女孩性子刚烈,当然不能容忍如此背叛,决意拆穿他的画皮。孙维光好不容易得到这一切,当然无法接受真相被公布的后果,便决定先下手为强。他花了大价钱多方买通,伪造出一份精神失常的鉴定证明,把人强行关进精神病院长达半年之久,并执意不肯离婚。
曾经的恩爱夫妻,就此反目成仇。
那是一段地狱般的黑暗时光,正常人沦落到如此地步也要被逼疯。就像醉酒的人总爱说自己没醉,没有谁会相信一个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人说她没疯。
女孩在逆境中展现了惊人的韧性。她冷静下来,尽可能理智地分析自己的处境,不再哭闹,也没有再试图逃跑。渐渐地,晚上不用再被绑在约束床上,白天也有了一点自由活动的时间。
她温顺地配合护士,任由摆布。每天吞下大把药丸,过后再偷偷在厕所里抠喉咙吐掉。当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残留的药性积累,还是对她的身体造成影响。这些药会让人精神涣散,持续地犯困,记忆力逐渐衰退,每天都昏昏沉沉。整个人像吹气球一样浮肿发胖,胃口却极糟糕。原本细腻的皮肤变得油腻粗糙,头发也大把脱落。
唯一坚持下来的事,就是阅读。她看书,强迫自己每天背诵单词,全凭惊人的意志力保持头脑清醒,没有一分钟忘记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着怎样的罪恶。支撑她活着离开的信念,是尚在襁褓中的孩子。
孙维光的妹妹孙佳来看望过一次,发现这个曾经明丽潇洒的女人,已经面目全非到根本认不出来。她很胆小,说话声音几乎听不清,像只愚笨容易受惊的小动物。就这样,一点一点地骗取了小姑的信任。终于有一天,提出想要回去看看孩子。
这姑娘年纪尚轻,并不知道她哥哥背地里对妻儿的所作所为。毕竟可怜她们母子分离,询问过医生后,瞒着孙维光把女孩接了出去。只有半天的假期,晚上还要把人再送回精神病院。
第一次,女孩没有跑。她无比配合,表现得温和安静。
第二次也没有。
第三次还是没有。
直到第四次,得知孙维光在国外出差尚未回来,那是绝无仅有的机会。
女孩等这一天等了太久,早就把流程在脑海里演练过千千万万遍。她有条不紊,先把偷藏的镇定药物放进水里,让孙佳喝下,然后拿走了身份证件和能找到的全部现金,带着孩子开始逃亡之旅。再耽搁下去,可能真的会被耗死在孙维光手里。
做这一切的时候,心里毫无波澜,觉得自己终于成了一个冷静的疯人。
女孩历经万难才重获自由,也已经一无所有,还要养活幼弱的婴孩,只得咬牙重新开始。
在尼斯初遇顾秀谦,已经是八年以后。
甄真听到这里便明白了,故事里的女孩,就是唐舜华。
蝴蝶好不容易冲破茧壳,外面却是冰天雪地。她迁徙过许多国家,从蛮荒野性的西西里到东部的香柏利城,尼斯到布拉格,曼哈顿到布兰克,停留最长的地方还是法国。像个流浪的吉普赛女人,被命运不断驱逐,却怀着最大的勇气与之周旋,永不言弃。
漂泊的日子里,唐舜华学会了各种混杂的奇怪语言,在酒吧当舞娘,中餐馆里刷盘子,跟一帮落魄学生在街头做艺术表演……吃尽了人情冷暖的苦。双手长满冻疮裂口,又须终日泡在水里,没有愈合的机会。夜晚天寒地冻,没有空调也烧不起暖炉,登台之前就灌一大口烈酒取暖。两颊被劣质酒精烧得酡红,连腮红都省了。但这些跟在国内被囚禁的绝望相比,都算不得什么。
被狠狠捅过一刀的人,等于把浑身的血液都换过一遍。失去幻觉,也就无所畏惧。孙维光没能杀死她,这一切遭遇令她自废墟中重生,变得更强。
天赋是唐舜华骨子里的钢铁,支撑着她,即使被惨烈地凌辱折损过,一样熠熠生光。因本身有一定的设计绘画基础,她跟那帮美院的学生一起学了油画和粉彩,给画廊画复制品和装饰小框画。租住在狭窄阁楼,衣服上到处抹着颜料。从早到晚,一天可以画上十几张,赚取微薄薪酬。手头还是拮据,常等在课室外,把学生画完静物练习的水果蔬菜要了来,切好拌成沙拉,和孩子分吃掉。
有时跟一大帮人出去采风,一走半个多月,孩子就放在朋友家里寄养。她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母亲,也并不很懂得如何去做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母亲。只是遵循天性里的情感,但相处起来,又经常找不到感觉,也不知道如何相处才是妥当。
常年浪迹天涯,自然结交下无数三教九流。潦倒的作曲家、做军火生意的俄罗斯人、会唱歌剧的意大利人、爱喝酒的外科医生……唐舜华天性刚强洒脱,不造作,讲义气,言谈也俏皮有趣,会讲各式各样的笑话,男人女人都喜欢她。就此跟很多人有过或长或短的交往,同性的,异性的,年轻的、年老的、英俊或普通的……有情人多少能让日子好过些。只是不再轻言爱或不爱。情深不寿,她可不想下半生都跌跌撞撞。
她从不需要一个男人,不寻求虚幻的诺言和保护。同样,她的孩子也就学会不需要父亲,对生命中的缺失习以为常。
后来收入慢慢稳定,孩子也到了需要上学的年纪,唐舜华便在巴黎定居下来。同时打三份工,在洗手间狭窄的水池上摆一块木板,趴在上面画设计稿。
两年多没有过情人。别人抽烟喝酒烧大麻,她说我不去了,就关在房间里听磁带、画画素描本上涂涂抹抹,每周花七个小时学习西语。她从来都是自己的主人,清醒固然痛苦,失去自制力则意味着堕落无止尽。
和顾秀谦再次相遇,彻底改变了她的未来。那时顾秀谦还在奥地利做酒店生意,回法国是为了探望女儿。
回忆起来也是个寻常日子。
八月夏天,又热闹节庆。彼时刚交完房租,已经拿不出多余的钱给孩子买礼物。暴烈日头底下,她在途经的教堂前即兴跳了支舞。
城里有风,天空是陈旧的蓝色,有点脏。那天唐舜华穿一条火红的桑蚕丝裙子,袖口的线头已经脱落散开。细节的落魄无处不在,却无损于她的美貌和张扬。
她的佛朗明哥跳得似模似样,是在西班牙时跟酒吧舞娘学的。舞多么炽烈而真实,是独属于身体的语言,有汗有痛,铿然作响。裙摆烈如一团火,卷起干燥尘沙。
急速地敲击转身,仿佛扬手就能触到天空。落点时常都不准,但速度极稳极快,她专注的时候很美,散了一鬈长发。
鸽子扑翼飞过,广场上有老妪弹印度西塔琴。人群渐渐聚拢起来,手鼓铃打拍子,用听不懂的语言发出欢呼。
黄昏降临这样迅疾。
她跳完舞,把地上散落的纸钞和硬币全部归拢捡起,跑去买回一支超大的手工冰激凌,蹲下来放进孩子手里:“宝贝,生日快乐。”
坐在台阶上点清剩余的钱,才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枚不认识的硕大金币。颜色发乌,形状也不太规则,看得出有年头了,图案被摩挲得十分光润。正面是向右站立的王像,右手伸向祭坛,左手持三叉戟,背面是靠在牛背中间的湿婆,手持三叉戟。
一个亚洲男子走到身旁坐下,说:“这是1第纳尔。上面那圈古希腊文的意思是‘王中之王,贵霜王波调’。”【第纳尔:古罗马货币计量单位】
这是波调一世时期的霜贵帝国金币。
她抬眼看他,压根就没想起来这人是谁,但心知古董金币出自他手。真是一份阔绰的馈赠。
唐舜华跳得口渴,到喷泉前面用手接几捧水来喝,又给自己点了根烟,发现他还没走,便垂下眼说:“谢谢。”
他告诉她,围观人群里那一串发音的意思是:“东方的艾丝美拉达”。拉丁语。
又说,“不如你请我抽一支。”
她从烟盒里取出最后一根递过去,他却不接,只笑道:“帮我点上可以吗?”
她没所谓地耸肩,就去替他点。结果打火机半天都摁不燃,男子便从她唇间拿走只剩三分之二的香烟去抽,“我跟你换。”
那支抽过的烟身上还印有纹路凌乱唇痕,像一个欲言又止的诱惑。
劣质烟草辛辣呛人,但劲儿很足。男子笑时露出一口白牙,说:“我是顾秀谦,我们在尼斯见过。”
他邀她共进晚餐,唐舜华没多想就答应了。左右不过一顿饭,跟谁吃都是吃。孩子舔着冰激凌,沉默地跟在后面。甜腻的汁液化开,淌在手上有点黏。
没想到男子厨艺很好。切几片火腿加青橄榄,腌制好的鹰嘴豆,青瓜芦笋和面包,意大利面上洒切碎的罗勒叶,配一支勃艮第红酒,滋味清淡不俗。
那天唐舜华吃了很多。她总是感到饿,需要很多的热量来维持体能。坐在窗前,旁若无人地大口咀嚼食物,完全不在乎形象。吃完了把餐盘推开,问他:“还有没有别的?我是肉食动物。”
她不是娇柔花朵,更像一束蓬勃而奔放的,烈火荆棘。那样瘦,却又丰盛浓艳,眸子里闪着母兽般的光。
他便又煎了一客香草牛排,放到她面前。
顾秀谦拎起酒杯啜饮,望着她专注吃食物的样子,说:“你的舞跳得很好。”
后来他们一起看了部电影,《黑暗中的舞者》。“that"s all……”的歌声响起,她的孩子已经蜷在沙发上熟睡。唐舜华喝光剩下的半瓶酒,有一点醉了,眼眸却极淡静。只抬手抹一把额上热出的细汗,说:“都是精明算计。这男人,换我一样毫不犹豫枪杀他。”
这部电影是丹麦导演拉尔斯创作的金心三部曲中最后一部。热爱舞蹈却即将失明的单身母亲玛莎,为了筹钱给孩子治疗遗传眼疾,甘愿隐瞒真相,最终被控一级谋杀。
灵感来自一则导演最喜欢的童话故事,顾秀谦用慵懒语调讲给她听:一个小女孩独自去森林游玩,她手里有面包,口袋里有玩具,但她却愉快地把所有的东西一件件给予了沿途遇到的人,最后什么也没剩下,一贫如洗。
可女孩说:“我一切都会顺心如意,一切都将完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