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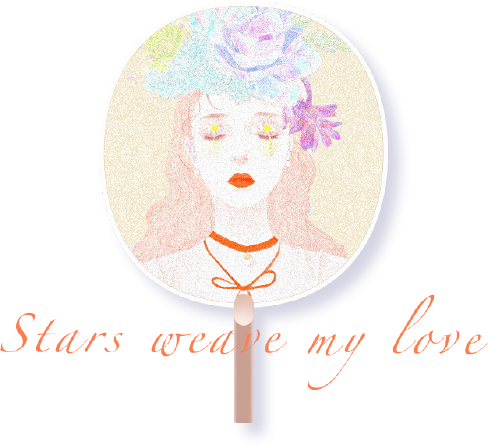
甄真蜷在鸟笼形状的秋千椅里,桌上横七竖八摆了十几支喝空的科罗娜瓶子。
一张清水脸,被细碎灯影照得泪痕好斑驳。她是有一点醉了,也不过弓下身用双手捂住脸。单薄的背脊突出两枚蝴蝶骨,微微颤抖。
像飞了好久的鸟,躲在无人知晓处,舔舐折翼的伤。袖口潦草挽起,雪白上臂露出大片彼岸花纹身。近看才晓得,是用印度海娜膏画出的纹样。没有色彩,分明又触目的黑。
彼岸花,叶开不见花,花开不见叶。象征着黄泉渡的凄绝爱情。
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她终于接起来,一字一字低哑道:“蓝绍纶,事到如今我也没力气再同你纠结什么爱或不爱。他们欠的,我还。还不起,用命赔给你,够不够?”说完关掉手机,随手扔进角落里。
睫毛好似黑蝴蝶,扑两下,又颓然静止。
欢喜从来没见过,有人可以哭得那么惨烈又那么平静。踟蹰了半晌,还是决定默默离开。
心里莫名触动,往后退时不小心撞翻了一把椅子,发出刺耳声响。
突兀的动静引来一束目光。连越从三米外的藤椅里懒洋洋转过脸,他也看见了甄真——和那个拎着两杯特调前来搭讪的男子。
“Bonsoir。”(法语,你好。)别致的开场白,分明又是个黄皮肤黑发的中国人。
此人个子不高,衬衫领口内系一条手帕方巾。梳溜光背头,细看脸上是带了点妆容的,每处细节都打扮得很花心思,只是略显油腻。
甄真仍蜷在秋千里不语不动,全当没听见。
男人并不气馁,把手里的酒放在她面前,说:“它叫‘寒江雪’,特意为你调的。愿你想念的人,此刻也正想你。”
盛在细长柯林杯里的酒液通体雪白,冰块里还放了小灯泡,冷光莹莹。这是近来流行的夜光鸡尾酒,看着炫目,喝起来未必。
甄真微微抬起眼,目光里全是熄灭的余烬。说:“可惜了,不适合我。”
男子耸肩,“那么换一个——敬,爱恨扯平两不相欠。”
真是别开生面的祝酒辞。甄真眉心轻动,终于接过酒杯喝了一口。男人趁势在她身边坐下,“让这么美丽的女孩子一个人喝闷酒掉眼泪,是最大的犯罪。”
相熟的侍应生把一杯加冰威士忌放在连越面前,顺着他的视线望去,低声说:“连公子,瞧见没?有人砸你场子来了。这不是班门弄斧嘛,能忍?”
连越不置可否,食指轻叩桌面,漫不经心问:“那家伙什么人?”他今晚换了身黑风衣,宽宽松松一点花样也无,融进夜色里毫不引人注意。
侍应生撇撇嘴,不屑道:“旁边威臣广告的White胡,登徒子一个。装什么外宾呢,兜里没几个钱,整天花蝴蝶一样到处聊骚,变着花儿地把人灌醉了就带走。才来了小半年,惨遭毒手的女孩子起码六、七个。那女的你认识?”
连越喝一口威士忌,垂目冷道:“不认识。”
侍应生满脸促狭:“长得挺漂亮哈,这年头不化妆还能看的女的不多了。这就叫什么,是白菜就别怨猪跟着。”
那边厢,White正使出十八般武艺,卯足了劲要拱下这棵冷冰冰的高岭白菜。连越转过头不去看他们,盯着手机里的通讯录划来划去,终于下决心拨了个号码。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甄真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被White半扶半抱地拖着往外走。她明显是不愿意的,奈何连站都站不稳,战斗力基本成渣,推搡看起来就像打情骂俏。
秒针还差半圈指向零点,仙德瑞拉即将失去她的水晶鞋。连越有点烦躁,把杯底剩下的一点酒仰头饮尽。突然起身拦住他俩,用力把White推开,唇间冷冷迸出一个字:“滚。”
White冷不丁被推个踉跄,愤而揪起连越的领口:“哪来的娘炮?你他妈有病啊!”
欢喜站在酒柜后看完了全过程,忍不住就要去把这桩闲事管上一管,被醉醺醺的绿萝死命拉住:“你冷静一点,连越好歹是个男的……他既然出手了肯定会有办法,再说他和那个甄真的事你也不清楚,先别瞎掺和。”
欢喜把连越从头到脚打量一遍,担忧道:“看他那样子,说是男的我姑且相信,真打起来怕是会吃亏。”
风姿绰约的连越确实不擅长用武力解决问题,只会以德服人。
他掰开White的手,弯腰从地上捡起被拽掉的两颗纯银纽扣,清清淡淡说:“酒吧有二十四小时摄像头,在公共场所灌醉女性强行带走,是非法控制人身自由,涉嫌诱奸。至于寻衅滋事,损毁他人财物么——”
连越故意顿了顿,拨弄着手里的纽扣,续道:“这件Hermes私人高定,手工限量版,售价二十七万人民币。具体怎么个赔法,你可以和我的律师谈。又或者,我亲自去找威臣广告的许总聊聊。许进安你应该认识,是你们部门的直属上司,对吧?胡宏伟。哦还有,听说你老婆冯韵在威臣做行政管理,我找她也行。”
这波操作精准地打在七寸上。White底细被摸个门儿清,顿时有点慌。强作镇定说:“哥们儿别激动,我不知道你跟这妞认识……今晚这事儿吧其实,都是误会……”
绿萝叼着手指赞叹:“我头回觉得,仗势欺人也能这么帅。活脱脱的正义版高衙内啊!你说他那件衣服,穿了能延年益寿不?”
欢喜也表示服气:“这就是金钱的魅力。”想了想,又说,“能不能延年益寿我不清楚,但在增加男子气概这方面明显没什么作用。好就好在,幸亏现在不是冷兵器时代。”
绿萝小眼神里的幽怨呼之欲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前方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White还在絮絮赔罪,突然发现连越的视线落在他身后,表情有点古怪。刚要回头,后脑勺便狠狠挨了一记。
甄真摇摇晃晃站起来,脱下右脚的高跟鞋用力砸在White脑袋上,发出醒狮的咆哮:“给老娘滚!”
回光返照的清醒只是一瞬,发作过后,整个人又支持不住软软倒向沙发。White顺势滚远,连越犹豫了片刻,捡起地上的鞋子朝她走过去。
绿萝吓得酒都醒了,打着手势对欢喜说:“咱们还是走吧……”
欢喜还是不放心:“他俩白天掐得那么厉害,你说连越会不会秋后算账?”
绿萝说:“不会不会,你想多了。他不像那么小肚鸡肠的人,要真想落井下石,刚才犯不着帮忙。”
没想到此话一出,很快就被现实打脸。
连越拿起剩下的半杯“寒江雪”闻了闻,顿时皱眉。里面不知调了什么猛料,酒精浓度应该不低于百分之六十。
他招手叫来两杯冰水,刚才的侍应生朝他竖起拇指,眉飞色舞道:“连公子,厉害啊!这就顺利截胡了不是?佩服佩服!”
连越被说得越发尴尬,慢回娇眼不屑道:“你什么时候见我品味这么糟糕过?她这浑身上下,有哪点像个女的?”
甄真恰在此时醒来,太阳穴像被重斧抡过,一阵一阵地疼。睁开朦胧醉眼看了好半天,认出身旁坐着的黑衣男子,正是刚才解围的人。
她清一下嗓子,说:“这位先生,请问,怎么称呼?”语速很慢,显然是在拼命克制晕眩,试图集中注意力。
连越瞥她一眼,“既然你没事,我先走了。”
正要起身,被甄真一把拉住袖口,“等等……我、我还没谢你。”
连越无奈地仰头看天花板:“我没打算要你谢。”
“不行。”甄真垂下眼,匀了匀呼吸,坚持道:“要谢的。我不喜欢欠人情。”
看来她确实醉得很厉害,已经完全认不出眼前的死对头。也难怪,白天互掐的时候,连越从头到尾敷着面膜,本就没几个人见识过真容。
他抽了两下胳膊,没抽出来。只得重新坐下:“行,那就重新认识一下。”
甄真怔怔地望着他,眼睛里都是茫然。
连越挑挑眉,好整以暇拿起另一杯冰水,反手就从她头顶浇下。
“我,连越,是个喜欢斤斤计较的人,吃了亏一定会以牙还牙。你泼我一杯水,我还你一杯,以后两不相欠,用不着谢了。”
她还没反应过来,连越已经系好风衣起身离开。
欢喜躲在暗处打了个跌,被绿萝扶稳。她扶额冷静半晌,无力道:“我看甄真酒也醒了,应该没什么事。咱俩功成身退吧?”
绿萝巴不得赶紧远离是非之地,忙点头:“臣附议。”
连越的以牙还牙让矛盾持续升级,果然造成一连串灾难性后果。欢喜正式上班的第一天,简直可以用鸡飞狗跳来形容。
兢兢业业把闹钟提前半小时,到了公司才发现,大多数人都比她来得更早。
办公室成了乱糟糟的战场,大家都在忙着查漏补缺,因为这是唐舜华回国的日子。坊间传闻,平均每个月都要骂走一名私助的唐总,是个不折不扣的女魔头加工作狂。据说这次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机,凌晨三点才落地虹桥机场,刚打开手机就在内网发邮件,安排今早九点的会议。
林佩数着行程表,满脸的生无可恋:“开完会中午见两个客户,接着在茶园跟面料供应商午餐,然后去工厂看生产线;下午四点之前,和顾总敲定开发主题和产品计划书,六点半到再赶浦东机场的航班飞深圳,当地厂商负责接风,估计得应酬到半夜;明天还要参加产品订货会,路上大概能睡两个多小时……我的天,超人也不过如此了,就差一条红裤衩的距离。”
眼镜小吴从茶水间里出来,讨好地递给林佩一块慕斯蛋糕:“你说女魔头现在也算事业有成,怎么就不抽空谈个恋爱什么的?整天活得像台工作机器,自己变态就算了,还要拉着大伙儿一起变态。”
小王抱拳表示敬谢不敏:“跟她谈恋爱,这谁顶得住啊?哪位英雄如此舍身取义,小的五体投地。”
小吴立即打蛇随棍上:“那是,在Patty面前,什么样女的不得靠边站?”
两人轮着番逗闷子,林佩咯咯笑得枝摇柳颤。
甄真新招的助理庄采采声音甜软,故作天真地睁大眼,说:“真有那么夸张啊,她是不是特别凶?我胆子小,你们别吓唬我。”
林佩把咬了一小口的蛋糕扔进垃圾桶,同情地望住庄采采:“你呀,以后就晓得了。你那位甄大设计,跟大老板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变态双姝。”
小王附和道:“顾总也不好伺候,格么有腔调唻。刚还特意交代,布丁要趁热洒一点柠檬汁,点心匙用贝壳的,说金属有一股子怪味。啧啧……”
小吴琢磨一会儿,想起什么似的:“哎不对,唐总早年离过一次婚来着,有没有孩子就不知道了。我也是听嘉腾那边的客户瞎聊,都说一个女人家,能单枪匹马撑起这么大一家公司,也挺不容易。”
“她的经你可取不了。”林佩掏出镜子,边补粉边说:“一个两手空空的女人,也没见长出来三头六臂啊?谁知道靠什么发达,我就不信背后没点弯弯绕。人家再单枪匹马,脸蛋身材还是在线的,实在不行可以傍上位嘛,你行吗?扔大街上都没人捡。”
小王说:“你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制版部杨叔好像提过一嘴,她跟老顾当年是在法国认识的,貌似还好过一段?反正关系不一般,要不能一手提携她到如今?老顾何许人也,真不是谁想傍就能傍上的。”
为了尽快融入小团体,庄采采自觉有义务互相交换消息。神秘兮兮说:“今天一大早,甄总就气冲冲跑去总裁办公室找唐总来着,两人在里面待了好半天,也不知道商量什么……然后唐总就找顾总去了,一聊又是半个多钟头。那一会儿还开什么会啊?”
小吴拿出前辈的派头,指点江山道:“不懂了吧?一般开这种会,都不是奔着讨论问题去的,就为把人找齐了宣布决定。今天准有大事发生,还不晓得赶上谁遭殃。”
林佩朝欢喜的方向望了一眼,嘴角往下瞥:“我看呐,甄汉子八成是去告那位的御状来着。你是不知道,昨天中午……”
欢喜对他们的办公室政治全无兴趣,奈何要守在饮水机前等水开,听得一阵阵犯恶心。普罗大众对成功女企业家的意淫真是缺乏想象力,来来回回不过那么几种,最后总要往下流的路子上去。
友好的八卦氛围突然中断,所有人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刷刷归位,板着脸噤若寒蝉。
在各种“唐总好”、“ Good morning”的招呼声里,一连串高跟鞋叩击地面的脆响由远及近。
那天欢喜第一次见到唐舜华,脑子蹦出来的就俩字:生猛。
伊年纪怎么也有四十了,然而保养得宜,看起来不过三十出头。身高起码一七二,还穿8.5厘米的Ferragamo。一眼望去,是那种大气雍容的长相,美得极具侵略性。高额头,深栗色卷曲的大波浪挽在肩膀一侧,挑眉丹凤眼,很有点睥睨众生的味道。
林佩适时端上准备好的咖啡,按她的习惯,Double Esprssso,不加奶不加糖也不要肉桂。
唐舜华边喝边看最新的市场调研报告,精致得一丝不苟的妆容,把眼底疲倦的青色遮去。连日昼夜颠倒的奔波,丝毫也没影响她的状态,目光仍旧清醒坚毅。所谓野心全写在脸上,就是这种面相了。
她没发话,林佩就不敢乱动。煎熬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唐舜华抬起头问:“人都到齐了吗?十分钟后准备开会。”
林佩眼睛盯牢地面,老老实实说:“除了连总监,其他都到齐了。”
唐舜华沉默两秒,利索地做了决定:“不用等他。前台的工作让让庄采采先代一下,你跟我一起去会议室——就坐连越那个位置。”
说完起身朝会议室走去。林佩留在原地,嘴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
庄采采凑上前,表情凝重得像遗体告别:“Patty姐,保重。”
比起林佩的面如土色,甄真的云淡风轻更令人惊讶。除了面色略苍白,昨夜的颓唐脆弱早已一扫而空,淡静得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她用内线电话把欢喜叫到办公室,递过一摞提货单,说:“你去取回这几套样衣和鞋,还有海报立板,下午拍摄要用。”又撕下一张便笺纸,“然后去这个地址接七喜,一起带到公司。江知白上午要和跟妆师做最后的造型沟通,没时间去。午休结束前必须全部就位,有没有问题?”
欢喜忙点头,“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甄真看她一眼,淡道:“你是连越的助理,具体工作本不该由我安排。不过今天状况特殊,每个人都忙得抽不开身。连越翘班,采采要代林佩的岗,只能让你去。”
欢喜从善如流,再三保证一定按时完成。
甄真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合上电脑的姿势,就像女刺客在还剑归鞘。
错身而过的瞬间,欢喜匆忙追问:“等一下,谁是七喜?他有没有联系方式?男的女的啊?”
意料之中地没有回答。甄真已经大步生风地朝会议室走去,也不知是没听见还是不想搭理。
欢喜望着她笔直的背影,默默叹一口气。也难怪同事总在背后嚼舌根,甄真和唐舜华确实有某种相似之处。她们长相完全不同,一个清冷一个明艳。唐舜华像一把出鞘的剑,很美然而气势太迫人,满脸的我命由我不由天。甄真不爱化妆,大多数时候穿男装,骨子里却有藏不住的倔强和锋芒。
欢喜振奋地想,将来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像她们那样的行业翘楚。
刚跑出公司,就有陌生号码打进来。接通才发现,竟然是连越。
欢喜把甄真刚交待的事给报备了一遍,说:“我下午两点前肯定回公司。”
“那你去吧。”连越听完,没什么特别反应。顿了顿,又不放心似地补了一句,“别出篓子。”
欢喜想他有这种担忧很正常。要是头天上班就出纰漏,连越面子上肯定也过不去。于是又信誓旦旦地保证了一遍,表示绝对不会给大佬脸上抹黑。
对这种豪情壮志,连越只在电话那边笑了一下,说:“明唐真正的核心设计团队里,全是怪物,每天都有人想辞职。你要学的第一件事,是承认自己的一无所知。”
欢喜面对打击向来迟钝,木讷说:“我承认啊。然后呢?”
“多干活,少八卦。”
“对了你今儿怎么没来啊?唐总上午开会,大家都到齐了。她好像很生气,还让林佩——”
连越简洁明了道:“你别管。”然后挂断。
扛着巨大的海报立板在大街上狂追七喜的时候,欢喜深刻重温了一遍朴素的真理:豪情壮志这种东西,真是消磨容易重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