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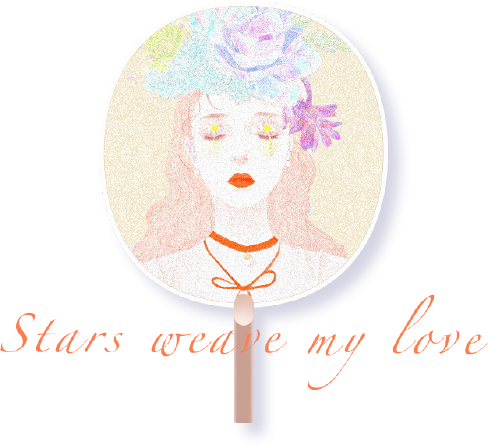
刺目白炽灯下的面孔不断流动,只有沈望被询问的位置不曾变换。口干舌燥,周身泛起阵阵乏力和虚脱。
不停地回答,是,或不是。
当对方问出“你们是什么关系”时,他犹豫了片刻,着实不知该如何回应。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情侣?床伴?还是熟悉的陌生人。他几乎对她一无所知,了解的情况恐怕还没有警察多。但或许有过那么一刻……
“她是我的——”
将要开口的瞬间,父亲委派的律师推门而入,示意他不必再多说半个字。
啊,不能说出的恋人。
从警局拿回的遗物放在透明塑封袋内。钥匙、银行卡,还有一张被海水浸泡模糊的车票。他给她的那张银行卡里余额充足,一分都没动用过。
东京没有直达奈良的新干线,需要先到新大阪间或京都再转乘。她是打算回家乡吗?在那么清冷的雪夜。天那么黑,路又那么远。
如果他当时肯去接她,她会不会改变决定,结果是否不一样。
还有那个尚未成型的孩子……他永远没机会去问,也失去被亲口告知的资格。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措施一直都很注意,他不知道是哪里出了意外。但他不会用任何无谓的揣测来侮辱她,内心十分确定,自己是孩子的父亲。
某种意义上,他是杀死小夜子的共犯和同谋,不必出庭的肇事者之一。
沈望用那把钥匙打开了公寓的门。
月光透过和纸窗,泛起一层幽幽的蓝光。
桌上陶罐里的花束早就干枯。巷口传来野猫凄厉的叫声。冰箱里孤零零放着一盒半额便当,已经腐败变质。室内一景一物都如旧,就像她只是出门去喂了趟猫,很快就会回来。
他没开灯,跽坐在有点返潮的榻榻米上,聆听寂静里血液的轰鸣,直到腿脚发麻失去知觉。站起身时踉跄跌一下,碰倒角落的藤编箱屉。里面掉出来一枚神社御守袋和一支白色录音笔,电量还剩不到三分之一。
大约经常抚摸的缘故,织锦花纹的御守有点旧了,就这么静静躺在苍白安静的掌心。她有何所思,何所愿?拆开来看,是祈愿孩子平安无事的子安地藏。
沈望呼吸一窒,被突然打断肋骨的软弱,藤蔓一样缠上四肢百骸。
还有录音笔。他不记得在她身边看到过这样东西,摆弄了片刻,犹豫着按下“Play”键。
她的声音水一样淌满了房间。即使欢快的语调,听起来也有种莫名伤感,在寂静里尤其温柔。
小夜子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很少与人往来,于是把想说的话都记在这支录音笔里。
原来在便利店初遇的那个晚上,她已经认出他。商学部沈望,很多同校生耳熟能详的风云人物。小夜子也曾远远观望,却从来没尝试过靠近,甚至不敢上前讲一句话。他当然不会记得身边那么多芜杂的注目和像她这般毫不起眼的存在。
那晚他开车载她回家,两人一起喝寡淡的朝日啤酒,吃了焦糖烤布丁,她兴奋得整晚都睡不着,在录音里说:“沈桑真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第一次亲吻她的唇,她那么惊讶,像突然被天使之翼拍了面额。她说:“我不知道我是在接近爱恋,还是失去爱恋?”
排架上都是小夜子平日看的书,听的歌。唱片机里塞着一张很老的唱片,Seven Lonely Days,七个寂寞的日子。他留给她多少暗无天日的寂寞与绝望?沈望发现自己从未尝试了解过她,尽管彼此的身体如此契合而熟悉。
他想起往日做功课累了,她会念《源氏物语》里的和歌俳句给他听:“既非明灯照,又非暗幕张。朦胧春月夜,美景世无双。”【《源氏物语》,紫式部著作,称日本红楼梦。】
古老优美的故事里,胧月夜是右大臣家的贵族小姐,未嫁之时便跟源氏公子有炽烈的爱情。然源氏公子早已跟左大臣家的葵姬定亲,右大臣与左大臣两大家族是敌对势力,让这段爱情充满痛苦和无望。后胧月夜进宫嫁与朱雀帝为妃,很得宠爱,却始终不能忘情。两人私相往来,源氏公子因此被贬黜须磨。
她们都有一样美丽的名字,和哀愁的爱情。
她说:“樱花应该在最美的那刻被风吹下枝头,而不是忍受漫长的枯萎和凋谢。”
她说:“如果可以,我希望一直不要让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因为你从我这里需要的,并不是这个。”
不是喜欢,不是悦纳,她用了这么严重一个词,爱。
如果她哭闹、哀求甚至指责,他都会给她们母子一个妥善的安排。结婚当然是不可能的,但绝也不会太委屈了她。至于小孩是生下来还是放弃,统统都可由她自己定夺。
可她不要让他知道。
天光大亮时,沈望走出公寓,把钥匙塞回脚垫底下。云朵被清凉猛烈的风刮过,蓝得令人眩晕。空彻的蓝,就是一无所有。他抬手挡住眼睛,从指间的缝隙里微漏下一线天光,在这束光里,最后一次想起她的脸。梨瓣一样白得透明的脸容,长发蓄得又直又长,嘴角倔强。
那年的春太凉薄,樱花果然谢得匆匆。
后来沈望回了美国,带走“本缀”丝织技术,无可挑剔的立双博士学位,以及一枚半旧御守。
他从来都清醒、理智并坚强,以后还要一直坚强下去的。至于“爱”这个字,既然在很年轻的时候错过了说出口的机会,大抵再也不会说。
把一切当成不可抵逆的意外,会不会心安理得一点?总之后来的沈望,愈发精于设防,从不暴露软弱、亲密的意志,也不去思考爱或不爱到底怎样。他的人生像一只精密的钟表,可以出现无伤大雅的跳跃音符,万不可荒腔走板乱了节奏。哪怕在底子里留下一道隐秘的裂缝,只要他守口如瓶,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这个猝不及防的夜晚,沈欢喜莽撞而固执地追询,勾起尘封已久的岁月残片。他惘然地对着月色重复这句话:“更可怕的是,它本来是真的,我却没有当真。”
……
心里装着事儿,怎么都睡不踏实,欢喜七点多就醒过来。躺在床上侧耳听了一会儿,套间外面安静异常。
她匆匆套上衣服,把门拉开一小道缝,看见沈望穿戴整齐,坐在沙发里对着笔记本键盘敲字。
厚厚的遮光帘拉得很严,地灯也被关掉,只有电脑屏幕发出柔和的蓝白光,照亮他沉静面容,有极清俊的形与影。单手托在下巴上,另一只手搭在膝头,目光很关注,像是在考虑什么事情。
她打着呵欠走过去,随意地坐在沙发扶手上,“这么早就醒了?”
沈望有点惊讶地抬起头,她这才发现他耳朵上夹着耳麦,里面清清楚楚飘出一个惶恐的男声:“沈总您现在要是不方便……”
原来他在开视频会议。
看清了屏幕,欢喜瞠目结舌地从扶手边摔下来,“咕咚”一声掉在地上,还连带着撞翻了一把椅子。
沈望飞快把电脑合上,俯身过来扶她,“摔没摔着?”
她龇着牙直吸气,“对、对不起啊,我真不是故意——”
他提了下嘴角,无所谓地打断她的道歉:“尴尬是他们。”
他说得对,除了他以外,视频对面的所有人都该很有默契地假装信号突然不好。这叫什么事儿。欢喜淹没在巨大的羞臊里,觉得此处应有乌鸦叫。
沉默中匆匆吃完早饭,半个小时后,他俩已经出现在地址上的那所民宅门口。
这是个很旧的居民楼小区,共六层高,还没加装电梯。楼道里逼仄昏暗,所有灯泡全是破的。
欢喜屏住呼吸,敲响了最里面的那户铁门。
一直没人应。只得继续敲,用力越来越大。她心里有点慌,难道来晚了?沈望安慰她,“别着急,要不就先问问邻居。”
又过了五、六分钟,门后响起熟悉的声音,有点暗涩沙哑:“……谁?”
欢喜浑身的血都往脑子里冲,“是我啊萝卜!你快开门!”
木门突然被拍撞出惊天动地的一声响,“欢喜!真的是你?!你怎么才来啊……”
紧接着是一阵崩溃的嚎啕大哭。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先开门啊,见面再——”
绿萝哭得上气不接下气:“锁死了,我打不开。他们……就快回来了……”
“谁们?谁要回来了?到底是谁把你关起来?!”她额上渗出细密的汗,手脚却冰凉。没头苍蝇似地在原地转了两圈,拎起墙角一只瘸了腿了废旧木凳子就要朝铁门上砸,被沈望眼明手快拦下,取下她手里的凳子掂了掂:“这玩意儿砸不开门。”
欢喜颓然垂下胳膊,复又抓住他的衣袖:“你车里有没有钳子啊扳手什么的,快借我用用。”
他比她冷静得多,“你知道这是谁家,就要大白天的强行破门入户?把周围邻居都吵出来,真的会对绿萝现在的处境有帮助?”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绿萝又拍两下门,抽噎的声音清清楚楚从里面传出:“欢喜你听、听我说,我爸妈就快回来了。他们看过你的照片,千万别让他们撞见……你先走,晚上、晚上十点,我开着窗户等你。别报警啊……说不清的。总之你先离开这儿……”
欢喜明白了,这所房子果然是绿萝在扬州的“家”。
她整颗心都揪得难受,泄气地蹲下来,把脸贴住铁门答应着:“那你先别哭了,乖啊。我晚上一定过来找你,好好等着,别干傻事听见没?”
“走吧。”沈望拉着她的胳膊把人拽起来,见她踟蹰不舍,又劝道:“事情要一样样解决,真和她爸妈撞上,反而节外生枝。”
他的语速慢而笃定,带来镇静的安抚。欢喜抬袖飞快地在脸上擦一把,一言不发起身就走。
沈望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刚出楼道口,却见她突然停住了,猛地转回身,用眼神示意身后,神情有点紧张。
他偏头望一眼,两个人影正从窄巷另一头搭伴儿走过来。衣着很平淡的中年夫妇,两人手里都提着菜篮子,里面装得满满当当。
沈望反应过来,这大概就是宋绿萝的父母。
千躲万躲还是慢一步,真要迎头撞上,画面太美不敢想。巷子那么窄,也就只能勉强容下两人并肩通过,完全找不到能暂避的地方。沈望往那儿一站,从头到脚都扎眼得不得了,明显不是这附近的住户,难免引人注意。
欢喜一点也没把握,真要硬着头皮挤过去,老两口不太可能面对面都认不出她来。
沈望眉心一动,当机立断把她的腰拨到怀里,面对面压到墙上。像是担心她太过惊讶会站不稳似的,还用胳膊从背后托住。一个标准的亲昵姿势,巷子顿时多出一半的空间。他个子高,微微俯身下来正好挡住她的脸。
真是神来一笔,这突如其来的凶猛操作简直令她招架不住。但欢喜能明白他的用意,当下也只能配合。腿还是不住发软,紧张地拽住他身后的衣服,手轻微发抖。
很久以后她都回忆不起来当时脑子里在想什么,只剩下一片空白。依稀记得那天穿了双平底鞋,站直了也只到他肩膀刚过半寸的位置。慌乱中仰起脸,正对上他的眼睛,咫尺的黑色眸子里波澜万千。
沈望呼吸平稳,半敞开的领口散发着微酸却又清新的木质香调,若有若无的广藿气味,如同雷雨过后的大地。她颤一下,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就听见他在耳畔命令道:“把头低下。”
声音极低,带一点沙哑的蛊惑意味,像呢喃。欢喜整个人晕乎乎,赶紧听话地垂着头,感觉到他的下巴抵住前额。方寸之间的皮肤相触,很轻很暖,似被一簇羽毛柔滑拂过。由他这么抱在怀里,几乎算得上耳鬓厮磨。她心跳得咚咚,耳廓变得像烧红的贝壳一样发红发烫。
绿萝爸妈越来越近,侧着身从巷子的另一边过去了,走出两三米远还小声嘀咕:“现在的年轻人呐,大白天的搂搂抱抱也不挑地方……”
他不说话,她就不敢轻举妄动。直到老两口彻底走远了,沈望才描淡写地退开一点,胳膊仍然力道十足地箍在她腰间,发现这女孩表情纠结,皱着眉,一直睁大眼盯住他锁骨的位置,认真得像天桥底下给手机贴膜的,又觉得有点好笑。
“你要是紧张,就不能把眼睛闭上吗?”话出口却有片刻恍惚,仿佛曾在何时何地说过同样的句子。
他终于彻底放开,右手还安抚地拍了拍她僵硬的肩背。欢喜骤然松弛下来,就像在被海草缠在水底窒息的人,好不容易一个猛子冲出水面,立即深吸一大口气。
她稳了稳情绪,待冷静下来,发现自己慌张成这样也是够丢脸。
沈望就好整以暇地站在面前,却看不清脸上的表情,声音像从遥远的天外传来:“不会吧,真吓着了?”
欢喜简直无地自容得要拔脚就跑,生生给忍住,嘴硬道:“没有啊怎么可能,不是正赶在节骨眼上了嘛。这招还挺灵,一般人想不出来。我们江湖儿女不讲究繁文缛节——”
沈望沉默了好一会儿,就那么看着她虚张声势,表现得嚣张又浮夸。欢喜也不知道哪根弦搭错线,竟鬼使神差地冒出一句,“抱就抱了我不会对你负责的,想开点哈。”
还大咧咧掸一下他被揉皱的衣领,“行了咱们先回……”
话没说完就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道迫近,背脊再次重重贴在墙上,砖石冰凉,却渗出细汗。欢喜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再次被同样的姿势牢牢圈住。沈望没碰她,两条胳膊伸直了撑住墙体,漆黑的眼眸里溅出一点危险的火星。
她看一眼沈望,又低头看一眼自己的处境,说:“你这是干嘛?”
他微偏过头,表情带几分消遣的玩味,皱眉道:“我是谁随随便便想抱就可以抱一下,还不用负责的吗?我想不开。”
脑门上有个惊雷轰然炸开。她吸着气说:“那……你想不开,然后呢?”
沈望煞有介事地想了想,又凑近了道:“再来一次?”
欢喜直发懵,完全搞不清这是什么峰回路转的状况,隐约觉得自己摊上事了,急急地解释:“不对啊,不是我想要占你便宜,明明是你先——”
申辩无效,他的手已经作势滑落到腰际,欢喜看呆了,忙一把揪住他胸前的薄毛衣:“我我我错了!我说错话了行吗,冰清玉洁的沈先生你冷静一点……”
光抵住他的上半身显然没什么用。距离这样近,温热的呼吸拂过面颊,他只要稍勾下头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玩笑是不是过火了?昨晚明明还很君子风度的一个人,怎么到了白天就退化得这么厉害。真要当场把他给揍趴下,又仿佛不大合适。再说人家千里迢迢来帮这个忙,万一揍得重了也说不过去,力度实在不好拿捏。
举棋不定间,本能已经作出反应。欢喜只想脱身,立即松开前襟改去抓他的手腕。大概太紧张,手心全汗湿了,一个锁扣还没完成就滑出去,反被他反扣住双腕,飞快地控在头顶。
怎么会这样?!几乎与此同时,沈望跻身而上,两人毫无缝隙地紧贴着,或者说,她受到单方面的压制,被一种绝对的力量禁锢到忘了该怎么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