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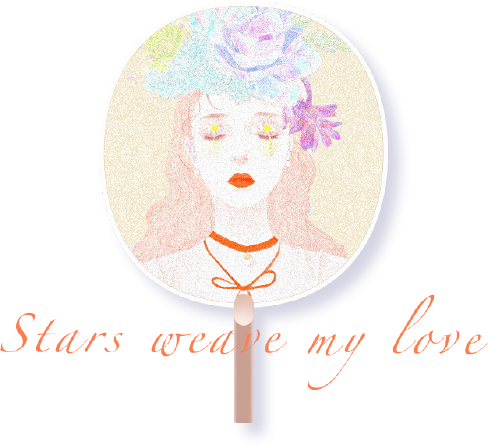
夜很深了。
甄真的回忆带着一种忧愁特有的涟漪,在喧哗雨声里一波一波荡得到处都是。连越也跟着伤感起来,那一瞬间想起了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爱过的所有容颜。
他对风月情事,总有一种异乎敏锐的直觉,于是忍不住把结论说出来。
半晌,她幽幽地应道:“你猜对了,蓝绍纶就是蓝叔……”这个称呼让她顿了顿,转而涩涩地改口,“蓝亚飞的儿子。”
甄、蓝两家除了父辈人情,更是事业上的利益共同体。连带着这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孩子,关系之亲密也非比寻常。
蓝绍纶自幼调皮捣蛋难以管束,但极聪明,成绩不好不坏,每逢大考总有福至心灵的好运气。逃课但凡被甄真堵住,也就笑嘻嘻重新翻墙回来,老实坐进教室里睡大觉。
他个子长得高,初中就进了校篮球队。隔三差五就带不同的小女生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招摇而过,身后有大把热闹的故事和传言,而甄真没有。
隔三差五就有女同学在甄真面前嚼舌根,说你家蓝绍纶又跟谁谁好了,为哪个班花和外校的男生打架了……诸如此类。甄真都会认真地生气和否认,面红耳赤地跟人争辩。
到了高中,时间一下子紧张起来。蓝绍纶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突然收了心,排名一跃千里,很快就与甄真比肩。他的理综成绩比甄真还好些,却总是故意拉着她给自己补习,死皮赖脸地要她手把手解题给他看。两人约好,将来要考同一所大学。
这就相当于某种心照不宣了。
还有很长远的未来可期吧,甄真当时以为。
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很多都会拉着爸爸的手在商场里吃冰激凌,扑到橱窗里设计最粉嫩幼稚的衣服说多好看啊,我要这个。
甄真从不这样。她会皱着眉挑剔那些繁琐的蕾丝和层层叠叠的花边,说丑死了,就像厂里做的那些皮凉鞋和单肩包,俗不可耐。
甄永嘉便宠溺地摸摸女儿的脸,说,等你长大了,给爸爸的厂子设计更好看的鞋子。
有种人,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甄真一直觉得自家厂子做的那些奇形怪状的箱包鞋子又丑又俗气,梦想将来能到一流的设计学院念书,设计真正具有美感也有实用价值的东西。
她对连越说,“我其实一直很向往蓝绍纶那种无拘无束的性子,却知道自己永远也做不到。”
内心深处,甄真是个装在优等生壳子里的坏小孩。她会做符合所有人眼里标准的好女孩,但会对尝试越界的、刺激的、不正确的机会眷恋不已。只有逃离开母亲的眼睛,那些蠢蠢欲动的热望才会结束冬眠。
邱月茹生完孩子后身体一度很不好,辞职在家休养。直到甄真上小学了也没有再工作,一直做全职主妇,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女儿身上。
她年轻时很美,当然后来也不差,开家长会时常常是妈妈们眼里艳羡的对象。甄真一天天长大,一门心思想着挣脱桎梏远走高飞。那么聪明漂亮,青春又朝气的小姑娘,仿佛是从她身上吸取了精力和年华,而她只能留在原地日渐衰老。
枯燥的日子,一眼望不到头是种恐怖,一眼就能望到头,更是种绝望。
时间是每个女人的毒药,会让母女之间也变得微妙。
甄永嘉的新厂刚落成不久,成本还没收回来,忙得脚打后脑勺,连吃饭睡觉也很少在家。邱月茹脾气越来越大,暴躁易怒事事多疑,控制欲极强,夫妻关系一度很紧张。
甄真半夜总被他们的争吵声惊醒,早上起来甄永嘉又去了厂里,客厅沙发上铺着凌乱的被褥。
家里气氛如坠冰窖,甄真渐渐习以为常。一个人洗衣服,一个人做饭,写完作业自己关灯睡觉。邱月茹也开始不回家,从来不说去了哪儿。她不问,只当没看到。
甄永嘉越来越忙,工作的压力让眉头拧得越来越深。除了在匆匆见面的时候给女儿多塞点零花钱,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关注。
街坊邻里都说,这孩子真懂事听话,一点儿也不给大人添麻烦。书又念得好,什么都不用操心。
甄真从那时候起就觉得,“懂事”是个特可笑特悲哀的词。意味着辜负了也没所谓,没成本没负担。哪有人天生懂事呢,不过是种自我保护,不想再受伤罢了。
夫妻俩碰不上面,连架都没得吵。邱月茹的不满无处发泄,怨恨只得转嫁到女儿身上。经常莫名其妙就是一顿没来由的喝骂,“整天板个死人脸,和你爸一模一样!你们父女俩都是没良心的混账!”
甄真看一下表,又看一下,十分钟后说:“你骂完了吗,我上学要迟到了。”
邱月茹更加狂躁,一耳光刮辣地甩在女儿脸上:“你是不是也跟你爸一样看不起我?!挣那仨瓜俩枣的臭钱就了不起了是不是?从生下来那天起你奶奶带过你一天吗,到底是谁辛辛苦苦把你拉扯这么大?我问你,我和你爸要是离婚,你跟谁?”
甄真挨了打也不哭,漠然答:“你们自己的事,离不离自己决定。我马上就成年了,谁也不跟。”
到了学校,蓝绍纶一眼看见她脸上的巴掌印,咬着牙愤愤然:“你妈怎么又打你?”
她把头发拨下来挡住脸颊,摇头说没事。
他一拳狠狠砸在墙上,“她要不是你妈,我真就——”
那个瞬间,她想起小时候为他在老师面前辩诘,说:“蓝绍纶绝对不是故意先动手的!我最了解他!别人不惹他,他是最讲义气的。可谁要是挑衅他,他肯定会以牙还牙!”
如果能懂得人生的莫测,她是不是还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我最了解他”。
真想一直一直,停留在那段时光里。
谁也不知道邱月茹和蓝亚飞究竟是什么时候好上的。这场灾难般的婚外恋,打破了甄真关于未来所有的憧憬。
离高考还有不到三个月,邱月茹在和蓝亚飞躲在库房里幽会,却被下夜班的工人撞破。
然后意外发生了。
命运的齿轮绞紧,一切无可挽回。
他们在匆忙逃离的时候,踢掉了老化的电插头,火星子又把散落的纸板和棉絮点燃,最终酿成火灾。
当时的小型民企,大多沿袭了家庭作坊时期的用人模式,制度还没形成规范。流水线工人大多是从城郊或乡村招来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早早出来打工,相当一部分都还没成年。
这些人有男有女,正是最容易出差错的年龄。管理宿舍的老头为人古板,为了贪图方便,每晚九点刚过就把门落了锁。
三指粗的大铁链子在门上缠满好几层,把挤挤挨挨的宿舍直接变成了烈火地狱。
火势太大,舍管老头喝得太醉,等察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熟睡中的工人被浓烟呛醒,惊慌失措,却无法及时逃脱。铁门被烧得通红发烫,手摸上去能直接烙掉一层皮,根本撼动不了。皮革焚烧发出刺鼻恶臭,有毒的滚滚浓烟能在三分钟内把人呛晕。到处都是绝望的哭喊,倒下的人被后面的人慌乱踩踏,再也没能爬起来。
工人年纪都很小,基本没受过安全常识培训,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
“永嘉皮革厂大火事件”异常惨烈,死伤数量之多令人瞠目,厂子也被烧成了一堆废墟。
这么严重的生产事故,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牵扯出工厂存在的一系列安全隐患。消防设施不合格、大量招募黑工……尤其是宿舍上死锁的不合理制度,往深了追究,甚至涉及非法控制工人人身自由。
厂主甄永嘉,企业唯一法人,不仅要支付巨额赔偿,还有不能逃脱的法律责任,家财散尽后更面临二十年牢狱之灾。甄家一夜破产,债台高筑。
即使过去若许年,这场巨变还是让甄真痛苦如昨。她闭着眼,把头深深垂在胸前,肩膀一起一伏,是不堪重负的姿势。
连越迟疑着,往前伸了伸胳膊,左手刚够着她的指尖。肌肤触压的温热,让甄真如遇电击般猛然张开眼。似从一场噩梦里轰然惊醒,发现自己仍苟活于世上,转而吁一口气。
真遇上过不去的坎,什么否极泰来、绝处逢生……都是虚的。谁能把这辈子活成一句吉祥话?生老病死爱恨别离的苦啊,又有哪一样会缺席呢。唯一能做的,只有死顶硬扛。牙齿咬碎了,肝肠如绞骨头寸断,也要憋住一口气在泥泞里扑腾。
风雨飘摇之下,祸不单行。
邱月茹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抛下看守所里的甄永嘉和即将高考的女儿,跟着情夫一起远走高飞,从此杳无音讯。
蓝亚飞背叛兄弟在前,抛妻弃子在后,绍纶的妈妈薛琴承受不了流言蜚语,在他们私奔半个月后,开煤气自杀。
幸亏被发现得及时,薛琴捡回半条命。精神的坍塌,拖累得身体从此垮了。后遗症让她不良于行,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活动范围是轮椅能去到的最远处。
厂子出了这样的事,蓝亚飞自身难保,干脆把后路彻底断绝。他带着邱月茹消失,或许是早就做好的准备,甚至拿走了最后一点家底。
蓝绍纶的日子一点也不比甄真好过。薛琴受刺激过度,得了郁躁症,发起病来谁都骂,疯了一样砸东西,用刀片割伤自己。两条手臂上全是一道道凌乱的划痕,像竹篾席子。有时候又很安静,拿梳子不停地梳头发,梳不开就用力往下拉扯,头发被扯掉也不觉痛,落得满地都是。或许她需要这样的暴戾,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溺在日复一日的羞辱和绝望里癫狂。
两个家庭毁于一旦,蓝绍纶也等于双失父母,而始作俑者却是甄真的妈妈。
雨势渐小些了,电流仍不稳,走廊里的日光灯噼啪闪动。连越望着甄真,眼里分明起了动荡,语声却是静而沙哑的:“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甄真慢慢眨了眨眼睛,突然就感到一阵软弱。良久,说:“真好听。你能不能,再说一次给我听?”
于是他握住她的手,一字一字认真重复道:“不是你的错。”
长久的默认、隐忍、自抑和承受,她多渴望能重新回到十八岁那年,抱抱当时的自己,说一声“不是你的错”。
然而没可能。她的少年时代在四面楚歌里惨烈而仓促地画上句号,没有任何一个人曾柔声安慰,告诉她这些都不是她的错。
那年甄真刚成年。心是无处安放了的,连带着她整个人,都成了一场罪恶里的余孽、包袱和负担,变得非常多余。
和蓝绍纶的感情无路可走,彼此都陷入巨大的痛苦和矛盾,还有摆在眼前的生存问题。
甄永嘉入狱,面临二十年牢狱生涯,调往内蒙监狱服刑。讽刺的是,判决书和录取通知书同时寄到。他俩都如愿双双考上了上海的大学,甄真学服装设计,蓝绍纶也被有“江南第一学府”之称的复旦录取。
甄真把梦寐以求的录取通知书抱在怀里,整晚都没合眼。心里清清楚楚知道,曾经的约定,或许永不可能实现了。
连越眼神一绞,皱眉道:“浙商做生意,左膀右臂向来是先带宗族里的人。你家那些亲戚呢,一个能站出来管事的都没有吗?就把你撂在这种处境里自生自灭?”
他对甄真和蓝绍纶的苦情戏没多大兴趣,更关心火灾事件如何善后。在生活的苦难面前,什么情情爱爱都太微不足道。
“有啊,怎么没有呢。他们人多势众,生怕站出来晚了,要账要不回来。”
不幸没人关心已是大幸,起码不会被落井下石。甄家树倒猢狲散,且是以这么不光彩的形式。人情冷暖撕开最后一层面纱,直接钝重地砸在脸上。甄永嘉被捕后,亲朋皆避之唯恐不及,哪怕当初受过恩惠提携的,也都翻脸不认,反而拿出许多不辨真假的借条开始“挽回损失”。
甄家的家产全早就被法院查封,还远不够赔偿数额,拖成一笔烂债。两个刚成年的孩子,失去一切经济来源,连家具都几乎被搬空,没有人想过他们要怎么活下去。
犹豫是因为还有选择,只是内心还不愿意接受。面前只摆着一条窄道的时候,反而不会考虑那么多。
蓝绍纶没有更好的打算,走一步看一步。要照顾生活难以自理的薛琴,只能放弃继续读书的机会。甄真也决定不去大学报到,留下来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尽量弥补对蓝家造成的亏欠。
这个想法换来的,是一轮耳光。从小到大,蓝绍纶第一次对她动手。两人大吵一架,他简直气疯了,说尽狠话,要求她滚去上海读书。至于学费和生活费,助学贷款以外的部分,都由他来解决。
他是怎么解决的呢?甄真至今都不知道,不敢细问,问了他也不会说。他们在这么多年的纠葛里,酝酿出一种深刻的默契,其中就包括不追问和回答。
她只记得他来找她那天是处暑,烈焰浓烟的炙夏终于结束了,紧接着是万物渐凋的瑟瑟之秋。
家里出事后,甄真变得更沉默。白天头脑昏沉,只是渴睡,睡过去就能让一切回归静止。纷乱的梦境里,突然听到蓝绍纶在一声声喊她的名字。把意识拉回清醒,才发现他果真在窗外,就像小时候叫她一道去上学那样。
她坐起来,撩开窗帘往下望,灿白的光从地面反照上来,晃得满眼是泪。
正午日头仍很烈,皮肤上粘着一层薄薄的汗。甄真从午睡中惊醒,穿着皱巴巴的棉裙子走下楼,看见他靠在墙角,一只手夹烟,另一只手上拎着个黑色塑料袋。
空气又燥又烫,他却还穿着长衣长裤,运动衫的帽兜拉起来罩住脑袋。走近了,才发现脸上都是伤。鼻梁青肿,嘴角凝固着血痂,连眉骨也磕破了一块。但那还是他,无论变成什么样子她都能从人群里准确地把他找出来。
他正在弄堂角落等着她。时间如何跌宕冲刷,只有他俩的关系是永恒的,不会消失,不被离间。
想到这里,甄真伸手去触摸他红肿溃破的唇角,却被他挥胳膊挡开了。指间的烟灰掉落在她胳膊上,一阵刺烫。
两人都没想好话要怎么说。半晌,甄真低低问:“你又去跟人打架了?”
他却没头没脑地丢一句:“九月开学,你收拾收拾,准备去上海报道。”
甄真说,“我哪儿也不去。”
那个黑色塑料袋就啪地丢在她脚下,蓝绍纶闷声道:“里面的钱你带着,不够的过一阵再说。”
甄真确实惊讶了,第一反应是拒绝:“我不可能要你的钱。我不去。”
话音未落便挨下他一巴掌,接着反手又是一记。
“你他妈当你还在青春期啊?玩叛逆?你凭什么放弃?这件事你根本没资格决定!你没资格!”
她不闪也不躲,站在太阳底下让他打。眼前直发黑,三魂七魄都震荡出去。身体变得不像自己的,被扇得一左一右偏晃。
蓝绍纶打过她的手仿佛有火在烧,又辣又痛,却还不解恨,又狠狠扇了自己几下。之后弯腰捡起袋子,粗暴地塞进她手里,转身掉头走了。
她一直留在原地看他的背影,他却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