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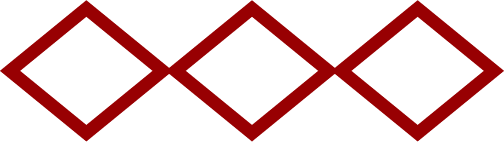
不过两个礼拜工夫,思嘉便从小姐一变而为人妻,但也不过两个月工夫,她便又从人妻一变而为寡妇。她那为人妻的羁绊,是她用着那么大的匆忙和那么少的思想自己套了上去的,现在总算很快就被摆脱了,但她未结婚日子的那种无忧无虑的自由,却是一失而不可复得。在那个时候,寡妇的资格往往紧追着结婚的脚跟而来,原也不足为怪,使她吃惊的是母性也就很快地跟着来了。
那一八六一年四月的末了几天日子,后来思嘉是再也记不十分明白的。时间和事件都像套合在一起,混乱得跟一场非真实亦无理性的梦魇一般。一直到她死的一天,那几天日子都要在她记忆里成为几个省略号。特别模糊的是从她选定了察理到她结婚那一段期间的记忆。只有两个礼拜呢!若在太平日子,这么短的一段订婚期间是万万不可能的,平常从订婚到结婚,总得要一年,方算成个体统,至少也得六个月。但是这时的南方已经遍地战争热,凡事都进行得风驰电掣一般,旧时那种好整以暇的调子已经失去了。郝太太是不住地搓手踌躇,主张缓一步办婚事,以便思嘉可以多一点时间把事情细细考虑。但是思嘉对于母亲的劝告,总是摆着一张悻悻的面孔,装做了充耳不闻。她简直就要结婚!而且要办得快。就在两个礼拜以内办。
后来听见希礼已将预定在秋季的婚期提早到五月一日,以便营里召集时随时可走,于是思嘉就决定比他抢先一日结婚。郝太太提出抗议,可是察理雄辩滔滔地请愿,因为他急于要到南卡罗来纳去加入寒卫德的军队了,而郝老头子也是站在他们两小这边的。他那时已被战争热激动得了不得,又因得着这么一个好女婿,心里正得意,怎么还会阻止他们两小的事呢?于是郝太太一不拗众,终于只得让步了。其实这样的事情当时南方正在到处风行着。他们那个悠闲的世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了,做父母的不管怎样对儿女劝导、祈求、哀告,总之挡不住那一阵势如狂澜的推动力。
整个南方都沉醉在热情和激动中了。人人都知道这回的战争只消一仗就可以结束,因而每个青年都怕战争结束了没有自己的份儿,大家争先恐后地去入伍,而在去入伍之先,又都急急忙忙跟自己的爱人结了婚。单以本区而论,霎时之间就已有几十起这样的战争结婚,而且一结了婚就出发,连从容话别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人人都非常匆忙、非常兴奋,再没有工夫去想这些事情,也再没有工夫淌眼泪了。女子们都在做军服、缝袜子、卷绷带,男人们都在操练、射击。每天都有一列车一列车的军队经过琼斯博罗,向北开到亚特兰大和弗吉尼亚去。有些分队穿着漂亮的军服,有的大红,有的浅蓝,有的交际队所穿的是绿色;有些小队穿着土布的军服,戴着软便的帽子;还有的没有军服,只穿着宽幅绒布的外衣和细麻纱的衬衣。大家都是教练未熟的、武装不齐的,却都发狂似的兴奋着、喊嚷着,仿佛去赴野宴一般。本区的青年们因看见这些军队天天经过,便大大恐慌起来,生怕等不及自己赶到弗吉尼亚,战争便已过去了,于是营里加紧准备出发的工作。
在这纷扰当中,思嘉结婚的事情也在匆匆准备着,只是一霎时工夫,她就已经披着母亲当年结婚的礼服和蒙头纱,倚在父亲肩膀上,从陶乐本宅的宽阔楼梯走下来,面对着满满一屋子的客人了。后来她回忆这时的情景,简直同做梦一般,只记得墙壁上亮着几百支蜡烛,记得她母亲的脸非常可爱,却带点儿惶惑的神情,嘴唇微微地颤动,默默祈祷着女儿的幸福,又记得父亲已给白兰地和满肚子的得意醺得脸绯红,得意的是女儿嫁到这样的好丈夫,钱又多,名誉又好,门第又高——而希礼也在楼梯脚,跟媚兰挽着手臂站在那里。
思嘉看见当时希礼脸上的神情,心里便想:这不能是真实的,决不能的。这是梦魇。我不久就会醒转来,就会发觉这完全是一场梦魇。我现在决不能想,否则就要在这许多人面前喊起来了。我现在不能想。我要过一会儿才想,等我经当得起的时候才想,等我看不见他的眼睛的时候才想。
一切都像在梦中。从她所经过的那些笑容满面的人的夹道,以至于她自己的绯红的脸,嗫嚅的声音,她自己那些虽则非常清晰却是十分冷酷的答话,没有一样不像在梦中。还有以后的道喜、亲吻、酒宴、跳舞——一切一切都像在梦中。甚至于当希礼的嘴亲在她脸上的时候,甚至于当媚兰对她轻轻耳语着“现在我们逼逼真真做了姑嫂了”的时候,也是非真实的。甚至于当察理的矮胖姑妈韩白蝶小姐因快乐过度而昏晕过去,以致引起一阵纷扰的时候,也像是梦魇中的事。
但是等到酒宴跳舞都已完毕了,天也快亮了,所有亚特兰大来的客人都在床上、沙发上、稿荐上、地板上横七竖八地躺下睡着了,所有邻舍家的贺客都已各自回家去休息,以备明日参加十二根橡树的婚礼,于是这种梦一般的昏睡状态就在现实面前像水晶一般粉碎了。那现实便是察理——这时他正从思嘉的更衣室里走出来,身上光穿着一件寝衣,只见思嘉从被头上露出半身,正带着一脸惊惶的神色向他抛来一眼,他便羞得红着脸不敢对她正视。
当然,她也知道结过婚的人是要同床的,但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想过一下。她只觉得自己的母亲跟父亲同床,似乎是极自然的,却从来没有把这观念应用在她自己身上。自从大宴会那天起,直到现在她方才明白自己是怎样的自作自受了。她想到这么一个陌陌生生的男子,自己并非真要跟他结婚的,现在却要来跟自己同床,便不由得不寒而栗,况值自己正在痛悔当初行为的操切,又要痛伤今后希礼的永失,真是万分无可奈何的时候呢!所以当察理踟蹰着将身移近床去的时候,她就用着粗鲁的声音对他低语。
“你如果要近我的身,我就大声喊叫起来。我一定要喊!一定要——放开喉咙喊!你替我走开些吧!我碰也不许你碰!”
因此,韩察理就得在房角里一张圈手椅上过了他的新婚夜,可是他并不怎样懊恼,因为他明白,或者自以为明白,他的新娘子是多么怕羞,多么娇嫩的。他很愿意等着她的恐惧慢慢减退下去,只不过——只不过当他在椅子上辗转反侧着想要找一个舒适坐姿的时候,也不免叹了一口气,因为他不久就要出去打仗了。
她自己的结婚既是这样梦魇一般,希礼的结婚就尤其像是梦魇。那天是她的“二朝”,她穿着一件苹果绿的二朝服,站在十二根橡树的大客厅里,四周也点着几百支蜡烛,也熙攘着头一天晚上的那班客人。她看见韩媚兰当变成了卫媚兰的时候,那一张平淡的小脸蛋上的确焕发出一种美来。到这时候,希礼是永远地失去了。本来是她的希礼,现在不是她的了。但是从前果真是她的吗?她觉得一切都搅不清了,只感到自己的心非常地疲倦,非常地迷惑。他仿佛曾经说过爱她的,但是什么东西将他们隔开的呢?她再也想不起来了。她跟察理结了婚,总算已经杜绝了全区人的谈论,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一个时候,这似乎是很重要的,现在却像并不重要了。有关系的就只希礼一个人,而现在他已失去了;她呢,已经跟一个不但并不爱并且实在很轻视的人结了婚了。
啊,这种种的事情她如今是多么懊悔!她常常听见人说吞了毒药去药老虎的话,总以为不过是一个譬喻,现在她懂得这话的真正意义了。她恨不得立刻摆脱察理的关系,重新去做她的女孩子,但是不可能了,因此她深深尝到自作孽的滋味了。她的母亲曾经屡次极力劝阻她,她总不肯听,这还能怪谁呢?
希礼结婚的晚上,她仿佛在迷雾里似的跳了一晚上的舞,一直是机械地说着话,机械地笑着。她看见人家都只当她是个快乐的新娘子,一点儿没有看出她的心是碎的,便觉得非常诧异,为什么这一班人都会这么蠢?然而,正要谢谢上帝,亏得他们是没有看出呢!
那天夜里,嬷嬷帮她卸了装,走出房去,察理就羞答答地从更衣室里出来,心里正在疑惑,这第二个晚上不知是否也得在那马鬃椅子上过,不想朝她一看,她正在那里哭。这一哭就哭个不住,于是察理不得不爬上床去,伏到她枕边去安慰她,直至她一言不发地哭干了眼泪,这才将头靠在他肩膀上静静地呜咽。
假如是没有战争的话,那就要有一个礼拜的工夫,这里开跳舞会,那里开野宴会,来请他们这一对新婚夫妇,然后再到萨拉托加泉或是白硫泉去作新婚旅行。假如是没有战争的话,那么方家、高家、汤家,一定都要替她大开宴会,而她一定要有三朝、四朝、五朝的新衣服可穿。可是现在,宴会没有了,新婚旅行也没有了。她结婚后一个礼拜,察理就动身到寒卫德上校那里去入伍了,再两个礼拜之后,希礼跟全营的营丁也出发了,全区的人都尝味到黯然销魂的别离情绪了。
在这几个礼拜之内,思嘉没有跟希礼单独见面的机会,自然更没有机会跟他细细晤谈了。就是希礼出发的时候,也不过顺便到陶乐来过一下,并不曾耽搁很久。当时媚兰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俨然是个少奶奶的气度,一直挽住他的臂膀,不曾离身过一步,同时陶乐的全体人员,无论黑的白的,都出来给希礼送行,以致思嘉连跟他话别的机会也没有了。
后来还是媚兰先开口:“你跟思嘉亲一亲嘴啊,希礼。她现在是我的嫂子了。”于是希礼弯着身子,拿冰冷的嘴唇在她面颊上碰了一碰,他的面孔是板着的,绷着的。思嘉对于这一个嘴,觉得一点儿没有乐趣,这是由媚兰怂恿出来的,只给了她一肚子的闷气。及至媚兰自己跟她分别的时候,却给了她一个拥抱,抱得她连气都转不过来。
“你要常到亚特兰大来看看我跟白蝶姑妈,好吗?啊,你来了我们会高兴得什么似的呢!你现在是我的嫂子了,我们得要多亲昵亲昵。”
此后五个礼拜之内,察理常常有信从南卡罗来纳寄来,都写得那么婆婆妈妈的,讲到他的爱,讲到他战后的计划,讲到他要为她的缘故做一个英雄,又讲到他怎样崇拜他的司令寒卫德。谁知到了第七个礼拜时,却由寒上校本人发来一个电报,随后又是一封信,一封措辞非常客气而庄严的信。原来察理病故了。当察理病时,寒上校本来就要打电报来的,可是察理还以为是小病,不肯让他惊动家里人。可怜这不幸的孩子,他怀着那一腔的热爱,既然不过是画饼充饥,而今抱着一肚子立功疆场的希望,也霎时间悉成泡影了。他的足迹不曾越过南卡罗来纳,连北佬儿的营幕也没有见过一眼,便先之以肺炎,继之以痧子,刹那之间就这么无声无息完掉了!
到了相当的时期,察理的遗腹子生下了,这时正有一种风气,男孩子都要照父亲所隶属的司令官取名,因此他这儿子就取名为韩寒卫德。当初思嘉发觉自己怀了孕,心里顿觉非常的绝望,竟至于痛哭起来,恨不得立时便死。但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她却丝毫不感痛苦,不知不觉已经足了月。那天嬷嬷私底下告诉她,说胎气十分平稳,叫她尽管放心。于是孩子终于出世了。她对于这孩子并不觉得喜爱,可是她把这不喜爱的感情竭力掩饰过去。她并不曾要孩子,她很讨厌他来,然而孩子已在眼前了,照她看起来,这似乎决不会是她的孩子,决不会是她自己的分身。
产后她的身体复原得非常之快,不过心理上觉得有些昏迷,有些病态。她的精神一天天颓唐下去,虽然全家人都努力着要鼓起她的兴致来。因此,她母亲是终日的愁眉不展,父亲也烦闷得常常要发脾气。他每次到琼斯博罗去,总要带点好东西回来哄着她开心,像哄小孩子似的,可是一点儿没有效果。方老医生曾经拿含硫黄之类的补剂给她,希望能够把她补养起来,而结果也没有效验,于是连他也觉莫名其妙了。他暗底下告诉郝太太,说思嘉时而暴躁,时而失神,便是一种伤心过度的症候。其实思嘉的症候要比这复杂得多,只是她自己不肯说出口来。至于症结所在,则不外一面因实做了母亲而感觉厌烦,一面因思念希礼而神魂颠倒罢了。
她的厌烦是非常深刻的,无时或息的。自从营里的青年们出去参战以后,区里就什么娱乐、什么交际都没有了。所有有趣味的青年都走了——汤家的四个,高家的两个,还有方家的、孟家的,乃至琼斯博罗、费耶特维尔、洛夫乔伊所有中意点儿的青年人都走了。留下来的尽是些老人、妇女和残疾者。而这些人又一天到晚在那里替军队编织,缝纫,种棉,种稻,养猪,养羊,养牛。真正的男子是一个也看不见了,就只有苏纶那个中年情人甘扶澜所带的差委队,每月要到这里来采办一次军需品。那个差委队里的男子也并不怎么使人兴奋,至于甘扶澜那种婆婆妈妈式的追求,思嘉一看见就要生气,几乎连礼貌都不能维持。她只恨不得他跟苏纶早些儿有个解决。
即使那差委队里的人们比较有趣味,对于她也实在无济于事。她是一个寡妇了,她的心是在坟墓里,至少人人都要当她的心是在坟墓里,而且期望她专心一致在坟墓里的。她虽然尝试照着人家所期望的做,却觉得非常懊恼,因为她对于察理是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就只记得当初自己对他表示愿意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脸上那副死牛一般的神气。而且就是那一个记忆也渐渐地淡了。不过她毕竟是一个寡妇,行为上不能不时时检点。未结婚女子的快乐于她是没有份儿了。她必须端庄而贞洁。有一次甘扶澜队里的一个副官陪她在花园里打秋千,把秋千架拼命地荡着,使她笑得鸡猫子似的喊叫起来,这事被她母亲看见了,将她大大训斥了一顿。她母亲告诉她,一个做寡妇的人最容易招人议论,所以凡行为都非加倍地谨慎不可。
“天才晓得呢,”思嘉一面谨听着母亲温和的训诲,一面想,“做了少奶奶,已经一点儿没有意味了,那么做了寡妇简直是等于死了。”
原来南方的风俗,做寡妇的都要穿可怕的全黑衣服,连镶绲都不能有,不能插花、挂飘带、镶花边、佩首饰,所能佩的只有条纹玛瑙的丧服胸针,或是拿死者头发做成的项圈罢了。而且那从帽子上垂挂下的黑绉纱面罩,必须要挂到膝盖,必须等做了三年寡妇才可以缩短到平肩。又,凡做寡妇的都决不能兴高采烈地谈,嘻嘻哈哈地笑。就是微笑,也必须是一种伤心的惨笑。尤其可怕的,就是她们跟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决不能露出一点有兴趣的意思来。如果男人方面有缺教养的,竟对一个寡妇表示有兴趣的意思,那么她就必须对他装起一副尊严的面容,并且设法谈到亡夫身上去,以便使那人听了寒心。然而有些寡妇到老还是要改嫁的,这就使思嘉莫名其妙了。她想一个寡妇被人这么众目睽睽地监视着,又怎么能办到改嫁的呢?何况她们所嫁的人,又多半是有田地有儿女的年老鳏夫呢?
结婚已经是不幸透了的事,至于做寡妇——啊,那么一生一世就算完结了?然而人家还都在谈论,说察理死了,幸而留下一个小寒卫德,对她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啊!思嘉却以为这一班人都是大傻瓜。其实她对于卫德是一点儿不感兴趣的,有时她竟完全忘记了他是自己的儿子。
每天早晨她从梦中乍醒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个似梦非梦的顷刻。在那顷刻之中,她觉得自己仍旧是郝思嘉小姐,窗前的山茱萸仍旧浴着灿烂的阳光。反舌鸟儿仍旧在那里歌唱,仍旧有那一阵阵的熏肉香气不断飘进她鼻孔里来。在这当儿,她又无忧无虑了,又年轻了。然后,她会突然听到一种啼饥的哭声,因而不由得吃了一惊,心想:“怎么,屋子里有一个小孩子吗?”然后她记起来了,记起这就是她自己的孩子。就像这样,她觉得一切都在迷离惝怳中。
然后就是希礼!是的,希礼是她想得最多的!一想到了他,她就憎恨起陶乐来了,她憎恨那条从山上通到河边的路,憎恨那些密密栽着棉花的红土田。每一英尺土,每一株树,每一条小溪,每一条狭弄,每一条马路,都要使她想起希礼来。他现在是属于别的女人了,并且出去打仗了,但是他的鬼魂仍旧要在苍茫暮色之中出没在这些道路上,仍旧要在那走廊底下用着那一双瞌睡兮兮的眼睛对她微笑。她每次听到十二根橡树那边的溪沿上有马蹄声响,就无有不悠然神往地想到他——希礼的!
十二根橡树是她从前很爱的,现在她也恨了。但虽然恨,却又舍不得不去,去了可以听到卫约翰跟女孩子们谈希礼的事情,听到他们读他从弗吉尼亚寄来的信。她听了不免要伤心,却又不能不听。她不喜欢那个硬颈梗的英弟,不喜欢那个一张嘴唠叨不息的蜜儿,又知道她们也同样地不喜欢自己,可是不知怎么的,她总觉离不开她们。而每次从十二根橡树回家,她总要发脾气,躺在床上,连晚饭也不肯起来吃。
就因她不肯吃饭,爱兰跟嬷嬷越发着急起来。嬷嬷总把托盘拿上去,曲意殷勤地劝她,说现在她做了寡妇,可以尽她的量吃了,可是思嘉一点儿不想吃。
方医生郑重地告诉爱兰,说伤心之症往往要一点点衰耗下去,终至于无可救药。爱兰听见这话,就吓得面孔雪白,因为她也早就担心这一层。
“难道一点儿没有办法了吗,先生?”
“最好的办法是换一换环境。”方医生说,因为他也巴不得早些摆脱这个棘手的病人。
于是思嘉勉强带着孩子到各处去跑起来,先是到萨凡纳,去看郝家、罗家的本家亲戚,然后到查尔斯顿,去看两个姨妈,宝玲和幽籁。可是她比预定的日期早一个月就回来了,也不说明所以早回的缘故。在萨凡纳的时候,两位伯伯、伯娘待她都很好,可是他们年纪都老了,一直喜欢静坐在家里谈过去的事情,思嘉觉得一点儿没有兴趣。罗家那些人也是这样。而且思嘉觉得查尔斯顿那个地方简直也是可怕的。
在宝玲姨妈家,姨爹是个小老头子,外面装得很客气,一直是那么没精打采的。他家住在沿河一块垦植场上,比起陶乐要僻静得多,就是最近的邻家也离开二十英里地,而且相隔着一片柏树、橡树夹杂的丛林。那些橡树都是枝叶参天、爬满苍苔的,思嘉一看见它们,就要长出一身的鸡皮疙瘩,立刻会想起父亲平日讲的那些爱尔兰森林的鬼故事来。她在那里,白天就唯有编织,晚上就唯有听姨爹念书。
幽籁姨妈深深隐藏在查尔斯顿僻静处的一座大房子里,生活也过得非常乏味。思嘉是看惯了绵延不断的起伏地面的,觉得这里简直是坐监牢了。她家的交际比宝玲姨妈稍为广一点,但是思嘉很不欢喜她家的那些来客,看不惯他们的态度、习俗以及专讲门第的风气。他们都知道思嘉的母亲是罗家的小姐,可不知为什么嫁给一个没来没历的爱尔兰人,因而把思嘉看做一个堕落女人的孩子。这种态度,不免在辞色之间流露出来,思嘉自己时时感觉到。而她那位姨妈,偏又要在背地里替她掩饰,这就使思嘉发起脾气来,因为她跟自己的父亲一样,再也不管他妈的门第不门第。而且她不但不看轻父亲,反觉父亲那么赤手空拳地挣起一份家业,正是大大地足以自豪呢。
查尔斯顿人一直都把嵩塔儿要塞的事情讲得津津乐道,认为这是他们发难的首功,殊不知这事他们不干,别人也照样会干的!还有他们那种拖长的语音,思嘉也很听不惯——她是听惯了佐治亚州高地的干脆语音的。有一天她跟姨妈出去拜客,觉得那种呢呀嗯呀的调子实在太不耐烦了,便故意学起父亲的爱尔兰土腔来,把个姨妈直羞得面红耳赤。于是她回到陶乐来了。她情愿回家来痛念希礼,也不愿再在那里听查尔斯顿人的口音。
爱兰见女儿从查尔斯顿回来,反而瘦了、白了,口音也变了,不由得大吃一惊。这种伤心的症候是她自己也尝到过的,因而她每夜在嘉乐枕头边嘟囔,要他想个法儿减少女儿的愁恼。刚巧察理的姑妈韩白蝶小姐写过几次信来,要她让思嘉到亚特兰大去多住几日,现在她见女儿这样,就把这事认真考虑起来。
白蝶小姐信里说,现在只有她跟媚兰两个人住着一所大房子,“察理死了,家里没有一个男人保护。当然,还有我的哥哥亨利在这里,但是他不跟我们住在一起的。而且,关于亨利的事情,思嘉也许跟你说过了,我信里不便多写。如果思嘉跟我们在一起,媚兰同我会觉得适意得多,放心得多。三个孤单的女人总比两个多了一个了。媚兰现在医院里看护伤兵,思嘉来了也照她这么做,或许可以减轻她心里的愁恼。还有,媚兰跟我都急于要看看那个乖乖娃子……”
于是思嘉的行箧里边重新装满了她的居丧衣服,便带着寒卫德跟他的奶妈百利子到亚特兰大去了。此外带去的就是爱兰跟嬷嬷给她的一脑袋关于她的行为的训诫,以及嘉乐给她的一百元联盟州的纸币。她这一去,实在是并不怎么出于心愿的。她觉得那个白蝶姑妈是个再蠢不过的老太婆,而且想起了去跟希礼的妻子同室而居,也使她不寒而栗。但是她在家里,随时随地都要触起前情,简直无法再住下去了,所以无论怎样,换一换环境总是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