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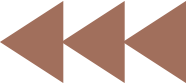
法国语言学家泰尼埃尔在1959年最先提出配价语法(见其著作《结构句法基础》),他认为:句子的结构表现为各个构成成分之间一层层递进的从属关系,顺着这种从属关系向上推演,句子的结构顶端就成为一个支配所有成分的“中心结”。这个“中心结”大多由动词充当,所以动词是句子的中心。研究配价语法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动词对名词性成分的支配能力。
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这一阶段主要是对国外配价理论的介绍,以及对配价理论进行的基础性研究。
最早将配价语法理论引入中国的是朱德熙先生,他在1978年发表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提出了“单向动词”“双向动词”“三向动词”的定义,认为“只能跟一个名词性成分发生关系的动词叫单向动词”“能够跟两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的动词叫双向动词”“能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的动词叫三向动词”,并用配价语法的观点分析动词性成分加“的”构成的“的”字结构的歧义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的”字结构所组成的判断句。
此外,冯志伟《特斯尼耶尔的从属关系语法》(1983)、张烈才《特斯尼埃的〈结构句法基础〉简介》(1985)、方德义《法国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概况》(1986)、《德语配价理论的发展及成就》(1987)等都对国外配价语法进行了介绍和评价。
在这一阶段,学者开始尝试运用配价语法理论对语言事实进行研究,如文炼(1982)在《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一文中讨论了动词的“向”和动词跟名词性成分之间的搭配关系,并指出跟动词发生联系的名词性成分有两种:一种是强制性的,如果在没有语境的帮助下,一定要在句中出现;一种是非强制性的,根据表达的需要,在句中出现或不出现。廖秋忠在《现代汉语中动词的支配成分的省略》(1984)一文中从配价的角度分析了动词的支配成分的省略问题。吴为章在《“×得”及其句型——兼谈动词的向》(1987)一文中从配价的角度讨论了由“×得”构成的句子的语义关系问题,认为能同动词发生主谓或述宾句法关系的除了名词还有动词性成分,因此决定动词“向”的因素不限于名词性成分。决定动词“向”的必要成分有两项限制:①位置的限制,必有成分是能够出现在主语或宾语位置上、跟动词发生显性的主谓或者述宾关系的成分;②意义的限制,只有表示施事、与事、客体等及物性关系的从属成分才能决定动词的“向”,而工具、方位等状语性的成分不参与决定动词的“向”。袁毓林在《准双向动词研究》(1987)一文中讨论了“辩论、握手”等其中一个配价成分必须由介词引导的双向动词,描写了由这类动词构成的各种句式的变换关系,构拟了这些句式由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换和生成的过程。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汉语配价语法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文炼、袁杰在《谈谈动词的“向”》(1990)中认为汉语跟其他语言一样,动词的从属成分也可以是动词性成分,并运用赫尔比希的方法,将跟动词关联的从属成分分为必有行动元、可有行动元、自由行动元三种。范晓在《动词的“价”分类》(1991)中提出了形式上确定动词价的四种方法,认为动词的“价”是根据动词在一个动核结构中所联系的强制性语义成分的数目决定的,并据此对动词进行了分类。吴为章在《动词的“向”札记》(1993)中对价所属的语法范畴的性质、如何确定“向”、语言学引进“向”的目的等理论进行了讨论。沈阳在《动词的句位和句位变体结构中的空语类》(1994)中用形式语法的方法构造动词的句位系统,通过三条原则来确定动词的“价”。沈阳、郑定欧主编的《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1995)收录了12篇配价语法的专题论文,并对以下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①配价的性质。②确定配价的原则和方法。③对动词进行价分类并研究动词短语的配价。④结合汉语研究的事实提出了动词的配价成分不限于名词性成分。袁毓林的《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1998)是我国较早的有关配价理论的专著。一方面,他提出并建立了配价层级的思想和理论,认为应该把“价”理解为包含“联”“项”“位”“元”四个层面的有层次的系统。这种配价层级思想和理论能充分地反映动词的各种组配能力,能更好地说明一个动词能构成各种不同句式的原因以及各种不同句式之间的转换关系和制约条件。另一方面,用配价层级的思想和理论具体描写了现代汉语中1 640个左右的动词的配价、配位情况。这对编写现代汉语的配价词典,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第三阶段是21世纪初,配价语法的研究从现代汉语延伸到了古代汉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殷国光的《〈庄子〉动词配价研究》(2009)一书,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方面:①研究了《庄子》里以动词为核心的句式,并确立了22个基本句式。②概括了《庄子》一书中由基本句式派生为派生句式的四种手段。③总结出一价、二价、三价动词各自的语义角色的句法配位规则,并进一步概括出五条各类动词语义角色的句法总配位规则。
近年来,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开始运用配价语法对古汉语中的动词进行研究,如张瑞芳《〈易经〉动词配价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皮佳佳《〈墨子〉动词配价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弋丹阳《〈左传〉单音节谓语动词的配价结构浅析》(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张婵娟《〈孟子〉动词配价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侯雅丽《〈荀子〉动词配价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李玲玲《〈史记〉交互动词配价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赵冬梅《〈晏子春秋〉单音节动词配价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罗静《〈论语〉动词配价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等。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配价是一种语义范畴
廖秋忠(1984)认为支配成分主要是语义即认知上的概念。支配成分的从缺,是句中某些语义成分的从缺,不是句法成分的从缺。
文炼、袁杰(1990)认为动词具有“向”是动词在各种场合具体运行时所有的一种语义功能,所以语言学家都是从动词活动范围之内归纳出“向”的。
范晓(1991)认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分以及体宾动词和谓宾动词的区分等等,属于句法层面,动词的“价”分类,则属于语义层面。句子的语义平面包括两部分,一是动核结构(或称述谓结构),一是语态。而动核结构是一种语义结构,也就是一种深层结构,它是构成表层句子的基础。
周国光、张国宪(1993)认为配价属于语义范畴,词汇意义是决定配价的基础。
(二)配价是一种语法范畴
袁毓林(1993)认为“向”的基础是动词在句法结构中和名词性成分的组合功能的潜势,因而“向”是建立在句法基础上的语法范畴,是动词的组合功能的数量表征,但是,应当承认,动词的“向”是有相当的语义基础的。但是,动词的这些语义要求(涉及的个体数目)一定要在句法结构中得到实现,才能计入“向”的指数,所以作为句法概念的“向”和作为语义概念的动作所涉及的个体的数量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
(三)配价是一种“句法—语义”范畴
吴为章(1993)认为“逻辑—语义”的“向”是认知上的概念,不和语义相联系的纯形式的句法“向”是不存在的。任何句法“向”都是“形式—意义”的结合体,它是“逻辑—语义”的“向”在具体语言结构中的实现,是因语言而异的,是有确定的数量的,是有序的。语法学引入“向”的目的既然主要是说明动词的支配功能以及句法和语义之间的复杂关系,那么它对“向”的解释,就应当是“句法—语义”的。因此,可以把语法平面的“向”理解为“句法—语义向”。
邵敬敏(1996)认为应该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价”:“语义价”和“句法价”,为了使两者有明显的区别,将前者属于语义平面的关系叫作“语义价”,把后者属于句法平面的关系称为“句法向”。“句法向”是以“语义价”为基础的,但是它必须符合“同现”原则,即在一个句法结构中最多可以同时出现几个“语义格”。“句法向”不等于“语义价”,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语义问题,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是必须受到句法结构的制约,即表现为一种现实性。
陈昌来(2002)认为配价是语义平面上的语法范畴,配价是语义的,但这里的“语义”是指跟句法相关的语义。动词所支配的必有语义成分的数量决定了动词的价数和价类,语义功能是配价的基础,但给动词定价的标准是句法上的,动词在最简单的抽象句中所能带的句法成分的数量决定了动词的价类。
殷国光(2009)赞同邵敬敏的观点,认为配价涉及语义、句法两个层面。所谓“语义价”是指在语义层面上一个动词在以该动词为核心的语义结构中所能支配的、不同类型的语义角色。所谓“句法向”是指在句法层面上一个动词在以该动词为述谓中心词的基本句式中,不借助介词所能关联的、处在主宾语位置上的、不同类型的语义角色。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第三种观点,即认为配价是一种“句法—语义”范畴。
(一)关于提取价的句法框架
袁毓林(1987)认为,应当在动词出现的所有句法结构中,选取与之同现的名词最多的结构,在这个句法结构中提取向的指数。即“向”是动词在所有句法结构中与之同现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的最大值,且这些名词性成分与动词的联系具有句法强制性。
吴为章(1993)认为,决定汉语动词之间的“向”的因素是在一个简单句中与动词同现的必有成分。其中的必有成分在位置和意义上有着严格的限制:必有成分是能够在句子中占据主语、宾语位置并跟动词有显性的语法关系的成分,它们跟动词有显性的语义关系。
殷国光(2009)认为,语义层面的基本结构是动核结构,它以动词为核心,由动词和它所联系着的语义成分(语义角色)组成。动词所联系的语义成分主要有支配成分和说明成分两种。在动核结构中,支配成分直接参与动词的行为,并受动词的支配;说明成分则说明动作发生的背景,不受动词的支配。支配成分和动词所共同构成的最小的、意义自足的动核结构是提取“语义价”指数的框架。
关于提取价的句法框架问题,我们同意袁毓林(2010)的观点,即认为在原子句中提取动词的价。所谓原子句,是简单的基础句,所谓“价”是指一个动词在简单的基础句中所能关联的名词性成分的数量。
(二)由介词引导的名词性成分能否计入价的指数
关于有介词引导的名词性成分能否计作动词的一个价,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
朱景松(1992)认为,确定动词的价,首先要分清动词跟名词性成分在语义上和语法上两类不同的联系;分清动词在语法上联系若干名词性成分的功能(可能的)和在具体用例中实际出现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现实的)。动词的“价”应该指形式上能跟这个动词直接组合(不必借助介词)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能够确定一个动词“价”的名词性成分,是指以这个动词为中心的述宾结构的直接宾语或间接宾语,以及出现在这个动词之前的大主语或小主语。
吴为章(1993)根据其必有成分的位置限制,把由介词引导的在结构上必不可少的成分排除在必有成分之外,认为其不能看作动词的一个价,其理由是介词的宾语是受介词直接支配的。事实上,介词是表示动词和名词之间的句法、语义关系的一种标志;介词宾语固然是受介词支配的直接成分,但整个介宾词组在结构和意义上又是从属于动词的。
袁毓林(1987)认为,应该将结构和意义上不可或缺的,但又一定要用介词引导的名词性成分也算作“价”,但将其称为准价以区别于那些不用介词引导的必有成分。
殷国光(2009)和袁毓林的看法相同,并举了“麋与鹿交”一例,认为在动词“交(雌雄交合义)”所激活的语义场景中,必须有交合的双方,缺一不可,因此,与“交”联系的两个语义成分都是支配角色,“交”是二价动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基本的观点是,一般的动词配价成分是不需要介词来引导的,因此有介词引导的名词性成分一般不能计作动词的一个价。但是对于有些动词,其动词的配价成分一般要由介词来引导,对于这类动词,有介词引导的名词性成分就要计作动词的一个价,如互向动词就是这样。对于这类动词,我们同意使用准价的术语。
(三)确定配价的方法
文炼、袁杰(1990)认为动词的必有成分和可有成分决定动词的“向”,主张借用赫尔比希等人的省略法(即消元测试)来确定汉语中动词的必有成分。
范晓(1991)提出了四种从形式上给动词定价的方法:①按照动词在主谓结构中所联系的强制性的句法成分的数目来定价,而强制性的句法成分指构成一个最小的意义自足的主谓结构所不可缺少的成分(动元);②按照动词在最小的意义自足的主谓结构中所联系的名词性成分的数目来定价,这种方法对“觉得(别扭)、打算(辞职)”等谓宾动词不适用;③借助动元的标记(介词)定价,如“被、叫、让、由、归、使”等介词常用于引出施事,“把、对、管”等介词常用于引出受事,“跟、与、给、为、向”等介词常用于引出与事;④利用提问形式定价,大多数动词联系的动元可用“谁”或“什么”代替和提问,因此可以用“谁/什么+V”“V+谁/什么”等形式提问,出现在“谁”“什么”位置上的都是动元。
张国宪(1994)认为,汉语配价是由必有补足语和可有补足语共同决定的,借助德国语言学家提出的消元法来确定汉语动词或形容词的必有补足语。所谓消元法,就是删去某一句子成分,看留下的句子结构是否符合语法;如果符合语法,那么删去的成分是可有补足语和自由说明语;如果不符合语法,那么删去的成分是必有补足语。
周国光(1995)认为,理想的确定谓词配价的方法,应该是以语义分析为基础,而又有形式上的可操作性。
殷国光(2009)认为,现代汉语可以采用内省的方式来确定动词的配价结构,并采用演绎的方法来推演出动词所能构成的句式;古代汉语则只能采用归纳的方法,从语料中已经实现的句式来确定动词的配价结构,并用它来解释动词已经实现的句式分布。
关于如何确定动词的配价,我们同意袁毓林(2010)的观点,即认为在原子句中来确定。这里要说明的是袁毓林用的术语是“元”,但他所说的“元”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价”,下文径称为“价”。
袁毓林认为,原子句就是简单的基础句。它在结构上是简单的,在意义上表示基本的命题。一个原子句有一个表述者和至少一个参与者。参与者属于名词的句法类,而表述者属于动词或形容词的句法类。原子句跟派生句有不同:①原子句中只有一个动词;②原子句中没有and、or、but或其他有连接平行成分作用的词;③原子句中的参与者和谓词都只能有最低限度的限定;④原子句中不含有否定、语气、命令、疑问等二级算子。总之,原子句就是一种语言里面最简单的直陈的表述结构。
袁毓林认为,结合汉语句子结构的实际情况,可以用包孕测试、自指测试、删除测试从形式上规定汉语的原子句。所谓包孕测试,就是让待测试的句子作宾语。因为只有基础句才可以作小句的宾语,派生句是不大能作小句的宾语的。所谓自指测试,就是在句子的后面加上“……的时候/地方/原因/消息/提议/事实”等,把句子转换成一个表示自指的偏正结构。所谓删除测试,是指把基础句中不影响句子结构合格性的介词结构删去,直到剩下不能删除的成分。由于有了原子句的概念和一套规定原子句的测试方法,因此不仅能从形式上确定动词价的数值(价数),还可以从形式上确定到底由什么语义格来实现动词的“价”(价质)。
我们使用袁毓林的方法确定动词的“价”。
本书对于动词的分类,采用的是按照其配价不同进行分类的方法。
我们基本上采取了陈昌来(2002)对于动词的分类,只是在陈昌来(2002)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了几点修改。
陈昌来(2002)对于动词的分类是:
一价动词:一价动作动词;一价性状动词;一价心理动词。
二价动词:二价动作动词;二价致使动词;二价心理动词;二价性状动词;二价关系动词。
三价动词:三价动作动词;致使类三价动词;互向类三价动词;三价性状动词。
对于陈昌来(2002)的观点,我们作以下几点修改:
(1)由于我们不把形容词归入动词,所以把性状动词都修改为状态动词。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形容词应该独立为一个词类,不把形容词归入动词。形容词无论从其概括意义来说,还是从其语法特征来看,都有其独特性,单独列为一个词类是有道理的。状态动词这个术语,学术界以往有不少人用,不是生造的词。
(2)致使类三价动词这个术语与二价致使动词不一致,我们改为三价致使动词,以求统一。
(3)互向类三价动词独立为一类,与三价动作动词、三价状态动词等并列,也不合适。在二价动词中也有互向动词,陈昌来(2002)把它分为两类,一类归入二价动作动词,另一类归入二价状态动词,并没有列为一个独立的类而与二价动作动词、二价状态动词等并列。既然如此,三价互向动词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方法进行处理,不独立列为一类,而是把它分为两类,一类归入三价动作动词,一类归入三价状态动词。
(4)从上古汉语的实际来看,是存在三价心理动词的,如“闻”。所以还应该有三价心理动词这一类。
(5)陈昌来(2002)把含有“使令”义的动词分析为三价致使动词。以“典、田典令黔首皆智(知)之”(龙岗150)为例,“令”的三个配价成分是:致事“典、田典”、使事“黔首”、补事“皆智(知)之”。陈昌来(2002)并未取消兼语句,他指出,“喜欢”类、“称呼”类、“有无”类的所谓兼语句就不是致使动词句。含有“使令”义的动词所构成的句式,过去一般分析为兼语句。例如“典、田典令黔首皆智(知)之”(龙岗150)一句,把其中的“黔首”分析为前一个动词“令”的宾语,又分析为后一个动词语“皆智(知)之”的主语,这样“黔首”兼有宾语和主语的双重身份。如果这样分析,则这种含有“使令”义的动词应为二价动词。本书仍从传统的说法,把含有“使令”义的动词所构成的句式分析为兼语句。
根据上述五点修改,本书从配价角度对动词进行的分类如下:
一价动词:一价动作动词;一价状态动词;一价心理动词。
二价动词:二价动作动词;二价状态动词;二价致使动词;二价心理动词;二价关系动词。
三价动词:三价动作动词;三价状态动词;三价致使动词;三价心理动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