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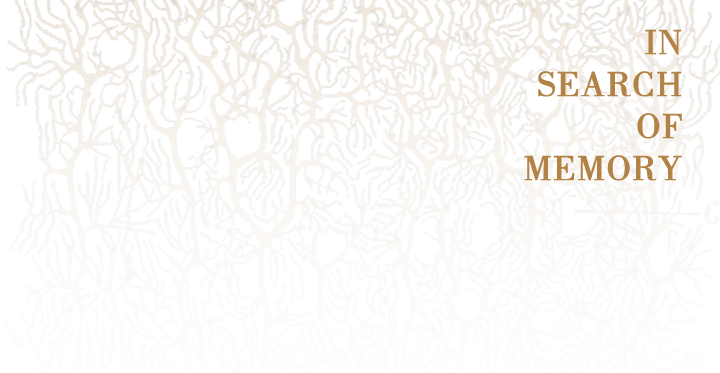
 4
4

1955年秋季,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格伦德费斯特的实验室,开始为期6个月的选修课,希望从中学到一些有关大脑高级功能的知识。我并不期待开始一项新事业或者开启一段新生活。但与格伦德费斯特的首次谈话给了我反思的机会。在那次谈话中,我描述了自己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并表示希望学习关于自我、本我与超我可能位于脑中何处的知识。
点燃我要找出这三个心理主体的欲望的,是弗洛伊德一部著作中的一幅图,他这本著作总结了自己在1923—1933年间发展出的关于心智的全新结构性理论(图4-1)。这个新理论延续了他早前对于意识和无意识心理功能所做的区分,但添加了三个相互作用的心理主体:自我、本我与超我。弗洛伊德将意识视为这个心理装置的表面。他认为我们的很多心理功能位于表面之下,就像一座冰山的大部分都浸在海水里一样。一种心理功能在表面之下所处的位置越深,它就越难以进入意识层面。精神分析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用来挖掘埋藏在心理深处的前意识与无意识人格成分。

图4-1 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 弗洛伊德构建了三个主要的心理结构——自我(ego)、本我(id)与超我(super-ego)。自我包括一个接收感觉信息并与外部世界进行直接联系的意识成分(又称知觉性意识,缩写为pcpt.-cs.),以及一个在无意识过程中已经准备好进入意识层面的前意识(preconscious)成分。自我的无意识(unconscious)成分通过压抑(repression)及其他防御机制来抑制本我(性本能和攻击本能的制造者)的本能冲动。自我还对超我(道德价值观的主要无意识载体)的压力做出反应。虚线将可进入意识层面的部分和完全无意识的部分进行了划分。(出自《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3])
这三个相互作用的心理主体给弗洛伊德的新模型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弗洛伊德没有将自我、本我与超我定义为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而是在认知风格、目的和功能上对它们进行了区分。
根据弗洛伊德的结构理论,自我是负责执行的主体,它既包括一个意识成分也包括一个无意识成分。意识成分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觉器官与外部世界进行直接联系,它涉及知觉、推理、计划行动、体验快乐与痛苦。在哈特曼、克里斯和鲁文斯坦的文章中,他们强调自我的这个无冲突成分是通过逻辑来运转的,并且以现实原则来指导行动。自我的无意识成分涉及心理防御机制(压抑、否认、升华),这些机制通过自我来抑制、引导和改变第二个心理主体本我的性本能和攻击本能内驱力。
本我是完全无意识的,这个术语是弗洛伊德从弗里德里希·尼采那里借来的。它不受逻辑或现实的支配,而是遵循享乐原则,寻求快乐、避免痛苦。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本我代表了婴儿的原始心智,也是人们唯一在出生时就具有的心理结构。第三个管制者超我,是无意识的道德主体,也是我们理想的化身。
虽然弗洛伊德并没有将他的图解视作一幅心智的神经解剖图谱,它却激发我想去弄清楚这些心理主体可能存在于人脑精致褶皱中的什么地方,正如它之前激发过库比和奥斯托的好奇心那样。我之前提到过,是这两位对生物学有着强烈兴趣的精神分析学家鼓励我跟从格伦德费斯特进行研究。
格伦德费斯特耐心地听完了我那颇为浮夸的想法。要是换一个生物学家,恐怕已经把我赶走了,心想面对这么一位头脑简单误入歧途的医学生该如何是好。但格伦德费斯特没有那样做。他解释道,我想理解弗洛伊德的心智结构理论的生物学基础这一愿望远远超出了目前脑科学的能力。他转而告诉我,为了理解心智,我们需要以每次关注一个细胞的方式来研究大脑。
每次一个细胞!我一开始听到这几个词儿时感到很泄气。怎么能够通过在单个神经细胞的水平研究大脑来解决精神分析关于行为的无意识动机或者我们有意识的行动这类问题呢?但随着谈话的进行,我突然想起,弗洛伊德在1887年开启自己的事业时,就曾试图以每次一个神经细胞的方式来研究大脑,以期解决藏在精神生活背后的谜团。弗洛伊德从一名解剖学家做起,研究单个神经细胞,并预见到了后来被称为神经元学说的主要观点,即神经细胞是大脑的基础构件。而只有到了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开业治疗心理疾病患者之后,他才做出了关于无意识心理过程的不朽发现。
现在,格伦德费斯特鼓励我反其道而行之,把对自上而下的心智结构理论产生的兴趣转移到自下而上地研究神经系统的信号传导元件,亦即神经细胞的复杂内部世界,这让我感到一丝讽刺意味,同时又印象深刻。格伦德费斯特将引领我走进这个新世界。
我特别想跟格伦德费斯特一起工作,因为他是纽约市知识最渊博、最睿智风趣的神经生理学家,实际上也是全美国最好的神经生理学家之一。他时年51岁,正处于其卓越智识力量的巅峰期(图4-2)。

图4-2 哈里·格伦德费斯特(1904—1983年),哥伦比亚大学神经学教授,引领我进入神经科学。我念到医学院第四年时,于1955—1956年间在他的实验室工作了6个月。(来自埃里克·坎德尔的个人收藏)
格伦德费斯特1930年在哥大获得动物学和生理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并继续在那里从事博士后工作。他于1935年进入洛克菲勒研究所(现在的洛克菲勒大学),在赫伯特·加瑟实验室工作。加瑟是神经细胞的电信号传导研究方面的先驱,这个传导过程是神经细胞如何运作的核心。格伦德费斯特加入实验室时,加瑟被任命为洛克菲勒研究所所长,正处于事业的高峰。1944年,加瑟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时格伦德费斯特仍然在他的实验室工作。
,并继续在那里从事博士后工作。他于1935年进入洛克菲勒研究所(现在的洛克菲勒大学),在赫伯特·加瑟实验室工作。加瑟是神经细胞的电信号传导研究方面的先驱,这个传导过程是神经细胞如何运作的核心。格伦德费斯特加入实验室时,加瑟被任命为洛克菲勒研究所所长,正处于事业的高峰。1944年,加瑟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时格伦德费斯特仍然在他的实验室工作。
当格伦德费斯特在加瑟实验室的学术训练结束时,他已经具备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和坚实的电子工程学基础。不仅如此,他还掌握了从简单无脊椎动物(如螯虾、海螯虾、枪乌贼等)到哺乳动物在内的多种动物神经系统的比较生物学知识。那时很少有人拥有如此广博的知识背景。于是在1945年,格伦德费斯特被母校聘为医学院神经学研究所新开设的神经生理学实验室负责人。入职之后不久,他与著名生物化学家戴维·纳赫曼佐恩开展了一项重要的合作。他们一同研究了神经细胞信号传导中的生物化学变化。格伦德费斯特看起来前途一片光明,但他很快就遇到了麻烦。
1953年,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担任主席的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传唤格伦德费斯特作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伦德费斯特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激进分子,在新泽西的蒙莫斯堡信号实验室气候研究组从事创伤修复和神经再生的研究。麦卡锡暗示格伦德费斯特同情共产主义,他或者他的朋友在战时曾把技术知识透露给苏联。在麦卡锡听证会上,格伦德费斯特作证说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他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赋予自己的权利,拒绝进一步讨论他本人或其同事的政见。
麦卡锡没有找到哪怕一丝证据来支持他的指控,而格伦德费斯特却好些年拿不到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项目资助。纳赫曼佐恩害怕自己的政府资助会受到连累,便将格伦德费斯特请出了他们共享的实验室,并中断了他们的合作。格伦德费斯特不得不把自己的研究组成员减到只剩两人,如果不是哥大学术部门给予他强有力的支持的话,他的事业恐怕会遭受更严重的打击。
对格伦德费斯特来说,在他科研生涯的顶峰阶段,科研实力反遭削弱的后果是毁灭性的。矛盾之处在于,这样的环境对我而言却是因祸得福。格伦德费斯特有了比以往更多的时间可供支配,他把其中大部分时间用来教我脑科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以及它如何从一个描述性的和松散的领域迅速转变成一门建立在细胞生物学基础之上的贯通性学科。我对现代细胞生物学几乎一无所知,但格伦德费斯特概述的大脑研究新方向让我着了迷,引发了无限的遐想。通过以每次一个细胞的方式来研究大脑,大脑功能之谜开始揭开面纱。
自从在神经解剖课上塑了那个黏土模型之后,我便将脑视为一个单独的器官,它与身体其他部分的运作方式极其不同。这当然是真的:肾脏和肝脏既不能接收和加工感觉器官受到的刺激,它们的细胞也不能存储和提取记忆或产生有意识思维。然而,格伦德费斯特指出,所有的细胞都具有若干共同特征。1839年,解剖学家马蒂亚斯·雅各布·施莱登和西奥多·施旺创立了细胞学说。该学说认为所有活着的实体,从最简单的植物到复杂的人类,都是由称作细胞的相同基本单元构成。虽然不同植物和动物的细胞在细节上存在重大差异,但它们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格伦德费斯特解释道,一个多细胞生物体内的每个细胞都覆盖着一层油性膜,将其与其他细胞以及浸着所有细胞的细胞外液分隔开。细胞表面的膜对特定物质具有渗透性,允许细胞内部与细胞外液之间进行营养成分和气体的交换。细胞内部有细胞核,它自身包含一层膜,环绕其外的是被称作细胞质的细胞内液。细胞核含有细长状染色体,由携带基因的DNA组成,看上去就像绳上的串珠。除了控制细胞让自身得到复制,基因还指导细胞制造执行各种功能所需的蛋白质。而真正制造蛋白质的装置位于细胞质中。从以上共享的特征来看,细胞就是生命的基本单元,也是所有动植物的全部组织和器官的结构与功能基础。
除了共同的生物学特征,所有细胞都具有特定功能。比如肝细胞执行消化功能,而脑细胞之间则有加工信息并进行交流的特定方式。这些相互作用允许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形成完整的环路来传递和转换信息。格伦德费斯特强调,正是特定功能使得肝细胞专门适于新陈代谢,而脑细胞则专门适于信息加工。
我在纽约大学的基础科学课上和指定的教材阅读材料中已经学习过所有这些知识,但直到格伦德费斯特把它们放在情境中进行讲解之前,这些知识没能激起我半点的好奇心,甚至对我也没有多大意义。神经细胞不仅仅是生物学中一页非凡的篇章。它是理解大脑如何运作的关键。随着格伦德费斯特的教学对我产生重大影响,他关于精神分析的洞见也同样影响了我。我开始认识到,在我们能够用生物学术语理解自我如何运作之前,需要先理解神经细胞如何运作。
格伦德费斯特强调,理解神经细胞如何运作至关重要,这一点成为我日后研究学习与记忆的基础;他坚持从细胞水平研究脑功能,这一点对新心智科学的诞生非常关键。回过头来看,考虑到人脑是由1000亿个神经细胞组成,而科学家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仅仅通过对脑中个体细胞进行研究,就已经取得了有关心理活动如此多的进展,这成绩着实斐然。细胞学研究是在理解知觉、随意运动、注意、学习和记忆存储的生物学基础方面迈出的第一步。
神经细胞的生物学建立在三大原理之上,这三大原理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成型并形成了我们今天理解大脑功能性组织的核心。 神经元学说 (即应用于大脑的细胞学说)指出,神经细胞,或曰神经元,是大脑的基本构件和基本信号传导单元。 离子假说 关注神经细胞内的信息传递。它描述了个体神经细胞产生电信号(称作动作电位)的机制,使得信号可以在特定细胞内进行长距离传输。 突触传递的化学理论 关注神经细胞间的信息传递。它描述了一个神经细胞如何通过释放化学信号(称作神经递质)与另一个神经细胞进行交流,以及第二个细胞如何识别这一信号并依靠它表膜上的特异性分子(称作受体)做出反应。这三大原理关注的都是个体神经细胞。

图4-3 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1852—1934年),伟大的西班牙解剖学家,创立了神经元学说,这一学说是现代所有关于神经系统的认识的基础。(承蒙卡哈尔研究所惠允)
使精神生活的细胞学研究成为可能的那个人名叫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
 ,他是一名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神经解剖学家(图4-3)。卡哈尔为神经系统的现代研究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他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脑科学家。他起初渴望成为一名画家。为了熟悉人体,他跟随当外科医生的父亲学习解剖学,父亲用从古墓中挖掘出的尸骨教他。对这些骨骼残骸的着迷使卡哈尔最终从绘画转向了解剖学,进而又专攻脑解剖学。与弗洛伊德和许多年后的我一样,卡哈尔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转向脑研究的。卡哈尔想要创立一门“理性心理学”。他认为第一步需要获得详细的脑细胞解剖学知识。
,他是一名与弗洛伊德同时代的神经解剖学家(图4-3)。卡哈尔为神经系统的现代研究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他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脑科学家。他起初渴望成为一名画家。为了熟悉人体,他跟随当外科医生的父亲学习解剖学,父亲用从古墓中挖掘出的尸骨教他。对这些骨骼残骸的着迷使卡哈尔最终从绘画转向了解剖学,进而又专攻脑解剖学。与弗洛伊德和许多年后的我一样,卡哈尔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转向脑研究的。卡哈尔想要创立一门“理性心理学”。他认为第一步需要获得详细的脑细胞解剖学知识。
他有一项不可思议的工作能力,能从已经死去的神经细胞的静态图像推断出活体神经细胞的性质。这种想象力上的飞跃也许源于他的艺术爱好,使他得以用生动的术语和美丽的图画来捕捉并描述他所观察到的事物的本质特征。著名的英国生理学家查尔斯·谢林顿后来这样形容他:“在描述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景象时,(卡哈尔)习惯于把它描述成一幅鲜活的场景。由于他的观察材料全都(是)死掉的和不会动的,这就更加令人吃惊。”谢林顿继续写道:
卡哈尔通过观察染色固定的脑切片而给出的极度拟人化的描述,乍听上去太让人吃惊,以至于难以接受。他对显微镜下的景象的描写让人觉得它是鲜活的,里面住着和我们一样去感受、行动、希望和尝试的生物。……一个神经细胞用它那四散的纤维“摸索着去找寻另一个”!……听着他的描述,我问自己,他作为一名研究者所取得的成功怎能不归功于这种拟人化的能力。我从未遇到第二个拥有这等显著能力的人。
在卡哈尔进入这个领域之前,生物学家完全被神经细胞的形状搞糊涂了。不同于身体内有着简单形状的其他大多数细胞,神经细胞具有高度不规则的形状并被大量非常精细的延伸部分(当时称作突起)环绕着。生物学家不清楚这些突起是否是神经细胞的一部分,因为当时还无法追踪它们往回连到某个胞体或者往前连到另一个胞体,于是也就无法知道它们来自哪里或通向何处。此外,由于突起都极其纤细(大约是人的发丝直径的百分之一),没人能够观察到并分离出它们的表膜。这就导致包括伟大的意大利解剖学家卡米洛·高尔基在内的许多生物学家得出结论,说这些突起没有表膜。不仅如此,由于环绕一个神经细胞的突起会与环绕其他神经细胞的突起紧密相邻,这让高尔基觉得不同突起内的细胞质是自由混杂的,由此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神经网,和蜘蛛网很像,这样信号可以同时向所有方向传递。因此,高尔基认为,神经系统的基本单元一定是这个自由交流的神经网,而非单个神经细胞。
到了19世纪90年代,卡哈尔尝试寻找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让神经细胞从整体上显像。他通过结合两种研究策略做到了这一点。第一种是研究新生而非成年动物的脑。在新生动物中,神经细胞的数目很小,细胞密度更低,突起也更短。这使卡哈尔能在脑的整片细胞森林里观察具体的树。第二种策略是使用一种由高尔基发明的特定银染色法。这种方法的任意性很大,标记细胞完全基于随机,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神经元会被染色。不过每一个被标记的神经元都会被完整地染色,允许观察者看到神经细胞体和所有的突起。在新生动物的脑中,这种碰巧被标记的细胞在整片未被标记的森林中凸显了出来,如同一棵被点亮的圣诞树。卡哈尔因此写道:
由于事实证明繁茂的森林是难以理解和描述的,为什么不转而研究处于育苗期的小树苗呢?……如果恰当地选择发育阶段……神经细胞相对而言仍然很小,但各个部分都完全长出;那些终端的分枝……能被极其清晰地描绘出来。
以上两种策略揭示出,尽管神经细胞的形状很复杂,但它们是完整的单个实体(图4-4)。环绕它们的精细突起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直接从胞体长出来的。不仅如此,包括突起在内的整个神经细胞,是被一层表膜完全包裹着的,这与细胞学说相符。卡哈尔进一步区分出了两类突起——轴突和树突。他将这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神经细胞称作神经元。除了极少的例外,脑中所有神经细胞都由一个包含细胞核的胞体、一条轴突和许多精细的树突组成。

图4-4 海马体中的一个神经元,由卡哈尔绘制。 卡哈尔认识到一个细胞的树突和轴突都是从胞体长出的,信息则由树突(上部)流向轴突(下部)。这幅图是根据卡哈尔原图修改的。(根据哈维尔·德费利佩和爱德华·琼斯编译的《卡哈尔关于大脑皮层的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图23修改,得到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使用)
一个典型神经元的轴突从胞体长出后可以延伸数英尺
 长。轴突常常沿着延伸的方向,分叉成为一个或多个分枝。每一个分枝的末端有很多细小的轴突终端。树突常常从胞体的另一侧长出(图4-5-A),分枝众多,形成一个从胞体伸出的树状结构并散布到很大一块区域。人脑中有些神经元的树突分枝多达40个。
长。轴突常常沿着延伸的方向,分叉成为一个或多个分枝。每一个分枝的末端有很多细小的轴突终端。树突常常从胞体的另一侧长出(图4-5-A),分枝众多,形成一个从胞体伸出的树状结构并散布到很大一块区域。人脑中有些神经元的树突分枝多达40个。

图4-5 卡哈尔的神经组织方式四原理。
19世纪90年代期间,卡哈尔将他的观察汇总到一起,形成了神经元学说的四原理,从那时起到现在,这一关于神经组织方式的学说一直支配着我们对大脑的理解。
第一条,神经元是大脑的基本结构及功能单元,也就是说,它是大脑的基本构件和基本信号传导单元。而且,卡哈尔推断轴突和树突在信号传导过程中扮演大相径庭的角色。一个神经元通过树突接收来自其他神经细胞的信号,并通过轴突向其他细胞发送信息。
第二条,他推断一个神经元的轴突终端与另一个神经元的树突只在特定区域进行交流,这个区域后来被谢林顿称作突触(synapses,源自希腊语synaptein,意思是“绑在一起”)。卡哈尔进一步推断两个神经元之间的突触的特征是存在一个小间隙,现在称作突触间隙。在这个空间,一个神经细胞的轴突终端——卡哈尔将其称作突触前终端——靠近另一个神经细胞的树突,但并没有完全接触(图4-5-B)。因此,就像嘴巴贴着耳朵呢喃细语,神经元之间的突触交流包括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轴突的突触前终端,用于发送信号(相当于上述类比中的嘴巴);突触间隙(嘴巴和耳朵之间的空间);以及树突上用于接收信号的突触后区域(耳朵)。
第三条,卡哈尔推断出连接特异性原理,认为神经元并非不加区分地形成连接。而是每个神经细胞通过突触与特定神经细胞进行交流,且不与其他神经细胞交流(图4-5-C)。他运用连接特异性原理来展示神经细胞是在特异性通路中相连接的,他将这些通路称为神经环路,信号在这些环路中以一种可以预测的模式进行传导。
通常情况下,单个神经元通过它的多个突触前终端与许多靶细胞的树突进行交流。通过这种方式,单个神经元能够把它接收的信息广泛地散布到不同的靶神经元中,这些靶神经元有时位于大脑的不同区域。反过来,一个靶神经细胞的树突能够从多个不同神经元的突触前终端接收信息。通过这种方式,一个神经元能够整合来自多个不同神经元的信息,即便这些神经元位于大脑的不同区域。
基于对信号传导的分析,卡哈尔把大脑构想为一个由特异性的、可预测的环路构成的器官,这与当时流行的看法不同,后者将大脑看作一个弥散性神经网,其中到处发生着各种可能形式的相互作用。
通过直觉上的惊人跳跃,卡哈尔得到了第四条原理:动态极化。这条原理认为信号在一个神经环路中的传导方向只有一个(图4-5-D)。信息从一个给定细胞的树突流向胞体,再沿着轴突流向突触前终端,然后穿过突触间隙进入下一个细胞的树突,依此类推。这个信号单方向流动的原理极其重要,因为它将神经细胞中的所有组成部分通过一个单一的功能——信号传导——联系在了一起。
从连接特异性原理和信号单方向流动原理出发,能够推导出一套规则,从那时起,人们就用这套规则绘制神经细胞之间的信号传导线路图。卡哈尔对神经环路的描绘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他发现存在于脑和脊髓中的这类环路包括三种主要神经元,每种都有专门的功能。 感觉神经元 位于皮肤和各种感觉器官中,对来自外部世界的特定刺激——机械性压力(触觉)、光(视觉)、声波(听觉)及特异性化学物质(嗅觉和味觉)——做出反应并向大脑发送这些信息。 运动神经元 由脑干和脊髓向效应细胞——如肌肉和腺体细胞——伸出轴突,并控制这些细胞的活动。 中间神经元 是脑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神经元,在感觉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之间起中继作用。卡哈尔由此得以追踪指示肌肉细胞运动的信息流:它从皮肤的感觉神经元传到脊髓,再从脊髓经由中间神经元传到运动神经元(图4-6)。卡哈尔是从对大鼠、猴子和人的研究中得出这些洞见的。

图4-6 由卡哈尔分类的三种主要神经元。 脑和脊髓中的每种神经元都有专门的功能。感觉神经元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运动神经元控制肌肉和腺体细胞的活动。中间神经元在感觉神经元和运动神经元之间起中继作用。
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认识到每一种细胞都可以依据其生物化学特性进行区分,并能受到不同的疾病状态影响。比如,在梅毒后期,来自皮肤和关节的感觉神经元会受损;帕金森氏病会攻击一类特定的中间神经元;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和脊髓灰质炎会选择性地破坏运动神经元。事实上,有些疾病的选择性很强,它们只影响神经元的特定部分:多发性硬化症影响某种特定的轴突;高歇氏病影响胞体;脆性X染色体综合征影响树突;肉毒杆菌中毒影响突触。
卡哈尔因其革命性的洞见与高尔基共同获得了190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正是高尔基的银染色法让卡哈尔的发现成为可能。
虽然高尔基发明的技术为卡哈尔的杰出发现铺平了道路,他却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卡哈尔的学说,而且从未认可过神经元学说的任何一个方面。这是科学史上奇怪又扭曲的一幕。事实上,高尔基甚至利用他的诺贝尔讲座
 再次发起对神经元学说的攻击。他一开场就再次断言,他会一直反对神经元学说而且“这一学说大体上已经不再受欢迎”。他接着说道:“依我之见,根据所有已经提到的那些……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任何结论来支持或者反对神经元学说。”他进一步辩称动态极化原理是错误的,而且一个神经环路的基本单位通过精确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或者不同的神经环路具有不同的行为功能的观点也不正确。
再次发起对神经元学说的攻击。他一开场就再次断言,他会一直反对神经元学说而且“这一学说大体上已经不再受欢迎”。他接着说道:“依我之见,根据所有已经提到的那些……我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任何结论来支持或者反对神经元学说。”他进一步辩称动态极化原理是错误的,而且一个神经环路的基本单位通过精确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或者不同的神经环路具有不同的行为功能的观点也不正确。
直到1926年去世,高尔基还在非常错误地认为神经细胞不是自成一体的单元。至于卡哈尔,他后来针对分享诺贝尔奖一事写道:“命运是如此残酷而讽刺,如同肩膀连在一起的暹罗双胞胎那样,将科学上个性差异鲜明的对手配到了一起。”
上述分歧揭示了科学社会学中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我后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屡次遇到过。首先,存在像高尔基这样的科学家,技术过硬却未必对其研究的生物学问题有很深的洞察力。其次,甚至最优秀的科学家也会各执一词,特别是在研究的早期阶段。
有些情况下,始于科学问题的争论会演变成几乎带有报复性质的私人恩怨,正如在高尔基的案例中那样。这类争论揭示出,科学家之间不仅有慷慨和分享的举动,他们也会因为野心勃勃、骄傲自满及怀恨在心而彼此竞争。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很清楚。科学的目标是发现关于世界的新真理,而发现意味着优先权,看谁抢先一步。正如离子假说的创立者艾伦·霍奇金在其自传文章中写道:“如果纯粹的科学家仅仅受到好奇心的驱使,他们就应该对别人解决了他们正在研究的问题感到高兴,但这可不是他们通常的反应。”同行的认可和尊重只会给予那些对共有的知识大厦做出原创性贡献的科学家。这使得达尔文指出,他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很大程度上是由渴望得到科学家同行尊重的雄心驱使的”。

图4-7 查尔斯·谢林顿(1857—1952年)研究反射行为的神经基础。他发现神经元可以被抑制或激动,对这些信号的整合决定了神经系统的活动。(翻印自《神经系统的整合活动》,剑桥大学出版社1947年版)
最后一点是,重大的争议往往发生在现有方法还不足以给核心问题提供一个明白无误的答案之时。直到1955年,卡哈尔的直觉才最终得到证实。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桑福德·帕莱和乔治·帕拉德通过电子显微镜证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存在一个将一个细胞的突触前终端与另一个细胞的树突分隔开来的微小空间——突触间隙。这些新图像还揭示出,突触是不对称的,很久之后才发现的释放化学递质的装置,只存在于突触前细胞。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个神经环路的信息流只有一个方向。
生理学家很快就注意到了卡哈尔所做贡献的重要性。查尔斯·谢林顿(图4-7)成了卡哈尔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并邀请他于1894年访问英国,在伦敦皇家学会的克鲁尼安讲座上作报告。这是大不列颠能够授予一名生物学家最尊贵的荣誉之一。
谢林顿在其1949年纪念卡哈尔的文章中写道:
把他称作有史以来神经系统方面最伟大的解剖学家,这个评价过分吗?一直以来有很多一流的研究者对神经系统感兴趣,在卡哈尔之前做出过一些发现,这些发现常常给医生们带来比以往更多的困惑,徒增谜团且毫无启发。如今即便是个新手瞥一眼,也能认出一个活细胞及一个完整的神经细胞链中神经电流的方向,是卡哈尔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
他一举解决了神经电流在脑和脊髓中的传导方向这一重要问题。比如,他发现每一个神经通路永远只是一条单行道,而且它的方向始终保持一致,永不可逆。
谢林顿在其很有影响力的《神经系统的整合活动》一书中,以卡哈尔发现的神经细胞结构为基础,进一步将结构与生理学和行为学联系起来。
他通过研究猫的脊髓做出这一成果。脊髓接收并加工来自皮肤、关节和四肢及躯干肌肉的感觉信息。它自身包含很多基本的神经装置来控制四肢和躯干的运动,包括走路和跑步所需的运动。谢林顿尝试理解简单神经环路,他研究了两种反射行为——猫身上相当于人类膝跳反射的行为,以及受到一个引起不愉快感觉的刺激时猫爪的缩回反应。这些与生俱来的反射不需要学习。而且它们是脊髓固有的反射,不需要将信息发送到脑。一个适当的刺激就能立刻诱发这些反射,比如轻敲膝盖或者让爪子接触电击或热的表面。
在研究反射的过程中,谢林顿发现了一些卡哈尔仅仅通过解剖学研究无法预料到的现象——并非所有的神经活动都是兴奋性的——换言之,并非所有的神经细胞都通过它们的突触前终端来刺激相邻的接收细胞往前传递信息。有些细胞是抑制性的,它们通过自身的终端终止接收细胞的信息传递。谢林顿在研究不同的反射是如何协调产生一致的行为反应时做出了上述发现。他发现,当特定部位受到刺激以便诱发特定的反射性反应时,只有这个反射被诱发,其他与之相反的反射则被抑制。因此,轻敲一下膝盖骨的肌腱会诱发一个反射活动——向前踢腿。这次敲击同时抑制了与之相反的反射活动——向后屈腿。
谢林顿接着探究了运动神经元在上述协调一致的反射性反应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发现,当他轻敲膝盖骨的肌腱时,伸展下肢(伸肌)的运动神经元产生兴奋,同时屈曲下肢(屈肌)的运动神经元受到抑制。谢林顿将抑制屈肌的细胞称作抑制性神经元。后来的研究发现,几乎所有的抑制性神经元都是中间神经元。
谢林顿立刻意识到,抑制不仅对协调反射性反应,而且对增强反应的稳定性都很重要。动物常常遭受可能诱发两种对立反射的刺激。在这些竞争性反射中,抑制性神经元通过抑制除了某个之外的其他全部反射(这个机制称作交互控制),使得某个特定刺激产生一个稳定、可预测、协调的反应。比如,腿的伸展总是伴随着对屈曲的抑制,腿的屈曲总是伴随着对伸展的抑制。通过交互控制,抑制性神经元在竞争性的反射中做出选择,以确保可能发生的两个甚至多个反应中只有一个会表现成行为。
脑和脊髓对反射的整合和决策能力源自个体运动神经元的整合性特征。一个运动神经元加总它从其他神经元接收到的全部兴奋性和抑制性信号,通过计算执行一系列合适的动作。当且仅当兴奋的总和超过抑制的总和且达到某个临界最小值时,运动神经元才会传递信号到靶肌肉,引发其收缩。
谢林顿将交互控制视为协调优先顺序的一般性手段,以实现活动的单一性和行为要达到的目的。他通过脊髓研究揭示出的神经整合原理,很有可能也是大脑的一些高级认知决策功能的基础。我们所形成的每一次直觉和思维,所做的每一次运动,都是大量相似的基础性神经计算的结果。
19世纪80年代中期,当弗洛伊德放弃他对神经细胞及其连接的基础研究工作时,神经元学说的若干细节及其对生理学的启示尚未确立。但他持续关注着神经生物学的进展,并尝试将卡哈尔关于神经元的若干新主张吸收到其一份未出版的手稿《科学心理学大纲》中,这份手稿写于1895年末,那时他已经开始运用精神分析治疗患者并揭示出梦的无意识含义。虽然后来弗洛伊德变得全神贯注于精神分析,但其早期实验研究对他的思想有着持续性影响,因此也影响了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心理学家罗伯特·霍尔特这样写道:
从许多方面来看,弗洛伊德似乎经历了一次重大的重新定位。他从一名神经解剖学研究者转变成了一名通过心理治疗进行实验的临床神经科医师,并最终成为首位精神分析师。然而,如果我们想象这个转变过程中的延续性远少于变化,那么我们就只是平庸的心理学家了。当弗洛伊德决定转变成为心理学家,去研究一个纯抽象的假想模型时,他很难将倾注了20年热情的神经系统研究经历弃如敝履。
弗洛伊德把他用于研究简单生物(比如螯虾、鳗鱼和原始鱼类)神经细胞的这一时期称作“我学生时代最快乐的时光”。在与后来成为其妻子的玛莎·伯奈斯相遇并相爱后,他放弃了这些基础研究工作。在19世纪,一个人需要用另外的收入来负担研究事业。考虑到自己可怜的财务状况,弗洛伊德转而开了一间诊所,这可以赚到足够的钱来支撑家庭开销。如果那时能像今天这样,从事科学职业的收入就能养家糊口,弗洛伊德也许会作为一名神经解剖学家闻名于世,并成为神经元学说的共同创立者,而不是精神分析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