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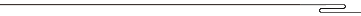
季先生语录:
我们常讲,在世界上,争来争去,不外名利两件事。名是为了满足求胜的本能,而利则是为了满足求生。二者联系密切,相辅相成,成为人类的公害,谁也铲除不掉。古今中外的圣人贤人们都尽过力,而所获只能说是有限。
古人云:名利之心,人皆有之。自古以来,不论是君子,还是小人,概莫能外。从古至今,多少人因追名逐利而付出惨痛的代价,从中,人们的名利之心,可见一斑。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一个极端,它深为世人所推崇,即如陶潜那般对名利予以淡泊的态度。前者是不当为我们所取的,因为将名利作为人生的追求,不仅是人生价值缺失的表现,也是人格上的一种缺陷。而后者,人生在世能淡泊名利,是坚守本真,不与世人同流合污的表现,自古以来,深为人们赞许。
但是,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人,在当今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中,一个毫无名利之心的人,可以说,是难以立足于社会的。一旦有竞争,就必然会有求胜之心,而这不正与名或利密切相关吗?说完全没有求胜的渴望,那是非常牵强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求胜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追名求利的人。这是对自我人格的一种亵渎,更是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毁灭。
试问,当今社会的一些贪官腐败之徒,若不是追名逐利之心过剩、过强,他们能走上被枪毙或者是被终身监禁的道路吗?“自作孽不可活”,到底还是追名逐利之心让他们自食苦果了。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正常的现象。换句话说,人生中,该拥有的名誉或者利益,用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是无可厚非的。这样的人,其为人是坦荡的,其品行是端正的,其人格是良好的。但是,如若将逐名逐利定为人生的全部或者是最高追求,那么,这样的人格是不足为道的。下面这个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宋国有个叫曹商的人。他被宋王作为使臣派往秦国。他出发的时候,宋王给他的全部财产是几辆车。但是,曹商从秦国回来的时候,却带回了一百辆车,还有许多银两和珠宝。
曹商回国后见到庄子,便不断地炫耀自己。他说:“先生啊,像您这样长年住在偏狭的陋巷里,穷得揭不开锅,饿得面黄肌瘦,每天只能靠编织草鞋勉强维持生计的生活,我一天都过不下去!您看看我现在,靠着自己的能言善辩,赢得秦王的欣赏,秦王一高兴,便赏了我一百辆车,我现在的生活多好啊。这就是我曹商与您不同的地方。”
庄子轻蔑地看了曹商一眼,直言不讳地说:“我听说秦王在生病的时候召来了许多医生,对他们当面许诺:凡是能挑破粉刺排脓生肌的,赏车一辆;而愿意为其舐痔的,则赏车五辆。治病的部位愈下,所得的赏赐愈多。曹商你得到的赏赐这么多,一定是舔了秦王的痔吧?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
曹商为了赢得秦王的赏识,为了追名逐利而不惜放弃自己的人格尊严,一切以“利”为重,把名利当作是自己的最高追求,试问,这样的行为是可取的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正是庄子蔑视和嘲笑曹商的缘故。曹商的例子对于生活中那些以追名逐利为最终目的的人来说,不失为一面明镜。
那么,我们究竟该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名利,才不损害我们的人格,至少不给我们的人格带来负面的影响呢?对此,季先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季先生直言不讳地相告,“我名利之心兼而有之”,但是,他也坦诚地告诉人们:“即使我想再往上爬,我也绝不会奔走、钻营、吹牛、拍马,只问目的,不择手段。那不是我的作风,我一辈子没有干过。”的确,季先生一生对待名利的态度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比如他在《病榻杂记》中的“三辞”就将他对名利的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季先生是一个极为谦虚的人。纵然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有名利之心的人,但是,他不会刻意地追名逐利,更不会因利而求名,相反,他的做法是:成名不逐利。
何以见得?拿“学术泰斗”一名来说,不论是从季先生在语言学上的成就来看,还是从他在比较文学上的成就来看,“学术泰斗”这一桂冠戴在季先生头上都是当之无愧的,试问,当今学术界,还有谁能如季先生一样在梵语研究上取得那么高的成就?再问,又有谁能如季先生一样,精通几十种冷僻的外语?然而季先生用自己的成就铸就了自己“学术泰斗”之名,却不去争夺“学术泰斗”之利,而是公然请辞“学术泰斗”之冠冕,把自己打成一个“平民泰斗”。
与学术界那些为了争名逐利而卖弄玄虚的人相比较,季先生真实、坦然、谦虚的品格更为突出。而这也正是季先生完美人格的真实写照。
人生于世,对待名利之心,我们应当以季先生为榜样,成名不逐利,做一个有真才实学却又不追名逐利的人。这样一来,我们自身的人格也会因之而不断地完善,而不会沦为名利的囚徒,成为一个人格有缺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