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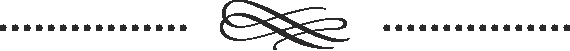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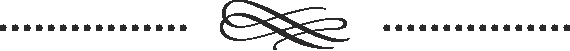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1876年,英格兰买下了苏伊士运河,这是迪斯累里担任首相后开的第一枪,就是这一枪,宣告了英国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大规模帝国扩张,只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征伐能与之相比。苏伊士之后的逻辑演进即是1878年签订的《塞浦路斯协定》。根据这份协定,英国承诺用军事手段保证土耳其在亚洲的领土。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这片历史性地区是上帝划给亚伯拉罕的,如今都进入了英国的势力范围。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此后又延续了40年,但英国在获得苏伊士运河和塞浦路斯之后,最终得到巴勒斯坦仅是个时间问题。
英国在成功处置1858年的印度暴动之后正式成为帝国,此后英国的一切都是围绕印度展开的。这就出现了“获得可防御边境的迫切不可抗拒的需要” [1] ——按照建立帝国的功臣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所说——于是英国在1879年至1889年一共取得了125万平方英里的土地 [2] 。阿富汗在北面阻止俄国进入印度,缅甸是印度的东部边疆,埃及用以保护苏伊士运河,这条运河就是在这段时间买下的。接着英国来到非洲,从非洲底部的德兰士瓦(Transvaal)到顶部的埃及,中间保留出足够的土地建造一条从好望角到开罗的道路,让穿着红色军服的英国军人穿越这片黑色的土地。如此扩张的帝国不仅是为了建立可防御的边境,还有个同样重要的目的,就是急迫地为曼彻斯特生产的棉布寻找市场。这个组合之所以如此的不可抗拒,是因为英国人心怀傲慢且真诚的信念,即英国正在实现自己的天命——扩大不列颠种族的统治以传播文明。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是“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统治种族”。 [3]
“上帝的英国人”(God’s Englishman)这个说法是被米尔纳(Milner)勋爵推广出名的,他是帝国的发言人。罗斯伯里(Rosebery)勋爵在帝国扩张中看到了“神的亲手帮助”
[4]
。利文斯通博士以传教士的身份打开了中非的大门。戈登将军踏上了去苏丹的不归之途,衣兜里揣着《圣经》,经常拿出来读,如同奥利弗·克伦威尔一样。斯特德(W. T. Stead)写了《评论的评论》,他在前言中宣告,帝国主义分子的信条是“说英语的种族是上帝挑选出的主要助手,将要帮助上帝改进人类”
[5]
。另一方面,以格拉德斯通为首的“小英格兰”派认为帝国扩张是“疯狂的掠夺”
 ,“害死帝国的欲望”
[6]
。
,“害死帝国的欲望”
[6]
。
但发展趋势与格拉德斯通等人的看法相反,苏伊士运河仅是英国的初始冲动。英国在获得了从红海通往印度和远东的航线之后,地中海东南角就变成了帝国的战略要地。自此以后,圣地变成了英国的军事左侧翼,而埃及和苏丹变成右侧翼,并在1880年代被英国占领。这就是陆军部以《圣经》研究为由,送皇家工兵去巴勒斯坦绘制地图的原因。
英国迈出的第二步是用《塞浦路斯协定》的形式保证土耳其在亚洲的权益,这个协定不是太有名气,但同样重要。协定意味着英国已经看出巴勒斯坦地区的重要性,于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以各种托管形式占领了它。安全保证代表为之开战的意愿,实际上,安全担保通常隐含对战争即将到来的预期。英国在1939年向波兰提供安全担保就是一例。所以,《塞浦路斯协定》标志着英国已经下定了决心,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这个地区是值得为之开战的。实际上,《塞浦路斯协定》中英国预想的结果并没有出现。这个协定的预想敌是俄国,但到了19世纪末,德国超过俄国成为英帝国的主要敌人。后来,战争真的来了,英国借机成为土耳其亚洲领土的继承者,但这场战争不是支持土耳其抵御俄国,而是与德国和土耳其为敌。
在19世纪的一头一尾,先是拿破仑与英国为敌,后是德皇与英国为敌,在这两个时段之间,俄国是英国的首要敌人。不是针对不列颠岛,而是针对大英帝国。俄国自古对其南方就表现出贪婪无度的欲望,这与英国迈向帝国的道路发生了冲突,叶卡捷琳娜大帝之后的俄国统治者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皮特为阻止叶卡捷琳娜大帝占有敖德萨,宁愿与俄国开战;帕麦斯顿在1830年挫败了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攫取黑海的企图。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也是为这个目的而展开的。迪斯累里在1870年为同样的原因几乎走到了战争边缘。俄罗斯人从来不放弃。1844年,尼古拉一世访问伦敦,他向英国外交大臣阿伯丁提出建议,俄国和英国联手瓜分土耳其帝国,俄国成为土耳其在欧洲巴尔干领土的保护者,而英国拿走埃及和克里特,君士坦丁堡则变为自由城市,由俄国“临时占领”。 [7] 尼古拉是个头脑简单的独裁者,不觉得加速历史进程有什么坏处,因为当时所有人都预计土耳其帝国随时会崩溃。然而,他的计划虽然有吸引力,但在议会制的英国是不可能的。虽然英国有诡计多端的名声,却总是根据现实需要制定政策,而非反过来。正如西利(Seeley)给出的精辟解释,英国几乎是通过一系列无计划的偶然动作,“心不在焉地”征服了半个世界。 [8]
俄国的下一个企图是强行闯入奥斯曼帝国的地盘,耶路撒冷为俄国提供了借口。克里米亚战争因圣所的纠纷而爆发
[9]
,这是人类历史上引发大规模战争最荒谬不过的理由。“就为了几个希腊教士。”
 利芬(Lieven)公主不屑地说道。虽然借口微小,但如果没有尼古拉一世和拿破仑三世的借题发挥,根本不会引发一场大战。俄国在历史上一直充当圣地内希腊东正教机构的保护人,而法国则保护拉丁或罗马天主教徒。两边的修道会、教士、朝圣者经常就圣所和圣殿的使用权发生冲突。1535年,苏莱曼与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签订协约,给予法国保护下的拉丁教士以主导权。但这项权力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期间的反基督教政策下衰败了。在沙皇的蓄意支持下,东正教不断扩张。尼古拉用东正教作为深入奥斯曼帝国的楔子,要求土耳其苏丹答应让他做奥斯曼治下的圣所和东正教徒的保护人。
利芬(Lieven)公主不屑地说道。虽然借口微小,但如果没有尼古拉一世和拿破仑三世的借题发挥,根本不会引发一场大战。俄国在历史上一直充当圣地内希腊东正教机构的保护人,而法国则保护拉丁或罗马天主教徒。两边的修道会、教士、朝圣者经常就圣所和圣殿的使用权发生冲突。1535年,苏莱曼与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签订协约,给予法国保护下的拉丁教士以主导权。但这项权力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一世期间的反基督教政策下衰败了。在沙皇的蓄意支持下,东正教不断扩张。尼古拉用东正教作为深入奥斯曼帝国的楔子,要求土耳其苏丹答应让他做奥斯曼治下的圣所和东正教徒的保护人。
此时,拿破仑三世是欧洲新晋的帝国统治者,他刚刚把本不属于他的王冠从储藏柜中拿出来,戴在自己头上。与他叔叔相比,他对东方的野心并不小。笼罩在他叔叔的阴影下,他为自己的王位担心,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他需要荣耀。对,他需要一场战争,一次胜利,给法国在东方找一块土地做礼物,这能让他坐稳王位,并建立起拿破仑王朝。他急切地要求在圣所给拉丁人特权。可怜的苏丹,深陷在两个皇帝之间,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但这方案令两个皇帝都不满意。沙皇想与土耳其开战,取得胜利后,他就能拿走巴尔干诸省份,得以进驻多瑙河河口。他发出了最后通牒。土耳其苏丹向英国求救。英国早有不许俄国进入地中海的决心,并且无论输赢都不愿看到法国独自行动,于是派遣舰队开赴达达尼尔海峡。沙皇错误地以为英国公众不支持战争,于是从塞瓦斯托波尔调来他的舰队,在黑海之滨亚洲一侧的锡诺普(Sinope)消灭了土耳其人的一支舰队。英国公众激动得狂暴起来,英国回荡着恐俄症。帕麦斯顿因为在党派斗争中失利而被发落到内政部,正为战事愤怒不已。女王问他是否有关于英格兰北部罢工事件的新进展。“没有,陛下,”他痛苦地回答,“但似乎土耳其人已经跨过了多瑙河。” [10] 克里米亚战争很快全面展开了,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支援土耳其抗击俄国。
这场战争打破了俄国的如意算盘。1856年签署的《巴黎条约》
 规定所有签署国均要尊重土耳其领土的独立和完整性,并允许土耳其作为列强进入“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orpean powers);作为回报,土耳其要给予其领土上的基督徒相同的权利,并像过去一样承诺进行改革。这份条约本应该帮助土耳其恢复活力,但这个“病夫”仍然不辜负沙皇尼古拉轻蔑地给他取的这个绰号。土耳其政府仍然独裁,像过去一样腐败,似乎没有改革的迹象。秃鹰依然在土耳其周围盘旋,等待着它的死亡。实际上,《巴黎条约》没有改变任何情况,反而为下一次危机提供了火花。
规定所有签署国均要尊重土耳其领土的独立和完整性,并允许土耳其作为列强进入“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orpean powers);作为回报,土耳其要给予其领土上的基督徒相同的权利,并像过去一样承诺进行改革。这份条约本应该帮助土耳其恢复活力,但这个“病夫”仍然不辜负沙皇尼古拉轻蔑地给他取的这个绰号。土耳其政府仍然独裁,像过去一样腐败,似乎没有改革的迹象。秃鹰依然在土耳其周围盘旋,等待着它的死亡。实际上,《巴黎条约》没有改变任何情况,反而为下一次危机提供了火花。
听说要给予基督徒同样的权利,穆斯林恼怒了,这一情绪的巅峰是黎巴嫩好战的德鲁兹人(Druses)在1860年的爆发。他们对黎巴嫩地区的天主教马龙派教徒(Maronite)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大屠杀,
[11]
这一教派自圣路易率领十字军东征时就受法国人的特别保护。拿破仑三世抓住这次机会,立即派遣军队维持秩序,因为土耳其人对此没有兴趣。帕麦斯顿和罗素深深地怀疑拿破仑的动机,但又无法表示反对,因为基督徒正在被屠杀。他们犹豫地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授权法国军队为维持秩序占领黎巴嫩六个月。
 条约中的每一行文字,都能嗅出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他们都宣称自己“完全不感兴趣”,“不想也不会谋求任何领土,不谋求排他的影响力或任何特许贸易权……”。拿破仑又争取到四个月的延期,这使得英国人疑心更重。“我们不想在东方创造出一个新的罗马教皇国,这会给法国永久占领以新借口。”
条约中的每一行文字,都能嗅出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他们都宣称自己“完全不感兴趣”,“不想也不会谋求任何领土,不谋求排他的影响力或任何特许贸易权……”。拿破仑又争取到四个月的延期,这使得英国人疑心更重。“我们不想在东方创造出一个新的罗马教皇国,这会给法国永久占领以新借口。”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勋爵写道。只要还没有把法国人赶出叙利亚,他就寝食难安,因为他把英国的利益置于基督徒的安全之上。他死后,《牛津英国外交政策史》为此谴责了他。但他实现了自己的主张。他逼迫土耳其批准在黎巴嫩实施半自治,总督须是一名土耳其基督徒,且必须由诸大国提名。他用这个办法消除了法国人继续占领的理由。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罗素(John Russell)勋爵写道。只要还没有把法国人赶出叙利亚,他就寝食难安,因为他把英国的利益置于基督徒的安全之上。他死后,《牛津英国外交政策史》为此谴责了他。但他实现了自己的主张。他逼迫土耳其批准在黎巴嫩实施半自治,总督须是一名土耳其基督徒,且必须由诸大国提名。他用这个办法消除了法国人继续占领的理由。
1861年,拿破仑撤出了军队,但营救基督徒的举动为法国赢得了声誉,使法国在叙利亚建立起一个落脚点,一直延续到我们的时代法国对叙利亚的托管。与此同时,拿破仑没有放弃他的梦想。他委派吉福德·帕尔格雷夫(Gifford Palgrave) [12] 在1862年至1863年间去阿拉伯旅行,报道阿拉伯人对法国的态度。帕尔格雷夫是英国人,基督教传教士、探险家。他旅居叙利亚,曾经向外界提供了大马士革屠杀的目击报告。但这次旅行没有任何结果。另一方面,他继续追求他前辈的旧梦。1866年,他征得苏丹同意开凿一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运河。1869年,雷赛布成功了,苏伊士运河的梦想变成了现实。1869年11月17日,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乘坐着帝国游艇,率领庆典的游行船队通过了运河的水闸,这是法兰西第二帝国荣耀的最后一刻。此后不到八个月的时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被俾斯麦打败,一位新的征服者出现在欧洲大陆上,德国扩张的新时代开始了。
至此,苏伊士运河已经是既成事实。英国一直梦想拥有这样一条运河,但同时又加以阻挠,因为运河是法国东方野心的体现,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均是如此,法国之所以做穆罕默德·阿里的保护人,也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这位埃及帕夏希望用铁路和运河构建一条通往红海的通道。英国视这个项目为法国妄想占领埃及的信号,于是决心另辟蹊径,沿幼发拉底河建造一条通往红海的铁路,虽然进行了多次试验,但结果证明这个方案不切实际。帕麦斯顿关心的其实不是运河,而是害怕运河引发新的中东冲突,使得东方问题愈发无解。“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他对雷赛布说,“我们害怕失去商业和海上的优势,因为这条运河将使其他国家获得与我们相同的地位。”

老迈的帕麦斯顿似乎要永远将英国首相做下去,但他终于还是于1865年去世了。于是新思想和新人有了发展的空间。大约十年后,《坦克雷德》的作者成为英国首相。“迪斯累里先生,”女王高兴地发现,“有宏大的想法,对这个国家的地位有很高明的见解。” [13] 迪斯累里先生将这条运河看作帝国通往东方的途径,并下决心将之控制在英国手中。他采取的行动是如此大胆,如此独出心裁,那个时代绝对不会有第二位政治家会像他那样做。他在几天之内就买下了苏伊士运河。
“热心于英格兰的强大,为此他倾注了一生的激情。”
 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听到迪斯累里的死讯时说。就如同《阿尔罗伊》是他的理想抱负一样,英国是他理想中的以色列。而正是他为英格兰买下苏伊士运河,使英国开始充当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进程中的中间国了。
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听到迪斯累里的死讯时说。就如同《阿尔罗伊》是他的理想抱负一样,英国是他理想中的以色列。而正是他为英格兰买下苏伊士运河,使英国开始充当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进程中的中间国了。
情况来得很突然。穆罕默德的孙子、埃及总督伊斯梅尔(Ismail)破产了。有传言说他正在与法国人谈判,卖出他拥有的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英国外交部获得一份电报证实总督确实要出售股份,价格是400万英镑。迪斯累里约罗斯柴尔德一起吃饭。饭后,他召集内阁会议。他的私人秘书蒙塔古·科里(Montagu Corry)在屋外等着事先定好的信号。当迪斯累里把头从门口伸出来,说了一声“是”的时候,科里立即去新宫(New Court),告诉罗斯柴尔德,首相“明天”需要400万英镑。
根据科里的描述,罗斯柴尔德停下手中的工作,吃了一粒葡萄,然后问道:“谁来担保?”
“英国政府。”
“好的,你能拿到这笔钱。”

第二天,迪斯累里收到一封贷款确认信,他将在不到一周后的12月1日获得100万英镑,在12月至次年1月之间获得剩余的部分。这位银行家能获得2.5%的佣金和5%的利息,直到所借款项还清为止。女王处于“狂喜”之中,《泰晤士报》感到“震惊”。除了格拉德斯通以外,整个国家都狂热起来。女王的“利奥波德舅舅”比利时国王,向她祝贺道,这是“现代政治生活中最伟大的事件”。女王的女儿、德国王储的王妃,给女王寄来未来的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封信,当时他16岁:
亲爱的外婆:我必须写点什么,因为我知道英国买下了苏伊士运河你会非常高兴的。多么快活啊!威利。

英国议会召开会议,迪斯累里在会上为自己收购运河做了辩护,说运河是去印度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环。议会全票批准拨款400万英镑,没有人提出异议。从那时以后,“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腹地,就变成了对英国高度敏感的地区。守住奥斯曼帝国的大门,不许外来者入侵,这项任务比从前更加关键,除非英国准备自己去接管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地区。考虑到法国在叙利亚和埃及的利益,直接控制这一地区可能会触怒法国,加之英国国内自由派的反帝国主义倾向,这尚不可行。唯一的可能是支持那个“病夫”站住,把腰杆挺得足够直,不让俄国近身。
但就在这个时候,从北面传来了隆隆炮声。1875年保加利亚人起义反抗土耳其的独裁统治,俄国就好像听到吃饭铃声的狗一样,口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这导致“一切都被大火吞噬了”,迪斯累里写道,“我确实认为折磨欧洲一个世纪的东方问题……要落在我们这群人头上——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是他从柏林会议上带回了“体面的和平”,这让他名声大噪。但想“解决”东方问题超出了迪斯累里的能力,也似乎超越了所有人力可及的范围,即使在今天,这一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世界。然而,迪斯累里的努力有一个成果,就是获得了离巴勒斯坦海岸150英里远的塞浦路斯,作为英国保证土耳其亚洲领土完整的交换。1877年的俄土战争为此提供了机会,但为了避免谈论任何涉及巴尔干的战争,就让我们直接讨论结果吧。土耳其战败了,俄国占领了土耳其在欧洲的省份,于是大国召开了一次大会,限制俄国的战争果实。
结果是他从柏林会议上带回了“体面的和平”,这让他名声大噪。但想“解决”东方问题超出了迪斯累里的能力,也似乎超越了所有人力可及的范围,即使在今天,这一问题仍然在困扰着世界。然而,迪斯累里的努力有一个成果,就是获得了离巴勒斯坦海岸150英里远的塞浦路斯,作为英国保证土耳其亚洲领土完整的交换。1877年的俄土战争为此提供了机会,但为了避免谈论任何涉及巴尔干的战争,就让我们直接讨论结果吧。土耳其战败了,俄国占领了土耳其在欧洲的省份,于是大国召开了一次大会,限制俄国的战争果实。
为什么英国没有像从前那样支持土耳其?实际上,英国几乎就要参战了。这时仇俄情绪达到了巅峰。女王形容自己一想到俄国可能会进入君士坦丁堡,就“感觉焦虑得像生病了一样”。 [14] 对这件事,她表达了“极大的惊愕、恼怒和警觉,必须庄严地重复一遍:如果我们允许这件事发生,英格兰就不再是一个强国了!!”
伦敦的音乐厅里回荡着合唱声:
我们不想打仗,但如果一定要打,我们都是爱国猛士——
我们有战舰,我们有大炮。
我们也有钱——
俄国人绝对拿不走君士—坦丁—堡! [15]
所谓的“爱国猛士”都赞同参战。但内阁有分歧,国民也有分歧。此外,仇视土耳其人的心理也高涨起来。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暴行引发了众怒,至少自由党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是愤怒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土耳其公开结盟变得不可能。谁能抵挡得住极度兴奋的格拉德斯通先生的长篇大论?谁能抵挡得住描述保加利亚梦魇的宣传册?格拉德斯通咆哮道:土耳其人是“人类中最邪恶的反人类标本”,土耳其“那魔鬼般的纵欲,残暴的激情,腐败得无可救药的政治”使欧洲蒙羞。英国政府保护土耳其人统治的政策简直就是“在豁免其无穷无尽的暴行,满足其肆无忌惮的野蛮欲望”,就是在延续其“魔鬼般”的滥权,维持由“不可救药的罪人”组成的“令人憎恶的独裁”。让土耳其覆灭吧。让“那些土耳其军人和高官都滚出欧洲,带着他们的皮包和行李,从那些被他们破坏得荒凉、污秽的省份里滚出去吧”。连欧洲监狱中的囚犯和南太平洋诸岛的食人族,在听完土耳其的罪行后,都不能不感到愤慨。必须把土耳其人赶出被他们“浸满鲜血”的土地,只有这样才能让“气得发抖的世界”获得安慰。
显然,这个让食人族战栗的魔鬼不适合做英国的盟友。不过,当俄国舰队接近君士坦丁堡后,迪斯累里成功地压制了内阁中的反对派,派遣英国舰队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从印度调来增援部队,进驻远至马耳他岛的地方,并且召集预备役部队。在《笨拙》杂志的漫画中,迪斯累里和不列颠站在标示着“战争”的悬崖边上,迪斯累里要求不列颠继续向悬崖“再靠近一点”。 [16] 德比(Derby)勋爵与《笨拙》杂志持相同看法,并提出辞职。这让迪斯累里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任命外交大臣了,他选择了后来成为首相的索尔兹伯里勋爵。
在索尔兹伯里勋爵的构想下,英国签署了那份秘密协定,获得塞浦路斯,并承诺保护土耳其在亚洲的领土。在迪斯累里做首相前,他就已经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考古学家、时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莱亚德一起寻找“某块对英国有益的领土”,苏丹在极端情况下能接受劝诱,割让给英格兰。许多年前,在1840年的东方危机中,有读者给《泰晤士报》写信,建议吞并塞浦路斯和阿卡,作为对英国帮助苏丹从穆罕默德·阿里手里收回叙利亚的补偿。
 如今历史又提供了一次类似的机会,迪斯累里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机,”他在一封私信中说,“我们必须控制局势,甚至可以去创造局势。”
如今历史又提供了一次类似的机会,迪斯累里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机,”他在一封私信中说,“我们必须控制局势,甚至可以去创造局势。”

塞浦路斯是一个小地方,从未按照迪斯累里和索尔兹伯里的本意成为一个军事基地。对英国来说,这块地方的重要性在于让英国向巴勒斯坦又迈出了一大步。一位杰出的外交史学家
 认为,“迪斯累里可能认为如果英国得到塞浦路斯,那么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迟早会进入英国控制”。
认为,“迪斯累里可能认为如果英国得到塞浦路斯,那么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迟早会进入英国控制”。
这一步背后的理由由索尔兹伯里做了严肃且准确的说明。
索尔兹伯里在一封给莱亚德的信中发出警告,土耳其统治的地区对英国的安全极为关键,其中包括附近的苏伊士运河。如今土耳其政府几乎变成了俄国的附庸,其在亚洲维持地位的唯一办法就是与英国结盟。如果英国希望把俄国从去往印度的道路旁赶走,就必须与土耳其建立盟约。

“我们应该做出抉择,要么让俄国主导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 要么将之据为己有 ,无论选择为何,都是很艰难的。” [17]
我用斜体字记录下做出这个决策的历史性时刻,这个使理查一世因未能实现而在离开耶路撒冷之时遮住眼睛不愿看到的目标。这位蓄着黑胡须、穿着长礼服的索尔兹伯里,独自一人在外交部办公室里写下了上述这段话,他的钢笔在纸上划出的声音刺破了办公室的寂静。这个决策虽然当时没有付诸行动,但自此之后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但索尔兹伯里当时的建议不是上述两个,而是提出与土耳其建立防御同盟。“为此,英格兰必须比马耳他更加接近土耳其。”
 从马耳他到叙利亚海岸需要四天的航程,这“使高效、迅速的军事行动根本无法实现”。土耳其必须交出塞浦路斯,作为联盟的代价。联盟虽令人生厌,却是必需的。更少的承诺虽然能让自由党感到不那么受约束,但英国就会对中东失去控制。联盟是“在用英格兰的名誉做抵押”,所以“当关键时刻到来的时候”,不计代价保卫和平的党派就不能阻止政府采取行动,“国家的郑重承诺”是必须兑现的。
从马耳他到叙利亚海岸需要四天的航程,这“使高效、迅速的军事行动根本无法实现”。土耳其必须交出塞浦路斯,作为联盟的代价。联盟虽令人生厌,却是必需的。更少的承诺虽然能让自由党感到不那么受约束,但英国就会对中东失去控制。联盟是“在用英格兰的名誉做抵押”,所以“当关键时刻到来的时候”,不计代价保卫和平的党派就不能阻止政府采取行动,“国家的郑重承诺”是必须兑现的。
1878年6月4日,双方签署了《塞浦路斯协定》
 。英国承诺“用武力”抵御俄国“任何时候针对土耳其苏丹在亚洲的领土”的企图,并使苏丹将塞浦路斯“提供给英格兰占领和管治”。
。英国承诺“用武力”抵御俄国“任何时候针对土耳其苏丹在亚洲的领土”的企图,并使苏丹将塞浦路斯“提供给英格兰占领和管治”。
稳稳地拿着这份文件,迪斯累里和索尔兹伯里来到柏林,加入其他几个欧洲大国的行列,收紧国际套索,迫使俄国吐出打败土耳其后的非法所得。“那个老犹太人,他是个人物。”
 俾斯麦很不情愿地夸奖迪斯累里。在迪斯累里这边,他看到那位德国首相“一只手抓满了樱桃,另一只手抓满了虾,左一口右一口地吃着,抱怨他的失眠,抱怨他必须回基辛根(Kissingen)去”。
俾斯麦很不情愿地夸奖迪斯累里。在迪斯累里这边,他看到那位德国首相“一只手抓满了樱桃,另一只手抓满了虾,左一口右一口地吃着,抱怨他的失眠,抱怨他必须回基辛根(Kissingen)去”。
 当会议所有棘手问题都最终写成条约后,迪斯累里拿出《塞浦路斯协定》,整个欧洲都被惊呆了,但基本上是持欣赏的态度。
当会议所有棘手问题都最终写成条约后,迪斯累里拿出《塞浦路斯协定》,整个欧洲都被惊呆了,但基本上是持欣赏的态度。
 大家很难不为这个协定喝彩,这位年迈大师的大胆举措基本上恢复了英国在东方的威望。这份协定“给世界留下很深的印象,使英格兰的老朋友十分高兴”,
大家很难不为这个协定喝彩,这位年迈大师的大胆举措基本上恢复了英国在东方的威望。这份协定“给世界留下很深的印象,使英格兰的老朋友十分高兴”,
 维多利亚女王的好友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写道。女王欣喜若狂,赐迪斯累里公爵爵位。
维多利亚女王的好友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写道。女王欣喜若狂,赐迪斯累里公爵爵位。
但也有例外。俄国的戈尔恰科夫(Gortchakoff)亲王离开的时候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沮丧” [18] 。在英国国内,迪斯累里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自由党“怒吼说你犯了可怕的罪恶”,说协定违背宪法,威胁要解除协定。格拉德斯通大怒,抗议说即使是独裁者也做不出像迪斯累里所做的事,他逾越了大臣拥有的权限,秘密谈判是“欺骗行径”,迪斯累里答应了一个“不理智的协定”,过度地扩大了英国的责任。
遇到如此尖刻的攻击,迪斯累里的反驳值得记忆。他说如果有人失去理智,那也是“那个过度陶醉于自己三寸不烂之舌的诡辩家”
 。关于保证土耳其人在亚洲的领土安全问题,他回答说,最好是提前向野心家表明英国的底线,态度坚决地指出“绝不可逾越这条界限”。这就是《塞浦路斯协定》所做的,这样做没错,他将坚守这份协定。尽管格拉德斯通的雄辩给予他巨大的压力,但他获得了议会的支持,协定被通过了。后来,协定发挥了预期的效果。俄国不仅停止通过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向地中海扩张,也停止了通过小亚细亚向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扩张。迪斯累里的传记作者巴克尔(Buckle)先生高兴地在1920年写道,俄国人的这些行动“显然停止了,此后再也没有依靠武力重新启动”
[19]
。然而,时间来到1955年,情况有所改变。
。关于保证土耳其人在亚洲的领土安全问题,他回答说,最好是提前向野心家表明英国的底线,态度坚决地指出“绝不可逾越这条界限”。这就是《塞浦路斯协定》所做的,这样做没错,他将坚守这份协定。尽管格拉德斯通的雄辩给予他巨大的压力,但他获得了议会的支持,协定被通过了。后来,协定发挥了预期的效果。俄国不仅停止通过土耳其的欧洲领土向地中海扩张,也停止了通过小亚细亚向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扩张。迪斯累里的传记作者巴克尔(Buckle)先生高兴地在1920年写道,俄国人的这些行动“显然停止了,此后再也没有依靠武力重新启动”
[19]
。然而,时间来到1955年,情况有所改变。
就19世纪而言,俄国很快就不再是大英帝国的严重威胁了。格拉德斯通给德国开了绿灯,取代了俄国。他极害怕帝国的承诺,在1880年上台后马上就致力于废除《塞浦路斯协定》,虽然被英国议会挫败了,但他嫌恶土耳其的一切,因此割断了英国与土耳其的所有联系。他从君士坦丁堡召回了莱亚德,这使得英国彻底失去了对土耳其宫廷的影响力,被疏离的土耳其则投入了等在一旁的德皇的怀抱。此刻德皇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已经盯在了他从柏林至巴格达的帝国之路上。
此时,迪斯累里已死,但巴勒斯坦已进入英国的势力范围。
[注释]
[1] Cromer’s Ancient and Modern Imperialism , p. 20.
[2] Ibid. , p. 20.
[3] S. H. Jeyes, Joseph Chamberlain , London, 1896, p. 245.
[4] Question of Empire , London, 1900.
[5] W. T. Stead, Review of Reviews , January 15, 1891.
[6] From Liberalism and Empire , London, 1890. (Three anti-imperialist essays.)
[7] Martin’s Prince Consort , I, 215; Temperley’s Near East , pp. 255-57.
[8] Expansion of England , p. 10.
[9] Temperley’s Near East , chap. XI. For Crimean War, see also Cambridge BFP , Vol. II, chap. VIII and Marriott, pp. 249-85.
[10] Guedalla’s Palmerston .
[11] Cambridge BFP . Also Seton-Watson.
[12] DNB .
[13]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 II, 428.
[14] Letter to Disraeli, July 15, 1877, Queen ’ s Letters , 2d series, II, 548.
[15] Disraeli by D. L. Murray, Boston, 1927, p. 268.
[16] Mr. Punch ’ s History , Vol. III.
[17] Letter to Layard, May 10, 1878, Temperley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
[18] Letter from Crown Princess Frederick of Prussia (Queen Victoria’s daughter) to the Queen, July 16, 1878, Ibid .
[19] Ibid. , VI, 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