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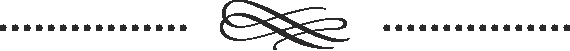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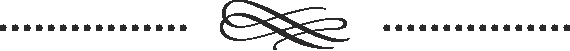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1862年,威尔士亲王去了一趟圣地 [1] ,他就是未来的爱德华七世,这是自英王爱德华一世在1270年率十字军东征之后,英国王储第一次踏足巴勒斯坦。就在同一年,摩西·赫斯宣称犹太复国的“钟声敲响了”。虽然这两件事毫无关联,但说明历史正在把流亡者和中间人推到一起。爱德华的这次旅程包括希伯伦的清真寺,这里的列祖墓如今已经变成穆斯林圣地。他此行突破了不许基督徒进入圣所的规定,“可以说为基督徒研究叙利亚全境打开了大门”。这番话取自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制订的计划书,该基金会是在亲王这次旅行之后三年建立的,圣地从此对现代考古学、现代地图勘察和绘制开放了。
没有什么能比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更能体现英国人的两面性——这个基金会虽然为了《圣经》的研究而建立,但所有工作都由陆军部派遣的军官完成。克劳德·康德(Claude Conder)上校是最知名的野外工作人员,据说他对《圣经》知识的贡献之多,自廷代尔翻译《圣经》之后无人能比
 。他绘制的地图由陆军军械部出版,1918年耶路撒冷之战的胜利者艾伦比将军就使用了他绘制的地图。在这里“圣经”与“利剑”再一次结合了。事实上,康德上校是英国人在巴勒斯坦活动的缩影,总是带着对《圣经》的怀旧和帝国扩张的利剑,就好像是两次曝光的底片——可以分辨出有两张照片,但又无法分开。
。他绘制的地图由陆军军械部出版,1918年耶路撒冷之战的胜利者艾伦比将军就使用了他绘制的地图。在这里“圣经”与“利剑”再一次结合了。事实上,康德上校是英国人在巴勒斯坦活动的缩影,总是带着对《圣经》的怀旧和帝国扩张的利剑,就好像是两次曝光的底片——可以分辨出有两张照片,但又无法分开。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野外工作人员,在长达数年的调查和发掘过程中,逐渐揭示出了巴勒斯坦高度文明的过去,但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卷入这个国家的前途之中。康德上校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不必期待本地犹太人能对巴勒斯坦的复兴提供多大帮助,“他们仍然被犹太法典束缚着……他们对过去的崇拜似乎阻止了他们前进或改善现状的可能” [2] 。推动力和人力主要来自东欧,康德上校说,如果他们能在沙皇统治下生存,他们就能在苏丹统治下生存并繁荣。他的同事查尔斯·沃伦(Charles Warren)爵士也是一个多次参加探险基金会远征的老兵,他更进一步提出巴勒斯坦可以交给东印度公司开发,但这家公司要“承诺逐步引进朴素的犹太人,最终让犹太人占据和管理那个国家”。他给自己的书取名为《应许之地》( The Land of Promise ),并坚持认为在良好的政府管理和更繁荣的商业情况下,人口能增加十倍,“而且还有发展空间”。根据他的预计,土地生产率“将会提高,其幅度与投入的劳动力成正比,最后人口能达到1500万”。沃伦的书在1875年面世,这时乔治·艾略特正在写《丹尼尔·德龙达》,而维也纳的《黎明》杂志正在呼吁重建犹太人的国家。
此时英国的主要兴趣仍然是《圣经》,但非常不同于沙夫茨伯里的兴趣,实际上正好相反。当时“不敬神的理性主义”已经战胜了福音主义,但随之而来的是《圣经》变成了一份充满火药味的文件,圣地变成古罗马城市广场一样的斗争舞台。理性主义的战士决心证明《圣经》是历史,冲进圣地希望能找到必要的证据。他们拒绝承认《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所以《圣经》也可能有错,这等于说他们也否定了预言。但以色列复国没有顺着这一股新潮流漂走,因为他们在历史研究中重新发现了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教士亨利·哈特·米尔曼(Henry Hart Milman)的《犹太人历史》( History of the Jews ,注意,不是希伯来人历史,不是以色列人历史,也不是“上帝选民历史”),成为高等圣经批判(Higher Criticism)的先驱。当有人发现他称亚伯拉罕是酋长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米尔曼去世时是圣保罗教堂的主持牧师,有名望而受人尊敬,但当他的书1829年面世时,被认为几乎是在侮辱一个民族。
米尔曼坚持说,犹太人的历史是有待发掘的史实,并非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不能因为它与神的启示有关就不许进行科学研究。恰恰相反,犹太人历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他说,犹太人在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发挥的作用是“如此的重要和持久”,所以信奉基督的历史学家有责任研究他们的历史,因为这才是获得最高等级的宗教真理的唯一可靠途径。古代希伯来人是人类的一部分,说人类的语言,有能听人声的耳朵,总之(后面跟着的句子让读者愤怒)“亚伯拉罕有自己的信仰,与至高无上的上帝有过交流,但他不过就是一个游牧民族的酋长而已”。而他的这句话打击力更大:摩西劈开红海的奇迹其实就是一场暴风雨,跟英吉利海峡上那场恰逢其时摧毁西班牙舰队的暴风雨差不多。
柯勒律治(Coleridge)的风格也很相似,他发现耶稣是个“柏拉图式哲学家”。他是哥廷根大学的学生,这所大学的德国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大举对《圣经》进行批判。他刚从这所大学毕业就宣称,那种视《圣经》的一字一句皆为真理的态度,实际上比“那种视教皇的一字一句皆为真理的态度更加过分”。他通过文章和闲谈极大地激起了研究热情。神职人员开始担忧起来,特别是在1832年通过了标志着自由党大捷的《第一改革法案》后,他们被彻底吓坏了。自由的环境威胁教会的权威。1833年,教会开始反击,启动了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再次强调信仰。这是一次绝望之举,目的是在理性主义的攻势下加强宗教启示的防御能力。基布尔(Keble)展开了著名的巡回布道。 [3] 同年,他与纽曼(Newman)和皮由兹(Pusey)出版了《时代书册》( Tracts for the Times )。《摩西五经》的作者是谁?《但以理书》可信吗?如何从道德角度看待大卫的恶劣举止和雅各的阴谋?思考这些令人恼怒的问题得需要多少热情和知识啊!纽曼认为,提出这些问题的人都是异教徒;基布尔断定只有卑鄙的人才会通过提问破坏《圣经》的神性;皮由兹甚至去德国学习历史方法,这样才能更好地打败它,他在被聘为牛津大学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后,每周授课九次,全面地向神学系学生讲解《旧约》语言惯用法知识,以便让他们更好地理解上帝的圣谕。 [4]
但从长远看,这一切都是无用的。《时代书册》基本上是被动之举,是反时代的,这些小册子是战胜不了时代潮流的。纽曼在1845年投向天主教(曼宁紧随其后)是很自然的事。他认为信仰需要不可置疑的权威。当《圣经》不再永远正确,罗马就成为唯一的避难所。基布尔和皮由兹继续抗争,在纽曼放弃后坚持牛津运动。甚至到1860年,合写《文章和评论》( Essays and Reviews )——理性主义者反驳《圣经》权威的著名文章集——的七位作者中的两位,竟然被以散布异端罪审判。 [5] 这个问题引发社会各界激烈争论了几年,最后枢密院在1864年判决两人无罪,这标志着旧秩序的完结——那旧秩序曾经被清教徒统治过,又被福音主义者复兴过,并在牛津运动中唱出最后的天鹅之歌。
就在这个时候,理性主义者们马不停蹄地飞驰在前往巴勒斯坦的道路上,去获取犹太教和犹太人作为基督教之源的新证据。斯坦利(Stanley)是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他在牛津大学开设的教会史课程以“亚伯拉罕的呼唤”作为第一讲。不用说,他肯定会亲自去当地看看。在圣地游历了两年后,他出版了《西奈和巴勒斯坦》(1857)。巴勒斯坦,他写道,是“人类史上最重要事件的现场”。在这里,上帝直接晓谕犹太人。只有在这里,才能对塑造“地球上最非凡民族”的精神之地进行独立研究。在这里,旅行者看到的沙漠里的灌木丛就是以利亚曾经休息的地方。在毗斯迦山上看到的景象,就是摩西曾经看到过的。在四处看到的地理特征,“都成为基督世界家喻户晓的图画”。在这里,确实能找到《圣经》活生生的证据。
在1862年爱德华王子访问期间,斯坦利再次回到巴勒斯坦,担任爱德华王子的牧师兼向导。作为对他探求历史的热情的回报,他被允许进入自1187年之后就没有欧洲人踏足过的希伯伦列祖墓参观。“当亚伯拉罕圣殿的大门打开的时候,参观者中传来低沉的呻吟声,而在雅各和约瑟的神殿里呻吟声成倍增加
 。当我把手臂深深地探入石墓,跪在地上仔细查看亚伯拉罕的坟墓被埋入山体多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斯坦利感谢王子让他有机会看到列祖墓,王子回答说:“你看,地位高是有些好处的。”
。当我把手臂深深地探入石墓,跪在地上仔细查看亚伯拉罕的坟墓被埋入山体多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心情。”斯坦利感谢王子让他有机会看到列祖墓,王子回答说:“你看,地位高是有些好处的。”
三年后,斯坦利的《犹太教会史》更加深入地揭示了基督教的犹太渊源,后来史密斯(W. R. Smith)对这个主题做了进一步挖掘。史密斯是《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九版的编辑,撰写了其中有关《圣经》的条目。他扩展了他在《犹太教会中的旧约》和《以色列先知》中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与此同时,斯坦利在牛津大学的朋友、《文章和评论》的作者之一、伟大的乔伊特(Jowett),也提出犹太先知是我们文明的“初级教育阶段的老师”。“他们教导人们上帝的真正品性,上帝是爱,上帝是正义,上帝不仅是人类的父亲,也是人类的审判者。”乔伊特说,我们的知识体系是希腊哲学家创造的,而我们的道德情感来自犹太先知。
如果这听上去很像马修·阿诺德的话,其相似性并非偶然。阿诺德在那个激动人心的1860年代同样也是牛津大学教授(诗歌方面);同事中有乔伊特——钦定希腊语教授,皮由兹——钦定希伯来语教授。这两个人是死对头,难怪阿诺德在这样的环境里选择的论题是“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我们这个世界就在这两种文化确立的两点之间来回摆荡。阿诺德提高了我们对英国文化中希伯来文化影响的认知,随后米尔曼和斯坦利才把基督教视为“改良后的希伯来文化”。所有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宗教痴迷和由此引发的口诛笔伐,都包含在阿诺德在接下来的五年里写作的几本书中:《圣保罗和新教》、《文学和教义》和《上帝和圣经》。他给《文学和教义》所加的副标题是“一篇有关如何更好地理解《圣经》的文章”。他写《上帝和圣经》是为了反驳批评家对他前一本书的批评。
在这百家争鸣之中,还能听到理性主义信徒那充满激情且洪亮的声音。莱基痛恨神学的教条,他因此而去赞美神学教条的所有受害者,特别是犹太人。在论及宗教审判这个问题时,他说:“在这个殉教的民族面前,其他宗教的英雄人物都会黯然失色,变得毫无意义。13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勇敢面对最疯狂者设想出的邪恶,忍受着最丑恶的惩罚,但依然不放弃信仰……对犹太人的迫害具有最恐怖的形式……但这个充满才智的伟大民族仍然高高地耸立着。”莱基的散文在描绘犹太人追求知识的过程时达到了情绪高潮,他说犹太人高举希腊人的知识,熬过阿拉伯人的占领,这才使知识的火焰在欧洲再次燃起。而基督世界的知识分子则“在愚昧无知的黑暗中摸索”,热衷于“杂耍中的奇迹和谎言中的遗物”。伟大的19世纪历史学家一点也不“客观”,他们在表达观点的时候毫无顾忌。
莱基的《理性主义史》在1865年出版,同年出版的还有斯坦利的《犹太教会史》,而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也于同一年成立,这是用新方法研究圣地的直接结果。请注意,仅一年前,法官在那起异端案件中已经判定,神职人员认为《圣经》的作者是人而不是上帝并不触犯法律。思想阻碍破除了。《圣经》这本书是有自己的真实历史的,书中谈到的民族是真实的,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赋予自己的任务就是去重新发现这些真实的历史。列入基金会计划的不仅有巴勒斯坦的考古学,还有地形学、气象学、植物学等,差不多所有的学科都包括在内了。基金会在募捐时公布了其运作的三个原则:野外工作要按照科学原则进行;基金会要避免宗教争执;基金会不能按宗教社团方式运作。牛津大学自然捐助最多,共500英镑,剑桥大学250英镑,叙利亚改进委员会250英镑,女王150英镑,共济会总部105英镑。

奇怪的是,虽然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建立在理性的探究精神之上,但原始动机却来自福音主义者芬恩和他在耶路撒冷的几位朋友。他们为研究本地的“古迹”建立了一个耶路撒冷文学会。 [6] 这个学会很快就成为研究《圣经》的历史学家的中心。那些年,这些历史学家如同一群兴奋的猎犬,冲向年代久远的遗迹,“我们信奉的经文就在那个时候写成”。本地会员在外出做了一些挖掘工作后,收集到了足够多的文物,开办了一个小型博物馆。他们还建立了一个图书馆,收集了上千卷书籍。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赞助人。阿尔伯特亲王寄来了25英镑。博学的外国人和著名的考古学家成为学会的通讯会员。一些杰出的访客还来参加学会的会议——包括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霍尔曼·亨特(Holman Hunt)、斯坦利、雷赛布(de Lesseps),以及尼尼微的发现者莱亚德(Layard)。
在这些手忙脚乱的发掘之后,人们才认识到发掘巴勒斯坦的过去是一项巨大的任务。协调和专业必须取代狂热和业余。
1864年,陆军部接受建议,计划派一个工兵军官(但不提供经费)去勘察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区。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爵士自告奋勇,他的工作成果构成了于次年成立的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第一份出版物(包括一份地中海和死海海拔高差的地势图)。 [7] 后来,威尔逊又前往贝鲁特和希伯伦地区进行勘察。他曾经指挥赴苏丹营救戈登将军的远征行动,但营救行动失败了。许多年之后,在他退伍后,他于1899年和1903年两次回到巴勒斯坦,对存有争议的各各他和圣墓的位置进行了定位。
在威尔逊之后,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又派出了查尔斯·沃伦,他的研究结论是巴勒斯坦这片土地能像过去一样再次硕果累累。这个结论引自他已经出版的《应许之地》。1872年,两名二十几岁的皇家工兵在最广泛的地理范围上展开了基础性的勘察工作,他们是克劳德·康德中尉和注定将在另一个领域里获得更大声誉的基钦纳(Kitchener)中尉。基钦纳勘察了东巴勒斯坦;康德去了约旦河以西的地区,三年内绘制了4700平方英里的地图。他给《圣经》中150个还不知道位置的地名做了定位,绘制了十二支派的统治范围图,追踪了军队和移民的路线图,破译了古代经文。回到英国后,他和基钦纳又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准备出版所需的材料。历史方面的发现刊登在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七卷本的《回忆录》里,自1880年开始出版;地图由军械部的勘察办公室印制。康德出版了自己的记述,书名叫《在巴勒斯坦帐篷下的工作》( Tent Work in Palestine ),书中包含他自己的手绘图。他后来多次回到圣地。在他的余生里,除了参加在埃及和南非的军事任务之外,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在发掘圣地和犹太民族还不为人知的历史上。1882年,他被选为乔治亲王去圣地旅行的向导,就好像斯坦利在20年前给爱德华做向导一样。乔治亲王就是后来的英王乔治五世。
康德知识渊博,有探索精神,富于创新,他的兴趣很广泛,文章写得很活泼。他能说写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并精通古代楔形文字。他翻译了阿玛尔纳泥板文字(Tel-Amarna tablets),这些泥板出土于巴勒斯坦的前希伯来时代,是了解那个时代的一手材料。每到一处,他都能追溯往昔,从十字军东征年代一直追溯到《圣经》年代,讲解从穆斯林到拜占庭、罗马、亚述的年代。他可以在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医学、农学、艺术、建筑、文学和神学等学科发表权威的论述。教义是否正确,他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深入挖掘宗教外表之下的历史情况。他不屑在圣墓前俯首,而是称之为“阴暗且邪恶的古老建筑”,因为人类为它遭受的磨难和流淌的鲜血比为世界上任何其他建筑都要多。在不为康德单写一章的情况下,把他的部分著作罗列一下就是他工作的最好摘要:《犹大·马加比和犹太独立战争》(1879)、《圣经地理基础》(1883)、《叙利亚人的石头传说》(1886)、《迦南人》(1887)、《巴勒斯坦》(1891)、《圣经在东方》(1896)、《耶路撒冷拉丁王朝》(1897)、《赫梯人及其语言》(1898)、《希伯来人的悲剧》(1900)和《耶路撒冷城》(1909)。他于最后一本书写成的次年逝世。
除了这些作品之外,他还帮助查尔斯·威尔逊收集和编辑为巴勒斯坦朝圣者文本协会提供的材料,这个协会是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分支机构。材料收集范围包括从公元4世纪至15世纪世界各地朝圣者对巴勒斯坦的记述,这些材料的翻译工作花费了11年的时间,最后分12卷出版。
当康德在书中讨论通过犹太人殖民复兴巴勒斯坦时,他给这个问题带来了一个真正了解那片土地的人所具有的操作层面的常识。他坦白地说:“从但到贝尔谢巴根本没有人铺成的道路。” [8] 这句话足够让世界理解让巴勒斯坦再次变成可居住的地方而必须付出的艰苦努力。康德说,道路上能跑有轮子的车,这是第一要务。他还指出,殖民计划必须还包括如下工作:灌溉和湿地排水道、沟渠和蓄水池的重建、公共卫生设施、铺草地和重新造林以阻止土壤受侵蚀。
在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出版研究成果之前,有实践经验的人几乎都不认为那片土地真的能够复兴。基金会用事实说明巴勒斯坦曾经养活过相当庞大的人口,文明程度比公众想象的还要先进,所以那片土地可以再次繁荣起来。这是基金会的伟大贡献(除了其在历史方面的发现之外)。当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巴勒斯坦是一片荒地,正如以赛亚所预言的,“是大龙和野鸟的居所”。荒凉的土地给人错误的印象,似乎这片土地自《圣经》时代就贫瘠得养不活普通百姓。但在掩盖真相的表面现象被逐渐抹去之后,昔日辉煌显示出来了。浮现出来的不仅是城市的概貌,还有圣殿的轮廓、葡萄园的外观、王国和道路、市场和集市,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是一个“有稳定机构、神职人员、国王、官员、学校、文学、诗歌”的文明。田地里曾经种满谷物,即便以沙漠为主的内盖夫(Negeb)在拜占庭时代也有六座人口在5000至10000之间的镇子,镇子之间还有许多小型村落。考古学家发现这片土地并没有受诅咒。之所以后来衰败荒凉,原因很简单——缺少耕作。阿拉伯征服者一举横扫了拜占庭文明,“就如同蝗灾扫荡了玉米田”,最后只留下贝都因人和羊。
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研究工作的意义不久之后就被巴勒斯坦事业的热心支持者沙夫茨伯里伯爵发现了。在基金会成立十周年时,他成为基金会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在表述对以色列的希望时比任何人都更雄辩。“我们不能再等待了,”他在就职讲演时对基金会成员说,“必须马上派最优秀的人……去搜索、去勘察。如果可能,去所有角落看看,为土地排水、丈量,为其古代拥有者的回归做准备,因为我确信这个伟大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9]
“我记得,当阿伯丁做首相的时候,我跟他说起圣地的事,他对我说:‘如果要使圣地脱离土耳其人之手,应该把它交给谁?’我回答:‘除了以色列人还能给谁呢?’”
沙夫茨伯里伯爵非常清楚,他的听众并不会完全同意,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只对以色列的过去感兴趣,而并不关心其未来。(听众中有个著名的怪人伯顿上尉,他是阿拉伯探险者,翻译了《一千零一夜》,他对犹太人的看法极不友好。他在沙夫茨伯里伯爵之后发言,他的观点是“欧洲的犹太人”不会太乐意“打开自己的荷包为犹太地区花钱”。很遗憾,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沙夫茨伯里作为坚定的福音主义者,坚决不接受科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警告。他告诉听众,英格兰到处都有人跟他一样“胸中燃烧着对这片土地[巴勒斯坦]的爱”,未来的复兴应该跟重新发现过去一样重要。对这个问题他总结说:“我的老年并不比年轻时更平淡。”
他的老年显然不是平淡的。1876年,距离他在《评论季刊》发表那篇文章接近40年之际,他又写了一篇文章。他对福音主义的热情仍然高涨,他谈及自己从犹太民族主义在这段时间的崛起中所学到的东西,也许这极好地表达了英国在复兴巴勒斯坦上所发挥的作用: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很快就会变得极为重要。古代的时光要回来了……这个国家需要资本和人口。犹太人能提供这两者。难道英格兰对这样的复兴没有特殊的兴趣吗?……英格兰必须把叙利亚留给自己。如果英格兰需要制定某种政策,难道不该制定扶植犹太民族,协助他们寻找机会返回并重建其古老家园的政策吗?英格兰是世界上伟大的海上贸易强国。对英格兰来说,自然应在安置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作用……犹太人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性,他们的民族精神已经存在了三千年,但其外部形式即整个民族的团聚仍未实现。一个民族必须有一块国土。古老的土地,古老的民族。这不是一项人为的实验,而是天理,是历史。

[注释]
[1] P.E.F., Quarterly Reports . Also Prothero’s Stanley .
[2] Tent Work .
[3] Sermons, Academical and Occasional , Oxford, p. 127.
[4] Cambridge Lit. , XII, chap. XII.
[5] Ibid. , chap. XIII.
[6] Ibid .
[7]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Sinai , P.E.F., 1869.
[8] Tent Work .
[9] P.E.F., Quarterly Report , 1875, p. 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