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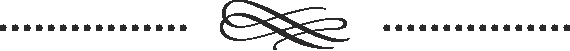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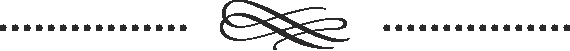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阿什利的努力没有白费。他计划的核心是符合政治逻辑的,尽管他想看到的形式完全不合理。他的计划搅动了英国公众的情绪,人们逐渐意识到英国对中东的影响力是战略优势。围绕着圣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大事——拿破仑的远征,纳尔逊在尼罗河的胜利,不时被英国海军的炮声打断但仍然不失其传奇本色的穆罕默德·阿里的兴衰史,帕麦斯顿在叙利亚危机中的迅捷胜利,福音主义者疯狂地想让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和想在耶路撒冷建立主教区的愿景——这些大事交织在一起,使英国人对巴勒斯坦产生了一种私密的感情。阿什利曾想通过英国主导的以色列复国吞并那块土地,这个想法开始吸引其他人。追随他的人,一致强调他提出的战略理由,但他提出这些战略理由并非真心实意,而仅是对那个古老宗教理由的补充。
在阿什利的后继者中,最有远见和智慧的人是查尔斯·亨利·丘吉尔(Charles Henry Churchill)上校,他是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温斯顿·丘吉尔的先祖)的孙子。他在推翻穆罕默德的那支军队中担任军官。他驻扎在大马士革期间发生了血祭案件,蒙蒂菲奥里也正好在该地访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丘吉尔被阿什利的想法所吸引。就是丘吉尔,在蒙蒂菲奥里的指派下,把土耳其苏丹在1840年颁布的勒令交给了大马士革的犹太人。
 为酬谢丘吉尔在那个恐怖之年里对犹太人的帮助,大马士革的犹太人为他举办了一次宴会,向他和14名刚从监狱里释放的受到血腥指控的受害者致敬。他在会场所做的发言以及他稍后给蒙蒂菲奥里写的一封信,表明他的观点已经脱离了福音主义者的空泛废话,变得更加实际。他对犹太人返回家园的支持似乎是为了犹太人本身,而不是为《圣经》中的预言。他丝毫没有提及犹太复国的先决条件是皈依或皈依是返回锡安山的必然结果。他对大马士革的听众说,他认为以色列解放的时刻即将到来,那时犹太国能重新成为万邦之中的一员。他补充说,英国是唯一支持以色列人这一愿望的国家。
为酬谢丘吉尔在那个恐怖之年里对犹太人的帮助,大马士革的犹太人为他举办了一次宴会,向他和14名刚从监狱里释放的受到血腥指控的受害者致敬。他在会场所做的发言以及他稍后给蒙蒂菲奥里写的一封信,表明他的观点已经脱离了福音主义者的空泛废话,变得更加实际。他对犹太人返回家园的支持似乎是为了犹太人本身,而不是为《圣经》中的预言。他丝毫没有提及犹太复国的先决条件是皈依或皈依是返回锡安山的必然结果。他对大马士革的听众说,他认为以色列解放的时刻即将到来,那时犹太国能重新成为万邦之中的一员。他补充说,英国是唯一支持以色列人这一愿望的国家。
1841年6月14日,他在给蒙蒂菲奥里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一个当时没有人提出过的观点:“应该让犹太人做发起人。”
“我无法在你面前掩饰,”他写道,“我极渴望看到你的同胞再次努力屹立于民族之林。我认为这个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但有两点必须考虑:第一,全体犹太人必须达成一致并主动行动;第二,欧洲列强要支持他们。”
接着他谈起另一件大是大非的问题:英国支持土耳其帝国的政策是重大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19世纪中困扰着英国的外交。丘吉尔预言,这样的努力注定要遭到“痛苦的失败”。必须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从土耳其人和埃及人“愚蠢、衰老的独裁统治下”解救出来,置于欧洲人的保护之下。当这一天到来之际,犹太人应该做好准备并能说:“我们早就是个民族了。”他“强烈地要求”蒙蒂菲奥里做犹太人代表委员会(Jewish Board of Deputies)
 的主席、伦敦西班牙系犹太人总督,马上展开这场“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光荣战斗”。他还鼓动犹太代表们去召集会议,递交请愿书,激起公众的热情。
的主席、伦敦西班牙系犹太人总督,马上展开这场“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光荣战斗”。他还鼓动犹太代表们去召集会议,递交请愿书,激起公众的热情。
在一年之后的第二封信中,他吸纳了阿什利的观点,建议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犹太人向英国政府请愿,请求英国政府任命一个驻叙利亚特派员,保护叙利亚犹太人的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并在“大英帝国的赞助和支持下”鼓励殖民。
这样的行动犹太代表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如果遇到像大马士革那样的事件,他们能够为受难的犹太人奔走。但他们过于关注在国内的公民权利斗争,而难以顾及远方的犹太民族。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犹太人获得更多自由后,自然就更想不起去建立某种形式的国家了(显然有几个例外情况)。但这个故事不是本书要讲的。1842年,甚至蒙蒂菲奥里也无法打动犹太人,他们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委员会“没能采取任何措施实现丘吉尔上校提出的好观点”表示遗憾。他们还说,东欧的犹太人和近东的犹太人要先提出自己的要求,然后英国的犹太人才可能冒险采取支持性的步骤。丘吉尔回复说,他们可以“对国家复兴这个如此有趣和重要的问题,力求查明欧洲其他地方犹太人的感情和意愿”。 [1] 但没有证据表明这项建议被提交给了董事会。根据记录,剩下的只有沉默。
西方的犹太人不愿听取意见,东方的犹太人委身于贫民窟中听不到外面的意见,而丘吉尔无法对外交大臣进言,也没有阿什利在饭桌上影响国家政策的机会。实际上,在阿什利和帕麦斯顿1840年的行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除阿什利自己外,没有政府高层人士再提出过犹太人返回家园。而作为沙夫茨伯里伯爵,阿什利又继续跨越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诸多顶点将近50年时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还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给出了最精确的表述。
 他一直与帕麦斯顿保持密切关系,帕麦斯顿很快又回到外交部的岗位,随后又担任了10年首相。但他们都为其他大事所困扰,没有能在犹太人问题上有所作为。无论如何,福音主义者劝化犹太人的努力的全盛期就此结束了,因为沙夫茨伯里的特殊动机已经过时了。
他一直与帕麦斯顿保持密切关系,帕麦斯顿很快又回到外交部的岗位,随后又担任了10年首相。但他们都为其他大事所困扰,没有能在犹太人问题上有所作为。无论如何,福音主义者劝化犹太人的努力的全盛期就此结束了,因为沙夫茨伯里的特殊动机已经过时了。
后来,拥护以色列复国的人更加关心大英帝国向东扩张的问题,而不是精神向上提升的问题。“每个英国人必须清楚,”丘吉尔上校在他的《黎巴嫩山》( Mount Lebanon )中写道:“如果英格兰在东方的霸权想要维持的话,必须使叙利亚和埃及或多或少要受制于英国的影响力。”这本书是他在中东15年生活的结晶,于1853年出版,次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像往常一样,东方发出的隆隆炮声都被视为土耳其帝国的丧钟。当巴勒斯坦不再属于土耳其的时候,按照丘吉尔的预计(虽然他是正确的,但为时尚早),巴勒斯坦要么属于英国,要么成为独立的国家。这个前景使他爆发出一阵像阿什利一样的文采:“这片土地是雅各展现力量、以实玛利漫游其上的土地,是大卫弹琴作诗、以赛亚雄辩滔滔的土地,是拥有亚伯拉罕的信仰和以马内利之爱的土地——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上帝开始了与人的神秘交往,在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后,上帝和人有了约定——这片土地也引起英格兰不眠的警惕和怜悯的关照,已经得到了英格兰之盾的保护。”
他并非是唯一表示要拿着羊皮盾去巴勒斯坦完成使命的人,任何从伟大的东方旅程回来的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1844年,所有人都在阅读沃伯顿的《新月和十字架》,这本书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再版了17次。这本书概述了几代人去圣地朝圣的经历,作者称之为“某种视巴勒斯坦为祖国的爱”。他是个善于观察的旅行者,听到儿时就记住的地名所唤起的激动情绪,以及“在天使面前接受亚伯拉罕的酋长的款待”的激动情绪,都没能使他忽视一个事实,即亚伯拉罕的足迹是通往印度的最短途径。当谈论到十字军东征没能建立落脚点时,他评论道:“为了印度的利益,我们也许会完成为耶稣圣墓征战时没有达成的使命。”他承认这个问题“很复杂”,然后便去谈论其他问题了,直到后来才返回讨论。他报告说,他所到之处,都遇到了期望英国返回东方的人。当那个疯狂的老帕夏穆罕默德·阿里死后,英国不应该允许埃及恢复到“愚蠢的土耳其独裁统治之下”。英国要“大胆地索要”穿越埃及去印度的道路权,使埃及的经济复苏,给人民以“自由”——当英国作者使用时,这个词表示摆脱土耳其的统治。
沃伯顿没有注意到犹太人是英格兰帝国主义的先锋。在这点上,他的前辈林赛反而看得更清楚一些。阿什利受林赛著作的启发,写出了《评论季刊》上的那篇开创性的文章。就在林赛跟着“以色列人的脚步走向应许之地”的时候,就在他“面对着红海”再次阅读犹太人过红海感受到那种“奇怪但令人战栗的快乐”的时候,就在他在沙漠里宿营,“想着雅亿和西西拉”砸着帐篷桩的时候,上帝选民的前途开始占据了他的思维。他相信周围的荒凉是必然的,不是这片土地遭受了诅咒的缘故,而是为了“赶走居民”。他相信这是天意,就是为了让“现代的居民不能人数太多”,以免影响“合法的继承者返回”。在他看来,“这片曾经肥沃的土地,正等待着那些被流放的子孙,这些子孙会用与他们农业生产能力相符的勤劳,使这片土地重获繁荣,就跟所罗门王在世时一样”。
弗朗西斯·埃杰顿(Francis Egerton)女士是另一位勇于冒险的旅行者,她发现自己对上帝选中的古老民族的生活条件非常好奇,因为她看农村里的每个人都像是摩西和以利亚再世。在耶路撒冷,她探访犹太家庭和犹太人集会,向伦敦来的传教士询问情况,讨论大马士革发生的迫害事件和犹太复国的各种理论。她不断地感受到眼前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有某种非凡的事要发生,大约是与犹太人返回锡安山的预言有关,这种感受在那个时期被许多旅行书提及。埃杰顿女士将其归结为人们普遍盼望奥斯曼帝国衰败的结果,她相信随之而来的巴勒斯坦权力真空将会被犹太复国填补。但她发现英国流行着虚幻的印象,觉得犹太人正大批地涌回祖国。她认为,在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之前,绝对无法返回故里。她的书,按照她自己的说法仅是私人日记,但她的朋友诚恳地请求她为了爱尔兰女子学校协会出版,这本书终于在1841年付梓。假惺惺的本森男爵也把这本书摆上了他的床头桌;当他拜访太后时,他一边展示一边说:“一群身份恰当的英国绅士簇拥着一位高雅和友好的女王。” [2]
1840年代有关土耳其就要灭亡的报道被事实证明言过其实了。土耳其又昏昏沉沉度过70多年后才寿终正寝。但当时大家都觉得圣地该易主了。有什么能比新房东老房客这种搭配更方便和自然呢?这个想法出现在形形色色的英国人头脑里。“奥斯曼帝国将被取代,古代的商业航线将会重新开放。”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Clarke) [3] 博士在他的一本名叫《印度和巴勒斯坦:从通往印度的最短路径看犹太复国》( India & Palestine: 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s Viewed in Relation to the Nearest Route to India )的专著中写道。
“犹太人,”他继续写道,“基本上是从事贸易的民族。把他们安置在贸易大道的旁边不是很自然吗?谁能比他们更有技能做东西方直接的中介呢?……只有把叙利亚放在一个勇敢的、独立的、有信仰、有高昂的民族自豪感的民族手里才是安全的……犹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民族……恢复他们的民族性,恢复他们的国家,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大国能夺走他们的国家。”
另一本类似的小册子《时代之书:为犹太人呼吁》( A Tract for the Times, being a Plea for the Jews )于1844年出版,作者是教士塞缪尔·布拉德肖(Samuel A. Bradshaw) [4] 。他建议英国议会批准400万英镑预算,教会应该收集100万英镑,用于以色列复国。同年,一个委员会在伦敦成立了,其目的是形成一个“英国和外国共同推进犹太民族返回巴勒斯坦的协会”。虽说这个协会胎死腹中,但有一件有趣的事值得注意。在开场白中,名字颇为有趣的主席塔利·哭背(T. Tully Crybbace) [5] 教士呼吁英国从土耳其手中获取整个巴勒斯坦,即“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从地中海到大漠”的整个地区。英国人想从别人手里要回巴勒斯坦,归还给其古代的所有者,但要求提得也太慷慨了。
教士哭背先生说的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地区是上帝最初标出的应许之地:“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创世记》15:18)这是古迦南的地盘,这片土地重新许诺给了摩西,后又许诺给了约书亚。上帝的许诺是很明确的。十二支派要赶走迦南人和赫梯人,以及亚摩利人和耶布斯人,而且“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荒原(西奈半岛)到黎巴嫩,从西海到幼发拉底河(《约书亚记》1:3)。
实际上,历史上的犹大王国和以色列王国,从来没有占据过那么大的地盘。他们的地盘从但(Dan)到贝尔谢巴,从地中海到基列(Gilead)和约旦东面的摩押(Moab),这是一般公认的巴勒斯坦的范围,直到白皮书和调查委员会介入才被改变。对我们思想简单的祖先来说,巴勒斯坦就是约定给以色列的土地,但他们没有想想——真是幸福的人——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1922年,巴勒斯坦约旦河以东的部分被分割给了以实玛利的阿拉伯子孙们。如果维多利亚时代的教士哭背先生、沙夫茨伯里伯爵、丘吉尔上校活着看到这一天,肯定会大声抗议!这样分割,以色列失去了埋葬列祖的希伯伦,约柜所在的示罗(Shiloh),约瑟被卖之地多坍(Dothan),雅各做梦之地伯特利(Bethel),约书亚打胜仗的耶利哥,以及耶稣的降生地伯利恒。这样的分割方案,不知道要招致多么大的争议。当联合国的精英们提出那份非凡的犹太国建议——一个没有耶路撒冷的犹太国——遭遇到的肯定是一片可怕的沉默。
当然,我们的祖先是无知的,他们不知道沙漠下面的宝藏,那是一种比水贵重的液体,尽管旷野中泉水拯救了夏甲和她奄奄一息的儿子以实玛利。或许那传奇的泉水是个预兆。无论如何,夏甲的儿子,也就是今天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祖先,不仅占据着巴勒斯坦之外相当于以色列所继承土地90倍的地盘,还占据着巴勒斯坦的一大部分。
然而,回顾1840年代那个时期,使中东成为控制去印度道路的战略要地的,除了即将到来的土耳其的崩溃之外,还有一件事也很重要,这就是蒸汽动力船的出现。蒸汽船需要经常停靠港口加煤,不能走绕非洲好望角的航线,而需要走地中海—红海航线,并在苏伊士换船(那时苏伊士运河尚未开通)。1840年,P. & O.公司开通了一条从英格兰经红海去印度的定期航线。这也被用作支持以色列复国的理由。1845年,在锡兰公务公司(Ceylon Civil Service)工作的米特福德(E. L. Mitford)建议“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并由大英帝国做保护国”。
 在不计其数的好处中,他预计英国将要把“蒸汽动力的交通的管理全部置于我们手中”。此外,他相信这会使英国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在黎凡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能阻止入侵,威慑胆敢来犯之敌,如果有必要,则打退他们的进攻”。
在不计其数的好处中,他预计英国将要把“蒸汽动力的交通的管理全部置于我们手中”。此外,他相信这会使英国处于“发号施令的地位(在黎凡特),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能阻止入侵,威慑胆敢来犯之敌,如果有必要,则打退他们的进攻”。
从大英帝国的另一个角落里,另一位官员——前南澳大利亚总督乔治·高勒(George Gawler)上校 [6] 提出了另一项具体计划,同样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他也呼吁在叙利亚安置犹太人,这样可以防止其他国家的干扰。他说:“英格兰急需最便捷、安全的交通线……埃及和叙利亚处在密切相关的位置上。无论在埃及或是叙利亚,只要存在一个外国强大的敌对力量,就可能对英国的贸易形成威胁……如今英格兰必须整顿叙利亚,方法是借用唯一在工作时能迸发出巨大能量且持久的民族——那片土地的真正孩子,以色列的子孙们。”高勒跟丘吉尔一样,不断回到他的论点上,从各个角度加以论述。他与蒙蒂菲奥里相识,并陪同他在1849年对巴勒斯坦进行了一次勘测。他比沙夫茨伯里走得更远。沙夫茨伯里认为做保护国并不需要“花钱”,建议各大国提供资金支持,用以补偿对犹太人的不公正待遇。高勒则竭力主张犹太人主动迎接土耳其可能的崩溃,并“大胆地索要”巴勒斯坦,宣传词是:“这片土地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民的,他们最终能打败敌人守住以色列的山峦。”
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神职人员和军人主导着有关以色列人返回巴勒斯坦的讨论——他们要么为《圣经》而活,要么为“利剑”而活。在芬恩夫人写的有关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处的回忆录中,有一段稍微反映了一点英国的军事兴趣。1858年,从停泊在雅法的英国护卫舰“欧律阿罗斯”号(Euryalus)下来一组尊贵的客人。女王的小儿子——14岁的王子阿尔弗雷德(Prince Alfred) [7] 在这艘战舰上做候补军官。他在私人教师少校考埃尔(Cowell)、舰长塔尔顿(Tarleton)及卫兵的陪同下上岸观光,由芬恩一家人做向导。“在去伯利恒的路上,”芬恩夫人回忆说,“考埃尔少校和塔尔顿舰长(他俩对《圣经》很熟悉)一路都在谈这片土地和犹太人的前途。” [8]
此后再也没有人说过少校和舰长的名字。同时,领事和芬恩夫人依旧沿沙夫茨伯里的传统路线,努力使犹太人能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生根。芬恩一家跟沙夫茨伯里一样,试图利用手头的材料,即耶路撒冷古老的犹太人社群。这个社群有大约4000名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m),他们是1492年被驱逐的西班牙犹太人后裔,后来苏莱曼大帝允许他们在耶路撒冷定居下来。此外,社群里还有大约3000名来自中欧的德系犹太人阿什肯纳兹(Ashkenazim),他们来此就是想在死后把自己的尸骨埋在锡安山上。他们基本上处于“赤贫”状态,部分原因是本地居民拒绝给他们工作,还有部分原因是犹太拉比的独裁统治把他们禁锢在中世纪的贫民窟里。面对这样的阻力,芬恩一家仍然热衷于劝化犹太人改宗,自然基本上没有进展。不过,他们都很注意分寸。芬恩夫人说她很注意不让给孩子找的犹太奶妈看到十字架,因为她“相当理解我们犹太朋友对这个主题的感情”。她说一方面她“完全相信并期待有一天以色列将能满足神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不想去解释理想与现实的明显差距。无论什么理由,都是让他们坚定信仰,用芬恩夫人的话说,“这项工作将继续,圣地将再次住满其合法的拥有者,希伯来人的国家将要再次繁荣昌盛起来”。
所以他们继续工作。他们启动了几个项目,不仅给没有工作的犹太人寻找工作,还在开垦土地方面取得了进展。为了开展灌溉项目,他们租用了土地,但由于项目雇佣的人体力都太虚弱,无法走到几英里外的田地里,所以项目的成果不佳。桑福德(Sandford)先生是个英国外科医生,他是芬恩的帮手,他发现犹太人的死亡率很高,原因“主要是缺少食物”。如果他们为非犹太人工作,他们就会被犹太拉比驱逐出教会。但芬恩夫妇仍然坚持,不断写信回国,在英国寻找资金支援。她发现只有少数人相信“犹太人能干活,圣地值得耕作”。这个发现很令人失望。
但钱还是凑足了,他们购买了一大片土地,称之为“亚伯拉罕的葡萄园”。除了让赤贫的人获得短暂救济之外,基本没有成果。尽管如此,他们又坚持了数年。在这期间,他们成立了“圣地犹太人农业劳动促进会”(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Jewish Agricultural Labor in the Holy Land),这个组织生存了下来,虽然换过好几个名字,但一直坚持到了英国托管时代。
只要芬恩领事在耶路撒冷,他就会为犹太人进行政治活动。1849年,他劝说英国外交部授予他保护被俄国政府抛弃的巴勒斯坦俄国犹太人的权力。他积极督促土耳其帕夏执行对犹太人权利的保护,遇到犹太人受迫害的案例,他也愿意出面斡旋。有一次,他成功地让一名土耳其士兵公开地当着整个卫戍部队的面接受训斥和惩罚,因为这名士兵在14个月前攻击了一个可怜的犹太人,这件事“极大地震撼了当地人”。1857年,他试图恢复沙夫茨伯里的老计划,于是把计划提交给了外交大臣克拉伦登(Clarendon)伯爵,这是一份很详细的计划,阐述了“如何劝说犹太人大规模地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与当地阿拉伯农民形成合作关系” [9] 。就计划中的“劝说”而言,合适的时间仍然没有到来,欧洲的犹太人还没有形成自发的意愿。
就在这个意愿的形成过程中,英格兰有一个人正在准备使大英帝国成为巴勒斯坦的开拓者。有人说,在支持英国—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权的人中,除了沙夫茨伯里伯爵,没有人有能够影响19世纪的政策。但有个明显的例外。他是英国历史上最富于煽动性的人物,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迪斯累里。虽然他并未与犹太复国有直接联系,但本书如果不涉及他,就像在哈姆雷特的故事中忽视鬼魂一样荒谬。但他与犹太人复国的关系,就如同他与时代和祖国的关系一样很难分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众多知名人物中,他是唯一不以宗教情怀著称的人。犹太教,他抛弃了;基督教,他虽接纳了,但仅是为其带来的方便,并不是真心信仰,宗教预言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不过,他感到自己骨子里散发出古老巴勒斯坦的力量。他在《阿尔罗伊》( Alroy )中热情地描写了以色列的复兴,但他没有为之采取政治行动。他对沙夫茨伯里和丘吉尔这一派提出的主张置之不理,也不参与蒙蒂菲奥里的冒险事业。他不是犹太民族主义者,因为他的民族主义是个人的和独一无二的。他为之摇旗呐喊的是以色列的传统而不是以色列的命运。他关心全世界欠犹太人的债,而不是犹太人未来在世界中的地位。
“如果不相信他们的犹太教,哪里会有你们基督教呢?”他在下议院为犹太人《解放法案》辩论时问道。“在每个圣坛上……我们都能找到犹太律法……早期的基督教徒都是犹太人……在基督教会初期,能利用权力、热情、天赋去传播基督教信仰的人,是一个犹太人……如果你没有忘记你欠这个民族的东西……作为基督徒你早就应该寻找机会去补偿信仰这个宗教的人。”
 他冒着政治生命的危险发表这番讲演。作为下议院议员,他有赖于党内高层的提携,但他不怕成为保守党内唯一支持这个法案的议员。每次投票,他都走过议会大厅与自由党一起投票,反对自己的党。
他冒着政治生命的危险发表这番讲演。作为下议院议员,他有赖于党内高层的提携,但他不怕成为保守党内唯一支持这个法案的议员。每次投票,他都走过议会大厅与自由党一起投票,反对自己的党。
他对自己种族和传统的自豪感,不断出现在他的小说中,出现在书再版的前言中。在他为乔治·本廷克(George Bentinck)勋爵所写的政治传记中,突然冒出了有关犹太人的著名章节。“世界到目前为止发现无法摧毁犹太人……无情的自然法则已经做出判决,劣等民族是无法摧毁或吸收融合优秀民族的。制止这个法则发声是徒劳无益的企图。”跟马修·阿诺德一样,他相信英国的实力和意志源自《圣经》,但《圣经》是从希伯来人的道德法律变换而来的。他说,英国“虽然缺乏神学,但总是能想起锡安”。
他最终对英国的巴勒斯坦事业是有贡献的,但不是以犹太人的身份,而是以帝国建设者的身份。虽说巴勒斯坦吸引着他,但帝国对他的吸引力更大。英国在19世纪后期向东方的扩张是在他的指引和努力下展开的。很久以前,英王狮心理查在去圣地的途中停下脚步,攻占了塞浦路斯。1878年,迪斯累里重新获得了这个地方。他知道帝国为解决物资供应问题肯定要向巴勒斯坦进发,于是他买下了苏伊士运河,从此进发巴勒斯坦变得不可避免。
但在1840年,上述成就还需要等一代人的时间,而迪斯累里此时还是一个稚嫩的议员,以善写优美的小说著称。他具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力量,下院的议员们不安地意识到,眼前的这只奇怪的雏鸭有一天会变成雄鹰。1831年,他做了一次拜伦式的东方游,从希腊去往埃及,所到之处皆是古迹,每天的旅途都走在帝国昔日的道路上。他去了雅典卫城,见识了埃及金字塔,走过了亚历山大、恺撒、穆罕默德帝国的大道。在他所去过的地方,最重要的莫过于遭毁坏的祖先神殿,这些神殿在他的思维里闪耀着,仿佛皇冠上的宝石。在君士坦丁堡,他拜见了土耳其苏丹。在亚历山大,他拜见了穆罕默德·阿里。他从塞浦路斯坐船沿着叙利亚海岸航行,途经了贝鲁特、提尔、阿卡和雅法。最后,他“全副武装地爬上了战马”,骑着战马走过无数的荒凉山冈,最后“那个我凝视的城市就是耶路撒冷!”

接下来是他一生中最迷人的几天。过去辉煌的历史和几个世纪的怀旧一齐涌上他的心头。他仅停留了一周的时间,但他离开时已经开始动笔写一部小说了,小说的主题是“一部有关我的神圣、浪漫的祖先民族的辉煌编年史”,即假弥赛亚、“被囚禁的王子”大卫·阿尔罗伊,在12世纪领导犹太人民反抗巴格达哈里发的故事。迪斯累里写英雄,经常写得跟自传一样,不难看出,《阿尔罗伊》中反映出了他自传式的内心梦想。
“你问我的愿望是什么,”那位为阿尔罗伊担任幕后智囊的犹太智者说,“我的回答是民族的生存,我们的民族不能算是活着。你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应许之地。你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耶路撒冷。你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圣殿。所有我们失去的,所有我们怀念的,所有我们为之奋斗的,我们美丽的国家,我们神圣的信仰,我们简洁的举止,我们古老的习俗。”
迪斯累里写这段话时动了真情。与小说中其余部分的华丽文风相比——穿罗着缎、腰佩弯刀,恶魔和秘术家,水银喷泉和骄奢淫逸的公主——这段真情十分显眼。《阿尔罗伊》,按照作者的神秘说法,代表了他的“理想抱负”
 。像迪斯累里这样的年轻人,对自己的种族有自豪感,内心涌动着快要燃烧起来的野心,站在他祖先曾经统治过的高贵环境之中,如果无动于衷,不想为自己的民族赢得国家地位,那才是奇谈怪事。
。像迪斯累里这样的年轻人,对自己的种族有自豪感,内心涌动着快要燃烧起来的野心,站在他祖先曾经统治过的高贵环境之中,如果无动于衷,不想为自己的民族赢得国家地位,那才是奇谈怪事。
他确实是动了想干大事的心,英国的政治现实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四年后,他进入议会,目标就是做拥有最高权力的首相。(“上帝啊,”墨尔本勋爵说,“那家伙肯定能得手。”)接下来他出版了一本有关东方的小说《坦克雷德》( Tancred ),这显示出他正迈向自己的目标,此时他关心的不再是以色列王国,而是英格兰帝国。他想把《坦克雷德》写成“年轻的英格兰”寻找精神复活的故事。书中的英雄虽然是公爵的儿子,但因厌世愤然离开英格兰,来到耶路撒冷,想参透“亚洲的奥秘”。但英雄和作者很快就忘记了这个目标,纵身跳入了中东的政治旋涡,试图回答英格兰面临的如何控制通往印度道路的大问题。叙利亚危机刚刚结束;穆罕默德·阿里试图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引发的政治浪潮还没有因他的失败而平息。十分奇怪的是,在迪斯累里眼里,英格兰的机会在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而不是犹太民族主义。他描绘未来的可能性,虽然用了冷嘲热讽的口气,但准确得难以解释。
法克里丁(Fakredeen)是黎巴嫩埃米尔,一个诡计多端、野心勃勃的叙利亚人,唯一信仰的就是“我需要一个王位”。迪斯累里借法克里丁之口说道:“让英国女王组织起一支舰队……把她的王座从伦敦转移到德里……与此同时,我要与穆罕默德·阿里交易。他将获得巴格达和美索不达米亚……我则将得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我们承认印度女王是我们的君主,保证她拥有黎凡特沿岸。如果她喜欢,她还能拿走亚历山大,就好像她现在拥有马耳他,这是可以安排的。你们的女王很年轻,她还有时间……”确实是这样。30年后,那位写《坦克雷德》的作者正式地把“印度女王”的冠冕加在了女王的众多头衔之上。
《坦克雷德》包括了一些令人吃惊的预言。两个滑稽人物在讨论世界政治时有如下对话:
“‘帕麦斯顿不拿下耶路撒冷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巴利孜说。”
“‘英国人必须得到市场。’领事帕斯奎利哥说。”
“‘很公道,’巴利孜说,‘我正想着自己也做点棉花生意。’”
当然,迪斯累里这是在说笑——但他真是在说笑吗?在书的后面,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人告诉坦克雷德:“英国人是不会无缘无故地与土耳其人做生意的。他们要拿走这座城市,他们要占据它。”1847年的英国公众也许没有把《坦克雷德》当真,但历史成真了。
[注释]
[1] Ibid .
[2] Letter to his wife, July 13, 1841, Baroness Bunsen’s Memoirs .
[3] Hyamson’s British Projects .
[4] Ibid .
[5] Ibid .
[6] Hyamson’s Projects . See also Cohen, p. 52.
[7] Mrs. Finn’s Reminiscences .
[8] Ibid .
[9] Consul Finn’s correspondence with Foreign Office. F.O. 78 11274, Pd. No. 36, Hyamson’s Consul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