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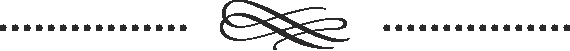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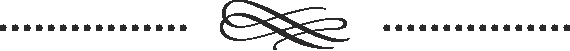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在18世纪的最后一年,距十字军最后一次在阿卡战败500年后,英国人再一次在阿卡的海滩上作战。阿卡是著名的要塞,不仅控制着通往巴勒斯坦的海上通道,还控制着沿海军事通道,在过去30个世纪里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1291年,土耳其人把最后一批欧洲人从这里赶走。这个扼守巴勒斯坦咽喉的要地,连同整个圣地,最终都被土耳其帝国吞并了。
在伊斯兰沉睡了五个世纪之后,突然之间,英国的炮舰隆隆地驶进港口,一支欧洲军队从陆地发动攻击,凶猛的马穆鲁克人绝望地守卫着城墙。但在这一仗里,英国人是守卫者而非进攻者,他们这次与土耳其人共同抵御一个来自欧洲的敌人。英国人的大炮对准的不是阿卡的城墙,而是城下拿破仑的军队。
巴勒斯坦的地理位置再次成为它的诅咒。巴勒斯坦地处通往印度的要道上,而拿破仑则决意占领此地,切断他的死敌英国与其东方财富和贸易的联系,从而统治一个无可匹敌的亚历山大第二帝国。埃及和叙利亚是他计划的关键,而扫除拿破仑对两地的控制对英国人同样关键。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军队与他为入侵英国而集结的是同一支军队。但拿破仑在最后一刻却步了,就像希特勒1940年面对英吉利海峡时的致命迟疑一样。拿破仑的犹豫迫使他转向东方,希冀从背后打击英国——这与希特勒转向北非的无效战略一样。
事实上,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战役是如此相似,仿佛历史的重演。两个时代中围绕巴勒斯坦的战略也是一样的,并且现在亦然。用最简单的话说,这个战略就是:无论哪个骄横的专制君主——当然不包括英国自己——将要控制整个欧洲,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能允许它再控制中东。拿破仑时代如此,德皇时代如此,希特勒时代如此,今天
 对苏联也是如此。不能允许任何想成为世界统治者的人占据开罗、君士坦丁堡及位处其间的地区,不能允许他把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从而阻断通往远东的道路。从战略角度看,小小的巴勒斯坦在谁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须符合中东的战略大局。最初是土耳其人,后来是英国人,如今是以色列人。就权力政治而言,谁掌握巴勒斯坦并不重要,只要他不是统治欧洲的霸主。
对苏联也是如此。不能允许任何想成为世界统治者的人占据开罗、君士坦丁堡及位处其间的地区,不能允许他把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从而阻断通往远东的道路。从战略角度看,小小的巴勒斯坦在谁手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须符合中东的战略大局。最初是土耳其人,后来是英国人,如今是以色列人。就权力政治而言,谁掌握巴勒斯坦并不重要,只要他不是统治欧洲的霸主。
这样说或许太过简单化,但这个问题的核心在19世纪的外交领域被称为“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这个词给人一种古朴的味道,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连鬓胡子一样。令人联想到卡斯尔雷(Castlereagh)、坎宁(Canning)、塔列朗(Talleyrand)和梅特涅(Metternich)们,那些“突发事件”和秘密协定,还有俄国沙皇、土耳其帕夏和贝伊,以及克里米亚、迪斯累里和苏伊士运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词与19世纪所有的外交明星一起被废弃不用了。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又有了新的演员——石油和阿拉伯人,以色列和美国,但其背后的逻辑仍然跟英国18世纪末在中东外围插上“禁止入内!”的标牌时一样。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的基本政策即为支撑着衰败的土耳其不被入侵者瓜分。当1918年土耳其帝国终于崩塌后,英国随即决定自己取代土耳其,要么自己直接统治,要么通过阿拉伯傀儡间接统治。这种方法的效果起初很好,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有老办法终于难以为继。此时我们已与这些事件距离太近,无法看清谁或者什么将成为未来中东的主导力量——可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也可能是苏联,或者假如你是阿拉伯人,那可能会认为是蠢蠢欲动的“世界犹太复国主义”。但历史学家关注的是过去,而非未来。
第一个迫使英国在中东选择立场的不是拿破仑,而是沙俄。事实上,任何人要想寻找历史的重合,只需翻开1780年以来的历史书,沙俄无时无刻不在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口处挪动。沙俄并非想将巴勒斯坦据为己有,但巴勒斯坦的命运是与土耳其帝国捆绑在一起的。克里姆林宫庞大的身影每次逼近土耳其边境,欧洲高官的办公室里就会骚动起来,仿佛他们突然感觉到来自遥远的中东的寒冷和黑暗。外交官们穿梭于各使馆之间,外交文书往来于各国首都之间,仿佛成群的蚂蚁。统计一下19世纪发生的各国涉及与土耳其关系的事件、最后通牒、战争、国际会议、协定和决议,就会发现东方问题比当时任何其他外交问题吸收的外交界的周旋、阴谋和精力都更多。(“19世纪”又是一个为简化语言而被赋予一定弹性的词汇。如果坚持要限定为100年,那它可以指1815—1914年这段时间。而从攻陷巴士底狱到滑铁卢这四分之一个世纪,即1789—1815年,则是18世纪和19世纪间的幕间表演,剧目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
巴勒斯坦的未来——以色列最终在此复国——在各大国介入土耳其事务的这段漫长时间中上演。这些大国在土耳其边境徘徊,就像贪婪的继承人在等待富裕的舅舅咽下最后一口气。“有死尸的地方就有秃鹰盘旋。”
 虽然土耳其这具残躯仍然顽固地喘着气,但却并不能阻止饥饿的秃鹰一口接一口地吞噬它的残肢。
虽然土耳其这具残躯仍然顽固地喘着气,但却并不能阻止饥饿的秃鹰一口接一口地吞噬它的残肢。
令英国意识到做中东头号秃鹰的战略需要的,是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统治下野心勃勃的沙俄。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8世纪的纷乱战争中打败土耳其后,决心拿下一块被外交史学家称为“奥克扎可夫地区”(Oczakoff district)的土耳其领土。只有仔细查看地图集之后现代读者才能搞清楚,那块地区实际上就是敖德萨(Odessa),叶卡捷琳娜大帝想要的是在黑海边上有一处不冻港。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是否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尚存争议,但他当政期间竭尽全力使英国避免陷入欧洲大陆的战争中。不过,他在这件事上对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态度与今天西方政治家对叶卡捷琳娜在克里姆林宫的继任者
 态度一致,那就是绝不能让她得手。他冒着开启战端的危险,以自己的政治生涯做赌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叶卡捷琳娜交出那个黑海港口。但他因未受到公众支持而失败。虽然他向议会施压获得了信任案的通过,但议会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们不想为一片“遥远的陌生之地”开战,就像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说过的话一样。皮特被迫让步,默许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对敖德萨的占领。但他在这次事件中制定的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土耳其领土被蚕食的原则,却成为日后英国处理东方问题的固定原则。
[1]
态度一致,那就是绝不能让她得手。他冒着开启战端的危险,以自己的政治生涯做赌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叶卡捷琳娜交出那个黑海港口。但他因未受到公众支持而失败。虽然他向议会施压获得了信任案的通过,但议会的意思是很清楚的,他们不想为一片“遥远的陌生之地”开战,就像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关于捷克斯洛伐克说过的话一样。皮特被迫让步,默许了叶卡捷琳娜大帝对敖德萨的占领。但他在这次事件中制定的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土耳其领土被蚕食的原则,却成为日后英国处理东方问题的固定原则。
[1]
大多数英国人都不支持这一政策,因为他们反感那个被伯克(Burke)称为“挥霍无度的可耻帝国”
[2]
的土耳其。但英国面临的选择是支持昏庸的土耳其人,或者允许对手威胁其通往印度的道路。皮特做出了选择,尽管在此之前土耳其几乎是英国的最末选项。在1770年的俄土战争中,皮特的父亲查塔姆伯爵(Earl of Chatham)在给同僚的信中写道:“阁下清楚我很亲俄。我相信在奥斯曼帝国倒下的时候会将波旁王朝也一起拉下马。”
 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英国失去了美洲的殖民地,其帝国主义的发展方向被彻底改变,转向了东方的印度和通往印度的沿线国家。此后,英国专心致志地通过支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保护其中东的通道,抵御沙皇和拿破仑的介入。1799年,当法国东侵时,皮特立即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一份为期八年的秘密协定,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安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799年英国士兵会像本章开始所述,在巴勒斯坦的港口阿卡作战。
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英国失去了美洲的殖民地,其帝国主义的发展方向被彻底改变,转向了东方的印度和通往印度的沿线国家。此后,英国专心致志地通过支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保护其中东的通道,抵御沙皇和拿破仑的介入。1799年,当法国东侵时,皮特立即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一份为期八年的秘密协定,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安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1799年英国士兵会像本章开始所述,在巴勒斯坦的港口阿卡作战。
这也把我们带回了“以色列的希望”。除了波拿巴将军,还有谁会突然宣布他是犹太人复国的支持者呢!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这位创下无数纪录的杰出将军是历史上第一位提议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的国家元首。
 当然,这完全是个出于私利的举动,没有任何宗教意义。波拿巴毫不关心《圣经》或其预言,无论是犹太教的还是基督教的。对他这样的不信教者,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只要符合他的利益,他甚至可以宣称自己是个穆斯林——实际上,刚踏上埃及的土地他就这样做了。他在对犹太人的宣言中称他们是“巴勒斯坦的真正传人”。他这样说仅是一种军事计谋,就如同他在此前呼吁阿拉伯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统治一样。但他在任何宣言中都掩饰不住对荣耀的追求,他将对犹太人的承诺扩大到恢复古代的耶路撒冷王国。他像戏剧演员一样高呼:“以色列人,起来吧!”“你们这些被流放的人,起来吧!快起来吧!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你们要把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被剥夺千年的公民权利夺回来!你们要把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权利夺回来!你们要把按照自己的信仰永世公开敬拜耶和华的自然权利要回来!”他呼吁犹太人投入自己麾下,并向他们提供法国的“保证和支持”,帮助他们夺回遗产,“做自己遗产的主人,不由任何人剥夺”。
当然,这完全是个出于私利的举动,没有任何宗教意义。波拿巴毫不关心《圣经》或其预言,无论是犹太教的还是基督教的。对他这样的不信教者,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只要符合他的利益,他甚至可以宣称自己是个穆斯林——实际上,刚踏上埃及的土地他就这样做了。他在对犹太人的宣言中称他们是“巴勒斯坦的真正传人”。他这样说仅是一种军事计谋,就如同他在此前呼吁阿拉伯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统治一样。但他在任何宣言中都掩饰不住对荣耀的追求,他将对犹太人的承诺扩大到恢复古代的耶路撒冷王国。他像戏剧演员一样高呼:“以色列人,起来吧!”“你们这些被流放的人,起来吧!快起来吧!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你们要把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被剥夺千年的公民权利夺回来!你们要把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权利夺回来!你们要把按照自己的信仰永世公开敬拜耶和华的自然权利要回来!”他呼吁犹太人投入自己麾下,并向他们提供法国的“保证和支持”,帮助他们夺回遗产,“做自己遗产的主人,不由任何人剥夺”。
 [3]
[3]
考虑到波拿巴这番叙利亚冒险 [4] 的现实情况,他的宣言仅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姿态,就好像舞台上任何一个昂首阔步假装英雄的演员一样。然而,拿破仑为未来设定了一条路径,以色列人沿着这条路在当代实现了一个不比拿破仑逊色的英勇、伟大的成就,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在拿破仑之后,无论哪个大国在中东陷入战争,总有人会建议以色列复国,此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块战略要地可以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同时犹太人的财富和影响力也会归到自己一方。犹太人获得的利益从来都是各国争端所产生的副作用,比如英国在20世纪对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但无人能否定这是拿破仑的首创。
拿破仑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法国人早就有统治黎凡特的梦想。早在1671年,路易十四即对莱布尼茨(Leibnitz)的一项建议十分感兴趣。莱布尼茨为了转移路易十四入侵德国的野心,建议他重修那条穿越苏伊士地峡、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古老运河。“埃及才是对敌人的致命打击,”莱布尼茨写道,“在那里能找到去印度的真正航线……还能获得法国对黎凡特的永久控制。” [5] 在贸易上,法国确实已在黎凡特成为主宰,英国在这个时期的注意力因集中于绕道好望角去往印度的航线而忽视了黎凡特。但法国在下一个世纪中也在印度获得了殖民地和野心,与英国产生了直接矛盾,最后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被打败。在那场斗争中,舒瓦瑟尔(Choiseul)本计划使法国控制埃及和阿拉伯,开辟出一条通向红海的运河,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赢取“势力范围”,因此可以在印度消灭英国人。一个世代之后轮到波拿巴尝试实现这一愿景了。
但拿破仑的梦想与前人有所不同——在他华丽的梦想中,他不仅要成为亚历山大第二,还要重现亚历山大那个从埃及绵延至印度河甚至恒河流域的帝国。他视埃及为摧毁英国的机会。他将开辟一条新苏伊士运河,将地中海变成法国的内湖,引导印度和黎凡特的贸易都进入法国人之手。欧洲太小了,东方广阔的空间、丰富的资源、庞大的人口才是真正值得赢取的帝国。东方是永恒的荣耀之地,那里能给人史诗般不朽的名誉。拿破仑渴望的不是贸易、财富,甚或权力,他真正渴望的是不朽,像亚历山大和恺撒一样。“这世上的一切都会消逝,我的荣耀已经开始消减。”他对他忠实的记者布里耶纳(Bourienne)说。此时他还不到30岁。“欧洲这个小角落太小了。我们要去东方,世界上所有伟大的人都是在东方获得他们伟大的名誉。”

跟亚历山大出征时的年龄一样,拿破仑30岁时出征埃及,征服开罗。甚至当舰队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被纳尔逊(Nelson)摧毁后,他仍然不顾反对继续向前推进,坚信他仍然能征服叙利亚,进而赢取土耳其、波斯、印度,带着一个新帝国返回欧洲,成为世界的主宰。1799年2月,他攻占了西奈半岛上位于埃及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埃尔阿里什(El Arish)。几天后,他入侵巴勒斯坦,在3月7日攻占了雅法,并于3月18日抵达阿卡城下。“东方的命运就在阿卡的城墙内。” [6] 他说道。一旦阿卡到手,他即可向大马士革、阿勒颇、君士坦丁堡进发。“然后,我将推翻土耳其帝国,在东方建立新的帝国,奠定我永世不朽的地位。”他从未放弃这个愿景。20年后,当他在圣赫勒拿岛(St. Helena)的乱石丛中口述回忆录时,又说起:“如果攻占了阿卡……我将抵达君士坦丁堡和印度,改变世界的面貌。”
当波拿巴在距离耶路撒冷25英里处的拉姆拉安营扎寨的时候,堆满他脑子的就是这些宏大的愿景,也就是在这里他向犹太人发出了宣言。由这个支配命运的人举笔挥剑之间重建大卫的王国,还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吗?天时、地利、战局都适宜得难以阻挡。当时的战局如此有利,波拿巴可能真的相信他就要进入耶路撒冷了。
拿破仑对阿卡的围攻陷入了僵局。在西德尼·史密斯爵士(Sir Sidney Smith)的英国海军的支持下,马穆鲁克人顽强抵抗。但在4月16日,拿破仑在他泊山取得大胜,击溃一支从大马士革前来救援阿卡的土耳其部队。他认为阿卡马上就要投降,巴勒斯坦的全部领土即将落入他的手中,他将胜利地进入耶路撒冷。他是如此自信,竟然在4月17日他泊山之役胜利的第二天向巴黎送去一份公报(刊登在5月22日的《箴言报》上),宣布:“波拿巴发表声明,呼吁亚非的犹太人团结在他的旗帜下重建古耶路撒冷王国。”此外,公报落款为4月19日从“耶路撒冷总部发出”,可见拿破仑一定认为他在那天能抵达耶路撒冷。但他不仅没有踏上耶路撒冷的土地,甚至连阿卡都没能进入。因为就在他紧盯着眼前的荣耀和不朽之时,他被脚下的障碍绊倒了——那就是西德尼·史密斯爵士的英国大炮。“他令我错过了我的天命。”
 他在战斗结束后简略而痛苦地说道。阿卡拒绝沦陷,在被围攻了又一整个月后,史密斯召集起炮艇上所有能上阵的水手,像600年前英王理查在雅法一样,手持长矛向海岸发动了冲锋。此时的法军,因疾病、饥饿以及其前辈腓力四世曾遭遇的所有困难,终于溃败了。到5月20日,波拿巴终于承认失败,带着他残破不堪、七零八落的军队踏上归途。他的帝国梦破灭了。这是拿破仑的第一次失败,也是他最痛苦的失败,即使在日后他在巅峰之时,也不能忘怀。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的胜利时刻,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Lucien)听皇帝低声说:“如果我在阿卡有这样的运气就好了。”
[7]
他在战斗结束后简略而痛苦地说道。阿卡拒绝沦陷,在被围攻了又一整个月后,史密斯召集起炮艇上所有能上阵的水手,像600年前英王理查在雅法一样,手持长矛向海岸发动了冲锋。此时的法军,因疾病、饥饿以及其前辈腓力四世曾遭遇的所有困难,终于溃败了。到5月20日,波拿巴终于承认失败,带着他残破不堪、七零八落的军队踏上归途。他的帝国梦破灭了。这是拿破仑的第一次失败,也是他最痛苦的失败,即使在日后他在巅峰之时,也不能忘怀。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的胜利时刻,拿破仑的弟弟吕西安(Lucien)听皇帝低声说:“如果我在阿卡有这样的运气就好了。”
[7]
或许拿破仑在撤退的痛苦中已经撕毁了那份对犹太人的宏大承诺。毫无疑问,他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掩盖措施是因为不愿回忆这段耻辱的失败。但这次远征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很大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东方的兴趣,产生了若干有价值的考古发现和大量浪漫诗作。为绘制未来帝国的蓝图,有一群科学家、工程师和学者跟随拿破仑远征,对翻译埃及象形文字起到关键作用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即由他们发现。1803年,乌尔里希·泽岑(Ulrich Seetzen)来到叙利亚,花了两年时间学习当地语言和阿拉伯人的举止,他因此得以扮作朝圣者,像本地人一样在巴勒斯坦、西奈半岛、开罗甚至跨越红海到达麦加进行了四年旅行。泽岑的杰出研究成果仅散杂于德国的期刊之中,或作为未发表过的手稿躺在德国博物馆里发霉。只有少量选段因被译为英文收集在一本题为《太巴列湖、约旦和死海地区简介》( A Brief Account of the Countries Adjoining Lake Tiberias, the Jordan and the Dead Sea )的书中保存下来,这本书于1813年在伦敦出版。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在1806年去东方短暂旅行后写出了畅销书《从巴黎到耶路撒冷》( Itinéraire de Paris à Jérusalem ),这本书被翻译为英文后得到广泛阅读。
1810年,威廉·皮特的外甥女和长期秘书赫丝特·斯坦诺普(Hester Stanhope)女士
 因舅舅的死而悲痛不已,决定永远离开英国,在黎巴嫩的山区过起了神话般的隐居生活。“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一名了解她的人写道,“但高傲的人在悲哀的刺激下往往产生一种对东方的渴望。”金莱克(Kinglake)的这番话精炼出了赫丝特女士在那个浪漫时代中给东方带来的浪漫名气。像女先知一样,她躲在一个隐蔽的王国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从最初上千奴隶守护中的宫殿和花园,到在贫困和孤独中死去。在这30年里,她一直在等待着白马与弥赛亚能从耶路撒冷的城门中走进来。去东方旅行的上层人士视拜访赫丝特女士如同看到金字塔一般。
因舅舅的死而悲痛不已,决定永远离开英国,在黎巴嫩的山区过起了神话般的隐居生活。“我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一名了解她的人写道,“但高傲的人在悲哀的刺激下往往产生一种对东方的渴望。”金莱克(Kinglake)的这番话精炼出了赫丝特女士在那个浪漫时代中给东方带来的浪漫名气。像女先知一样,她躲在一个隐蔽的王国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从最初上千奴隶守护中的宫殿和花园,到在贫困和孤独中死去。在这30年里,她一直在等待着白马与弥赛亚能从耶路撒冷的城门中走进来。去东方旅行的上层人士视拜访赫丝特女士如同看到金字塔一般。
巴勒斯坦协会(Palestine Association)早在1804年就成立了,其目的是促进圣地的探险和研究,但由于去圣地旅行太过危险而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1834年,这个协会在并入皇家地理学会后便消失了;但几年后,又以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的形式坦然出现。不过,出版泽岑信件的工作要归功于巴勒斯坦协会,这些信件激励了19世纪最杰出的探险者约翰·刘易斯·伯克哈特(John Lewis Burckhardt)的旅行。跟泽岑一样,他在东方生活多年,他的最终目标是可以扮作贝都因人代表非洲学会去中非探险。他死前没能实现目标,不过在做准备的六年时间里,他游遍了叙利亚和阿拉伯,甚至成功进入了麦加,这要归功于他的成功伪装、深入细微的《古兰经》知识和与当地人毫无二致的举止。他死后,他的随笔和日记《叙利亚和圣地游记》( Travels in Syria and the Holy Land )和《阿拉伯游记》( Travels in Arabia )在1822年出版发行。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我们能看到这个孤独的人不知疲倦地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睡在阿拉伯村庄里,跟随着牧羊人发现圣殿的废墟,我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位田野考古学家的真实写照。他的书没有连贯的计划,而是汇集了他的各种观察:阿拉伯人的习俗和性格,当前的农作物和古代器物,石头上的铭文,根据废墟绘制出的建筑图以及地理和地质学方面的发现。但他的文字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他描述每天的旅途、每一根倒塌的石柱、每一段废弃的城墙都与《圣经》中的故事有关。
无法想象除拜伦(Byron)外谁还能与伯克哈特形成更加鲜明的反差。就在同一年,拜伦与霍布豪斯(Hobhouse)去黎凡特闲逛了一遭,回国后他即因1812年写成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和1813年的《异教徒》( The Giaour )而成名,并使东方成为时尚。拜伦这次旅行有一个意外的附带后果,就是重新向现代考古学家打开了《圣经》中以东的首都佩特拉(Petra)古城的大门。这里曾经非常繁荣,是往来于波斯湾和黎凡特之间商人的中转站,但已被废弃了几百年。威廉·班克斯(William Bankes) [8] 是拜伦在三一学院的朋友,可能是在拜伦经历的激励下,他在1812年带着拜伦的介绍信动身前往东方。或许是受失踪城市传说的吸引,或许是受伯克哈特进入佩特拉谣言的刺激,他决定亲自去寻找这个还不为英国所知的佩特拉城。1816年,他进行了第二次旅行,这次他带上了两名英国海军军官——厄比(Irby)上校和曼格利斯(Mangles)上校。虽然面对土耳其官员的坚决不合作态度——上至土耳其苏丹、大马士革帕夏和耶路撒冷总督拒发安全通行证,下至最底层的向导和赶骆驼的人警告他们贝都因人渴望拿西方人的鲜血给妻子做药品,但这队英国人还是上路了,他们“决意信任和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披荆斩棘穿越长满灌木和野生无花果的狭窄峡谷,进入了古代社会最伟大的首都之一。此时,大理石建筑尚孤寂地立于空无一人、覆满藤蔓的遗址中,猫头鹰静静飞过,老鹰的尖叫声在圣殿、陵墓和宫殿里回荡。但不久之后,阿拉伯的佩特拉就奉献出自己的宝藏。
上述几位都是先驱。真正去圣地探险的大潮在1840年之后才出现,他们中间有为“证实”《圣经》前往圣地的野外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想“寻访耶稣足迹”的热情旅行者。与此同时,拿破仑的远征还产生了其他后果。欧洲人回到中东战场激起的地区动荡至今仍未消退。拿破仑离开中东后,危机便在酝酿中了,到1830年,东方问题引发了欧洲危机的全面爆发,使欧洲列强陷入长达十年的混乱,英国和法国走到了战争边缘,东方于十字军东征后再次回到公众的想象中。
这场危机的核心人物是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他是自萨拉丁之后最著名的穆斯林,一名极为非凡的阿尔巴尼亚强人,自命为埃及的统治者,哈里发的觊觎者,几乎凭一己之力提早一百年分解了土耳其帝国。我们对他的兴趣主要不在他震撼欧洲各国首都的功业,而在于他将英国永久地拉入中东事务之中,并给英国人提供了一个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是人为的。沙夫茨伯里伯爵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不成熟尝试属于下一章的范畴,但它必须被放在穆罕默德·阿里时期的政治和战略形势背景之下。
问题的根本是谁将“占据去印度的道路”
 ——如同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所说。穆罕默德虽出身卑贱,但最终跃升为比其宗主还强大的封臣。他已经有能力抛弃土耳其苏丹的统治,建立一个包括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独立伊斯兰国家。野心勃勃的沙俄跃跃欲试地支持土耳其对抗穆罕默德的狂妄挑战,意图利用这一机会成为土耳其的保护国,将达达尼尔海峡并入自己的怀抱。野心勃勃的法国此时仍然怀念拿破仑统治东方的梦想,也非常想成为穆罕默德的保护国,通过支持这个东方的拿破仑去完成自己昔日英雄的未竟之业。英国既不想要俄国和法国得偿所愿,更不希望穆罕默德获得对这一关键地区的影响或控制,决计阻止这三方。一个年迈虚弱因而任人摆布的奥斯曼君主仍然比一个独立亲法的“活跃阿拉伯君主”
[9]
(帕麦斯顿语)更适合占据去印度的道路。
——如同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所说。穆罕默德虽出身卑贱,但最终跃升为比其宗主还强大的封臣。他已经有能力抛弃土耳其苏丹的统治,建立一个包括埃及、叙利亚和阿拉伯的独立伊斯兰国家。野心勃勃的沙俄跃跃欲试地支持土耳其对抗穆罕默德的狂妄挑战,意图利用这一机会成为土耳其的保护国,将达达尼尔海峡并入自己的怀抱。野心勃勃的法国此时仍然怀念拿破仑统治东方的梦想,也非常想成为穆罕默德的保护国,通过支持这个东方的拿破仑去完成自己昔日英雄的未竟之业。英国既不想要俄国和法国得偿所愿,更不希望穆罕默德获得对这一关键地区的影响或控制,决计阻止这三方。一个年迈虚弱因而任人摆布的奥斯曼君主仍然比一个独立亲法的“活跃阿拉伯君主”
[9]
(帕麦斯顿语)更适合占据去印度的道路。
不过吊诡的是,如果不是英国人,穆罕默德的武功可能还没有开始就完结了。1798年,他是一个土耳其非正规军团的团长,与拿破仑在埃及作战。他在尼罗河河口海战中落水,被后来阿卡的胜利者西德尼·史密斯放下的舢板救起。40年后,穆罕默德自己的帝国梦想被另一位英国海军上将的大炮粉碎在了阿卡。如果回顾穆罕默德的早期经历,我们就能看出他正是在拿破仑撤退后留下的混乱中成为埃及强人的。到1805年,他已经成为埃及帕夏,随后又将统治范围扩大到苏丹和阿拉伯,包括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到1830年,他已为挑战土耳其苏丹做好了准备,拥有一支由法国军官训练的陆军和海军。在他争霸的道路上,浸透着鲜血的巴勒斯坦再次成为战场。 [10]
1831年11月1日,埃及陆军跨过叙利亚边境,与穆罕默德之子易卜拉欣(Ibrahim)指挥的海军在雅法会合,并立即开始围攻兵家必争之地阿卡。阿卡这次陷落了。易卜拉欣在攻占了加沙和耶路撒冷之后,挥兵进击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到1833年夏季,他已占领整个叙利亚,并开始攻打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交通要道。土耳其苏丹惶恐地向英国求救,请求建立攻守联盟。但帕麦斯顿此时正想着让穆罕默德做英国的受保护国,没有接受。苏丹大为苦恼,像溺水者抓住蟒蛇以图获救一样接受了自己的世仇俄国沙皇的帮助。俄军早已在土耳其边境等待,一经允许立即开动,阻挡住了易卜拉欣去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俄国顾问出现在土耳其宫廷里,俄国军官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走着,俄国工程师运作着海峡边的堡垒。“这显示出,”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庞森比(Ponsonby)勋爵在给国内的信中写道,“土耳其人已经是俄国的傀儡了。”
[11]
更严重的问题是土耳其以什么条件交换海峡的呢?据说庞森比勋爵和法国大使一起床就去窗边看,“一个在早晨6点,另一个在傍晚6点”
 ,预期看到长久以来让他们害怕的情景——俄国舰队在他们眼皮底下停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里。他俩的恐慌并非虚谈。俄国救援的代价是著名的《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其中有一个秘密条款,规定一旦俄国要求,土耳其将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过。
,预期看到长久以来让他们害怕的情景——俄国舰队在他们眼皮底下停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里。他俩的恐慌并非虚谈。俄国救援的代价是著名的《温卡尔—伊斯凯莱西条约》(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其中有一个秘密条款,规定一旦俄国要求,土耳其将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的军舰通过。
帕麦斯顿极为懊恼,如今他同意了庞森比的看法,认为“俄国能有所节制不谋求让土耳其臣服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如何阻止俄国的扩张变成了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在20年后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再次出现,并仍然困扰着今天中东的外交家。英国开始全力构筑一个统一阵线来抵御俄国对这一地区事务的干预。这个统一阵线的任务就是化解土埃危机,采取联合行动,不计代价地防止任何人未来私自发动袭击的可能性。穆罕默德暂时退让了,但在1838年再次出手。一支在叙利亚的土耳其军队被他歼灭,土耳其舰队在亚历山大港向他投降,老苏丹随即在君士坦丁堡羞愧而死。法国对穆罕默德取得的荣耀大加赞许,他此时看起来似乎也即将成为一个可与萨拉丁的帝国媲美的新帝国的主人,并挂上法国的三色旗。幸运的是,沙皇极端厌恶带着资产阶级绅士派头的法王路易·菲利普和他的民主思想,所以愿意用尽各种办法挫败他,特别是能扩大英法两国间裂痕的方法。所以,沙皇同意了帕麦斯顿的联合行动计划,甚至宁愿放弃他的海峡特权。与此同时,普鲁士和奥地利也表示同意,就在法王和梯也尔(Thiers)大张旗鼓地支持穆罕默德对新近成为苏丹的小男孩提出的要求之时,四个大国悄悄在伦敦签署了协定,一起支持土耳其,强迫穆罕默德满足于其在埃及和叙利亚南部的统治。这些条件宣布后,法国感到荣誉受损,异常愤怒,就在他准备宣战的时候,叙利亚爆发了反抗易卜拉欣暴政的起义。为支援起义,英国派遣一支舰队炮击并占领了贝鲁特,查尔斯·内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指挥下的突击队攻占了古老的西顿城,然后向南航行,把炮口对准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阿卡要塞。围攻还没有开始,易卜拉欣就溃败了,他父亲那几乎实现的帝国转眼间就像纸牌屋一样垮塌了。“内皮尔万岁!”帕麦斯顿喊道。一位同僚发现他“非常愉快”,说了好多有关贝鲁特和阿卡的笑话,确信法王和梯也尔“被打败了,事情就此结束了”。
。如何阻止俄国的扩张变成了主要问题——这个问题在20年后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再次出现,并仍然困扰着今天中东的外交家。英国开始全力构筑一个统一阵线来抵御俄国对这一地区事务的干预。这个统一阵线的任务就是化解土埃危机,采取联合行动,不计代价地防止任何人未来私自发动袭击的可能性。穆罕默德暂时退让了,但在1838年再次出手。一支在叙利亚的土耳其军队被他歼灭,土耳其舰队在亚历山大港向他投降,老苏丹随即在君士坦丁堡羞愧而死。法国对穆罕默德取得的荣耀大加赞许,他此时看起来似乎也即将成为一个可与萨拉丁的帝国媲美的新帝国的主人,并挂上法国的三色旗。幸运的是,沙皇极端厌恶带着资产阶级绅士派头的法王路易·菲利普和他的民主思想,所以愿意用尽各种办法挫败他,特别是能扩大英法两国间裂痕的方法。所以,沙皇同意了帕麦斯顿的联合行动计划,甚至宁愿放弃他的海峡特权。与此同时,普鲁士和奥地利也表示同意,就在法王和梯也尔(Thiers)大张旗鼓地支持穆罕默德对新近成为苏丹的小男孩提出的要求之时,四个大国悄悄在伦敦签署了协定,一起支持土耳其,强迫穆罕默德满足于其在埃及和叙利亚南部的统治。这些条件宣布后,法国感到荣誉受损,异常愤怒,就在他准备宣战的时候,叙利亚爆发了反抗易卜拉欣暴政的起义。为支援起义,英国派遣一支舰队炮击并占领了贝鲁特,查尔斯·内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指挥下的突击队攻占了古老的西顿城,然后向南航行,把炮口对准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阿卡要塞。围攻还没有开始,易卜拉欣就溃败了,他父亲那几乎实现的帝国转眼间就像纸牌屋一样垮塌了。“内皮尔万岁!”帕麦斯顿喊道。一位同僚发现他“非常愉快”,说了好多有关贝鲁特和阿卡的笑话,确信法王和梯也尔“被打败了,事情就此结束了”。

局势的发展证明了帕麦斯顿的判断。尽管梯也尔十分恼怒,但法王正如帕麦斯顿预计的那样不愿为东方的利益发动战争,东方的伟业就像海市蜃楼一样躲避着他。他不仅默许了叙利亚和阿拉伯回归土耳其,还默许将不久之后即疯癫而死的穆罕默德限制为土耳其在埃及的世袭封臣。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国加入四国于1841年7月在伦敦签署了五国协定。土耳其帝国在经受了群集的秃鹰的利爪撕扯之后,虽已衣衫褴褛,却终究得以残喘保全。这对帕麦斯顿和英国是一场彻底的胜利,通往苏伊士以及最终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就这样被打开了。
[注释]
[1] Rose’s Pitt , chap. XXVI, pp. 585-606; Marriott, pp. 153-58; Temperley, pp. 43-46. See also Cambridge BFP , Vol. I, chap. I, “Pitt’s First Decade.”
[2] Parl. Hist . XXIX, March 1791, 75-79. Quoted in Temperley, p. 44.
[3] Text in Kobler. See also Guedalla’s Napoleon and Palestine .
[4] Allison; Rose’s Napoleon , chap. IX, “Egypt” and chap. X, “Syria”; Bourienne, Vol. II; Marriott, pp. 164-92.
[5] A. L. Thiers,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 , 10 vols., Paris, 1828, IX, 63.
[6] Ibid. , II, 243.
[7] Lucien Bonaparte, Mémoires , II, chap. XIV.
[8] DNB .
[9] Ibid .
[10] Temperley, pp. 87-156; Marriott, pp. 225-49; Cambridge BFP , Vol. II, chap. IV, “The Near East and France” (covers the period 1829-47).
[11] Foreign Office, Turkey, July 12, 1833, quoted Cambridge BFP , II, 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