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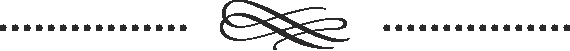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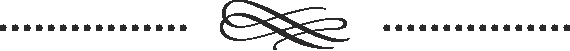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清教政权垮台后,清教徒的极端虔诚和严肃也随之消减,但并没有从英国消失。王朝复辟后,以及在其后的18世纪里,时代的主调由戴着黑色卷发头套、具有冷静的头脑、为人轻松放纵的查理二世设定。英国在紧绷了50年后,终于松了口气,决定愉快、随和一些,不再严肃。
但清教主义就跟地下的暗河一样,在不奉国教的人中间流淌着。清教徒被驱逐出重组后的英国国教会,被禁止进入政府、大学,排除在社会之外,甚至在1689年之前没有公民权,但他们的传统仍然得到了保持,并在19世纪再次浮现。在这中间的18世纪,这些不奉国教者生活在阴影中,而贵族政治盛行。按照屈勒味林(Trevelyan)的说法,这是个“贵族统治的自由年代,是法治和没有改革的年代” [1] ;是个“优秀”的年代,有秩序,讲礼貌,富于理性,尽可能地排除了希伯来文化的影响。
如果想确定18世纪的本质特征,必须调整一下起止时间,它起始于王朝复辟的1660年,一直延续到1780年代美国赢得独立,法国大革命开始,工业革命随卡特赖特的动力织机、瓦特的蒸汽机而正式开启。这是理性和自由思想的时代。科学的自然法则开始挑战《圣经》的权威。牛顿发现使苹果掉落的不是上帝而是地球引力。约翰·洛克(John Locke)可怕的逻辑开辟了不确定性的新视野。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圣经》的至上权威就像日光照射下的黄油一样融化了。信仰的安全感被知识带来的不安全感所代替。自然神论试图取代《圣经》。带着对人类理性必将战胜宗教争端的新兴信仰,自然神论者提供了一个所有具有理性的人都可以信奉的上帝,他的存在是通过自然现象来证明的,不需要通过奇迹、预言或其他超自然启示作证。
为了扭转“虔诚得可怕的清教主义”倾向,希腊主义复兴了。它使人们的头脑变得清醒,但无法满足他们对某种全能权威的渴望。阿诺德在文艺复兴时期注意到的“道德缺失”也重现了。当王朝复辟的闹剧在台上上演的时候,英国政权落入了一群毫无原则的贵族阴谋家手中。终结斯图亚特王朝和带来《权利法案》的不流血革命只是历史的逆流,在四位来自德国的乔治的统治下,政治道德下滑到了最低点。他们的统治留下了南海公司的股票泡沫(South Sea Bubbles)、腐败的选区、奴隶交易的暴利,以及在半疯国王治下争权夺利的大臣们,他们几乎无暇顾及正在失去美洲的帝国。虽然文学评论家把这个时代称为文学的“全盛时期”,但这也是贺加斯(Hogarth)画笔下泡在杜松子酒里的浪子和妓女的时代。那个时代仅有的愤怒之声来自斯威夫特(Swift),他说,在这个耶胡(Yahoos)
 的丑陋世界里,“礼貌和得体不过是个习俗而已”。
的丑陋世界里,“礼貌和得体不过是个习俗而已”。
这是高教会派(High Church)成为官方宗教的时代,有礼貌,但仅满足于为贵族孩子及其亲属提供肥缺。教会的独立精神消失了。作为国教它虽然缺少激情,但相比由十几个虔诚教会组成的无政府状况,人们仍青睐于它所提供的秩序和合法性。在一个充满简·奥斯汀笔下的牧师柯林斯先生式人物的教会里,《圣经》能得到多大权威呢?信奉《圣经》的人,无论《新约》或是《旧约》,都跟清教徒一样是极端分子。他们中没有生活舒适满足的人。在18世纪的英国,先知们的神圣怒火无法穿透吉本(Gibbon)所说的“教会的昏睡” [2] 。
不过,有一股渴望正直道德的强烈热流,在18世纪的文雅外表下涌动着。卫斯理兄弟的循道主义(Methodism)和赞美诗,与蒲柏(Pope)的《夺发记》( Rape of the Lock )或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的《教子书》( Letters to His Son )一样是时代的产物,只不过来自不同阶层而已。这个时代产生了两部历史上最杰出的著作——时代开始时班扬的《天路历程》和时代结束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如何才能概括这样的一个时代呢?吉本代表的是怀疑主义的、科学的、反基督教的,而班扬则代表有信仰的、狂热的、有使徒般美德的。一个代表知识,另一个代表信仰,或者按照阿诺德的说法,一个是希腊主义的,另一个是希伯来主义的。《天路历程》可能是《圣经》之后被最广泛阅读的英文作品。这本书被奉为第二本《圣经》,如果不受庄园主的欣赏,也至少是农舍中的第二《圣经》。有教养的阶层起初忽视这本书,但它最终却被上等社会接受,如麦考莱所言成为“唯一一本使有教养的少数人向普通民众趣味靠拢的书” [3] 。这一宗教虔诚的典范竟然与威彻利(Wycherley)描绘极端放荡的《村妇》( Country Wife )和《掮客》( Plain Dealer )在同一个十年里出现,这令人略感意外。虽然班扬属于老一代的清教徒,但他的书属于他身后的几代人,受到他们的追捧。他既是清教的继承人,也是循道宗的先声——他是清教主义和19世纪福音主义复兴运动之间的桥梁。
就在普通百姓急切地阅读基督徒去天国的历程时,俗世的智慧先生却在主导国家的事务。他不关心弥赛亚,无论弥赛亚的承诺让清教徒多么兴奋。他自然同样不关心犹太人的复国。事实上,犹太人在18世纪唯一引起注意的事就是1753年的《移民归化法案》(Naturalization Act)所引发的敌对情绪。这部法案被称为“犹太人法案”,因为它“允许所有犹太人在没有接受过基督教圣礼的情况下归化”。一位反对者警告说,允许犹太人拥有土地违反了《新约》中的预言。根据基督徒对《新约》的解读,它预言犹太人在承认耶稣为弥赛亚之前只能流浪。另有人补充说:“如果允许犹太人拥有王国的大片土地,我们如何肯定基督教将继续被视为最主流的宗教呢?”然而,法案被下议院批准,并在获得主教的同意后获得上议院的通过。但反对的小册子和抗议者像暴风雨一样扑来,法案在次年即被废止。这一动议直到1858年通过《解放法案》(Emancipation Act)后才被正式施行。
这份法案虽遭否决,但它最初能被通过反映出了18世纪启蒙运动中那种不拘泥于教义的包容精神。与此同时,18世纪的理性主义反对那种为让预言成真而支持以色列复国的论点。理性主义者认为这个论点是站不住脚的。霍布斯、休谟等理性主义作家在逐条研究过基督教的信条基础之后发现,耶稣实现了希伯来人的弥赛亚预言这种寓言性解释是“不理性的”。在理性的审视下,把《旧约》中的每一行都解读为对未来事件的预言是站不住脚的。安东尼·柯林斯(Anthony Collins)在他1713年的著作《论自由思想》( Discourse on Freethinking )中大胆地宣布,《但以理书》不是一部自传,而是由一位马加比时代的作者写成的——这就使人们以一种极为不同的角度看待其中的预言了。还有更危险的思想家怀疑《摩西五经》是否真由摩西写成。他们研究越深入就越发现,基督教根据希伯来预言而产生的对基督复临的期盼是没有依据的。
只要理性主义者仍然占据主导,人们就不会对犹太人返回锡安产生多少兴趣。不过,在理性主义者对《圣经》的历史学基础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将巴勒斯坦视为一个国家研究的新兴趣。巴勒斯坦的考古遗址不再被当做圣物来研究,而是昔日生活的反映。这方面的最早研究成果是富勒博士所写的《巴勒斯坦的毗斯迦山风景》( A Pisgah-sight of Palestine )。尽管出版于1650年,但它丝毫不受清教主义的影响,实际上富勒在性情和兴趣方面更加接近保王派。没有任何清教徒能以如此超然的态度描写《圣经》的家园。即使在他最沉重的著作中,字里行间也透着绝妙的幽默和智慧。富勒对客观、中立的追求(这使得他超然于两派之间,即使在内战最激烈的时期也是如此)使他有别于时代。他说,他著书描述巴勒斯坦的初衷是为了对真正理解《圣经》做点贡献,尽管“这些对迦南地理的现实研究在见识更广的基督徒中不再流行”。他仔细地描绘动植物、矿物资源、地形情况,不断纠正大众的错误印象。事实上,虽然《圣经》里提过好几次,但这个国家并不是个沙漠,他指出:“沙漠这个词对英国人来说似乎很可怕,好像意味着到处是废墟、野兽、悲凉,而在希伯来语里,它意味着树木稀少的地方;这些地方大多并不比英国的大公园面积大,它因幽静而非常吸引人,根本不是令人感到悲伤的荒凉之地。”
他试着澄清什么是“肘尺”(cubit)等希伯来人的丈量单位;他讨论古代的法律和习俗、家庭习惯、耕种方式、食物和衣服。他画了好多张地图,上面标注着帐篷、圣殿、战场和有尖塔的城市;画了建筑物的布局图,例如所罗门圣殿里的陈设、器具、珍宝;还画了少女、妇人、寡妇、妓女等各种女性的穿着和打扮。如果说富勒的书在内容上算不上科学,那么至少他写作的初衷是科学的。他在最后一章讨论了犹太人复国的问题,他认为能从巴比伦的流亡返回已经实现了所有预言,如果未来还有什么承诺有待兑现,那则是犹太人改宗基督教,“重新获得”原有的国土并不是必需的。他认为这只是个梦想。至于改宗,他不能肯定上帝是否真的有此意愿,但既然上帝并没有明确反对过,最好认为这便是上帝的意愿。富勒确信,尽管有各种困难,但只要上帝愿意,那么“在刹那之间,他们就会顿悟”。此时,他以无法掩盖的公平态度承认,只要基督徒继续排斥犹太人,他们就不可能改宗,因为“必须先有交谈,才可能有改宗”。
另一本畅销书是《两次耶路撒冷旅行》( Two Journeys to Jerusalem ),1704年由纳撒尼尔·克劳奇(Nathaniel Crouch)出版。他曾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廉价历史书,被约翰逊博士称为“很适合吸引低层次读者”。他的这本书,除了旅行日记,还包括:“一些有关古代和现代犹太国的著名评论”、塞缪尔·布雷特对匈牙利犹太委员会的描述、萨瓦塔伊·塞比写的有关犹太人的“奇妙幻觉”,以及关于国务委员会辩论玛拿西·本·以色列的1655年提案的报道。两次旅行包括前文(第6章)提及的亨利·廷伯莱克的“既奇怪又真实”的冒险,以及初版于1683年的描述14个英国人在1669年旅行的故事。这本旅行集似乎有稳定的读者群,因为此后的一百年里它不断再版,甚至出了威尔士语译本,最后一版印刷于1796年。
克劳奇使用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这个笔名发表了那些“著名评论”,他把大量精力用于回答困扰了几代作家的巴勒斯坦问题:如此荒凉的土地如何能支撑在《圣经》、罗马和拜占庭时代那些繁忙、繁荣的城市。当在我们的时代英国政府白皮书以这片土地无法支撑更多人口为由削减犹太移民时,这个被命名为“经济吸纳能力”的问题在英国议会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但是伯顿(或克劳奇)在200年前写作的时候,尚无需考虑如何安抚阿拉伯人或“政治上限”的问题,他采用了当时那个时代特有的现实主义精神解答这个问题。假定恢复了“古代”的精耕细作,他估算如果每人每天定量2磅6盎司面包,一英亩土地每年能养活四个人。“但由于我们以色列人胃口大,让我们把定量加倍,即每天4磅12盎司”,或者说每英亩可以养活两个人。他估计古代犹太王国的面积是336.5万英亩,减去一半无法耕种的土地,他最后的结论是每英亩仍然能养活一个人。350万这个数字与现在以色列政府的目标惊人地相似,但这个数字被当时的所有政府白皮书专家嘲笑为疯狂的、不可能的数字。
伯顿接着解释了巴勒斯坦给人的荒凉印象,是因为旅行者看到的仅是从雅法到耶路撒冷之间的乡村,这里从来不以土地肥沃闻名,且“由于野蛮异教徒疏于耕种……他们不断打仗和毁坏,致使这里变得跟沙漠一样荒凉”,“像被上帝抛弃的土地”。然而,在《圣经》时代这里流淌着奶与蜜,需要感谢以色列人的耕种,他们修建梯田、施以肥料,不把一分土地浪费在修建“狩猎场、大道、滚木球草场、花园”上。
巴勒斯坦在伊斯兰统治下的衰败也被那14个英国人看到了。他们是黎凡特公司在阿勒颇代理站的员工,他们把所看到的情况写进书里。他们经过凯撒利亚和雅法北面的农村时,发现那里“破败不堪,住着一大群野蛮的阿拉伯人”。雅法不仅是英王理查曾经英勇战斗过的地方,还是大批搭乘威尼斯客船的朝圣者下船的地方,可如今这些商人认为这里已经变成劣等港口。主要贸易货品是制肥皂用的草碱、棉花和棉纱。既不跪拜也不再陷入沉思,这些300年前旅行者的举止就和今天导游带领的旅游车中的旅客一模一样。在耶路撒冷,他们挤在访客登记簿前寻找自己熟悉的名字,并数出自1601年以来英国访客共有158名。在伊甸园遗址,“我们花了点时间削木棍,把我们的名字刻在大树上”。在通往伯利恒的路上,他们遇到一些本地基督徒。“这些人的手艺是在你手臂上刺上圣墓或你喜欢的圣经故事图案;他们用蓝色墨水,用两根针不停地在你胳膊上刺。”每个人都选了画册中的图案,然后在胳膊上刺上了相应的花样。
1776年,即一百多年后,阿勒颇代理站又有一批人来到这里。记录旅途的是理查德·蒂龙(Richard Tyron),他语气平淡,就好像一个乡下人来到伦敦旅行一样。他们丝毫不在乎古代预言或预言的实现。蒂龙看到周围一片废墟,简单地评论说“这里就像被诅咒的土地”。在这两次访问之间的一个世纪里,几乎没有英国人来巴勒斯坦。此时时髦的旅行地是具有古典风格的希腊和罗马。只有定居东方的黎凡特公司的代理人和牧师偶尔来巴勒斯坦游逛,但不是为寻找宗教体验,更多的是为了解这里的情况。
阿尔及尔牧师托马斯·肖(Thomas Shaw)就是其中一位。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手绘当地植物上,他1738年出版的游记中有极其优美的铜版印刷插图。同样,阿勒颇牧师亨利·蒙德雷尔(Henry Maundrell)也并未沉浸在宗教喜悦之中,而更喜欢记录古代铭文、研究废墟、寻找古代蓄水池和沟渠的遗迹。他的《从阿勒颇到耶路撒冷的旅程》首版于1697年,再版两次,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多次被收录在其他游记集中。他写道,虽然巴勒斯坦如今是“悲惨、干旱、荒凉的不毛之地”,但“这些石地和山坡在古代显然是被泥土覆盖和被人耕种的”。他精彩而简洁地解释了土壤是如何被侵蚀的,展示了古人为“耕种这些山坡”是如何建起土墙,形成“从山脚到山顶一阶又一阶的覆盖着肥沃土壤的土床”。在死海,蒙德雷尔用自己的观察驳斥了过去的传说。他写道,鸟从水面飞过,不会落入水中死掉。他还在岸边发现有牡蛎壳等水生生物迹象。他还如实地记录了土耳其人统治臣民的办法——通过在民族之间制造矛盾(后来的大英帝国也使用了同样的办法)。“通过这种手段可以在民众中制造利益和党派对立,防止他们团结在某位亲王下——如果他们真这样做(他们人数众多,并且在当地占主导地位)就可以推翻土耳其人的统治,实现自治。”
18世纪有关巴勒斯坦的最博大的著作是由理查德·波科克(Richard Pococke)所写,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希伯来和阿拉伯学者。他的三卷本《东方介绍》( Description of the East )在1743—1745年间出版,其中第二卷介绍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
波科克这位未来主教代表了18世纪对待巴勒斯坦的最典型态度。他在题献中将介绍圣地的那卷献给了物质美德的典范——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他在前言中说,圣地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那里的许多地名是“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并乐于有所了解的”。秉承这种精神,他从埃及出发,徒步走完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途经的荒野,决定精确地描绘这条著名的路线。他观察了每一处地标,详细地描述植被,在各种海拔下画了无数幅平面图和地图,画出了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他抄录下石刻文字,寻找摩西40年路途中的每一处落脚地。他尽量避开贝都因人(Bedouin),因为“他们是个很坏的民族”。他还遇到了一个似乎信奉犹太教的友好部落,他推测他们可能是摩西的岳父叶忒罗(Jethro)的后裔。
到耶路撒冷之后,他逐一研究当地的传统,看看是否与已知的事实、历史、可能性相符,绝不轻信。有根石柱据说是《圣经》中的押沙龙(Absalom)之柱,很受旅行者喜爱。他对其真实性的攻击就像福尔摩斯解开泥脚印之谜一样:“约瑟夫斯称之为大理石柱子,并说它距离耶路撒冷有2化朗(约400米),但这个汲沦溪(Kedron)流经的山谷可能是王谷。由于距离不符,这是否是那座纪念碑值得怀疑。真正的押沙龙之柱可能在比欣嫩子谷(Gehinnon)更偏西南的地方。但如果这里是王谷,即撒冷王麦基洗德与亚伯拉罕相会的地方,这就能证明耶路撒冷是古代的撒冷城。”最后,他提示那根柱子属爱奥尼柱式,说明它明显晚于押沙龙的年代。
波科克遍历了整个国家,从死海一直走到加利利,不错过任何一处可能与著名历史事件相关的地方。他在埃斯德赖隆平原(Plain of Esdraelon)上看到的蓄水池、池塘、水井,显示出这片土地过去是如何灌溉的。在拉姆拉附近,他看到了绽放的郁金香田野,于是他推测这里肯定是盖过所罗门所有荣耀的“百合花田野”。他的著作为《圣经》注入了新生。将他精心制作的清真寺和圣墓雕版画(考古学家后来证明他的画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都加起来,其作用也不如这些郁金香,包裹在巴勒斯坦身上的昔日裹尸布由此被徐徐揭开。
[注释]
[1] Social History , III, chap. II, 47.
[2] From his Autobiography .
[3] From Macaulay’s article, “Bunyan,”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 11th ed., p. 806,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