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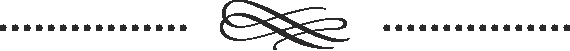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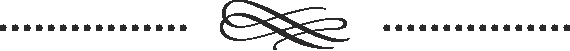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1649年是清教统治英格兰的顶点和中点,两名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英国清教徒向政府请愿:“英格兰和荷兰居民应该最先准备好,把以色列的儿女用船送到他们父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之地和永恒遗产上去。”这份请愿还进一步要求,犹太人“应再次被接纳在这片土地上与你们一起居住和经商”
 。
。
这份请愿书的作者是乔安娜和埃比尼泽·卡特赖特(Joanna and Ebenezer Cartwright),他俩不仅要求英格兰协助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还要求废止爱德华一世350余年前颁布的驱逐犹太人的法令。促使他们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呢?为了理解他俩的动机,我们必须了解《圣经》通过清教运动带来的变革。它对时人思想的影响就好像是将今天的报纸、广播、电影、杂志的传播力都集中于一本记录上帝圣谕的书中,并通过最高法院的世俗权威进一步放大。清教徒的思想主要受《旧约》主导,因为《旧约》描述了一个坚信自己被上帝选中在地球上替他行事的民族。清教徒把这个故事放在自己身上,认定自己继承了亚伯拉罕与上帝的约定,是以色列圣徒的再现,是耶利米所说的“上帝的战斧”。他们追随着先知,从《诗篇》中获得慰藉。他们的虔诚、服从、启示不是来自耶稣的天父,而是万军之耶和华(Lord God of Hosts)
 。《圣经》是上帝启示给他的选民的语录,是对他们的指令,无论在家中或是战场,议会或是教堂。
。《圣经》是上帝启示给他的选民的语录,是对他们的指令,无论在家中或是战场,议会或是教堂。
到本书上一章为止,我们已经讲到了约公元1600年,在英国人心目中,巴勒斯坦仅是一片纯粹的基督教圣地,但不幸落入穆斯林手中。但此时,这片土地被认为是犹太人的故土,《圣经》中承诺以色列人将会重返的土地。实现《圣经》中的承诺成为清教徒的重点。随着清教的兴起,让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的运动在英国开启了。
这场运动并不是为了犹太人本身,而是为完成《圣经》中对犹太人的承诺。根据《圣经》的说法,当以色列人回到锡安后,全人类的以色列国将会到来。此时弥赛亚,或者按基督教的术语——基督将再次降临。当然,在清教徒眼中,犹太人重返家园意味着犹太国将皈依基督教,这是他们认为的承诺被实现的标志。就是这个期待在激励着卡特赖特母子,正如他俩坦言:“写这份请愿书的人在这座城市里(阿姆斯特丹)与一些被称为犹太人的以色列人很熟悉……在与他们交谈并仔细研读了先知的预言之后,他们和我们发现预言就要实现了;他们与我们将会一起见证以马内利(Emanuell)
 ——生命、光明和荣耀之神……为了虔诚地实现他的荣耀,请愿者在这里谦恭地祈祷……”后面紧跟着我们前面引用的文字。
——生命、光明和荣耀之神……为了虔诚地实现他的荣耀,请愿者在这里谦恭地祈祷……”后面紧跟着我们前面引用的文字。
允许犹太人再次进入英格兰有两个理由。第一,清教徒认为由于他们的教义比较接近犹太教,一旦犹太人与清教徒接触后,便不会抵制皈依基督教了。“英国人更有条件说服他们。” [1] 杰出的清教牧师亨利·杰西(Henry Jessey)在1656年写道。第二,严格的《圣经》尊崇者坚持说,只有犹太人流散到各国的过程完成后,他们才能开始返回锡安。所以,犹太人必须先来到英格兰,才能再回巴勒斯坦。
卡特赖特的请愿代表了这些想法,它不是孤立的古怪行为,而是时代的产物。从1620年“五月花”号轮船载着英国清教徒首次远航北美,到1666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期间,英国都处于一种狂热的状态,这也许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段狂热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英国,用卡莱尔(Carlyle)的话说,陷入“对清教的可怕虔诚中”
[2]
,是大叛乱的时代,这期间发生的弑君事件给英国带来的罪恶感使它保留君主制至今;这一时期的英国是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的英国,他就“如同上帝的仆人,手执《圣经》和利剑”
 。
。
紧随着清教徒,希伯来文化借助《旧约》的传播入侵了英格兰。此时的英格兰已进入“后文艺复兴”时期,为了将两千多年前一个中东民族所特有的伦理、律法和举止应用到此时的英国社会,传播到英国的希伯来文化出现扭曲。由于清教徒对《旧约》的章节和诗篇的挚爱,他们无惧于作出跨越两千年的精神跳跃:他们将自己想象为生活在亚伯拉罕时代的牧民,正摸索着从偶像崇拜向一神论转变;或是逃离埃及、战胜法老的奴隶;或是扫罗王和大卫王时代开辟疆土建立新国家的武士。他们不在乎希伯来人的故事谈论都是野蛮的古老传说。故事中的希伯来人在实现一种法治公社生活、建立国家和抵御敌人的努力中挣扎。他们像西绪福斯(Sisyphus)一样一次又一次地爬出罪恶的泥沼,走向先知指出的道路。他们不在乎这个故事跨越了从亚伯拉罕到马加比将近1500年的漫长时间。清教徒以同样的热情传颂着这些故事。
这样的故事不适合作为原则和先例照搬到17世纪的英格兰,但清教徒正试图这样做。早在1573年——根据伦敦主教桑兹的指控
 ——清教徒的信条即是“摩西的律法应同样约束信仰基督教的贵族,而且不能有半点偏差”。清教徒严格按照《旧约》的字面意义行事,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觉得自己也是一群在上帝的指引下与偶像崇拜者和暴君斗争的人。上帝的言语、旨意和律法写在了《旧约》里,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他们越是严格地遵循,他们的正义信念就越是牢不可破。“上帝与你们的敌人有争执,”克伦威尔在给一位将军的信中说,“从这个方面看,我们是在为上帝而战。”
[3]
——清教徒的信条即是“摩西的律法应同样约束信仰基督教的贵族,而且不能有半点偏差”。清教徒严格按照《旧约》的字面意义行事,因为他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们觉得自己也是一群在上帝的指引下与偶像崇拜者和暴君斗争的人。上帝的言语、旨意和律法写在了《旧约》里,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他们越是严格地遵循,他们的正义信念就越是牢不可破。“上帝与你们的敌人有争执,”克伦威尔在给一位将军的信中说,“从这个方面看,我们是在为上帝而战。”
[3]
清教徒对《旧约》的狂热直接源自英国国教会对他们的迫害。教会追捕他们,折磨他们,甚至把他们送上绞刑架,因为他们拒绝承认《圣经》和他们宗派之外的任何权威。他们对主教制度的仇恨与新教徒对罗马教皇制的仇视一样,理由也是相同的:他们认为,无论是主教制还是教皇制中的统治集团,都是站在人与上帝之间的自封的入侵者,他们所拥有的利益和权力,显然都是由人赋予的,是对宗教的一种嘲弄。清教的基本信仰是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解读上帝的律法,这些律法体现并仅体现在《圣经》中,它高于其他一切权威,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
由于教会和政府是一体的,国王必然联手教会镇压独立派(Independents)。独立派是不同于长老会(Presbyterians)的清教派系,他们要求得到自主进行宗教集会的权利。英王詹姆斯反驳道:“没有教会,就没有英王。”这句著名的反驳之词反映出詹姆斯比清教徒更早认识到清教运动对英国君主制的根本威胁。在仇恨主教制之余,这些清教徒不可避免地开始仇恨君主制,结果就是共和制。他们的宗教原则就是他们政治原则的种子和根源。因为对主教权力神授的否定必然导致对君权神授的否定,所以对个人信仰自由的认可,也自然导致对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由的认可。正如麦考莱(Macaulay)所言,从认可“教会权力应根植于宗教大会,到政府权力应根植于议会”仅需要一小步。
麦考莱接着说,宗教迫害“在他们身上产生了和以往一样的影响。像其他受迫害的宗教派别一样……他们觉得对自己敌人的仇恨就是对天国敌人的仇恨”。在《旧约》中,“对暴躁又阴郁的人来说,不难找到大量可以按照自己意愿加以扭曲的东西”。他们开始喜欢《旧约》中的一切感情和习俗。他们推崇希伯来语,但拒绝对写成福音书和保罗书信
 的语言给予同样的尊重。“他们给孩子洗礼取名时,不用基督圣者的名字,而用希伯来元老和武士的名字。他们把教会每周用于纪念耶稣复活的古老节日变成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从《士师记》和《列王纪》中寻找自己的行为规范。”
的语言给予同样的尊重。“他们给孩子洗礼取名时,不用基督圣者的名字,而用希伯来元老和武士的名字。他们把教会每周用于纪念耶稣复活的古老节日变成犹太人的安息日。他们从《士师记》和《列王纪》中寻找自己的行为规范。”
麦考莱在记述清教徒那些令人不快的特征时越写越气愤:“那步态,服装,平直的头发,一本正经的苦相”,不许正常行乐的禁令,鼻音和古怪的隐语被“骤然引入英语,以及从遥远的年代和国家的最极端的诗篇中借鉴来的比喻,也被应用于普通英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4]
麦考莱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通常不会在自己强大的辞藻中显露偏见,但他在这里的叙述并不公允。他既没有谈及旧体制中清教徒极力想克服的弊端,也没有谈到清教徒的美好理想。他在这方面不幸成为了典型。由于清教徒不招人喜欢,他们很少得到公正的评价,而更多的是成为嘲笑的对象。尽管如此,他们为民主社会奠定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议会制政体的安全性;第二,信仰自由。包容的原则是他们建立的,尽管他们没能付诸实践——这个原则由布朗、福克斯和罗杰·威廉斯制定,引领清教徒前辈来到美洲,并在新大陆上建立了一个以之为道德基础的新社会。
如果说清教徒放弃了怜悯和宽容而选择了《旧约》中更加好斗的一面,这是因为他们也是在不利的情形下试图建立原则和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约书亚的战斗号角比转过另一侧脸让对手打更加合适。在《旧约》中,他们不仅找到了杀敌的理由,还找到了荣耀。扫罗王“组织一支军队,重击亚玛力人,把以色列人从敌人的压迫中解救出来”。当扫罗王宽恕亚玛力国王亚甲的时候,先知撒母耳不是抓住亚甲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吗?“于是,撒母耳在吉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砍成碎片。”
查理一世(Charles I)就是亚甲,或者可以说是所罗门王的继任者罗波安(Rehoboam)。罗波安不肯听从人民的意见,反而粗鲁地说:“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听到这样的话,以色列的十支派起义了,他们叫喊道:“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当查理一世坐马车驶过白厅街时,有人将一张纸条扔进车厢,上面写着“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 [5]
或许查理和他的保王派是法老和他的军队。当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和纳斯比(Naseby)取得对英王的胜利后,人们用摩西打败埃及人后唱的歌谣庆祝:“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啊,你的右手摔碎仇敌。” [6] 与之相对,保王派就是以东(Edom)、摩押或者巴比伦的孩子。耶利米面对摩押大怒道:“禁止刀剑染血的人必受诅咒。玛德缅啊,你必被砍倒;利剑必追赶你……上帝说,我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看我惩罚巴比伦之王和他的土地,我要让以色列人再次回到他们的家园……巴比伦必成为废墟,成为巨龙的居所,令人惊骇,令人蔑视,没有一个居民。”
英国人向来不喜欢自己处于激动情绪中,后世几乎为清教徒感到羞耻。坎宁安(Cunningham)在他的经典英国经济史著作中写道:“清教的大方向是抛弃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并用犹太人的习俗取而代之。”他继续说道,清教徒遵循“古老犹太人的行为准则,而不是神谕的基督教伦理……这使国内外社会的道德水平都退化到了更低层次上”。
 不过,坎宁安并没有进一步分析,与清教徒在德罗赫达(Drogheda)屠杀爱尔兰人以及其他不光彩事件中所展示出的道德水平相比,在“神谕的基督教伦理”指导下,亨利八世处死费希尔和莫尔,在圣巴托罗缪节前夜对胡格诺派的大屠杀,宗教审判中的严刑拷打和火刑,这些行径是否比清教徒的作为更高尚呢?
不过,坎宁安并没有进一步分析,与清教徒在德罗赫达(Drogheda)屠杀爱尔兰人以及其他不光彩事件中所展示出的道德水平相比,在“神谕的基督教伦理”指导下,亨利八世处死费希尔和莫尔,在圣巴托罗缪节前夜对胡格诺派的大屠杀,宗教审判中的严刑拷打和火刑,这些行径是否比清教徒的作为更高尚呢?
的确,清教徒所效仿的古代希伯来人的睚眦必报,在道德层面上要低于山上宝训(Sermon on the Mount)中所宣扬的理念,就如同它们在道德层面上低于摩西在西奈山上所获得的十诫一样。以色列人的兴衰史表明他们并没能坚定地遵守西奈山的训诫,就如同基督教世界未能谨守耶稣的训诫一样。基督徒的道德训诫只有一个问题——总体而言,基督徒并不能实践这些训诫。如果说十诫代表了人们可以努力去实践的法典,那么山上宝训就是社会根本无法领会的法典。
虽然清教徒并未否定《新约》,但有一些极端分子确实拒绝承认耶稣的神性,至死不改。甚至温和的清教徒在向詹姆斯一世提出的《千人请愿书》
 中,也请求在教堂里可以不再向耶稣的名字俯首。在“净化”基督教中的法衣、圣礼、跪拜等努力中,他们中的极端分子想重返过去那种上帝的神性不与他人分享的旧观念,这同犹太教的口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表达的观念一样。宗教中的真理是无法争辩的。独立派在对旧制的推崇中找到了新的支持者。卡莱尔是英国历史学家中唯一对他们怀有同情的人。他称呼他们是“我们最后的英雄,具有神性的人从此在英格兰消失了;信仰和诚实让位于伪善说教和形式主义。古代那种为操各种语言和社会形态的民族所追求的‘上帝的统治’,被如今非上帝之魔鬼的统治所取代”
[7]
。
中,也请求在教堂里可以不再向耶稣的名字俯首。在“净化”基督教中的法衣、圣礼、跪拜等努力中,他们中的极端分子想重返过去那种上帝的神性不与他人分享的旧观念,这同犹太教的口号“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所表达的观念一样。宗教中的真理是无法争辩的。独立派在对旧制的推崇中找到了新的支持者。卡莱尔是英国历史学家中唯一对他们怀有同情的人。他称呼他们是“我们最后的英雄,具有神性的人从此在英格兰消失了;信仰和诚实让位于伪善说教和形式主义。古代那种为操各种语言和社会形态的民族所追求的‘上帝的统治’,被如今非上帝之魔鬼的统治所取代”
[7]
。
但卡莱尔是个古怪的人,他跟清教徒一样充满激情,但并不公允。对清教带给英国人思想的影响做出更真实估计的,是更理性的马修·阿诺德。他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写道,清教主义是希伯来精神的复兴,是对文艺复兴前夕兴起的希腊精神的回应。阿诺德本人爱好希腊文化,他称希腊文化的精髓是进行“正确的思考”,而希伯来文化的精髓是“在法律框架内做正确的事”。他说,清教主义试图弥补伴随着文艺复兴而来的道德缺失。清教徒怀念对法律的服从,这显示出了“一种亲近希伯来人主要生活偏好的信号”。清教主义给英国留下了永恒的烙印。“我们这个种族,”阿诺德宣称,“信念的坚定、坚韧、强烈(我们的力量很大程度来源于此)……与希伯来人十分相似。这反映在清教主义中,并且在过去两百年里对我们的历史有极大的影响。”
随着清教难民于1604年开始在荷兰定居,以色列人重返家园的历史出现了重大转折。第一个记述清教难民历史的史学家丹尼尔·尼尔(Daniel Neal)写道,他们说,“去歌珊
 定居,无论它在哪,都比生活在埃及人的奴役下好”。
定居,无论它在哪,都比生活在埃及人的奴役下好”。
来到荷兰的,还有上个世纪逃避西班牙和葡萄牙宗教迫害的犹太难民。这些人在阿姆斯特丹建立起一个欣欣向荣的社群,包括很多在荷兰殖民地贸易和欧洲大陆与黎凡特贸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富商。在荷兰,清教移民踏着古代希伯来人的脚印与现代犹太人产生了接触,而犹太人也接触到这个提倡为包括犹太教在内的所有宗教提供自由的基督教新派别。(在受到迫害的时候他们提倡包容,但当他们获得权力后,便开始看到宗教自由的坏处了。)
实际上,从宗教典礼以外的教义上看,清教独立派与犹太教没有多大区别,这个事实双方信徒都承认。但在极端清教徒中出现了一些派别,他们宣称自己在信仰上是犹太人,并遵循利未族的律法。
 其中有些坚定的教徒还去欧洲大陆求教于犹太拉比,熟读《塔木德》法典和文献。1647年,英国长期议会拨款500英镑用于购买“意大利一位有学识的犹太拉比的珍贵藏书”。
其中有些坚定的教徒还去欧洲大陆求教于犹太拉比,熟读《塔木德》法典和文献。1647年,英国长期议会拨款500英镑用于购买“意大利一位有学识的犹太拉比的珍贵藏书”。

在清教徒逐步接近犹太教的过程中,他们将犹太人也包括在宗教宽容的大旗下。在阿姆斯特丹流亡的伦纳德·布舍尔(Leonard Busher)于1614年写成的小册子《宗教和平或为宗教信仰自由的请愿》,是最早呼吁全面宗教自由的出版物。
 罗杰·威廉斯在他更有名的小册子《假名正义实为迫害的血腥信条》(1644年)中,开篇便说明了原则:“按照上帝的旨意,自上帝之子我主耶稣降临以来,各国、各民族之人即被赋予自由信仰的权利,无论多神教、犹太教、土耳其教,还是敌基督者……上帝不强求在文明国家里保持宗教信仰的一致……在一个国家或王国中,即使允许犹太教或非犹太教等各种对立宗教的存在,真正的文明与基督教都可以繁荣发展。”
罗杰·威廉斯在他更有名的小册子《假名正义实为迫害的血腥信条》(1644年)中,开篇便说明了原则:“按照上帝的旨意,自上帝之子我主耶稣降临以来,各国、各民族之人即被赋予自由信仰的权利,无论多神教、犹太教、土耳其教,还是敌基督者……上帝不强求在文明国家里保持宗教信仰的一致……在一个国家或王国中,即使允许犹太教或非犹太教等各种对立宗教的存在,真正的文明与基督教都可以繁荣发展。”
威廉斯是在大西洋对面的新世界写下这番话的。在英格兰,只有癫狂的、主张分裂的狂热教派,以及如霍尔主教(Bishop Hall)早前所言的“鞋匠、裁缝、毡匠这些跟垃圾差不多的人”
 ,才真正相信这类想法能付诸实践。在“普赖德清洗”
,才真正相信这类想法能付诸实践。在“普赖德清洗”
 之后独立派取得胜利的那几个动荡的月份里,一个名叫“程序委员会”(Council of Mechanics)的决策机构投票做出一项决议,主张应“包容所有宗教信仰,包括土耳其人、教皇派、犹太人的信仰”
之后独立派取得胜利的那几个动荡的月份里,一个名叫“程序委员会”(Council of Mechanics)的决策机构投票做出一项决议,主张应“包容所有宗教信仰,包括土耳其人、教皇派、犹太人的信仰”
 。但理想主义再次服从于政治现实。在克伦威尔与极端清教徒的斗争中,宗教自由的请求最终还是消失了。一些疯狂的派别要求克伦威尔下台,为千禧年和圣徒的王国
。但理想主义再次服从于政治现实。在克伦威尔与极端清教徒的斗争中,宗教自由的请求最终还是消失了。一些疯狂的派别要求克伦威尔下台,为千禧年和圣徒的王国
 让路,克伦威尔因害怕助长这些极端派别,放弃了将勇敢的宗教包容原则写进法律。“我宁愿允许伊斯兰教在我们中间传播,也不愿上帝的信徒被迫害。”
让路,克伦威尔因害怕助长这些极端派别,放弃了将勇敢的宗教包容原则写进法律。“我宁愿允许伊斯兰教在我们中间传播,也不愿上帝的信徒被迫害。”
 护国公克伦威尔曾如此说。但他却无法容忍平等派(Levelers)和第五君主国派(Fifth Monarchy Men)
护国公克伦威尔曾如此说。但他却无法容忍平等派(Levelers)和第五君主国派(Fifth Monarchy Men)
 。
。
与此同时,一些清教理论家改进了让犹太人重返英国的计划,目的是使犹太人在更好的条件下尽快皈依基督教。什么能比完成这件拖延已久的事能更有力地证明清教理想的正义性呢?罗杰·威廉斯反对强制国教时的一个理由即是,“我们所盼望的犹太人皈依基督的愿望”将必须被放弃。按照公认的神学理论,当犹太人皈依基督后,便可以复国了。早在1621年,就有一本名为《伟大的犹太复国与继之而起的全世界向基督教的皈依》(
The World’s Great Restauration or Calling of the Jews and with them of all Nations and Kingdoms of the Earth to the Faith of Christ
)的专著。作者是国王大律师亨利·芬奇爵士(Sir Henry Finch),他预言犹太人在不远的未来将回到自己的领土上,建立起一个世界范围的帝国。
 在英国的所有事项中,以色列复国仍是最重要的。根据与芬奇同时代的托马斯·富勒的说法,这本书被理解为在暗示“所有基督教国君应该交出权力,去做那个至高无上的犹太帝国的封臣”
[8]
。考虑到詹姆斯一世对王室特权的极端敏感,他立即逮捕芬奇并以叛国罪对他进行审判的做法一点都不令人惊讶。芬奇在发誓否定所有有损王权的章节后最终被释放。
在英国的所有事项中,以色列复国仍是最重要的。根据与芬奇同时代的托马斯·富勒的说法,这本书被理解为在暗示“所有基督教国君应该交出权力,去做那个至高无上的犹太帝国的封臣”
[8]
。考虑到詹姆斯一世对王室特权的极端敏感,他立即逮捕芬奇并以叛国罪对他进行审判的做法一点都不令人惊讶。芬奇在发誓否定所有有损王权的章节后最终被释放。
这本书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很难估计。一方面,由于这本书受到打压,其思想很可能未能得到传播;另一方面,对这本书的打压和对其作者的审判可能反而激发起人们的兴趣。总之,这本书提出的理念并没有消失。在下一代人中,清教的左翼独立派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最终获得了政权,他们的人数、影响力和愤怒都在逐年增长。随着独立派的发展,希伯来文化的入侵四处蔓延起来。越确信自己是在敌人中间为上帝行事的上帝选民的化身,他们在语言和习俗上就越靠近希伯来人。英格兰出现了一波按照《旧约》给婴儿取名的浪潮。
 盖伊、迈尔斯、彼得、约翰这样的传统名字,被伊诺克、阿莫斯、奥巴代亚、乔布、赛斯、伊莱
盖伊、迈尔斯、彼得、约翰这样的传统名字,被伊诺克、阿莫斯、奥巴代亚、乔布、赛斯、伊莱
 这样的名字取代。玛丽、莫德、玛格丽特、安妮,则让位于萨拉、丽贝卡、德博拉、埃丝特
这样的名字取代。玛丽、莫德、玛格丽特、安妮,则让位于萨拉、丽贝卡、德博拉、埃丝特
 。在赫特福德郡,一个名叫昌西(Chauncy)的人给自己的六个孩子分别取名为艾萨克、伊卡博德、萨拉、巴纳巴斯、纳撒尼尔、伊斯雷尔
。在赫特福德郡,一个名叫昌西(Chauncy)的人给自己的六个孩子分别取名为艾萨克、伊卡博德、萨拉、巴纳巴斯、纳撒尼尔、伊斯雷尔
 。《圣经》中的名字被洗劫一空,而且越古怪、冷僻的名字越受欢迎,比如所罗巴伯或哈巴谷,甚至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剧作家考利(Cowley)为讽刺这种风尚,创造了一个名叫卡特的人物,此人在变成清教徒后宣称:“我不能再用卡特这个名字了……我的新名字叫亚伯尼歌。有个幻影在钥匙孔中对我说:‘你应该叫自己亚伯尼歌。’”
。《圣经》中的名字被洗劫一空,而且越古怪、冷僻的名字越受欢迎,比如所罗巴伯或哈巴谷,甚至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剧作家考利(Cowley)为讽刺这种风尚,创造了一个名叫卡特的人物,此人在变成清教徒后宣称:“我不能再用卡特这个名字了……我的新名字叫亚伯尼歌。有个幻影在钥匙孔中对我说:‘你应该叫自己亚伯尼歌。’”
 恶人和苦命人的名字尤其流行,这可能是自我惩罚的一种形式。许多人给孩子取名为在《圣经》中曾被其兄奸淫的她玛,将钉子钉入睡在自己帐篷里的西西拉头中的雅亿,以及饱受苦难的约伯。
恶人和苦命人的名字尤其流行,这可能是自我惩罚的一种形式。许多人给孩子取名为在《圣经》中曾被其兄奸淫的她玛,将钉子钉入睡在自己帐篷里的西西拉头中的雅亿,以及饱受苦难的约伯。
对《旧约》的狂热并未局限于洗礼盘。《圣经》研究和注释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学术活动,大学里充斥着神学研究,而希伯来语则成为进行神学研究必须掌握的三大神圣语言之一。1644 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公务员必须通过阅读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经文的考试。
[9]
希伯来语甚至入侵了文法学校。当时的一部讽刺剧,讽刺一位女教师“用迦勒底语教编织课,拿希伯来刺绣当样品”。
[10]
弥尔顿从小就学习希伯来语,并在《说教育》中建议在文法学校开设希伯来语课,“使学生可以读经文原文”。在那个著名传言中,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描绘了弥尔顿失明后,一醒来“就让人用希伯来语给他朗诵《圣经》……然后陷入沉思”。

学者马修·普尔(Matthew Poole)每日凌晨三四点起床,吃一只生鸡蛋,然后写作他的《圣经评论大纲》( Synopsis Criticorum Bibliorum )直到傍晚。他这部五卷本的皇皇巨著采用双栏排印,共有5000页之巨。在英王詹姆斯时代译经者的引领下,下一代学者进一步钻研古代语言和民间传说。他们就像猎狗一样,鼻子贴着地面,深入探索了古叙利亚文、迦勒底文、阿拉伯文文献的沃土。厄谢尔(Ussher)大主教根据自己的研究制作了一份世界年表。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仔细分析了《旧约》中提及的异教神灵,完整地研究了异教的信仰。爱德华·利(Edward Leigh)在1646年出版了一本当时最完整的希伯来语词典。 [11]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又出现了包含九种古代语言的多语种圣经合参,其中包括撒马利亚语、埃塞俄比亚语和波斯语。
爱德华·波科克(Edward Pococke) [12] 是多语种圣经合参的编者之一。1630—1635年间,他在黎凡特公司的阿勒颇代表处做牧师。波科克的学识渊博,曾担任牛津大学希伯来语教授和首任阿拉伯语首席教授。他在阿拉伯史方面的开创性著作《阿拉伯史》( Specimen Historiae Arabum )和他编辑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对密西拿(Mishna)口述律法的评述分别是牛津大学的首部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出版物。波科克用从叙利亚带回的球果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的花园里种下了一棵无花果树和几棵雪松。在他去世三百年后,这两棵树像所罗门时代的遗物一样依旧枝繁叶茂。
这些丰富的知识并没有局限于学者中间:通过各种摘要、专著、索引、讲座,以及牧师、非神职传道者和任何想要讲道之人的布道,这些知识在民众中传播开来。成人和孩子都能背诵《圣经》中的大段文字,并按经文中的指导生活。这些资源向所有人开放,并不需要神职人员的解读,《圣经》改变了民众的道德生活。
圆颅党人(Roundhead)唱圣歌、随身携带《圣经》的习惯为世人所熟知。查尔斯·弗思爵士(Sir Charles Firth)曾在他关于克伦威尔军队的著作中引用当时人的描述:“早晚都要在苍天下做布道和祷告,只不过军鼓声代替了教堂的钟声。”早晚都会从帐篷里传来“圣歌、祈祷和诵经声”。在马斯顿荒原,保王军的一个连迷路了,几乎走入圆颅党人阵中,只因“听到对方唱圣歌才知道是敌人,于是转头逃跑”。官兵都热衷于按照自己的神学观点布道,这引起牧师的不满。牧师特别反对军官坐在马背上布道,但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不让他们布道,他们就不能上阵打仗。”
克伦威尔和副官在制订作战计划时,甚至从《圣经》中寻找指导和先例。作战会议的议程包括祈祷和读经。作战时的口号是:“万军之耶和华!”胜利后在战场上的庆祝方式是唱圣歌颂扬上帝。克伦威尔在讲话中很爱引用圣歌和先知。根据司各特的记录,克伦威尔讲话中“有浓重的教义意味”。司各特在他的小说《伍德斯托克》( Woodstock )中塑造的克伦威尔可能并非格外夸张。小说中的克伦威尔说自己是“受使命召唤为以色列做大事”的人;说斯图亚特王朝“折磨以色列长达50年之久”;谈论“那个犹太公会”;说英格兰是“我们英国人的以色列”、“我们英国人的锡安”。他命令部队静默行军,“就像基甸行军去攻打米甸人一样”。当一个保王党家庭为英王查理提供藏身地和保护时,克伦威尔愤怒地称他们是“在以色列人即将永远摆脱苦难之时帮助西西拉逃跑”的人。他的士兵称他是“耶西的英格兰儿子”,并将他的信念、力量和智慧与耶西之子大卫王相比。保王党则被称为“异教偶像崇拜分子”,在战场上高呼“打倒巴比伦!”,而本阵营中的极端分子被称为“持异见的拉比”。
司各特在《伍德斯托克》中描绘的生动场景虽非当时的记录,但看来似乎可信。清教徒对《旧约》中人物的姓名、生活经历、个人历史都极为熟悉,这使得他们熟知犹太人的历史和传统,知道犹太人的永恒希望:“明年耶路撒冷见。”当时的犹太人普遍认为这一希望即将实现。在英格兰和其他新教国家,人们都认为1666年是决定犹太人命运的年份,他们要么皈依基督教,要么恢复他们在俗世间的王国,这将是罗马教皇要垮台的信号。
这种思想也传到了犹太人中间,这也是他们那么轻易被假弥赛亚萨瓦塔伊·塞比(Sabbatai Zevi)所迷惑的原因。他在1666年带领一群被他迷惑的人踏上了那既悲惨又无谓的东方旅途。在此前的1650年,欧洲的犹太人在匈牙利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弥赛亚即将来临的事宜。一个名叫塞缪尔·布雷特(Samuel Brett)的英国人参加了大会,他认为大会预示着犹太人即将皈依基督教,并就此写了一份报告。甚至罗马教皇都被惊动了,他派遣了六名教士去大会做“顾问”,讨论预言中的弥赛亚是否已经到来。根据布雷特的报告,他们被允许宣讲了他们的教义,但与会人员并未听从。犹太人自己也没能形成决议,他们于八天后宣布散会,达成的唯一共识是大会将于三年后再度召开。布雷特先生给英国公众的主要结论是:罗马是“犹太人皈依的最大敌人”,因为罗马教会是崇拜女神和雕刻偶像的教会,但新教仍然可以促成犹太人的皈依。 [13]
阿姆斯特丹的卡特赖特母子已经确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实际步骤。1649年1月,他们将“请求议会撤销驱逐犹太人之法令的请愿书”提交给了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Fairfax)和战争委员会。同月,英王被处以极刑,请愿书消失在其后的斗争和混乱中。但在新局势下,英国国内出现的新因素正促进着卡特赖特母子愿望的实现。一位犹太人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在当时特殊情形的作用下,他的努力使英国再次向犹太定居者打开大门。
阿姆斯特丹一位博学的犹太教拉比玛拿西·本·以色列(Manasseh ben Israel),或许出于弥赛亚情结,或许认定自己受到加快弥赛亚降临的召唤,于1650年发表了一部名为《以色列的希望》(
The Hope of Israel
)的著作。玛拿西认为,为完成世界范围的犹太人离散应让犹太人先来到英国,其后犹太人才能开始重返家园的进程。他后来在一封信中做了解释,根据《申命记》28:64,“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他接着补充说:“我看‘地那边’就是这个叫做英格兰的岛屿。”

玛拿西之所以这样期待弥赛亚,是因为听了犹太旅行者安东尼奥·德蒙特西尼奥(Antonio de Montezinos)讲的故事。德蒙特西尼奥于1644年给他讲述了一个有关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人部落的故事,这些部落做犹太教礼拜,诵读犹太教的《施玛篇》,他们的皮肤虽被“太阳晒得焦黑”,但无疑是希伯来人。德蒙特西尼奥极力想说服他的听众,这些印第安人正是以色列失散的十支派之一的吕便支派。在南美的西班牙传教士早就提出一个理论,即美洲的印第安人就是以色列失散的十支派,他们向西穿越亚洲到达中国,然后到达美洲。(现代人类学家认为印第安人实际是蒙古人,跨越白令海峡后来到美洲。)德蒙特西尼奥无疑很熟悉这类观点,他像歌剧《日本天皇》中的人物一样,“为原本干巴巴的故事丰富细节、提高真实性”。他的故事包含人名、地名、日期等具有当地色彩的细节。他讲述了一个印第安向导如何偷偷告诉他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故事;他如何经过一周的跋涉穿过密林、横渡河流、翻越高山,最后见到了一个操希伯来语、蓄胡须的印第安部落。在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大会的要求下,德蒙特西尼奥甚至签署了一份誓词,保证他的目击报告的真实性。
这个故事很快就在阿姆斯特丹的清教徒中间流传开来,千禧年教派(Millenarian sect)的成员尤其受到鼓舞,因为他们正信心十足地等待着圣徒王国的到来。根据他们对《圣经》中预言的解读,以色列人回归一定包括在公元前10世纪流散的十支派。只有当他们像在大卫与所罗门统治时代一样与犹大的子孙重聚之后,大卫的儿子弥赛亚才能出现在地球上。
德蒙特西尼奥的美妙发现被玛拿西抓住,当做犹太人分散到“所有民族中”的过程已经完成的证据,这意味着十二支派在弥赛亚的统治下获得团聚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在《但以理书》里难道不是写着,“当神圣的民族分散到世界各地之后,所有苦难就会结束”吗?这就是玛拿西当年在《以色列的希望》中用西班牙语写下的话。但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没有犹太人。在玛拿西与他的清教徒朋友的交谈中,他意识到可以用这个理由促成犹太人返回英国。他后来用拉丁文重写了这本书,增加了一个题献:“献给英国议会、最高法院和尊敬的国务委员会”。在书中,他请求获得“帮助和善意”,以便“使那些上帝令先知预言的事情都能获得实现……使以色列终于能回到自己的家园,预言中在弥赛亚治下的世界和平能够恢复”。
受到千禧年临近的鼓舞,玛拿西的英国信徒把他的书翻译为英语,并在英格兰印刷,一共印刷了两次,都很快销售一空。此书的出版正逢其时。克伦威尔正在与葡萄牙交战,这是英国为了恢复海上霸权、修补与殖民地贸易联系而与大陆强国打的一系列战争中的第一战。在漫长的内战期间,英国对外贸易远远落后于其他强国。英国的商业贸易阶层主要由清教徒构成,他们尤其妒忌荷兰,因为荷兰利用英国内战的机会坐上了黎凡特贸易、远东贸易及美洲殖民地转运贸易的第一把交椅。荷兰人的这些胜利是在犹太人的帮助下取得的,犹太商人、船主、阿姆斯特丹的掮客通过他们与美洲和黎凡特地区的联系拿回了大笔生意。克伦威尔了解犹太人的作用,因为几个马拉诺家族已经为他所用。 [14]
这些马拉诺人为躲避西班牙中世纪的宗教审判,以西班牙人的身份寄居在其他国家,公开宣称信奉天主教,在大使馆教堂做礼拜,但在家里私下进行犹太教活动。自从1492年西班牙开始驱逐犹太人,伦敦和布里斯托尔就出现了这些家族的足迹。在克伦威尔当政期间,伦敦有几个非常活跃的富裕马拉诺人,最有名的是西蒙·德卡塞雷斯(Simon de Caceres)和安东尼奥·德卡瓦哈尔(Antonio de Carvajal)。后者在内战期间是克伦威尔的谷物经销商,控制着从西班牙来的大部分金条进口。他的船在英葡战争期间被明令免于征用,并被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设为特殊设备,准予继续进行海外贸易。克伦威尔与查理一世一样急需“造船费”,他希望从犹太人那里获得。他还将犹太人视为“情报员”,因为犹太人的关系网遍及欧洲大陆,能带回敌国的贸易政策信息和保王派在海外的阴谋信息。
玛拿西的书出版后不久,英国官方在1650年与他进行了接触。为谈判结盟事宜出使荷兰的奥利弗·圣约翰(Oliver St. John)被授权与玛拿西进行交涉。圣约翰与这位犹太拉比进行了几次谈话,促成玛拿西向英国国务委员会正式递交了要求允许犹太人重返英国的请愿书。
此时形势已发展到高潮。富裕的荷兰傲慢地拒绝了这个新兴共和国的结盟邀请。英国则按照“不能合作就征服他们”的原则,迅速通过了《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不允许外国船只与英国及其殖民地进行贸易。这打在了荷兰人的要害上,一年后荷兰与英国开战。预见到这个结局,克伦威尔在法案通过的当天即发给玛拿西一本护照,让他来英国亲自宣传他的主张。正如塞西尔·罗思(Cecil Roth)指出的那样,这一时间上的巧合值得关注。克伦威尔急于把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商人转移到伦敦,以期在与荷兰的贸易战中获得优势。
玛拿西还没到英国,英荷战争就爆发了。在战争期间他的主张没能付诸实践。如果实现了,结果可能是惊人的,因为在1653年,英国组建了贝邦议会(Barebone Parliament),按照卡莱尔的说法,这是现代世界“最非凡的”时代,希伯来文化的影响力也在这一年达到巅峰。这一小撮由克伦威尔亲自挑选的严厉而充满激情的人于1653年7月4日开会,讨论如何重写英国宪法以推行摩西律法和耶稣的质朴原则。不论民众意愿如何,英国人在股票交易场中、法庭上和市场里都必须像爱自己一样爱他的邻人。莫利勋爵(Lord Morley)在他关于克伦威尔生平的著作中说,这是一次“按经文的字面意义构建社会的尝试……代表了当时《圣经》政治的最高潮”。
克伦威尔本人也受这一情绪鼓舞,在贝邦议会的开幕演说中,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愿景中,把自己视为先知以利亚(Elijah),引领一个国家归向上帝。“上帝在真诚地召唤你们,犹大将与上帝共治。”他对台下怀着浓厚使命感和历史感的议员们如是说。“你们站在承诺和预言即将实现的历史性时刻,”他接着引用《诗篇》第六十八篇说道,“有预言说‘他要带着他的子民从深海而回’,就像他曾经带领以色列人穿越红海。也许上帝会像有些人想的那样,‘从海中的岛屿上’带犹太人回家,并实现他们‘深海处’的愿望。”他越说越激昂,连续引用圣诗和先知,向他的听众保证《诗篇》第六十八篇中上帝对他的古老子民的承诺,将会向他在英吉利共和国的现代子民兑现。

如果玛拿西·本·以色列当时来到英国亲自向这样的听众陈词,他们会无动于衷吗?但在短短的六个月内他们就失败了。他们为将《圣经》付诸实践做出的真诚而又无谓的努力,被谴责为企图“犹太化”英国法律。与财产权的冲突注定其失败的命运。克伦威尔站在他发表“预言即将实现”的演说台上,草草解散了议会。他们在历史中成为嘲讽的对象,人们以其中一名议员的名字戏谑地称这一议会为“赞美上帝的贝邦议会”(Praisegod Barebone)。
虽然清教徒的高潮期过去了,但犹太复国的问题没有被放弃。此时英荷战争结束了,但与西班牙的战争即将来临。克伦威尔仍然催促就犹太人问题做出决定,犹太商人仍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保持密切关系。1654年,玛拿西派自己的妻弟大卫·多米多(David Dormido)和儿子向国务委员会提出请愿。然而正统派犹太教信徒因认为不应人为地加速弥赛亚的到来而反对他,他感到有必要保持一段时间的低调。虽然克伦威尔请求委员会“迅速做出回应”,“给出所有应得的答复”,但委员会仍然拒绝了多米多的请求。在克伦威尔的劝说下,玛拿西决定亲自到英国来。他将新的论点写入《给护国公的谦卑致辞》
 ,在三个犹太拉比的陪同下来到英国。在这份讲稿中,他利用自己作为犹太法学权威的地位,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犹太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这一点上,“但只有这个伟大的岛屿上没有犹太人”。他说:“在复临的弥赛亚为我们复国之前,我们必须先在这个岛屿上落脚,就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
,在三个犹太拉比的陪同下来到英国。在这份讲稿中,他利用自己作为犹太法学权威的地位,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犹太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这一点上,“但只有这个伟大的岛屿上没有犹太人”。他说:“在复临的弥赛亚为我们复国之前,我们必须先在这个岛屿上落脚,就像在其他所有地方一样。”
接着,他拿出“利益是有力的动机”做论据,指出犹太人在贸易上帮助英国对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施加影响的作用有多大。他宣称犹太人对共和国有感情,因为共和制比君主制更加宽容。在谈及对犹太人的指控时,他回应说基督徒自己也曾经被罗马皇帝指控进行人祭,并指出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人很容易去痛恨和蔑视遭遇了不幸的人”。最后,他明确提出要政府为犹太人提供保护,使犹太人能“自由、公开地”举行集会和葬礼,自由经商,对犹太人内部的民事案件持有审判权,英国法庭只做终审。最后,他要求废止现存所有与上述要求相悖的法律。
这份讲稿发表之后引发了剧烈的争论,支持一方被反对一方完全压倒。不仅所有旧的责难都重新出现,还冒出了新的指责:有人指责克伦威尔是犹太人,还有人说犹太人要买下圣保罗教堂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犹太人是一个卑贱的种族,因为邪恶而不断招致上帝的惩罚;犹太人被流放是上帝对他们杀死耶稣的惩罚(清教徒也要因杀死英王查理而遭受同样的惩罚);如果把犹太人召回英国,他们会破坏基督教的圣洁,导致社会偏离基督教原则和习俗,带来假币、失业,破坏英国商业和海外贸易。另一方面,拥护者则坚称:犹太人是“世界上最高尚的民族,上帝的选民”;要对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负责的是犹太大祭司,而不是整个犹太民族;犹太人返回英国会给国家“带来福气”;内战是上帝对英国驱逐他的子民的惩罚,如果召回他们就能取悦上帝,带来和平;犹太人来经商能减低价格,扩大贸易,使社会繁荣,因为大家都知道“对犹太人最好的国家是最富裕和强大的国家”。然而,拥护者的最主要理由也是他们最弱的论据:只有把犹太人带到英国,才能实现他们的改宗。威廉·普林(William Prynne)是反对派的领袖人物,他的《简短抗辩》( Short Demurrer )一针见血地指出试图使犹太人改宗的可笑之处,是反对观点的典范。 [15] 反对派在这点上确实说对了,使犹太人改宗的观点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它在19世纪竟然又强劲地再次出现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恰恰是推动英国支持以色列复国的最有力动机。
尽管如此,克伦威尔于1655年12月10日在白厅召集了包括法官、神职人员和商人的特别委员会,讨论玛拿西的请求。 [16] 正反两方争论了14天,由于双方实力相当,大会陷入僵局。但大会至少达成了一项共识,克伦威尔为大会制订了议题:“接纳犹太人是否合法?”“如果合法,接纳他们的条件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大法官格林和斯蒂尔的意见是,确实没有法律禁止重新接纳犹太人——一项极大的成就。但当谈到犹太人应以什么条件重返英格兰定居时,出现了克伦威尔所说的“噪嚷的争论”。大部分神职人员赞成再次接纳犹太人,他们认为“英格兰的善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相信上帝对犹太人使命的承诺,并真诚地为他们祈祷”,所以为使他们的“使命”——即改宗——成真,我们应该允许他们进入英格兰。此外,英格兰应该弥补过去对犹太人的残酷无情,他们确实是在威廉一世的邀请下才来到英格兰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继承了肉体,我们继承了精神”。
商人们则坚决反对。有谣言说如果再次接纳犹太人,后果极其险恶。这些谣言是荷兰人、西班牙人及保王派散播的,因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认为允许犹太人回归英国是为《航海法案》的执行,保王派则因“这是护国公极力支持的”而反对。在这些谣言的影响下,商人们认为接纳犹太人的结果将极其可怕,会对外国人有利,而使英格兰贫困。至于改宗,他们说,人们如今热衷于各种奇怪的新教条,所以改信犹太教的人可能比改信基督教的人还要多。最后,双方达成的妥协是允许犹太人重返英国,但对犹太人施加的贸易和金融限制使克伦威尔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
但大门被推开了,护国公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他再次对无能的懦夫不能按他的意愿行事感到愤怒。接纳犹太人来英国难道不是每个基督徒应尽的义务吗?他斥责道。世界上只有英国在宗教教育方面是绝对纯粹的。“难道让犹太人去向天主教徒或偶像崇拜者这些教授错误思想的老师求教吗?”这个论点说服了神职人员。接着他将蔑视转向市民。“你们真的以为这些吝啬和令人蔑视的民族能胜过全世界最高贵、最受人尊敬的英国商人吗?”“他继续讲着,”一位当事人说,“最后大家被他说得无可争辩……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讲者。” [17]
但奥利弗已忍无可忍,他解散了这个蒙羞的委员会,就如同他解散长期议会和小议会一样,因为他们不能为他的目的服务。实际上,他已经从法官的裁决中获得了他的部分诉求。或许他因害怕触发更大的骚动而不再坚持全部诉求的达成。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认为,奥利弗可能决定用半正式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按照一名当事者的话说,就是“默许”犹太人重新进入英国 [18] 。事实上,这也是当时人们的观察。“现在犹太人被允许进入英格兰了。”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在1655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这显然是指法官对接纳犹太人没有法律障碍的裁决。
每个人都对避免做出明确决议就能丢掉这个棘手问题而感到满意,只有一个人除外。对玛拿西·本·以色列来说,他在这件事上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热情、学识和辩才,加之自己民族的古老愿望和在波兰的犹太人受迫害事件所带来的新紧迫感,这个妥协的结果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此时年事已高,身无分文地带着失败回到荷兰,不到一年就心碎地死去了,终年53岁。
克伦威尔“默许”的直接后果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由于这个决议的模糊性,当时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移民潮;但当1656年英国与西班牙交战的时候,尽管仍有反对声,马拉诺人终于得以撕下他们作为西班牙基督徒的伪装,赢得了英国政府正式给予的公开集会和作为英国居民的有限权利。玛拿西的外甥在他舅舅绝望而死的同年被允许在英国皇家交易所做交易员。实际上,克伦威尔的妥协是一种典型的英国式方案,不合逻辑但却实用,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给犹太人带来了实惠。查理二世找不到任何可废除的法令,明智地选择了维持现状,没有理睬呼吁再次驱逐犹太人的请求。
 由于许多保王派犹太家族在斯图亚特王室成员流亡期间对他们给予了同情和帮助,查理二世拒绝对犹太人权利进行任何限制。总之,他跟克伦威尔一样默许了对自己有利的现状。
由于许多保王派犹太家族在斯图亚特王室成员流亡期间对他们给予了同情和帮助,查理二世拒绝对犹太人权利进行任何限制。总之,他跟克伦威尔一样默许了对自己有利的现状。
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班牙裔犹太人的人数逐渐增长。尽管始终面临新的普林们和反对之声,但犹太人一点一点地赢得了公民权。
毫无疑问,在清教徒统治下萌发的这第一波对犹太人复国的支持是出于宗教原因,源自《旧约》对17世纪中期的清教徒统治者们思维和信念的影响。但仅有宗教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政治和经济利益,仅靠清教徒跟古以色列人那跨越时空的兄弟情谊,或对宽容理念的追求,或加速千禧年到来的神秘主义希望,最终肯定是无果而终。克伦威尔对玛拿西的建议产生兴趣,与劳合·乔治在十代人之后对哈伊姆·魏茨曼的建议感兴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都相信犹太人对他们所面对的战局有利。从克伦威尔的时代开始,其后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关切都出于双重动机:一个是商业、军事、帝国方面的利益动机,另一个则是从《圣经》继承来的宗教动机。无论这两个动机中的哪个缺席,如18世纪宗教热情明显降温时,都不会有行动发生。
[注释]
[1] From A Narrative of the Late Proceedings at Whitehall Concerning the Jews , 1655. Quoted by Osterman.
[2] Cromwell ’ s Letters and Speeches , I, 32.
[3] From a letter to Major-General Fortescue quoted by Firth in Oliver Cromwell .
[4] History of England , I, chap. I, 71.
[5] Gardiner, History of England , X, 142. 这一事件发生于1642年1月5日。国王在前一天闯进议会试图逮捕五名议员,但发现他们已经逃走。第二天,他去市政厅要求对五名议员开具逮捕令,未能如愿。民众闻讯涌上街头,传言四起,在国王返回白厅的路上,民众包围了他的马车,并高喊“议会权利!”。一个红发的胆大者向车厢里扔了一个具有煽动性标题“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的小册子。就像Gardiner所写,“对罗波安暴政的影射,查理一世不可能不明白”。据某些来源记载,那个胆大的人是记者亨利·沃克(Henry Walker),他和他的印刷商前一晚忙了整夜,他写好一页就交给印刷商迅速排印。但这个小册子现已无存。请见J. G. Muddiman, Trial of King Charles the First , Edinburgh and London, n.d., pp. 15-16.
[6] Firth, Cromwell ’ s Army .
[7]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 , I, chap. I, 1.
[8] A Pisgah-sight of Palestine , Book V, p. 194.
[9] Watson in Cambridge Lit .
[10] The City Match , Mayne, 1639.
[11] Watson in Cambridge Lit .
[12] Watson in Cambridge Lit . Also DNB .
[13] Relation of the Great Council of the Jews in the Plains of Hungaria in 1650 to examine the Scriptures Concerning Christ , by S.B., an Englishman there present. In Crouch.
[14] Wolf, Introduction, p. xxx, Patenkin, Roth. Bishop Burnet在 A History of His Own Times (1724)中说,当克伦威尔了解了犹太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后,他邀请犹太人来英国定居并允许他们建立犹太教会堂,更多是基于这一原因,而非出于宗教宽容原则。
[15] Prynne. Also Edward Nicholas, An Apology for the Honorable Nation of the Jews and All the Sons of Israel , 1648. Israel ’ s Condition and Cause 35 . Pleaded; or some Arguments for the Jews Admission into England , by D.L., 1656. Quoted by Osterman. See also Wolf, pp. xli-xlvi.
[16] Henry Jessey’s “A Narrative of the late Proceedings at Whitehall Concerning the Jews,” Harleian Miscellany , VII, 623. Also “The Proceedings about the Jews in England in the year 1655” in Crouch. 其他关于此次会议的成员和讨论的文献包括 Thurloe State Papers , IV, 321 ff.,和 State Papers Domestic , 1, 76 (1655), passim。Wolf, pp. xlvii-lv. Gardiner,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Protectorate , III, pp. 216-24.
[17] 认为这是克伦威尔最好的演说的人是保罗·莱科特爵士(Sir Paul Rycaut),他黎凡特公司的前外交专员,Knolles的 History of the Turks 的编辑。见Wolf, p. liii, note 2。
[18] 此语出自包含在 State Papers Domestic 中的罗宾逊(Robinson)的一封信中,被Gardiner在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and Protectorate , III, 221, note 3中引用。William Godwin在准备 History of the Commonwealth (1828)时检索了Bevis Marks犹太会堂的记录,发现了一个1656—1657年的墓地租约,证实白厅会议后一年内,犹太人已获得以犹太人而非马拉诺人身份定居英国的权利。见Graetz, V,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