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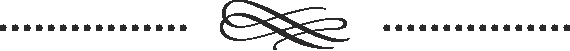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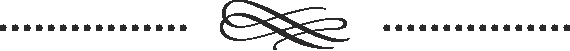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欧洲人沿着各个方向突破地理局限时,伊丽莎白时代的航海家和商业冒险家是开路先锋。这些“海外挑战者和偏远地区的探索者”,哈克卢特(Hakluyt)赞扬道,“比地球上任何人都要优秀”。 [1]
“在女王陛下之前的众多国王之时,”他继续说道,“他们的旗帜曾经在里海的海面上飘扬过吗?他们曾经像女王陛下一样跟波斯皇帝打交道并为英国商人争取到大量优惠条件吗?有谁在君士坦丁堡苏丹的堂皇门廊前看见过有英国人在卫队前面闲逛?有谁在叙利亚之的黎波里、阿勒颇、巴比伦、巴尔萨拉……建起了领事馆和代表处?迄今为止有哪艘英国船曾经在宽广的拉普拉塔河上停泊过……面对敌人还能在吕宋岛靠岸……与摩鹿加群岛的君主们做生意……返航的时候满载着中国的商品?有谁能像现在这位繁荣兴盛的王朝的臣民一样做到过这些?”
伊丽莎白时代扩张的主要动因就是想“满载货物”回家,推动探险的力量是贸易,探险家的目标是东方的货物。这时巴勒斯坦首次不以圣地被人们熟知,而变成了一个与奥斯曼帝国通商的贸易站。充满激情、想劈开土耳其人脑壳的十字军战士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携带礼品,以温言承诺向土耳其人申请贸易优惠条件的使者。英格兰和土耳其苏丹的帝国建立起来的商业和外交关系,成为英格兰日后战略介入中东事务的基础。
英王与商人、航海家建立起了伙伴关系,资助他们的远征活动,待他们返航后收取可观的利润。最重要的结果是英格兰的海军成长起来了。由于贸易扩大了,就需要建造更多的船只,训练更多的水手驾船出海。
与此同时,特许公司作为帝国的另一种工具,随着海军一起发展起来。特许公司由商人组成,英王授予其在某个地区的垄断贸易特权,并收取一定的岁贡。第一家特许公司是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1554年成立。第二家是黎凡特公司(Levant Company),1581年成立,这家公司的特许经营区域是土耳其苏丹的领土。
巴勒斯坦是土耳其的领土,但它已经被一整代人所忽视,无人访问,几乎被英国人忘记。从最后一位朝圣者托金顿在1517年到达巴勒斯坦,到第一位冒险商人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在1553年来到巴勒斯坦,此间没有任何英国人去那里旅行的记录。在这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英格兰推翻了天主教会,奥斯曼帝国统治了耶路撒冷。这两件事导致英格兰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453年,更可怕的新一代土耳其人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至今仍统治着这座城市。到1540年苏莱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统治的巅峰之时,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开罗、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罗得岛、阿尔及尔都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控制着通往巴勒斯坦的所有陆路和水路通道。在他们眼里,基督徒就是合法的猎物,可以抓来做奴隶,或作为异教徒杀掉以保证自己进入天堂。
不仅是去圣地的危险显著增加,迫切的动机也消失了。根据新教的理论,救赎是心灵的历程,而非肉体。“最好的朝圣,”塞缪尔·珀切斯(Samuel Purchas)写道,“是安宁的内心抵达天国的耶路撒冷。”
 宗教改革所到之处,朝圣活动就停止了,至少是暂时停止了。买卖赎罪券和赦免,被新教教徒斥为天主教最令人厌恶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用公开的表演取代了个人的伦理道德。在当时,新教信仰(Protestantism)仍意味着反抗,宗教改革仍要改变形式,最急需改革的形式就是抛弃罗马教廷授予恩典的呆板形式,转为通过个人努力获取内在美德。珀切斯说,亲身到圣殿朝拜只能给旅行者的心路历程带来危险,他还补充警告道,“给某地赋予圣洁性是犹太人的传统”。
宗教改革所到之处,朝圣活动就停止了,至少是暂时停止了。买卖赎罪券和赦免,被新教教徒斥为天主教最令人厌恶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用公开的表演取代了个人的伦理道德。在当时,新教信仰(Protestantism)仍意味着反抗,宗教改革仍要改变形式,最急需改革的形式就是抛弃罗马教廷授予恩典的呆板形式,转为通过个人努力获取内在美德。珀切斯说,亲身到圣殿朝拜只能给旅行者的心路历程带来危险,他还补充警告道,“给某地赋予圣洁性是犹太人的传统”。

东方的新诱惑不是救赎,而是贸易。当初朝圣者下船的地方,如今是大捆英国毛纺品上岸的码头,换回的是香料、丝绸、红酒、油料、地毯和珠宝。从阿拉伯半岛出发的沙漠商队要通过巴勒斯坦,在经过商人以物换物倒手后,被装载到静候在港口里的欧洲商船上。巴勒斯坦对新兴贸易的贡献有限。在经历阿拉伯人、塞尔柱人、基督徒、鞑靼人的入侵后,这片土地在土耳其人的暴政下继续遭受蹂躏。错落有致的葡萄园荒废了,山坡受到侵蚀,水槽和沟渠堵塞了。这片在圣经时代里曾经拥有所罗门王的花园和宫殿的“熙熙攘攘的繁忙”土地,如今成了奥斯曼帝国的穷乡僻壤。至于巴勒斯坦的港口雅法和阿卡,虽仍然繁忙,但重要性退居北部阿勒颇的斯堪德隆港(Scanderoon)以及南部的亚历山大和阿尔及尔港之后。
但巴勒斯坦的命运却维系在了黎凡特贸易的整体发展上。英格兰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开始的“土耳其贸易”,为后来帝国在印度和中东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虽然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其意义。黎凡特公司的商人为英格兰打开了与中东通商的大门。此后,这些商人继续向东挺进,并于20年后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而这家公司在大英帝国发展中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这一次,惯常的次序发生了逆转,政治势力是跟着贸易扩张的。印度、苏伊士运河、摩苏尔油田,以及1918年促使英国介入巴勒斯坦的复杂政治和战略条件,都由伊丽莎白时代的商业冒险者开启。他们使英格兰与奥斯曼帝国建立起正式的外交关系。对巴勒斯坦的宗教情结,虽然在过去和后来曾发挥过极大作用,但此时却没有出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在女王及其大臣与这些通商土耳其的英国商人,就与土耳其苏丹的交涉、大使任命、特许公司章程等事项的通信往来中,除了偶然涉及之外,几乎没有提及几代十字军战士为之战斗和牺牲、朝圣者千年来朝拜的那片土地的名字。
在伊丽莎白女王之前,与土耳其的贸易基本上被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垄断了。他们的舰队都很老练,熟悉每片海域的风向和潮汐情况,知道地中海上的每一处海湾和港口。哈克卢特罗列了16世纪初几次“从伦敦出发去叙利亚的黎波里和巴鲁提(Barutti)”的航行。 [2] 尽管如此,英国人在此时期没有试图齐力推翻意大利人的垄断,直到1571年勒班陀(Lepanto)战役之后,地中海上的力量平衡才被打破。参加海战的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教皇国和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派出的联合舰队,指挥官是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ohn of Austria)——他是西班牙国王的弟弟,旗下有270艘战船和8万士兵。在那可怕的一天结束的时候,伊丽莎白时代的土耳其史学家诺尔斯(Knolles)写道:“海面被血染红了,漂满了死尸、武器和船只的碎片。” [3] 土耳其舰队被摧毁,他们在地中海上的海军力量被击溃,损失了220艘船,阵亡2.5万人,被俘5万人,1.2万名被奴役的基督徒被解救。历史学家拉富恩特(Lafuente)宣称:“像这样残酷、可怕的战役和英勇、愤怒的战士,地中海上从来没有过,世界也再不会看到了。” [4] 这次胜利唤醒了恢复对君士坦丁堡的统治,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和黎凡特,赶回他们西徐亚荒凉的家乡的美好愿景。
唐·胡安视自己为拜占庭的皇帝。然而,土耳其人即使在战败后仍然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欧洲形成威胁,直到1683年在维也纳城门外被打败,此后仍保持强国地位长达两个多世纪。不过,在勒班陀海湾击败土耳其舰队后,地中海的航路就打通了。当胜利的消息传到伦敦时,史学家霍林斯赫德(Holinshed)写道:“整座城市被篝火照亮了,人们高兴得大吃大喝,因为这次胜利对基督世界有重大的意义。”

但胜利者没能将海军优势维持多长时间。威尼斯对海上香料贸易的垄断被葡萄牙人打破,其贸易和海上力量开始衰落。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西班牙强大的舰队被英国人打散、击溃,这被后世认为是海洋控制权开始向新教国家转移的标志。莱基(Lecky)充满正义感地称其“对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 [5] 当然,权力的转移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此后,西班牙的强国地位仍然维持了一段时间,但西班牙舰队精锐的损失,战败于土耳其人,以及威尼斯的衰败,为英格兰打开了通往中东的海上通道。
没等德雷克(Drake)打败“进行宗教迫害和魔鬼统治的西班牙”,
 英格兰的商人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早在勒班陀战役胜利之时,商人们就意识到了黎凡特的商机。两个伦敦富商马上组织人力、钱财、船只,向“土耳其贸易”展开集体进攻。其中一人是爱德华·奥斯本(Edward Osborne),他是纺织公司的主要成员。另一人是理查德·斯塔珀(Richard Staper),他的墓志铭称他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商人,土耳其和东印度贸易的最主要发现者”。
英格兰的商人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早在勒班陀战役胜利之时,商人们就意识到了黎凡特的商机。两个伦敦富商马上组织人力、钱财、船只,向“土耳其贸易”展开集体进攻。其中一人是爱德华·奥斯本(Edward Osborne),他是纺织公司的主要成员。另一人是理查德·斯塔珀(Richard Staper),他的墓志铭称他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商人,土耳其和东印度贸易的最主要发现者”。
 支持他们的是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精明的财政大臣,他关注的是地中海贸易航线上的英国船只能给女王带来的黄金。到了1579年,奥斯本和斯塔珀已经召集起一群投资者。就在这一年,作为第一步,他们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一名代理人洽谈贸易条件。
支持他们的是伯利勋爵(Lord Burghley),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精明的财政大臣,他关注的是地中海贸易航线上的英国船只能给女王带来的黄金。到了1579年,奥斯本和斯塔珀已经召集起一群投资者。就在这一年,作为第一步,他们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一名代理人洽谈贸易条件。
威廉·哈伯恩(William Harborne)就是被选定的人。他是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议员,两年前曾经访问土耳其,并带回一封苏丹邀请英格兰女王建立友谊的信。这是个极为明智的选择。英格兰在中东的全部前途,连同巴勒斯坦的前途,都维系在这位出使土耳其宫廷的首任大使身上。他是一位坚韧不拔、充满伊丽莎白时代自信的外交天才。他出使的是个以险恶著称的敌对国家。虽然苏丹曾经表示过友好,但穆拉德三世(Amurath III)以喜怒无常著称。他处于忌妒心重的大臣和喜欢随意开枪的近卫军的守护中。已与土耳其建交的欧洲其他国家使节对哈伯恩也都抱有敌意,肯定会从中作梗。但不到一年,他就带回了一份包含22项条款的完整协议,授权英国臣民在土耳其领土上进行贸易。此后六年,他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研究黎凡特公司历史的史学家伍德(A. C. Wood)说:“他为他的国家在近东的影响力建立起坚实的基础,此后再也没有受到过竞争对手的实质性威胁。”
得到哈伯恩的协定后,斯塔珀和奥斯本请求女王授予其在黎凡特进行贸易的特许权。他们指出,这样做的好处是增加关税收入和提升海军实力。为了支持他俩的请愿,首席秘书沃尔辛厄姆(Walsingham)写了一份题为《与土耳其通商之考虑》的备忘录。 [6] 在这份备忘录中,他阐述了女王应该对土耳其贸易给予官方支持的若干理由。“第一,”他写道,“这可以使您最先进的船只持续工作,有助于维持海军的实力,否则海军力量就会衰败,海军是保护王国的最主要力量。”此外,他继续写道,由英国公司做直接贸易避免了中间人的转手,因此,“您的商品能获得最大的利润,避免了利润落入外人之手”。为此,值得用黎凡特贸易拉拢土耳其苏丹,使他疏远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本就不太坚固的同盟关系。
确信了政治上的好处,又受到了预期利润的诱惑,伊丽莎白女王在1581年9月1日批准了斯塔珀、奥斯本及其余10名商人的特许公司申请,
 公司定名为“黎凡特贸易公司”。根据条款,只有公司的成员才被允许与土耳其进行贸易,因为他们“发现并建立了与土耳其的贸易,根据当代人的记忆,我们的祖先不曾与之进行过贸易”。奥斯本被提名为总督,公司的成员数量被限制在20人。公司的船只打女王的旗号,船员和货物要受英国海军的监管。作为对垄断贸易权的回报,公司每年向女王上交500英镑的贡税。
公司定名为“黎凡特贸易公司”。根据条款,只有公司的成员才被允许与土耳其进行贸易,因为他们“发现并建立了与土耳其的贸易,根据当代人的记忆,我们的祖先不曾与之进行过贸易”。奥斯本被提名为总督,公司的成员数量被限制在20人。公司的船只打女王的旗号,船员和货物要受英国海军的监管。作为对垄断贸易权的回报,公司每年向女王上交500英镑的贡税。
但公司拖了一年多没有运作,因为女王和特许公司就大使的费用应由谁承担而争执不定。除了工资和献给苏丹的丰厚礼品外,大使还需要一笔如今被赋予污名的行贿基金。对于吝啬的伊丽莎白女王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她拒绝任命大使,除非特许公司负担费用。奥斯本和他的下属也拒绝再多付一先令。
最后,面对装满毛织布料的整装待发的商船,商人们妥协了,同意承担大使的费用。1583年1月,“大苏珊”号(Great Susan)启程向君士坦丁堡驶去,船上除了哈伯恩,还有给土耳其苏丹的礼物:三只大獒、三只西班牙猎犬、两只大猎犬、“两只着丝绸狗衣的小狗”、两只银色鹦鹉、一座价值500英镑的珠宝钟表,以及一些其他装饰品和宝物。 [7] 伊丽莎白女王则只给大使提供了一个骑士头衔和几封国书。
到达目的地之后,哈伯恩再次不辱使命。他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丰厚的礼物和压制敌手的巧计,不仅重获苏丹的好感,恢复了因为他的离开而被取消的贸易协定,还获得了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加优惠的条件,以及更低的出口关税。“这位雄辩、机智的哈伯恩先生,”剧作家兼记者汤姆·纳什(Tom Nash)写道,“使我们这个岛国在土耳其人中名声大噪,以至于这个野蛮残忍的异教国度的幼童,谈论伦敦就跟谈论他们的先知在麦加的坟墓一样频繁。”

这样的盛名对做买卖和外交谈判都有好处。在公司运作的头五年里,这些“土耳其商人”总共进行了27次海上航行,到达了10个黎凡特港口,有时可以实现300%至400%的利润,总共向英王上交关税11359英镑。
 公司的总督奥斯本被封为骑士,后来被推选为伦敦市长。特许权续签了两次,第二次给英王带来了800%的利润。英国还在阿勒颇建立了一家领事馆,
[8]
处理阿勒颇、大马士革、阿曼、的黎波里、耶路撒冷,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犹太下属各省”的贸易事务。圣地此时已经沦落为一家领事馆管辖下的若干贸易点中的一个。
公司的总督奥斯本被封为骑士,后来被推选为伦敦市长。特许权续签了两次,第二次给英王带来了800%的利润。英国还在阿勒颇建立了一家领事馆,
[8]
处理阿勒颇、大马士革、阿曼、的黎波里、耶路撒冷,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犹太下属各省”的贸易事务。圣地此时已经沦落为一家领事馆管辖下的若干贸易点中的一个。
并非每一次航行都能够凯旋。海盗和令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破产并落入夏洛克之手的“撞沉商船的可怕礁石”也困扰着英国人。黎凡特公司在1591年远航的三艘船中只有一艘安全返航。另一艘由船长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掌舵的商船带着伊丽莎白女王致中国皇帝的信前往中国,但出发后便音信全无。斯塔珀和奥斯本会是怎样焦虑地等待自家船只安全抵达的消息啊!他们不知多少次在码头徘徊踯躅,翘首期待着地平线上返航船只第一次隐约闪现的身影。如果他们的船避开了礁石和风暴、土耳其人和海盗的劫掠、西班牙人和威尼斯人的伏击而安全返航,他们就能赚取极其丰厚的利润。根据公司的报告,一艘大商船带回了“丝绸、靛蓝染料、各种香料、各式药品、罗缎、棉线、棉绒、土耳其地毯、棉布和珠宝”。
 报告还说,“我们的冒险可以给女王带来至少3500英镑的收益”。
报告还说,“我们的冒险可以给女王带来至少3500英镑的收益”。
棉花对英格兰的未来具有特殊意义。这是一种新奇的植物纤维,在阿卡和西顿售卖。根据当时的描述:“王国中的许多人,特别是兰开斯特郡(Lancaster)的人,用一种纤维制作粗布。它是一种矮树或者灌木的果实,被土耳其贸易商带入王国。”
 这就是兰开斯特织布业的起源,在珍妮纺纱机和动力织布机出现后,织布业成为英格兰的支柱产业。
这就是兰开斯特织布业的起源,在珍妮纺纱机和动力织布机出现后,织布业成为英格兰的支柱产业。
这家公司从波斯经黎凡特带回了当时稀罕但如今很普遍的花园植物:百合花、鸢尾花、番红花、风信子、水仙花和月桂树。后来在英国人生活中十分流行的咖啡却不知为何被土耳其贸易商人忽略了。商人们注意到一种在土耳其很流行的饮品。一名叫桑兹(Sandys)的旅行者写道,土耳其人整天坐着聊天,他们喝一种“极烫的,颜色和味道像黑灰一样的饮品”。
 不过,英国的咖啡屋要等到黎凡特公司的继承者东印度公司,才开始批量进口咖啡豆。
不过,英国的咖啡屋要等到黎凡特公司的继承者东印度公司,才开始批量进口咖啡豆。
东印度公司注定要将英格兰变为一个帝国,并对巴勒斯坦的命运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黎凡特公司的商人们为了涉入远东贸易建立了这家公司。当时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垄断着远东贸易。他们把东印度群岛的香料、中国的丝绸、印度的平纹细布和珠宝,用船运过印度洋之后,再由商队走陆路运到黎凡特的城市中,然后卖给英国商人,他们从中赚取惊人的利润。除非黎凡特公司把大笔金钱塞进外国人的腰包里,英国人就买不到一盎司胡椒或一块绿宝石。荷兰人的垄断使胡椒的价格翻倍。英国人决定建立自己去东方的贸易路线。1601年,几个做土耳其贸易的商人建立起这家新公司,专门发展与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直接海上贸易。
东印度公司的历史对英国中东政策的影响将在后续章节中讨论,在本章中我们的重点是黎凡特公司。这家公司通过贸易使英格兰与土耳其建立了近乎正式的外交关系。虽然伊丽莎白女王吝啬得不愿负担大使的费用,但她充分利用了哈伯恩和他的继任者爱德华·巴顿爵士(Sir Edward Barton),试图拉拢土耳其苏丹与英格兰一起对抗西班牙。“英格兰女王正在施加影响力,”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在1590年的一封官方信件中写道,“向苏丹承诺巨大的好处以说服他攻击西班牙国王……”他还报告了其他重大准备工作,造船工作正在大规模开展,土耳其首相与英国大使几乎每日会面。
[9]
当时在欧洲外交官中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很普遍,每个人都想拉拢土耳其,改变欧洲大陆不稳定的力量平衡。有一次,在一帮希腊人嬉戏时,一个大雪球击中了法国大使。“他勃然大怒,”英国大使巴顿报告说,“认定是我的仆人干的。”他回到家里,召集随行人员拿着匕首、棍棒和利剑向英国人发动攻击,“体现了他对我国抱有极大的愤怒和恶意”。

尽管或者也许正因为雪球事件之类的事情,在哈伯恩于1568年过世后,继任的巴顿比他的前任更成功地改进了与这位喜怒无常的土耳其暴君的关系。尽管不断有其他欧洲国家大使提醒苏丹,他们的英国同人只是个“从商人那里领工资的人”,
 但是他作为黎凡特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并没有影响苏丹以“极为尊重”的方式对待他。他甚至暂离岗位,陪同继承了穆拉德三世王位并残杀兄弟的穆罕默德三世(Mahomet III)去周边征战。事实上,由于巴顿太过追随土耳其宫廷的生活方式,有人抱怨说英国大使馆像土耳其宫廷的后宫一样,大量使馆人员召妓,“据传最多时达到17个。但大使把她们都轰走了,只留下自己的女人,在这个女人和炼金术上花光了他的收入”。
但是他作为黎凡特公司代理人的身份并没有影响苏丹以“极为尊重”的方式对待他。他甚至暂离岗位,陪同继承了穆拉德三世王位并残杀兄弟的穆罕默德三世(Mahomet III)去周边征战。事实上,由于巴顿太过追随土耳其宫廷的生活方式,有人抱怨说英国大使馆像土耳其宫廷的后宫一样,大量使馆人员召妓,“据传最多时达到17个。但大使把她们都轰走了,只留下自己的女人,在这个女人和炼金术上花光了他的收入”。

道德败散的爱德华·巴顿爵士似乎是唯一喜欢生活在这个被他称为“幸福的土耳其宫廷”
 里的人。在他的国人眼里,奥斯曼帝国被视为——照诺尔斯所说——“当今世界的恐怖力量”。商人斯塔珀认为,土耳其人是“一个极坏的民族”
[10]
。面对这个撒拉逊人之后的专制政权,英国民众有一种好奇的恐惧感,混合了害怕、仇视和敬畏。这种复杂情绪部分为十字军东征时期的遗留,而有关这个政权闻所未闻的残暴和淫荡传闻加剧了这种情感。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登基时,像以往的君王一样杀死了所有可能的王位竞争者,但他杀害全部19位兄弟的狂暴程度让欧洲惊骇不已。大使们发回了大量目击报告,描述了被割喉的尸体鲜血淋漓地躺在大理石阶梯上。这些目击报告传遍了西方的首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仍然余波不断,人们不断在戏剧和诗篇中增添血淋淋的细节。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舞台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棍永远是模仿苏莱曼大帝、巴雅泽、残忍的谢里姆一世、土耳其近卫军、埃及的马穆鲁克人和宦官等人物的角色,这些角色演尽了各种邪恶和淫欲。
里的人。在他的国人眼里,奥斯曼帝国被视为——照诺尔斯所说——“当今世界的恐怖力量”。商人斯塔珀认为,土耳其人是“一个极坏的民族”
[10]
。面对这个撒拉逊人之后的专制政权,英国民众有一种好奇的恐惧感,混合了害怕、仇视和敬畏。这种复杂情绪部分为十字军东征时期的遗留,而有关这个政权闻所未闻的残暴和淫荡传闻加剧了这种情感。1595年穆罕默德三世登基时,像以往的君王一样杀死了所有可能的王位竞争者,但他杀害全部19位兄弟的狂暴程度让欧洲惊骇不已。大使们发回了大量目击报告,描述了被割喉的尸体鲜血淋漓地躺在大理石阶梯上。这些目击报告传遍了西方的首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仍然余波不断,人们不断在戏剧和诗篇中增添血淋淋的细节。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舞台上,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棍永远是模仿苏莱曼大帝、巴雅泽、残忍的谢里姆一世、土耳其近卫军、埃及的马穆鲁克人和宦官等人物的角色,这些角色演尽了各种邪恶和淫欲。
在这段时间里形成的“恐怖的土耳其人”印象,在此后很长时间里就这样固定在英国人心目中了。这点与我们这本书讲述的故事是有关的,因为真正的土耳其人统治巴勒斯坦长达四百年之久。16世纪时,奥斯曼帝国的实力处于鼎盛时期,而英国刚刚开始海外扩张,正在挑战西班牙人的霸权,而这个时期形成的同盟关系在19世纪土耳其和西班牙沦落为二流国家后并不一定同样有用。虽然从变化的形势和历史逻辑看,所有的论点都是负面的,但纯粹是出于惯性,在土耳其漫长且痛苦的衰败过程中,英国仍然坚守了对一个垂死政权的支持。在哈伯恩和巴顿的时代显得合理的政策,在土耳其成为“欧洲病夫”后已完全不合时宜。但这项政策越是难以为继,英国外交部就越发不愿放弃,直到土耳其人自己在1914年抛弃了与英国的盟友关系。最后,英国几乎是被迫地亲手送这个自己一直支持的帝国走上末路,并在叙利亚至苏伊士这一关键地带取代土耳其的统治,其中就包括了长期被土耳其人压制的巴勒斯坦“省”。
即使是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这位当时最有智慧和学识的人,也感到了土耳其人的恐怖,并呼吁对土耳其暴君进行新的圣战。他愤怒地说:“这个残酷、暴虐的土耳其政权每次传位都浸没在他们君主的血泊中。他们就是一群奴才和奴隶,没有贵族、没有绅士、没有自由人……一个没有道德、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科学的国度。他们不会丈量土地、不会计时……简直是人类社会的耻辱。”他谴责道,他们“让世界这个花园变得荒芜,凡是奥斯曼帝国马蹄所到之处,人民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1] 这番谩骂被称为“圣战呼吁书”,发表于培根失去大法官职位之后的1623年。让人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它与250年后格拉德斯通那番让土耳其人“夹着行李滚出去”的更知名的讲话,用词几乎一样。
然而,执着的英国旅行者不会轻易放弃,甚至连培根描绘的可怕情景也无法让他们却步。有些旅行者是黎凡特公司的代理商,如商业冒险家约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他曾在1584—1602年间游历东方,并于巴顿随苏丹出外征战时成为临时代办。另一些旅行者是英国“代理站”的牧师,比如阿勒颇的威廉·比达尔夫(William Biddulph),他的旅行日记被收录在珀切斯的旅行日记集中。
 还有一些是纯粹的游客,就是想去遥远的地方看看陌生的景观。苏格兰人威廉·利思戈(William Lithgow)在中东地区徒步旅行了19年,按照他自己估计共走了3.6万英里。法因斯·莫里森(Fynes Morison)、亨利·布朗特爵士(Sir Henry Blount)、乔治·桑兹(George Sandys)、亨利·廷伯莱克(Henry Timberlake)四人都是家境殷实的绅士,他们出于好奇心,沿着黎凡特公司打通的道路游历了因古典时代而闻名的希腊和爱琴海、《圣经》中的圣地巴勒斯坦和埃及,以及传说中的奇境、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还有一些是纯粹的游客,就是想去遥远的地方看看陌生的景观。苏格兰人威廉·利思戈(William Lithgow)在中东地区徒步旅行了19年,按照他自己估计共走了3.6万英里。法因斯·莫里森(Fynes Morison)、亨利·布朗特爵士(Sir Henry Blount)、乔治·桑兹(George Sandys)、亨利·廷伯莱克(Henry Timberlake)四人都是家境殷实的绅士,他们出于好奇心,沿着黎凡特公司打通的道路游历了因古典时代而闻名的希腊和爱琴海、《圣经》中的圣地巴勒斯坦和埃及,以及传说中的奇境、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他们旅行时的心态与此前的朝圣者截然不同——他们嘲笑圣地的宗教传奇,质疑宗教奇迹和遗迹,几乎每个人都会认真做记录和写日记。回国后,他们会很快出版自己的日记,英国公众也带着对东方永恒的好奇心积极地阅读。这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住了他们对圣地的认知,因为此时的圣地在其他方面并不被关注。每天晚上,旅行者在住处都会把一天的见闻写在日记里,逐条反驳修道士向导所说的迷信和神话故事,试图用新时代的理性、历史和概率论眼光解释它们。例如,利思戈在他写的《关于一次神奇而痛苦之旅的实录》(
Delectable and True Discourse of an Admired and Painefull Peregrination
)中评论说,各各他山(Mt. Calvary)
 上那块石头上的裂缝,“看上去像是用楔和槌子砸开的”,而不是奇迹产生的。廷伯莱克是在1603年去旅行的,加沙附近的荒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埃及国王和犹大国王数次大战的地方不可能在这里,因为“这里无法为军队提供给养,只有沙土和咸水”。桑德森对黎巴嫩的雪松很失望,觉得“并不算高大”,但同样的树却让利思戈感到很是壮观,他说“这些树的树尖几乎吻到了天上的云朵”。比达尔夫牧师体现了从虔诚的朝圣者到品头论足的记录者的典型转变,他把在耶路撒冷的见闻分为“明显为真”、“显然不实”和“可疑的”三类。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旅行者的新探索精神。
上那块石头上的裂缝,“看上去像是用楔和槌子砸开的”,而不是奇迹产生的。廷伯莱克是在1603年去旅行的,加沙附近的荒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埃及国王和犹大国王数次大战的地方不可能在这里,因为“这里无法为军队提供给养,只有沙土和咸水”。桑德森对黎巴嫩的雪松很失望,觉得“并不算高大”,但同样的树却让利思戈感到很是壮观,他说“这些树的树尖几乎吻到了天上的云朵”。比达尔夫牧师体现了从虔诚的朝圣者到品头论足的记录者的典型转变,他把在耶路撒冷的见闻分为“明显为真”、“显然不实”和“可疑的”三类。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旅行者的新探索精神。
他们记述的共同特点就是细节事实。为了使他的读者能更好地想象出巴勒斯坦的样子,廷伯莱克把圣地诸景点之间的距离与英国国内熟悉地点间的距离相比较:“约旦河与耶路撒冷之距离(两者之间最近的部分),就如同埃平(Epping)与伦敦之间的距离……所多玛和蛾摩拉湖与耶路撒冷之距离,就如同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与伦敦之间的距离。”
英国公众是永不满足的,他们喜欢每一个细节。这可能也是旅行者记录如此详尽的原因——这是读者对旅行者的期待。在1633年上演的由詹姆斯一世时期多产的剧作家托马斯·海伍德所作的《英国旅行者》( English Traveller )中,主角为朋友讲述:
耶路撒冷和圣地的故事:
新旧城市之间有多大差别,
被毁的圣殿还残存什么,
锡安和那些山峦,
以及周围的镇子和乡村,
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否仍是那样。 [12]
与宗教传统相比,当地的地貌和习俗更吸引旅行者。桑德森甚至拒绝进入耶稣圣墓堂,“因为我与天主教修道士之间有巨大的分歧”。利思戈嘲笑希腊和拉丁天主教修道士敬拜和亲吻耶稣像时的古怪姿态,说“那幅代表我们救世主的呆板肖像,画了一具有五个伤口的尸体”。他称这个宗教仪式是“老糊涂的罗马式蠢行”,并以赞许的口吻描绘土耳其人“脸上挂着轻蔑的笑容”嘲笑这种仪式。喜欢冒险的廷伯莱克宁愿进监狱也不愿接受希腊牧首的帮助。有一次他与土耳其人陷入了争执,有人建议他称自己是希腊人,以获得牧首的保护,但被他拒绝了。“因为我宁愿接受土耳其人的保护,也不愿接受希腊教皇本人的保护。”一名与廷伯莱克同船的摩尔人最终调解了矛盾,使廷伯莱克获得释放。
但圣地的气氛有时能压倒这些坚定的怀疑者。法因斯·莫里森刚一踏上巴勒斯坦的土地,就发现自己的内心充满了“神圣的动机”。 [13] 他的兄弟亨利虽然是个彻底的新教徒,但本能地像传统朝圣者一样跪倒在地,亲吻土地。他的感情如此激烈以致头竟然撞到地面,“鼻子撞出了许多血”。
在这个时期,很少有旅行者表现出对圣地原住民的好奇。此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黎凡特犹太人,其生存状况已经与生活在基督徒统治下的欧洲犹太人一样糟糕。根据哈克卢特的说法,在任何穆斯林城市里,“基督徒最安全的住处就是在犹太人家里,因为如果受到伤害,这个犹太人和他的家财就要遭殃,所以犹太人都因害怕惩罚而极力照顾好基督徒”。

约翰·桑德森是黎凡特公司的一名代理人,他描述了他在1601年与七八个来自士麦那、大马士革和君士坦丁堡的犹太商人共同旅行的经历。这些犹太人的领头者是被称作“拉比”的亚伯拉罕·库恩(Abraham Coen),“此人很照顾我”,他说。这是桑德森的福气,因为他总是与“天主教修道士”和“邪恶的摩尔人”发生争执。拉比亚伯拉罕数次为桑德森成功解围。还有一次,桑德森被“恐怖的土耳其人和恶棍帮凶”抓起来,拉比亚伯拉罕把他从监狱中赎了出来。毫无疑问,所用的赎金肯定出自“我那富裕的犹太旅伴”在离开大马士革时为防“当地盛行的盗贼”而缝进仆人内衣里的1万到1.2万枚杜卡特金币。
桑德森记录了在旅行期间几次进入旅伴做礼拜的房间,“学校和学堂”。他看到旅伴不断地在买“有关他们律法的圣书”,足够两三匹骡子驮着。他记述了犹太人如何向他们的“伟大博士和学者”捐献一年一度的薪俸,他们如何努力在有生之年至少去一次巴勒斯坦,或是让他们自己埋骨于此;与他同行的是犹太人中“比较严肃、有修养的”,为避免冒犯从来不与他讨论宗教问题,但通过其他人他了解到犹太人对基督徒的看法是,即使最有学识的基督徒也说不清字母A的来历,而犹太学者能就这一个字母写出一本厚厚的书来。
桑德森注意到,他的旅伴们有救济穷苦犹太人的习惯。拉比亚伯拉罕在赛费特(Sefet)施舍了2000元,在耶路撒冷施舍了1000元,而其他旅伴则各自量力而行。拉比亚伯拉罕“如此和善有礼,我在其他基督徒身上从未得见”。他俩含泪道别。“他是个极虔诚、热情、好心肠的人。我对他的仁慈和善良的钦敬已无以复加。他的言行比许多基督徒都要优秀。”
对这个已经被流放了1600年的古老民族,桑德森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他们说,他们知道耶路撒冷将会重建。他们的弥赛亚终会降临,像过去一样使他们成为主人,继而统治整个世界。”
桑德森回到英国后的第二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了,这迫使黎凡特公司不得不向新国王申请新的执照。这位新国王就是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位国王詹姆斯。黎凡特公司又就谁应负担大使费用的问题与英王进行了漫长的争论。如果说斯图亚特王朝和都铎王朝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吝啬。由于詹姆斯是个目光短浅之人,他根本看不出有向“异教徒国家”派遣大使的必要。对从事土耳其贸易的商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因有资本投入在新的印度贸易公司里,而不愿继续负担费用。但要想获得执照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同意由国王任命大使,而大使的费用则由公司负担。1605年,新执照终于发下来了,授予了“在黎凡特海进行贸易的公司和总督”。每次更新执照,同样的争论就会复现一次,因为斯图亚特王朝没有不缺钱的时候,他们从来都不曾负担大使馆的全部费用。
英王的全力支持是否可以避免黎凡特贸易的最终衰败,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但毫无疑问,法王路易十四的第一大臣科尔贝(Colbert)推行的强势商业政策,使法国成功地从英国人手中抢走了大量土耳其贸易。法国从17世纪开始代替了16世纪的西班牙,成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当坚定的新教徒——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成为英国国王时,他结束了斯图亚特王朝一个世纪的统治,终结了向教皇的靠拢,赶走了法国情人,断绝了英国王室想与天主教建立联系的渴望。这必然导致与法国的战争,这场战争从17世纪开始,持续了整个18世纪,延续至19世纪,止息于1815年拿破仑最终战败。在英国与路易十四交战期间,法国赢得了与土耳其的同盟关系。在战争的间隙中,法国产品取代了英国产品。在法国贸易被革命打断后,英国的黎凡特贸易出现了短暂恢复,但却再也复现不了过去的辉煌。在失去美洲殖民地之后,英国将原本投入西方的精力和资金撤回,全部投向了印度。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对特许公司的贸易保护成为不合潮流的政策。重商主义死亡了,帝国主义时代开启了。黎凡特公司在其辉煌的下属东印度公司的阴影下苟延残喘一个世纪后,终于衰败而亡,其特许贸易执照在1825年被终结。
[注释]
[1] Epistle Dedicatorie , Hakluyt, I, xviii.
[2] Hakluyt’s “The Antiquitie of the trade with English ships into the Levant,” from Voyages and Travels , ed. C. R. Beazley, 2 vols., II, 181.
[3] Generall Historie of the Turkes , 1604, ed. Sir Paul Rycaut, 1700.
[4] Quoted in Historians ’ History of the World , IX, 475.
[5] History of Rationalism , II, 320.
[6] State Papers Domestic , Elizabeth, Vol. CXLIV, No. 7.
[7] Ibid , 243.
[8] Ibid .
[9] Calendar State Papers , Vol. VIII, No. 994.
[10] Letter from Staper, State Papers Domestic , James I, Vol. XV, No. 4.
[11] Works , III, 477, eds. Spedding, Ellis, and Heath, 7 vols., London, 1857-74.
[12] Act I, Scene 1, Dramatic Works , 6 vols., London, 1879.
[13] Itinerary , II,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