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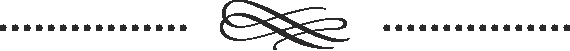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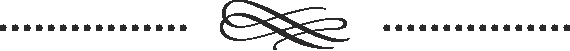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1538年,英王亨利八世发布公告,要求英格兰的每座教堂都要放置“一部最大的全本英译《圣经》”。公告还要求教士把《圣经》放在“最方便的地方……使教区居民能方便地找到和阅读”;不仅如此,“你们不得阻碍任何人聆听和阅读这本《圣经》,而应该明确地鼓励和劝告所有人都来读《圣经》”。

《圣经》被翻译成英文,成为独立的英国教会的最高权威,由此希伯来人的历史、传统和伦理法则成为英国文化的一部分,并在此后的三个世纪里成为影响英国文化的最主要因素。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来说,《圣经》把“我们英国人的精神和历史与希伯来人的精神和历史联系在一起了”。 [1] 这远不是在说英格兰是个亲犹太人的国家,但如果没有英译《圣经》的背景,即使考虑到后来出现的战略因素,英国政府也很可能不会发布《贝尔福宣言》或对巴勒斯坦进行托管。
宗教改革所到之处,《圣经》就取代了教皇成为最终的精神权威。为了打击罗马的权威,基督教源自巴勒斯坦这一事实被不断加以强调。那些过去被教皇诏书统治的地方,如今改由上帝直接管理,上帝的旨意通过希伯来人的约书传达给了亚伯拉罕、摩西、以赛亚、以利亚、但以理、耶稣和保罗。
“考虑一下这个伟大的史实,”托马斯·赫胥黎说,“这本书已经融入英国历史中最美好和最高尚的东西,成为不列颠的民族史诗。” [2]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个民族的史书变成了另一个民族的史诗。到1611年英王詹姆斯钦定版(King James Version)《圣经》出版后,这一过程彻底完成了。此时,英格兰已经对《圣经》视如己物,就像伊丽莎白女王和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当时的作者在谈到英译《圣经》时总习惯性地称之为“这本我国的《圣经》”、“这本最经典的英国作品”等;霍尔(H. W. Hoare)在《英译〈圣经〉的演化》( Evolution of the English Bible )一书中甚至说《圣经》是英国“最古老的传家宝”。可见学者也会因为激情而步入歧途,因为英译《圣经》既不如乔叟的作品古老,也并非传家宝,只在翻译方面有所传承。《圣经》的内容是对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的起源、信仰、律法、习俗和历史的记录,成书之时英格兰还没人会读写。尽管如此,没有一本书能像《圣经》那样深地渗透到英国人生活的精神本质之中。沃尔特·司各特临终时请洛克哈特(Lockhart)为自己诵读,当洛克哈特询问读哪部书时,司各特回答:“唯有那一部。”
《圣经》对英国人影响如此之大,究竟是由于其本身的内容还是钦定版的优美文字,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研究钦定版《圣经》对英格兰语言和文学产生的影响之书籍能装满一整座图书馆。但这并非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真正关注的是《圣经》对英国人民熟悉和亲近巴勒斯坦的希伯来传统所起到的作用。
为什么这本犹太人的家族史成了英国文化的第一书?当弥尔顿在《失乐园》和《斗士参孙》( Samson Agonistes )等作品中撰述英格兰起源的史诗时,他为什么使用了《圣经》中的题材?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 Pilgrim ’ s Progress )在多数家庭里近似于第二本《圣经》,为什么他在写作时也去《圣经》中寻找题材?威尔士作家约翰·考珀·波伊斯(John Cowper Powys)曾问道:为什么英国人对《旧约》那么“狂热”?为什么“我们盎格鲁—凯尔特族人只在犹太人的感情和想象中找到了个人信仰”?他猜测:“或许在不列颠岛的原住民中存在一支非雅利安的前凯尔特人,他们内心深处的祖先记忆被这本闪米特语的书唤醒了?” [3] 普通英国人对这种凯尔特解释嗤之以鼻(不过这个解释对盎格鲁—以色列运动的追随者可能有一定吸引力,他们通过对《圣经》某些零散篇章的扭曲解读,认为英国人是以色列十大流散支派其中一支的后裔 [4] )。但要想理解《旧约》对英国人的吸引力,其实不必上溯到不列颠原住民那么久远的时代。它的魅力是基于两个与其他原始宗教著作都不同的基本理念:其一,上帝的唯一性;其二,一个通过人与人、人与上帝之间的行为准则建立秩序的理想社会。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先生是在《圣经》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典型英国绅士,为人处世就跟古代的先知一样。他写道,基督教有关上帝唯一性的概念源自希伯来人。当我们问“这个在古时候被完全否定的概念,是如何在漫长的黑暗中保持生机,并被稳妥地交给我们的。答案是,这个真理是被一个为他人所蔑视的弱邦小国作为宗教责任维护下来的。他们从《旧约》中获得了这个宝贵的真理,并把它保存了下来”。 [5]
至高无上的上帝选定了一个民族替他传达训诫,这个民族努力谨守训诫,虽然做得不够完美,但依然不断尝试——《圣经》中的这些说法为一代又一代的英国人所熟知。每个人都熟知《圣经》,许多人家只有《圣经》这一本书,所以人们一遍接一遍地读,直到书中的文字、图像、故事像面包一样熟悉。孩子们会背诵《圣经》中长长的章节,他们往往在认识自己国家之前先认识了巴勒斯坦的地理。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回忆,他与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在1914年12月第一次见面时,谈话中出现的地名“比西线的地名更熟悉”。 [6] 贝尔福勋爵的传记作者说,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趣源自他少年时期在母亲的教导下受到的《旧约》教育。他受到的教育会像罗斯金(Ruskin)一样严格吗?他在自传的第一页上说,母亲要求他朗读整本《圣经》,“每个音节、每个拗口的名字,从《创世记》一直到《启示录》,每年完成一次……完成的次日再从《创世记》开始重新读起”。 [7] 或许他不知道他所做的就是犹太教堂里每年在做的(但不包括《新约》),但他说这是“我所受的必备教育中最珍贵的部分”。
英格兰的国教何时诞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何时成为英国的上帝,《旧约》中的英雄何时替代了天主教的圣者,这些没有人能给出确切的日期。1500年前后全欧洲都在经历深刻的变革,中世纪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或按当时人的叫法——新学时代(the New Learning)。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另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1454年活字印刷的发明,或者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再或者是1517年路德把反抗罗马的文章钉在教堂门上。实际上,新时代的产生不是因某一个事件,而是这些发生在50年内的事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英格兰经过动荡的16世纪才完成宗教改革。这个世纪的每个十年都有人在断头台上人头落地,在火刑柱上被烧死。这些洒下鲜血的人包括《圣经》的翻译者廷代尔(Tyndale)、国务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信仰旧教的托马斯·莫尔爵士(Thomas More)和信仰新教的大主教克兰麦(Cranmer)。与此同时,翻译《圣经》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新世纪初随英王詹姆斯钦定版的完成达到了巅峰。翻译的过程代价极大,但正如波斯诗人所言,染着伟人鲜血的土地,开出的玫瑰最红。
1611年完成的英译《圣经》是由廷代尔在1525年开始翻译的,但他的版本绝非《圣经》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由于没有印刷术,早期版本的复制只能靠人工誊写,因此难以流传。印刷技术一出现就像洪水涌出了堤坝,再也没人可以阻止英译《圣经》的大范围流传。无论教会怎样想方设法收买、焚毁,总是会有更多的《圣经》被印刷出来。
亨利八世为离婚而反抗罗马教皇、支持新教,并不是宗教改革发生的原因,它只是使英王提早站在了改革者一边。即使没有亨利,或者他不曾爱上安妮·博林(Anne Boleyn),宗教改革一样会发生。新教的思潮来自海外,而且自14世纪约翰·威克利夫和他的罗拉德派(Lollard)教徒与罗马教廷的弊端做斗争时就在英格兰广泛传播。威克利夫和他的信徒在1380年代就把《拉丁通行本圣经》完整地翻译成了英文。想想这个工作量就能知道他们的宗教热情有多么巨大。威克利夫版的《圣经》
 留存下来170部手抄本。当时肯定有更多的手抄本,因为罗拉德派被斥为异端遭到迫害的时候很可能有很多抄本被毁,更多的抄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散佚。估计当时可能总共有200至400部抄本,每部都需要精心抄写(《圣经》共有约77.4万字),且抄写者还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或自由。在那时,拥有一本英译《圣经》甚至也可以被作为异端罪的证据。“我们的主教谴责和烧毁上帝的旨意,仅仅因为它用的是自己的母语。”
[8]
一名罗拉德派作家在15世纪批评说。
留存下来170部手抄本。当时肯定有更多的手抄本,因为罗拉德派被斥为异端遭到迫害的时候很可能有很多抄本被毁,更多的抄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散佚。估计当时可能总共有200至400部抄本,每部都需要精心抄写(《圣经》共有约77.4万字),且抄写者还可能因此而失去生命或自由。在那时,拥有一本英译《圣经》甚至也可以被作为异端罪的证据。“我们的主教谴责和烧毁上帝的旨意,仅仅因为它用的是自己的母语。”
[8]
一名罗拉德派作家在15世纪批评说。
但让主教们担心的问题不是阅读《圣经》本身,而是谁在阅读。真正激怒主教们的也不是翻译工作本身,而是翻译未经授权,且阅读非授权版《圣经》的人来自有异端和反叛倾向的阶层,这个倾向已经在1381年的农民起义中显现出来了。富人和正统信徒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乐于维护教会的权威,他们因此经常能获得持有和阅读英文《圣经》的特别许可。但高级教士不希望普通人接触《圣经》,以防他们绕过教堂的圣礼找到直通上帝的途径。1408年,阿伦德尔(Arundel)大主教颁布教令,规定任何人制作或使用未经许可的《圣经》译文可被判处火刑。
[9]
这项教令是基于英王和议会在1400年通过的一项名为“关于对异教徒施以火刑”的恶法,
[10]
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条允许因宗教信仰判处死刑的法令。法令写道,“近来出现了一种新教派,有很多堕落的成员,公开或私下里散布、宣讲各种新教条、异端邪说和错误思想……建立学校,著书立说,恶毒地教导大众”,他们必须受到地方法院的审判,如果不发誓放弃异端,就应该被烧死,“这样的惩罚是为了在其他人的内心引发恐惧”。不难理解为什么托马斯·富勒在他的《教会史》中谈及1397年翻译《圣经》的威克利夫派成员约翰·德特里维萨(John de Trevisa)时,感叹他不知最应该赞叹的是“他完成如此困难和危险的工作时所展示出的能力、勇气还是韧性”
 。
。
一般而言,威克利夫版的《圣经》是可以放在衣袋里的小型本,供游走的罗拉德派教士使用,他们在布道时可以用日常用语把经文念给民众听。记录显示一本威克利夫版的小型《圣经》成本约为40先令
 ,相当于今天
,相当于今天
 的150美元。尽管受到了压制,但仍能保留下170本,这进一步说明了其价值所在。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一版本的残卷仍然为人所用。福克斯(Foxe)在《殉教者之书》(
Book of Martyrs
)中提到,1520年时有人用一车干草换取英文《新约》中的几章。
的150美元。尽管受到了压制,但仍能保留下170本,这进一步说明了其价值所在。近一个世纪之后,这一版本的残卷仍然为人所用。福克斯(Foxe)在《殉教者之书》(
Book of Martyrs
)中提到,1520年时有人用一车干草换取英文《新约》中的几章。

罗拉德派的本质是对宗教民主化的尝试,使民众直接读经文,而绕过教会的什一税和赎罪券,以及出售赎罪券的人、用以自肥的修道院长、道貌岸然的主教等整个教会的贪腐帝国。威克利夫想把经文翻译成英文,因为他相信《圣经》才是人间和天国律法的本源,而非罗马教廷宝座上的那顶红帽子。如果《圣经》不能以日常用语存在,就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指导民众的日常生活。虽然威克利夫翻译了《圣经》,但不能说他让英格兰熟悉了《圣经》,特别是《旧约》。当时的手抄本太少,成本太高,民众识字率太低,无法形成广泛的影响。威克利夫最大的贡献是他创造的理念,即《圣经》是每个人都能自己诉诸的最佳精神权威。他的努力为英国新教运动建立了深厚的根基,使宗教改革的萌发成为可能。但英文《圣经》显现真正的生命力还需要等待印刷术的到来。
在威克利夫之前的年代里,《圣经》已经为人所熟知,特别是《旧约》中的《创世记》、《出埃及记》、《诗篇》,以及新约中的《福音书》。我们已经看到,在英国最早的史学家、凯尔特人吉尔达斯的《使徒书》中,每一行都有《旧约》的痕迹。从比德开始,很多人早在诺曼征服之前就把许多《旧约》和《新约》的章节翻译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
 根据约翰的说法,比德本人翻译了《福音书》,阿尔弗雷德大帝翻译了《诗篇》和《十诫》,作为他翻译教会和教父历史以更好地教育人民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多个版本的《诗篇》、《福音书》及“圣经故事”被翻译为古英语,但都是出于信仰的虔诚,并非像威克利夫那样为了改革宗教。盎格鲁—撒克逊的神职人员所能接受到的教育是有限的,他们的拉丁语知识少得可怜。在撒克逊人掌权时代,布道是用本国语言。为了帮助识字不多的神父进行布道,译文写在拉丁文经文的旁边或行间。《旧约》中的故事也是布道中的内容,包括亚当和夏娃、先祖、约瑟和兄弟们,以及摩西出埃及的故事。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是撒克逊吟游诗人在宴会上吟唱诗歌的主题,以及哑剧和神迹剧的内容。
根据约翰的说法,比德本人翻译了《福音书》,阿尔弗雷德大帝翻译了《诗篇》和《十诫》,作为他翻译教会和教父历史以更好地教育人民的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此外,还有多个版本的《诗篇》、《福音书》及“圣经故事”被翻译为古英语,但都是出于信仰的虔诚,并非像威克利夫那样为了改革宗教。盎格鲁—撒克逊的神职人员所能接受到的教育是有限的,他们的拉丁语知识少得可怜。在撒克逊人掌权时代,布道是用本国语言。为了帮助识字不多的神父进行布道,译文写在拉丁文经文的旁边或行间。《旧约》中的故事也是布道中的内容,包括亚当和夏娃、先祖、约瑟和兄弟们,以及摩西出埃及的故事。在更多的情况下,它们是撒克逊吟游诗人在宴会上吟唱诗歌的主题,以及哑剧和神迹剧的内容。
卡德蒙(Caedmon)是英国第一位诗人,写了很多以《旧约》为题材的叙事诗。在比德令人难以忘却的故事中,卡德蒙是个牧人,被一群人叫来在篝火宴会中唱歌,但他不会,无法让客人高兴。那天晚上,他在牛群中睡觉时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陌生人命令他唱歌,当他表示自己不会唱时,上帝给了他歌喉和歌词,于是他起身拿起竖琴,唱出了一首歌。之后他又唱了一遍,这次歌词被记录下来。“他的歌,”比德说,“唱的是世界如何产生,人如何诞生,就是创世的历史。他还唱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往应许之地的故事。” [11]
许多卡德蒙诗篇其实是在他生活的7世纪之后完成的作品,被归在他名下是因为比德让他成了名人。这些诗篇的作者可能是一些撒克逊吟游诗人,内容选自《旧约》中比较有可能为撒克逊听众所欣赏的典故:国王和暴君的传说,诗人和听众能理解的战斗和英雄故事。在诺曼人征服不列颠之前的四个世纪里,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经常入侵,大肆劫掠,使得英格兰的许多地方长期处于战争之中。几乎每年都有丹麦人坐着船在沿海的某处跳下发动袭击,烧杀劫掠;几乎没有居民点未曾被焚为灰烬过。当诗人说起亚伯拉罕率领他的“贵族”和“军队”在西订谷(vale of Siddim)与国王们作战的故事时,他们心里想到的实际上是丹麦人的入侵。撒克逊人败多胜少,亚伯拉罕的胜利在精神上能给他们带来虚幻的满足,他们沉浸在诗人描绘的“自由人民的屠杀者被猛禽撕碎”的图景中,和亚伯拉罕杀死麦基洗德(Melchizedek)的敌人后说的话中[由斯托普福德·布鲁克(Stopford Brooke)翻译成现代英语]:
你不必害怕与我们厌恶的敌人打仗——
与那些北方人的战争!——因为那群食腐肉的鸟
身上溅满鲜血,正站在山坡之下
咽喉里塞满了那些坏蛋的血肉。

“法老的军队”被红海的巨浪吞没的可怕命运,也是撒克逊听众喜欢的暴君横死的故事。“在那个众所周知的日子,在大地中央有一大群人向前涌去。”不具名的诗人在古英文版《出埃及记》中写道。埃及军队冲了过来,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使以色列人战栗不已。但摩西指挥以色列人进行防守,要求他们“穿上战衣,想着高尚的行为”。然后,他劈开波浪,众部落这才穿越了红海。“他们持盾走过盐沼”,在他们身后,红海又复原了,埃及人在做垂死挣扎——“高傲的海浪从来没有这样高过!敌军全部沉没了!”
随着北欧人每年的袭扰逐渐变成领土占领,想把敌人赶出家园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像阿尔弗雷德大帝那样的斗士,以及阿尔弗里克修道院长(Abbot Aelfric)
[12]
那样的宗教领袖,试图在民众中激起一种共御外敌的爱国情怀。阿尔弗里克死于1020年,因学识渊博被称为“文法家”。他被誉为“当时和死后五个世纪里最伟大的用英语写作的神学家”。为了传播宗教教育,以及一种爱国的战斗精神,阿尔弗里克利用了古代希伯来人的例子。除翻译《摩西五经》之外,他把《旧约》缩写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并根据《士师记》、《以斯帖记》——以斯帖“拯救了她的民族”——以及《犹滴传》(
Book of Judith
)和《马加比传》(
Book of Maccabaeus
)写成了布道词。
 他解释了选择马加比的理由:“那个家族以无比勇敢的精神,与试图消灭他们并把他们从上帝赐予的土地上铲除的异教徒军队战斗,屡次取得伟大的胜利……他们之所以获胜,是依靠了真正的上帝,并遵循了摩西的律法……所以我把它们翻译成英语,你们通过阅读他们的事迹能获得启示。”阿尔弗里克把犹大·马加比的故事收入他写的《圣徒生平》(
Lives of the Saints
)中。他说,马加比“在《旧约》中和上帝的选民一样圣洁,因为他从不违背上帝的意志……他是上帝的骑士,总是为保护他的子民而与侵略者做斗争”。
他解释了选择马加比的理由:“那个家族以无比勇敢的精神,与试图消灭他们并把他们从上帝赐予的土地上铲除的异教徒军队战斗,屡次取得伟大的胜利……他们之所以获胜,是依靠了真正的上帝,并遵循了摩西的律法……所以我把它们翻译成英语,你们通过阅读他们的事迹能获得启示。”阿尔弗里克把犹大·马加比的故事收入他写的《圣徒生平》(
Lives of the Saints
)中。他说,马加比“在《旧约》中和上帝的选民一样圣洁,因为他从不违背上帝的意志……他是上帝的骑士,总是为保护他的子民而与侵略者做斗争”。
犹大裹着闪闪发亮的胸甲
像个巨人一样全副武装
执剑保护着主人。
他在战斗中的举止就像一头狮子一样……
阿尔弗里克在故事中增添了帮助读者理解的内容,如果任何人想知道为什么上帝的天使会在犹太人面前降临,他们需知道:
犹太人跟上帝最亲
在古老的律法书中就是这样,因为他们
尊万能的上帝为圣,并持续祭拜,
后来上帝的儿子耶稣降临,
耶稣生下来就是犹太族人
当时有些人不相信他是上帝
对他进行迫害……
但那个民族中有许多好人
古老的律书和新约中都有
族长、先知、圣徒……
阿尔弗里克可能是看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征兆。他发现撒克逊人在与信仰异教的丹麦人的接触中,开始转信他们的先祖信仰的异教诸神。他特别指出,当古代以色列人“放弃了真实存在的上帝之后,立即就遭受到了他们周围的异教国家的折磨和羞辱”。然而,“当以色列人再次真诚忏悔,请求上帝援助的时候,上帝还是给他们送来一位士师(judge),他打败了敌人,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阿尔弗里克罗列了几位英国国王——阿尔弗雷德、阿瑟尔斯坦(Athelstan)、埃德加,他们像以色列的士师一样,在上帝的帮助下打败了敌人。
与此相似,有关犹滴的故事,阿尔弗里克解释道,“也按照我们的方式翻译成英语,希望你们以她为榜样,与入侵的敌人做斗争,保护家园”。阿尔弗里克关于犹滴诛暴君的布道词,是受了盎格鲁—撒克逊圣经诗中最鼓舞人心的《犹滴》( Judith ) [13] 的启发。这首诗据称是为纪念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继母犹滴而写的,年轻的犹滴于856年与阿尔弗雷德大帝的父亲完婚,成为皇后。但另有学者认为这首诗的写作年代晚于阿尔弗里克,是受他的布道词影响写成的,内容可能是赞颂10世纪初麦西亚(Mercia)女王率领国民抗击丹麦人的事迹。无论如何,这首与《贝奥武甫》( Beowulf )齐名的古英语文学作品,使犹滴成为英国人最爱戴的女英雄。在遗留下来的残篇里,我们看到荷罗孚尼(Holofernes)像典型的撒克逊领主一样醉醺醺的样子,他:
大笑、大吼
远远就能听到他的吼声
伴随着爆笑声和酒后的疯狂。
犹滴走进帐篷,亚述王正醉卧昏睡。她的剑光落处,暴君的人头落地。她像胜利者一样举起滴着鲜血、蓄着黑须的人头,展示给站在城墙外的人群看,鼓励他们发动暴动。
自豪的希伯来人用剑砍出一条去路
人们举着长矛冲过去发动进攻。
胜利了,地上躺满了被杀死的亚述人,成了乌鸦的美食。
虽然这些用古英语写成的诗篇一定使聆听布道的撒克逊英格兰人熟悉了基督教的希伯来起源,并使古巴勒斯坦的历史变得活灵活现,但后来的英文《圣经》与这些残篇没有关系。原因之一是语言,威克利夫时代的人已经无法读懂这些诗篇所用的语言,更不用说廷代尔时代的人了。原因之二是外族的征服割裂了历史,征服者之前的大部分文化会被迅速忘记。当时懂拉丁文的人很少,民众的识字率不高,这让阿尔弗雷德大帝和阿尔弗里克十分苦恼,所以早期《圣经》译本是为了启蒙——让人民熟悉自己的宗教传统,就如同今天给孩子读圣经故事一样。诺曼人征服之后的不列颠受更好的拉丁文知识以及强调辩证法和经文的经院派神学家影响,更严格地遵循拉丁文《圣经》和神父的权威。这种情况至少延续到威克利夫的时代。像阿尔弗里克那样随意地改述马加比的故事,缩写《旧约》,并略去其中艰涩的段落和《利未记》中的律例,即使当时人可以读懂他的语言,这对他们也无异于异端邪说。
下一个翻译《圣经》的罗拉德教派,与撒克逊时代受国王和教会的授权相反,是在统治阶层的禁令下完成的,尽管威克利夫本人就是神父。虽然在15世纪遭到严厉的镇压,但罗拉德教派的努力使宗教改革最终冲破堤防,从而改变了欧洲的历史。廷代尔曾经骄傲地对那些信仰教会权威胜于《圣经》的“学者”说:“我将让一个种地的孩子知道的经文比你们还要多。”
 这句话概括了这场大变革的实质。
这句话概括了这场大变革的实质。
当廷代尔在1520年代开始他的工作时,未经授权翻译《圣经》依然是可入刑的行为,因为亨利八世尚未与罗马教廷决裂。在科隆的一间小顶楼里,点着蜡烛的桌面上摆着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语法书,当时仍处于流放之中的、英译《圣经》的真正开创者廷代尔开始了翻译工作。威克利夫的版本是对翻译的翻译,因为他使用的底本是拉丁通行本;但廷代尔懂希腊文,并略通希伯来文,因此采用了《圣经》原文本进行翻译。此外,他手中也没有威克利夫的译本——他是从零开始的。在他的《新约》译本的前言中,有一封致读者的信,他在信中明确表示,“没有人可以帮助我造假,因为我找不到其他人的译本”。希腊文和希伯来文研究在拉丁文占主导地位的中世纪一直被忽略,但自从威克利夫时代起,新学运动使这两种语言的研究获得新生。红衣主教沃尔西(Wolsey)此时刚在牛津建立起一座学院,后来成为著名的基督教堂学院,罗伯特·韦克菲尔德(Robert Wakefield)担任第一任希伯来语首席教授;剑桥也成立了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采用三语教学。
在牛津,希伯来文研究在13世纪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在伟大的主教格罗斯泰特(Grosseteste)的教导下,新成立的方济各会(Franciscan Order)致力于研究知识和哲学。牛津在犹太人被驱逐前曾经拥有全世界最大的犹太人社区之一。格罗斯泰特和罗杰·培根(Roger Bacon)是当时方济各会的头面人物,他们都在牛津与犹太人研究过希伯来语。培根认为要想获得真知必须通晓希伯来文,因为所有知识都源自上帝的启示,最初是以希伯来文出现的。
 现存的一部希伯来语法著作残篇,据说是出自他之手。但方济各会衰败后,希伯来文研究就消失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重启。
现存的一部希伯来语法著作残篇,据说是出自他之手。但方济各会衰败后,希伯来文研究就消失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重启。
1480年代和1490年代,欧洲大陆的犹太拉比指导印刷了新版希伯来文《旧约》。1516年,伊拉斯谟出版了新版希腊原文《新约》,并以之为底本翻译为拉丁文。路德于1522年根据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本将《新约》翻译为德文,而他的德文《旧约》(1534年)则是根据1494年的希伯来马所拉抄本(Hebrew Masoretic text)翻译的。
廷代尔先翻译了《新约》,译本在德国印刷,于1526年偷运入英格兰。在全部6000本中只有三本流传到今天,因为当局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主教们紧张地想买下所有译本加以销毁,这实际上给廷代尔提供了稳定的收入,供他翻译《旧约》之用。同时期写成的霍尔(Hall)的《编年史》( Chronicle )记载了时任英国大法官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审问涉嫌异端罪的乔治·康斯坦丁(George Constantine)。莫尔说:“康斯坦丁,请实言……海对面有廷代尔、乔伊和许多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知道如果没有人帮助,他们无法生活,肯定有人送钱支持他们。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你应该知道钱从哪里来。请告诉我是谁在帮助他们。”
“‘大人,’康斯坦丁说,‘我能说真话吗?’‘请说!’大人说。‘我很乐意。’康斯坦丁说。‘实际上,’他说,‘是伦敦主教在帮助我们。为了买下《新约》尽数烧毁,他给了我们大量的钱,这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来源。’‘说实话,’莫尔说,‘主教买书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告诉他的。’” [14]
除了这个意外的经费来源之外,为廷代尔以及后来的科弗代尔(Coverdale)及其合作者提供资金支持和鼓励的,主要是一群富裕的伦敦商人。他们代表了崛起中的资本家阶层,渴望摆脱罗马官僚的控制。他们支持着流放中的廷代尔,支付他在德国印刷新版《圣经》的费用,并偷运入英格兰后分销。后来,官方同意公开印刷的“大圣经”(Great Bible),也就是亨利八世下令在各教堂阅读的那本,全部印刷费用都是由富裕的纺织商人安东尼·马勒(Anthony Marler)
 负担的,但他没有想到这笔投机给他带来一份好回报。他获得了特许销售权,定价10先令(否决了克伦威尔建议的13先令4便士)。他所获得的回报超过了他的原始投入。
负担的,但他没有想到这笔投机给他带来一份好回报。他获得了特许销售权,定价10先令(否决了克伦威尔建议的13先令4便士)。他所获得的回报超过了他的原始投入。
不过,这是十年之后的事了。当廷代尔的《新约》刚刚偷运入英格兰时供不应求,但商人们面临的风险不是亏本,而是掉脑袋。需求在接下来的几年并未衰减,在廷代尔翻译的《圣经》面世之后四年,伦敦主教压制的努力如此失败,以致他觉得有必要在圣保罗教堂院内公开焚毁。
 同年,即1530年,廷代尔完成了《摩西五经》的翻译,在马尔堡(Marburg)印刷,然后由代理人运过英吉利海峡,送到了望眼欲穿的英格兰读者手中。
同年,即1530年,廷代尔完成了《摩西五经》的翻译,在马尔堡(Marburg)印刷,然后由代理人运过英吉利海峡,送到了望眼欲穿的英格兰读者手中。
与此同时,在托马斯·克伦威尔的高明操纵下,政治局势向着与罗马决裂的方向发展。在红衣主教沃尔西因不愿或无法实现亨利的愿望于1530 年被处决后,克伦威尔的崛起开始了。不久之后,他就给他的君主娶了一位新妻子、奉献了一个新头衔。1533年,亨利八世与安妮完婚。1534年,议会通过法案要求神职人员服从英王。1535 年,《至尊法案》(Act of Supremacy)确立亨利为“英国国教会最高领袖”。推出官方英文《圣经》的工作随即展开。由于在书页边的批注中尖锐地批评了拉丁通行本歪曲文本原意以迎合天主教教义,廷代尔的译本已经引发了太大的争议,所以不能被接受。1534年,神职人员向英王请求“出于指导的目的给人民提供”《圣经》的新译本。
 其结果就是“马修圣经”(Matthew Bible)。这个新译本实际上包括了廷代尔已经完成的部分,以及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接续完成的部分。这个译本印好的书页运入英格兰后,于1535—1536年间出版发行。后来,在大主教克兰麦的指导下,于1538—1539年间进行了修订和再版,这就是第一次在英格兰印刷的官方授权的完整英文《圣经》译本。这个被称为“克兰麦圣经”(Cranmer's Bible)或“大圣经”的译本,就是英王1538年公告中提及的版本,扉页上的这句话代表了150年斗争的最终结果:“此《圣经》即为官方授权所有教堂使用的版本。”其卷首插图很是精美,据说由霍尔拜因(Holbein)设计,图中一群收到书的小人高呼“国王万岁!”。
其结果就是“马修圣经”(Matthew Bible)。这个新译本实际上包括了廷代尔已经完成的部分,以及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接续完成的部分。这个译本印好的书页运入英格兰后,于1535—1536年间出版发行。后来,在大主教克兰麦的指导下,于1538—1539年间进行了修订和再版,这就是第一次在英格兰印刷的官方授权的完整英文《圣经》译本。这个被称为“克兰麦圣经”(Cranmer's Bible)或“大圣经”的译本,就是英王1538年公告中提及的版本,扉页上的这句话代表了150年斗争的最终结果:“此《圣经》即为官方授权所有教堂使用的版本。”其卷首插图很是精美,据说由霍尔拜因(Holbein)设计,图中一群收到书的小人高呼“国王万岁!”。
与此同时,被福克斯称为“英格兰的使徒”的廷代尔——这位勇于献身的顽强学者,因翻译经文被处以火刑。他没有死在英国人手里,但讽刺的是他却是因英国教会认同了他的观点而死。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而言,这位在他的领土上进行翻译工作的英国翻译家代表了胆敢脱离罗马教会的异端——英国教会,因此将他处以火刑。另一讽刺之处在于,廷代尔被处死后仅几个月,他的宿敌托马斯·莫尔即因拒绝承认英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而被处死。莫尔试图阻止新教浪潮,而廷代尔顽强地传播新教思想,双方因此发生了一场伟大而激烈的争论,收录在莫尔的《对话录》( Dialogue )和廷代尔的书信回复之中。双方都因信仰而死,却站在了不同的阵营。虽然莫尔的名声更大,但廷代尔的影响更深远,因为他的译作永恒地响彻在他身后的英语世界里。
斯特赖普(Strype)在一个世纪后描述“大圣经”受到的欢迎时写道:“不仅有知识的人,所有英格兰人,包括普通平民,都因获得这本上帝之书而快乐,并贪婪地阅读上帝的话。这真是太奇妙了!所有能买到书的人都买了,并如饥似渴地阅读,或让别人读给他们听。”作为大主教克兰麦的传记作者,斯特赖普所说的带有个人偏见。实际上,英格兰至少有一半的人仍是忠诚的天主教徒,他们视本国语《圣经》译本如毒蛇一般恐怖。福克斯的《殉教者之书》中有一个例子:埃塞克斯郡(Essex)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的15岁男孩威廉·马尔登(William Maldon),因偷读《圣经》而惹怒了他的父亲,愤怒的父亲差点杀了他。“我和父亲的学徒,”他写道,“凑钱买了一本英文《新约》,藏在我们的床下……我父亲拿着一根大棍子走进我们的房间……父亲问:‘你的老师是谁?’我说:‘父亲,我们除了上帝,没有老师。’”被激怒的父亲没有能够让儿子认罪,便打他,大叫道:“给我绳子,我要把他吊起来……”他写道:“我父亲拿着绳子过来了,母亲央求他放过我,但没有用。父亲把绳子套在我脖子上,猛地一拉,几乎把我拉下床来。我母亲大哭起来,拉住他的胳膊,我兄弟理查也在旁边大哭。父亲终于松了绳子,让我回到了床上。直到六天后我脖子上的伤还很痛。”

英王亨利和主教们更像威廉的父亲,而不是那个孩子。不久之后,他们便被授权出版英译《圣经》所释放出的路德宗改革浪潮惊呆了。亨利对新教的支持仅限于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他并不信奉新教的教义。他允许翻译《圣经》,只不过想以英文《圣经》作为自己代替罗马教廷权威的符号。他把自己视为英格兰的教皇,并随时准备像罗马教皇一样镇压异端。事实上,他于1540年在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以异端罪烧死了三名路德派教徒,并在同一天以叛国罪处死了三名支持教皇的教徒。 [15] 对此,路德做了如下评论:“大地主亨利想要的即是英国人必须信奉的,不信即死。” [16]
但大坝已经有了裂痕,即使是大地主亨利也阻止不了变革的大潮。虽然他在公告中警告他的臣民,在使用这本书的时候,要“谦卑、虔敬”,要低声诵读,而不能在酒馆里为难以理解的段落进行争论,“也不要在小客栈里公开说理”,
 但民众在能用自己的语言阅读经文后,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沉醉其中。每个教堂的讲道坛前都用铁链系着一本巨大的《圣经》,只要有人能朗读经文,人们就会围拢过来兴奋地听着,就像我们今天听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比赛结果一样。在圣保罗大教堂,有六部《圣经》系在“不同的柱子上,供想读的人阅读”,那热烈的场面让当局感到震惊。福克斯说,这些《圣经》很受欢迎,“特别是有人朗读的时候”。有一个叫约翰·波特(John Porter)的人,“很年轻,且身材高大”,在这项“神圣的活动中成了专家”,“有大量的人来听波特朗读,因为他读得清楚,声音洪亮”。这种世俗的布道,神职人员怎么可能会欢迎?波特被逮捕,罪名是阐释经文,聚众引发混乱,违反国王公告。他被投入纽盖特(Newgate)监狱“最深的地牢里,用铁链拴着。大约六天或八天后死去”。
但民众在能用自己的语言阅读经文后,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沉醉其中。每个教堂的讲道坛前都用铁链系着一本巨大的《圣经》,只要有人能朗读经文,人们就会围拢过来兴奋地听着,就像我们今天听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的比赛结果一样。在圣保罗大教堂,有六部《圣经》系在“不同的柱子上,供想读的人阅读”,那热烈的场面让当局感到震惊。福克斯说,这些《圣经》很受欢迎,“特别是有人朗读的时候”。有一个叫约翰·波特(John Porter)的人,“很年轻,且身材高大”,在这项“神圣的活动中成了专家”,“有大量的人来听波特朗读,因为他读得清楚,声音洪亮”。这种世俗的布道,神职人员怎么可能会欢迎?波特被逮捕,罪名是阐释经文,聚众引发混乱,违反国王公告。他被投入纽盖特(Newgate)监狱“最深的地牢里,用铁链拴着。大约六天或八天后死去”。

随后,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明确禁止未经授权的人朗读《圣经》。这项法案规定:贵族和绅士可以为家人轻声朗读《圣经》;女贵族、女绅士可以私下阅读,但不能读给其他人听;但社会“底层”——女人、技师、学徒、自耕农以下的人——被禁止私下或公开朗读,除非国王认为朗读对他们的生活有补益,给予特别许可。 [17]
这项法案被执行的可能性和禁酒令一样渺茫。虽然英国民众并未在一夜之间都变成《圣经》的读者,但有足够多的新教徒,或按当时的称谓——路德宗信徒——把自由、独立地阅读《圣经》当做基本信条,这就使亨利的压制性措施毫无效果。特别是在玛丽女王治下的天主教复兴时期,由于《圣经》被丢出教堂并被禁止,它因此像一切被暴君禁止的文字一样获得了额外的意义。当“好博士泰勒”被架上火刑柱的时候,他向自己教区的居民说道:“善良的人们,我教给你们的都是上帝的圣言和从《圣经》中提取出的教诲。今天我就用我的鲜血给它上封条。”
 在那个烈火熊熊的1555年,在玛丽女王强迫国民重新臣服罗马教廷的徒劳企图中,67名新教徒被公开烧死。有些人如罗兰·泰勒(Rowland Taylor),死于对自己原则的忠诚不渝,另一些像克兰麦,又宣誓放弃之前改宗的誓言,但死于火刑使他们成为英雄和殉教者。拉蒂默(Latimer)主教的临刑遗言预示了玛丽女王的失败:“在上帝的恩典下,今天我们在英格兰点燃了一根我相信将永不熄灭的蜡烛。”
在那个烈火熊熊的1555年,在玛丽女王强迫国民重新臣服罗马教廷的徒劳企图中,67名新教徒被公开烧死。有些人如罗兰·泰勒(Rowland Taylor),死于对自己原则的忠诚不渝,另一些像克兰麦,又宣誓放弃之前改宗的誓言,但死于火刑使他们成为英雄和殉教者。拉蒂默(Latimer)主教的临刑遗言预示了玛丽女王的失败:“在上帝的恩典下,今天我们在英格兰点燃了一根我相信将永不熄灭的蜡烛。”

后来,到了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一切又都颠倒过来,宗教改革得到恢复,《圣经》又回到了教堂。女王下令出版《圣经》的新版,并要求编辑们不要对原版“大圣经”做大改动,“仅是修改与原始希腊文本或希伯来文本有明显出入的地方”。
 所以,这一版仍然是廷代尔译本的延续,被称为“主教圣经”(Bishop
’
s Bible)。伊丽莎白的这个版本一直使用到英王詹姆斯时代。彼时,崛起的清教徒偏爱加尔文教派的“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这使得教堂里使用的官方《圣经》与许多家庭里私下阅读的《圣经》并不一致。1604年的汉普顿御前会议请求国王授权修订新的译本,这项庞大的工程随即开始了,由54名学者共同承担,这就是英王詹姆斯钦定版。
所以,这一版仍然是廷代尔译本的延续,被称为“主教圣经”(Bishop
’
s Bible)。伊丽莎白的这个版本一直使用到英王詹姆斯时代。彼时,崛起的清教徒偏爱加尔文教派的“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这使得教堂里使用的官方《圣经》与许多家庭里私下阅读的《圣经》并不一致。1604年的汉普顿御前会议请求国王授权修订新的译本,这项庞大的工程随即开始了,由54名学者共同承担,这就是英王詹姆斯钦定版。
从廷代尔开始翻译工作算起,已经过去差不多一个世纪了,在这段时间里,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学术研究有了新发展,对古代经文的研究有了新的成果,也有许多新语法、新词典、新论文可供参考。参与修订《圣经》工作的学者包括:爱德华·莱夫利(Edward Lively),牛津大学希伯来语皇家教授;兰斯洛特·安德鲁斯(Lancelot Andrewes),威斯敏斯特教士长,通晓希伯来语、迦勒底语、古叙利亚语、希腊语、拉丁语等十种语言;威廉·贝德韦尔(William Bedwell),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资深学者,欧洲最伟大的阿拉伯语学者;此外还有至少9名当时或后来的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希伯来语或希腊语教授。
 这些修订者被分为6组,每组9人,牛津、剑桥、伦敦各两组。为指导修订工作制订的13条规则体现了这些17世纪神学家和学者工匠般的严谨工作方式。每组负责若干篇章,每人独立负责若干章节。然后,所有人“一起开会讨论他们已经完成的部分,共同认定修订的部分”。接着,各组交换他们完成的篇章,“严肃、审慎地加以审读,英王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如有不同意见,修订者要把自己的疑虑明确地写下来,“注明有异议的地方,写出自己的理由,在最后的组长大会上讨论解决”。有时还会请教外部有学识的人。每位主教受命把项目的进展传达给他认识的古代语言学者,鼓励这些学者给“工作组”提出有益的意见。
这些修订者被分为6组,每组9人,牛津、剑桥、伦敦各两组。为指导修订工作制订的13条规则体现了这些17世纪神学家和学者工匠般的严谨工作方式。每组负责若干篇章,每人独立负责若干章节。然后,所有人“一起开会讨论他们已经完成的部分,共同认定修订的部分”。接着,各组交换他们完成的篇章,“严肃、审慎地加以审读,英王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如有不同意见,修订者要把自己的疑虑明确地写下来,“注明有异议的地方,写出自己的理由,在最后的组长大会上讨论解决”。有时还会请教外部有学识的人。每位主教受命把项目的进展传达给他认识的古代语言学者,鼓励这些学者给“工作组”提出有益的意见。
1611年,在成书的前言里,这些修订者称自己为“匠人”(workemen),并坦率地说,他们“是想把一个好译本修改得更好,或者说在众多好的译本中最好的版本。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的目标”。他们并不抗拒“修改自己的成果,或将做好的作品返工”。他们也不限制自己把每个原文单词都对应一个固定英文单词,理由很简单,“难道天国就是单词和音节吗”?他们这种在语言上的自由性保留了前人的工作成果;事实上,13条规则中的第1条就保证了廷代尔的风格得到保留,它要求“对‘主教圣经’的改动要尽可能小,除非有悖原文”。从他们制定的规则中可以看出他们摆脱教派纷争,对遵从源自巴勒斯坦古老年代的原始文本的诚意。例如,先知的名字和其他名称“应尽可能维持原样,采纳通俗用法”。第6条规则禁止做有倾向性的解读:“不许加旁注,除非是为解释希伯来语或希腊语单词。”最后,修订者在前言中坦承他们一直在努力避免“清教徒的谨慎”和“天主教徒的隐晦”,并坚定地申明了他们的最终目的——“经文应传达自己的意思,就如同迦南的语言一样,可以被最粗俗的人理解”。这一点,他们做到了,这是他们的荣耀,因为他们的《圣经》不仅能被从“最粗俗的人”到最博学者等所有人理解,而且举世闻名,被广泛流传和热爱。
[注释]
[1] “Hebraism and Hellenism,” chap. IV of Culture and Anarchy , 1869.
[2] Quoted Cambridge Lit ., IV, 48-49.
[3] Enjoyment of Literature , New York, 1938.
[4] 盎格鲁—以色列运动最早由理查德·布拉泽斯(Richard Brothers)于1794年提出,在随后的100年中吸引了近200万名英国和美国追随者。这些追随者相信盎格鲁—撒克逊人是以色列十支派的子孙(犹太人是留在犹太的支派)。其理论基础是,《耶利米书》中的“远处的海岛”指的正是英国。这一理论将《圣经》的个别字句做脱离语境的解读,并混合基于相似词语、语音的伪哲学。它认为“英国人”(British)一词来自希伯来语中的“Berit”和“ish”两词,分别意为“契约”和“人”,所以“英国人”是“立约之人”的意思。撒克逊人(Saxons)是“以撒之子”(Isaac’s sons)的意思。布拉泽斯称自己是大卫王的直系后代,所以应取代乔治三世成为国王。他因叛国罪被捕,但被认定为精神错乱。关于这一理论的主要著述有:Richard Brothers, A Correct Account of the Invasion of England by the Saxons, Showing the English Nation to be the Ten Lost Tribes , London, 1822; J. Wilson, Our Israelitish Origin , 1845; Edward Hine, Identification of the British Nation with Lost Israel , 1871. 另见以下期刊: The Nation ’ s Glory Leader, weekly (irregular), 1875-80; Our Race , quarterly, 1890-1900; The Watchman of Israel , monthly, 1918- .
[5] Introduction to Sheppard ’ s Pictorial Bible .
[6]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 , New York, 1949, p. 152.
[7] Praeterita , London, 1885, p. 1.
[8] Trevelyan’s Age of Wycliffe .
[9] Ibid .
[10] Ibid .
[11] Cambridge Lit. , Vol. 1, chap. VII. Also Penniman.
[12] Caroline White, S. J. Crawford. Also Cambridge Lit ., I, chap. VII, 136 ff.
[13] Brooke. Also Cambridge Lit. , I, chap. VII.
[14] Hall’s Chronicle , pp. 762-63.
[15] Gardner’s Lollardy , II, 289.
[16]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Reign of Henry VIII , XV, 737.
[17] Gairdner’s Lollar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