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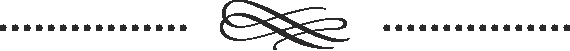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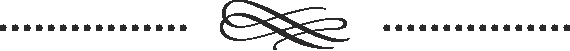
十字军东征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下水道,排走所有的不和谐”,教士托马斯·富勒在他1639年所著的《圣战史》( History of the Holy Warre )中如此写道。这虽然是带有新教偏见的观点,但想驳倒他也不容易。十字军东征的起因是对物质利益和荣耀的渴望,以及以宗教的名义对异教徒的报复。带着嗜血的兴奋和无情的残酷,在对地理、战略、后勤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战士一头向东扎去,没有任何作战计划,只想着从土耳其人手中把耶路撒冷夺回来。他们竟然能够成功,唯一的原因是敌人内部的不和。此后,十字军内部也出现了不和,甚至连出于自保考虑的最低限度的盟友关系都无法维持。在随后中世纪中期的二百年里,虽然他们的燕尾旗招展,但不过是为重现第一次东征的胜利而进行的一系列徒劳的努力。
失败似乎没有教会他们什么。一代又一代十字军骑士像旅鼠
 一样,跟着父辈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奔向死亡。巴勒斯坦,作为战场和战利品,成为欧洲大半家族的第二故乡和坟墓。鼓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明谷的圣贝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曾自豪地说,他只为每七名寡妇留下一个男人。
一样,跟着父辈的足迹一次又一次奔向死亡。巴勒斯坦,作为战场和战利品,成为欧洲大半家族的第二故乡和坟墓。鼓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明谷的圣贝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曾自豪地说,他只为每七名寡妇留下一个男人。
 但真正让这片遥远的土地变得家喻户晓的原因,不是在任何时段有多少人去了那里,而是人们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地去那里,以至于经常会出现同一个家族有两三代人甚至四代人都曾在巴勒斯坦作战、定居或去世。
但真正让这片遥远的土地变得家喻户晓的原因,不是在任何时段有多少人去了那里,而是人们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地去那里,以至于经常会出现同一个家族有两三代人甚至四代人都曾在巴勒斯坦作战、定居或去世。
在英格兰,四位牛津伯爵的墓葬坐落在赫里福德(Hereford)的教区教堂里,他们的石雕双腿交叉,表明他们都参加过十字军东征。第一任伯爵阿伯里库斯·德维尔(Albericus de Vere)人称“无情者”,他披挂全套作战装备,身披从头到脚的锁子甲和白色法袍,腰悬宝剑,脚蹬带马刺的靴子踏在一头狮子身上。他的不朽形象被保留在坟墓上的石雕中,坟墓上的时间是1194年。他身边的第二任伯爵,死于1215年;第三任伯爵,死于1221年;第五任伯爵,死于1295年。每位伯爵的墓上都刻有双腿交叉的雕像。在伯克郡的奥尔德沃斯教堂也有五个双腿交叉的雕像冢,他们都来自德拉贝什(de la Beche)家族。 [1] 这样的雕像在英格兰每个地区都能找到,有的踏着野猪或牡鹿,有的手握半出鞘的宝剑,有的双手作祈祷状,有的手持绘有圣殿骑士(Templar)十字徽章的盾牌,有的身旁合葬的夫人也双腿交叉,她们长袍上的褶皱永远是僵直的。大量带有贝壳或乔治十字图案的族徽印证了十字军的影响。直到今天,在英国仍有名为“撒拉逊人的首级”的客栈。 [2]
不过,十字军东征似乎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深入英国人的意识当中。英国没有为十字军东征树立过纪念碑,在19世纪众多的学术巨人里,没有像斯塔布斯、弗劳德或弗里曼一样的巨擘为之做研究,所有的基本学术研究都是法国人做的。十字军的东方历险故事也没有激发出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只留下了一些可笑的传奇韵律诗,如赞颂英王理查吃烤撒拉逊人的故事,以及吟游诗人布隆代尔(Blondel)营救英王理查的故事。 [3] 事实上,英语世界的人们主要是通过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十字军英雄记》( Talisman )了解到美化版的十字军东征,它也是英语文学中唯一出色的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虚构作品。
这种匮乏部分是由于英格兰在十字军东征期间的真正精力都投入了国内撒克逊人与诺曼人、贵族与国王以及国王与教会间的争斗中。
英格兰在十字军东征中的传说和荣耀绝大部分都集于英王理查一人身上。然而,他几乎不能算是个英国人。他的王后从来没有到过英格兰,他在在位的12年里也仅在自己的王国待过不足7个月的时间。巴勒斯坦把他变成了英格兰的英雄。英格兰怎样看待这位国王呢?他身材高大
 ,满头红发,穷兵黩武,带着安茹(Anjou)人的火爆脾气登上王位,只为搜刮掉国库中的最后一分钱来支付他率十字军东征的开销。他走得如此匆忙,以致英格兰几乎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只有一波又一波的征税浪潮。这股浪潮刚刚退去,又迎来新的浪潮,这次是为了把他从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Leopold of Austria)的监狱里赎出来。
,满头红发,穷兵黩武,带着安茹(Anjou)人的火爆脾气登上王位,只为搜刮掉国库中的最后一分钱来支付他率十字军东征的开销。他走得如此匆忙,以致英格兰几乎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只有一波又一波的征税浪潮。这股浪潮刚刚退去,又迎来新的浪潮,这次是为了把他从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Leopold of Austria)的监狱里赎出来。
不过,英格兰对他的印象最终还是被他在巴勒斯坦手持利剑和战斧在撒拉逊人的阵地中冲杀的英勇形象所替代。巴勒斯坦使他成为了狮心王理查,使他从一个好斗、鲁莽、不知廉耻的阿基坦(Aquitaine)和安茹人子弟成为英格兰自阿尔弗雷德大帝之后又一位英雄国王。
当然,他不是唯一以朝圣者或“十字军”骑士的身份去巴勒斯坦的英格兰国王。英格兰的王位曾两度出现空缺,因为候任国王身在圣地。理查的曾伯祖父罗伯特·柯索斯(Robert Curthose)是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一世的长子。他在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被他的弟弟亨利一世夺走了王位。理查的侄孙长腿爱德华(Edward Longshanks)运气较好,他父王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巴勒斯坦指挥第九次十字军东征。他回国后成功继承了王位,成为爱德华一世,并统治英格兰长达20年,人称“英国的查士丁尼”
 。
。
理查的父亲亨利二世、他的兄弟约翰和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都曾立誓要参加十字军东征。但前两者忙于内斗而没能成行,第三位因不愿打仗也没有兑现誓言。其他王室成员代替他们去了。威廉·朗索德(William Longsword)的父亲是狮心王理查父亲的私生子,朗索德在圣路易领导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中有出色表现;亨利三世的兄弟康沃尔伯爵理查(Richard, Earl of Cornwall)也表现不凡。那位曾率领贵族们反对亨利三世的西蒙·德蒙福尔(Simon de Montfort),可能算是英国在13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了,他在自己生涯的早期曾率领一支十字军去巴勒斯坦。还有无数人带领着骑士、扈从、士兵甚至妻子踏上这徒劳的征程,去征服“我们应得的遗产”、“上帝的土地”,但从未获得过成功。
如果英国人没有在如此长的时间中在这块产生《圣经》的土地上洒下如此多的鲜血,恐怕《圣经》不会在日后如此深地植入英国人的内心。
英国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作用没有受到公众的应有重视。根据编年史家阿古勒斯的雷蒙(Raymon of Aguelers)的目击记录,一支由30只船组成的、全部为英国船员的舰队,从海上为十字军战士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援,直到他们攻下了安条克获得第一个基地。
[4]
一代人之后的英国历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说,“当亚洲的消息传到不列颠海对面的居民耳中时,只有微弱的低语”。
 不过,这低语肯定比他想象中的要响亮。无论这支英国舰队是出于对“圣战”的热忱,还是仅为躲避征服者威廉而出逃的,他们是在英格兰集结,在自己领袖的率领下远航,并攻占了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Seleucia)。他们在此地坚守,直到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十字军主力部队从陆路赶来。攻克安条克后,英国舰队与热那亚人合作,打退了撒拉逊舰队的进攻,保证了连通塞浦路斯的供给线。当十字军战士准备向耶路撒冷进发的时候,英国船队只剩下9到10艘船。他们把剩下的船烧掉,并加入了陆军,此后就消失在历史中了。
[5]
虽然被历史所遗忘,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先例,才使理查一世在一百年之后选择海路,而不是像之前的十字军领袖那样走灾难性的陆路。如果真的如此,这些默默无闻的无名战士便对英格兰发展海上力量并最终成就帝国做出了贡献。
不过,这低语肯定比他想象中的要响亮。无论这支英国舰队是出于对“圣战”的热忱,还是仅为躲避征服者威廉而出逃的,他们是在英格兰集结,在自己领袖的率领下远航,并攻占了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Seleucia)。他们在此地坚守,直到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十字军主力部队从陆路赶来。攻克安条克后,英国舰队与热那亚人合作,打退了撒拉逊舰队的进攻,保证了连通塞浦路斯的供给线。当十字军战士准备向耶路撒冷进发的时候,英国船队只剩下9到10艘船。他们把剩下的船烧掉,并加入了陆军,此后就消失在历史中了。
[5]
虽然被历史所遗忘,但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先例,才使理查一世在一百年之后选择海路,而不是像之前的十字军领袖那样走灾难性的陆路。如果真的如此,这些默默无闻的无名战士便对英格兰发展海上力量并最终成就帝国做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罗伯特·柯索斯随同陆军前进。虽然他按出身和领地都是诺曼人,但他也是新兴王室的成员,可以被称为第一代英国人。事实上,当他死去的时候,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称他是“罗伯特,英国人”。追随他东征的主要是诺曼人、布列塔尼人和安茹人。那些跟随他的无名“英格兰人”,可能都是普通士兵,因为在他的360个有名有姓的骑士中,只有几个是战败的撒克逊贵族,以及对国王不满的盎格鲁—诺曼人(Anglo-Normans)。

虽说英国人没有跟随罗伯特的十字军东征,却被迫出了钱。为了装备部队,罗伯特把诺曼底公国领地以五年期限抵押给了他那位令人反感的弟弟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换来一万马克。鲁弗斯为收回这笔钱,向英格兰的所有居民课以重税,使得“整个国家都在呻吟”。
不过,这个交易并不坏。在巴勒斯坦,罗伯特一改在国内受制于父亲和兄弟的卑微处境,抓住机会,在濒临失败的不利战局下成功夺取了安条克,并亲手杀死了土耳其指挥官“红狮子”克孜勒阿尔斯兰(Kizil-Arslan)。罗伯特又矮又胖,脸上堆着笑容,看起来并不像武士,但根据当时的记录,他曾一剑将一个土耳其人从头至胸劈成两半。他的勇猛和慷慨有目共睹。饥荒和贫困之时,他会把食物、武器和马匹与其他十字军战士分享。相对当时的艰难环境而言,他可能有些过度仁慈,以致不能有效管理自己的领地。“如果一个痛哭流涕的罪犯等待他给予判决,他也会跟着哭起来,并释放那罪犯。” [6] 罗伯特只在巴勒斯坦经历了人生的短暂辉煌。他回国后,再次成为他那苛刻家族另一位成员的牺牲品。
耶路撒冷在1099年被十字军攻占。由于罗伯特是唯一的王子,大家最初推举他为国王。但他却拒绝了,因为他还想继承英格兰的王位。他于1100年离开巴勒斯坦回国。当他还在路上的时候,不明身份者在新福里斯特(New Forest)用箭射死了鲁弗斯,为英格兰除掉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国君。可没等罗伯特回国,亨利一世就稳稳地坐上了鲁弗斯的王位。亨利一世迅速挫败了哥哥对王位的主张,把这位归国的十字军骑士终身囚禁在监狱里。据记载,亨利一世甚至还给了他一件国王遗弃的衣服,聊慰他对王位的渴望。
据记载还有一群英国人也参加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情形比较模糊。曾经为这个时期写过极有价值的编年史的奥德里克斯·维塔利斯(Ordericus Vitalis)记载,撒克逊王室最后一位传人埃德加·阿瑟林(Edgar Atheling)带领“近两万名来自英格兰和其他岛屿的朝圣者”,来到拜占庭统治之下的叙利亚劳迪西亚(Laodicea),并说服他们拥戴他的朋友罗伯特公爵为指挥官。 [7] 这些朝圣者是谁?他们对拉丁王国的发展有何影响?他们的结局如何?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
可怜的罗伯特,总是离王位咫尺之遥,但他在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所作的表现十字军东征的话剧《伦敦四学徒》( Four Prentices of London )中出现,总算在死后获得了短暂的荣耀。这部狂暴的传奇剧于1600年左右在伦敦的红牛剧院上演过几次,受到伊丽莎白时代观众的喜爱。剧中出场的有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主要人物。此外还有众多虚构角色——骑士、贵妇、匪徒、巨龙、隐士及学徒。他们都打扮成其他人的模样,出现在一系列虚构的故事中。在圣城前,剧情达到高潮,那位“英国人罗伯特”以一名十字军骑士的口吻说出了一段明显与时代不符的话,就好像是他拿着一杆枪站在戏台上一样。
看那耶路撒冷的高墙,
那曾经被提图斯和韦斯巴芗攻破的高墙。
在这些尖塔之下是古老的犹太人,
看到全世界的人都在平原上聚集。
哦,王子们,睁开你们干枯的眼睛,
看到那被摧毁的圣殿吗?
远处曾挺立着耶和华的房子……
那里有约柜、供饼和亚伦之杖,
至圣之所和基路伯。
现在那圣所,那上帝曾经现身的地方,
却被异教徒所占,
伪圣树立在每座圣殿里,
哦,谁见此景能不流泪? [8]
这段话中没有提到耶稣圣墓或圣十字架。而实际提到的神圣符号则是“耶和华的房子”,即圣殿,以及约柜,因为此时在英译《圣经》的影响下,耶路撒冷的形象来自《旧约》,而非《新约》。
 然而,应该注意,海伍德生活的年代距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比我们距海伍德的时代还要遥远。
然而,应该注意,海伍德生活的年代距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比我们距海伍德的时代还要遥远。
实际上,对那些十字军战士而言,耶和华的房子是如此陌生,以至于他们发出的竟是屠杀犹太人的呼喊声。对于后世的犹太人,他们开启了一直延续到希特勒时代的种族屠杀。按照教皇乌尔班(Urban)的说法,虽然十字军战士拿着“马加比人的利剑”,但他们还没离开欧洲就将利剑刺向了马加比人。 [9] 在东征路上的每一个犹太人社区,都被这些嗜血的基督徒武士血洗。犹太人遭到屠杀,部分原因是作为“圣战者”到圣地铲除异教徒前的预演,他们是最方便的牺牲品,更有谣言说犹太人极力鼓动土耳其人在圣地迫害基督徒。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类屠杀是劫掠的好机会,这也一直是十字军战士参加东征的强大动力。
公众对犹太人的仇恨情绪本来其实并不高涨,但被“圣战”激化了。 [10] 部分原因是中世纪的人们对教会以外的“异教徒”有一种迷信般的恐惧。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对债主的仇恨。很多中世纪犹太人成为放贷者,即靠出借钱财获利,是因为当时的行会制度排斥犹太人,而犹太律法虽禁止犹太人之间互相放贷,却允许给非犹太人放贷。 [11] 另一方面的前提是,基督教法禁止基督徒之间互相放贷,但社会对借贷又有需求。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货币经济使借贷变得更加必不可少,基督徒的顾虑减轻,并最终允许基督徒之间的放贷行为。然而,在中世纪,几乎只有犹太人从事放贷业务,这也给国王们提供了丰厚的税收来源。只有泽竭鱼殁的担忧才使国王们对犹太人的压榨有所收敛。虽然理论上犹太人有财产权,但这在实际中毫无意义,因为犹太人不能控告基督徒,所以犹太人的地位只依赖于国王的好恶。
国王越鼓励犹太人的放贷行为,人们就越痛恨犹太人。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人们认识到在十字军旗帜下动用的暴力,是轻松抹掉债务、夺取犹太人财产而不受惩罚的捷径。到1146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传教士已经开始抨击整个犹太民族。1144年牛津的犹太人被控进行了人祭,成为第一起有记录的宗教谋杀指控。 [12] 到了1190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十字军与犹太人大屠杀已经变得不可分割。理查的加冕礼刚完成,杀戮就开始了,虽然没有他的命令。 [13] 一旦开始,杀戮风潮就像汹涌的波涛一样从伦敦蔓延到所有犹太人居住的城市,最后的恐怖高潮出现在约克——在那里,只有那些先杀死妻儿后引颈自杀的犹太人才能逃脱暴民的屠杀。根据各种记录,即将出征的十字军战士和煽动暴民屠杀耶稣敌人的修道士是屠杀活动的领袖。这些人肯定给编年史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描述详细而充满恐惧。理查的大臣惩罚了一些犯罪者,虽然此后没有发生新的袭击,但这些事件加重了民众的反犹情绪。一个世纪之后的另一位十字军国王爱德华一世,终于厌倦了继续一点一滴地榨取日渐枯竭的资源,索性一次了结。他把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并将他们的全部财产充归王室。
不知采取了何种手段,中世纪的人能把古代与现代的犹太人截然分开。狮心王理查和罗伯特·布鲁斯的崇拜者都把他们与一个典型的爱国武士相比较,即犹大·马加比(Judas Maccabaeus)。实际上,“骑士”时代的尚武者推崇的是希伯来人的伟大首领和国王,而不是他们的先知。在教堂门上或挂毯的刺绣图案上常出现的“九伟人”——“三个异教徒、三个犹太人和三个基督徒”,其中的三个犹太人是约书亚(而非摩西)、大卫和犹大·马加比。 [14]
理查在勇气、力量和战略方面可以与马加比相比拟,但在动机方面不同。他是为消遣作战,不是为巴勒斯坦的自由而战。理查把剩余百分之九十的时间用于在法国跟他的父亲、法国国王或其他对手争斗。但十字军东征的伟大历史覆盖了这一切。对于理查,“公认的神话”把他塑造为亚瑟王第二,其实他完全不是。但他给英格兰提供了一段传奇,因为这段传奇发生在圣地,所以他使英格兰对圣地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以致在他的时代和此后的几百年里,许多英国人都会这样说:“当我死后打开我的胸膛,你们会发现巴勒斯坦躺在我的心里。”这是玛丽女王关于加来的那句名言的演变。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功绩乏善可陈。那是一场耻辱的失败,当时的评价是,“虽然它没能解放圣地,但不能说是不幸,因为它为天堂输送了很多烈士”。
 几乎没有英国人参与其中,因为大部分英国人深陷玛蒂尔达(Matilda)和斯蒂芬(Stephen)两派间长达17年的战争之中。当安茹的亨利在1152年继承王位时,收拾残局占用了他的所有精力。他仅满足于在各教堂中摆上为圣殿骑士团募捐的布施箱。
几乎没有英国人参与其中,因为大部分英国人深陷玛蒂尔达(Matilda)和斯蒂芬(Stephen)两派间长达17年的战争之中。当安茹的亨利在1152年继承王位时,收拾残局占用了他的所有精力。他仅满足于在各教堂中摆上为圣殿骑士团募捐的布施箱。
 此后,他设置了一项“为耶路撒冷之存亡”而征的税,第一年是每英镑收二便士,此后四年里,每英镑收一便士。
此后,他设置了一项“为耶路撒冷之存亡”而征的税,第一年是每英镑收二便士,此后四年里,每英镑收一便士。
在贝克特大主教于1170年遇刺之后,亨利被迫发誓加入十字军进行三年东征,以弥补他在这桩世纪大案中的罪责。 [15] 但为巩固他在英格兰的王权以及在法国的王朝斗争,使他不断推迟出发的日期。他虽立下东征誓言,但他是否真准备履行诺言令人怀疑,因为他的真正兴趣在国内,而不是去东方获得荣耀。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直接原因,是萨拉丁在1187年从法兰克人手里夺下了耶路撒冷。当圣城再次落入异教徒手里的消息传来时,据说整个欧洲都战栗了。此后不久,教皇乌尔班二世过世,被普遍认为死于悲愤。
 这件事甚至刺痛了亨利,他这次真的开始做出征准备,参加新教皇格列高利八世(Gregory VIII)鼓动的新一次东征。当时各方对东征的响应是如此强烈,许多国王、贵族、骑士都发誓出征,德文索夫(de Vinsauf)甚至因此说道,“问题已经不是谁立下了东征誓言,而是谁还没有”。他还记录,将女人用的纺纱杆和羊毛送给犹豫不决的武士成为当时的风尚。[据传德文索夫曾被认为是拉丁文叙事长诗《英王理查行记》(
Itinerarium Regis Ricardi
)的作者,这部著作以目击者视角记述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与巴哈丁(Bohadin)的作品齐名,是关于第三次东征最有价值、可读性最高的记录。但现代学者发现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叫德文索夫的人,即使有也不是此书的作者。]
这件事甚至刺痛了亨利,他这次真的开始做出征准备,参加新教皇格列高利八世(Gregory VIII)鼓动的新一次东征。当时各方对东征的响应是如此强烈,许多国王、贵族、骑士都发誓出征,德文索夫(de Vinsauf)甚至因此说道,“问题已经不是谁立下了东征誓言,而是谁还没有”。他还记录,将女人用的纺纱杆和羊毛送给犹豫不决的武士成为当时的风尚。[据传德文索夫曾被认为是拉丁文叙事长诗《英王理查行记》(
Itinerarium Regis Ricardi
)的作者,这部著作以目击者视角记述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与巴哈丁(Bohadin)的作品齐名,是关于第三次东征最有价值、可读性最高的记录。但现代学者发现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叫德文索夫的人,即使有也不是此书的作者。]
遥远的耶路撒冷对英格兰产生的一个影响是,亨利二世为支付远征的费用首次开征所得税。十字军战士得以免税,但其他人都要上交所有各种租金和动产的十分之一。每人对自己的财产进行评估,但如果涉嫌低估,他所属教区的评审团将决定财产的真实价值。这个被称为萨拉丁什一税的税种虽然具有高尚的目的,但正如文多弗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所言,被视为“在慈善名义掩盖下的贪婪而无德的暴力勒索,必然引发神职人员和人民的警觉”。
 凡是税,都不受欢迎。
凡是税,都不受欢迎。
虽然事出紧迫,但这次十字军东征因无休止的家族争斗被耽搁下来。亨利与他那些反叛的儿子们以及法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永远处于尔虞我诈的争斗之中。在其中一次争斗中,56岁的亨利身心交瘁,被亲生儿子挑落马下,死于1189年7月。暴躁的理查成为国王。他在两年前耶路撒冷陷落的消息传来之后的第二天即已立下东征誓言,现在他不能再等待了。与父亲不同,他没有做国王的责任意识,不在乎英格兰王国,只在意这个王国给他的机会,使他可以满足自己对战争、冒险和荣耀的欲望。十字军东征给了他作为骑士的最高挑战——一个显赫的劲敌,以及灵魂的救赎,可以满足他的所有欲望。他赶紧回到英格兰称王,安排好他出征后的摄政问题,但最主要的是填满国库。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放肆,通过课重税、勒索以及各种已知的和独创的方法大肆敛财。他遣散了父亲手下的大臣,公开卖官鬻爵。他卖掉每一个需要批准的职爵、每一座有争议的城堡、每一处有足够多钱的买主的国王封地。“他什么都卖——权力、爵位、治安官职位、城堡、镇子、庄园等等。” [16] 对那些不想花钱获得好处或财产的人,他或是处以各种名目的罚款,或是罗织罪名投入监狱,逼迫他们花钱赎回自己的自由,或是要求他们付钱换得自己财产的安全或誓言的解除。就在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和他的得力助手执事长威尔士的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Giraldus Cambrensis)走遍英格兰,忙着鼓动东征并为十字军征募战士的时候,理查的大臣为敛集罚款、贿赂和“礼品”更忙得不亦乐乎。当有人质疑理查的敛财方法时,他大笑着咆哮道:“如果能找到买家,我连伦敦都卖。” [17]
不出四个月,他就带着所能搜刮到的每一便士出发了。随他去的还有最能干、忠诚的大臣,包括鲍德温大主教、他父亲的首相雷纳夫·格兰维尔(Ranulf Glanville)——二人后来都死在了巴勒斯坦。此外,他还带上了自己的新首相休伯特·沃尔特(Hubert Walter)。如果换作比他精明许多的父亲,肯定会把值得信赖的人留在国内,以维持稳定,但理查从没想到过这一点。这是个致命的错误。他在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年,不时传来约翰要篡位的消息,使他在去留问题上犹豫不决,削弱了他的意志,否则他真有可能拿下耶路撒冷。
理论上讲,参战的骑士要自备武器以装备自己、扈从和士兵。虽然理查不会治理国家,但并非一个不负责任的骑士。他疯狂地敛财,唯一目的就是要保证他能供养一支高效军队坚持一年以上的时间,从而实现他战胜萨拉丁的梦想。此外,他可能还想在排场和气势上压过傲慢的腓力和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公爵。然而,最关键的是他决定不再重蹈前几次沿陆路远征的灾难结局。十字军沿途获取补给的做法惹怒了当地民众,并引发了冲突,还没有抵达巴勒斯坦,就有数千十字军争斗致死或饿死。理查不想采用土耳其人的焦土政策,但海上运兵和补给需要大笔的资金。从当时的国库卷档中可以看出组织舰队的详细计划。例如,伦敦治安官康希尔的亨利(Henry of Cornhill)记录了国王的总管交给的5000英镑是如何花的 [18] :

这当然仅是一小部分。理查还要求“英格兰每座城市贡献两匹骑用马和两匹货运马,每个国王的庄园贡献一匹骑用马和一匹货运马”。 [19]
理查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法国和西西里招兵买船,并与法王腓力达成了一项和解协议。但法王仍然很恼火,因为无论他俩去哪里,所有人的目光都停留在理查身上。根据叙事长诗《英王理查行记》的描绘,他身材高大,穿着绣有银色弯月的玫红色法衣,赤褐色的头发上戴着一顶绣有各色鸟兽的绯红色帽子,腰间一把金柄利剑栖身于嵌金剑鞘之中。谁能不崇拜这样的人物?确实,他看上去就跟人们理想中的骑士一样,跨着一匹完美无缺的西班牙战马,那战马套着金色缰绳,身披金色和猩红的亮片,马鞍上装饰有两只奔跑追逐的金狮子。
1191年春,军队和船只集结完毕。理查又额外征用了一些大型帆船,备足了可供两年所用的小麦、大麦、红酒,带上他妹妹乔安娜女王(Queen Joanna)的金盘,预备在4月动身。法王腓力已于3月先期出发。理查的舰队非常令人震撼,共有219艘船,是当时最庞大的海军力量。 [20] 船上飘着旗帜,吹着号角,横渡地中海,向巴勒斯坦驶去。舰队中有39艘大型战船,船体瘦长,有两层划桨手;24艘大船,有三层划桨手,每艘能载40名骑士、40名步兵和40匹马,以及他们的武器和人畜一年的粮草;156艘小船,能载大船一半的定员。舰队采用楔式队形,分成八队,首排有3艘船,最后一排有60艘。这种安排能使人的喊声在船之间传递,各队之间用号角传递信号。领航的是乔安娜和贝伦加丽娅(Berengaria),国王的母亲让人把贝伦加丽娅带到墨西拿,让她与理查成婚。但他们直到经停塞浦路斯时才得以完婚。国王理查殿后。
有多少人跟着理查投身于那场伟大而悲剧性的冒险呢?中世纪编年史家很少记录具体数字,而爱用“大量”、“无数”这样的词汇,或反问“谁能去数呢?”,或是泛泛地说,凡是有影响力和知名的人没有不在那里的。按照《英王理查行记》的估计,理查在攻占墨西拿时的兵力为一万人,这个数字符合200余艘船的定员。此外,鲍德温大主教随一支由200名骑士和300名步兵组成的小舰队独立航行;还有不知数目的英国水手加入北欧人和佛兰芒人的舰队,共1.2万人,早在1189年理查继位前就去支援拉丁王国了。
当时英格兰的人口数量没有记载。但人口学专家估计英格兰人口在理查东征的那个十年里大约是200万人。
[21]
如果我们假定有一万至两万名英国人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那么大约最多每100人里有一个人,或最少每200人里有一个人去了巴勒斯坦。根据文献记载,英格兰每个郡都给理查提供了部队,许多士兵来自威尔士。
 相当一部分战士没有回来。《英王理查行记》提及,在头两个冬季之后,各支军队在巴勒斯坦的伤亡情况包括:6位大主教、12位主教、40位伯爵、500位贵族、“大量”教士和“无数”其他人员。许多人在到达阿卡(Acre)之前病死在肮脏拥挤、瘟疫横行的兵营里。在理查攻下圣城后,又与萨拉丁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又有许多人被俘虏或战死。想获得各支军队的总人数是不可能的,因为自从耶路撒冷陷落后,就有十字军源源不断地从欧洲不同地方来到巴勒斯坦。有人留下,有人死去,有人返回。从安条克、提尔等当地封邑中聚集起的基督徒人数,则随他们领袖的政治计算而变化。
相当一部分战士没有回来。《英王理查行记》提及,在头两个冬季之后,各支军队在巴勒斯坦的伤亡情况包括:6位大主教、12位主教、40位伯爵、500位贵族、“大量”教士和“无数”其他人员。许多人在到达阿卡(Acre)之前病死在肮脏拥挤、瘟疫横行的兵营里。在理查攻下圣城后,又与萨拉丁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又有许多人被俘虏或战死。想获得各支军队的总人数是不可能的,因为自从耶路撒冷陷落后,就有十字军源源不断地从欧洲不同地方来到巴勒斯坦。有人留下,有人死去,有人返回。从安条克、提尔等当地封邑中聚集起的基督徒人数,则随他们领袖的政治计算而变化。
根据萨拉丁的编年史家巴哈丁的估计,在阿卡城外的基督徒军队有5000名骑士和10万名步兵。 [22] 这个估计可能是令人信服的。骑士与步兵1:20的比例是合理的,不过由于步兵的伤亡较大,最后这个比例降低到1:10或1:5。到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结束的时候,军队人数肯定损失了一半以上。在理查离开前的最后一次战役中,他命令所有人都跟他上阵,根据《英王理查行记》的记载,只有500名骑士和2000名携盾士兵,这些士兵的领主已经战死了。当他最后坐船回国的时候,只用了一艘可搭乘不到50人的帆船。不过,确实有人先期离开。
考虑到缺少可靠数据的实际情况,想推测出有多少比例的英格兰人去巴勒斯坦服役是愚蠢的。我们只能说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参与了东征,去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回国。
当理查在6月份抵达的时候,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在阿卡的城墙之外陷入了僵局,对这座城市无望的围攻已经持续了一年。如果说被围者陷入了困境,那么围城者也是一样。他们失去与其余战场的联系,在拥挤、肮脏、疾病滋生的军营里,靠吃饿死的马匹度日,或用大把的金子去买流浪猫的尸体。城攻不下,又不能放弃,十字军与大批的追随者一起在放荡中逐渐麻木,陷入腐臭和停滞的痛苦之中,我们如今似乎仍能从史书中嗅到这种气息。
即使法王腓力在1191年3月赶到,并带来了新的补给,仍然没能使军营振奋起来,有限的士气也迅速消退了。直到理查到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他在东征路上征服塞浦路斯,并聚敛了一些物资。他的到来终于激励起整个兵营,展开了大动作。理查于6月抵达阿卡,不出四个星期,这座城市就投降了。在过去近三年的围城中,这座城市成功抵御了九次大战役和上百次的小战役。这并不是说胜利应归功于理查一人,但没有他的旺盛斗志激励十字军战士拼尽全力,就难以攻破城墙。理查虽然刚到就患了疟疾,浑身发抖,卧床不起,但他仍然在病榻上指挥战斗。当十字军在土耳其人暴雨般的枪箭下一次又一次后退时,理查让人把他抬到前线,用雷鸣般的吼声激励士兵发动最后一次进攻,终于取得了成功。
理查与萨拉丁商定休战并交换战俘,规定要在三个月内的指定时点完成。当萨拉丁不断拖延兑现承诺时,理查屠杀了2000多名穆斯林战俘,而且没有任何内疚。
[23]
这个残忍的举动甚至使他自己的士兵感到惊骇,也使后世史家惊恐和义愤。自从那些伪斯特雷奇
 学派的学者们发现理查不完全是传奇故事中那个勇敢的骑士后,他们就挥舞利爪,把理查剩余的名誉撕成了碎片。《英王理查行记》的作者崇拜理查,说理查具有赫克托耳的勇敢、阿喀琉斯的宽宏、提图斯的慷慨、涅斯托耳的善辩和尤利西斯的谨慎;说他足以与亚历山大相媲美,也丝毫不让罗兰。但后世史学家倾向于把理查描绘成一个冷酷薄情的恶人。他可能不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人,金雀花王朝
学派的学者们发现理查不完全是传奇故事中那个勇敢的骑士后,他们就挥舞利爪,把理查剩余的名誉撕成了碎片。《英王理查行记》的作者崇拜理查,说理查具有赫克托耳的勇敢、阿喀琉斯的宽宏、提图斯的慷慨、涅斯托耳的善辩和尤利西斯的谨慎;说他足以与亚历山大相媲美,也丝毫不让罗兰。但后世史学家倾向于把理查描绘成一个冷酷薄情的恶人。他可能不是一个可亲、可爱的人,金雀花王朝
 本就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但他肯定是个伟大的战士和指挥官。他拥有作为指挥官最重要的品质——必胜的决心,而其他品质——仁慈、节制、分寸——都被牺牲了。他令批评者惊骇的贪婪并不是简单的贪财,而是军需官为军队搜寻供给的贪婪。他屠杀穆斯林战俘,并非是简单的残酷,而是提醒萨拉丁遵守承诺,而这位伟大的对手也理解并照做了。实际上,这位英王是萨拉丁唯一尊敬的法兰克人。萨拉丁曾经说:“如果我注定要丧失圣地,那我宁愿让理查而不是其他人拿去。”
本就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但他肯定是个伟大的战士和指挥官。他拥有作为指挥官最重要的品质——必胜的决心,而其他品质——仁慈、节制、分寸——都被牺牲了。他令批评者惊骇的贪婪并不是简单的贪财,而是军需官为军队搜寻供给的贪婪。他屠杀穆斯林战俘,并非是简单的残酷,而是提醒萨拉丁遵守承诺,而这位伟大的对手也理解并照做了。实际上,这位英王是萨拉丁唯一尊敬的法兰克人。萨拉丁曾经说:“如果我注定要丧失圣地,那我宁愿让理查而不是其他人拿去。”

然而,理查没能拿下耶路撒冷。为什么?蓄水池淤塞,天气炎热,疾疫流行,部队供给困难,为适应巴勒斯坦荒凉的山地和沙漠改变战术的困难——这些问题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都曾出现过,但没有遇到过的,是敌人有了一个伟大的指挥官。萨拉丁在本土作战,他能从巴勒斯坦各地召集兵力,他的背后没有敌人削弱他的实力。但真正打败理查的是他的盟友之间的矛盾。提尔侯爵康拉德(Conrad)投奔了敌人。法国国王也退出了,可能因为他无法忍受被理查的光芒覆盖,也可能是因为他想抢先回国夺取理查在法国的领土。但法王的背信弃义并不是完全的损失,正如萨拉丁的兄弟所说,“理查被法王拖累了,就如同尾巴上系着榔头的猫”。 [24]
从1191年7月阿卡陷落到理查于1192年10月离开的15个月里,理查在敌人的不断袭扰下沿海岸向南推进,直至到达雅法——挺进耶路撒冷的基地,并与敌人进行了谈判,向阿什凯隆(Ascalon)和达鲁姆(Darum)发动了辅攻,还对坐落在山上的圣城发动了两次无效的进攻。
理查的部队从阿卡出发,沿着罗马人修建的古老道路向南挺进,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从供应舰队获得补给。为此理查极为仔细地做了计划。这支军队分成圣殿骑士、布列塔尼和安茹、普瓦图、诺曼、英格兰等五个主要军团,以及医院骑士团(Hospitaller)
 。这五个军团又分为三个纵队:最靠内陆的是步兵,抵御埋伏在山上的敌人的频繁伏击;中间是骑兵;靠海的是运输辎重的队伍。英王的旗帜树立在有篷的四驾马车上,但英王一般穿梭在队伍前后检查队列,保持秩序。由于天气炎热,他规定只在清晨行军,每天只能走8到10英里,每隔一天休息24小时。盛夏的高温、军队情况的恶化,以及阿卡之战驮兽的大量损失,使放慢行军速度成为必要,一半的步兵必须背着行李和帐篷,与战斗部队轮休。为抵御弓箭,十字军战士在铠甲外还要穿上厚厚的皮质长袍。巴哈丁记录了土耳其人惊异地看到法兰克人背上扎入5到10支箭,仍然毫发无损地行军。在太阳的暴晒下,许多人倒地而死,还有人晕倒,必须用船运走。每天晚上停止行军后,一名传令兵站在队伍中央大喊“圣墓保佑!”,队伍跟着举手高呼三声,泪流满面。根据《英王理查行记》的描绘,这个仪式使部队得到休整和振奋。
。这五个军团又分为三个纵队:最靠内陆的是步兵,抵御埋伏在山上的敌人的频繁伏击;中间是骑兵;靠海的是运输辎重的队伍。英王的旗帜树立在有篷的四驾马车上,但英王一般穿梭在队伍前后检查队列,保持秩序。由于天气炎热,他规定只在清晨行军,每天只能走8到10英里,每隔一天休息24小时。盛夏的高温、军队情况的恶化,以及阿卡之战驮兽的大量损失,使放慢行军速度成为必要,一半的步兵必须背着行李和帐篷,与战斗部队轮休。为抵御弓箭,十字军战士在铠甲外还要穿上厚厚的皮质长袍。巴哈丁记录了土耳其人惊异地看到法兰克人背上扎入5到10支箭,仍然毫发无损地行军。在太阳的暴晒下,许多人倒地而死,还有人晕倒,必须用船运走。每天晚上停止行军后,一名传令兵站在队伍中央大喊“圣墓保佑!”,队伍跟着举手高呼三声,泪流满面。根据《英王理查行记》的描绘,这个仪式使部队得到休整和振奋。
在行军的途中,他们知道每行进一天就离激战更近一天,萨拉丁肯定会发动进攻,阻止他们到达雅法。土耳其前锋骑兵部队不断袭扰缓慢移动的方阵,试图引诱他们离开队伍交战。萨拉丁的战略就是割裂并分散方阵,使骑兵易于各个击破。理查坚持保持队形,以保护运输马车,并迫使土耳其人近身作战。越往前走,神经绷得越紧,每个人都能从脊骨中感知到在山后集结的敌人。理查下了死命令,时机不成熟时不许任何人出列与敌人交战。 [25]
在距离雅法11英里处一个叫艾尔苏夫的地方,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医院骑士团忍耐不住,向土耳其人发动了进攻。“英王理查,”《英王理查行记》写道,“看到自己的部队行动起来,立即跳上战马,率领医院骑士团突破了土耳其步兵部队。土耳其人大为惊骇,四处躲闪。”但土耳其人重新集结,并发动了反击。“漫山遍野都是严整的土耳其部队,无数战旗飘扬,穿着盔甲的人超过两万人……他们冲下来的速度,比鹰还快,马蹄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他们喊声震天,号角齐鸣。”英王身体左侧被矛刺伤了,但步兵稳住了阵脚,抵御住了敌人的冲锋。士兵们单膝跪地,将长矛前伸,他们身后的弩车不断将长矛射向敌阵。虽然战斗进行了一整天,但土耳其人没有能突破十字军的战线,最后踏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土地撤退了。
此时,双方都在实战中了解了对方的实力。此役之后,萨拉丁意识到他无法阻止十字军前进的步伐,但可以先撤退,等待敌人的实力消耗殆尽。他把守军从雅法以南至阿什凯隆的堡垒中全部撤出,以免重蹈在阿卡的覆辙,只留下通往埃及最后的堡垒达鲁姆的守军,但被理查四天就攻下了。
如果此时发动对耶路撒冷的全面进攻,有可能成功,但十字军开始分崩离析了。首先发难的是法国人,他们坚持要留在雅法加固城墙,并在野地的艰苦行军之后借机享受一下城里的奢侈生活。但在众人的坚持下,联军终于还是在新年那天对耶路撒冷发动了进攻,但勃艮第公爵在已经能望见耶路撒冷的地方退出了战斗,并最终完全撤出战斗。其他部队要么撤退到了阿卡,要么跟随康拉德叛逃到提尔。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甚至也提出不进攻耶路撒冷的建议,以免破城后成为孤军与附近的土耳其人作战。自从腓力退出后,理查也担心他的对手和他的弟弟约翰阴谋篡权,急于赶回国内,唯恐王国易主无国可回。
除了这个担忧,他还逐渐意识到分裂的军队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这使他有了协议停战的意愿。谈判的过程很漫长,从那年的冬天一直拖到1192年春,双方就耶路撒冷、几个海边城市和十字军城堡的归属等问题反复拉锯。理查甚至荒谬地提出一个令人发笑的建议——让自己的妹妹乔安娜与萨拉丁的兄弟联姻,共同统治耶路撒冷。 [26] 礼貌而老练的萨拉丁通过娴熟的外交辞令和持续不断的礼物使谈判持续推进。他送给理查一匹西班牙良马、一顶绯红色帐篷、新鲜水果、从高山上运来的冰雪、七头装饰华丽的骆驼和一名医术高超的医师。 [27]
与此同时,从英格兰来的信使向理查报告了约翰在国内的行径,恳求理查返回。他决定在1192年6月向耶路撒冷发动最后的攻势,但各支部队无法达成一致,理查最后气愤地放弃了。当他放弃了那个消耗了如此多艰辛、鲜血和财富的伟大目标之后,他像骑士一样爬上一座山的顶峰,从这里能看到耶路撒冷的尖塔。但理查没有看耶路撒冷,而是用长袍掩面,并说道:“上帝保佑,我祈求不要让我看到那座我无法从你的敌人手里夺下的圣城。”

显然没有必要留在巴勒斯坦了。就在理查准备从阿卡乘船离开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撒拉逊人包围了雅法,一小股基督徒部队正在坚守,随时可能全军覆没。这似乎是命运给遭受奇耻大辱的英雄所做的补偿。在雅法战役中,理查表现得如此英勇,使他赢得的荣耀得到了全天下人的传颂。他的英勇改变了人们对他盘剥勒索的印象。三年后,当埃莉诺(Eleanor)为赎回理查穷尽所能四处筹集赎金时,英格兰人表现出了对这位狮心王的爱戴,纷纷倾囊相助。
《英王理查行记》记述的雅法战役,很可能正是激战之夜写成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英王壮举的骄傲和狂喜。作者说,理查打断了所有要求谨慎从事的建议,大声喊道,“上帝见证,我将与他们同在,并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此时,他已经登船,于是命令掉转船头向南航行,冲上雅法的海滩。他率领一小队人马涉水上岸,兵力仅有80名骑士和300名弓弩手。
刚上岸的时候,他手拿一把劲弩,但很快就换成了他的那把“凶猛的利剑”。他和他的部队向海滩上密集的土耳其军队发动猛攻,很快把敌人击退了。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镇子被攻下,基督徒守军获救了。然而,土耳其人因被如此少的敌人打败而深感羞耻,派来援兵,趁理查在帐篷中熟睡的时候发动奇袭。“拿起武器!拿起武器!”这最后时刻的呼喊惊醒了英王。
“万能的上帝啊!谁在这种情况下不被惊醒?啊,谁能全面地描绘异教徒的可怕进攻呢?土耳其人喊声震天地发动了猛攻,疯狂地投枪、射箭。英王在队伍中穿梭,鼓励士卒稳住阵脚,不要退缩。土耳其人像旋风一样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佯装进攻,诱使我们的战士退缩。但当他们靠近时又突然掉转马头。当英王和骑士看到这些后,策马冲入敌阵,所到之处敌人四处遁逃,他们用长矛刺杀了大量敌人……这可真是一场可怕的战斗!大批的土耳其人……涌向竖立着英王狮旗的马车,因为他们宁愿杀死英王一个人,也不愿去杀一千个士兵……但他的勇气似乎找到了展示自己的机会。他手中的利剑像闪电一样砍倒敌人和马匹,将他们劈成两半。”
战斗进行了一整天,《英王理查行记》描述了英王在战场上一手舞剑,一手挥矛,像收割庄稼一样一路砍杀过去。他使土耳其人如此恐惧,所到之处敌人夺路而逃。他看见莱斯特(Leicester)伯爵从马背上掉了下来,但仍然勇敢地与敌人搏斗。英王赶紧拍马跑过去,扶伯爵上马。敌人抓住了拉尔夫·德毛本(Ralph de Maubon),英王冲上去把他救下并送回军中。在激烈的战斗中,萨拉丁送给英王两匹战马,向他的勇气致敬。英王说,即使是比萨拉丁更加恶劣的敌人送来的战马,他都不会拒绝,因为他急需战马。最后,“勇猛而非凡的国王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朋友们中间……但他身上插满了标枪,好像被猎人追捕的鹿一样。他的马匹护具上覆盖着密布的箭”。当萨拉丁问垂头丧气的武士为什么没有抓住英王,他们回答:“说实话,自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过这样的骑士……与他交战必死无疑,他的英勇超越人之本性。”
双方签订了三年休战协定,耶路撒冷和山地地区归阿拉伯人所有,但圣墓堂和基督徒自由朝拜的权利得到恢复。此外,从提尔至雅法的沿海平原和港口也归属了基督徒。有三群十字军战士去了圣城,但理查没有去。他如果不是作为征服者,就坚决不去。狮心王乘船离开了,但他的传奇壮举在阿拉伯人中间流传。如果马在树丛里受惊,阿拉伯人会以为那是狮心王的魂灵在作怪;要吓唬哭闹的孩子使他安静时,他们会说:“安静点,英格兰人来了!” [28]
十字军东征对英格兰的影响之一是土地所有权发生的巨变,因为许多骑士用土地做抵押借款购置装备。英王不是唯一一个为筹措资金无所不用其极的人。有个叫约翰·德卡莫伊斯(John de Camoys)的人,他把妻子的财产连同妻子本人都卖掉了。安德鲁·阿斯特利(Andrew Astley)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卖给了沃里克郡(Warwickshire)的库姆修道院(abbey of Combe),换回320英镑。
 其他一些人则把土地抵押给富裕的修道院三年、四年或七年,即使活着回来,也都穷得无力赎回财产,只能在修道院里贫困地了此余生。
其他一些人则把土地抵押给富裕的修道院三年、四年或七年,即使活着回来,也都穷得无力赎回财产,只能在修道院里贫困地了此余生。
16世纪利兰和卡姆登通过对修道院和教区档案的研究,发现了许多有关十字军东征的史实。有个叫奥斯本·吉福德(Osborne Gifford)的人,因为绑架两名修女而被逐出了教会(一个明显不够用),获得救赎的条件是他必须去圣地参加三年的十字军东征。在此期间,他不能穿衬衣或骑士服装,且一生都不能进修女院。
 罗杰·德莫布雷(Roger de Mowbray)是个奇迹,他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两次前往巴勒斯坦,被撒拉逊人俘虏后又活着回来了。任何有这样好运气的人必定成为传奇故事的主角。据说罗杰干预了一场龙与狮子的殊死决斗,他杀死了龙,因而赢得了狮子的感激之情,那狮子跟着他回到了英格兰。他的儿子奈杰尔(Nigel)跟随理查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另一个被撒拉逊人俘虏的是休·德哈顿(Hugh de Hatton),他在做了七年俘虏后衣衫褴褛地逃回了家。一个放羊人没有认出他,告诉他德哈顿已经死了。他回到了自己的城堡,但我们不知道他受到了怎样的接待,故事讲到他走到门口后就结束了。同尤利西斯从特洛伊回来后被迫隐姓埋名的故事类似,这是一长串武士离家多年后归来的故事之一。
罗杰·德莫布雷(Roger de Mowbray)是个奇迹,他在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两次前往巴勒斯坦,被撒拉逊人俘虏后又活着回来了。任何有这样好运气的人必定成为传奇故事的主角。据说罗杰干预了一场龙与狮子的殊死决斗,他杀死了龙,因而赢得了狮子的感激之情,那狮子跟着他回到了英格兰。他的儿子奈杰尔(Nigel)跟随理查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另一个被撒拉逊人俘虏的是休·德哈顿(Hugh de Hatton),他在做了七年俘虏后衣衫褴褛地逃回了家。一个放羊人没有认出他,告诉他德哈顿已经死了。他回到了自己的城堡,但我们不知道他受到了怎样的接待,故事讲到他走到门口后就结束了。同尤利西斯从特洛伊回来后被迫隐姓埋名的故事类似,这是一长串武士离家多年后归来的故事之一。
许多人因为被流放而去参加圣战。强悍的富尔克·菲茨瓦林(Fulk Fitzwarin)在下棋时激怒了约翰亲王,亲王用棋盘打他的头,富尔克回敬一拳,差点把亲王打死。他随即被朝廷流放,向巴勒斯坦进发,但暴风雨把他吹到了巴巴里(Barbary)海滩。在那里,他被撒拉逊人俘虏。他被囚禁期间似乎很愉快,据说他在苏丹的领土与一个“贵妇”相爱了。最后,他到达东方,加入了理查的军队,参加了阿卡围城战。与理查一同征战的还有一位威廉·德普拉特勒(William de Pratelles) [29] ,因为在狩猎途中被敌人偷袭时救了理查而出名。威廉大叫“我是国王!”而被俘虏,但幸运的是理查在巴勒斯坦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就是用10名土耳其人把这位勇敢的朋友换了回来。
在理查死后继位的无道的约翰也立下过东征的誓言。 [30] 在已经褪色的《英国大宪章》中,我们仍能读到他是如何承诺在“动身去东征前”调整财税问题。但男爵们不相信他的诚意,迫使他立即履行承诺,以免出现“如果因故耽搁而未能去圣地”的情况。
约翰当然没去东征,但他的小儿子康沃尔伯爵理查 [31] 东征的决心像同名的理查一世一样坚定。但理查伯爵那位昏庸的哥哥亨利三世任用的法国佞臣使朝廷一片混乱。作为朝廷中唯一的能臣和王位的法定继承人,理查伯爵无法离开。当国王得子后,他立即动身奔赴巴勒斯坦。所有人都试图劝阻他,包括教皇也劝他购买豁免权以解除东征的誓言。罗马教会的关怀无疑是因理查拥有康沃尔的锡矿、铅矿和大片林地,被誉为欧洲最富有的亲王。但伯爵没有解除誓言,而是通过变卖林地筹集到必要的资金。根据提尔的威廉的说法,当他上路的时候,人们都流泪了,因为他是一个全心关注公众福祉的人。但理查告诉他们,即使他没有立下誓言,他也宁愿去东征而不愿目睹即将来临的灾难。跟着他东征的有后来战死于埃及的索尔兹伯里伯爵威廉·朗索德 [32] 、7位男爵、五六十名骑士,以及众多弓弩手和长矛手。1240年10月,他们在阿卡登陆后,发现法兰克人与穆斯林已处于停战状态。此时的伊斯兰世界正深陷埃及与叙利亚王国惯常的战争中。由于停战协议没有被遵守,理查伯爵踏着伯父的脚印,向雅法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埃及苏丹被逼无奈,提出议和。伯爵是个很难对付的人,在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十字军获得了历史最好的协议条件:耶路撒冷、拿撒勒、伯利恒等大部分圣地都归属了基督徒。理查伯爵回国后被誉为圣墓堂的拯救者。
陪同理查伯爵一道去巴勒斯坦的还有西蒙·德蒙福尔,由于刚与英王的妹妹完婚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审慎起见他决定离开英格兰一阵子,于是去了巴勒斯坦。西蒙虽然在战场上被称为约书亚再生 [33] ,但带着十字军战士常有的对犹太人的敌意,不久前却把约书亚的后裔从他在莱斯特的领地上驱逐了。他尚未成为王室暴政的伟大反抗者,但可能是自诺曼征服至都铎王朝这段历史时期各种国王和贵族间血腥争斗中唯一一个为原则而战的人。虽然他在巴勒斯坦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但他强大的人格和个人能力肯定给当地的法兰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想把王国的摄政权交给他,协助未成年的国王。但西蒙更渴望回归故土,并成为英格兰之主。不过,他最后失败了,以惨死而告终。
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就要结束了。巴勒斯坦成为新兴伊斯兰势力的战场。在蒙古人的挤压下,花剌子模人和库尔德人被迫从北方迁来,紧随其后的是鞑靼可汗们自己。在康沃尔伯爵成功签署协定之后两年,耶路撒冷再次陷入敌手。提尔和阿卡成为法兰克人在巴勒斯坦最后的据点。此后几次十字军东征的目标均为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巴巴里沿海一带。西方最后的有组织行动是法国的圣路易发动的两次毫无结果的远征,他被穆斯林诗人称为“牛皮大王” [34] 。
后一次东征发生在1269—1272年间,英格兰的爱德华亲王为兑现其在打败西蒙·德蒙福尔之后立下的誓言,也加入了东征。 [35] 当他和4位伯爵、4位男爵以及约1000名士兵到达突尼斯后,愤慨地发现路易和其他亲王已经与苏丹签订了条约。爱德华带领人马立即乘船去往阿卡,在那里征集了一支由7000名当地法兰克人组成的队伍。但他唯一的战绩就是征服了拿撒勒,作为对撒拉逊人破坏当地基督圣殿的报复。被刺客用涂有毒药的匕首刺伤后,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都处于垂死之中。最后,他也签署了停战条约,停战维持了10年10个月又10天。他随后回国,并随即成为英王。他是西方最后一位在巴勒斯坦作战的亲王。
1281年,爱德华收到来自约瑟夫·德坎希(Joseph de Cancy)爵士的一封信 [36] ,他是圣约翰医院的骑士,受英王所托随时报告“圣地发生的新闻”。约瑟夫爵士在信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撒拉逊人和蒙古鞑靼人之间爆发的一场战役,并悲叹道:“在我们的记忆中,圣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悲惨过,土地因缺雨而荒芜,瘟疫和异教徒横行……我们在圣地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少的战士(法兰克人)和智慧。”他确信只要有英明的将军和足够的军需品就能把异教徒赶走。他在信的结尾请求爱德华回到圣地完成征服。
但此时已经没有机会了。爱德华正忙着征服那个距离更近的王国,再也没有回到东方。后世的教皇为了充盈梵蒂冈的钱柜,热衷于劝说十字军战士用黄金赎回东征誓言,彻底玷污了“圣战”的圣洁。当圣殿骑士团的大首领为对抗复兴的马穆鲁克王朝回到欧洲求援时,他只征到几百名意大利雇佣兵。 [37] 收复巴勒斯坦已经没有希望了。就在狮心王理查攻破阿卡之后整100年之际,20万马穆鲁克武士向十字军战士把守的最后一座城市挺进了。1291年,阿卡陷落,在爱德华把犹太人逐出英格兰的同年,最后一个基督徒被逐出了巴勒斯坦。
[注释]
[1] Richard Gough, Sepulchral Monuments of Great Britain , London, 1876.
[2] C. W. Bardsley, English Surnames, Their Source and Significations , London, 1889.
[3] See Appendix to Scott’s Talisman .
[4] David, Robert Curthose .
[5] David, Robert Curthose .
[6] DNB .
[7] DNB , David, Dansey.
[8] Ancient British Drama , 3 vols., London, 1810.
[9] William of Malmesbury, Book IV, chap. II. Also Michaud’s History , Book I, p. 49.
[10] Gibbon, VI, chap. LVIII. Also Cambridge Medieval , Vol. II, chap. VII.
[11] W. E. H. Lecky, History of Rationalism , New York, 1883, II, 266. Also H. W. C. Davis.
[12] Michaud’s History , Book VI. Also H. W. C. Davis.
[13] Contemporary authorities are Ralph of Diceto and William of Newburgh. See Stubbs, Introductions . Also Jacobs and Ramsay.
[14] Caxton’s Preface to Morte d ’ Arthur .
[15] Roger of Hoveden, Stubbs, Introductions .
[16] Ibid. , p. 350, quoting Richard of Devizes.
[17] Ibid. Also Norgate’s Richard , Book II, chap. I.
[18] Pipe Roll 2 Richard I in Archer.
[19] Ibid.
[20] Contemporary authorities are Roger of Hoveden, Ralph of Diceto, Richard of Devizes, and Pipe Roll 2 Richard I . See Stubbs’ Introductions . Also Norgate’s Richard , Book II, chap. II.
[21] 英格兰于1200年左右的人口数量,请见S. R. Maitland, Domesday Book and Beyond , Cambridge, 1897, p. 437。1377年收取人头税时的人口,请见David MacPherson, Annals of Commerce , 1805, I, 548。另见M. Postan, “Population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 2d series, II, No. 3, London, 1950. Josiah Cox Russell, British Medieval Population ,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48.
[22] Michaud’s Bibliothèque , Vol. IV, passim. Also excerpts in Archer.
[23] IRR , Bohadin, Roger of Hoveden in Archer.
[24] Richard of Devizes, quoted Historians ’ History of the World , VIII, 389, note 1.
[25] IRR in Archer.
[26] Bohadin, IRR , etc., in Archer.
[27] Book I, chap. III in Bohn’s Chronicles .
[28] 这些故事都来自Joinville,他晚于理查50年来到巴勒斯坦。Gibbon, VI, chap. LIX; Michaud’s Bibliothèque , IV, 304; Norgate’s Richard , p. 262.
[29] IRR in Archer, etc.
[30] Stubbs, Constitutional History , chap. XII, quoting Walter of Coventry.
[31] Joinville, Matthew Paris, Continuers of William of Tyre, Mills, Vol. II, chap. V. Also DNB .
[32] Ibid .
[33] In the “Song of Lewes,” in Political Songs of England from the Reign of John to that of Edward II , ed. Thomas Wright, Camden Society, London, 1839.
[34] Bohn’s Chronicles , Appendix, p. 554.
[35] Archer and Kingsford, chap. XXV; Mills, Vol. II, chap. VI; Fuller, Holy Warre , Book 4, chap. 29.
[36] A Crusader ’ s Letter from the Holy Land , PPTS, 1890.
[37] Historians ’ History of the World , published by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26 vols. and index, Vol. VIII, chap. V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