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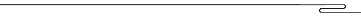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确定、并找出了见于《大乘要道密集》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国家图书馆中的那些汉译藏传密教修法和仪轨中的大部分的藏文原本,并对其中的一些文本作了对勘、整理和研究。从我们迄今已经完成的这部分研究来看,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无疑是属于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lam'bras)的文献,其中有多部是对传为印度大成道者密哩斡巴亲传“道果法”之最根本的文献《道果金刚句偈》( Lam'bras bu dang bcas pa'i rtsa ba rdo rje'i tshig rkang )或者《道果教诫和要门》( Lam'bras bu dang bcas pa'i gdams ngag dang man ngag du bcas pa )的释论,其余则多为与“道果法”修习相关的各种修法和仪轨。其中很多是萨思迦派历辈祖师,特别是三世祖葛剌思巴监藏(Grags pa rgyal mtshan,1147—1216)、四世祖萨思迦班智达(Sa skya pand··ita Kun dga' rgyal mtshan,1181—1251)和五世祖八思巴帝师所造释论、修法和仪轨的汉译文。
粗略地说,《大乘要道密集》基本上就是一部“道果法”的修法和仪轨汇集。这与萨思迦派上师曾世袭为蒙古皇帝之帝师、很多萨思迦喇嘛曾在蒙古宫廷和京城内外活动的历史事实相符。萨思迦喇嘛于元朝宫廷中的独尊地位应当与其传授密法而得到蒙古大汗推崇有关。八思巴贵为帝师,藏文史书中一再提到他曾三次为元世祖忽必烈汗和察必皇后授喜金刚灌顶。可是,在汉文《大藏经》中,我们只见到有三部归于八思巴帝师名下的作品,即《彰所知论》《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范》和《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习学略法》,它们是分说佛教宇宙观和佛门戒律的寻常经轨,与藏传密法无关。故只有当《大乘要道密集》和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国家图书馆中的这些汉译藏传佛教文献再度被公之于世,藏传密法于元朝宫廷内外传播的历史真相才真正得以揭露。这些汉译藏传佛教文献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密教文献,这显然更加符合元朝宫廷内外所传藏传佛教多为密教性质这一历史事实。而仅从当时曾有《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十卷传世这一事实,即可窥见萨思迦派之“道果法”于汉地信众中流行之盛况。
与《大乘要道密集》等在元、明、清三代帝都北京城内发现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相比,黑水城出土的同类文献不管是内容,还是种类都比前者丰富得多,但其中也包括了不少与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修习相关的经续和仪轨。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两部长篇“道果法”释论,即《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和《解释道果逐难记》,显然都是西夏时代的作品,前者为“西番中国法师禅巴集、中国大乘玄密帝师传、北山大清凉寺沙门慧忠译”,后者是“甘泉大觉圆寂寺沙门宝昌传译”,它们的西夏文译本也见于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之中。这一发现即可证明《大乘要道密集》不是一部纯粹的元代的作品,其中包括了西夏时代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同时还说明萨思迦派的教法也早已经在西夏王朝内有过传播了。此外,元朝十分流行的大黑天(摩诃葛剌)崇拜在《大乘要道密集》中我们并没有找到直接的文献依据,但这样的依据却出现在黑水城出土文书中。在俄藏黑水城文献和以后陆续在黑水城发现的汉文文书中出现了大量有关大黑天崇拜的修法、庆
 和密咒,其中有的源出于西夏,有的则是元朝的作品。这证明大黑天崇拜也是在西夏时代就开始传入并流行起来的,元代蒙古人如此迅速地接受藏传佛教信仰,特别是如此普遍地流行大黑天崇拜显然有其深厚的西夏背景。
和密咒,其中有的源出于西夏,有的则是元朝的作品。这证明大黑天崇拜也是在西夏时代就开始传入并流行起来的,元代蒙古人如此迅速地接受藏传佛教信仰,特别是如此普遍地流行大黑天崇拜显然有其深厚的西夏背景。

黑水城出土汉、西夏文译藏传密教文献反映出来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藏传佛教噶举派曾于西夏所传藏传密教中占主导地位,这与可以确定曾担任过西夏王室之帝师的西藏喇嘛多为噶举派上师这一历史事实相符合。
[5]
在黑水城出土汉文佛教文献中,我们见到了一系列与噶举派最核心的修法《捺啰六法》(
Na r
ō
chos drug
)相关的仪轨,如修习“中阴”“梦幻身”“拙火”“光明”和“迁识”的修法,它们显然直接传授自噶举派的上师,像其中的《梦幻身要门》可以肯定就是达波噶举派祖师岗波巴锁南领真(sGam po pa bSod nams rin chen,1079—1153)所造《捺啰六法》释论中的一段——“梦幻身要门”的汉译。
 而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译藏传密教文献中,我们见到了一系列有关噶举派之“大手印”修法的文献。
而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译藏传密教文献中,我们见到了一系列有关噶举派之“大手印”修法的文献。
 噶举派的“大手印法”和“捺啰六法”都是在11世纪才由噶举派祖师玛尔巴译师(Mar pa Chos kyi blo gros,1012—1097)等自印度传入吐蕃,并经岗波巴等大师于西藏传播开来的。它们如此迅速地传入西夏,足见西藏佛教与西夏佛教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曾是何等的密切。
噶举派的“大手印法”和“捺啰六法”都是在11世纪才由噶举派祖师玛尔巴译师(Mar pa Chos kyi blo gros,1012—1097)等自印度传入吐蕃,并经岗波巴等大师于西藏传播开来的。它们如此迅速地传入西夏,足见西藏佛教与西夏佛教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曾是何等的密切。
在《大乘要道密集》中,也有一系列短篇仪轨皆为修《捺啰六法》之要门,例如《十六种要仪》《拙火定》《九周拙火》《光明定》《梦幻定》《幻身定》《辨死相》《转相临终要门》《迁识配三根四中有》《迁识所合法》《赎命法》《弥陀临终要门》,等等。然而,这些修法要门似均为萨思迦派上师所传,与黑水城文献中所见到的噶举派所传的六法要门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传承。同样,在《大乘要道密集》中,也有一系列“大手印要门”,其中有些当与见于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书中的同类作品相同,或为噶举派的传轨,如其中的《新译大手印不共义配教要门》,乃“大巴弥怛铭得哩斡集、果海密严寺玄照国师沙门惠贤传、果海密严寺沙门惠幢译”,显然就是西夏时代的作品。但其中的部分或许也是萨思迦派上师所传,或乃道果法果乘的修法,此尚待进一步研究。 [6]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乘要道密集》中我们还发现了沙鲁派始祖布思端大师(Bu ston Rin chen grub,1290—1364)的《大菩提塔样尺寸法——造塔仪轨名为摄受最胜》和觉囊派始祖摄啰监灿班藏布大师(Dol po pa Shes rab rgyal mtshan dpal bzang po,1292—1361)所造《总释教门祷祝》两篇仪轨。此外,我们也还在《大乘要道密集》和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了与藏传佛教息解派(Zhi byed pa)和断派(gCod pa)的祖师、藏传佛教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帕当巴桑杰(Pha dam pa sangs rgyas,卒于1117年)相关的四个文献。
 这或说明不只是萨思迦派、噶举派这样的大教派,就连沙鲁派(Zhva lu pa)、觉囊派(Jo nang pa),乃至息解派这样的小教派亦曾对西夏、元、明时代中国的佛教有所影响。当然也有可能尽管布思端和摄啰监灿班藏布两位大师后来被分别认作沙鲁派和觉囊派之教主,但当时他们与萨思迦派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他们的教法或许是作为萨思迦派所传教法的一个部分而传入汉地的。据这两位上师传记的记载,他们都曾受到过元顺帝要求他们进京觐见的邀请,但他们为了吐蕃本土的教法事业都借故拒绝了蒙古大汗的邀请。
这或说明不只是萨思迦派、噶举派这样的大教派,就连沙鲁派(Zhva lu pa)、觉囊派(Jo nang pa),乃至息解派这样的小教派亦曾对西夏、元、明时代中国的佛教有所影响。当然也有可能尽管布思端和摄啰监灿班藏布两位大师后来被分别认作沙鲁派和觉囊派之教主,但当时他们与萨思迦派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他们的教法或许是作为萨思迦派所传教法的一个部分而传入汉地的。据这两位上师传记的记载,他们都曾受到过元顺帝要求他们进京觐见的邀请,但他们为了吐蕃本土的教法事业都借故拒绝了蒙古大汗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