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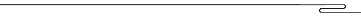
藏传佛教曾经于蒙元时代在蒙古宫廷和大元帝国疆土内得到过广泛的传播,这是早已为人所知的事实。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治蒙元史或者佛教史的学者们对这一段历史的了解,基本上只是局限于见于《庚申外史》和《元史》中的一段相当简单和尚未得到正确解读的文字,缺乏更多相关的第一手的文献资料,故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研究多半流于皮毛而少有实质性的进展,对这一事实的探讨时常停留在十分表面的历史性的描述和铺陈,而没有深入的宗教性的揭露和分析。很多相关的历史事实至今依然扑朔迷离,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澄清;很多涉及语言的和宗教的问题横亘于前,成了阻碍我们进一步揭露和探讨这段历史之真相的拦路虎。仅仅是那几个在《庚申外史》和《元史》中出现的以汉语音译流传下来的藏传佛教专有名词
 ]就曾令天下硕儒一筹莫展,至今没有人对它们作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一些元人雾里观花看不明白,却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地记录下来的蒙古宫廷所修藏传密法的故事,本来或只可当作小说家言,却给元以来历代汉族士人误解、甚至妖魔化藏传佛教留下了充满异域情调的作料和广阔的想象空间。
]就曾令天下硕儒一筹莫展,至今没有人对它们作出令人完全信服的解释。一些元人雾里观花看不明白,却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地记录下来的蒙古宫廷所修藏传密法的故事,本来或只可当作小说家言,却给元以来历代汉族士人误解、甚至妖魔化藏传佛教留下了充满异域情调的作料和广阔的想象空间。
 可以说,对蒙元时代藏传佛教于元代中国传播历史的研究尚未真正展开,要彻底弄清这段常遭人渲染、歪曲的历史史实,我们首先必须致力于发掘第一手的历史和宗教文献。
可以说,对蒙元时代藏传佛教于元代中国传播历史的研究尚未真正展开,要彻底弄清这段常遭人渲染、歪曲的历史史实,我们首先必须致力于发掘第一手的历史和宗教文献。
在笔者多年前率先注意到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那些汉译藏传佛教文献,并对这些文献对于研究西夏和蒙元时期藏传佛教于西域和汉地传播之历史的意义作出初步的评定之前,
 我们唯一知道的一种元代所传汉译藏传密法的文献是误传为元朝帝师八思巴('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1235—1280)编集的《大乘要道密集》。六十余年前,中国近代佛学研究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吕澂先生(1896—1989)曾对《大乘要道密集》作过初步但相当精湛的研究,他于1942年出版了一部题为《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的小册子,其中的前一部分《汉译藏密三书》对《大乘要道密集》之结构及主要内容作了介绍,然后挑选集中所录三部密典,即《解释道果金刚句》《大手印金璎珞要门》和《成就八十五师祷祝》,作汉、藏译对勘,并略加诠释,以示其源流和胜劣。
我们唯一知道的一种元代所传汉译藏传密法的文献是误传为元朝帝师八思巴('Phags pa Blo gros rgyal mtshan,1235—1280)编集的《大乘要道密集》。六十余年前,中国近代佛学研究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吕澂先生(1896—1989)曾对《大乘要道密集》作过初步但相当精湛的研究,他于1942年出版了一部题为《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的小册子,其中的前一部分《汉译藏密三书》对《大乘要道密集》之结构及主要内容作了介绍,然后挑选集中所录三部密典,即《解释道果金刚句》《大手印金璎珞要门》和《成就八十五师祷祝》,作汉、藏译对勘,并略加诠释,以示其源流和胜劣。

吕澂先生曾在此书的导言中指出:“元代百余年间,帝王笃信西藏之密教,其典籍学说之传播机会极多,顾今日《大藏经》中所受元译密典不过寥寥数种,且皆为寻常经轨,无一涉及当时西藏传习之学说,是诚事之难解者。十年前,北方学密之风颇盛,北平某氏旧藏钞本《大乘要道密集》因以方便影印,流布于信徒间。集中皆元代所译西藏密典,不避猥亵,尽量宣扬,与唐宋剪裁之制迥异。此不仅可以窥见当时输入藏密之真相,并可以了解译而不传之缘由;积岁疑情为之冰释,至足快也。”可见,吕先生将《大乘要道密集》视作揭开元代“输入藏密之真相”的宝贵资料,他对这部文献对于研究元代藏传密教传播历史的意义有非常准确的领会。
可是,吕澂先生或自觉多年疑情已经冰释,毋需再多费笔墨,故此后再没有继续对收录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些文本的内容,及其与元代所传藏传密法的关系作更多的讨论,很难说他也已经为世人真正揭开了元代所传藏传密教之详情和真相。而他率先倡导的这项研究几十年来更无人问津,迄今为止中外学者中能像吕澂先生一样兼通汉藏佛学、有能力处理和研究像《大乘要道密集》这样专业的藏传密教文献的学者寥寥可数。对于西方治藏传佛教的学者来说,能读懂汉文佛教文献者本来就不多,更不要说能读懂《大乘要道密集》这样的汉文旧译藏传密教文献了。早年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西方学者多为著名的汉学家,如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1910—1967)先生,他曾在其名著《明秘戏图考》和《中国古代房内考》中翻译、介绍了《元史》中有关元代宫廷所传藏传密教史事的记载,但不管是翻译,还是解释,显然都有错误之处。随后,汉、藏、蒙古学大家石泰安(Rolf Stein,1911—1999)和傅海博(Herbert Franke,1914—2011)两位先生也曾尝试过解读这段汉文文献中出现的藏传佛教专有词汇,以揭开元朝宫廷所修藏传密法的谜团。 [1] 可惜当时他们对藏传密教的了解十分有限,也没有机会接触到《大乘要道密集》这部最重要的汉文文献,因此他们的相关研究只是停留在对几个汉文音译藏传密教术语所作的不成功的字面解读上,具有很多臆测的成分,并没有触及事实的核心,也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线索。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杰出汉藏语言研究大家、印第安那大学中央欧亚系教授Christopher Beckwith先生曾在台湾偶然得到了这部宝贵的文献,并认识到了它对于研究元代藏传佛教史的重要意义,曾专门撰文介绍《大乘要道密集》。其文罗列了集中各篇文献的题目,同定了其中一些文本的作者和藏文原本,并对其内容作了一些简单的解释。 [2] 根据他的介绍,我们方知这部藏传密乘佛典主要由属于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与“大手印法”的长短不一的八十三篇仪轨文书组成。这些文书是元以来汉地藏传佛教修行者们珍藏的秘本,也是中国港台地区藏密行者至今日常修习时所依靠的法本。可惜,Beckwith先生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很多的注意,此后西方藏学界也从未有人提起过这部《大乘要道密集》。事实上,西方学者也是晚近十余年来才高度重视藏传密教研究的,对藏传密教传统于前、后弘期之间形成历史的研究更是最近几年才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的。 [3] 如果没有对藏传密教的深入探讨和对藏文密教文献的全面了解,那么即使精通汉语实在也是不可能对《大乘要道密集》这样纯粹、精深的藏传密教文献进行任何有深度的研究的。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藏学研究发展之迅速令举世瞩目,但迄今为止从事西藏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以研究西藏历史者居多,专门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学者凤毛麟角,对藏传密教的了解多半略知其皮相,而很少触及其内核。至今在中国学者中间能够像吕澂先生当年这样对藏文佛教文献,特别是藏传密教仪轨文书用语文学的方法进行专业、深入研究的佛教学者和藏学家屈指可数,所以吕澂先生于六十余年前开始的这项研究工作长期以来无人问津,藏传密教研究在中国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当然,中国大陆学者长期以来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利用《大乘要道密集》这部秘笈,更谈不上对它进行仔细检讨和深入研究了。
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藏学研究前辈王尧先生利用访学中国港台地区的机会,终于有缘亲见这部秘密法本,对它的内容有了比较直接和感性的了解,遂撰专文介绍其内容梗概,提醒读者《大乘要道密集》中所录的这些藏传密教文书可能与元朝宫廷中西天僧和西番僧所传“秘密大喜乐法”有很密切的关联。
 此文虽于国内蒙元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可在藏学界却应者寥寥。直到21世纪初,中国新生代优秀藏学家陈庆英先生同样利用在海外访学的机会,开始对《大乘要道密集》从历史学角度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有不少新的发现,终于引起了中国学者对这部珍贵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的高度重视。陈先生不但对全书的内容作了全面的介绍,对其中一些文献的传、译者的身份作了考证,而且非常正确地指出了一个前人尚未曾注意到的事实,即《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那些文本实际上不全是元代的译本,其中数种长篇密教文献当是西夏时代的作品,与西夏王朝所传藏传密法有很大的关联。
此文虽于国内蒙元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可在藏学界却应者寥寥。直到21世纪初,中国新生代优秀藏学家陈庆英先生同样利用在海外访学的机会,开始对《大乘要道密集》从历史学角度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有不少新的发现,终于引起了中国学者对这部珍贵的汉译藏传佛教文献的高度重视。陈先生不但对全书的内容作了全面的介绍,对其中一些文献的传、译者的身份作了考证,而且非常正确地指出了一个前人尚未曾注意到的事实,即《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那些文本实际上不全是元代的译本,其中数种长篇密教文献当是西夏时代的作品,与西夏王朝所传藏传密法有很大的关联。
 这让世人开始了解到藏传佛教实际上早在元朝以前的西夏时代就已经在西藏以外地区传播和流传了。
这让世人开始了解到藏传佛教实际上早在元朝以前的西夏时代就已经在西藏以外地区传播和流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