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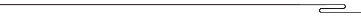
《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另一半文献当属于元、明两代的译本,特别是明代的译本。其中收录了九部标明为持咒沙门莎南屹啰所译的文书,均属萨思迦派之道果法。以往人们习惯于把莎南屹啰当作是八思巴帝师的弟子,所以普遍认为《大乘要道密集》是元代的译本。事实上,我们对这位译师的来历一无所知,以往大家只是因为莎南屹啰这个名字显然像是一个普通藏人名字的汉文音译,可还原为藏文bSod nams grags,所以,我们也自然而然地将他当作一位藏族的译师,希望从元代藏传佛教上师中寻找与他同名的人来确定其身份。见于《大乘要道密集》卷四之《苦乐为道要门》有载其修法之传承如下:“此师传者,世上无比释迦室哩二合班的达、枯噜布洛拶咓、看缠洛不啰二合巴、看缠爹咓班、看缠屹啰二合思巴孺奴、看缠莎南屹啰、法尊莎南监藏。”
 吕澂先生据此认为:“按《苦乐为道要门》属于百八通轨,故五世达赖喇嘛《闻法录》(
lNga pa'i gsan yig
)亦尝记其传承,与《密集》所载大同,今据以勘定各家藏文原名如次:Kha che pan chen [
吕澂先生据此认为:“按《苦乐为道要门》属于百八通轨,故五世达赖喇嘛《闻法录》(
lNga pa'i gsan yig
)亦尝记其传承,与《密集》所载大同,今据以勘定各家藏文原名如次:Kha che pan chen [
 akyasrībhadra]、Khro lo、lHo brog pa、bDe ba dpal、Grags pa gzhon nu、bSod nams grags pa、Bla ma dam pa bsod nams rgyal mtshan。复检嘉木样《西藏佛教年表》(
bsTan rtsis re mig
),莎南屹啰(福称)卒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其资莎南监藏生于元仁宗皇庆元年,卒于明太祖洪武八年(1312—1375)。故莎南屹啰之翻译传授,当在至正年间。”
akyasrībhadra]、Khro lo、lHo brog pa、bDe ba dpal、Grags pa gzhon nu、bSod nams grags pa、Bla ma dam pa bsod nams rgyal mtshan。复检嘉木样《西藏佛教年表》(
bsTan rtsis re mig
),莎南屹啰(福称)卒于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其资莎南监藏生于元仁宗皇庆元年,卒于明太祖洪武八年(1312—1375)。故莎南屹啰之翻译传授,当在至正年间。”
 显然,吕澂先生自然地将译师莎南屹啰与传承《苦乐为道要门》的宗承师之一的莎南屹啰认同为同一人了。
显然,吕澂先生自然地将译师莎南屹啰与传承《苦乐为道要门》的宗承师之一的莎南屹啰认同为同一人了。
同样,陈庆英先生也认为这个传承系列当就是迦什弥罗班智达之教法传承中的曲龙部,历任法师为mKhan chen Byang chub dpal、bDe ba dpal(1235—1297)、Grags pa gzhon nu(1257—1315)、bSod nams grags pa。
 虽然吕、陈二位先生所列的这两个传承系列互相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但显然都与《苦乐为道要门》中所载的那个传承系列有关。然他们进而认定通常被认为是元代的那位著名译师莎南屹啰就是这儿提到的这位同名上师,则缺乏足够的证据。从这两个传承系列来看,其中的莎南屹啰曾是布思端辇真竺和《西藏王统记》的作者、萨思迦派大学者法尊莎南监藏二人的上师。
[4]
其实,除了和《大乘要道密集》中常常出现的这位译师同名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确定他们就是同一个人。如果我们真能证明这么重要的一位西藏佛学大师同时亦是一位精通汉文、曾于汉地传播藏传密法的大译师的话,那实在是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了。莎南屹啰对于藏传佛教于汉地传播所作出的贡献实在可以和吐蕃时代汉藏兼通的大译师法成相媲美,可惜其真实面目与法成法师一样扑朔迷离。以常理来说,作为布思端辇真竺和法尊莎南监藏两位大师之上师的萨思迦派上师莎南屹啰显然不可能就是这位十分高产的大译师,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他曾于汉地长期逗留、传法,还有能力可以翻译如此众多且十分高质量的藏传密教仪轨。
虽然吕、陈二位先生所列的这两个传承系列互相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但显然都与《苦乐为道要门》中所载的那个传承系列有关。然他们进而认定通常被认为是元代的那位著名译师莎南屹啰就是这儿提到的这位同名上师,则缺乏足够的证据。从这两个传承系列来看,其中的莎南屹啰曾是布思端辇真竺和《西藏王统记》的作者、萨思迦派大学者法尊莎南监藏二人的上师。
[4]
其实,除了和《大乘要道密集》中常常出现的这位译师同名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可以确定他们就是同一个人。如果我们真能证明这么重要的一位西藏佛学大师同时亦是一位精通汉文、曾于汉地传播藏传密法的大译师的话,那实在是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了。莎南屹啰对于藏传佛教于汉地传播所作出的贡献实在可以和吐蕃时代汉藏兼通的大译师法成相媲美,可惜其真实面目与法成法师一样扑朔迷离。以常理来说,作为布思端辇真竺和法尊莎南监藏两位大师之上师的萨思迦派上师莎南屹啰显然不可能就是这位十分高产的大译师,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载他曾于汉地长期逗留、传法,还有能力可以翻译如此众多且十分高质量的藏传密教仪轨。
此外,莎南屹啰翻译的藏传密教文书远不止于收录进《大乘要道密集》中的那几种文献,近年来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标明为莎南屹啰所译的藏传密教文本。如此众多的署名为莎南屹啰译的藏传密教文献之汉译本的发现,只能说明他更应当是一位常居汉地的职业大译师,而不可能是一位短期来汉地传法的西番上师。在我们新发现的莎南屹啰译藏传密教文献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明代正统四年泥金写本长篇藏密仪轨《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和《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前者署名“大元帝师发思巴述、持咒沙门莎南屹啰译”,而后者则仅署“持咒沙门莎南屹啰二合集译”。而颇令人欣喜的是,就在这两部文书中,我们找到了或可揭开莎南屹啰生平年代的有力证据。
在《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这两部仪轨中,有好几处都出现了其所传仪轨之传承宗师的名录,从其所列传承上师生平年代推算,即可推知莎南屹啰不可能是我们习以为的元朝(1271—1368),而更应当是明朝(1368—1644)人氏。例如,《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于其中的“奉大黑兄妹二尊施食”仪轨中列出了一个传承上师名录,于“辣麻发思巴”,即八思巴帝师之后列出了五位上师,分别是“辣麻俄玩八咓、辣麻多儿租八、辣麻端孤噜巴、辣麻舍辣藏卜、尼牙二合拿啰释弥”。
 这份名录亦见于《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中,上师名称的写法略有不同,后者作:“辣麻娥玩二合发斡、辣麻多儿二合粗巴、辣麻端孤噜巴、辣麻舍剌藏卜、雅纳啰释迷。”
这份名录亦见于《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中,上师名称的写法略有不同,后者作:“辣麻娥玩二合发斡、辣麻多儿二合粗巴、辣麻端孤噜巴、辣麻舍剌藏卜、雅纳啰释迷。”
 作为这两部仪轨的译师,莎南屹啰的生平年代无疑当与该传承中的最后一位上师,即“尼牙二合拿啰释弥”的生平年代最为接近。“尼牙二合拿啰释弥”,或“雅纳啰释迷”,显然是梵文名字 Jñānara
作为这两部仪轨的译师,莎南屹啰的生平年代无疑当与该传承中的最后一位上师,即“尼牙二合拿啰释弥”的生平年代最为接近。“尼牙二合拿啰释弥”,或“雅纳啰释迷”,显然是梵文名字 Jñānara
 mi的音译,译言“智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以梵名“尼牙二合拿啰释弥”见称的智光法师实际上指的竟然是明代名僧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1349—1435),此即是说,《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直接传承自明初的大国师智光。如此说来,翻译这两部仪轨的译师莎南屹啰自然最早也应该是智光国师的同时代人,他应该是一位明代的译师,而不可能是一位来自西番的元代上师。
mi的音译,译言“智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以梵名“尼牙二合拿啰释弥”见称的智光法师实际上指的竟然是明代名僧西天佛子大国师智光(1349—1435),此即是说,《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直接传承自明初的大国师智光。如此说来,翻译这两部仪轨的译师莎南屹啰自然最早也应该是智光国师的同时代人,他应该是一位明代的译师,而不可能是一位来自西番的元代上师。

值得庆幸的是,在晚近新发现的一部明代汉译藏传佛教上师、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的一部传记《西天佛子源流录》中,我们又见到了一段或与《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的汉译直接相关的记载,也可证明《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确实是一部明代的翻译作品。《西天佛子源流录》中记载宣德元年(1426),班丹札释从乌斯藏回归京师,即曾奉命翻译藏传密教仪轨:
是月十五日,召至文华殿,命译《喜金刚甘露海坛场修习观仪》。自是凡出入金阙,小心慎密,日近天颜,敷宣法要,无不称旨。又命译《大轮金刚手坛场法仪》、《金刚怖畏十三佛中围坛场法仪》、《普觉中围坛场法仪》、《〈喜金刚二释本续〉注解》、《无量寿佛九佛中围坛场法仪》、《多闻天王修习法仪》、中有等诸要门。

这里提到的《喜金刚甘露海坛场修习观仪》或应当就是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这部《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如此说来,这部仪轨的译师莎南屹啰或应该是属于大智法王班丹扎释麾下之西域僧团中的一名弟子,他当然应该是一位明代的译师。
于今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收藏中,我们亦找到了同样是莎南屹啰翻译的《端必瓦成就同生要》《因得啰菩提手印道要》《大手印无字要》《喜金刚中围内自受灌仪》等多种藏传密教仪轨文书。
 由于我们可以确定莎南屹啰确实是一位明代的大译师,所以,《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标为莎南屹啰翻译的九部仪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两部长篇仪轨,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那些新发现的多种同样也是由莎南屹啰翻译的萨思迦所传道果法的仪轨等,都应当是明代的作品。这样说来,《大乘要道密集》的成书年代最早也不可能早于明朝初年了。
由于我们可以确定莎南屹啰确实是一位明代的大译师,所以,《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录的标为莎南屹啰翻译的九部仪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的两部长篇仪轨,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中那些新发现的多种同样也是由莎南屹啰翻译的萨思迦所传道果法的仪轨等,都应当是明代的作品。这样说来,《大乘要道密集》的成书年代最早也不可能早于明朝初年了。
在确定莎南屹啰为明代译师之后,我们对藏传佛教于明代传播的历史自然产生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以前我们完全不知道明代依然有藏传密教文献被翻译成汉文,现在看来明初宫廷不仅承元朝蒙古宫廷之余绪,流行修习藏传密法,而且还曾组织翻译了大量藏传密教仪轨,也有相当数量的前代所译藏传密教仪轨、经咒被重新抄录和刊印,并广为流通。不管是《大乘要道密集》,还是国家图书馆所见的《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和《修习法门》等,
 它们所收集的这些法本大概依然还只是从西夏到明代曾经流传过的所有藏传密教法本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相信一定曾经还有更多的同样性质的文献存世,它们或已经永远流失,或还有待我们继续发现。至少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一定还收藏有多种藏传密教仪轨,迄今已知的即有一部传为明代的写经《各佛施食好事经》(
gTor ma'i cho ga la sogs bzhugs so,gTor ma byin rlabs
),该经藏、汉文双语对音,泥金写本,护经封版为象牙所制,上面雕刻有精美的佛像,并刻有清晰的明成化款识。其主要内容即是施食供养诸密宗主尊及护法神,如本尊大持金刚上师、喜佛、上乐轮、哑蛮答葛、大轮金刚、多闻天王、六臂护法、二臂护法、四臂护法、葛剌噜巴、一切空行等。此外还有向其他各神祇,如根本上师、一切护神、一切居士婆罗门天仙、多闻天王咎巴剌拥财佛母、南瞻部洲一切土主并当坊地祇等的施食仪轨。
它们所收集的这些法本大概依然还只是从西夏到明代曾经流传过的所有藏传密教法本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相信一定曾经还有更多的同样性质的文献存世,它们或已经永远流失,或还有待我们继续发现。至少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一定还收藏有多种藏传密教仪轨,迄今已知的即有一部传为明代的写经《各佛施食好事经》(
gTor ma'i cho ga la sogs bzhugs so,gTor ma byin rlabs
),该经藏、汉文双语对音,泥金写本,护经封版为象牙所制,上面雕刻有精美的佛像,并刻有清晰的明成化款识。其主要内容即是施食供养诸密宗主尊及护法神,如本尊大持金刚上师、喜佛、上乐轮、哑蛮答葛、大轮金刚、多闻天王、六臂护法、二臂护法、四臂护法、葛剌噜巴、一切空行等。此外还有向其他各神祇,如根本上师、一切护神、一切居士婆罗门天仙、多闻天王咎巴剌拥财佛母、南瞻部洲一切土主并当坊地祇等的施食仪轨。
 此外,还有一部藏、汉双语文字加配图的《修[欢]喜佛图》,传为清代制作,图解修持喜金刚本尊等法门,其内容或与噶举派怕木古鲁派上师朵儿只监卜(rDo rje rgyal po)、萨思迦三世祖名称幢师所传的有关道果机轮(lam'bras'khrul'khor,或曰幻轮)之修习仪轨相似。
此外,还有一部藏、汉双语文字加配图的《修[欢]喜佛图》,传为清代制作,图解修持喜金刚本尊等法门,其内容或与噶举派怕木古鲁派上师朵儿只监卜(rDo rje rgyal po)、萨思迦三世祖名称幢师所传的有关道果机轮(lam'bras'khrul'khor,或曰幻轮)之修习仪轨相似。
 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恐也还不止《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这两部仪轨,例如在其所藏的《大乘经咒》中便收录有《大悲观自在菩萨总持经咒》和《佛顶尊胜总持经咒》两部经咒,它们不见于现有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中,却和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或西夏文版《大悲观自在菩萨总持功能依经录》和《佛顶尊胜总持功能依经录》完全一致。这说明西夏时代汉译的密教续典也曾经流传到内地,并在历代宫廷中被保存了下来。总而言之,对西夏、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中亚地区和内地传播的历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资料有待发现和研究,这个领域还大有可为。
而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恐也还不止《吉祥喜金刚集轮甘露泉》和《如来顶髻尊胜佛母现证仪》这两部仪轨,例如在其所藏的《大乘经咒》中便收录有《大悲观自在菩萨总持经咒》和《佛顶尊胜总持经咒》两部经咒,它们不见于现有各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中,却和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汉文或西夏文版《大悲观自在菩萨总持功能依经录》和《佛顶尊胜总持功能依经录》完全一致。这说明西夏时代汉译的密教续典也曾经流传到内地,并在历代宫廷中被保存了下来。总而言之,对西夏、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中亚地区和内地传播的历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资料有待发现和研究,这个领域还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