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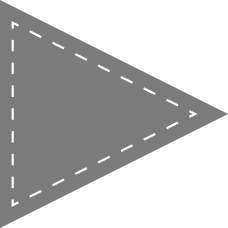 二 一个论题,两样判断
二 一个论题,两样判断
凡是读过《全真七子》一书的读者,想必不会忘记该书给予丘处机的绝顶崇高的美誉。它称丘处机为“天下之至神”、
 “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文化的光荣”,
“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文化的光荣”,
 又说丘处机“静则寂然无声,动则惊天动地,……真是龙一般的人物”。
又说丘处机“静则寂然无声,动则惊天动地,……真是龙一般的人物”。
 给出这些美誉的主要依据就是丘处机有所谓的“一言止杀”历史功绩。《全真七子》这样写道:
给出这些美誉的主要依据就是丘处机有所谓的“一言止杀”历史功绩。《全真七子》这样写道:
长春用博厚的仁爱之心去化解成吉思汗的杀戮之气,并确有成效。……尔后成吉思汗确实收敛了杀心,减少了军事行动中屠戮平民的行为。成吉思汗用军事的力量征服了西域,而长春大师又用道德的力量征服了成吉思汗,谁更伟大呢?

“确有成效”、“确实收敛”,——这就是《全真七子》对丘处机进言止杀功绩的认定,可谓言之凿凿,毫不含糊。可是,该书既没有交代可信的史料依据,也没有举出一个成吉思汗减少屠戮的实例。为此,我在《再辨伪》一文中一面举出长春西行后蒙古军继续在许多地区屠戮民众的事实,一面率直地向《全真七子》作者们索要“一言止杀”的证据。我在文章的末段说:
历史学是一门重实证的学科,议论历史必须以真凭实据为证。“一言止杀”故事可以分解为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一是丘处机进言止杀,二是成吉思汗听其言而止杀。主张“一言止杀”实有其事的学者理应对这两个方面均予举证,规避举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后我套用了鲁迅的一句话:我们“总是说些真实的好”。

《再辨伪》一文发表后,我听到一些议论,有说我过于尖锐的。赵先生的文章则说我对《全真七子》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
 其实我的“尖锐”、“严厉”所针对的无非是该书的一些无稽之谈,只是要求对方出示证据而已。出示证据原是史学工作的本分,对于已经发表了结论的作者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怕的是证据未握而结论先行,及至有人索讨证据,便立刻陷入窘境。这次我读赵文,便看到了赵先生的窘态。他这篇题为《“一言止杀”辨正》的文章,不仅没有为“止杀”之确有举出证据,反而引用我在《再辨伪》中的说法,承认了“止杀”之实无。谓予不信,请看下文:
其实我的“尖锐”、“严厉”所针对的无非是该书的一些无稽之谈,只是要求对方出示证据而已。出示证据原是史学工作的本分,对于已经发表了结论的作者来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怕的是证据未握而结论先行,及至有人索讨证据,便立刻陷入窘境。这次我读赵文,便看到了赵先生的窘态。他这篇题为《“一言止杀”辨正》的文章,不仅没有为“止杀”之确有举出证据,反而引用我在《再辨伪》中的说法,承认了“止杀”之实无。谓予不信,请看下文:
……对于“丘处机进言止杀”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讨论,按照杨先生的说法,仅此尚嫌不够,要想证明“一言止杀”确有其事,还必须举出成吉思汗止杀的证据来。
正如杨先生所言,根据各种史料记载,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之后,蒙古军并没有停止杀戮,但这不足以证明丘处机没有向成吉思汗建言止杀。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时,蒙古军正是所向披靡、锋芒正盛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候向成吉思汗建言止杀,既(即)使成吉思汗接受了建议,也不可能马上产生效果。这就是为甚么丘处机觐见之后,蒙古军还在继续着杀戮。

赵文约两万两千字,上引这段话出现在两万字以后,已接近文章尾段,它讲了成吉思汗没有接受丘处机的止杀建议,即使接受了也不可能生效。
 在一位先前断言止杀“确有成效”的《全真七子》作者笔下,在一篇题为《“一言止杀”辨正》的文章里,出现这样一段文字,完全出乎我意外。难道赵先生忘了,自己这篇文章的前两万字一直在为论证止杀之实有作铺垫,在第二章末尾还斩钉截铁地说对《西游记》等文献“只有一种解释,即丘处机‘一言止杀’确有其事”,
在一位先前断言止杀“确有成效”的《全真七子》作者笔下,在一篇题为《“一言止杀”辨正》的文章里,出现这样一段文字,完全出乎我意外。难道赵先生忘了,自己这篇文章的前两万字一直在为论证止杀之实有作铺垫,在第二章末尾还斩钉截铁地说对《西游记》等文献“只有一种解释,即丘处机‘一言止杀’确有其事”,
 怎么临到“必须举出成吉思汗止杀的证据”时,“确有”的事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呢?请问,在同一篇文章中对同一个论题可以作出两种互相矛盾、截然相反的判断吗?
怎么临到“必须举出成吉思汗止杀的证据”时,“确有”的事就成了“不可能”的事呢?请问,在同一篇文章中对同一个论题可以作出两种互相矛盾、截然相反的判断吗?
尤可怪者,赵先生一面声称“正如杨先生所言,……蒙古军并没有停止杀戮”,一面又挑明他是在同我“商榷”。在他既判断止杀“确有”,又判断止杀“不可能”的情况下,要我同他哪一种判断“商榷”呢?自称“长于思辨”的赵先生,
 焉能如此不顾逻辑。故而我断定,赵先生讲出“正如杨先生所言……”这番话,只是为了摆脱别人对止杀证据的追讨,切莫以为他改变了原先的观点。
焉能如此不顾逻辑。故而我断定,赵先生讲出“正如杨先生所言……”这番话,只是为了摆脱别人对止杀证据的追讨,切莫以为他改变了原先的观点。
果然,就在讲了“蒙古军还在继续着杀戮”之后,赵先生又借着一个“然而”把立场翻回到原点,继续论证“一言止杀”之“确有”。他的原话是:
然而,若从总体上来审视丘处机觐见前后成吉思汗军事政策的变化,还是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赵先生没有明讲,他找出的是甚么事物的蛛丝马迹,但从上下文看,无疑是指可据以探寻丘处机、成吉思汗止杀功效的蛛丝马迹。一件已被判定“不可能”生效的事还能留下其生效的蛛丝马迹,倒也够奇怪的。这中间的逻辑关系不妨留待“长于思辨”的学者自己来解释,我更关心的是赵先生找出的蛛丝马迹究竟为何物。
赵先生找出的蛛丝马迹共两条。第一条是《元史》卷一《太祖纪》记载的太祖二十二年(1227)六月成吉思汗对群臣言:“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成吉思汗是当年七月去世的,上引的话讲于去世前一个月,他正进军秦州(今甘肃天水)时。所言“去冬五星聚时”指太祖二十一年(1226)十一月二十六日丁丑,《元史·太祖纪》有记载:“丁丑,五星聚于西南。”
 “五星聚舍”又称“五星连珠”,是难得出现的天象,被中国古代星占学视为异常,或判为凶,或判为吉,详说请看江晓原先生所著《星占学与传统文化》。
“五星聚舍”又称“五星连珠”,是难得出现的天象,被中国古代星占学视为异常,或判为凶,或判为吉,详说请看江晓原先生所著《星占学与传统文化》。
 1226年十一月正值成吉思汗攻打西夏灵州(今宁夏灵武),已是丘处机觐见四年之后,又过半年成吉思汗才想到把自己“许不杀掠”的想法布告中外。在他有这想法的半年里,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做了甚么,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有一段集中的叙述:
1226年十一月正值成吉思汗攻打西夏灵州(今宁夏灵武),已是丘处机觐见四年之后,又过半年成吉思汗才想到把自己“许不杀掠”的想法布告中外。在他有这想法的半年里,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做了甚么,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有一段集中的叙述:
(1226年)十一月,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进攻灵州(朵儿篾该),(西夏国王赵)遣嵬名令公统率十万军队来援。蒙古军渡河进击,消灭西夏军,杀死无数,尸体堆积如山。随后成吉思汗到盐州川驻冬,蒙古军在盐州一带肆行杀掠,居民有的打土洞、石洞避兵,得免于难者百无一二。
成吉思汗认为经过此次打击,西夏已不再有力量抵抗,……于1227年正月率军南下,进入金境,攻陷临洮府和洮、河、西宁、德顺等州,别遣一军攻入宋境掳掠。四月,驻夏于六盘山。六月,继续向南进兵,至秦州清水县。七月,病死。临死前吩咐:秘不发丧,以免被敌人获悉;待西夏国主和居民在指定时刻出城时,立即全部把他们消灭。

这段史事在周良霄、顾菊英两位先生合著的《元史》中也有叙述,
 两书互有详略。赵先生可能未读韩书,但周、顾的书他是读了的。判断成吉思汗是否止杀,为甚么不顾如此确凿的事实,而要挖空心思去另找所谓的蛛丝马迹?而且这第一条蛛丝马迹同丘处机毫无关系,成吉思汗自己讲,是半年前星象的异常促使他考虑禁止杀掠。那时丘处机身在千里之外的燕京,星变既非他所预言,亦非由他作出解释,成吉思汗“许不杀掠”与他有何相干?赵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用常话讲叫作生拉硬扯的错误。
两书互有详略。赵先生可能未读韩书,但周、顾的书他是读了的。判断成吉思汗是否止杀,为甚么不顾如此确凿的事实,而要挖空心思去另找所谓的蛛丝马迹?而且这第一条蛛丝马迹同丘处机毫无关系,成吉思汗自己讲,是半年前星象的异常促使他考虑禁止杀掠。那时丘处机身在千里之外的燕京,星变既非他所预言,亦非由他作出解释,成吉思汗“许不杀掠”与他有何相干?赵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用常话讲叫作生拉硬扯的错误。
赵先生找出的第二条“蛛丝马迹”是木华黎经略华北时期(1217—1223)蒙古国“军事、政治政策的变化”。他引周良霄、顾菊英《元史》中的一段记述为据,然后说:
他们(指周、顾)还列举了《元史》中的相关史料来说明导致木华黎军事、政治政策产生变化的原因。虽然他们只提到了史天倪与刘世英曾劝谏木华黎减少杀掠,没有提到丘处机,但丘处机建言止杀对当时整个大气候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这是说,是丘处机建言止杀所造成的大气候推动了木华黎麾下两员汉人将领向木华黎劝谏止杀,而周、顾的《元史》忽视了丘处机的作用。可是,赵先生为甚么不说说史天倪与刘世英劝谏木华黎的年份呢?《元史》卷一四七《史天倪传》记史天倪劝谏在庚辰年,同书卷一五〇《刘亨安传》记刘世英劝谏也在庚辰年,庚辰年即1220年。熟知丘处机西行历程的赵先生不会不知,丘处机直到庚辰年底尚盘桓于今日河北的涿鹿、宣化之间,要到壬午年(1222)四月才初次觐见成吉思汗,雪山讲道更在壬午年十月。一件1222年发生的事竟会对1220年的“整个大气候”产生影响,岂非咄咄怪事,莫非时光真的倒流了?宋濂的《元史》赵先生可能没有查,他引据的是周、顾的《元史》,但周、顾也是讲了史、刘劝谏年份的(只是把史天倪的劝谏说早了一年),赵先生为何仿若未见,不向读者交代?
木华黎经略中原六年(1217—1223),在此期间其经营方略的确有所变化,但同丘处机西行无关。木华黎于癸未年(1223)三月卒于闻喜(今属山西),当时丘处机尚在东归途中,还没有抵达阿里马,他的西行对木华黎能有甚么影响?
话讲到这里,关于成吉思汗究竟止杀了没有的问题,可以不再探讨了。不管赵先生是否心甘情愿,他在口头上总算承认了丘处机觐见后蒙古军继续还在屠杀,这就够了。接着要谈的问题,是丘处机究竟有无进言止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