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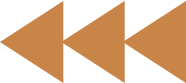
书中的绛珠草是否有什么象征与隐喻呢?在探讨这一课题前,有必要了解一下人参业在大清建国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及满族人的人参情结。
女真人南迁之前,主要居住在松花江和图们江两岸。东濒海,北接室韦,地饶山林,田宜麻谷,土产人参、貂皮、东珠、生金、松实等。
《清代东北参务》中讲:“辽金时,人参为支撑女真人经济生活之重要特产。至明代,女真人分布日广,采参更成了这个民族的‘支柱产业’。据明档记载,早在万历十一、十二年(1583、1584)间,以住居吉林为主的海西女真在广顺、镇北二关互市中,售出人参达三千六百一十九斤,价值时银达三万余两。在以东北人参与中原的互市中,女真人换取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及文化用品等,从而推动了女真社会经济文化的较快发展。”

清太宗皇太极时,参价每斤值银25两,每年可采收10万斤,人参一项即可收入白银250万两。可见,人参互市是后金经济和政治的生死线。
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因与明朝开展马市贸易,势力逐渐强大。特别是在人参贸易中,存在强买强卖的垄断行为,并阻塞远方江夷与明朝的貂参贡贸制度实施,这是明朝不能允许的。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明神宗采用熊廷弼之策略,暂停辽东马市上的人参贸易,致使后金人参烂掉10余万斤。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六月,努尔哈赤以五千骑叩抚顺关,挟参索值,未能奏效。逼使女真遂煮晒成红参、白参,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偿,粉碎了明朝人参封锁政策。
后金主要以人参贸易积蓄力量赖以立国。大清取得全国政权后,满族贵族从销售人参而国富民殷,到享用人参求寿世长命,社会需求旺盛,人参贸易仍是朝廷收入之大宗,“使得皇帝多亲自过问参务,参务细节也都一一奏闻……每年所到销售参额、价格、总银数等奏明皇上知道。可以认为,清朝皇帝是人参变卖的直接参预者”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三回有个眉批,活画出“皇帝老爷”贪婪的形象:“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稍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此时的大清皇上,不仅是人参变卖者、垄断者,也是人参的享用者。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三回有个眉批,活画出“皇帝老爷”贪婪的形象:“左手拿一金元宝,右手拿一银元宝,马上稍着一口袋人参,行动人参不离口。”——此时的大清皇上,不仅是人参变卖者、垄断者,也是人参的享用者。
人参的巨大利益,让人趋之若鹜。清朝统治者视东北为龙兴之地,尤珍重这里的一草一木,植柳挖壕筑柳条边墙,实行封禁,以保证其所谓龙脉风水不受践踏,并独享东省的方物特产。在这种心理支配下,名贵的人参自然成为皇家的神品。人参业的巨大经济利益,促使大清伊始,便实行皇家和皇亲贵族专制性垄断采收和变卖,以保证人参公用。
清入关统一全国之初,仍因袭入关前八旗分山采参制,将乌拉(吉林)地方110处参山放给八旗。除皇室自领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刨采外,后改由乌拉总管衙门与将军府合署的参务局制,每年有三百参丁引领兵丁刨采。康熙二十五年(1686),乌苏里江人参采场被发现,刺激了皇室和王府的胃口,刨采参丁一年不下三四万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参务局再次停止八旗采参,实行“放票制”,把采参专利权收归国有。因受到王公贵族的抵制,官办采参制未能通行。
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廷决定招商承包采参事务,先由盛京商人王修德呈领参票八千张,后又有其他富商招领参票,中小商户也出面转领,再由票头招领揽头、把头等,组织刨夫进山。清政府为防备领票人短欠人参或拐票逃走,规定由烧锅、铺户画押具保。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官商惧怕亏损,烧锅、铺户也不愿担保,采参业陷入困境。
这期间发生两件与曹家有关的事:其一,康熙五十七年(1718)正月初三,内务府奏请将人参一千零二十四斤交由曹、李煦、孙文成售卖。结果“售参价银比历年均少”,
 引起怀疑。后康熙逝世,雍正上台,雍正原本看不上包衣人,自然要追查责任。其二,也许受到承包刨采巨大利益的诱惑,或者预感到织造之职已岌岌可危,时任苏州织造的李煦,竟鬼使神差地“奏请欲替王修德等挖参”。奏请挖参,是否允奏是皇上的事,本无什么大不了的。不料,雍正却弗然变色,借机“而废其官,革其织造之职,请咨行该地巡抚等严查其所欠钱粮”。
引起怀疑。后康熙逝世,雍正上台,雍正原本看不上包衣人,自然要追查责任。其二,也许受到承包刨采巨大利益的诱惑,或者预感到织造之职已岌岌可危,时任苏州织造的李煦,竟鬼使神差地“奏请欲替王修德等挖参”。奏请挖参,是否允奏是皇上的事,本无什么大不了的。不料,雍正却弗然变色,借机“而废其官,革其织造之职,请咨行该地巡抚等严查其所欠钱粮”。

这段小插曲自然不能写入《红楼梦》,那就太露了。但雍乾年间皇商承包采参业,参价飙升,参商以次充好,甚至制假贩假,大清参务,难以为继,此状在《红楼梦》中有真实反映。
第七十七回为凤姐治病,须“上等人参二两”,王夫人与人商议买二两来。宝钗告诉说:
如今外头卖的人参都没好的,虽有一枝全的,他们也必截做两三段,镶嵌上芦泡须枝,掺匀了好卖,看不得粗细。我们铺子里常和参行交易,如今我去和妈说了,叫哥哥去托个伙计过去与参行商议说明,叫他们把未作的原枝好参兑二两来。

这段话很要紧。为什么宝钗对人参这么在行?原来雍正九年(1731)到乾隆九年(1744),一度实行皇商采参承包制,盛京将军纳苏图赴京城招请大皇商范玉馥、范清注父子承包采参,在乌苏里、绥芬、宁古塔年采收人参十三万五千余两,参须六万二千余两,获利甚丰。《红楼梦》中薛家是皇商,隐约有皇商范氏父子承包采参的影子。故言“我们铺子里常和参行交易”。交易自然不限于买,也包括卖。为皇上配制特药的全枝带叶参,也只有皇商薛家能搞到。
清代采参业如同其社会制度一样,从乾隆末年开始明显地呈现出衰败的迹象。贵族们无尽享用,竭泽而渔,资源枯竭,参价倍增,在《红楼梦》中亦有充分描写。
乾隆九年至十四年(1749),因所进人参不敷额收,将采参丁三百人罚采珠采蜜,以赎罪愆,参价也涨得令人咋舌。后金时人参在北京一斤售价25两银。康熙年黄参一两,银10两。到乾隆十五年(1750),人参则一钱售银1.7两~3.2两。当朝人参不敷额收,价昂货缺的情形在《红楼梦》中有真实的描写。
第七十七回,为治凤姐的病,按大夫开的方子,须用上等人参配制调经养荣丸。王夫人取时,翻寻了半日,只在小匣子里寻了几支簪挺粗细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须末出来。王夫人以为是下人“随手混撂”。丫鬟彩云告诉她说:“想是没了,就只有这个……”王夫人不信,要彩云再去找。彩云又找来些,王夫人一看没一枝是人参。她不信没了像样的人参,又遣人问管家凤姐。凤姐说:“也只有那些参膏芦须。”王夫人没法儿,去向邢夫人问,也没有,又亲自来问贾母。贾母命鸳鸯取出当日所余的来,竟还有一大包,皆有手指粗细的,遂称二两给王夫人送去。一时,周瑞家的又拿了进来,说经医生看过:
但这一包人参固然是上好的,如今就连三十换也不能得这样的了,但年代太陈了。这东西比别的不同,凭是怎样好的,只过一百年后,便自己就成了灰了。如今这个虽未成灰,然已成了朽糟烂木,也无性力的了。
人参年代久远,性力有所降解是可能的,却无有“百年化灰”这一说,只要防蛀虫,人参不会自然成灰。
贾母号称老祖宗,是代表贾家先世而存在的。这一大包人参是“当日所余”。这个“当日”大约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的立国之初。第七回焦大的醉骂“跟着太爷出过三四回兵”,当日太爷们是无须花银子去买人参的,靠“俘获”也无不是“塞江填海”似地。第七十七回如此细腻写寻找人参,一直寻觅到老祖宗那里,引出“百年人参成灰”的谶语,显然意在揭示“胡人无有百年运”这一政治谶言,只是在《红楼梦》中换了一种说法:人参“这东西比别的不同,凭是怎样好的,只过一百年后,便自己就成了灰了”。——联想到书中不断宣示“国朝定鼎不足百年”“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人参所喻,亦不言自明。
第十二回讲的是贾代儒之孙贾瑞,看上“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的凤姐,用言语调戏并欲上手。凤姐出狠招儿惩教他,使其害了虚劳之症。药吃了几十斤下去,未见动静。腊尽春来,病势转重,看来只能吃独参汤或能有救。独参汤主治虚极欲脱、脉微欲绝,一味独参汤能起死回生吗?作者在贾瑞临终前起用独参汤,是对贾瑞这些“自作孽,不可活”的丑类的绝大讽刺。
贾瑞在书中兼学监的角色。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偏偏安排他为代儒(代表儒家孔圣)之孙。乾隆朝提倡儒学,大兴孔孟之道,尊孔子为至圣先师,到处建孔庙,开办儒学学堂,授四书五经。贾家的私塾就是这类学堂,贾代儒是一位独尊儒术的教书先生。作者偏偏让这位代儒之孙堕落为淫念不绝、劣习难改、无耻行径、自寻绝路的蠢货,其尊讳为一“瑞”字,名贾天祥,将这位“自作孽,不可活”的丑类,寓为大清的祥瑞人物,多么大的讽刺,又是对大清朝教育制度失败多么真实的写照啊!
第二十八回,宝玉来瞧黛玉,两人误会解除,言归于好,双双到王夫人那儿吃饭。席间,王夫人问起黛玉服什么药,又偏偏记不起前日大夫让吃的丸药名。宝钗点醒是“天王补心丸”。人间的天王是谁呢?自然是皇帝,暗指皇帝的心坏了,须补心了。看来,天王只吃补心丸还不行,还须有人为之炮制特效药。作者拐弯抹角、煞费苦心地要薛蟠为皇上配制特效药。先是宝玉借黛玉的病大发议论:“林妹妹是内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点风寒……还是吃丸药的好。”宝玉要配一剂天下少有的丸药,名义是给林妹妹的,实则是“为君的药”,由皇商薛蟠来给配制。那药方子实在奇特得很:
头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千年松根茯苓胆。

这四味奇特的药不过是臣药中的四味,主药更奇绝,须是经过尸气的珍珠,即从古坟挖出来的珍珠。当时王夫人、宝钗等都以为是宝玉寻开心,胡诌的方子。宝玉据理争辩:“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才给了他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寻了二三年,花了上千的银子,才配成了。”为了证实真有此事,还请出凤姐郑重地作证道:
“宝兄弟不是撒谎,这倒是有的。上日薛大哥亲自和我来寻珍珠,我问他作什么,他说配药……我没法儿,把两枝珠花儿现拆了给他……”……宝玉又道:“太太想,这不过是将就呢。正经按那方子,这珍珠宝石定要在古坟里的,有那古时富贵人家装裹的头面,拿了来才好。如今那里为这个去刨坟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道:“阿弥陀佛,不当家花花的!就是坟里有这个,人家死了几百年,这会子翻尸盗骨的,作了药也不灵!”

其实,珍珠入药,忌用首饰上用过的珠子或经尸气者,书中偏偏要古墓里的或做过头面的,这绝非是笑谈,与黛玉在王夫人处看到的半旧的缎袱,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旧物绝非正路而来。
下面简单分析一下臣药中的四味:
其一,头胎紫河车,紫河车即胎盘,旧时认为以头生胎盘为最佳。功能在补气养血,是补先天不足之内症的良药。
其二,人形带叶参,人参用以大补元气。带叶参证明是真货;人形,是大货而有神者。作者夹注说“三百六十两不足”,说花三百六十两也不足以买到这样的参。雍乾朝,讲求这种大枝山参。乌拉地方,一旦挖到这种大参,须通过传驿,速速贡送京都“专备皇上独用”。
 等于说,薛蟠所配药中有大枝山参,是只供皇上专用的。
等于说,薛蟠所配药中有大枝山参,是只供皇上专用的。
其三,龟大何首乌。何首乌为蓼科,多年生草本,以粗壮根茎入药。此药主治虚烦不眠、多梦遗精。龟大何首乌世所罕见,暗骂皇上淫极,龟,指人的阴茎。
其四,千年松根茯苓胆。《淮南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茯苓多生赤松或马尾松下,为松根上寄生物。功能益脾安神,主治心悸失眠。
主药珍珠,功能在定惊,镇心,安魂魄。
宝玉开出的这个方子,特别是主药珍珠,无论给哪个皇上用,都是适症治疗。作者未必确指为康熙、雍正、乾隆个人治病。这三位处于盛世的皇上,哪位都曾遇到过烦恼,都需要定惊、安魂。康熙虽非嫡出,却是多子之君。正因多子,废立无常,到临终前,诸子夺嫡,让康熙寝食难安。雍正继位已让人疑惑重重,有改遗诏之嫌,可说是先天底气不足,须大补;执政时,民心不安,心悸失眠当是常有的事。乾隆是继雍正之位,并非正脉嫡出,故有太子胤礽之子弘皙逆案发生,险些让乾隆身首异处,怎能不心惊胆战。在作者眼里,哪位皇帝不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呢?确切讲都害着政治上的虚症。宝玉的药方并不一定指给哪位皇上治病,因此才说是为林妹妹配丸药。按说,皇商薛蟠没有花两三年、费银千两给黛玉配药的理。此时的林妹妹,已不是人们心中还泪的林妹妹,她那怯弱多病的小身板,已是大清衰微的国体的象征。纵使给皇上配出含人形带叶参的天下奇药,也如秦可卿所言:“任凭神仙也罢,治得病治不得命。”这个大清国呀,不过是挨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