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始走向衰落的罗马帝国。
在古代历史教科书中,罗马的灭亡时间是公元476年。也正是这一年,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了他的王座。但是,我们知道罗马的建立并不是一天完成的,因此它的灭亡过程也同样如此。罗马消亡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很多罗马人根本感觉不到罗马正在消亡,他们还依旧沉浸在昔日的荣耀之中。罗马人看到了政局的动荡不安,也因物价高、收入低而对艰辛的生活抱怨不已。商人们将谷物、羊毛和金币等资源囤集居奇,唯利是图,这让平民百姓叫苦连天。当有的总督十分贪婪,搜刮民脂民膏的时候,罗马人也会站起来进行反抗。但是,这只是生活中的小插曲而已,多数的罗马人在公元前4个世纪中,依旧过着安逸的生活。他们依旧吃喝无忧(由钱包中钱的数量决定),他们依旧爱恨分明(不同性格的人不一样),他们也会去剧场看演出(有不少免费的角斗士搏击表演)。不过,也有一些可怜的人会饿死街头,这类情况在任何时期都无法避免。罗马人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根本没有察觉到他们老迈的帝国已濒临覆灭。

罗马的消亡
尽管罗马身陷动荡的泥潭,但并没有多少罗马人注意到灭亡的临近,人们一边喋

看一下罗马帝国,就会明白罗马人为何意识不到迫在眉睫的危机了。罗马帝国,它是如此强大,到处都可以看到辉煌繁荣的景象。连接各个省份之间的大道四通八达;尽职尽责的警察严厉地打击着拦路盗贼;边防稳固,那些欧洲北部荒蛮的民族根本不敢有任何侵犯;众多的附属国每年都向罗马进贡称臣。除此之外,还有一群聪明、睿智的人在彻夜为国操劳,他们不断标正帝国前进的方向,为使其重现昔日的荣光而竭尽所能。
但是,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在于其根基已经被破坏,这在上一章就提到过。这让任何试图扭转局势的改革都变得徒劳,不会有丝毫作用。
其实,罗马只是一个城邦,从来都是,这和古希腊的雅典或科林斯没有太大的差别,要统治整个意大利的话,它是有足够资格的。但是,如果罗马想要做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实力上看,它都是没有足够能力的。因为常年的战争,让罗马的年轻人多数死在了战火中,农民则因为承担不了过于沉重的兵役和赋税,要么做乞丐,要么依附于庄园主,最后成为所谓的“农奴”。这些身陷苦难的农民不是自由民也不是奴隶,他们只能终身成为土地的附属品,如同牲口和树木一般。
在这里,国家就是一切,国家的荣誉更要大于一切,而那些普通的公民则微不足道。至于那些可怜的奴隶们,在听取保罗宣讲的思想后,他们很快就接受了谦恭的拿撒勒木匠儿子所散布的福音。他们不仅不再反抗了,反而变得更加温顺,一切都依照主人的吩咐去做。他们想着既然现在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寄居场所而已,自己也无力改变,所以奴隶们也就不再关注这个世界。他们是希望打仗的,以便可以更快地进入天堂,享受幸福的生活,不过,他们却不愿意为罗马帝国战斗,因为罗马帝国对努米底亚或帕提亚或苏格兰发动的战争,不过是他们野心勃勃的皇帝所期望获得的辉煌成就罢了。
就这样,当时光悄悄流逝,罗马帝国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坏了。刚开始的时候,罗马皇帝还会做一下领袖的样子,他将管理各地属民的权力授予各个部族的首领。但是到了2世纪、3世纪,罗马皇帝大多为军人出身,他们表现的就完全是军营的作风了,他们的安危依靠着手下禁卫军的忠诚度。皇帝变换得很快,犹如走马灯一般。当一个皇帝刚刚上台,就会被另一个野心勃勃且拥有足够财富可以拉拢士兵的家伙干掉,他们依靠谋杀登上高高的皇位,然后又会成为被谋杀的目标而摔下王座。
同时,罗马的北方边境也不时被野蛮民族骚扰着。罗马在自己的公民中已经招募不到士兵了,于是就只能借助外国雇佣兵来阻挡侵略者的脚步。雇佣兵虽然受雇于罗马,但是,当他们在战场上遇到自己同种族的敌人时,必然会产生恻隐之心,消极作战。最后,罗马皇帝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让某些野蛮民族到帝国内部定居,而其他部族也纷至沓来。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积蓄了一肚子的怨恨,埋怨罗马税官无情地掠走了他们全部的积蓄。如果没有人回应他们的呼声,他们就会冲到罗马抗议,以便让皇帝尽快答复他们的请求。
这类事件时有发生,因此,帝国的首都罗马成为了让人感到不愉快的地方。所以,康士坦丁皇帝(公元312—337年在位)有了一个寻找新首都的想法。后来,他选择了拜占廷,那里是欧亚之间的通商要地,设立于此的新都后被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康士坦丁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了皇位,为了更加方便地管理帝国,他们将罗马帝国分为两个部分。哥哥驻扎罗马,统治西部地区;弟弟驻扎君士坦丁堡,统治东部地区,成为东部的一方霸主。
到了4世纪,欧洲迎来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民族——匈奴。这些来自亚洲的神秘骑兵在欧洲各地不断流窜,并对罗马发动攻击。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依托欧洲北部的集结地,到处烧杀掠夺,直到公元 451年匈奴人在法国沙隆的马恩河被彻底打败才得以终止。在匈奴进军多瑙河的时候,当地的哥特人为了逃生不得不侵犯罗马的领土。公元378年,为了阻止哥特人的入侵,瓦伦斯皇帝在亚特里亚堡附近战死沙场。22年后,在国王阿拉里克的带领下,西哥特人向西进攻,攻破了罗马,他们只是将几座宫殿毁坏了,没有更多的劫掠。接着,汪达尔人又来了,他们对罗马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没有丝毫的怜悯,他们几乎将整个城市破坏殆尽。再后来,勃艮第人、东哥特人、阿拉曼尼人、法兰克人……无休止的侵略让罗马人应接不暇。此时,只要一个强盗拥有野心,能够召集一批追随者,那么,他就可以任意践踏罗马。

东罗马帝国的短暂崛起
饱受各地蛮族骚扰的罗马帝国幅员辽阔,为了便于管辖遂将帝国分为东、西两部

公元402年,西罗马皇帝逃亡到了一个防御坚固的海港城市——拉维纳。公元475年,日尔曼雇佣军的指挥官鄂多萨在这个城市中,采用了温柔的方式劝说最后一任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洛·奥古斯塔斯让出了皇位。然后,他宣布自己是罗马的新统治者,将意大利的土地纳为己有。此时,东罗马帝国皇帝自顾不暇,只能默许了这一事实。于是,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西罗马帝国剩下的省份都由鄂多萨统治着。
几年后,东哥特国王西奥多里克带领军队攻入了这个新成立的国家,一举占领了拉维纳,将鄂多萨杀死在餐桌上。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西奥多里克又建立起一个短命的哥特王国。6世纪,一群由伦巴德人、撒克逊人、斯拉夫人、阿瓦人联合起来的势力入侵了意大利,推翻了哥特王国,重新建立国家,将首都定在帕维亚。

废墟中的文明
多年的战火将这座有着悠久历史与荣耀的罗马城剥落得面目全非,蛮族将曾经安

帝国的首都罗马在连续不断的战争中,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毫无生气。历史悠久的宫殿遭到强盗们的数次洗劫,学校没有了,老师们受饿而死。蓬头垢面、满身臭气的野蛮人将别墅中的富人赶出家门,自己住了进去。帝国的街道、桥梁也因为年久失修而坍塌,不复使用。曾经繁荣的商业也消失了,意大利变得死气沉沉。在经过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几千年的努力,这块远古人类不敢奢望的文明之地面临着在西方大陆消亡的危险。
然而,位于远东的君士坦丁堡仍将帝国中心的旗帜又扛了1000年。但是,这里很难被人当作是欧洲大陆的组成部分,这里的趣味和思想都偏向东方,他们似乎不记得自己曾是欧洲人的后裔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希腊语代替了拉丁语,人们抛弃了罗马字母,使用希腊文书写罗马的法律,让希腊的法官来进行讲解。东罗马皇帝像神一般受到崇拜,这和尼罗河谷的底比斯一样。当拜占廷的传教士想要扩大传教的领地时,他们会向东走到俄国,为那里广袤的荒野带去拜占廷的文明。
此时的西方,已经被野蛮的民族牢牢占据。在将近12代人的时间里,社会准则沦为杀戮、战争、纵火和劫掠,而欧洲文明竟然没有被彻底毁灭。欧洲没有退回到原始、荒蛮社会的重要因素只有、也仅有一个,那就是教会的存在。
教会,这个群体的组成者,恰是那些追随拿撒勒木匠耶稣的人们。要知道,拿撒勒人死去的原因,仅是为了避免让叙利亚边境上一个小城市发生混乱而已。
罗马帝国所面临的奴隶制危机与社会的衰退,悄然间将帝国的生命力侵蚀殆尽,而走向分裂的帝国在迎来周边蛮族的迁徙与入侵时,身受最致命一击的罗马不得不低下了它高昂的头,昔日伟岸的身躯轰然倒塌沦为一堆瓦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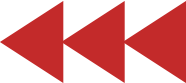
为何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在罗马?
帝国时期的罗马普通知识分子,对于那些祖辈所崇拜的神明并没有投入太多的关注。他们之所以每年还要定期几次到神庙敬拜,只是为了遵从既有的习俗而已,并非出于信仰。在人们为了庆祝某个大型的宗教节日而进行列队游行的时候,他们几乎不会参与其中,总是作为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存在。他们认为,罗马人的崇拜是幼稚滑稽的事情,无论是朱庇特(众神之王)、密涅瓦(智慧女神),还是尼普顿(海神)都一样,不过是共和国创立之初的遗产罢了。对于一个研究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其他杰出雅典哲学家著述的智者来说,这些根本不登大雅之堂。
基于此,罗马人对于宗教信仰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政策。政府规定,国家所有公民,包括罗马人、居住在罗马的外国人以及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人、巴比伦人、犹太人等,必须向神庙中设立的皇帝像表示应有的尊重。这样的规定和美国人向邮局中悬挂着的总统画像行注目礼是同样的概念,没有深层次的含义,仅是一个形式而已。在罗马,每一个公民都有权按其喜好去赞颂、崇敬、爱慕任何一个神,于是,罗马建起各种各样不同的庙宇和教堂,那里供奉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神明,甚至埃及的、非洲的、亚洲的神也可以随处看见。

信仰的转变
最早的耶稣追随者们同其他派别的传教士一样,在信奉自由与宗教宽容的罗马锲

当首个耶稣的追随者来到罗马,四处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新鲜教义时,不仅没有遭到大家的反对,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好奇的人前来聆听。罗马作为强盛帝国的中心,这里不断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传教士,他们每个人都在向罗马公民传述着他们的“神秘之道”。自封的传道者们向人们大声诉说新教义,他们说出了无限美好的未来和欢喜,告诉人们如果跟随他所信仰的神即可以拥有这一切。
一段时间后,那些聆听过“信仰基督教的人”(意为耶稣的追随者或被上帝涂抹了膏油进行祝福的人)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们所讲的东西自己竟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人不关心拥有多少财富,不关心拥有多高的地位,他们却大大赞颂贫穷、谦卑、顺从的美德。但是,罗马帝国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恰好不是借助这些品德。当帝国正处在欣欣向荣的时期,竟然有人跑过来告诉他们,世俗的拥有并不代表他们可以永远幸福,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此外,基督教传教士们还说过更加恐怖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要拒绝聆听真神的言论,那么他未来的命运将是无比凄惨的。很明显的,如果人们对此心存侥幸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当然,在不远处的神庙中,罗马的旧神还依旧存在着,但是,他们的力量够强大吗?他们可以抵御得了从遥远亚洲传播过来的新上帝的权威吗?人们越想越害怕,心中的疑惑也就越来越多。然后,他们为了加深对教义条款的理解,纷纷来到信仰基督教的人传教的场所。没过多久,他们和传播基督福音的男男女女们有了更深入的接触,结果他们发现这些人和罗马僧侣大相径庭。这些人全都穿着破烂的衣服,他们关爱奴隶和动物,他们对钱财没有任何的欲望,反而帮助更加穷苦的人们。罗马人被这样无私无畏的品质打动了,他们开始纷纷抛弃原有信仰,成为了信仰基督教的一员,罗马的庙宇变得异常冷清,而私人住宅的密室或露天田野却不断有信仰基督教的人们的聚会召开。

冲突与惨剧
羽翼渐丰的基督教逐步确立了其在罗马帝国的权威地位,促使罗马政府不得不重

时间一年年地悄然流逝,传教工作在继续进行着,信仰基督教的人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他们推选出神父或长老(“Presbyters”,希腊语中的意思是“老年人”),来担任保护社团利益的负责人。每一个行省的所有社团还会推选出一位统领全区基督教事务的主教。彼得是继保罗之后来罗马传教的基督教派信仰者,他很荣幸地成为了第一任罗马主教。当发展到某个阶段,彼得的继任者(被追随者尊敬地称呼为“父亲”或“爸爸”)进而开始被人们称作“教皇”。
由犹太人底层民众流行的秘密教派到罗马帝国认可并推行的国教,基督教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般的蜕变。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与对王权的靠拢让基督教最终与帝国政权结为一体。

教会逐渐发展成为罗马帝国中集影响力和权势于一身的复杂机构。基督教义不仅对那些在现实世界中感到绝望的人有着感召力,同时,也吸引了那些在帝国政府中无法实现自己抱负和理想的有才能的人。这些人的能力在耶稣追随者中得以充分地施展。基督教的逐步强大,让帝国政府不得不对其格外重视。我们前面说过,罗马对于宗教还是比较宽容的,它允许人们追求自己喜欢的宗教,但是,前提是一切宗教必须和平相处,“自己生存,也让别人生存”是基本准则。
然而,基督教社团却不能拥有宽容其他宗教的胸怀,他们认为自己信奉的上帝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真正主宰,其他的神都不过是招摇撞骗的骗子而已。而对于其他宗教来说,这样的言论显然是非常刺耳的,于是帝国警察出面要求禁止这样的言行,但是信仰基督教的人们并没有改正。

康士坦丁的梦境
罗马附近的米尔维亚桥战役一触即发,愁苦难眠的康士坦丁大

不久之后,更大的问题出现了。信仰基督教的人们不愿意向罗马皇帝施行表达敬意的礼仪,也不愿意去服兵役。政府扬言要重重惩罚他们,但是,他们却不以为然,他们说这个悲惨的世界不过是他们进入天堂乐土的“通道”而已,即使丧失现世的生命,也绝不背弃自己的信仰。对于这样的言行,罗马人显然是无法充分理解的,他们只能任其所为,偶尔将出现的几个敢于反抗的信仰基督教的人杀死。在基督教会成立的早期,有一些暴民对基督教追随者施行过私刑,将其杀害了,但是政府却没有这样做过。暴民们将一些子虚乌有的罪名加在顺从的基督教信仰者身上,而且罪名五花八门,例如杀人、吃婴儿、散布疾病和瘟疫、危难时刻出卖国家等。暴民们很容易就将信仰基督教的人处死了,他们压根不怕有人报复自己,因为他们很了解这些信仰基督教的人,他们只会以德报怨。
此时,周边蛮族对罗马的骚扰不胜其烦。在罗马军队动用武力也无法解决问题时,基督传教士挺身而出,来到了野蛮的条顿人面前,开始对他们宣讲和平福音。这些人是意志坚定的信仰者,他们不畏生死、沉着冷静,他们将不知悔改的人在来世地狱中悲惨的情景描绘得有声有色,因此,条顿人从内心深处感到了恐惧。这些野蛮人一直对古罗马的智慧抱有敬畏之情,他们认为这些人来自罗马,恐怕讲的都是事实。因此,基督传教团在条顿人和法兰克人居住的蛮荒之地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六个传教士相当于整整一个罗马军团的威力。此时,罗马皇帝终于开始重视基督教,他觉得基督教对于帝国应当是大有裨益的。所以,在一些行省中,基督教信仰者拥有了和信仰古老宗教的人们一样的权力。但是,在4世纪下半叶仍出现了本质上的颠覆。
康士坦丁是当时在位的皇帝,有的时候,大家也会称呼他为康士坦丁大帝(没人知道如此称呼他的真正缘由)。此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暴君,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仁慈的皇帝是很难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存活下去的。康士坦丁的一生算是比较坎坷的,有着无数次的起起落落。有一次,强大的敌人几乎就要将他打败了。这时,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想要借用一下这个亚洲的新上帝的威力。他发誓说,假如他能够在下一场战役中取得胜利,那么,他就信仰基督教。结果,他真的大获全胜。于是,康士坦丁开始相信上帝的权威,并且接受洗礼成为了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
从此,罗马官方正式接受基督教,这使得基督教在罗马的地位更加稳固了。
但是,相对于罗马的总人数来说,信仰基督教的人员总数所占比例依旧是较少的,大约只有5%~6%而已。基督教的终极目标是使全民信仰上帝,所以,它丝毫不让半步。他们认为基督教的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唯一主宰,所以,众多其他的旧神都必须被毁掉。当朱利安担任皇帝的时候,因为他是希腊智慧的热衷者,所以极力保护异教的神祇免受摧毁。但是,不幸的是,他很快就在征讨波斯的战争中阵亡了。接着,由朱维安继任皇帝之位,他将基督教的权威重新竖起,于是那些古老的庙宇接二连三地关门闭户。再后来,查士丁尼皇帝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了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将柏拉图一手创立的雅典哲学学院彻底解散。
这一举动意味着古希腊世界的彻底消亡,在新的世界里,人们充分享受着思考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意志构建未来。当世界到处充满着野蛮和愚昧的洪流,陈旧的秩序分崩离析。人生如在波涛起伏的大河中寻找航向的小船,古希腊哲学家微妙的准则似乎难以给人们指引一条明确的方向。抛掉这些不适用的东西,人们需要的是一个积极明确的指引,而教会恰好可以满足这些要求。

教皇格利高里
教会内部如同一个大家庭,教皇在拉丁语中有

这个时代,是一个万事飘摇的时代,任何事情都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教会却不是,它像岩石一般屹立不倒,它不会因为危险而退缩,也不会根据情况而改变,它总是坚持真理和神圣的准则。这样的毅力不仅加深了群众对其的敬仰,也使它从那些可导致罗马帝国覆灭的灾难中平稳度过。
当然,不得不说,基督教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也包含着一定的侥幸成分。5世纪时,当西奥多里克在罗马建立的哥特王国灭亡后,意大利的外来侵扰相对缓和了许多。之后担任意大利统治者的伦巴德人、撒克逊人和斯拉夫人则是一些没有强横实力的落后民族。罗马主教之所以能够维持城市的独立自主,完全得益于宽松的政局。没过多久,罗马大公(既罗马主教)就被意大利半岛上分布的诸多残余小国奉为政治和精神上的绝对主宰。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此时,只需一位强大的王者出来统治即可。因此,格利高里横空出世。格利高里出身于旧罗马的贵族统治阶层,在公元590年登上历史舞台。他曾担任“完美者”,即罗马市的市长;然后成为了僧侣,最后当上了主教。尽管他本人想做一位传教士,将基督的福音传到蛮荒的英格兰去,但还是被人强行带到了圣彼得大教堂,成为了教皇。在短短的任职14年间,他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基督教会领袖,直至他去世,整个西欧的基督教世界都已经正式承认了罗马教皇的地位。
但是,罗马教皇的权威也仅仅局限在西欧,并未扩展到东罗马帝国。位于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实行的依旧是旧传统,政府的最高统治者和国教领袖还是奥古斯都和提庇留的继任者(即东罗马皇帝)。1453年,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人的长期围困下最终沦陷,东罗马最后一位皇帝康士坦丁·帕利奥洛格被土耳其士兵杀死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台阶上。
在发生这一幕的几年前,帕利奥洛格的弟弟托马斯之女左伊公主同俄国的伊凡三世喜结良缘。由此,君士坦丁堡传统的继承人就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莫斯科大公。现代俄罗斯的盾形徽章中就加入了古老的拜占廷双鹰标志(为了纪念罗马被分为东西罗马而设立的),而曾经仅仅为俄国第一贵族的大公有了一个新身份——沙皇。他开始居于所有臣民之上,拥有和罗马皇帝一样高高在上的权威,不管是贵族还是农奴,在他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
沙皇建造的宫殿为东罗马皇帝从亚洲和埃及引入的东方风格,外观和亚历山大大帝的王宫极其相似(依照他们对自我的奉承)。这个由行将入土的拜占廷帝国留下的奇特遗产,赠予给了它完全不确定的世界,并且在前俄国宽广无垠的大草原上蓬勃发展,延续了长达600年的时间。沙皇尼古拉二世是最后一个享受这份殊荣的人,也是最后一个佩戴拜占廷双鹰标志皇冠的人。确切地说,他在不久之前才和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们一并被杀身亡,尸体被扔进了一口井中。随着他一同殉葬的,还有那些古老的特权,教会的地位又重新回到了康士坦丁皇帝之前的样子,与罗马的教会地位毫无差别。
但是,在下一章我将说到,西方教会的命运则完全不同。一个来自阿拉伯放牧骆驼的先知,他所宣讲的教义给整个基督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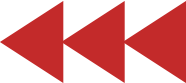
赶骆驼的穆罕默德成为了阿拉伯沙漠中的先知,他的追随者为了唯一真神安拉的荣耀,几乎将整个世界征服了。
讲述过迦太基和汉尼拔之后,关于强盛的闪米特族的事情我就没有再提及了。假如你还记得,你应当能想起前面章节中所叙述的关于他们在古代的事迹。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犹太人、阿拉米尔人、迦勒底人都是闪米特族的一分子,他们曾经统治西亚长达三四千年。后来,来自东边的印欧语族波斯人和来自西面的印欧种族希腊人打败了他们,从此他们失去了统领一切的权力和地位。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100年后,非洲殖民地迦太基城的腓尼基人为争夺地中海的霸主与罗马人展开恶战。最后,迦太基战败灭亡。罗马人统领世界长达800年之久。

大天使迦伯列
大天使迦伯列常以神的追随者形象出现,亦被

到了7世纪,闪米特的另一个部族再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并且对西方世界的权威造成了威胁。他们隶属于阿拉伯沙漠中的游牧部落,也就是天性温顺的阿拉伯人。起初,他们只是平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并没有任何称霸的企图。后来,在默罕默德的带领和感化下,他们开始跨上战马远征他国。在不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阿拉伯骑兵就已经深入到了欧洲的腹地,那些法兰克的农民面对这些强悍的敌人,只能颤颤巍巍地听着他们宣讲“唯一的真神安拉”的荣耀和“安拉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教条。
阿哈默德是阿布达拉和阿米娜的儿子,人们称其为“穆罕默德”,意为“应当赞美的人”。关于他的故事就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一样充满传奇。他出生于麦加,原本是一个赶骆驼的行商者,他似乎还有癫痫病,每当发病的时候就会昏迷过去。这时,他总会做一些奇怪的梦,在梦里他总是能听到大天使迦伯列的讲话,这些话在《古兰经》中都有记载。穆罕默德因为是商队的首领,所以他几乎到过阿拉伯的各个地方,和犹太人、信仰基督教的商人有过很多接触。时间久了,穆罕默德发现仅崇拜唯一的上帝是有很多好处的。要知道,当时的阿拉伯人仍尊崇祖先的教诲,膜拜奇怪的石头或树干。在伊斯兰圣城麦加至今还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方形神殿,其中就安置着受世人膜拜的偶像与伏都教供奉的奇特遗迹。
穆罕默德下定决心要当阿拉伯人的摩西,成为先知和领导者。一个赶骆驼的先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于是他娶了一个有钱的寡妇为妻,也就是他的雇主赫蒂彻,由此他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得以开展传教工作。他先是向自己的邻居们宣称,他是人们朝思暮想的由真主安拉派遣来拯救世界的先知。对于他的言论,邻居们非但不相信,反倒大声讽刺他。即使这样,穆罕默德也不灰心,继续做着自己的传道工作。终于,邻居们不再容忍他了,并决定试图杀死他,以摆脱这个让人生厌的疯子和异类。而得知消息的穆罕默德和他最忠诚的学生阿布·伯克尔连夜逃往麦地那。这次发生在公元622年的逃亡事件,成为了伊斯兰教史上的大事,伊斯兰教将那一年设为了穆斯林的纪元。
在麦加城里,穆罕默德在人们心中就是一个赶骆驼的商人,但是在麦地那,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所以人们对于他的传道事业并不反感,由此,传道事业开始出现转机。没过多长时间,穆罕默德的身边就围绕了很多的追随者,他们被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神旨”的信仰者。在穆罕默德那里,顺从神旨就是人值得赞赏的最高品质。穆斯林的队伍不断壮大,穆罕默德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来征讨那些嘲笑过他的人了。他带领一支麦地那军队,气势磅礴地穿过沙漠,麦加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他占领了。他将当地的很多居民杀死,由此,其他人就对他先知的地位更加深信不疑了。
从此,直至穆罕默德死去,他都没有遇到任何阻碍与困扰。
伊斯兰教成功崛起的原因很简单,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穆罕默德提出的宗教教义简单明了。凡是伊斯兰的追随者,都必须要热爱世界的主宰,热爱那位仁慈强大的神——安拉。追随者要尊敬父母,听从父母的命令。在和邻居相处的时候,不能随意蒙骗邻居。个人提倡谦虚温和,对待穷人和病人要仁厚、有礼。此外,不允许饮酒,以简朴为要,仅此而已,教义就是这么简单。伊斯兰教中没有类似于基督教中“看守羊群的牧人”那样的角色,也就没有了需要人们慷慨解囊、始终供奉的主教。在清真寺,即穆斯林的教堂,建筑风格也是极尽朴素,在石头垒砌的大厅中,没有长椅板凳,更没有画像。追随者们可以随意聚集在这里(依照自己的意愿),讨论或者阅读《古兰经》。对于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们来说,那些谨记的教条和戒律并没有对他们有太过的束缚。每天,他们都会面对着圣城麦加的方向,做五次简单的礼拜祷告。除此以外,他们任凭安拉的意志来掌控这个世界,乐观而顺从,听任命运的安排。
这种对生活的态度,可以让他们的内心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满足,但也不会出现什么发明电动机、修筑铁路或开发新航线等等的事情。它让穆斯林们变得心态平和,友善地与他所处的世界相处,这固然也是件不错的事情。

阿拉伯王子的晚餐
优雅的池塘边,衣饰华贵的王子倚坐在矮树旁

穆斯林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的战士和信仰基督教的人展开对战是为了实现信仰。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过,只要是在战场上勇敢抗击敌人,战死沙场的人,就能够直接进入天堂。和突然死于战场相比,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痛苦地生存,似乎前者更让人愿意接受。穆斯林有了这种信念,在同十字军对战时,在心理上就占据了极强的优势。十字军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境界,他们生活本身长期处于对黑暗来世的惶恐中,这让他们对于今生的美好享受更在乎一些。从这一点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为何时至今日穆斯林士兵依然可以毫不畏惧地奔向战场,压根对被杀死的危险毫不在意。也正是如此,对于欧洲来说,他们仍是危险而强大的敌人。
随着伊斯兰的发展,穆罕默德也被公认为众多阿拉伯部落的领袖,同时,他也拥有了极大的权力。当伊斯兰教的根基稳固之后,他便可以行使这些权力,尽管这种成功时常成为从逆境走出的伟人无法逾越的泥潭。他为了得到富人阶层的支持,还会特别制定一些为富人服务的规定,例如追随者可以娶四房妻子。那时候,妻子一般都是男方从女子父母手中购买过来的。娶妻是一项昂贵的投资,而娶四房妻子的奢侈想法除了那些拥有单峰驼和椰枣园的富翁以外,普通人家基本连想都不敢想。伊斯兰教创立的本意,是为了服务大漠中的劳苦牧人,但是如今却为了迎合城市集贸中的富户而不断改变。可以说,这样的改变对穆罕默德的宏伟事业没有什么益处,也有违初衷。先知本人则依旧辛苦工作,每天向他人传道、颁布新规定等,直到公元632年6月7日,穆罕默德患上热病突然离世为止。
继承穆罕默德位置的人被称为哈里发,意思为“穆斯林的领袖”。第一个继任者是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艾克尔,他曾经和穆罕默德并肩作战,共同经历了最初最困难的时期。两年后,阿布·艾克尔去世,奥玛尔接管重任。他继承领袖位置之后不到10年,就率领军队相继征服了埃及、波斯、腓尼基、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方,并建立了第一个伊斯兰帝国,定都于大马士革。
奥玛尔死后,哈里发的位置由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丈夫阿里担任,不久,阿里在一场关于伊斯兰教义的争吵中被人谋杀了。此后,伊斯兰国家就成为了世袭制度,原先的宗教领袖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强盛帝国的统治者。他们将新的首都建立在幼发拉底河岸附近、距离巴比伦遗址不远的地方,新城命名为巴格达。原先的阿拉伯牧民变成了无敌的骑兵兵团,出发到远方,将穆罕默德的福音传播给异教世界。公元700年,穆斯林将军泰里克翻过赫尔克里斯门,抵达充满峻峭山崖的欧洲海岸。他将那里命名为直布尔阿尔塔里克,也就是泰里克山或直布罗陀。
11年后,在泽克勒斯战役中,西哥特国王在和泰里克的对战中失败。接着,穆斯林继续向北推进,他们沿着当年汉尼拔进攻罗马的路线,翻越了比利牛斯山的山隘。在波尔多附近,穆斯林军队遭到了阿奎塔尼亚大公的袭击,不过,后者并未得手。穆斯林经此一役后继续向北,他们下一步想要夺取巴黎。但是穆罕默德逝世100年的时候,即公元732年,欧亚双方在图尔和普瓦捷展开了大战,穆斯林终尝战败的苦果。法兰克人的首领查理·马泰尔(绰号铁锤查理)赶走了穆斯林,挽救了欧洲,彻底熄灭了穆斯林企图征服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梦想。但是,被赶出法兰西的穆斯林仍控制着西班牙。阿布德·艾尔·拉赫曼在西班牙建立了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后来这里成为了中世纪欧洲科技与艺术的胜地。
这个掌控西班牙的摩尔王国延续了整整7个世纪,“摩尔王国”的名称源自那里的人来自于摩洛哥的毛里塔尼亚地区。直到1492年,欧洲最后一个穆斯林堡垒格拉纳达沦陷,西班牙人才恢复了自由。然后,西班牙皇室才委派哥伦布出发航行探险,揭开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没过多久,穆斯林再次集合兵力,征服了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迄今为止,世界上伊斯兰教信仰者和基督教追随者的数量并没有太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