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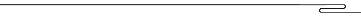
进入中医学院之后,深感理论知识欠缺的我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学习机会,不仅全面系统地学习了中西医学知识,而且在课余“帮老师干活”。担任既是学生又是老师的双重角色,遇到一些实践课程,老师因我有近6年的临床经历,经常让我给同学们补西医课。经过对理论知识的系统学习,对实践中那些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西医基础知识一一有了答案,但对中医的认识凭借在基层医院的粗浅经历只知道能治病,对其理论却不入门甚至抱有怀疑态度,在学到“肺主气司呼吸”等与西医学类同的知识还能接受,但遇“脾主运化”等反差较大的理论就感到费解,尤其认为科学已发展到原子、质子时代,怎么还在讲阴阳五行呢?思想陷入苦恼而混乱的状态,曾一度想退学,打算再改学西医。
中医学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当时学校经常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看病,可谓“开门办学”。在此间我有幸跟随石冠卿、赵清理、张磊、尚炽昌等中医学院著名教授参与了下乡巡回医疗队。在为当地农民看病的过程中,发现中医确实能为病人解决实际问题,一个个典型有效的病例使我对中医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和全新的认识,就在这种边学习边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喜欢上了中医并成为中医的虔诚信徒。
毕业后,我留在了河南中医学院(现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从事中医临床工作,曾经与国内省内著名中医、中西医儿科专家李晏龄、黄明志、苗培显、郑建民、高智铭、张子萍、范忠纯等老师朝夕相处数十年,在他(她)们的亲自指导下查房、出门诊、走上讲台并参与科研,他(她)们把精湛的技术、丰富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我,使我较快领略并掌握了辨证施治的基本思路与方法,积累了诊治儿科疾病的初步经验。为日后成为儿科学术骨干奠定了基础。
80年代末,已有20年临床工作经历的我因深受领导和患者好评,成为我院当年最年轻的科室副主任,1990年以后学院及医院又相继任命我为儿科研究所所长、儿科教研室主任、儿科医院院长。通过“擂台”选拔,成为河南中医学院儿科学科带头人,全面负责河南中医学院儿科研究所、儿科教研室、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临床的医教研工作。后先后又成为中华医学会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副会长,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儿科分会副会长,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儿科全国协作组大组长,河南省中医儿科、中西医结合儿科学会主任委员。2015年又成为中华民族医药学会儿科分会会长……这一个个不同角色的转换,一个个有分量的学术职务,是多年来身边多位老前辈支持的结果,也与全国中医儿科学会张奇文、王烈、汪受传、马融等会长的帮助分不开。这些汗水的结晶,似乎是荣誉,更是压力和动力,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学科带头人,应把自己团队的学术带领到全国领先水平;作为一名导师,应深受学生的爱戴;作为一名中医儿科名医,应对小儿常见病和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治具有丰富实战经验。我怀着这些理念坚定地去努力,并持之以恒。
我于1974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深感自己知识储备不足,曾一度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多年来,我始终以“勤能补拙”为信条,激励自己树立信心,拼搏上进。除“勤”之外,“恒”字是很重要的,无论书本知识或临床经验,均重在积累,由少到多,由易到难,一点一滴,日积月累,聚涓滴而成江河。在留校后的前五年中,我先后参加了大学举办的青年教师中医基础理论提高班、河南省中医管理局举办的中医师经典进修班、教育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举办的全国中医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进修班、全国中医儿科首届高级师资班等,系统学习了中医四大经典及中医儿科经典著作。无论临床、家务如何繁忙,我总要挤时间完成学习任务,并数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此外,日后有幸拜识了国医大师王烈,还有张奇文、汪受传、俞景茂、马融等国内儿科知名大专家,他们潜心杏林、精勤不倦、博极医源、矢志不移的风范感染了我,尤其在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汪受传教授主编的多部国家规划教材、参与他主持的“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以及制定儿科疾病临床诊疗指南的过程中,他厚重的理论沉淀、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杰出的教学与科研成就使我受益颇深。在参与马融教授领导的儿童用药及新药创制等过程中,他超前的创新及宏观管理驾驭能力使我受益匪浅。实事求是地说,在步入中医大门的十余年后,源于以上各种因素,我才逐渐触及到中医的文化及学术脉络,感悟出中医的博大精深。
“将升岱岳,非径奚为,欲诣扶桑,无舟莫适”,要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才干和本领,成为一个优秀的临床医生,需要正确的方法,即实践、思考和知识相结合。知识很重要,但知识不等于才能,知识只能在实践和思考中运用,并融会贯通,方可转化为才能。留校工作以来,我始终把实践放在第一位,工作在临床、教学第一线。临床工作确实十分辛苦,常加班加点,退职前几乎未曾享受过寒暑假,节假日大部分也被占用,但我却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锻炼,不但临床上能独当一面,且为较好地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使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是每一个中医人面临的挑战。我个人之见,除要有坚实的中医理论及丰富的临证经验外,也应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中医和西医的思维模式尽管不一致,但有其共同的研究对象和价值标准,共同的学科属性和发展方向,在这种前提和基础上,当一种医学不能圆满解决医、教、研中的全部问题时,两者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是非常有益的。也正是这种理念,造就了我日后带领团队在采用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解决疑难疾病方面,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跟上了时代,也促进了河南中医儿科临床专科、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