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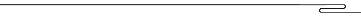
我出生于江苏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外语教师,系民国时期上海同济大学毕业生,典型的“老学究”;母亲是医生,性格开朗,吃苦耐劳。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响应国家号召,我们举家迁到河南。父亲教书,母亲做医生,一家人过着平静的生活。随着1957年全国“反右”运动的爆发,生性耿直的父亲因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而被打成了“右派”,年幼的我遂成了“右派子女”。1965年我初中毕业以优异成绩顺利考上省重点高中,后因当年“家庭出身不好无望上大学”的政治环境,加上家境困窘,为获得每月十元钱补贴,母亲做主让我转到卫校。上卫校一年半,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基础课刚学完,因史无前例的“文革”波及学校而停课,我随即成为“黑五类”。更因在校成绩名列前茅,年仅15岁的我竟被同学因嫉妒而写了一张“走白专道路、不问政治的资产阶级小姐”的大字报。在这种境遇下成长起来的我,继承了父亲生性执着和母亲吃苦耐劳的特点,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课余还常干家务活,虽在家排行老三却被称为“管家婆”,深得父母信任。
1968年,我卫校毕业被分配到林县河顺公社医院(现今的乡医院)。因性格开朗、勤快,眼里有活,看病、帮老中医抄方、抓中药甚至连炮制中药、制剂、护士打针的活儿也抢着干,很快就博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第二年就送我去当时已具有相当规模且已成全国典范的林县人民医院进修,期间适逢国家医疗队来县医院开展早期食管癌普查暨手术工作,由于人手短缺,且我表现突出,即把我留在县医院,这一干就是2年。在这2年中,我有幸先后与国家医疗队(由北京协和医院、阜外医院的医生组成)、河南省医疗队的老一代诸多专家朝夕相处一起工作,这些专家如胸外科邵令方、张汝刚、刘方圆、梁遵时,病理专家沈琼等后来大多成为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他们对医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1971年,全国大中专院校学生再分配之际,我调入安阳龙山化肥厂职工医院做临床医生。医院小分科不明,从内科到外科,从西医到中医,身兼多职,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医院领导和同事都对我这个“爱干活”的小姑娘印象非常好。1973年,邓小平同志二次复出,国家实施了“文革”以来首次以推荐为基础的大学升学考试。为圆曾经的大学梦,我报名参加了高考,成绩在安阳地区200多名考生中位列第二。不曾想发生“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后,国家传出了“此次高考无效”的消息,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幸运的是,1974年,单位领导和同事再次一致推荐我上大学,我因此很荣幸地进入了河南中医学院中医系学习,成为“工农牌”大学生,从此改变了人生的发展方向,与中医儿科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