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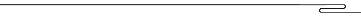
肾病总属中医“水肿”范畴,其病程较长,病机及临床表现复杂多变。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肾为先天之本。脾阳根于肾阳,脾健运、化生,须借助肾阳“温煦”,而肾中精气亦有赖水谷精微滋养、充润。它们相互资助,互为因果,脾阳虚可损及肾阳,致脾肾阳虚。可谓脾胃虚弱,诸症蜂起,因此从脾胃论治是治疗肾病的重要环节。
病位在肺脾肾,重点在脾肾。脾胃居中焦,为人体气机升降及水液代谢之枢纽。脾主运化水液并升清和输布精微物质。若脾失健运,升降失常,一则水液泛滥而为水肿,二则清气不升,精微不能归藏而下泄,成为尿蛋白。故脾胃失调与慢性肾病密切相关。如《素问·经脉别论》所言:“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若肺脾肾三脏虚弱,功能失常,必然导致“水精四布”的功能失调。水液输布失常,泛滥肌肤则发为水肿;精微不能输布、封藏而下泄则出现蛋白尿。
人体的气血津液的化生,有赖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在运化水谷、水液的过程中,胃主收纳、脾主运化,故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在此过程中,又依赖脾肾之阳推动脾气的上升、四散和温煦。《景岳全书·杂证谟·肿胀》提出:“凡水肿等证,乃肺脾肾三脏相干之病,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今肺虚则气不化精而化水,脾虚则土不制水而反克,肾虚则水无所主而妄行。”明确指出了本病以肾为本,以肺为标,而脾为制水之脏,三脏之间相互联系同时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本病病机属性为本虚标实。肾病的病程长,虽其病因涉及内伤、外感,病理责之于脏腑、气血、阴阳,但其病机属性却是一致的,均以正气虚弱为本,邪实蕴郁为标,属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病证。正虚是指气虚、阳虚、阴虚或气阴两虚,结合脏腑又可分为肺脾气虚、脾肾阳虚、脾肾之气阴两虚、肝肾阴虚等,此为肾病病机变化之关键,故为本;邪实是指外感及水湿、湿热、瘀血及湿浊等病理产物,故为标。
概括肾病的病情演变,初期及恢复期多以脾阳虚、脾气虚为主,难治病例,病久不愈或反复发作或长期使用激素者,可由阳虚转化为脾肾阴阳两虚或肝肾阴虚。而阳虚(尤其是脾肾阳虚)乃病情演变之本始。如本病早期或未用激素治疗之前,多表现为浮肿明显、面色苍白、畏寒肢冷、乏力纳差、腹胀便溏、舌质淡胖、苔白或白腻、脉沉无力等症,此属脾阳虚或脾肾阳虚所致。患病日久,尤其在使用足量激素以后,患儿出现面色潮红、盗汗、烦躁易怒、头痛眩晕、手足心热、舌红少苔、脉细数等症,则属阴虚,此多为病久不愈,阳损及阴;或激素助阳生热,或湿热郁久,热盛伤阴致肝肾阴虚所致。
在临床常见的五个分型中,与脾相关的证候占四个。有报道分析诊治小儿肾病437例,与脾相关的证候(脾虚湿盛、脾肾气虚、脾肾阳虚、脾肾气阴两虚)401例,占91.8%。
脾肾之实证经治疗,实邪渐去而出现脾胃虚弱之象,脾胃虚弱(气阴两虚)证持续时间较久。往往以乏力倦怠、纳少等症为主,甚至贯穿于肾病之始终。
如顽固性重症水肿,以腹水甚,屡用利尿无效为特征,用中药益气行气利水之剂(属湿热者以中满分消饮化裁,属寒湿者用中满分消汤加减)每获良效。再如尿蛋白屡治不消,用益气养阴兼清热利湿法,或补气健脾、益胃升阳法常可收功。
如益气活血、益气利湿、益气解毒等,较单纯活血利湿、解毒法疗效更佳。
小儿肾病多有水肿表现,临证常在辨证和辨病基础上根据水肿程度分期论治:①水肿期:多见于肾病的初期或病重期,水肿较甚(激素治疗前),临床常以脾虚湿困、脾肾阳虚表现为主,多兼标实表现(风邪、水湿、血瘀、气滞),治以温阳健脾化湿利水为主,兼以祛邪。②水肿消退期:多见于肾病的中后期(激素治疗的诱导期,减量巩固期),临床表现以肝肾阴虚、脾肾气虚、脾肾阳虚为主。肝肾阴虚,治以补益肝肾,滋阴清火;脾肾气虚或脾肾阳虚,治以健脾益肾或温补脾肾。
①激素诱导期,指足量[2mg/(kg·d)×4周]至激素减至半量之前的激素治疗期,临床常表现为肝肾阴虚,阴虚火旺,治宜滋补肾阴为主,兼以清热;②激素撤减期,指激素减至中等剂量[1mg/(kg·d)]以下或隔日服时,患儿常出现食欲下降等脾肾气虚症状,此期多采用健脾益肾的治法;③激素停药期,在激素减至维持量[0.5mg/(kg·qod)]或停药时,患者常阳虚症状明显,此期宜温补脾肾。
①大量蛋白尿期,多在复发期的水肿期,治宜扶正祛邪,扶正重在健脾益肾(重用参芪),祛邪重在疏风、清热、利湿、活血。②少量蛋白尿缠绵期,多见于难治性肾病患儿(激素耐药或激素依赖),治疗仍重在健脾益肾,佐以活血化瘀。③尿蛋白转阴期,多为恢复期和缓解期患儿,治疗重在健脾益肾。
董廷瑶教授认为:小儿肾病应属“阴水”“风湿肿”的范畴,常因禀赋不足、久病体虚、外邪入里等所致,其病理变化在肺脾肾三脏,而重点在脾肾。辨证重在识别本证与标证,权衡孰轻孰重,辨证上基本将其分为以下三型。
(1)肾虚湿滞型:因肾主水,肾虚气不化水,湿邪内滞,以致水溢肌肤而发病。症见患儿肢体浮肿,尿少便溏,面色萎黄,神倦乏力,纳呆,舌质淡,苔白滑,脉濡细。
(2)脾肾阳虚型:肾为水脏,主气化而利小便,脾属土,为制水之脏,素体脾肾不足或久病损伤脾肾阳气,则气不化水,水湿泛滥而起水肿。症见患儿明显水肿,按之凹陷不起,可伴胸水、腹水,形寒肢冷,面色㿠白或灰晦,时有恶心呕吐,便溏,舌体胖边有齿印,质淡,苔白,脉沉细无力。
(3)肾阴虚亏型:小儿属稚阴稚阳之体,肾精未充,久病后,肾阴亏耗,肾失其养,则肾气渐弱,气化失司,发生水肿。症见患儿水肿,头痛头晕,五心烦热,面色潮红,腰酸腿软,舌质红,少苔或剥苔,脉细数。
董老认为,在治疗上应紧扣“本元虚怯,脾肾两亏,而水湿泛滥之本虚标实”的病机,以扶正培本为主,重在益气健脾补肾,同时配合祛邪之法以治其标。治疗本病的关键在于根据虚实及标本缓急,确定扶正与祛邪的多寡。
李少川教授认为:脾虚湿困为小儿肾病的基本类型,症见面色㿠白无华,全身水肿,按之没指,小便短少,身体困重,胸闷,纳呆,泛恶,苔白腻,脉沉缓,起病较缓慢,病程较长。其发病机理由于小儿多为“脾常不足”之体,每多饮食不节,寒温失调以伤脾气而不能化湿,或外湿浸渍,脾受湿困而失其升降之职致三焦气化失司,脾病不能制水则下注乘肾,肾失开阖之用而出现水肿、蛋白尿、血浆蛋白低下等症。从临床所见小儿肾病发病的全过程来看,除去继发感染和长期服用激素的患儿外,病例可见面色㿠白无华、浮肿明显、精神倦怠等脾虚湿困之象,证明了“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的论述。
此外李老认为:小儿肾病之发,固然与肺、脾、肾三脏均有关系,但以脾气不足,脾胃升降枢机失其运化,脾虚湿困为其主要病机。依据脾虚湿困这一基本病机,提出“肾病治脾”的观点,在实际遣方用药之中,又依“脾虚应健不应壅补,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之训,采用健脾利湿这一治则,采用以胃苓汤为主化裁的小儿肾病合剂:方中太子参、白术、云苓、川朴、枳壳、甘草,以健运中宫,借其香燥疏化,祛湿化浊;苏梗叶辛温开腠以发其汗,重用葫芦、泽泻甘淡渗湿以利小便,又以知母、麦冬、黄精等药顾护里阴;以上诸药共奏健脾利湿、燥润相济之功,贯穿治疗肾病整个过程,但可根据不同证型,随证加减。
肾病患儿每因感受外邪、水湿、湿热、使湿邪困阻中焦,升降失司、统摄失职,导致肾病急性发作,症见蛋白尿、血尿复发或加重,周身浮肿(或有胸腹水),尿少等,此刻在辨证利水消肿的同时,即使无脾胃症状,也应于大剂量利水剂中伍以黄芪、党参、茯苓、白术等健脾益气之品,以利水祛邪而不伤正,调中扶正而不碍邪为度。
由于脾虚贯穿于肾病发生发展的慢性演变过程中,故补脾治本之法也应坚持始终,调补脾胃不仅有摄血、止尿蛋白之功,且有增强免疫、升高血浆蛋白、改善机体功能之妙。调补之法,常用益气健脾、温补脾阳、升阳举陷、益气养阴的方剂如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等。且在其他疗法中每伍以益气健脾之品可提高疗效。
肾病屡经中西药治疗,临床表现多以蛋白尿、血尿为主,常无其他明显症状。对于无症可辨,除了从舌脉上下功夫并结合实验室检查外,多从脾胃论治。每用益气养阴兼清利湿热法,或补气健脾益胃升阳法而取效。
肾病初愈或初获缓解,尿检阴性,或尿蛋白极微量,或见少许红细胞,不宜过早停药,主张继用益气健脾养阴之品,并少佐清热利湿之药,以培补脾胃,补中寓通,巩固疗效。
常用药物为黄芪、党参、白术、薏苡仁、麦冬、白花蛇舌草、益母草、甘草等。同时注意饮食起居有节,渐使胃气旺盛,以防肾病复发。另常酌加生熟地、菟丝子、桑寄生、山茱萸等益肾之品,以益肾有利于培土。临床治疗此类案例甚多,不再枚举。
综上可见,调理脾胃在肾病治疗中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