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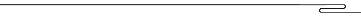
肾病综合征是一组由多种病因引起的临床症候群。以大量蛋白尿、低蛋白血症、高脂血症及不同程度的水肿为主要特征。其病程长,发病率高。本病属于中医学“水肿”范畴。本病病机以正气虚弱为本,邪实蕴郁为标,属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病证。正虚是指气虚、阳虚、阴虚或气阴两虚,结合脏腑又可分为肺脾气虚、脾肾阳虚、肝肾阴虚等,为病之本。邪实是指外感及水湿、湿热、瘀血及湿浊等病理产物,故为标。在小儿肾病的五个标证中,血瘀最为重要,瘀血是导致本病发病、缠绵难愈和促发病机恶性循环的重要病理因素。故血瘀是贯穿本病病程始终的关键病机。活血化瘀法正是切中小儿肾病的这一关键病机,通过消除瘀血,从而阻断病机恶性循环,使疾病痊愈并防止其转化为难治性肾病。故小儿肾病应突出血瘀病机,主张活血化瘀贯穿全程。临证曾数起沉疴,获取良效,逐步形成了自己从瘀论治小儿肾病的学术思想。
肾病属于中医学“水肿”范畴。《内经》对水肿的病因病机提出了“其本在肾”“其末在肺”“其制在脾”的重要论点。后代医家根据水和血的密切相关性,认为血与水二者是相互影响的,水肿可致血瘀,反过来,血瘀又可加重水肿。如《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曰:“血不利,则为水。”《诸病源候论·肿病诸候·诸肿候》言:“肿之所生也,皆由风邪寒热毒气,客于经络,使血涩不通,壅结皆成肿也。”《血证论》云:“又有瘀血流注,亦发肿胀者,乃血变成水之证。”“水火气血,固是对子,然亦互相维系。故水病则累血……瘀血化水,亦发水肿,是血病而兼水也。”“血结亦病水,水结亦病血。”
对于水肿的治法,《素问·汤液醪醴论》所举:“平治于权衡,去菀陈莝……以复其形,开鬼门,洁净府,精以时服。”诸多治疗方法中,“去菀陈莝”实际上已经蕴含活血化瘀之意。《仁斋直指方》正式提出活血化瘀法治疗水肿,并创立了桂苓汤等活血利水方剂。
肾病属本虚标实,正气虚弱为本,邪实蕴郁为标,属虚实夹杂之病证。正虚是指气虚、阳虚、阴虚或气阴两虚,结合脏腑又可分为肺脾气虚、脾肾阳虚、肝肾阴虚等,为病之本。邪实是指外感及水湿、湿热、瘀血及湿浊等病理产物,故为标。在肾病的发病与发展过程中,本虚与标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如正虚之本易感外邪,化热致瘀,而成标实之瘀;标实血瘀反过来又进一步耗伤脏腑之气,使正气更虚,并加重水湿、湿热,又成疾病之本,完成了“瘀”之标本转化,从而使瘀血表现出亦标亦本的特点。可见,瘀血既是贯穿于病程始终的病理产物,成为损伤人体正气的主要因素,同时又是进一步碍水阻气,使水肿形成,推动疾病发展的重要病理环节。
形成肾病血瘀的病因病理环节很多,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概括出以下几种:精不化气而化水,水停则气阻,气滞则血瘀;阳气虚衰,无力推动血液运行,血行瘀阻,或气不摄血,血从下溢,离经之血留而不去,或脾肾阳虚,失去温煦,日久寒凝血滞,均可导致血瘀;病久不愈,深而入络,致脉络瘀阻;阴虚生火,灼伤血络,血溢脉外,停于脏腑之间而成瘀;阴虚津亏,热盛血耗,使血液浓稠,流行不畅而致瘀;因虚或长期应用激素使卫外不固,易感外邪,外邪入侵,客于经络,使脉络不和、血涩不通,亦可成瘀。
标本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治则。治病求本,是指在疾病治疗时,必须寻求疾病的根本原因,并针对此进行治疗,为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一般情况下,要遵循“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但若病证复杂多变,出现标本主次之异,治疗上就应有先后缓急之变通,诚如《内经》所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若标本并重,则应标本同治。其实,“标”和“本”是相对的,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就肾病而言,瘀血不仅是正虚之本导致的“标”,反过来,此病理产物又损伤人体正气,并进一步碍水阻气,使水肿形成,形成病机的恶性循环,又成为治病之“本”,贯穿于肾病病程之始终。故从标本论治原则而言,活血化瘀法应得到重视,并贯穿于肾病治疗的始终。
肾病血瘀病机复杂,故遣方用药要谨守病机,做到法随证立、方随法转、机圆法活,正如《内经》所言“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鉴于此,临床常灵活运用理气活血、养阴活血、温阳活血、凉血散血四法,每收桴鼓之效。此外,鉴于肾病病机复杂,故常以本法结合他法应用,不可偏废。
肾病以水肿为主要表现,而水与血、气本不相离,水病可致血病,而血瘀亦可导致水肿。水肿可致气滞,而气滞则血瘀;反过来,血瘀又可致气滞,气化不利而加重水肿。可见,血气水三者是相互影响的,而血瘀可存在于肾病整个病程之中。另外,脾气虚则运化无力,水邪内停,气不摄血,血从下溢,亦可发为水肿、血尿。故气虚当用生黄芪、党参、太子参等以益气,气滞当用柴胡、郁金、枳壳以理气,另加丹参、当归、茜草、三七、蒲黄以活血化瘀。临证需要注意的是,若患者大便干多用太子参以补气养阴,大便稀选党参以益气健脾。且补益之药,多壅滞之弊,故少佐砂仁等行气之品,使其补而不滞。
肾病患者在发病中期,或在激素应用过程中,易出现热盛伤津、阴虚津亏、热盛血耗等病变,使血液浓稠,流行不畅而致瘀;或阴虚生火,灼伤血络,血溢脉外,停于脏腑之间而成瘀;故治疗当养阴活血,在丹参、当归、茜草、三七、蒲黄等活血化瘀药基础上加生地黄、麦冬、五味子、女贞子等以养阴。由于养阴药多为滋腻之品,易碍胃气,故应用时需注意脾胃功能,必要时酌加消导和胃之品,以资运化。
气虚日久,由脾及肾;或阴虚后期,由阴及阳;或在激素撤退过程中,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终致脾肾阳虚。阳气虚衰,无力推动血液运行,血行瘀阻,或脾肾阳虚,失去温煦,日久寒凝血滞,均可导致血瘀;故临证必须温阳活血,在丹参、当归、茜草、三七、蒲黄等活血化瘀药基础上加肉苁蓉、巴戟天、菟丝子等温阳之品。临床常根据皮质醇含量的测定来观察肾上腺功能,判断肾阳虚的程度,以加减温阳药的用量,此法仍值得进一步临床研究。
肾病患者感受热邪,或阴虚火旺,每易致热入血分,伤及血络,而致血瘀,治当清热解毒、凉血散瘀,正如叶天士言:“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常用水牛角、紫草、牡丹皮、生地黄、茜草、蒲黄、乌梅或五味子等。尤其需要说明的是,临证善用乌梅与水牛角同用,水牛角药性苦、寒,归心、肝经,功效清热凉血,解毒镇惊,治血热妄行之证,如《陆川本草》云“凉血、解毒……”;乌梅药性酸、涩、平,功擅收敛。二药合用,水牛角清热凉血以治“瘀”,而乌梅药性酸、涩,功擅敛以防“溢”,两者相得益彰,故效良。现代研究证明,乌梅性酸,降低了汤药的pH值,从而使水牛角在酸性环境中容易被吸收利用,且现代药理研究证实乌梅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及对非特异性刺激的防御能力,二者皆有抗过敏作用,应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
现代研究认为:肾病综合征血液高凝态与凝血酶原降低、辅助因子Ⅴ和Ⅶ显著增高、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增高、抗凝血酶Ⅲ水平和抗纤维蛋白酶活性降低、血小板增多、血小板凝聚增强、β-血栓球蛋白增高等有关。此外,肾病水肿时的低血容量、血液浓缩、血流缓慢、高脂血症及使用激素等,均可促使血液黏度增高,加重肾病高凝状态。高凝状态常常是作为一个恶性因素促使原发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又易反复引起肾内凝血,促进肾小球硬化,损害肾小球功能,导致肾功能衰竭,不仅增加了治疗难度,严重者甚至可危及生命。目前公认的观点是把高凝状态归属于“血瘀证”范畴,1986年中医肾脏病会议已将血液流变学指标中的全血黏度、血浆黏度增高作为“血瘀”的诊断标准之一。故血瘀证在肾病病理中有着重要地位。
临床及实验研究表明,中药活血化瘀可以阻断肾脏的病理损害,促进肾小球损伤修复,进一步改善肾功能,延缓病情进展。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活血化瘀药对降低补体活性,阻止纤维蛋白形成,稳定血小板活性,具有一定的效用,且活血化瘀药能改善微循环,改变毛细血管通透性及增强吞噬细胞功能恢复,抑制结缔组织代谢,从而促进纤维性病变的转化和吸收,对肾病治疗有很大价值。李红叶等采用破血逐瘀的水蛭治疗肾病高黏滞血症,无论单纯性肾病或肾炎性肾病,其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及水肿、蛋白尿的恢复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P <0.01)。朱辟疆用活血化瘀之蛇莲合剂(蛇毒、半枝莲、干地黄、生地黄、黄芪、丹参、川芎、红花、当归、川牛膝、京三棱、焦白术、陈皮、甘草)治疗肾病有高黏滞血症者,总有效率为84.4%,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此外,国内许多报道均显示,丹参注射液、复方丹参注射液、保肾康等中成药,对改善肾病时的高黏滞血症均有肯定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