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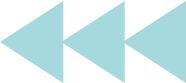
我认为区分四种社会形态是有意义的,它们是:原始社会(die vorhochkulturelle Gesellschaft)、传统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原始社会之外,其余都是阶级社会(这里,我把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称作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因为生产资料控制在政治精英手里):

考察晚期资本主义阶级社会或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的危机倾向,其目的是要揭示产生后现代社会的各种可能性。“后现代社会”不仅是尽管已经衰老但仍具有惊人活力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别称,而且也是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组织原则。 [1] 我想根据三种社会形态,来具体说明社会组织原则的含义,以及从这些组织原则中所能衍生出来的具体的危机类型。这些随意性的论述既不想冒充是社会进化理论,也不想取代社会进化理论;而只是想从经验层面上引入一个概念。对于每一种社会形态,我都将描述一下其中主要的组织原则,指出这种组织原则为社会进化所提供的可能性,并对其中所容纳的危机类型加以推论。如果不依靠一种社会进化理论,就不能从抽象的角度把握住组织原则,而只能依据不同发展阶段所具有的功能优先性的制度领域(诸如亲缘系统、政治系统以及经济系统),来简单地加以归纳和说明这些组织原则。
年龄和性别等原始角色是原始社会的组织原则。
[2]
其制度核心是亲缘系统(Verwandtschaftssystem)。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亲缘系统表现为一种总体性制度。家庭结构决定了整个社会的交往;家庭结构同时也保障了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世界观和规范几乎还没有分化开来。它们都是围绕着礼仪和禁忌而建立起来的,不需要单独加以认可。这种组织原则仅仅和家庭道德和部落道德联系在一起:凡是逾越亲缘系统的社会关系,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都不可能存在。在按照亲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生产力不能依靠剥削劳动力(通过强迫而提高剥削程度)来获得发展。学习机制被纳入工具行为的功能范围,在漫长的时间内,所带来的只是一些看起来很有序,实际上并不重要的革新。
[3]
在原始社会发展阶段上,似乎还没有任何有系统的动机促使人们去生产超出满足基本需求的产品,即使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允许生产剩余也是如此。
[4]
由于这种组织原则不会产生任何矛盾的要求,因此,外在的变化就可以打破这种按照亲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所具有的有效的控制能力,并摧毁家庭认同和部落认同。产生外在变化的原因通常包括:人口的增长以及相关的生态因素,特别是由于交换、战争和征服而带来的种族间的依赖关系。

传统社会形态的组织原则是具有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Klassenherrschaft)。随着官僚制统治机器的出现,从亲缘系统中分化出一个控制中心。这就使得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从家庭组织形式转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亲缘系统不再是整个系统的制度核心。它把权力和控制的主要功能转让给国家。这是功能专门化和分化的开端。在这个分化过程中,家庭丧失其全部的经济功能和某些社会化功能。在这一进入文明时期的发展阶段上,主要是为系统整合或社会整合服务的亚系统兴起了。在它们的交叉点上,法律秩序调节着生产资料的支配特权和权力的行使策略,而这种法律秩序本身则需要加以合法化。以统治机器和法律秩序为一方,以虚拟论证和道德系统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发生了分化,与这种分化相对应的是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制度分离。这种新的组织原则使得系统自律有了显著的加强;其前提是功能分化,并促使形成一般的媒介(金钱和权力)以及反思机制(成文法)。但是,控制能力的这种增长是以一种根本不稳定的阶级结构为代价的。
 在阶级社会里,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一起制度化的还有一种权力关系,长此下去,这种权力关系会对社会整合构成威胁。因为阶级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冲突。当然,在一个合法的统治秩序中,利益冲突可能是潜在的,并暂时被整合起来。这正是能够提供合法性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成就:它们把规范结构的虚拟的有效性要求同公共议论和共同检验的领域脱离开来。生产关系直接具有了政治形式,也就是说,经济关系由合法权力来加以调节。通过求助于传统的世界观和常规的国家伦理,统治秩序得到了维护。
在阶级社会里,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一起制度化的还有一种权力关系,长此下去,这种权力关系会对社会整合构成威胁。因为阶级关系中的利益冲突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冲突。当然,在一个合法的统治秩序中,利益冲突可能是潜在的,并暂时被整合起来。这正是能够提供合法性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成就:它们把规范结构的虚拟的有效性要求同公共议论和共同检验的领域脱离开来。生产关系直接具有了政治形式,也就是说,经济关系由合法权力来加以调节。通过求助于传统的世界观和常规的国家伦理,统治秩序得到了维护。
尽管垂直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新的组织原则却还是用非政治的交换关系(地区性市场、城邦国家)把水平层面上的社会化保持在狭窄的范围内。政治上的阶级统治要求用国家伦理来代替部落道德,但这种国家伦理还是依赖于传统,也就是说,还是具有抵御特征;因此,这样的阶级统治无法容纳普遍性的交往形式。在社会劳动的阶级系统中,随着剥削程度的提高,也就是说,通过有组织的强制性劳动,生产力可以获得发展,这样就出现了社会剩余产品,它们被享有特权的人所占有。由于技术创新始终是自发的(技术上可以利用的知识没有通过反思性的学习而获得发展),因此,生产力的提高无论如何都是有其限度的。
传统社会中的危机类型源于社会内部的矛盾。而矛盾存在于规范系统和论证系统的有效性要求与阶级结构之间;前者不允许公开进行剥削,后者则使依靠特权占有社会财富成为一种通则。如何不是平均而是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这个问题可以用意识形态对于虚拟的有效性要求的保障暂时加以解决。在遭到批判的时候,传统社会通过强化对劳动力的剥削而扩大其控制范围。也就是说,传统社会不是直接通过加强体罚力度(刑法史上有许多例子说明了这一点)来提高自己的权力,就是间接通过强制实施普遍税捐(如劳役、实物或货币)来提高自己的权力。因此,危机通常是由于控制问题导致的。控制问题迫使系统通过加强压迫来增强自己的自律;而这又导致了合法性的丧失,进而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通常是和外部冲突联系在一起的);阶级斗争最终危及社会整合,并且可能导致政治系统的颠覆和新的合法性基础的建立,即导致一种新的集体认同。
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是资产阶级民法体系中所确定的雇佣劳动(Lohnarbeit)与资本(Kapital)之间的关系。由于出现了私人商品所有者摆脱国家束缚的商业领域,也就是说,由于在拥有一定疆域的国家中,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等获得了制度化,由于世界贸易体系的建立,因此,“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也就从政治经济系统中分化了出来。 [5] 这意味着阶级关系的非政治化和阶级统治的匿名化。国家和用政治手段建立起来的社会劳动系统不再是整个系统的制度核心。相反,现代赋税国家(Steuerstaat)——韦伯分析了这种国家的原型 [6] ——变成了自我调节的市场流通体系的一个补充结构。 [7] 对外,国家依然用政治手段来确保领土的完整和国内经济的竞争秩序。但对内,原来处于支配地位的控制手段,即合法权力,现在主要是用于维持一般的生产条件,从而使由市场调节的资本能够顺利运行。经济交换变成主要的控制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国家主权在社会系统内部的运作就会局限于:
(1)按照民法保护资产阶级的交换(警察和司法);
(2)保护市场机制,消除其自我破坏的副作用(比如劳动保护法);
(3)满足整个经济的生产前提(公共教育、交通和运输);
(4)使民法体系适应资本积累过程的需要(税法、银行法和商业法)。 [8]
通过完成这四项任务,国家确保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发展前提。虽然在传统社会中,系统整合领域和社会整合领域之间已经开始制度分化,但经济系统依然依赖社会文化系统向它输送合法性。只有在经济系统从政治系统中获得相对独立以后,市民社会中才会出现一个摆脱传统束缚,并且纵容市场参与者倾向于策略功利主义行为的领域。相互竞争的企业家们依据竞争获利原则来作出决策,因此他们用利益导向行为(interessengeleitetes Handeln)取代了价值取向行为(wertorientiertes Handeln)。

这种新的组织原则为生产力的解放和规范结构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根据资本自我运行的要求,生产方式推动了一种扩大再生产。这种扩大再生产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机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对体力的剥削,即提高绝对剩余价值达到了极限,为了积累资本就需要发展技术生产力,并在发展过程中把技术上可以利用的知识和反思性的学习过程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已经获得自律的经济交换也减轻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压力。自我调节的市场流通体系需要其他方面的补充,这不仅包括合理的国家行政体系和抽象的法律体系,而且也包括社会劳动领域中具有策略功利主义特征的道德体系;在私人领域中,这种道德体系和新教伦理以及形式主义伦理是融合在一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可以具有普遍主义的结构,并且呼吁普遍化的利益,因为所有制秩序已经抛弃了政治形式,转变为一种似乎能够使自身合法化的生产关系。市场制度可以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公平原则上。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法治国家同样也可以在这种合法的生产关系当中找到替自己辩护的理由。这就是洛克(John Locke)以来理性自然法的核心内容。生产关系可以和似乎“授命于天”的传统统治秩序脱离开来。
当然,价值形式的社会整合作用也只能限于资产阶级。新兴的城市无产者主要来自农民。他们的忠诚和服从更多的是靠传统主义的束缚、听天由命的顺应心理以及缺乏远见和赤裸裸的压制等因素来共同维持的,而不是依靠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信服。但是,这并没有削弱这种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意义, [9] 这是一个不再承认个人政治统治的社会。因为,随着阶级统治在政治上的匿名化,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统治阶级必须认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具有统治地位。普遍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要想完成这一使命,就必须:
(1)科学地建立在传统批判的基础上;
(2)具有一种模式特征,也就是说,能够预设一种社会状况,其可能性从一开始就不会被能动发展的经济社会所否定。
可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市民社会必须对观念与现实之间明显存在的矛盾作出反应。因此,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主要也就表现为:把观念与现实加以对照,以此来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还是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就。它不仅解放了经济系统,使之摆脱了政治系统,摆脱了社会整合的亚系统的束缚,而且使经济系统在完成系统整合任务的同时,为社会整合作出了贡献。由于这些成就,当控制问题直接威胁到认同的时候,社会系统面临危机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了。我所说的就是这个意义上的“系统危机”(Systemkrise)。
由于经济发展处于自发状态(naturwuchsig),因此,社会组织原则不会束缚生产力的解放。同样,规范结构也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因为这种新型的组织原则在历史上第一次容纳了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但是,这种组织原则和交往伦理学(kommunikative Ethik)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交往伦理学不仅要求规范具有普遍性,而且要求通过话语来对规范利益的普遍性达成共识。这种组织原则把阶级矛盾的潜在冲突转移到了控制层面上,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表现为:繁荣、危机和萧条不断交替。建立在雇佣劳动和资本关系当中的利益冲突并没有直接表现为阶级冲突,而是表现为积累过程的中断,也就是说,表现为控制问题。从这种经济危机的逻辑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系统危机概念。
表3概括了上文扼要介绍的组织原则与相应的危机类型之间的关系。
表3

组织原则把可能进化的空间确定在三个发展纬度(生产、控制、社会化)上,因此也就同时决定了以下三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如果发生,那么:
(1)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在功能上如何分化;
(2)系统整合受到威胁的时候,何时才能危及到社会整合,也就是说,何时才能导致危机;
(3)控制问题怎样才能转变为对认同的威胁,也就是说,何种类型的危机占据支配地位。
[1] 贝尔(D.Bell):“后工业社会:一种观念的演变”(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The Evolution of an Idea),载《眺望》( Survey ),1971,第102页及以下诸页。
[2] 帕森斯(T.Parsons):“社会”(Societies),载《进化视角与比较视角》( Evolutionary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Englewood Cliffs,1966;伦斯基(G.Lenski):《权力与特权》( Power and Privilege ),New York,1966;萨林斯(M.Sahlins):《生存,进化与文化》( Service , Evolution and Culture ),Ann Arbor,1968;其余文献请参阅埃德:《社会进化的机制》。
[3] 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野性思维》( Das Wilde Denken ),Frankfurt,1968;萨林斯:《石器时代的经济学》( Stone Age Economics ),Chicago,1972。
[4] 卡奈罗(R.L.Caneiro):“论国家的起源”(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载《科学》( Science ),1970,第733页及以下诸页。
[5] 请参阅里德尔(M.Riedel)对这个概念历史的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研究》( Studien zu Hegels Rechts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1969;《黑格尔论市民社会与国家》(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und Staat bei Hegel ),Neuwied,1970。
[6] 韦伯(Max Weber):《经济与社会》(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Köln,1956,第1034页及以下诸页。
[7] 请参阅卢曼:“短缺、货币与市民社会”(Knappheit,Geld und 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载《社会科学年鉴》( 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1972,第186页及以下诸页。
[8] 这种理论模式是用来描述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的极点。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的系统描述,请参阅多布(M.Dobb):《资本主义发展论》(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London,1947。
[9] 布鲁纳(O.Brunner):“意识形态时代”(Das Zeitalter der Ideologien),载:《社会史的新路线》( Neue Wege zur Sozialgeschichte ),Göttingen,1956;伦克(K.Lenk)编:《意识形态》( Ideologie ),Neuwied,1961。